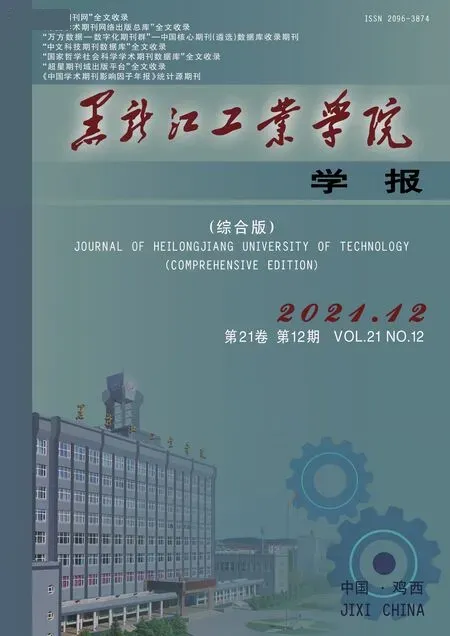马克·本德尔《苗族史诗》英译本的民族志式深度翻译研究
吴 斐,陈 卉
(湖南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4)
《苗族史诗》是中华民族经典的优秀文化作品,它又被称之为“苗族古歌”和“古史歌”,是一种活态口传民族文学,它以问答式的盘歌体,演绎着古老的文化,其蕴含的文化符号铸就了苗族独特的文化世界[1]。广义的苗族史诗包括日常叙事史诗苗族古歌和近年才挖掘出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本研究所探讨的是苗族古歌。此外,苗族是具有全球知名度的跨境民族,中国苗文化近年来也成为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研究的热点。怎样向世界完整真实地展示苗族文化,尤其是利用史诗典籍讲好中国苗族故事,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然而,目前国内外对其译介传播研究显得较为滞后,截至2021年7月,笔者在中国知网等学术期刊网进行检索,发现相关论文仅97篇,研究略显不足。另一方面,《苗族史诗》本身晦涩难懂,其海外译介传播工作是一项跨时空、跨文化的活动,对于传播主体而言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亟待理论创新,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去审视《苗族史诗》译介工作,破解文本之外的制约因素。近年来,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人类学视野下的民族志深度翻译方法备受关注,它也由此开辟了《苗族史诗》译介研究的新范式。本研究在回顾苗族文化及《苗族史诗》海外译介现状,阐述民族志式深度翻译理论基础上,将以马克·本德尔领衔翻译的《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为蓝本,探索民族志式深度翻译模式,提升译介效果,从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好文化自信精神的实践探索。
一、《苗族史诗》译介概述
了解《苗族史诗》海外传播历史与现状,首先需要回顾我国苗族文化对外译介传播概况。中国苗族文化是世界知名度较高的民族文化,它走向西方世界始于19世纪,当时西方国家传教士已踏足黔东南和湘西等苗族聚居区,并在无形中充当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而让苗族文化真正走上世界舞台,为世人所熟知归功于沈从文作品在西方世界的译介,其英译本向西方读者完整地展现了湘西苗族民俗与文化。由中西合璧翻译搭档杨宪益、戴乃迭所译的《湘西散记》,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译林出版社联合出版,一经出版就在国外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2009年,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出版了汉学家金介甫翻译的《边城》,进一步将苗族文化成功地推向世界。然而,由于《苗族史诗》的发掘和整理较晚,相对《边城》等苗族文学作品外译传播,《苗族史诗》海外传播理论与实践工作显得滞后。虽然《苗族史诗》流传了数千年,其历史文化价值完全可以与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媲美,但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较小。幸运的是,我国人类学界、文化学界和译介出版传播界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努力将其推介至国际学术圈。
20世纪50年代前,尽管《苗族史诗》广泛地流传于民间,但却缺乏系统性。仅1896年左右,英国传教士零星地整理并翻译了《开天辟地》《洪水滔天》等作品。抗战时期,随着大学西迁,一些民族学学者在本地进行田野考察过程中对《兄妹结婚》等史诗进行了关注,并进行了记载,但仍然不成体系。真正意义上的系统性挖掘和整理工作始于1952年,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研究团队,在马学良教授率领下,深入黔东南地区进行苗语调查,搜集了大量的苗族文学,顺便挖掘了不少苗族活态史诗,在贵州省文联的支持下,1979年编译出了不少版本的汉语译本,如《枫木歌》《跋山涉水歌》等。1983年,马学良和今旦合作编译了汉语版《苗族史诗》,为后来的《苗族史诗》英译传播奠定了基础。2006年,美国汉学家马克·本尔德以此为蓝本,将其翻译成英语版《蝴蝶妈妈》(ButterflyMother),并在美国出版传播。2012年9月,马克·本德尔与吴一方、葛融合作翻译完成了完整版本《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该书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发行,一经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它获得当年贵州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2012年11月,在史诗研究国际峰会上被学者誉为“跨国合作的经典文本”。《苗族史诗》英译的成功,离不开马克·本德尔等译者对民族志式深度翻译策略的灵活运用,并由此被视为民族典籍翻译成功的典范。
二、民族志式深度翻译的概念与内涵
首先需要厘清深度翻译的概念及理论发展脉络。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在1993年提出了深度翻译概念。关于什么是深度翻译,国内外译论者众说纷纭。但核心观点大同小异,即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通过序言、注释、评论、后记等形式,将译本最大限度地置身于原汁原味的语言与文化情景中,从而再现源文化和原作者表达意图。从内涵来看,阿皮亚所提出的“深度翻译”有三个维度:首先,它适用的领域或提出的文本是基于文学范畴的翻译;其次,必须和学术息息相关;最后,指出在理念和方法上,它通过附加评注的方式将译文融入原汁原味的源文化环境中。该理论曾名噪一时。世界著名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把这篇论文收录到知名度高的《翻译研究读本》,供全球翻译界同行参考。2003年,英国翻译理论家西奥·赫尔曼斯另辟蹊径,从跨文化视角来解读深度翻译模式和方法,认为该模式适用于多元文化词汇转换和翻译。沙特尔沃思和莫伊拉考伊(Shuttleworth & Cowie)则认为,尽管阿皮亚的深度翻译观起源于非洲谚语英译,显而易见也适用于包含大量文化元素的翻译文本,无论是以脚注、术语词汇表还是扩展介绍的形式,提供如此大量背景信息的目的是使读者对源文化产生更深刻的尊重,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思想行为方式被深刻理解。以上学者对深度翻译的原因、方法、目的、本质、社会政治意义等做了阐释。由此可见,“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得到了国外翻译界人士的普遍认可。
该理论与我国社会语境及翻译理论实践也存在诸多契合。新世纪以来,深度翻译引入中国后,在国内开始蓬勃发展。大多数是理论方面的研究,也有少量涉及指导翻译实践的。国内代表性研究者有张佩瑶[2]、段峰[3]、蓝红军[4]等。张佩瑶是国内较早引入“Thick Translation”的学者,认为该模式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实现文化重现,她也是该理论的身体力行者,其所编译的《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等专著中,都能看到“丰厚翻译”(深度翻译)的身影。蓝红军则认为与其说“Thick Translation”是一种翻译理论,还不如说是译者所采用的一种文化处理策略,其充分利用前言、脚注、译论和附录等手段,拓宽了诠释的可行性。
民族志式深度翻译是深度翻译理论和民族文化翻译结合起来的产物,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深度翻译理论在民族文化典籍翻译中的应用方法与实践。我国相关代表人物有段峰、王宏印、龙吉星等[5]。段峰在《深度描写、新历史主义及深度翻译——文化人类学视阈中的翻译研究》一文中提出了民族志深度翻译的概念,首次把深度翻译应用于民族文化翻译[3]。王治国认为民族志式深度翻译应当遵循以下步骤:首先是将本土内容口译成本民族志书写的语言;然后再将其改编成书面文本,在融于主流文化的同时保持其独特性。笔者认为,民族志式深度翻译,是将文化人类学相关理论嫁接到翻译领域,主张采用民族志书写的深度描写法和主客位关系来探讨翻译。民族志式深度翻译起步较晚,明确提出该范式的研究不多。在国外相对应的是“translation and anthropology”研究,他们关注人类学和翻译的关系,如Borgatti&Li、Barker等[6]。并将民族学深描的方法应用于翻译研究,探讨了深译法,如Hermans、Cheung、Sturge等[7]。由此可见,相关研究已经兴起,但尚未成熟。
从深度翻译理论内涵和发展历程来看,它对促进中国文化典籍发展,尤其是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也是由典籍自身的文本特点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典籍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对其进行编译必然涉及特有的语言和文化元素,它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而且是跨越时空的对话,以上因素使典籍翻译过程举步维艰。借助“深度翻译”所编织的“文化网”,为跨越以上障碍提供了可能性,它能让目的语读者通过译文之外与译文之内的厚语境来精准解读原文,最大限度地避免文化误读,让障碍重重的典籍翻译柳暗花明又一村。
三、马克·本德尔《苗族史诗》英译本的民族志式深度翻译阐释
本部分将从英译的民族志取向及民族志式深度翻译分析来揭示马克·本德尔《苗族史诗》译本成功的秘诀,从而为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译介与传播工作提供借鉴。
1.马克·本德尔《苗族史诗》英译的民族志取向
《苗族史诗》承载着苗族文化基因,它已经由过去的口头传承转向书面文本阶段,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和多元文化兴起,《苗族史诗》英译与传播工作如火如荼,其英译本具有民族志表征。以翻译为桥梁,马克·本德尔等译者将这一瑰宝级别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到英语读者面前,不仅仅是跨文化翻译的过程,更是一个民族志的书写过程,为了更好地进行跨文化阐释,让英语读者更好地理解《苗族史诗》英译本的苗族文化,译者进行了丰富的田野工作。马克·本德尔是汉学家,也是人类学家、翻译家与民族艺术研究者,他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国外的传播贡献很大。1985年他即开始《苗族史诗》英文版翻译工作,基于广泛的田野考察,深入了解苗族的历史渊源,虚心向今旦等专家请教。最可贵的是,作为美国表演理论研究的研究者之一,马克·本德尔提出把史诗的创作者、传承者、接受者置于一个立体的三维空间中进行宏观的综合考察,同时兼顾口传文学翻译中众多因素的各自作用和地位,从多维层面保存史诗民族志文化语境[8]。马克·本德尔认为,除了传统枯燥的文字翻译方式,史诗可以通过表演的形式重新被演绎,或是在新的语境下前行,抑或将这种传统持续保留于苗族生活中,这都是民族志式深度翻译的理念。将上述民族志方法融入翻译过程,使《苗族史诗》英译本成为了民族志式深度翻译的优秀样本。
2.《苗族史诗》民族志式深度翻译分析
深度翻译是《苗族史诗》译本最典型的特征,译本呈现明显的厚语境化。在现存的中国文化典籍译本中,马克·本德尔等人合译的《苗族史诗》(苗汉英版本)在深度翻译方面体现得更明显和透彻,具体表现为文化层面和语言特征层面的深度诠释,而在形式上分为译文内深度翻译及译文外深度翻译。
(1)译文外深度翻译
译文外深度翻译,包括献词、序言、前言、导论、后记、索引、术语表、插图、附录、封底推荐词等形式[9]。序言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有利于海外读者总览原文框架,汲取全文精华,迅速导入主题。绝大多数海外读者对苗族史诗不甚了解,故,苗汉部分编撰者吴一文特意撰写了27页的代序,名为:Aral Texts and Hmong Sprit:A disucssion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Hmong epic,(as preface)浓墨重彩,娓娓道来,将这一鸿篇巨制的来龙去脉描述得异常清晰。第二部分是马克·本德尔的preface to English translation,主体译者马克·本德尔分享了翻译历程,值得赞叹的是,他非常注意细节,锱铢必较,一丝不苟。“苗族”开始被译作“Miao”,但考虑到苗族遍布全球,大部分海外苗族并不精通汉语,为此改用了“Hmong”,更有助于译本的海外传播。第三部分的prelude(序歌)部分有马克·本德尔所写的长达2万多字的苗族及苗族古歌的介绍。为了最大限度地缩小东西方文化鸿沟,丰富海外读者的文化图式。《苗族史诗》每一部分都用序言的形式将苗族文化进行了生动地演绎,将苗族传统文化、家庭结构、红白喜事、风俗和宗教信仰等交代得非常清晰。尤其是在“史诗及其演唱方式”部分,马克·本德尔先对每部分史诗的内容进行了简介,然后简单阐述了苗语的语言特征;从语音来看,苗语和汉语一样具有声调,但苗语更复杂,多达8个声调。为此,马克·本德尔专门开辟了“Key to Pronunciation for Eastern Miao Dialect Romanization”进行了列举。此外,苗文语法和英语、汉语具有明显的区别,马克·本德尔也进行了简单介绍。苗族史诗的演唱形式也是独具特色,演唱者盘腿坐在长板凳上,观众呈圆形分布,据说一篇宏大的史诗演唱完毕耗时数十天。以上译者都有所交代,该深度翻译策略让读者实现了先入为主的效果。
再者,每组史诗前有题解为读者提供导读,如《古枫书》导读开篇简单介绍了种子之屋、寻找树种、梨耙大地等概念,这些是苗族先民对自然的认识。另外,66幅和文字对应的彩图相得益彰,活灵活现地再现了史诗所处的文化情境,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些都加深了海外目的语读者对苗文化的理解。
(2)译文内深度翻译
译文内深度翻译,包括文内隐注、括号内加注、双行小注、脚注、段后评注、尾注等形式。苗汉英三语版《苗族史诗》各类注释多达3000多条,涉及人物注解、古今地名考注、古语词解释、动植物注解、句子解意、段意解读、异文对比等内容。如在《制天造地》(CreatingHeavenandEarth)一节中,译注者对其中出现的“五倍子”使用了深描法,其英译本如下:The Hmong language for this line is“Ghab nix pab nil nangl”. It refers to various types of leaves, cogon grass roots, and gallnut of the Chinese gallnut…
对于史诗中存在的文化事象缺失的现象,马克·本德尔也采用了译文内加注的民族志深度翻译策略。亲属称谓语折射了不同文化的婚姻制度,英语国家亲属称谓语最简单,如“cousin”一词就足以涵盖所有同辈分的堂亲和表亲,汉语相对复杂,苗语则更加细化。汉语中的姐夫和妹夫在英语里面统统被表述为“brother-in-law”,而在苗语中,男性和女性称呼姐夫和妹夫的用词不同。英语中的“brother”和汉语中的“兄弟”一般用于同辈同宗男性,而苗语连襟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仍然称之为兄弟。《寻找祭服》这一部分描述了姜央的九个姐夫在祭祀过程中的职责,其中一段描写了在汉族姐夫家受到热情款待的事件。为了让读者清晰地掌握里面涉及的各种亲属称谓,译者颇费心机,在直译原文基础上,对“brother”进行了加注:According to Miao custom,sister’s husbands call each other brothers.Three of JangxVangb’s sisters married Han people and he thus had three Han brother-in-laws.
除了意译加注外,译者还采用了同类置换加尾注的形式,《铸日造月》(CreatingtheSunsandMoons)部分以十二地支来给十二个太阳和十二个月亮进行命名,尽管西方国家对苗语的十二地支比较陌生,但汉族的十二生肖早已家喻户晓,为了帮助目的语读者加强理解,译者用十二生肖代替十二地支,且用尾注的形式进行说明:The Earthly Branches (dizhi in Han) are part of an ancient Chinese system used to calculate time based on the twelve year orbit of the planet Jupiter…
为了传达更佳译介效果,除了同类置换,异类代偿也是文化层面常用的深度翻译模式。在形式上,《铸日造月》部分尾注和增译同时使用,“老大的名字叫做子”这节标题的译文如下:“the first was called said,the rat Earthly Branch”,苗文“said”原封不动,“the rat Earthly Branch”则为增补的同位语,在此起阐释说明的作用。同理,在《洪水滔天》部分,“一副芦笙剩一根,人手一份也难分”中的芦笙被译为“gix pipe”,其中苗语芦笙的“gix”得以保存,而“pipe”既表明了芦笙乐器的种属,又生动再现了苗族演唱场景。
以上将文化人类学深度描写法嫁接到翻译实践当中,依托形式多样的注解,译者可以补偿翻译过程中较为棘手的文化空缺现象。纵观《苗族史诗》译本,类似的译注数不胜数,旨在帮助海外目的语读者理解和鉴赏文化经典,恰到好处地解决了史诗中所蕴含的文化缺失和文化相异等问题,而部分诗歌韵律特色也得以保存,再现了翻译美。总之,丰富的注释和译文相辅相成,使其在目的语国家读者面前重现了原文所描述的古老而神秘的苗族文化画卷,起到了最佳传播效果。
结语
《苗族史诗》作为苗族最古老的口头语言艺术形式,具有较高的文化传承价值[10]。译者通过多种深度翻译策略的综合运用,重新演绎和再现了源语丰富的文化语境。诚然,深度翻译会因为大量的注释和冗长的序言使译本过于繁琐,降低可读性,但瑕不掩瑜[11],对于民族典籍翻译而言,深度翻译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翻译策略,该译本所采用的人类学民族志阐释方法,使这部晦涩难懂的民族典籍由学术殿堂走向海外普通读者[12]。亦对其它典籍英译具有启示的作用,将改善当前我国文化典籍翻译文本质量,提升整体译介效果,让文化真正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