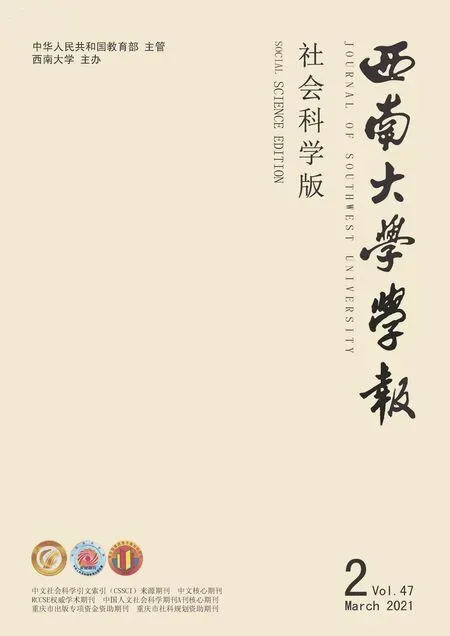政产学共同体制度链及其形态跃升
——地方本科院校向新型本科院校三种性质的跨越
徐 斯 雄,田 联 进,2
(宜宾学院 1.教育学部,2.高等教育研究所,四川 宜宾 644000)
全球经济、科技和教育正处于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紧要关头,而作为国家创新子系统的政产学共同体理应在大变局中对实现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促使中国经济从原来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及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等发挥动力作用。在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当下,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本科院校更需要以合作、结盟的姿态——政产学共同体的形式实现转型发展和创新发展。基于此,地方本科院校走政产学共同体发展道路,旨在促进政产学三方合作发展和创新发展,并且只要在政产学共同体合作的理论上解决合作创新的可持续性、稳定性和动力性问题,就能在实践上实现政产学共同体三方的共赢效应。因此,政产学共同体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并加以推广的创新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新型本科院校是新时代具有创新性的一类地方本科院校融入区域、扎根地方、服务社会,并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从而形成特色和优势的一类新型应用型大学。在新时代社会转型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趋势的大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只有主动联接融通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等组织,形成多方合作、协同创新的政产学共同体,并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前沿和应用型科研作后盾,形成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高地和科研高地,才能迈向新型本科院校行列。
政产学共同体是政府、企业和高校等实现产学研融合的共同性群体,是各方主体在资源、技术等方面实现对接耦合的创新性组织,由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赫曼·施纳德教授在1906年最早提出。从高校视角而言,政产学共同体就是高校因吸收政府、企业或行业等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全过程的一种协同合作的创新性组织。
地方本科院校向新型本科院校迈进的关键标志在于是否形成了政产学共同体的合作形态,是否走上了政产学共同体的服务形态,是否迈向了政产学共同体的引领形态,此三者标志着地方本科院校向新型本科院校三种性质的跨越:第一,政产学共同体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整合高校与行业企业、政府优质资源,推动课堂教学改革,搭建多形态的教育训练和科研训练环境,凝聚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合力,旨在提升应用型人才质量和应用型科研水平,形成了政产学共同体的合作形态,地方本科院校在多形态教育训练和科研训练方面无法与新型本科院校相提并论;第二,政产学共同体以应用型人才和应用型科研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势,构成政产学共同体的服务形态,地方本科院校在服务当地社会经济方面与新型本科院校无法比拟;第三,政产学共同体的引领形态体现产教研融合、互利共赢、引领发展的优势,既可减少企业改革的创新成本,也可促进社会转型升级的进程,地方本科院校在融合、共赢与引领发展上远远不及新型本科院校。因而,政产学共同体具有由初级向高级逐渐跃迁的合作形态、服务形态和引领形态,其形态跃升的实质是地方本科院校向新型本科院校发展的过程。由于政产学共同体是松散的机构,涉及各方利益问题,所以政产学共同体形成成熟的正常组织需要形成连续性制度链为其保驾护航。
二、政产学共同体运行的规矩准绳:连续性制度链
政产学共同体是由政府、企业和高校等组成的松散组织,只有创建政产学共同体运行的连续性制度链才能确保政产学共同体各方主体按照其意愿行事,政产学共同体才拥有规矩准绳。所以,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政产学共同体只有契合在连续性制度链上运行,才能走向协同育人创新、科研协同创新、促进社会转型和升级创新。
政产学共同体的目的在于实现以高校为供给侧主体,以企业为需求侧主体,以政府为调控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政产学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然而,政产学共同体的本质仍然是一种知识生产活动,知识的外溢性特征会引发知识市场失灵,而且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出发点往往存在差异,会造成政产学共同体系统的不稳定,难以实现共赢[1]。当然,个人能够在政产学共同体的早期发挥作用,个人信任、个人魅力及个人关系能够维持政产学共同体一段时间运行,但是通过个人而运行的政产学共同体很难长期化和固定化。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难以避免由于个人引起的“逆向选择”和“败德行为”[2],这些将直接影响政产学共同体各方合作的持久性。并且,政产学共同体各方具有的“潜在对立的组织文化和行为准则”[3]影响各方合作的意愿和热情。因而,能够将政产学共同体各方意愿联结在一起的连续性制度链是政产学共同体长期合作的根本保障。只有从制度链方面给予连续性支持,营造良好的外部协同创新环境,政产学共同体才能长期持久运行。任何组织行为定势的形成都需要制定相应的决策制度、管理制度和评价考核制度。所以,政产学共同体需要以决策、管理、评价考核组成的连续性制度链,共同促进各方主体走向协同合作,并实现协同创新。
(一)决策制度链:政产学共同体运行的指引性力量
决策制度链决定政产学共同体如何前行,构成政产学共同体运行的指引性力量。从美国的政产学共同体发展历史来看,1862年美国旨在促进农业技术与教育发展的《莫里尔法案》催生了政产学共同体的萌芽,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引导下由大学、军工、企业共同参与的“曼哈顿工程”“雷达研制”等项目都是政产学共同体的杰作,政产学共同体给美国国家、大学、企业及军界等带来的利益多赢促使了被誉为科学圣经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又称《布什报告》)的诞生,而1950年美国国会成功通过相关法案成立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一直扮演着国家层面的决策作用。美国政产学共同体决策制度链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及第三方非官方组织制定,主要包括倡导性、资助性、规范性及赋能性的政策制度链:倡导性决策制度链起公共咨询作用,并对政产学协同创新的效益进行评估;资助性政策制度链以科研项目形式进行资助,具有竞争性;规范性政策制度链对研究、竞争、成果等进行规范,如《美国法典》第35编第18章就明确指出:国会的政策和目标是利用专利制度促进联邦支持的研究或开发所产生的发明的利用;鼓励小型企业最大限度地参与联邦政府支持的研发活动;促进商业机构与非营利组织(包括大学)之间的合作;确保非营利组织和小型企业的发明被用于促进自由竞争和企业发展,而又不会过度妨碍未来的研究和发现;确保政府获得联邦支持的发明的充分权利,以满足政府的需求[4]。赋能性政策制度链给予相应的制度红利,如美国联邦政府实施的赋税政策以激励产业界融入产学研进程。
德国亦非常重视校企合作,其双元制在决策制度链上以法律进行规范和完善。与美国不同的是,德国更强调企业的主体性,德国大学在政府引导下配合企业实施产学研的任务。显然,政产学共同体需要制定政府、产业、高校各方主体融入协同合作的决策制度链,决策制度链构成政产学共同体各方主体协同合作创新的灵魂力量,在于策动各方主体共同发挥作用:政府可以通过政策、资金、舆论等方式促进各方合作的信念和决心[5],发挥方向性和协调作用;高校可以通过制定应用型人才、应用型科研和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等优势的决策制度链加大各方合作吸引力,发挥人才中心主体和智力中心主体作用;企业可以通过制定提供实训平台、创造创业就业岗位及提供企业技术开发需求等决策制度链加大各方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发挥企业创业中心主体作用。因而,决策制度链就在于策动政产学共同体各方主体沿何种方向发展的总体态势。
(二)管理制度链:政产学共同体运行的规范性力量
决策制度链需要细化为管理制度链,管理制度链是政产学共同体运行的规范性力量。地方本科院校走政产学共同体发展道路,需要突破唯论文思维,以产研融合、应用型科研为价值导向;需要突破学术型人才思维,以产学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价值导向;需要突破“象牙塔”思维,以校地融合、服务国家和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为其价值站位。因而,高校需要将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社会地方经济发展有关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纳入管理制度链。
政产学共同体管理制度不仅仅包含高校师生的管理制度,而且还涉及政府、企业等各方主体及其种种合作模式的管理制度,因而,政产学共同体需要将各种合作模式或合作研究中心、资源要素、知识技术和人力要素纳入管理制度链中。政产学共同体的运行主要涉及各方主体合作、成果共享和利益分红,因而其管理制度链主要包括合作管理制度链、成果共享管理制度链和利益分红管理制度链。
政产学共同体合作管理制度链需要规定各方主体合作中的权利和义务,并对科研成果予以保护,以契约的形式维护各方科研成果的权益,以形成政产学共同体成员内共同遵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制定实现政产学共同体的近期目标及长远目标。政产学共同体各方主体是按照各自目标运行,且各方主体都具有对方需要的优质资源,而共享相应优质资源显然是政产学共同体各方主体的要求。政产学共同体共享管理制度链需要致力于优质人力资源、物力资源、成果资源及财力资源上着力:在优质人力资源中,学校需要将企业骨干力量纳入人才培养和科研的共享进程,政府及企业需要高校决策智囊、研究骨干为政府、企业共享,其共享以何样的经济利益实现回报需要考虑在相应的共享管理制度链中;在优质物力资源中,政产学共同体需要实现相互共享,物力资源折旧成本及共享回报都需要纳入共享管理制度链中;在成果资源及财力资源中,各方成果共享时如何体现成果的创造性,财力资源的投入如何实现回报都需要细化为具体的共享管理制度链中。利益分红管理制度链在于如何量化各方主体在实施产学研融合进程中所作出的效益或贡献,包括产生的政治效益、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教育效益等的量化,这需要以契约形式或各方达到一致的可操作性规则才能作为保障。显然,管理制度链是政产学共同体运行的根基所在。
(三)评价考核制度链:政产学共同体运行的驱动性力量
政产学共同体长久持续运行的关键还在于确保如何激励各方参与的热情及其利益如何分配,各方热情的激发及其利益的驱动需要衔接于相关的评价考核制度链中,评价考核制度链是政产学共同体运行的驱动力量。政产学共同体各方参与的热情及其利益往往来自评价考核制度链的驱动,其评价考核制度链需要结合具体的参与模式。
由于政产学共同体主要涉及各方主体如何合作、成果如何应用及各方主体如何共建,因而政产学共同体参与合作模式可以划分为合作参与模式、成果应用参与模式和共建参与模式,而这三种模式类似于政产学共同体的合作形态、服务形态和引领形态。所以,政产学共同体评价考核制度链必然需要基于高校作为供给侧的结构性主体,企业作为需求侧的投入性主体和政府作为调控端的政策性主体,规范三大参与模式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归属,并形成具有驱动力的评价考核制度链,政产学共同体就具有长期运行的驱动力。在合作参与模式中,政府和企业都作为合作参与的育人主体和科研主体,对于参与育人和科研的政府人员和企业人员,高校应以一定的经济酬劳作为回报,当然,对于参与政府政策规划及企业技术开发的高校教师,政府与企业应以一定的经济酬劳作为回报,而各种经济酬劳都需要细化到评价考核制度链中,以吸引各方主体积极性;在成果应用参与模式中,高校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服务主体,高校教师研究或开发的成果一旦被采用,投入方甚至高校需要支付一定的经济报酬,并进一步促进教师向应用型人才和应用型研究转型,高校主要以其应用型人才和应用型成果服务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应用参与模式主要体现高校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评价考核制度链;在共建参与模式中,各方主体如何集资、如何分红都需要提前进行制度设计,从而确保各方主体主动融入共建模式的热情,在共建模式中高校成为社会转型和升级的引领主体,高校促进社会转型和升级的功能得到实现,因而各方共建与效益分红及高校对社会的贡献都需要体现于评价考核制度链中。显然,政产学共同体一旦契入相应的连续性制度链,就能实现人才培养与应用研究、社会应用或需求的结合,契入产业及行业轨道的人才培养不仅对人才创业能力的提升及绩效具有促进作用,而且更契合市场发展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6]。
政产学共同体建设只有在制度源头上进行连续性设计,才会拥有规矩准绳。建设政产学共同体连续性制度链旨在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应用型人才、应用型科研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方协同合作与协同创新的路径轨道,地方本科院校才有可能实现向新型本科院校迈进。
三、政产学共同体的形态跃升:不同的价值链
政产学共同体取决于政府、企业及高校各方的合作关系,政产学共同体各方主体的合作关系决定着其形态的跃升。按照伯顿·克拉克关于政府、市场和高校三种力量划分[7],政产学共同体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和高校主导型三种类型。从横向维度上划定政产学共同体三种不同类型旨在强调政产学共同体各方主体的主导性,尽管三种类型存在理论上的形态跃升,但是三种类型并不呈现具体价值,只是一种价值混沌状态。然而,从纵向维度把政产学共同体划分为合作形态、服务形态和引领形态则能体现出不同形态所实现的相应价值链,三种不同形态就能体现各方主体如何通过“沟通、协调、合作、协同”,将思想、知识、技术和机会进行跨界结合,从而实现各自所达到质变效率和创造价值的目的[8]。政产学共同体纵向维度上三种形态由于具有各自不同的运行特征,因而三种形态实现的价值链则具有明显区分:政产学共同体合作形态具有各方主体的合作特征,合作形态显然需要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质量体系链,寻求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及应用型科研水平的各方合作契合点,以实现培养应用型人才和应用型科研的价值链;政产学共同体服务形态具有服务地方经济特征,服务形态需要融入服务区域的产业链形成促进社会发展的驱动点,以应用型人才和应用型科研实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链;政产学共同体引领形态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引领特征,引领形态需要主动参与促进社会转型升级链的进程,以实现社会转型升级的价值链,才能立于引领社会发展的制高点。因而,政产学共同体的合作形态意味着新型本科院校的孕育或雏形,政产学共同体的服务形态标志着新型本科院校的正式形成,政产学共同体的引领形态象征着新型本科院校的完全成熟。
(一)合作形态:质量体系链及契合点
政产学共同体取决于三方主体的合作关系,其合作关系的根基来源于高校自身的优势。高校优势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只有奠定雄厚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高校才能更好地融入区域,才能更好地履行服务社会职能,政产学共同体才能拥有牢固的纽带。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取决于高校教师,而高校教师产学研合作能力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应用型人才质量的高低及应用科研的优劣[9]。因而,建设具有政产学共同体意义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质量体系链至关重要。
质量体系链是涉及质量研发、质量目标及标准设置、质量建设等一系列环节所组成的有机系统,主要包含人才质量和科研质量。质量体系链决定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因而,质量体系链是政产学共同体多方合作的契合点。各方合作只有契合在质量体系链中,才能共同实现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质量提升的目的。
高校存在学术型、应用型和技术型三类区分,地方本科院校具有的特有属性决定了培养应用型人才和生产应用型科研是质量使命:以培养学术型人才和生产应用型科研为使命,地方本科院校不仅很难应对传统本科院校带来的挑战,而且不符合新时代对地方本科院校的新要求,而以培养应用型人才和生产应用型科研为使命,一方面无形中压制了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不利于高职院校整个生态系统发展。显然,应用型人才和应用型科研的质量目标决定地方本科院校的专业、课程与学科建设、教学与科研及其评价必然具有应用型因子。因而,建设政产学共同体质量体系链,地方本科院校不仅需要进入产业和行业进行调研,而且需要吸引政产学共同体各方骨干力量参与其中。
大学与企业进行超前沟通,从企业搜集技术发展的方向,以及企业的技术需求,进而适度调整基础研究的方向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布局,引导科研人员将关注点转向科研成果可转化性和知识的商业价值[10]。应用型人才和应用型科研的质量目标,专业、课程与学科建设及教学与科学的目的在于促进高校供给侧要素契合企业或行业需求侧要求,高校培养的应用型人才才能成为企业或行业的刚需,高校的应用型科研成果才能融入政产学一体化进程中。校地科教产融合将成为政产学共同体的主要实践形式,实验室、实训平台、研发项目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企业或行业进入课堂及学生进企业或行业实践将成为常态。高校只有经过系统的深度合作,创业理念及态度才会得到强化,阅历逐渐丰富,学生创业素质和能力才会得到提升[11]。显然,政产学共同体合作形态的质量体系链就在于实现培养应用型人才和生产应用型科研的价值链,以激励各方主体契入在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应用型科研进程中。因而,高校质量体系链的完全形成构成政产学共同体的最初级形态-合作形态,意味着新型本科院校的雏形。
(二)服务形态:地方产业链与驱动点
政产学共同体的成长始于高校内部,高校内涵建设发展道路是政产学共同体成长的基础,而政产学共同体以应用型人才优势和应用型科研优势服务地方企业、行业及产业,并融入服务地方产业链则标志着其具有服务社会发展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驱动点。融入服务地方产业链是地方本科院校跃升为新型本科院校的标志,也标志着政产学共同体由合作形态上升为服务形态。显然,政产学共同体的服务形态高于其合作形态。
地方本科院校若要融入服务地方产业链实现服务地方的价值链,则需要地方本科院校耕耘于应用型人才,扎根于应用型成果,实施应用型成果的转化。能否融入服务地方产业链的实质取决于地方本科院校是否为地方培养应用型人才、产生应用型科研成果及应用型科研成果的转化,或能否具有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能力。从人才培养而言,地方本科院校培养的人才需要适应并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其判断标准主要有就业率、校友评价及用人单位认可度。并且,地方本科高校需要在应用科研方向下功夫,直面当地企业、行业和产业急需解决的应用研究,这需要从以强化应用型科研成果作为价值导向的科研投入机制和科研评价机制入手,以积聚应用科研优势。
实施应用型科研成果转化显然是地方本科院校推行应用型科研的目的和归属,而地方本科院校需要从多方面加大成果转化力度:建立应用成果转化的信息共享网络平台,打造应用成果转化的强大网络推手;成立校友应用成果转化信息助推平台,借助校友力量促使应用型成果转化;建立应用成果的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对接信息平台,以提升成果转化的时效性。因此,地方本科院校欲要实现向新型本科院校的质的飞跃,必然只有在应用型人才、应用型科研及应用型科研转化上下功夫。显然,融入服务地方产业链标志着,具有培养应用型人才、生产应用型科研及应用型科研转化等优势的地方本科院校步入新型本科院校行列。
(三)引领形态:社会转型升级链及制高点
政产学共同体在服务形态基础上需要主动参与促进社会转型升级的进程,并赢得引领社会发展的制高点,融入社会转型升级链,则标志着政产学共同体最高形态——引领形态的跨越。政产学共同体引领形态主要体现在地方产业或行业升级、地方应用型智库建设、中外合作办学等方面具有优势,其地位已远远超越高校传统职能,从而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成分[12]和社会转型升级的动力引擎。所以,助推产业或行业升级、加强地方应用型智库建设和发挥中外合作办学上的引领功效是新时代新型本科院校的最高使命。
产业或行业升级意味着资源要素、技术、管理水平的改变带来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升,这将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促使价值链升级[13]。产业升级则是企业、行业或产业根本性的变化,所以,促进产业升级必然要求高校拥有助推产业升级的集群优势,包括群体的应用型人才优势和应用型科研优势及应用型成果转化优势。企业无论是利用大学基础研究、人才聚集、学科专业相对完备的优势,还是借助大学在攻关体系中超前预研的作用,抑或是支持大学建设若干个产业技术研究院,都会选择那些更能促进产业或行业升级的大学,以集中攻克若干重要的前沿基础技术和通用技术,从而构架面向产业未来需求的预研体系[14]。毫无疑问,新型本科院校应朝建设领先的产业学院或行业学院(独建或共建)的方向发展,而产业学院或行业学院中应用型大师大多出于该高校,大批应用型人才则出自领先的产业学院或行业学院,新型本科院校就能在助推社会产业或行业升级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新型本科院校可以通过建设地方应用型智库,利用高校的应用型人才、应用型成果及其引领产业或行业等优势,并围绕地方各行各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侧及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供给侧、政府对地方人才培养的政策及对地方产业发展的布局等内容进行智库建设,以助推社会转型升级。新型本科院校需要在中外合作办学上发挥引领作用,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可以在政产学共同体的任意形态时期进行,其发展亦是不断深化的过程,最终上升为引领形态,新型本科院校在国际上就具有引领性和知名度,而在中外合作办学上彰显应用型人才、应用型科研等方面优势,其实质就能对整个社会转型升级带来巨大能量。因而,政产学共同体的引领形态象征着新型本科院校的成熟,决定了新型本科院校必然以一种全新的姿态亮相于社会及世界舞台。
四、结 语
地方本科院校与新型本科院校是同一类型但又不同质的一对概念,实现对新型本科院校的跨越是地方本科院校的新时代要求和历史使命。与地方本科院校具有天然的“血缘”是其身处其境的地方政府、企业、行业、产业等。因此,从地方政府、企业、行业、产业等吸收能量并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作贡献是地方本科院校的明智选择。走政产学共同体发展道路是地方本科院校向新型本科院校跨越的历史必然。
政产学共同体需要搭建连续性制度链才能维系政产学共同体的长期稳定运转,需要建设质量体系链才能形成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多方协同创新的契合点,需要融入服务地方产业链才能形成促推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点,需要形成引领社会转型升级链才能立于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政产学共同体由合作形态向服务形态和引领形态的跃迁进程是地方本科院校向新型本科院校的发展进程,也是实现价值链的上升过程。因而,地方本科院校只有促进政产学共同体的形态跃升,致力于应用型人才质量和应用型科研水平的提升,着手于应用型成果转化,并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以带动其产业和行业的升级,在通往新型本科院校的道路上才会顺畅无阻,进而实现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