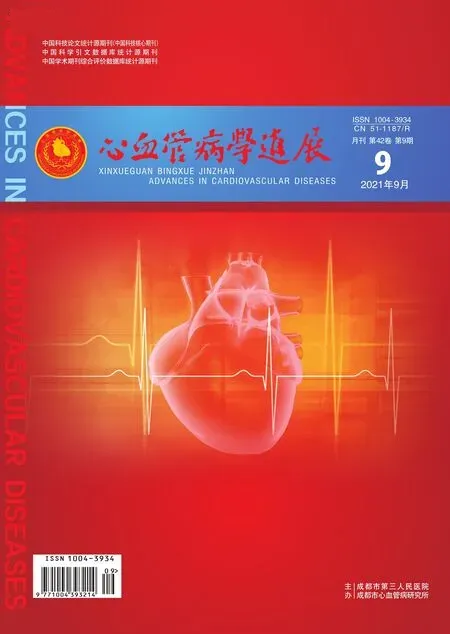心房颤动合并肿瘤患者的治疗现状及进展
薛祚臣 程爱娟
(天津市胸科医院,天津 300222)
心房颤动(房颤)是最常见的持续性心律失常之一,房颤对心功能的影响及血栓栓塞风险的显著提高严重地威胁了患者的健康。随着对房颤认知的不断深入,有关房颤的治疗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近年来,房颤患者中肿瘤的检出率逐渐增加,而肿瘤的存在使得房颤的抗凝治疗和心律与心率的控制治疗存在诸多矛盾与困难,同时房颤的存在又增加了肿瘤患者放化疗及手术治疗的风险。目前对于房颤合并肿瘤患者,治疗方面的的证据及经验相对较少,亦缺乏相关指南的明确推荐。
1 房颤和肿瘤的流行病学研究
房颤是临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目前统计的患病率为1.5%~2.0%,且随着年龄增长,房颤的患病率逐渐增高。房颤可导致脑卒中风险增加4~5倍,而心力衰竭的风险增加2~3倍,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并增加了死亡率[1]。在目前的临床工作中,房颤合并肿瘤的患者并不鲜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房颤与恶性肿瘤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肿瘤的存在,尤其是诊断为肿瘤的90 d内,可引起房颤发病率的进一步增加。如在O’Neal等[2]的横断面研究中,肿瘤患者的房颤发病率较非肿瘤患者更高(3.6% vs 1.6%,OR=1.19,95%CI1.02~1.38),近期一项研究显示房颤在癌症患者中的发病率为14.1%[3]。由于合并肿瘤患者存在更高的出血及血栓栓塞风险,并且多合并高龄和多脏器功能受损,需长期接受抗肿瘤治疗等危险因素,该类患者的治疗策略尚存在一定的争议与挑战。
2 肿瘤导致房颤的相关机制
首先,肿瘤患者易合并组织缺氧、代谢异常、感染、电解质紊乱以及经历外科手术等临床特征,这些特点均容易导致房颤的发生及维持。其次,自主神经系统功能改变亦是引起房颤的重要原因。抗肿瘤治疗、心肺功能适应力下降、社会及心理压力、代谢紊乱可导致胆碱能系统功能障碍,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引起心房电生理功能改变,通过折返机制及钙离子介导的触发活动造成房颤发病率进一步增加[4-5]。第三,副肿瘤综合征:针对自身肿瘤抗原而产生的抗体作用于心房组织,可能诱发房颤出现。同时,在肿瘤治疗过程中肺部手术对肺静脉电位的激发,放疗造成的心房细胞纤维化,化疗药物及靶向药物的细胞毒性以及对冠状动脉和心肌动作电位的影响,也是肿瘤患者易发房颤的重要原因。另外,炎症微环境和氧化应激等因素亦参与其中[6-8]。
3 房颤合并肿瘤的治疗
3.1 对因治疗
超重、吸烟、酗酒、睡眠呼吸暂停、高血压和糖尿病等均为房颤发生的高危因素,因此,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对危险因素的控制,乃至应用呼吸机辅助通气对组织缺氧的改善均显得尤为重要[9-10]。此外,抗肿瘤治疗与房颤发作密切相关。Moriyama等[11]的研究证实,氟尿嘧啶等化疗药物易导致血管内皮功能损伤,诱发冠状动脉痉挛,使心房缺血,导致房颤的发生。故对合并冠心病接受化疗的肿瘤患者,治疗期间应用扩张冠状动脉血管和解痉药物,有减少房颤发作的可能。
3.2 抗凝治疗
由于炎症微环境、高凝状态及骨髓毒性作用,肿瘤患者存在更高的血栓及出血风险,但对于房颤合并肿瘤患者其血栓栓塞及出血风险较非肿瘤患者是否增高尚存在争议。如在ROCKET AF等研究中,肿瘤患者存在更高的出血风险(2.3% vs 10.3%,P<0.000 1)、深静脉血栓风险(2.9% vs 4.0%,P<0.000 01)及死亡率(10.6% vs 23.9%,P=0.000 1),但血栓栓塞风险无明显升高(3.6% vs 3.9%,P=0.50),而在Deng等[12]的荟萃分析中,房颤患者无论是否合并肿瘤,其血栓及大出血风险类似。目前关于房颤合并肿瘤患者,其卒中及出血风险的评分系统仍推荐CHA2DS2-VASc评分和HASBLED评分,2019年发布的专家共识建议:对于CHA2DS2-VASc评分≥1分的男性患者和≥2分的女性患者,如果血小板计数>50×109/L,应接受常规剂量抗凝治疗,目前常规的抗凝药物为维生素K拮抗剂、新型口服抗凝药物和低分子肝素等。如果血小板计数为(25×109~50×109)/L,建议短期内应用半量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并考虑血小板输注,如果血小板计数<25×109/L,应视患者个体情况进行管理[13]。
低分子肝素目前广泛应用于肿瘤患者静脉血栓的预防,并且存在潜在抗肿瘤转移效应,与抗肿瘤药物相互作用的风险也较低,但对于房颤合并肿瘤患者血栓栓塞风险的预防,目前临床证据尚不充分,在Klerk等的研究中,对于肿瘤转移、高出血风险以及国际标准化比值(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不稳定患者,建议应用低分子肝素抗凝,较应用维生素K抑制剂患者预后更佳,但其价格及长期的针剂注射限制了其应用,目前多用于围手术期、血小板减少及药物相互作用较明显患者的短期替代治疗[14-15]。
目前的口服抗凝药物分为以华法林为代表的维生素K拮抗剂以及以利伐沙班、阿哌沙班和达比加群等为代表的新型口服抗凝药物,在ENGAGE AF和ROCKET AF等[16]研究中,服用新型口服抗凝药物的肿瘤合并房颤患者其血栓栓塞风险较服用华法林患者明显降低(3.5% vs 6.1%,HR=0.6,95%CI0.31~1.15;2.6% vs 4.9%,HR=0.52,95%CI0.22~1.21),其出血风险亦明显降低(14.4% vs 15.9%,HR=0.98,95%CI0.68~1.4;7.4% vs 10%,HR=0.71,95%CI0.42~1.21),而Deng等[12]的荟萃分析结果亦支持以上观点。这可能与华法林的有效治疗窗口窄,对INR的范围要求严格,以及与多种食物和药物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有关,故目前更适用于瓣膜性房颤、严重肾功能不全以及INR稳定在2~3的患者。而新型口服抗凝药物由于其广泛的治疗窗,无需频繁实验室检测以及药代动力学稳定的特点,更适用于肝肾功能频繁变化,基础状态消耗,需不定期接受外科手术的肿瘤合并房颤患者[16-17]。
3.3 抗心律失常药治疗
关于房颤合并肿瘤患者的心律与心率控制的药物治疗,2019年发表的专家建议如下:对于快速房颤造成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患者,建议紧急电复律治疗;对于心室率无法控制达标的,即使心室率控制稳定但仍存在明显房颤相关症状的,由于感染、甲状腺功能亢进和贫血等可纠正因素触发房颤的,以及无结构性心脏病和抗肿瘤治疗阶段性完成的患者,建议以转复心律治疗为主。而对于心室率控制良好,需持续抗肿瘤治疗,以及房颤发作明显与肿瘤相关的,合并结构性心脏病的,肿瘤活动期、终末期或处于姑息治疗阶段的,多种抗心律失常药物仍无法维持窦性心律的患者,建议控制心室率治疗。需注意的是,多种抗心律失常药,特别是Ⅲ类抗心律失常药均与抗肿瘤药物(如化疗和靶向治疗药物)存在药物相互反应,存在延长QT间期的风险,在应用过程中应密切监测。而β受体阻滞剂,由于其抑制交感神经和拮抗肿瘤相关的自主神经损害作用,是目前推荐的控制抗心律失常药[18]。
3.4 手术治疗
由于肿瘤患者药物转复窦性心律的可能性不高,且长期应用抗凝药物出血风险较大,射频导管消融、左心耳封堵及左心耳闭合等手术治疗可能亦是合适的选择。
在Giustozzi等[19]的研究中,房颤合并肿瘤患者在射频导管消融围手术期出血风险较非肿瘤患者高(19.00% vs 6.13%,OR=3.60,95%CI1.02~12.73,P=0.047),与前文所述ROCKET AF等[16]研究结论一致,但多为皮下及肌肉出血,未见大量或致命性出血情况。而术后房颤复发比例为24%,与非肿瘤组相当。故射频导管消融术对房颤合并肿瘤患者的治疗前景值得期待,但其安全性及有效性仍需更多的临床证据。
对于血栓栓塞高风险、出血高风险、不能耐受或不愿长期抗凝治疗的患者,可选择经皮左心耳封堵术,但尚未对癌症患者中该方法进行专门研究[18],而Toale等[20]近期对报道了关于房颤合并肺癌患者行胸腔镜左心耳闭合术成功的案例。由于封堵装置的存在,左心耳封堵术后的患者需接受从抗凝治疗到抗血小板治疗的过渡,并长期服用抗血小板药,而左心耳闭合术后的患者,无需终身服用抗栓药物,似乎是房颤合并肿瘤患者的又一合适选择。
4 总结与展望
罹患肿瘤的患者房颤发病率明显增加,但目前肿瘤与房颤的作用机制及内在联系尚未完全清晰。肿瘤患者有更高的出血及栓塞风险,但房颤合并肿瘤患者其出血及栓塞评估缺乏针对性的评分量表。目前对于该类患者的评估及治疗尚存在一定争议,未来仍需更多临床证据来指导该类患者的诊断、评估和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