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邯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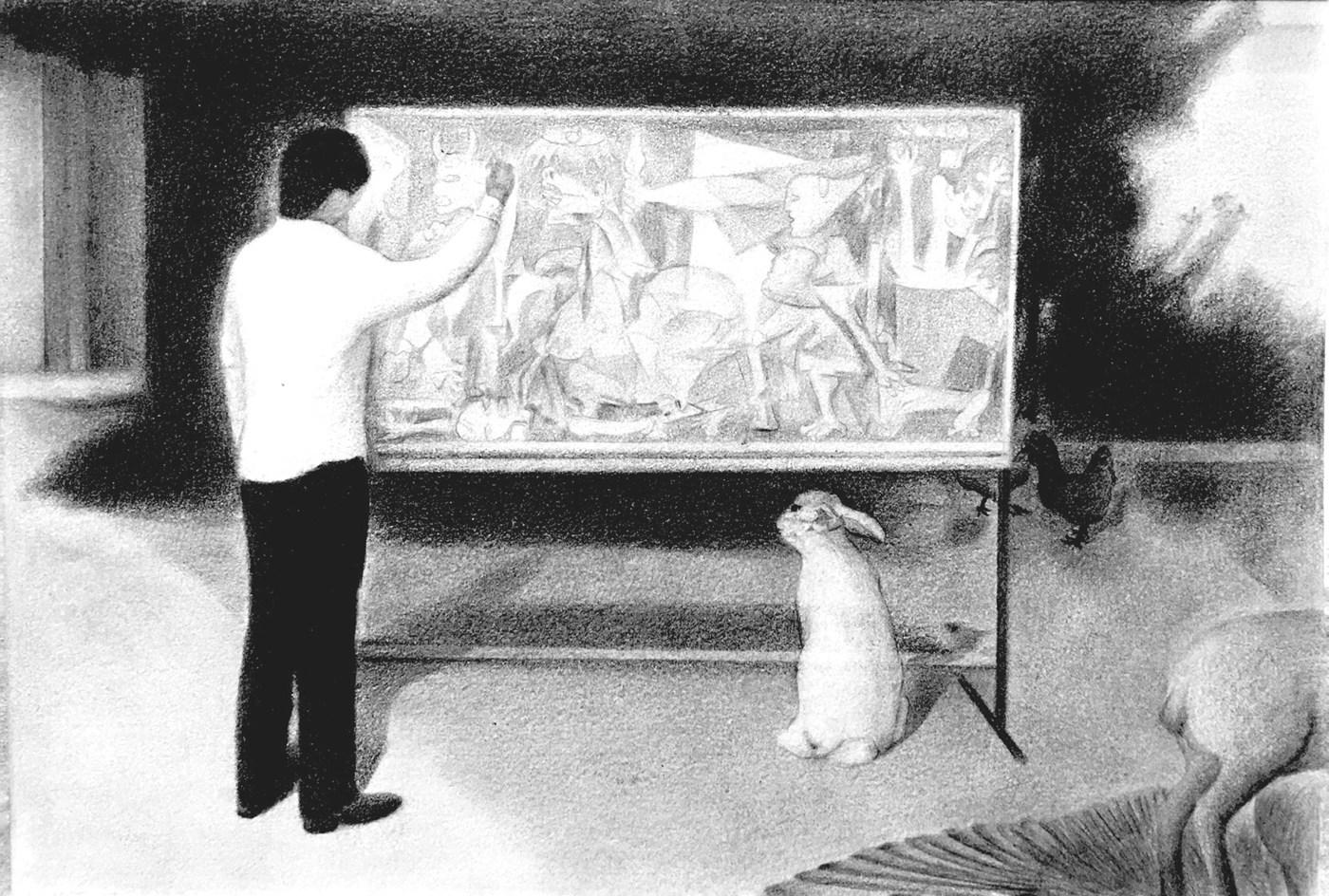
没能在九点半的第一次闹铃声中及时爬起来,对我来说是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其实我早就应该明白这一点的,如果没有被第一次的闹铃闹起来,接下来很有可能我也不会被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闹铃闹起来,而事实也正是这样。一直挨磨到十点十五分,栗莉打电话说她马上就要到了,我才手忙脚乱地爬起来,胡乱洗漱了一通。
我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栗莉已经到了。她那辆斯柯达明锐停在路边,她坐在车里。她,车,都显得很新。车是因为刚洗过,她是因为穿了一件我从没见过的白色羽绒服。我走过去拉开车门,指指她,又指了指副驾驶。她挪出来,我坐进去。然后我注视着她绕过车头,走到副驾座外面,拉开车门坐进来。你开?她一边系安全带一边把这句废话吐了出来。我开!我拧钥匙发动车子,同时意识到自己说的也是句废话。
说废话是正常的,事实上,又有谁不说废话呢?如果足够留心,你会发现几乎所有人都会说废话,你自己也不例外,甚至一点儿也不比别人更少。至于说得多还是少,取决于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关系越近则废话越多,反之亦然。对于这一点现在我越来越有体会,因为我和栗莉之间的废话就很多。当然,这也说明了我们的关系很近,不出什么意外的情况下还会更近。她是我谈了两年半的女朋友。
三年半前,我从一家半年都没发出过薪水的报社辞了职,先是在朋友的朋友的影视公司里干过几个月宣发,后来又跳槽到一家新媒体公司。有天中午,饭后,我到消防梯的拐角处抽烟——如果你也是在北京某座写字楼里上班的抽烟族一员,相信你对这个地方也会非常熟悉,并不亚于对自己工位的熟悉程度。抽到一半时,上面一层的消防楼梯拐角处走进来一个女的,也掏出烟,叼上,又摸出打火机啪啪打了一阵,不过却一直没能打着火。我冲她哎了一声,扬了扬手里的打火机,然后走了上去……一个多月后我们俩就好上了,或者像我同事所说的那样搞上了。她就是栗莉。
栗莉小我两岁,北京人,在我们公司上面一层的一家图书公司做少儿图书编辑,当时刚从一段失败的恋爱中走出来不久。她相貌中等,身材中等,个头也中等,而且早已过了挑挑拣拣的年纪,而我本人差不多也是这样,于是我们就这么在一起了。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在今天,也就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要想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待下来,要么你得有一份能挣钱的职业,要么你得有一个愿意为之献身的梦想,而如果两者皆无——就像我一样,那么你最好想办法把一个既不嫌弃你不能挣钱、也不嫌弃你没有梦想的女孩子——最好是当地人——变成你的女朋友。在当地找个女朋友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意味着你和所在的城市有了关系,同时也就意味着你有了把根扎下来的可能。是的,这么说吧,女朋友有时候并不止女朋友那么简单。
我们所在的那栋写字楼位于798艺术区附近,我租住在芍药居,栗莉家在西苑。熟悉北京的话你应该知道,这三点差不多在一条直线上。这也就意味着,每天早上栗莉可以顺路接我上班,每天晚上也可以再顺路送我下班,这么一来,我终于逃离了在北京持续多年的地铁—公交车—步行的上下班方式。而这也让我意识到,这份恋爱对我来说实在算得上一件买一送一的好事,不但找了个女朋友,而且还送了个司机。当然,对栗莉来说也同样如此,因为三不五时地我也会当一回司机,有时候开她的车,有时候开她——在我和一个小伙子合租下来的那套小两居的次卧里,偶尔也在车后座上。
不过,自从半年前开始,栗莉就明确表示不想继续跟我在我那间不足十五平方米的次卧里或者车后座上干那件事了,而是想在一套属于我们俩的房子里,以夫妻的名义。
对于这一点,我表示完全理解。一个跟我谈了两年半之久的已经迈进36岁大门的老姑娘,对我提出来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于情,于理,她也都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我给她一个明确的交代。何况我们此前已经见过了彼此的父母,她父母虽然对我并不是特别满意——主要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北京人同时也不具备成为北京人的可能,不过既然栗莉选择了我,他们倒也没有再继续表示反对;相比之下,我父母对栗莉倒是非常满意,他们的非常满意跟栗莉是不是北京人其实关系并不大,主要是因为她是个女的,更是个愿意跟他们家小儿子在一起、同时看上去也挺适合跟他们家小儿子在一起的女的。
后来的那几个月里,一到周末,栗莉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她的看房之旅。在她以为我或者我们加在一起能够承受的房价范围内,她带着闺蜜或者我先后去看了门头沟、房山、大兴、通州、顺义、昌平等北京郊区的十几个新楼盘。比较来比较去,比较去比较来,最后她选中了通州果园地铁站附近的一套房子。那是顶楼一个南北通透的小两居,外面带着一个说是免费赠送但是事实上谁都知道价钱早就包含在房价里了的大露台,室内总面积85平方米(含近20平方米的公摊),每平方米6.5万,最低首付款是165万。
这笔钱在北京或许并不算高,不过对我来说却无异于天文数字了。事实上,即使我们俩的存款都加起来也还存在着一笔不小的缺口,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里,无论我们俩怎么努力也不太可能把那笔缺口挣出来——除非下班路上去买一张必然会中大奖的彩票。最后我们俩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瞄向了对方的家庭,我说,让你爸妈支援点儿!她想了想,说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然后对我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虽然我知道父母手里已经没什么钱了,早就被我们三兄弟年复一年地榨干了,不过我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知道這是应该有的态度。我说,放心,我一定要他们把买棺材的钱都给他们的小儿子贡献出来!我盘算的是,我手头一共有六十五万存款,到时候就跟栗莉说里面有十五万是我父母出的——就这些还是他们挖地三尺、砸锅卖铁搜罗出来的,虽然不多,不过已经竭尽全力了,我想到她肯定也就没什么话说了。
栗莉从她父母那里弄过来三十万,再加上她自己的,以及我手里的——名义上有十五万是我父母出的,一共凑到一百二十万,还差了四十五万。我说,还不够啊,怎么搞?她两手一摊说,我们家反正拿不出来了,你们家再想想办法吧。我说,我们家你又不是不知道,还能想出来什么办法?我爸,我妈,两个老农民,能拿出来十五万已经是钻山打洞了。这时候她不失时机地提醒我说,还有你二哥呢,还有你大哥呢?
减速!减速啊!一拐上北三环东路,栗莉就开始指挥起我来。她总是这样,开车时不喜欢别人指挥自己,还老是指挥别人开车。我不太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同时也不太明白她究竟是以女朋友的身份在指挥我,还是以车子真正主人的身份在指挥我。
我知道!我一边减速一边说,我又不瞎,不是已经减速了嘛!你就是瞎,要是我不说你会减么?她指了指慢下来的车流说,前面都堵成这样了你还开那么快,是不想活了,还是没睡醒啊?她一连串地说教起来,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我没好气地说,你开还是我开?要不然你开好了!我实在不想跟她在这个已经纠缠了无数次的问题上再继续纠缠下去了。她这才不吭声了,摇窗开了一条小缝,又摸出来一根烟点上了。
半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开出东三环北路,拐上了通往通州和燕郊方向的建国路。
不知道怎么回事,建国路上的车子更多,车速更是越来越慢,五分钟过去了我们也没能往前挪动五十米。我也摸出一根烟点上了。今天降温,最低零下八度,晚上还有中到大雪,昨天的天气预报里是这么说的,但是那么恶劣的天气,不知道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出门。望着前方滚滚的车流,我不由得想,难道这些司机跟我一样,也都有个二哥住在燕郊?他们的老娘也都跟着他们的二哥一家住在燕郊?他们也都开着他们女朋友的车载着他们的女朋友打着冬至去看望老娘的名义去跟他们的二哥借钱付首付?
就这样,开开停停,又停停开开,一直到过了午饭的点我们才到达燕京航城。
停好车,我从包里摸出来昨天就准备好的那个信封递给栗莉说,等会儿你给我妈吧!她捏了捏,又看了我一眼说,什么?我说,还能有什么,钱啊!她愣了一下说,你给啊,怎么要我给?我说,这不显得你孝顺嘛!我又叮嘱她千万别当着我二嫂的面给,最好去我妈房间里单独给她。之所以提醒栗莉这一点,是因为我知道我二嫂天生就有一种把我妈的钱和我们给我妈的钱都拐弯抹角地花销到他们自己一家人身上的本领。
是我妈开的门。门刚一开,我就注意到了她那沾满了面粉的手指。二哥一家都在。二哥正捏着一根鸡毛掸子给他们家老大张成辅导英语,他面前的小黑板上写着How old are you、What is your name、Happy new year等几句英文,二哥念一句——他操着一口我们老家的口音,张成就跟着念一句——他则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一旁的沙发上,二嫂抱着他们家老二张功正在看电视。我和栗莉的到来,并没能把张功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他还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屏幕上,成千上万的角马在过河,其中一只刚过到河对岸的小角马被埋伏在那儿的狮群成功偷袭了,眼下它正被几只狮子撕咬得血淋淋的。我走过去,歪下头去看了看张功,他只瞅了我一眼,接着又把目光移到了屏幕上。我笑了笑,想,长大之后他肯定会比他哥哥张成更成功,因为才一岁多点儿他就开始接受这样的震撼教育,明白了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我妈正在包饺子,韭菜鸡蛋馅的——这是我最爱吃的馅,她面前的小方桌上已经快摆不下了。她是两年前从老家来到二哥家的,当时是来照顾我准备生二胎的二嫂。后来二嫂就不让她回去了,虽然对这个农村婆婆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不过她并没有感情用事,在每月花几千块钱请个保姆和让我妈继续待下来之间,她还是非常理智地选择了后者。这一点很符合她精打细算的性格,同时也很符合她信贷员的职业精神。
在我看来,这倒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安排,毕竟我妈年纪也大了,地里的活儿也干不动了,正好到二哥家里含饴弄孙一番什么的。但是,这么一来我大嫂心里却不平衡了,说我妈太偏心老二家。她要我大哥去做我二哥的工作,说让我妈也到他们家里去住一段——当然也是伺候他们一家之类的,而这个要求遭到了我二嫂的严词拒绝,为此这两个一共也没见过几次面的妯娌几乎快闹翻了,她不去她家,她也不去她家。
再后来,我大嫂就打上了我爸的主意,把他从老家接到了他们所在的香河县城。一开始我还挺纳闷,以为她和我二嫂在比谁更孝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是让我爸——这个当年的生产队二队队长、后来闻名乡里的种菜能手——到她弟弟开的那个物流公司去看大门,管吃管住,但是基本上不发什么工资,等于白出力。不过我爸对这份新工作倒还挺满意的,毕竟他现在一天到晚只需要拎个保温杯坐在门卫室里盯着进进出出的人就行了,相比于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地球,这样的工作简直太轻松了!
就这一点而言,有时候我对二嫂和大嫂还挺感激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她们俩毕竟把我父母从农村老家接了出来,让他们过上了想象中的城市生活,不,北京生活。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想父母最应该骄傲和自豪的还是他们自己——如果不是生了两个这样的儿子,进而又有了两个这样的儿媳,他们又怎么可能过上今天这样的生活呢?
是这样,跟那些一心想要个儿子最后却接连生了三个女儿的人家正好相反,我爸妈当年是因为一直心心念念地想要个女儿,没想到最后却接连生了三个儿子。对农村人来说,三个儿子就是三座大山,一个儿子一所宅院是跑不掉的,这也是娶上媳妇的首要保证。可能被自己制造出来的三座大山吓到了,在漫长的年月里,我爸妈一直都并肩奋战在我们家那七亩半薄田之中,种麦子,种玉米,种高粱,种大豆,种花生,种红薯,种蔬菜,想以此完成给三个儿子的原始资本积累。然而,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我们三兄弟会那么争气,竟然陆续都考上了大學,陆续又都到了北京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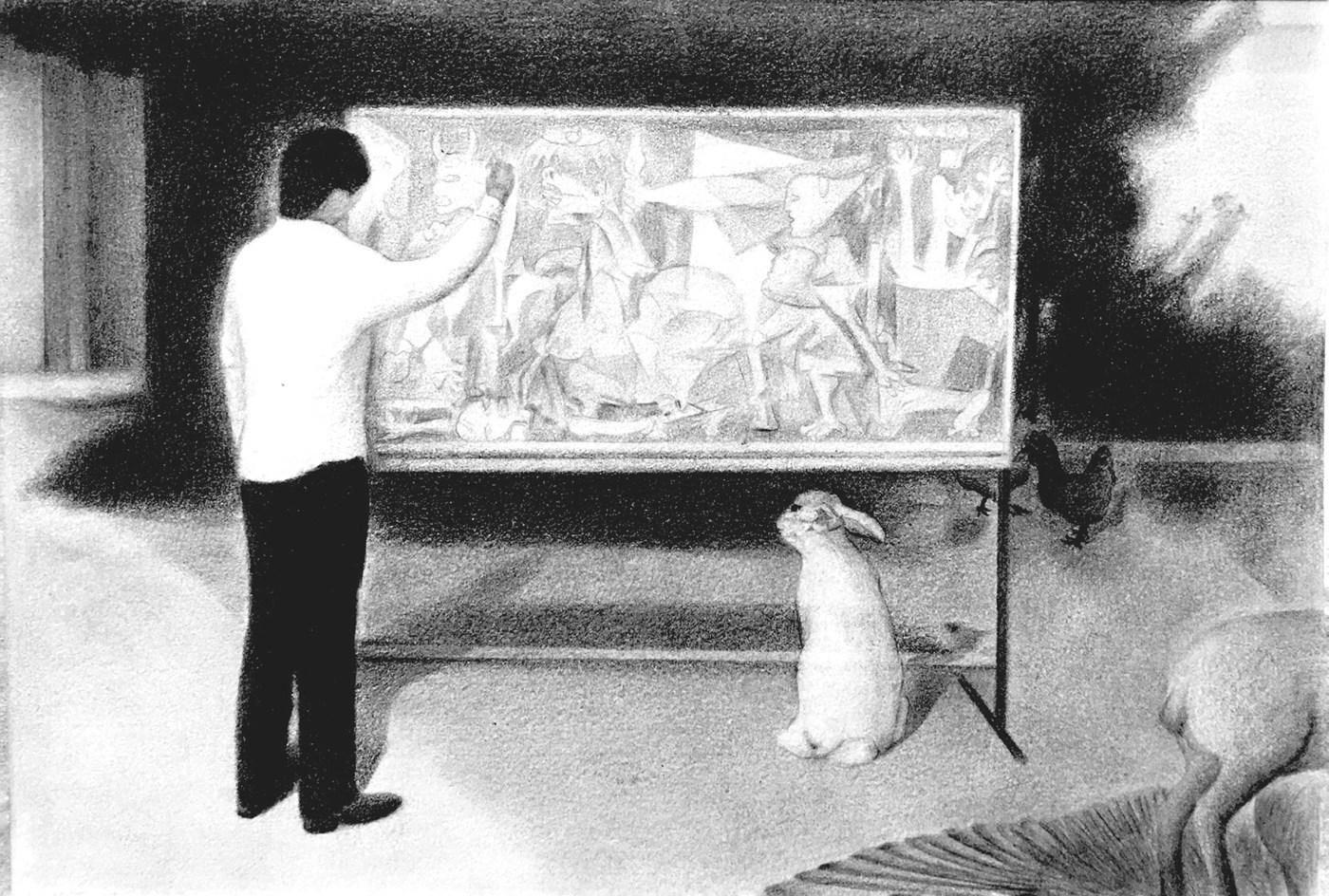
这一点,在我们村里产生的效应是轰动的。记得刚到北京工作那一年的春节,我代表大哥、二哥以及我自己回老家过年(大哥去了大嫂娘家过年,二哥也去了二嫂娘家过年),就在我到家的那个下午,有好几个邻居都跑过来看热闹,主要是看我,就好像他们从来没见过我似的。一个跟我妈年纪差不多的、我一直喊作婶子的妇女,凑到我妈跟前说,嫂子,你们老张家好福气啊,三个儿子都留在北京了,都成北京人啦!
“三个儿子都留在北京了,都成北京人啦”,我爸妈很享受这句话,或者说,他们很享受邻居说这句话时流露出来的那种羡慕之情,虽然这并不是事实。事实是,我们三兄弟虽然都在北京工作了,但没一个成为北京人。准确地说,我大哥是在靠近北京的香河县买了房,我二哥是在靠近北京的燕郊镇买了房,而我还是个北漂。空顶着一顶“北京人”的头衔,我心里很是发虚,一边不停地用鞋底磨蹭着地面,一边很想替自己也替两位哥哥解释几句,但是我终究没有,父母非常享受的表情让我没有那么做。
饺子很好吃,起码比我们写字楼旁边那家东北饺子店里的好吃多了。在我妈一而再再而三的热情催劝中,栗莉吃了整整两大盘,而我和二哥则每个人吃了三大盘。
吃完,一抹嘴,二哥就摸了两根烟出来,递给我一根,自己一根。他刚点上,十分享受地吸了一口,二嫂就阴着脸过来了,举着鸡毛掸子像挥赶鸡鸭一样把二哥往外面轰。二嫂说,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出去抽!出去抽!一点儿记性都不长?她这么一说,我也就不好把手里那根捋了又捋的烟再点着了,便跟着二哥来到门口的消防梯。
今天还回去不?一根烟快抽完时,二哥先开了口。不回了,等会儿去大哥那边看看爸,我说。哦,是该去看看了,我也很久没去啦,二哥说。说完他又续上一根烟,划开手机屏幕,看起了上面那张花花绿绿的K线图。看来时间还没把他教育好,让这个当年在西瓜车后面跟了二里路一心想白撿一只掉落下来的西瓜的少年,到了四十岁还在妄想着天上掉馅饼的那种好事,妄想着掉下来的馅饼会准确无误地砸到他身上。
涨了?我瞟了一眼他的手机问。他笑笑,很机警地看了我一眼说,涨了就好了。我说,上次跟你说的那个事考虑得怎么样了,能不能凑点儿出来?他先是愣了愣,然后才做出一副想起来了的样子说,哦哦哦,你说要买房是吧!我点点头说,你看看能凑出来多少。他面露难色地看看我,又指了指房门说,等会儿跟你二嫂说吧,她当家!
再进去,我直截了当地把借钱的事跟二嫂说了。二嫂说,小弟,你既然张口了,我们也不能一点儿不表示,这样吧,借给你五万,明天我给你转账过去,再多了我们也拿不出来啦,你看,大的要用钱,小的更要用钱。她指了指张成和张功。我说,五万哪里够,首付还缺四十五万呢!二嫂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栗莉,她冲栗莉说道,你们俩干吗非要在通州买房呢,通州那么贵,干脆就在燕郊买嘛,这边的房价降一半了快,均价也就两万多点儿,你们完全可以在这边买个大房子,还贷压力也会小很多!
栗莉笑了笑,但没有说什么。我连忙打圆场说,通州的房子已经看好啦,定金都交了呢!二嫂想了想说,小弟,真的就五万了,再多我们也借不了,要不你去大哥家看看,他们比我们有钱。她转身去了里间。再出来时,她手里多了一张纸和一支笔,笑嘻嘻地冲我说,亲兄弟明算账哈,小弟,你还是写个借条嘛!我愣了一下,迅即又笑笑说,应该的!应该的!等我写完,签完名,她又把准备好的印泥及时递了过来。
四点半,准备下楼的时候,我妈悄悄扯了扯我的衣角,又指了指她的房间。我顿时就明白了她的意思,便跟走到门外边的栗莉说,你先下去吧,我跟我妈再说几句。
不用猜我都知道我妈要说什么。果然,我一进去她就把门掩上了,压低声音说,你和小莉怎么样了?我说,还能怎么样,老样子!她说,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我说,急什么,房还没买呢,等买了房再说吧!我妈急了,说,先结婚再买房一样的嘛,小莉都多大了?你都多大了?张强,张强比你还小两岁吧,儿子都快小学毕业了,军生跟你一年的吧,孩子都两个了,你还在等什么?啊?她这么一说,我眼前顿时就浮现出了一个泥瓦匠和一个卡车司机的样子,张强,赵军生,我这两个发小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辍学没几年就结婚了。我连忙摆了摆手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
我妈又说,是不是小莉不愿意结婚啊?我听说现在城里有很多女孩子都不愿意结婚,也不想要孩子。我愣了一下说,栗莉怎么会呢,压根儿就没有的事儿,你别想东想西的!她这才笑了笑说,那就好,那就好,到时候我去给你们带孩子哈。哦,到时候让你爸也去!她又补充道。她的这个想法让我感到非常诧异,因为自打我记事起她和我爸就经常吵架,直到离开老家之前他们还经常吵,每次吵架我妈总会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这辈子我跟你过得够够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事实很可能并非如此。
我说,栗莉把钱给你了没有?她拍拍裤袋说,给了给了。我凑到她耳边压低声音说,你别舍不得花,也别都给他们花——我朝门外指了指。她说,我知道!我知道!
接下来,我妈又把话题拉到了我和栗莉身上。她说,你抓紧啊,实在不行就把生米煮成熟饭,女人啊,还是结了婚有了孩子才能栓紧。她这个想法把我吓了一跳,因为读书的时候她一直很担心我搞大了哪个女生的肚子,时不时就会拐弯抹角地提醒我这一点,而现在她却唯恐我搞不大栗莉的肚子。我妈动了动嘴唇,还想再说什么,我及时打断她说,我先走了,还要去大哥那边!说完我就走了出来,我知道,如果不及时打断她,她就会喋喋不休地一直说下去,没完没了,没了没完。这一点没什么好说的,所有到了结婚年龄却迟迟没结婚的年轻人的老娘都一样,都长着一张同样的嘴。
从单元门洞出来,我一眼就看见了栗莉,她正在抽烟,一只脚蹬在下边的那个小花坛边缘上。但是一看见我走下来,她马上就摁灭了烟,朝小区大门口的方向走去。
我冲过去,紧跟了几步,想和她并肩而行。她及时察觉到了这一点,也加快了脚步。这么一来,我们的距离又拉开了。我喊了她一声,这一喊不但没起到应有的效果,反而还起到了反效果,因为接下来栗莉用更快的速度对我表示了回应。她一不高兴就这样,但眼下我并不知道哪里惹到她了。我一边追过去,一边在脑海里把这几个小时快速过了一遍,最后我实在找不出来到底有什么地方惹到她了,于是也就放下心来。
一上车,栗莉劈头就问,你妈找你干吗了?没干吗啊,我说。没干吗?没干吗怎么待了那么久,她斜了我一眼说,还背着我!我说,我妈说,你比上次瘦多了,叫你多注意身体,多休息,少熬夜。她翻了个白眼说,胡扯!我说,不信你可以问她。她说,你妈说这些还用背着我?我说,估计她是说给我听的吧,叫我平时多照顾你些。
栗莉还是不信,但已经不像刚才那么不信了。她扭了扭钥匙,慢慢发动了车子。
从燕祁路拐上厂通路的时候,栗莉突然又冒出来一句,你妈该不会是催你结婚了吧,是不是要我们先把婚结了再买房?我心里一惊,对女人和女人之间惊人的感知力感到一阵恐怖,然后便悄悄地把眯着的眼睛闭上了,同时迅速盘算着接下来的对策。
是不是?她又问。我還是没吭声。这时候,她提高音量大喊了一声——张熙阳!我装作一副突然被惊醒的样子,又揉了揉眼睛说,什么,怎么了?她生气地说,跟谁装呢你,你丫压根儿就没睡着。我连忙说,怎么会没睡着呢,真睡着了,你看嘛,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我指了指自己的嘴角,她用力哼了一声,又问道,你妈到底找你干吗?是不是催你结婚了?我说,没有啊,没有的事,房子都还没买呢,拿什么结啊!
接下来,怕栗莉再盘问我什么,我就跟她说起了公司里的那些八卦,谁跟谁好了,谁跟谁掰了,谁跟领导有一腿了。她不时被逗得哈哈一笑,好像已经忘记了刚才的事情。快到香河县城时,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本来我想问他在物流公司还是在大哥家里,在物流公司就顺路去接他,不过他一直没接电话,于是我们就直接去了大哥家。
大哥在,大嫂在,他们的女儿贝贝也在,只有我爸不在。我问大哥,爸呢?他说,刚才上来一下又下去了,是不是迎你们去了?我又问贝贝,贝贝,你知不知道爷爷去哪里了?她举着小手朝窗外指了指说,跳舞!我愣了一下说,爷爷跳舞去了?她点了点头。我说,那你带三叔去找爷爷好不好?她又点了点头。下楼之后,贝贝一只手牵着我,一只手牵着栗莉,就像我们的女儿似的拖着我们俩往小区后门的小广场走去。
我爸果然在跳舞。此时此刻,他和几个年龄跟他差不多的老头儿正混迹在一群花枝招展的大妈中间,随着那曲嘹亮高昂的《十八的姑娘一朵花》起舞着,脸色明亮,身形矫健,拼命地摇动着两只膀子,像是把春种秋收的那股子劲都用在了这上头。
我让贝贝去把爷爷喊过来。贝贝走到他旁边,叫了一声,我爸往身后只一瞥,就连忙收住了动作,然后他又手搭凉棚四下里望了望。望见我和栗莉之后,他不好意思地咧开嘴笑了笑,然后就逃跑似的从那群妇女中间出了列,搓着手朝我们走过来。一直也等不到你们,就出来锻炼锻炼哈,锻炼锻炼!走到我们跟前的时候,他把笑容固定在脸上解释道,好像他跟那群妇女一起跳舞是因为我和栗莉没有及时到来才导致的。
紧接着,他给我递过来一根烟,又问我什么时候到的,晚上还走不走,有没有去过二哥家里,以及他的两个孙子张成和张功怎么样。我没接他的烟,也没接他的话。
回去的路上,栗莉牵着贝贝走在前面,我和我爸跟在后面。我没好气地说,闲不住了?老毛病又犯了?我知道,虽然一直没被抓住什么实质性的把柄,但是关于我爸和村里某个女人的风言风语却前前后后地传了很多年。他悄悄捅了捅我,又一本正经地指了指前面的栗莉和贝贝。我说,咱们家还是数你啊,你这日子过得潇洒得很啊!
回到大哥家,晚饭已经摆了上来,六个菜,一瓶酒。我不喝,栗莉不喝,大嫂也不喝,只有大哥和我爸两个人喝酒,他们俩一吸溜儿就是一盅,一吸溜儿就是一盅。
我一边吃一边琢磨着接下来该怎么开口。但是接下来,就好像知道我来这儿的目的一样,大嫂先开了口。她先是装作漫不经心地说了一通贝贝的教育问题,上了什么什么辅导班,花了多少多少钱,接着又对自己的单位效益下滑、奖金只有一半发了几句牢骚,接着话锋一转,她又说起她弟弟的物流公司,说物流行业现在怎么怎么挣钱,家里的钱都挤出来入她弟弟公司的股了。我不知道她扯了那么多到底是想表达什么。
直到最后,她才富有深意地看了我和栗莉一眼说,小弟,你们手头有没有闲钱,有的话也可以在我弟弟的公司里入个股,保证你们能挣到钱,真的!不得不承认,姜还是老的辣,比二嫂早三年嫁到我们家来,确实让大嫂比二嫂多了三年当儿媳妇的经验,也多了三年对付我们一家子的经验。好吧,现在既然她都说到这个地步了,我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开这个口了,于是便冲她摆了摆手说,算了算了,我们哪有什么钱。
我不知道大嫂是怎么知道以及是从哪里知道我是来借钱的,不过我想十有八九是大哥透露给她的,事实上我也只跟他和二哥两个人说过这个事。接下来,越吃我就越觉得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生硬的、机械的、勉强的,吃到一半就吃不下去了。我爸和大哥还在喝酒,一盅接一盅地喝。一喝酒我爸就上脸,我哥也是这样——这也间接证明了他确实是我爸亲生的。现在他们俩的脸都红透了,从脸上到额头上,一直红到发际线的位置,大哥发际线的位置已经基本接近我爸了——这也再一次间接证明了他确实是我爸亲生的。不过,眼下他们看上去却并不太像父子,反倒更像是一对兄弟。
再后来,大嫂就把大哥的酒杯收了起来,说不能让他再喝了,他也不能再喝了。大哥还想再喝两盅,起身去厨房又拿了个酒盅,大嫂又给他收走了,还咋咋呼呼地说了他一顿,说他逞能,说他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之类的。看得出来,她并不是真想说我大哥,而是以说我大哥的方式说我爸。我知道,每个当久了儿媳的女人都精通此道。
吃完饭已经九点多了,大嫂说去把客房给我们收拾出来。不过我已经没有心思再住下去了,看得出来栗莉也是,于是我便找了个借口说明天还有事,得马上回去了。
栗莉的脸色很不好看。下楼的时候,她把之前我让她给我妈的那个信封又从包里掏出来递给我。我愣了一下说,怎么还在你手上,我妈不是说你给她了吗?栗莉说,我给她她不要!我说,怎么会不要呢?栗莉说,那我怎么知道。信封比之前的明显厚多了,我捏了捏,又掏出来数了数,一共一万一。我说,不对啊,怎么多出来一万?栗莉说,你妈给的,说是给我们买房子用,我都装在里面了。我把钱装进去,又递给她说,那你拿着吧!她不要,说什么都不要。我说,嫌少?她瞪了我一眼说,嫌多!
下楼之后,还没走出去几步,我就听到后面有人喊了我一声——是我大哥。他走过来,把我拉到一边,又从怀里掏出来一个小塑料袋说,这三万你先拿着用,不够了回头我再想想办法。说完,他又十分小心地看了看单元门洞,凑到我耳边说,千万别让你大嫂知道了,这钱是我自己攒的。接过钱,我心头一热说,哦哦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上你呢。大哥说,算了算了,还什么还,你们赶紧回去吧,十点了都快。
大哥把我们送到小区门口,又看着我们上了车。已经开出来一段了,我还能从后视镜里看到他在路灯下站着抽烟。看着那个越来越小的他,我鼻腔里猛地一阵发酸。
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很多年前的一件事。有一阵子,二哥脖子里生了个疥疮,肿得老高,后来化了脓,父母要带他去石家庄开刀,就把大哥和我留在了家里。那时候我们家养了兩头牛,怕牛被牵走,平时晚上我爸就睡在那间东厢房改成的牛棚里,他一走,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大哥头上。而我那时候胆子比年龄还小,晚上不敢一个人睡,于是每天都要跑过去跟大哥一起挤在牛棚里的那张小床上。那头老牛和小牛卧在石槽里侧,我和大哥就躺在石槽外侧。靠在他的胳肢窝里,听着两只牛的反刍声和喷鼻声,那几天我睡得格外踏实,甚至比平日里睡在我妈身边还要踏实。
夜深了,看着窗外的旷野,旷野尽头偶尔闪过的几盏灯火,我心里又踏实下来。
栗莉一上车就睡着了,或者装睡着了。喊了她好几声,她才不耐烦地回了一句,怎么了?我说,我算了算,首付的钱还差三十六万呢,怎么搞?她侧侧身子,躺得更舒服了些说,什么怎么搞?你自己搞!我说,我能怎么搞?她悻悻地说,那我不管!我想了想说,其实二嫂说的也不是没道理,住在燕郊跟住在果园能差多远呢,也就半个小时,一脚油门的事儿,实在不行干脆就在燕郊买房算了,反正我们有车,也方便。
栗莉坐起来,很不屑地说,你的意思是要我跟你到河北去住?我说,那不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嘛,首付都凑不够,你说还能怎么搞?她突然提高音量说,河北我是不可能去住的,你想都别想!我说,你也看到了,我们家反正是拿不出钱来了,如果非要买通州的房子,那你就跟你爸妈再说说,要他们再凑点儿出来。她说,你说什么?我们家已经出三十万了,你们家才出了多少?你爸妈之前拿出来十五万对吧,今天你妈又给了一万,你二嫂五万,你大哥三万,一共二十四万,对吧,你算算,我们家比你们家还多出了六万呢,凭什么还要我们家再出?凭什么?到底是你娶我还是我娶你?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想占我们家便宜,你们全家都想占我们家便宜!栗莉又说。
我生气地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们家就是把不够的首付款都出了,也就三十六万吧,我又能占你多少便宜呢?她说,占多少便宜你自己不清楚么?我说,你说清楚,我到底占你什么便宜了?她冷笑一声说,真想听?我说,想!她清清嗓子说,跟我结了婚,你就有北京户口了吧,将来小孩也有北京户口了吧,一个北京户口值多少钱你总该知道吧,两个呢?没想到栗莉在这儿猫着我呢!尽管很生气,但我还是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克制,我并不想和她就此大吵一架,撞上别的车子或被别的车子撞上。
是不是?这个便宜你敢说没想过?你敢说一点儿都没想过?我把车子刚停好,栗莉又开始咄咄逼人起来。望着她那张挑衅似的小脸儿,我心头上憋了又憋摁了又摁的那股情绪几乎快要忍不住了。我很想用力扇过去一巴掌,在她小脸上留下五道鲜红的指印——就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我扬起手来晃了晃,又晃了晃,但终究也没有朝她落下去,而是摸了摸自己的脸。是的,我知道打女人不好,而最重要的是我没那个勇气,因为我爸没给我们三兄弟注入过这种东西,就像他爸也没把这种东西给他注入过。
我说,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庸俗了,一开始我怎么没发现呢?我真瞎!你瞎?我才瞎呢!她冷笑一声,然后解开安全带,用力一摔车门走了出去。透过后视镜,我看见她一直走到车后面二三十米的位置,又在护栏边上停下来,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几分钟后,等稍微平静下来一些,我也下了车。我沿着栗莉刚才的路线朝她走过去,并在她身后停下来。但是我并没有喊她,也没有走上前去,而是跟她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定定地望着她。栗莉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我走了过来,不过,对于我的到来她也没有表现出来任何反应——如果不是呼出的那两股热乎乎的白气被阵阵冷风吹歪吹散掉,烫成波浪卷的头发被吹得来回飘动之外,她和一具雕塑没什么两样儿。
她所站的地方离我非常近,仅仅一步之遥,或者说也就三十六万人民币的距离。
望着栗莉瘦削的背影,以及她面前那片空旷而黝黑的田野,我感到非常遗憾,遗憾自己怎么找了一个这样的女朋友,同时更遗憾父母怎么只为我生下了两个哥哥而不是更多。当年,如果他们能为那个迟迟没有到来的女儿再努力上几番,那么我上面肯定还会再多出来几个哥哥——或者姐姐,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支援我一笔,也就能把我顺利地送进北京城去了。如果那样的话,现在我也就有足够的勇气往前迈上一步,和栗莉站在一起了,不不不,我们也就不会在深夜时分一前一后地站在这个鬼地方了。
我呆呆地站着,目光越过栗莉瘦削的肩头停落在她也正望着的那片田野。我们所站立的路基下面是一垄垄低矮的麦苗,近处的几垄在路灯照耀下泛着一层青绿色的微光,越往里变得越黝黑,更远的地方挂着几盏零零星星的灯火。可以肯定的是,之前我从没来过这个地方,不过不知道怎么的我却对这里萌生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很多年前,那时候还没有收割机,所以到了麦收时节我们的父母就不得不扛着两把银光闪闪的镰刀下地割麦子,这时候我们三兄弟也总是会被驱赶到地里捡麦穗。当时我们都还小,总是捡着捡着就偷起了懒儿,互相追逐着打闹起来。此时此刻,望着那一垄垄从青绿变成黝黑的麦苗,我仿佛望见了正在金黄色麦茬地里追逐打闹着的我们三兄弟,以及我们弓着身子隐没在金色麦浪中的父母。我望见大哥正在前面拼命地跑,二哥正在后面拼命地追,年龄最小的我落在了最后面,落在最后面的我停下来,手搭凉棚望了一眼——是的,我远远地望见了我正在眺望着公路护栏边的我和栗莉。
现在,栗莉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望着,而站在她身后一步之遥的我也是这样。
以往,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会主动跟她认个错,或者她会主动冲我撒个娇,而我们彼此也都会顺利地屈服于对方的认错和撒娇,顺着对方搭好的那个台阶走下来。不过这一次我没认错,正如她也没撒娇,也许这一次她清楚地知道,我也清楚地知道,我们也都清楚地知道对方知道,我们面对的并不是认个错和撒个娇就能解决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栗莉突然转过身来,气呼呼地从我身边掠过,朝她那辆斯柯达明锐跑过去,拉开车门然后上了车。于是我也一路小跑着紧跟过去。上了车,我一边系安全带一边说,你开?要不然我来开吧?她没理我,并在接下来的这一路上都没理我。
回到我租住的电力公司小区时,已经深夜十一点多了。栗莉把车子在小区门口停下来,不过她自己却没有要下车的意思,同时也没有给车子熄火。我说,怎么,你不上去?她没有回答我,而是指了指我,又指了指小区大门。我说,那你呢?她望着前方说,我回家!我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回家?她又不吭声了,还是定定地望着前方,我注意到前方拐角处有一个穿橙色制服的清洁工正把垃圾从垃圾桶翻倒进三轮车里。
直到那个清洁工把三轮车开走了,栗莉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像是做出了一个很大的决定似的说,你快下车吧,我还得回家!我划亮手机看了一眼说,马上都十二点了,你回到家都什么时候了?她没回答我,而是解开安全带,拉开车门走下去,绕过车头一直走到我这边,又一把拉开我这边的车门,最后微笑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目送着栗莉的车子消失在前方路口之后,我还是继续站在那里。是的,暂时我还不想上去,此时此刻我需要在寒冷街头站上一会儿,同时需要抽一支烟,只有一支烟才能让我平静下来,也只有一支烟才能让我感受到一丝温暖。我摸了摸裤兜,没摸到烟,两个裤兜翻了一遍也没摸到,只摸到了那只打火机。奇怪,我明明记得还有大半盒烟呢,怎么没了?落车上了?还是掉哪里了?我努力想了想,最后終于想起来了。
果然,在背包里摸了几下,我就摸到了“中南海”烟盒上那层光滑的塑料膜。一起摸到的,还有我那串钥匙,那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以及那只同样鼓鼓囊囊的并有些涩手的牛皮纸信封。点上烟,抽了一口,我把那股烟气朝着头顶上的那盏路灯喷出去,又看着它像炊烟一样袅袅地飞升上去,最后一点点地被路灯的光芒吸收掉了。
旁边的那几片落叶,被风裹卷着吹了起来,打着旋儿飞舞到半空中,又飘飘忽忽地落下来。我突然注意到,与那几片叶子一起落下来的还有一片片细碎晶莹的雪花。是的,正像天气预报里所说的那样,下雪了。我裹裹大衣,又摸出来一支烟,续上。
这时候,一辆亮着绿灯的出租车开了过来,在我身边缓缓停下。那个司机降下窗玻璃,操着一口标准的京片子说,走么哥们儿?我摆了摆手。可以肯定的是,他显然看见了我的手势,不过他并没有把车开走,而是继续望着我,一脸不死心地说,走吧您,反正我这也最后一单了,给您便宜点儿。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天说,下雪呢,再不走,等会儿可就没车了啊。我看了看天,又看了看他,然后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哥们儿,去哪?他把车子往路中间开过去。我说,随便!他扭头看了我一眼说,去哪?随便!我又重复了一遍。他把车子缓缓停下来说,您到底去哪?我把烟头扔掉,摇上窗玻璃说,去邯郸。他笑笑说,哥们儿,喝多了?我从背包摸出来一叠钱,冲他晃了晃说,没喝,放心,钱一分也不少你的。他笑了笑,这才把车子又往路中间开过去。我把钱都掏出来,又数了数,一共四万一。这些钱,去到邯郸,去到我们张村集乡东屯村,足够了——就是再折返回来也足够了。我靠窗歪下来,望着玻璃上被哈出的热气晕染成一片金红色的小区里的灯火,望着它们快速闪过来,又快速被甩到身后去。
作者简介
林东林,作家、诗人。著有《迎面而来》《三餐四季》《人山人海》《跟着诗人回家》等各类作品多部。现居武汉,兼任《汉诗》主编助理。
责任编辑 菡 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