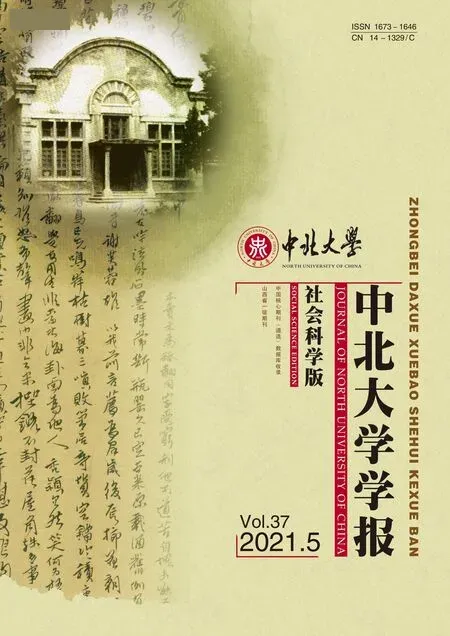后现代崇高美学的救赎
——基于利奥塔崇高美学的分析
杜 立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崇高(Sublime)作为一个典型的美学范畴一直是重大研究课题,从古希腊到康德,崇高理论在各美学家的不断完善中成为一个充满极大象征意义的概念。首先,最早对崇高概念提出解读的是古罗马修辞学家朗吉弩斯(Longinus),在著作《论崇高》(OnSublimity)一书中,他将崇高首先作为修辞学的概念使用,后来才涉及到崇高的效果,即更加注重道德层面的修养和内在心灵的关照,唤起人的自信与尊严;18世纪英国政治家博克(Burke)综合了朗吉弩斯的崇高理论并使其系统化,首次提出“美”和“崇高”的关系,在美学著作《关于崇高与美两种观念根源》(OntheOriginoftheTwoConceptsofSublimityandBeauty)中,他从崇高感产生的心理生理基础以及崇高对象的特质出发对崇高这一范畴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凡是以某种方式令人恐怖或类似恐怖的事物就是崇高的一个来源,并且指出崇高的最高效果是惊惧;受到博克崇高理论的影响,到了康德(Kant),他将崇高上升到哲学层面,明确提出崇高是主体在面对巨大灾难时产生的痛感转化为由肯定主体的尊严而产生的快感。崇高展现出来的不仅是在征服客体时的矛盾状态,更是体现出主体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所体现出来的巨大力量。人在感到崇高时表现出来的不是恐惧而是豪迈、不是害怕而是强有力。除了这三位哲学家之外,此后还有席勒(Schiller)、黑格尔(Hegel)、叔本华(Schopenhauer)和尼采(Nietzsche)对崇高范畴进行更进一步的完善。从古典崇高的发展轨迹中可以看出,各美学家对崇高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在康德这里实现了一种历史性突破。然而,进入后现代,崇高的发展方向发生极大转变,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eancois Lyotard)的崇高思想就是后现代崇高的典型代表之一,利奥塔的崇高分析成为研究后现代崇高美学的重要突破口。
1 不可通约性:后现代崇高美学产生背景
在利奥塔的后现代哲学著作中,无论是《后现代状况》(ThePostmodernCondition:AReportonKnowledge)还是《非人——时间漫谈》(TheInhuman:ReflectionsonTime),解构(deconstruction)始终是贯穿其思想的中心线索,这种解构思想可提炼出三个方面,即在元叙事危机中解构同一性、在语言游戏中解构规则、在非线性时间中解构必然。
1.1 解构同一性:元叙事危机
利奥塔所提倡的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完全相反,他反对总体性,反对以一种确定的原则去解释整个世界。所以,他提出要打破这种单一性陈规的现代性,并且不遗余力地提倡话语的多样性和不可通约性,从而提倡一种异质(1)利奥塔专门对这种“异质”作出解释:在其著作《迥异》(The Differend:Phrases in Dispute,1988年)中,利奥塔提到一个核心词汇:“différend”(异识),它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指语言游戏之间的异质性,即每一种语言游戏都有自己的风格,不同的语位体系(régime de phrase)有不同的规则,这意味着语言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具有诸多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游戏法则。利奥塔认为,对后现代的解构要首先以叙事危机为切入点来展开。
在叙事危机说明之前,首先需要对宏大叙事即元叙事做出解释。在利奥塔看来,元叙事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1]169这种元叙事主要包含两类,一类是哲学的思辨叙事,如德国哲学的思辨叙事,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哲学把所有这些叙事一体化了,在这意义上,它本身就是思辨的现代性的凝聚”[1]167;另一类是政治的解放叙事,如启蒙运动的叙事,基督教的叙事,“通过让灵魂皈依献身的爱的基督教叙事导致人们的解救”[1]167,思辨叙事与解放叙事合称为启蒙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在利奥塔看来,这种叙事本身是由习俗、权威、偏见等构成的,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完全有效的依据和论证方式,它适用于妇女和儿童所喜爱的寓言故事中,这种叙事最多只能开化他们的头脑,却无法赋予自身合法化和有效性。所以,随着科技的高度发达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启蒙现代性所认同的宏大叙事模式开始出现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出现冲突。与叙事相对,科学是在叙事中派生出来的一个变体,由此,“科学凭借所谓方法、论据和逻辑推理的合法性获得了唯一正确的霸主地位,由此导致了除了科学以外的一切叙事知识和人文精神的非合法化和存在的非合理性,而作为科学母体的叙事知识也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整体维系功能,最终导致了自身的叙事危机”[2]266。由此,知识的出现使得后现代状况中科学和叙事具有一定的不可通约性,这样,元叙事因其不具备合法性而随时面临失效的危险。那么,叙事危机消亡后,合法化问题又该如何解决,这依然是后现代状况面临的重大难题。在利奥塔这里,既然以一驭万的叙事已经失效,那么多元性便会随之出现,依据这种多元主义建构后现代社会就要以异质标准来取代总体性、统一性,这反映在叙事上,就意味着起作用的不再是宏大叙事,而是一系列的小叙事;不是某种压倒性的思辨行为的策略,因为后现代人不听信于任何标准和理论权威。由此,他认为历史不是按照某种理论定义的目标去发展,而是无数无序混乱的转折点和小叙事的结合。所以,对于叙事危机的考察,利奥塔没有沿着凯恩斯救赎政策下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去推导,而是从科学知识语用学层面出发,从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那里借来语言游戏思想解构了叙事和社会文化形态。
1.2 解构特权:语言游戏与异教主义
利奥塔认为,由于注重差异性反对同一性,世界的差异最终要通过语言的差异表现出来,正是语言中的分歧才能证明后现代中的差异特征。所以,“‘异质标准’作为利奥塔哲学的重要观念,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反对‘以一驭万’式的绝对化的观念和方法,认为用这种观念和方法根本无法真正说明世界的多样化和丰富性;二是主张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来建立多元话语的语用学,从而保证合法化规则的公正性。”[2]275从这个角度出发,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利奥塔参考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来表达话语的多样共生状态。“后现代知识不以追求总体性为旨归,相反它分裂为各式各样的语言游戏单元,而且在单元之间不存在通用的准则,而是分别表现为真、善、美、效率……等原则。科学只进行自己的游戏,它既不依赖其他话语为它立法,同时也不再担当知识典范的角色,去规范和约束其他知识。”[3]122由于上述讲到的,后现代社会中起作用的是一系列的小型叙事,所以不同类型的叙事应该应用到不同话语中,遵守不同的规则,从而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如描述游戏、指令游戏、叙事游戏等。在利奥塔看来,由于语言的共生性,在语言游戏中绝不存在宏大叙事那种总体对个体的压制,自由的异质标准下的话语类型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并置状态。各种语言都是独立的,没有语言统一体,虽然不同语言之间可以互相翻译,但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的规则不可通约,如果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必然要改变其规则,但规则一经改变就不是原来的语言游戏了。所以,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对语言游戏进行分析,他提出:“……要是没有规则,也就没有游戏;甚至每条规则的微小变化,都会改变游戏的性质。”[4]52正是对各种语言游戏独立性的尊重,解构主义体现在语言游戏中就是解构特权,即“异教主义”(paganism)。利奥塔将没有确切判断标准的认识、伦理和美学状况称之为“异教主义”。“异教主义”的判断不是没有标准,而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异教主义的标准或规范只是具体的,不能被普适化。所以,在语言的连接方面,利奥塔提出一种独特的“衔接法则”(cohesion rule)(2)“衔接法则”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一个完整的语句系统中,一个句子要紧跟另外一个句子,这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语句在进行连接时便会出现不同的连接法则,利奥塔称之为“衔接法则”。但是利奥塔明确总结出:“连接是必然的,但如何连接则不是。”有多少个语句发生,就可能存在多少种“衔接法则”。和“处境”(situation)(3)下一个语位的出现可以将前一个语用事件放到具体的语境之中,以此来确定它的含义和内容,利奥塔称之为“处境”,所以只有当另外一个句子紧跟最初语句出现的时候,“处境”才会发生。理论,以此来证明语言游戏的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预测性。就本质而言,异教主义的本质和叙事危机的本质一样,都是反对总体性、拒绝任何单一的标准,其特点之一是让那种普遍的指令悬置。就理论思想进程而言,利奥塔的“异教主义”可以看作是其后现代思想的初步尝试,也是其崇高美学思想的理论雏形。对语言游戏的极力推崇是利奥塔解构主义的落脚点,所以他的崇高美学也秉承这种原则,破除陈规、主张差异,并且在这个层面上与先锋艺术实现双重耦合,成为后现代崇高美学的载体。
1.3 解构必然:非线性时间观
利奥塔的后现代时间图景不是凭空出现,而是借鉴继承而来,其中所受影响最大的有三人,即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奥古斯丁(Augustine)和胡塞尔(Husserl)。利奥塔首先对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进行研究。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时间被称为流俗时间观,即时间被划分为“回忆、呈现、期待”,它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向度。这种时间观也被利奥塔称为线性时间观,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时间。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时间划分方式,三者是互相影响的,时间(早/晚)被现在确定、现在又受时间(早/晚)的影响,因此,亚里士多德这种意义上的时间反而遮蔽了当下的“现在”,使得“现在”无法作为一种原初生发之物来分配时间。利奥塔对这种流俗时间观进行批判,他反对这种用前后顺序来划分的时间;其次,在借鉴奥古斯丁时,利奥塔发掘出了奥古斯丁将时间赋予主体意识的思想。奥古斯丁第一次把时间与人的记忆、感觉相结合,不仅完成了时间的心灵化,而且还塑造了一种具有广延性的时间结构;到了胡塞尔,他提出“现在”成为一个在场域,这个在场域的核心为原印象,同时存在一个晕结构,这个晕结构是刚刚过去之物(“滞留”)和即刻到来之物(“前摄”)的晕。正是借助于主体意识的这种“滞留”或记忆功能,“‘瞬间’这样一个离散的、转瞬即逝、根本不可把握的时间点被我们把握住了”[5]66。不难看出,现象学在对时间的发掘中,最终发掘出主体,即从时间的发生根源寻找原因。由此,瞬间便随之出现,这种瞬间是处于“已经发生”和“尚未发生”之间。按照胡塞尔的原印象,这种瞬间完全依赖于人的感受性,这也成为利奥塔崇高美学中感性思想的来源。基于胡塞尔的思想,在重写现代性的过程中,利奥塔极力反抗那种程式的线性时间观提倡非线性时间观来强调时间的偶然性与不稳定性,并且寻求高度自由的和不可预测的瞬间。对于利奥塔来说,不存在线状的程式化、系统化的时间,有的只是点状的无中心、零散的瞬间,这种瞬间不可表达,代表一种不可预期的偶然性的存在。他认为,只有这种非线性的、当下的时间观念,才能突出“此刻”,避免“永恒”的和指向“未来”的时间概念对当下的遮蔽。这体现出一种极大的断裂性,这种断裂过程就是解构过程,是同一性消失的过程。当然,在利奥塔的后现代时间图景中,他提出三种时间样式,即物质时间、消费时间和审美式时间,物质时间和消费时间依然没有脱离现代性,是现代性发展的结果,而审美式时间则通过追忆来实现,在审美式的时间里,利奥塔所强调的依然是感觉的瞬时性和当下性,其实是为了抵制物质时间和消费时间这种技术性时间,最终还是对现代性的反抗和重写。
总之,无论是解构同一性、解构规则还是解构必然,都是秉承利奥塔的解构主义来反对确定性和总体性的表现,反对一种陈规对所有知识的整合化倾向,从而尊重各个知识领域的独立性。通过解构的三大方面可以总结出,利奥塔始终反对总体性和同一性,主张共生性和多样性;反对普遍性和确定性,主张此刻性和偶然性。由此可知,利奥塔思想体系的中心就是发现后现代状况的混乱去建立一套适用于这种混乱状态的机制,正是基于这样的解构思想使得利奥塔的崇高美学一经出现就在不确定中走向虚无。
2 虚无:后现代崇高美学的基本特征
从郎吉弩斯到康德对崇高的研究可以总结出崇高的本质,即“从美学范畴而言,崇高……即一种美的对象,具有形象上或精神上的伟大的特点,令人惊心动魄、心驰神往,是为崇高”[6]1。但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美学发生明显转向,其美学形式和美学意味都与现代美学的方向大相径庭,崇高作为美学范畴之一也深受其影响,后现代崇高在后现代美学的浪潮下也几乎成为被后工业同化的产物。较之于传统崇高,后现代崇高视觉感受性优于刻板的词语感受性,图像优于概念,感觉优于意义。利奥塔作为后现代理论家,其崇高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后现代崇高的大致转向,从利奥塔崇高美学的分析基础上不难看出,后现代崇高的基本特征可以大概分为三个特点,即非人性、断裂性和梦幻性。
2.1 非人性
就崇高产生的主体看,崇高感必须发自于人,由主体产生,人是崇高美学中最重要的一维,崇高感是由人的心灵所发生的审美感受,是崇高产生的必然结果,因而崇高是偏于从主体的角度而言的。但是,“后现代崇高不同于浪漫主义的怀旧式崇高,它不去表现失去合法性的普遍理性和宏大叙事,而是在否定当代科技和工业世界的一切之后,以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在非人的现实处境中,寻找属于人的切实的感觉。”[7]在尼采提出“上帝之死”之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又提出了“主体之死”,这里的“主体之死”不是人不存在,而是人的观念的失效。这种观念失效可以理解为,在后现代对传统哲学否定之后,人们的精神信仰逐渐迷失,人们的观念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后其思维方式出现极大偏颇,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下,“消解主体”和“终极意义的消失”成为其典型特征,这是前现代社会和人本主义的现代社会所不可能发生的。后现代主义的信条就是打破一切隔阂的界限,在这个分解过程中,分解的不只是后现代社会的社会文化,更是后现代社会的人。这里的“人”是人本主义意义上的人,是身心完整、具有伟大信仰的人。随着科技发展,工具理性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人本意义上的人成为被资本、科技理性规训与异化之后的非人。主体在支配和奴役的过程中陷入被支配和被奴役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人类似于马尔库塞提到的“单向度”的人,被各种大叙事所构想的那种理性、完整、自律的人都被资本与工具理性碾压而成为非“人”。利奥塔的非人之‘非’就是“指一种拒绝同化与肯定的否定性,非人是为他性、不确定性、非同一性所占据的主体(‘我’与‘我们’),一种极为秘密的、其灵魂被当作人质的非人。”[8]80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崇高的范畴走向“崇高之死”的境地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大环境也将后现代的人带上一条“不归路”。在这样的前提下,崇高的非人化使得传统崇高在后现代发生转向,人的有限性和人的最终消亡失去了传统崇高原本具有的整体的形而上内涵,一切都是偶然和碎片。但是,利奥塔对这种非人并不十分担忧,在他那里,他提倡用先锋艺术来抵抗这种非人化。利奥塔始终主张用先锋艺术来反抗传统,以一种非人对抗另外一种非人,但是这种在无人区寻找人性的举动只是一种自我欺骗,利奥塔的崇高“在消解了作为主体的“人”的同时,还试图实现人的解放或超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幻想和悖谬。”[9]
2.2 断裂性
这种断裂性与其非线性时间观紧密相连。崇高的主体和后现代人不同,具有崇高感的人首先是具有双重人性的完整人和自由人,也是具有生存意识和灵魂意识的人,而后现代人则成了工业物质社会的转换器,启蒙理性被工具理性所击垮,人不断丧失自我意识和情感,这是主体内部认识能力的退化与断裂表现。在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后,人们普遍感到人的存在无意义,后工业社会中的人成了被社会操纵的物品。在利奥塔这里,后现代社会作为一种消费社会具有不确定性和边缘性等特征,正是解构和分解整体性,线性时间的断裂导致瞬间的出现,后现代社会的人完全成为消费中的人群并且仅仅满足于消费带来的瞬间的感官快乐,脱离了宏大叙事束缚的人们对这种感受自然产生一种极大的狂喜感。在主体消逝和客体虚无的状态下产生了恐惧、狂喜、无力为具体情感状态的后现代崇高类型,这种狂喜状态表现的越强烈就越能反映出人内心情感的苍白与无力。后现代学者将这种状态称之为“歇斯底里式崇高”。这必然又要追溯到上述所讲的后现代时间图景。后现代下,“歇斯底里式”崇高的时间体验割裂过去,抛弃未来,仅仅追求当下。詹姆逊也曾经对后现代断裂特征进行探索,并将这种断裂状态下所发生的崇高称为“歇斯底里式崇高”。“歇斯底里式崇高”是针对后现代文化带给人们的庞大冲击而言的,是一种新型的情感体验,这种崇高虽然也注重情感的释放,但只是纯粹使人享受物质消费的娱乐快感,这种情感体验吻合了后现代人的特征,成为后现代崇高的代表。
2.3 梦幻性
梦幻性崇高的出现与后现代社会梦幻的社会氛围密切相关,这种梦幻的后现代社会首先表征为本雅明提到的机械复制时代中摄影技术制造的表象。由于工业文化的日益兴起,后现代世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形象,在复制性的摄影、照相技术的普及背后,人们越来越注重艺术作品的展示价值,这样的消费品迎合了后现代消费群体的消费口味,世界逐渐转化成一个光怪陆离的幻象世界。在这样的奇观社会中,表象的出现造成真实和本源的缺失,人们用符号来代替真实,并且沉浸在这样一个由摹拟体所勾勒出的世界里,疯狂地占有这些非真实化形象。人们“通过占有一个对象的酷似物、摹本或占有它的复制品来占有该对象的愿望与日俱增”[10]182。也就是说,这种梦幻性首先是客观世界开始走向虚无。这种客观世界不再是古典主义的崇高客体——庞大的自然,取而代之的是科技凭借摄影艺术、计算机等机械装置为我们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梦幻世界。后现代主体作为工具理性支配的傀儡,一方面追求物质欲望,一方面又想超越自身精神的虚无,但是问题在于,后现代主体无法想象也难以把握这样庞大的梦幻世界,在这样的状态下,他们只能通过幻象机制遮蔽真实社会中无法满足的欲望所带来的匮乏和焦虑,以保持自身的统一以及自身与社会的统一。因此,先锋艺术以及崇高美学都致力于取消线性时间,取消未来,“崇髙的感觉就是这种匮乏的名称”[5]107
总之,这三种后现代崇高特征均是在利奥塔解构主义基础上所反映出来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利奥塔的崇高美学是在基于后现代主义浪潮下提出的新的构想和方案,但是其崇高仅仅只是一种关于自由或试图超越现代性的构想,甚至终将会走向虚无。
3 可通约性:后现代崇高美学的救赎
利奥塔的后现代崇高是在其后现代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不可通约性本质使得利奥塔的后现代理论解构一切,其崇高也只是表现不可表现之物,从而一改传统崇高的内涵。但是,利奥塔的后现代崇高只是传统崇高的移花接木,其崇高理论仅仅是借用传统崇高的外衣,填充的则是后现代理论的碎片。所以,要还原面目全非的后现代崇高,必须要依据后现代社会文化进行崇高的自我救赎,实现崇高与后现代主体、后现代艺术、后现代文化的可通约性,从而改变后现代崇高的怪诞性质,实现崇高范畴的全新演绎。
第一,实现崇高与后现代主体的可通约性。“人是天地万物本身得以显示其意义的一个空隙,没有它,天地万物被遮蔽,是漆黑一团而无意义的。”[11]134从古希腊至康德对崇高的研究中不难看出,崇高的发展轨迹始终遵循人的生命精神。所以,要挽救崇高,实现崇高的自我救赎,就要从根源上挽救单向度社会下血肉双缺的人,反映在美学上就是将人的心灵提纯,使其生命圣化。“生命圣化之所以能够产生崇高,就是因为它内中暗含着:人作为类的存在具有不断追求进步、不断走向完善的坚强韧性的生命意识。”[6]152在崇高感中,崇高中的主体性并未因敌对的力量而消散,反而因敌对的力量而升华。基于这样的崇高本质,崇高作为一个美学范畴与人的精神生命息息相关,崇高的重生也就是人的生命意识和精神自由的再次觉醒,使主体最终产生净化或升华主体的精神自由。所以,主体产生崇高感的必然要求是人的存在,即有信仰有灵魂的主体的存在,崇高的找寻就是要重新找回人自身,找回被后现代主义拆分甚至抛弃了的主体意识,实现崇高与主体之间的可通约性。所以,通过生命圣化来净化崇高的内在灵魂,使其在后现代的杂乱无章中寻找出自身的发展轨迹,成为崇高进行自我救赎的核心。
第二,实现崇高与后现代艺术的可通约性。艺术是使人能够获取“不自由中的自由”为数不多的领域之一,艺术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可能的。然而在后现代社会中,艺术不可能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洁身自好。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涉及音乐、美术、建筑、电影等一系列艺术表现形式,主要表现为精神维度的消逝,后现代艺术充满了奇奇怪怪的价值观,带有颓废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特征。以绘画作品为例,与现代绘画相反并排斥的后现代作品都在后现代主义氛围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理由。比如被视为后现代艺术之父的马赛尔·杜尚(Marcel Duchamp),他总是选用最常见的日用品将其转化成艺术品。《泉》就是杜尚现成物中最知名的作品,一件普通的白底白瓷小便池通过被取消有用功能而被转变成艺术品;又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波普艺术,如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二十五个颜色的玛丽莲·梦露》,不断重复的梦露的肖像好像在诉说她作为消费产品的身份。由此可见,后现代的艺术形式表达更为直接,也更加关注艺术家对时代的敏锐感受,作品表达风格也更具个人性、时代性和包容性。后现代艺术在对媒介创造过程中将审美问题悬置起来,对“美”这一宏大观念不再过分关注,而是更强调社会文化背景后思想观念对当下的意义,注重对社会问题的阐释,它只对生活感兴趣,“美”不再成为判断艺术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准,从而将解构观念更多介入到艺术本体的变化中,跳出高雅艺术的金字塔。换言之,后现代艺术追求一种既新又旧、既雅又俗、既大众又现代化的多元样式。但是,这种被拆分得七零八落的后现代艺术溢出了艺术的容器,它仅仅用来证实艺术家的社会作用,却无法立刻获得大众认同,从而造成艺术的孤立与断裂,艺术家本身也很难得到社会认可。也就是说,文化工业颠覆了艺术解放人的作用,而只突出其消遣功能,用来减轻在资本主义剥削下的劳动者的疲惫。这种颠覆了的艺术形式不仅没有尊重对自由和和谐的向往,反而把不自由描绘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
在后现代社会这样特殊的环境下,在现实和对自由渴望的矛盾时,艺术必须两者兼顾,所以人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艺术。这种艺术形式必须要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主体自由,这是艺术得以形成的首要条件,这里的主体不止是创作主体,还包括欣赏主体,这两种主体要在同一种艺术作品中实现一种自然的融合和默契感,也就是要实现创作者与欣赏者的可通约性。创作主体和欣赏主体首先是不被工具理性侵蚀的完整人,这一点可以通过生命圣化实现,其次还要心灵相通,创作者通过艺术品这个载体传达出的情感要能被欣赏者准确地接收,而不是人云亦云般地跟随大众群体复制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仅是艺术家本人的崇高情感,也是欣赏者崇高情感在艺术中的反映;二是艺术要还原它固有的轻松感。正是在艺术的轻松中,主体性第一次为人所知并变得有自我意识。在轻松中,艺术摆脱了无谓的纠缠并回归自我。对于艺术来说,这种轻松感是获得快乐与自由的来源。也就是说,随着时代发展,艺术也会具有时代特征,但艺术本身的轻松特征是不会消失的,正是这种轻松感才能冲破后现代的系列弊病,这种巨大张力与具有超越性质的崇高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重逢。
第三,实现崇高与后现代文化的可通约性。“文化传统是使不同文化中的崇高的不同含义得以可通约的一个重要因素。”[6]12后现代作为一种存在形式,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其整体文化氛围主要体现为消费文化,后现代社会是以复制技术为典型特征的消费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崇高也成为了可消费的情感,缺乏深度,随意挥霍,后现代将崇高从天堂拉下凡尘,传统崇高黯然失色。这种情感与其看成崇高,倒不如说只是一种崇拜,对工业社会具有展示价值的商品的崇拜,这种崇拜只是一种简单的臣服,仅仅是在消费的过程中获得感官刺激,并非从主体强大的心灵中获得的力量。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也曾强调,在后现代社会,对艺术也从追求“膜拜价值”转向“展示价值”。这种现象说明,当被移植到后现代的文化土壤时,传统崇高已经无法再继续生长,当崇高进入到后现代时,传统崇高内涵无法解释后现代的特殊现象。从古希腊到康德的崇高观可以看出,他们的崇高均是建立在各自生存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背景下所提出的不同崇高,由于具有的相位不同,彼此之间的崇高受到文化影响也产生极大差异,为此,后现代崇高应该“立足文化情境,从不同的文化整体观念中探寻文化中的人关于崇高的观念,实现崇高在文化上的可通约性,使不同文化之间的崇高概念可以相互交流,也使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崇高的不同相位能够整合在相同的崇高观念之下,实现崇高问题研究的普遍性、理论化的表达。”[6]14而要实现这种可通约性必须重新树立理性的地位,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抗衡成为实现后现代崇高与后现代文化通约性的关键。
后现代下的人们之所以成为工业经济的傀儡,源于人们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产生眩晕,人只注重感官刺激造成了道德感消失,虚拟支配真实让人的感性与理性产生断裂。由此,实现后现代崇高与后现代文化的可通约性就是通过价值理性把人从工具理性的压制中解放出来,从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幻象中拯救自身,减轻后现代文化的迷幻性。所以,理性需要在这样的消费社会中重新发挥作用,还原在场感,重构社会责任感,“后现代被压制的东西本来就是人的理性的一部分,是人达到绝对理念所必须的东西。把这些被压制的东西释放出来,那么工具理性就会得到修正,人的理性就会得到进一步完善。”[12]置身于后现代语境下的崇高不可能完全还原为传统崇高的内涵,但可以传承其理性的超越作用来与工具理性相抗衡,从而整合被拆解的人的认识能力和社会秩序,实现后现代崇高与后现代文化的对话。
4 结 语
后现代崇高是一种“人造的崇高”,这个时代正在经历崇高性的高度分裂化,这种崇高令我们灵魂收缩,神经震颤。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崇高是美学研究甚至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概念之一,后现代崇高必须在后现代语境中寻找自我救赎的途径,实现崇高范畴的全新演绎。作为后现代的人,我们不仅要保持崇高对彼岸世界的探索,还要保留崇高带给我们的对日常生活批评和反思的距离,在后现代的浪潮中坚持崇高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