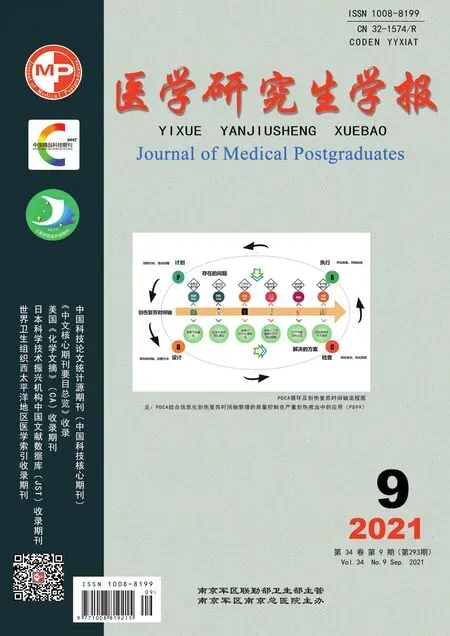c-Myc与肿瘤放射敏感性关系的研究进展
林兴华,秦性璋综述,赵玉婉,柳建军审校
0 引 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对肿瘤认识的加深,肿瘤的治疗方法也变得多种多样,如手术切除、化疗、放疗、免疫治疗等。放射疗法(radiation therapy,RT)是治疗人类癌症的主要方式之一,其应用于临床的时间达一个世纪之久,并且被确立为治疗恶性肿瘤的一种有效的局部治疗方法。然而,放疗抵抗是RT治疗癌症疗效的重要障碍之一。产生辐射抵抗的机制有很多,主要包括DNA损伤修复、细胞周期阻滞、癌基因与抑癌基因的改变、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的变化、自噬、肿瘤干细胞、肿瘤代谢等[1]。因此,大多数肿瘤细胞会产生放射抗性,导致最终放射治疗失败。将基因治疗与放射治疗相结合一直是放射肿瘤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其能够降低放射剂量、减少射线对正常组织的损伤及增强放射治疗的效果[2]。c-Myc是一种致癌转录因子,是人类致癌过程中最常见的原癌基因之一,与MYCL、MYCN均属于MYC家族的成员,分别编码c-Myc、L-Myc和N-Myc[3]。MYC的C末端区域包括碱性区域/螺旋-环-螺旋/亮氨酸拉链(BR/HLH/LZ)基序。MYC家族成员通过相同的BR/HLH/LZ基序与MAX结合,形成一个异二聚体DNA结合复合物,这是DNA-蛋白质相互作用所必需的,并通过与位于靶基因转录调节区的保守的E-box DNA序列(CACGTG)结合来激活靶基因的转录[4]。c-Myc首次被发现是从致癌逆转录病毒的研究中鉴定出来的v-Myc癌基因的细胞同源物[5]。不久后,在Burkitt淋巴瘤中也发现c-Myc持续受到染色体平衡易位的改变,这标志着其是真正的致癌基因[6]。此外,c-Myc位于许多促生长信号转导通路的交汇处,是许多配体-膜受体复合物下游的即时早期反应基因,如Notch和EGFR信号通路,这说明了c-Myc对癌细胞生长调节的中心作用[5]。大量证据表明,c-Myc在多种类型的恶性肿瘤中被异常激活[7],其高表达往往与不良预后相关。c-Myc在肿瘤细胞的生长、细胞周期分布、DNA损伤修复、转化、自噬、肿瘤干细胞的形成以及基因组的维持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抑制c-Myc可能是促进肿瘤放射增敏的一种有价值的新方法。本文主要就靶向抑制c-Myc导致放射增敏的潜在机制及方法作一综述。
1 c-Myc影响放射治疗敏感性的潜在机制
1.1 c-Myc与DNA损伤修复电离辐射(ionizing radiation,IR)被广泛应用于癌症的治疗,因其具有直接损伤DNA的能力,从而导致细胞的死亡,其中DNA双链断裂损伤(DNA double-strand break damage,DSB)被认为是辐射介导的细胞的主要致命性损伤。辐射后细胞是存活还是死亡,取决于细胞如何通过细胞周期阻滞或启动DNA修复来对细胞毒性DNA损伤作出反应。癌细胞有效识别DNA损伤并启动DNA修复途径的能力是导致其产生放疗抵抗的重要原因;此外,由于某些DNA修复基因的遗传或体细胞突变,癌细胞将比正常细胞更多地依赖未受影响和正常运作的DNA修复机制。因此,通过靶向DNA修复途径很有可能增强IR对癌细胞的毒性作用[8]。
ATM和ATR激酶在DNA损伤反应(DNA damage response, DDR)中起着关键作用,并通过ATM/ATR DNA损伤检查点将感知DNA损伤与DDR效应联系起来,调控细胞周期进程和DNA修复。在食管癌(esophageal cancer , EC)细胞中,电离辐射后c-Myc的上调促进了ATM和ATR的磷酸化,从而激活了DNA损伤反应[9]。DSB是电离辐射诱导的最严重的DNA损伤,其主要由两种不同的分子修复途径:非同源末端连接(non-homologous end joining, NHEJ)和同源重组(homologous recombination,HR),在癌细胞中被异常激活。这种异常的DSB修复基因激活是化疗和放射抵抗的重要原因之一[10]。c-Myc通过与DSB修复基因的启动子结合而在DNA损伤修复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基因包括NBS1、Ku70、Rad51、BRCA2、Rad50、Rad54l和DNA-PKcs等。抑制c-Myc介导的DNA修复可引起基因组不稳定性和有丝分裂损伤,从而促进肿瘤细胞对抗癌药物和辐射敏感[11]。在前列腺癌中也证实敲除c-Myc能够通过抑制HR修复途径的NBS1、RAD1、SMC1A及NHEJ修复途径的XRCC6、PRKDC和PNKP等基因的mRNA的表达水平参与DNA损伤修复的调节,从而导致肿瘤细胞放射增敏的作用[12]。在胚胎横纹肌肉瘤(embryonal rhabdomyosarcoma,ERMS)细胞中,抑制c-Myc通过激活内源性凋亡信号通路诱导细胞凋亡,并且通过促进DNA DSB损伤和抑制DNA-PKc(NHEJ通路)和RAD51(HR通路)等修复蛋白的积累而增强ERMS细胞的放射敏感性[10]。此外,c-Myc还通过调节错配修复基因的表达介导DNA损伤修复。错配修复消除了碱基错配和插入-缺失循环,从而显著提高了DNA复制的准确性和基因组的稳定性[8]。MLH1和MSH2蛋白是错配修复途径的核心蛋白,抑制MLH1和MSH2蛋白阻止了放射后DNA复制过程中发生的碱基错配校正,从而使细胞更容易受到辐射而发生凋亡。在黑色素瘤细胞中,c-Myc下调通过抑制MLH1和MSH2错配修复蛋白并激活p53非依赖的凋亡途径来降低凋亡阈值,从而增加细胞对γ辐射的敏感性[13]。c-Myc能够通过调控DNA损伤反应、同源重组修复、非同源末端连接修复以及错配修复等多种途径参与肿瘤细胞放射抵抗的形成,因此,通过抑制c-Myc介导的DNA损伤修复途径增强肿瘤细胞的放射敏感性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1.2c-Myc与细胞周期分布电离辐射主要通过诱导DNA损伤的方式杀死肿瘤细胞,其中DNA双链断裂通常被认为是最严重的DNA损伤。虽然同源重组和非同源末端连接等修复机制是肿瘤细胞对于电离辐射诱导的DNA双链断裂损伤的有效防御机制,但细胞周期调节可能才是决定电离辐射敏感性的最重要因素。细胞周期阶段也决定了细胞的相对放射敏感性,细胞在G2-M期放射敏感性最高,在G1期敏感性较低,在S期的后半阶段敏感性最低[14]。细胞周期的进程由高度保守的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家族控制。这些激酶是由一个催化亚单位(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cyclin dependent kinase,CDK))和一个调节亚单位(细胞周期蛋白)组成的异源二聚体。c-Myc癌蛋白对于细胞周期的刺激至少是通过三种机制实现的:细胞周期蛋白和Cdks的上调、CDK抑制剂p15、p21及p27的下调[15]。
Cdk1和Cyclin B1(细胞周期蛋白B1)是细胞从G2期向有丝分裂(G2/M)过渡的一个主要检查点,它们控制着有丝分裂的大部分启动和进展过程。YANG等建立了敲除c-Myc基因的B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lineage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B-ALL)细胞模型(Raji-KD),并且证实c-Myc的敲除能够通过抑制Tip60(60kDa Tat-相互作用蛋白)介导的特定染色体区域的组蛋白H4乙酰化,下调与G2/M期转变相关的基因的表达,包括Cyclin B1和Cdk1,从而导致Raji-KD细胞明显的G2/M期阻滞[7]。Cdc25A是一种公认的CDK激活剂,在调控细胞周期进程中起重要作用。此外,Cdc25A还能与Cyclin B1结合,激活Cdc2/Cyclin B1复合物,过表达Cdc25A的细胞可加速进入有丝分裂,而磷酸酶失活的Cdc25A突变体的表达细胞则延迟进入有丝分裂。c-Myc基因敲除可导致Cdc25A的表达降低,并显著降低Cyclin B1和Cdc2的活性,从而增强辐射诱导的G2/M期阻滞,并增强LNCaP细胞对IR的敏感性[16]。c-Myc不仅通过激活或诱导细胞周期蛋白和CDK的表达来促进细胞周期进程,还通过下调或损害一组充当细胞周期制动器的蛋白质的活性来促进细胞周期。P27、P21和P15都是CDK抑制因子,在细胞周期的调控中起着重要作用。p27必须在Thr-187位点被磷酸化才能被SCFSKP2泛素连接酶复合物识别,从而被有效泛素化降解。c-Myc通过三重效应促进p27降解:①诱导Skp2表达,这是p27泛素化和降解的主要途径;②通过上调其细胞周期蛋白伴侣来激活Cdk2;③激活Cdk1[15]。此外,在淋巴瘤细胞和骨肉瘤细胞中,c-Myc基因的抑制均导致了P21蛋白的上调,导致G2/M期细胞周期阻滞[7,17]。
1.3c-Myc与肿瘤干细胞肿瘤干细胞(cancer stem cells,CSCs)具有与胚胎或成体干细胞相关的能力,特别是自我更新和分化能力[18]。许多肿瘤的特点是能够在多代中保持稳定的CSCs数量。这归因于CSCs具有不对称细胞分裂的能力,其中一个子细胞保持自我更新能力,而另一个子细胞分化为非CSCs,构成了肿瘤的主体部分。大量研究表明,即使在多次连续移植后,CSCs仍能通过不对称的细胞分裂保持选择性或排他性自我更新的能力,并保持稳定的CSCs比例[19]。
有效的肿瘤治疗需要根除肿瘤干细胞,因为其可支持肿瘤的再生,从而导致复发。然而,根除CSCs是困难的,因为其往往是耐药的。CSCs可通过休眠、增加DNA修复、药物外排、减少细胞凋亡以及与微环境相互作用来介导治疗抵抗。此外,CSCs可能作为移行性CSCs经历上皮间充质转化(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formation, EMT)和转移[18]。c-Myc癌基因在正常干细胞和CSCs的自我更新中起重要作用[19]。c-Myc诱导的致癌和表观遗传重编程导致肿瘤细胞获得与CSCs相关的特性并诱导肿瘤内异质性[20]。
RARS-MAD1L1是一种融合基因,Zhong等[21]的研究表明,RARS-MAD1L1可能部分通过激活FUBP1 / c-Myc途径促进了鼻咽癌的发生,并诱导了化学和放射抗性以及类似CSC的特性。FUBP1的沉默或c-Myc抑制剂的使用消除了RARS-MAD1L1诱导的CSC样特征并降低了c-Myc下游靶标ABCG2蛋白的表达水平。ABCG2是ABC转运蛋白家族的一员,通过促进药物外排在CSCs的化学耐药性中起重要作用。雷公藤内酯(C1572)是一种小分子天然产物,能够通过蛋白酶体依赖性机制显着降低c-Myc蛋白水平,从而选择性地耗尽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TNBC)细胞中的耐药性CSCs。敲除c-Myc复制了C1572的CSCs耗竭效应,并诱导TNBC细胞衰老。这里表明c-Myc的抑制可能通过诱导干细胞亚群的衰老来减少CSCs[22]。缺氧诱导因子-2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2α, HIF-2α)是一种已知的能维持干细胞健壮性的转录因子,负向调节p53的表达和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水平以赋予干细胞自我更新能力。在T细胞急性淋巴细胞淋巴瘤中,c-Myc通过与HIF-2α启动子结合并激活HIF-2α的转录,从而维持CSCs的排他性自我更新,并且重编程因子Nanog和SOX-2也参与了c-Myc调控HIF-2α转录的作用。此外,在原发性T细胞淋巴瘤的ABCG2+CSCs和ABCG2-非CSCs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19]。
1.4c-Myc与肿瘤微环境照射血管会引起剂量依赖性的血管破坏,特别是影响微血管,导致肿瘤血管无法正常供氧。缺氧在肿瘤的放疗抵抗中起着关键作用。放疗后,缺氧会减少活性物质和细胞毒性物质的产生,如ROS,并最终防止肿瘤细胞发生无法修复的DNA损伤,减少肿瘤细胞的死亡。此外,缺氧还上调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 HIF-1α),HIF-1α活性升高是放疗后预后不良的独立预测因素[23]。HIF-1α属于碱性螺旋-环-螺旋转录因子家族中的Per-Arnt-SIM子家族[9]。据报道,在低氧条件下,HIF在各种癌细胞中过表达,调节一些基因的表达,这些基因涉及血管生成、肿瘤生长、转移、代谢重编程、放化疗抵抗等。而当缺氧细胞复氧后,HIF蛋白迅速降解,半衰期小于10 min[24]。在氧气充足的细胞中,脯氨酸羟化酶(proline hydroxylase, PhD)通过羟基化HIF-1α的氧依赖降解结构域,导致其随后的泛素化蛋白酶体降解,亚铁是PhD的底物之一。Oh等[24]研究发现,抑制c-Myc通过减少缺氧的癌细胞中线粒体的ROS的产生和随后ROS介导的亚铁向三价铁的转变来促进PhD活性,从而增加了HIF-1α的降解。在EC细胞中,沉默c-Myc能够通过抑制HIF-1α的表达增强其放射敏感性,并且HIF-1α的过表达逆转了c-Myc沉默对EC细胞辐射敏感性的增强作用[9]。综上,c-Myc能够通过稳定HIF-1α的表达介导肿瘤细胞的放射抗性,抑制c-Myc能够通过促进HIF-1α的降解来增加肿瘤细胞的放射敏感性。
放射治疗后,肿瘤细胞的免疫原性细胞死亡导致有效的抗肿瘤免疫系统的激活,然而,这仍然可能受到增强的抑制性免疫细胞的限制。目前免疫调节和放射治疗相结合的主要策略在于克服肿瘤及其微环境对适应性免疫反应的持续抑制。有效的T细胞激活需要抗原提呈和适当的抗原提呈细胞的共同刺激。调节这一过程的几个分子,包括CTLA-4、OX40、PD-1和CD137,可能是放射治疗诱导免疫启动后免疫调节的重要靶点[23]。其中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1, PD-1)是一种重要的免疫抑制分子。PD-1可通过负向调节免疫系统对人体细胞的反应,以及通过抑制T细胞炎症活动来调节免疫系统并促进自身耐受。一方面,PD-1的作用可预防自身免疫性疾病,但另一方面也可防止免疫系统杀死肿瘤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 PD-L1)是PD-1的配体之一,在多种肿瘤中高表达。PD-L1与存在于活化的T细胞表面的PD-1结合后可诱导T细胞凋亡、失能、耗竭,进而抑制肿瘤抗原特异性CD8+T细胞的激活、增殖和抗肿瘤功能,实现肿瘤免疫逃逸[25]。放射后TME中T细胞上PD-1和PD-L1的表达增加导致CD8+T细胞的功能衰竭,导致无效的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23]。
c-Myc能够与PD-L1和CD47(分化簇47)基因的启动子直接结合,促进其转录。Stephanie C. Casey等人首先建立了一个c-Myc诱导的T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T cell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T-ALL)Tet-off转基因小鼠模型,发现当c-Myc被敲除时,PD-L1和CD47的表达迅速下调,增强抗肿瘤免疫应答;而过表达PD-L1或CD47能够挽救敲除c-Myc对于肿瘤生长的抑制作用。与其一致的是,在T-ALL细胞系、Tet-off转基因小鼠肝细胞癌模型、肝癌细胞系HepG2、黑色素瘤细胞系SKMEL28和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系H1299中,发现抑制c-Myc均能降低PD-L1和CD47 mRNA和蛋白的表达水平。此外,通过检索了来自人类原发性肿瘤的可公开获得的基因表达数据库提示,在人肝癌、肾细胞癌和结直肠癌中,c-Myc的表达与PD-L1和CD47的表达显著相关。因此,c-Myc在多种肿瘤类型中调节PD-L1和CD47的表达,c-Myc过度表达可能是肿瘤细胞上调免疫检查点调节因子表达从而逃避免疫监视的机制之一[26]。Han等[27]开发的c-Myc抑制剂361(MYCi361)能够调节肿瘤免疫微环境并增强抗PD1免疫疗法 。经c-Myc抑制剂361处理后的小鼠肿瘤CD3+T细胞浸润增强,肿瘤细胞上PD-L1表达上调;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显示,治疗后肿瘤组织中总CD3+细胞百分率增加,CD3+CD4+和CD3+CD8+T细胞、表达干扰素γ的CD4+和CD8+T细胞、表达肿瘤坏死因子α的CD8+细胞、树突状细胞和NK细胞均增加。
1.5c-Myc与代谢代谢重编程,即肿瘤细胞在面对缺氧和营养不足的环境时所做出的适应性代谢变化,近年来已发现其是癌症的标志之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癌症的发展与葡萄糖代谢的改变密切相关。此外,现已证明葡萄糖代谢的改变有助于抗肿瘤治疗的适应性抵抗[27]。葡萄糖代谢的异常变化通过增强自噬、激活DNA损伤修复、促进外泌体分泌及诱导缺氧环境形成等方式调节癌症的放化疗抗性。然而,参与葡萄糖代谢变化的分子机制是复杂的。肿瘤微环境的变化、癌基因的激活和抑癌基因的失活都会使细胞代谢紊乱,最终导致糖代谢异常[28]。
事实上,原癌基因c-Myc在葡萄糖代谢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c-Myc的突变或过表达能够诱导癌症细胞的代谢表型向糖酵解转化[29]。此外许多参与葡萄糖代谢的基因已被证明是 c-Myc 的靶基因,如葡萄糖转运蛋白1、磷酸葡萄糖异构酶、磷酸果糖激酶、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磷酸甘油酸激酶和烯醇酶等。c-Myc还通过上调乳酸脱氢酶 A以生成NAD+,诱导乳酸过量产生[30]。在鼻咽癌中,c-Myc通过介导LMP1所诱导的己糖激酶2上调,从而显著增强糖酵解,并且敲低己糖激酶2能有效增强过表达 LMP1的鼻咽癌细胞对辐射的敏感性[31]。此外,c-Myc还能调节谷氨酰胺代谢。c-Myc通过增加谷氨酰胺转运蛋白和谷氨酰胺酶的表达,促进谷氨酰胺的摄取,增强谷氨酰胺分解代谢[32,33]。谷氨酰胺代谢增强后可通过解除G2/M期阻滞[34]、促进DNA修复和核苷酸合成[35]、调节氧化还原平衡[36]等途径增强肿瘤细胞对放射治疗的抗性。靶向细胞葡萄糖代谢或谷氨酰胺代谢可能会改善癌症对放射治疗的敏感性。
1.6c-Myc与自噬自噬通过双膜囊泡吞噬细胞蛋白质和细胞器以输送到溶酶体融合形成自噬溶酶体,并降解其所包裹的内容物。自噬发生首先激活ULK1复合物,随后诱导囊泡成核,囊泡的双膜不断增长使囊泡伸长最终形成自噬体,自噬体再与溶酶体融合,产生自噬溶酶体,最后囊泡内的产物被降解,大分子前体被回收或被用于参与代谢途径[37]。
在放射治疗中,自噬对肿瘤细胞的影响有双重作用。一方面,自噬通过回收和降解非必需的或受损的蛋白质和细胞器为细胞提供营养支持,导致放疗抵抗,也称为保护性自噬;另一方面,过度激活的自噬通过溶酶体消化功能导致细胞死亡,从而引入除细胞凋亡之外的另一种细胞死亡途径,称为自噬细胞死亡。虽然这两种方法均已被证明在治疗实体瘤方面是有效的[38],但是目前对于抑制保护性自噬或者诱导自噬细胞死亡哪种方法更加有效仍然是有争议的。现已证明高表达的c-Myc能够增强保护性自噬,促进肿瘤细胞的生长和治疗抵抗[39,40]。敲低c-Myc后通过激活JNK1-Bcl2通路抑制自噬体形成,从而抑制自噬[41]。在前列腺癌细胞中,保护性自噬会增强肿瘤细胞的放射抗性,而抑制c-Myc的表达能减弱保护性自噬途径,从而提升前列腺癌细胞的放疗敏感性[42]。
2 靶向抑制c-Myc的方法
目前尚未有文献证明有药物能够直接靶向作用于c-Myc,这主要是由于c-Myc本身的特殊性。首先, c-Myc是一种固有的无序蛋白(inherently disordered protein, IDP),在其延伸的非结构化表面缺乏能够被常规小分子药物有效靶向的特定活性位点,因此很难使用类似于激酶的策略来从功能上抑制其活性。其次,定位于细胞核中的c-Myc也限制了一些治疗方法的使用,药物既需要穿透细胞膜又需要有效地转运到细胞核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因此,研究间接消除c-Myc致癌功能的替代方法是目前的研究热点。
目前靶向抑制c-Myc的方法主要有3种:第一,靶向抑制c-Myc的转录和翻译。通过抑制与c-Myc相互作用并影响其活性的许多上游和下游蛋白质的活性间接调节c-Myc表达。例如,通过靶向抑制BRD4和CDK7和(或)CDK9能够大大降低c-Myc的表达,伴随着c-Myc目标基因的广泛转录下调。第二,瞄准c-Myc的降解机制。c-Myc蛋白的稳定性受几种机制的调节,最突出的机制是有序的磷酸化级联反应,其中c-Myc的丝氨酸62(PS62)位点首先被ERK、CDK和JNK等激酶磷酸化,随后GSK3β将c-Myc苏氨酸58(PT58)位点磷酸化。c-Myc PT58被E3泛素连接酶识别,并被26S蛋白酶体降解。Han等[43]开发出的c-Myc小分子抑制剂361和975能够通过促进T58上c-Myc的磷酸化来促进c-Myc的降解。第三,阻断c-Myc / Max复合物的形成或抑制c-Myc / Max复合物与E-box DNA的结合。c-Myc首先与Max结合,形成异源二聚体,随后,c-Myc / Max复合物通过其基本区域与位于靶基因转录调节区的保守E-box DNA序列(CACGTG)结合来激活转录。目前已经鉴定出许多常规的小分子或多肽抑制c-Myc / Max二聚化或与DNA结合。例如,IIA6B17、10,058-F4、10,074-G5、Omomyc等[44]。
3 结 语
c-Myc作为一种公认的原癌基因,其在恶性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受到了许多肿瘤研究者的关注。已经证实抑制c-Myc可增强肿瘤细胞的放射敏感性,抑制c-Myc结合放射治疗可能是增强患者治疗效果和预防肿瘤复发的可行方法。然而,由于c-Myc本身的特殊性,目前尚未有能够直接靶向抑制c-Myc的药物,因此必须开发更特异性的c-Myc药理抑制剂,以达到更好的临床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