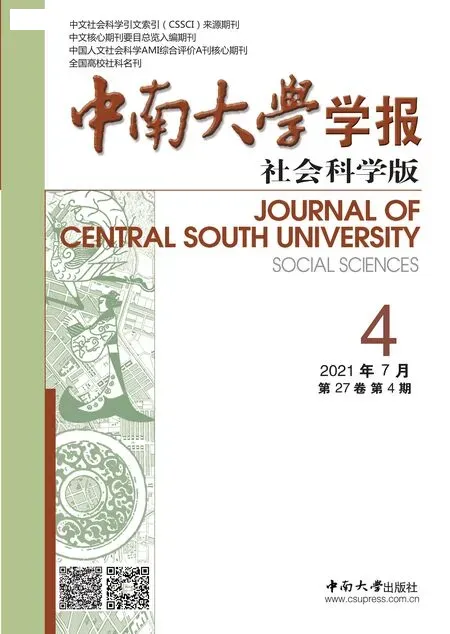吕留良“奇横”说发微
张振谦
(暨南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632)
吕留良(1629—1683),字庄生,号东庄,又字用晦,号晚村,崇德(今浙江桐乡)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时文评选家,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顾炎武将他与黄宗羲齐名并举,谓“梨洲、晚村,一代豪杰之胤,朽人不敢比也”[1](74)。但因吕氏故世四十年后为文字狱牵连而惨遭剖棺戮尸,其著述也遭清廷尽行禁毁,故关于他的研究长期以来未能有效展开。民国后,经梁启超、钱穆、容肇祖等人的阐幽发覆,吕氏的思想学说才重新被提及,其诗文作品才得以刊布。据俞国林编《吕留良全集》统计,吕留良现存诗歌544 首,文233 篇,评选诗文集20 余种。近人邓之诚曾称:“以诗文论,诚(黄)宗羲劲敌,唯史学不如。”[2](244)今人对其文学成就研究不多①。吕留良还发表了大量颇具影响的论文之语②,他在诗文批评中大力标举“奇横”说,具有独特的见解。“奇横”说成为清代文学批评常用术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然而却未引起当代研究者的关注。有鉴于此,本文对吕留良“奇横”说的生成和背景、美学内涵、诗文创作实践及其影响予以考察。
一、标举“奇横”的时代意义
“奇”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自六朝以降,产生了诸多子范畴,蔚为大观,学界已有深入研究③。晚明政治黑暗,社会思想、文艺创作中的尚“奇”风气颇为流行。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曾云:“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3](848)他认为好的文章一定要具备新奇且自然天成的艺术特征。万历三十九年(1611),汤显祖在为丘兆麟文集所作的《合奇序》中写道:“予谓文章之妙不在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4](1532)不久,陆云龙评点该序时首次提出“奇横”一词,“序中是为奇劲,奇横,奇清,奇幻,奇古,其狂言蒐语不入焉,可知奇矣”[4](1533)。对于“奇横”这一批评术语,陆氏虽有创立之功,但惜乎仅此一言,并未加以论说。
大约三四十年后,吕留良在时文评点中大力标举“奇横”说。据笔者统计,在吕氏文论中,用“奇横”二字者共七处,多见于时文批评。如:
文之奇横者,以其变化于法度之中,不可捉搦而自合,乃为真奇横耳,非蔑弃绳尺之谓。文之有体,犹人之有头目手足也,头未讫而手已生,目下降而足上出,岂复成形貌哉
文章之奇横必须暗合法度,若蔑弃法度,就如同头手、目足位置颠倒。吕留良评论时文既尚奇重变,又济之以法,强调“先辈极奇横文,于法律定不走作”[5](2028)。“奇”与“法”原本是两个相对的美学范畴,代表文学创作中的自我与规范。刘勰较早提出了“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文心雕龙·通变》)的通变观和审美标准。宋人阐释韩愈提出的“奇而法,正而葩”(《进学解》)时说:“《易》《诗》之体尽在是矣,文体亦不过是。……奇而有法度,正而有葩华,两两相济,不至偏胜。”[6](73-74)唐宋以来,“奇而法”这种既合乎法度又富于变化的美,逐渐成为中国文艺创作的最高理想。韩愈所谓“醇而后肆”(《答李翊书》)、苏轼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书吴道子画后》)均是“奇而法”这一至美境界的形象化表达。吕留良继承了前人对新奇和法度关系的看法,要求以古文的基本精神为法式,以作家自身的新奇感受和横溢情思为导引,贯通古今,以达到奇正相参、情法兼备的审美境界。他所说的“文至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之处,直是绝迹而行,起灭由我,而规矩神明,无不并至,斯最上之品也”[5](1940)、“先辈作文无他奇,只如题立局,不减不增,不倒不乱,规矩自然,变化万状,便是绝奇处”[7](612),均堪称“奇横”注脚。
吕留良所说的“奇横”既包含奇伟横溢之才与妙趣横生之效,又强调纵横变化的活法和通行于世的道义情理,不能蛮“横”无“理”。他指出:“变而当于理法,正是文人弄奇,妙境无穷处,如不当于理法,虽正格无益也。”[7](612)“平仄任用,故是词家横处,然法自可活,不足病也。”[7](772)吕留良称赞归有光文:“震川精于理,密于法,而出之以沛然之气,浑浩流转,斯为独立。”[5](1938)“须知此妙若以法求之,便成死板。但要道理烂熟,则沛然无疑。人看以为朴钝,不识其纵横自由处,直是生龙活虎。”[5](1957-1958)作家胸中肆意流淌的“沛然之气”即是“奇横”风格的来源。但必须以通晓道理为前提,“只是看得道理明白,坦然无疑,横冲直撞,无所不可,随地触发议论,不论金银铜锡,都可开点宝丹,则胆力足而气沛然矣”[5](2173)。可见,“奇横”并非舍弃理法而自由放纵、随意追新,而是要求在坚持理法的基础上转接突兀,跌宕多姿,刚健挺拔,自然高妙,既奇迈恣肆、纵横奔放,又合乎情理、透彻可行。
吕留良标举“奇横”说有其文学发展背景。明代“七子”倡导复古和模拟,对此吕留良在诗中予以猛烈抨击,“依口学舌李与何,印板死法苦不多。滥觞声调称盛唐,词场从此讹传讹。七子丛兴富著作,沙饭尘羹事剽掠”[8](83)。他曾对明代文风的发展演变进行总结,认为明代前中期文风质朴简重,瑰奇浩演,至明末骤变:
文体之坏,其在万历乎!丁丑以前,犹厉雅制;庚辰令始限字,而气格萎薾;癸未开软媚之端,变征已见。……至于壬辰,格用断制,调用挑翻,凌驾攻劫,意见宠逞,矩矱先去矣。再变而乙未,则杜撰恶俗之调,影响之理,剔弄之法,曰圆熟,曰机锋,皆自古文章之所无,村竖学究喜其浅陋,不必读书稽古,遂传为时文正宗。[9](176-177)
吕留良认为,明代文坛的萎靡之风肇端于万历癸未年(1585),继而走向恶俗、圆熟之途,并将时文创作领域出现的变化作为晚明“文体之坏”的根源。明代诗文风格不振,最大的弊端在于举业文字固守定法,专事模拟,抹杀了文人个性。吕留良说:“窃尝谓三百年来诗文无作者,或曰:‘是有故乎?’曰:‘有,病坐制举业。’‘罪至此乎?’‘举业无罪焉,学举业者为之也。’……今为举业者皆有俗格以限之,循是者曰中墨,稍异则否。虽有异人之性,必折之使就格。而其为法则之一曰套,取贵人已售之文,句抄而篇袭焉,无只字之非套也。以是而往试辄售,其为力省,其见效速。父以是传,师以是教,则靡然从矣。”[9](149)
吕留良“奇横”说正是针对囿于成法而造成甜俗滥熟的科举文风而提出的。清人黄中作于康熙辛酉年(1681)的《送友人科举序》道出了清初文人生态:“见博雅大部之书,本欲翻阅,惕然曰:‘岁试伊迩,不得工夫。’见子史历录之文、诗歌奇横之句,欲一簪笔,亾然曰:‘宗师有信,无此暇心。’……见庸鄙滥熟之文、游腔浮滑之调、臭恶说约之书,明知其不可而姑为一讲之、习之、晤之、对之、神之、奉之,且自解自恕曰:‘我职分之当为,我本行之应尔。’”[10](528-529)可见,自晚明至清初的近百年间,囿于科举考试的需要和指向,文人举子沉溺于圆熟滥俗的试牍文字,而无暇顾及甚至不愿关注“子史历录之文、诗歌奇横之句”。吕留良对此十分不满,他在给好友韩希的信中说:“试牍文字,弟素性所不喜。盖时论以至庸至俗之文,则名之曰墨卷体,而以无理无法者,则名之曰考卷体。世间惟此二种恶业流传耳。”[9](111)并且认为此现象的出现与选家关系甚大,于是,他提出“文体之弊也由选手”[9](178)的批评观念,认为“天下数科之风气,定于选手。……今之选手本领庸劣,其腹之空疏,手之甜俗,更甚于学究秀才,助彼说而张其谈。昔之选手能转天下,今之选手为天下转。故曰今之选手,今之秀才之罪人也”[9](177)。
吕留良坚决反对软媚、圆熟的文风,他说:“吾论文最不喜说‘圆’字,圆者,软熟之美称,文至软熟,其品极下。”[5](1957)为了纠正当时众多选家思想的空疏和庸俗,他自顺治十二年(1655)至康熙十三年(1674),从事时文评点前后整整二十年,坚持独立选文,“集中所痛削者,浮滑软熟之文”[7](470)。他试图通过编选、品评诗文来标举“奇横”风格,以此纠正晚明以来文坛上盛行的甜俗滥熟之调,从而改造文风,矫正文体。他曾收录编选清人钱禧时文集,“试读吉士自为文,于其所持之法无毫发之憾,而洸洋流宕,变动不居,有从容之乐,无布置之痕。世之豪纵自命为古文者,其奇横未有能出吉士之上也”[7](943)。吕留良正是通过编选“奇横”特征显著的作品选集来宣传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文学主张。由于经他评选结集的时文本子风靡全国,对当时及稍后的文士产生了很大影响④。因此,吕留良提倡的“奇横”说及其时文编选对纠正文风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清初沈季友所云:“当酉戌之交,文风靡敝,乃取历科房牍,大加选剔,为之抉书义、树文品,使天下学者取则焉。二十年间,为制艺者犹知去陋就高、斥邪崇正,晚村之力也。”[11](1622)
吕留良提倡“奇横”说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在清廷的民族高压政策下,怀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吕留良始终有一股无从发泄的压抑与悲愤,以“奇横”评文与他此际满腹不平的郁勃之气正相契合。面对清初文坛温柔敦厚、平稳缓和的盛世之音,“其议论无所发泄,一寄之于时文评语,大声疾呼,不顾世所讳忌”[7](865)。因此,“奇横”说可视为吕留良遗民思想的艺术表达,代表着一种清高傲世的姿态和睥睨外物的气度。同时,清初的宋诗风气,也可以说是明代遗民思潮的一部分。由于宋、明相似的历史际遇,宋诗往往成为汉族士人寄托民族情感的载体,甚至是宣传反清思想的工具。清初宋诗由晦而显,吕留良居功至伟⑤。他选编《宋诗钞》,提倡刚健硬直的宋诗,实际上是其学术理念和精神人格的一种投射。他特别欣赏亡宋遗民作品中那种苍凉激楚、奇崛横放的风格,《宋诗钞》选录了谢翱、文天祥、谢枋得、林景熙、汪元量、郑思肖等遗民诗人的作品,且评价极高。在倡导“奇横”风格的过程中,吕留良也完成了其主体形象的自我塑造。
因此,吕留良将这一时文批评术语用来品评诗歌,常以“奇”“横”论杜诗和宋诗。他以杜甫为古今诗人之冠,倡言“学诗学杜学夔州”[8](83),主张以杜诗为效法对象。其子吕葆中说:“忆自丱角时,家君子手批工部诗,朝夕讲解。且训学诗宜从老杜入手,谓是浑然元气,大吕黄钟,不作铮铮细响。五言七言,当于此求其三昧。”[7](950)《天盖楼杜诗评语》是吕留良批点杜甫诗歌的整理本,共收录519 题诗评,其中“奇”字出现频率最高,达112 次。虽然未直接出现“奇横”一词,但与“奇横”意义相近的“奇迈”“奇壮”“奇放”“奇峭”“奇崛”“豪横”“横逆”等词汇屡见不鲜。如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奇迈”、《秦州杂诗》“奇峭”、《上牛头寺》“奇崛”、《秋峡》及《漫兴》“豪横”、《三绝句》“横自立格”,等等。吕留良认为“宋诗大半从少陵分支”[9](303),因此,他与吴氏叔侄共同编选的《宋诗钞》也贯彻这一批评标准,“奇”“横”经常出现于他所撰写的《宋诗钞》诗人小传中⑥。如评苏舜钦诗“超迈横绝”、论陈与义诗“高举横厉”,言“(谢)翱诗奇崛”,谓徐照“其诗数百,斫思尤奇,皆横绝欻起,冰悬雪跨,使读者变踔憀慄,肯首吟叹不自已。”《宋诗钞》所选诗篇也多以“奇横”为衡,力倡刚健之气。在孔武仲小传中,他称赞道:“元祐文人之盛,大都材致横阔而气魄刚直,故能振靡复古。”对“气完力余,益老以劲”的梅尧臣诗,“雄健古淡,有气骨”张咏诗和“雄劲有气焰”李觏诗也十分推崇。
二、“奇横”的美学内涵
吕留良标举的“奇横”说指的是作品章法造意纵横奇放,笔势健拔遒劲,文气肆意流贯的状态,既有不期而然、出人意料的意味,又有自然率真、随处可见之意,是一种合乎法度的变化之美,可视为诗文的整体风格和审美境界。其美学内涵大致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是生新跌宕的章法和意脉。在章法结构上,吕留良以时文起承转合的八股作法来评论诗文的构造布局。如评时人陈际泰文云:“陈大士先生文,人但惊其奇纵,不知其法脉细净处。……章法首尾有体,股法次第相生,定一气呵成,转转见妙,此皆古文正法。”[7](593)与此相类,清中期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十六引郑方坤诗直接以“奇横”论陈际泰时文:“临川一老最奇横,千篇百赋书匆匆。”[12](379)就炼意而言,反常行之,往往可以形成奇横的审美效果。正所谓“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苏轼《书柳子厚〈渔翁〉诗》)吕留良推崇出人意料的“无中生有”:“漫空起云,雨点却落在天外,此无中生有之妙法也。”[5](1964)他认为“熟于史学,便多无中生有之法,东坡‘杀之三,宥之三’开想当然一例,是其家传史论习气,然苏氏文章奇横,亦出于此”[5](2074)。造就“奇横”的“无中生有”是苏轼作品中常用之法。刘熙载云:“东坡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13](66)如苏轼《神女庙》诗重新编织了一个神女故事,赋予神女以新的神格即巫山地方保护神,这与宋玉《高唐》《神女》赋中朝云暮雨、自荐枕席的媚神已大不相同。清人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九云:“大苏《神女庙》诗奇横独绝,于高唐一事置若罔闻,乃见此公心眼之妙。”[14](319)再如苏轼《荔枝叹》,前半部分引述汉和帝和杨贵妃吃荔枝事发表议论和感叹。后半部分忽然转入讽今,以“君不见”三字折回到现实社会,然后又酣畅淋漓地揭露本朝贡茶献花、争新取宠的事实,其激愤之情见于言表。正如《唐宋诗醇》卷四十所评:“‘君不见’一段,百端交集,一篇之奇横在此。诗本为茘枝发数,忽说到茶,又说到牡丹,其胸中郁勃有不可以已者,惟不可以已而言,斯至言至文也。”[15](172)“无中生有”不拘泥于常法、死法,而驰骋纵横,跌宕起伏,正所谓“天真烂漫,无中生有,空际散花,遂成奇绝”[5](1972)。吕留良曾云:“诗文有三字诀曰:熟里生。”[5](2209)在有与无、熟与生的转变中意趣油然而生,“善于用曲,善于用转,善于用顿用跌,便波澜不竭,奇趣横生”[5](2067)。
其二,是苍劲有力的骨气。吕留良倡导诗文遒劲有力,反对缺乏风骨的软媚,倡导“气贵横,横则运旋有力”[5](2099),“有力量气魄,则卷舒之际自生奇伟”[7](601)。文章所具有的奇特雄伟气势是逆向的,“文之一气呵成者,必用逆不用顺。盖用逆势,则一句磬一句,一层剥一层,涧翻云涌,势不可遏,读至终篇,恰如一句方佳”[7](597)。具有“奇横”特征的文学作品表现的是一种处于压抑氛围之下竭力抗争的意态和情感,是一种逆境心态下形成的艺术风格。其艺术精神表现为对当时文法规矩与审美观的蔑视,是文人压抑心态与抗争意识在文风层面的具体呈现。吕留良赞誉好友作品“各负奇伟,寓匏天才骏逸,迥绝尘姿,多于蕴藉中挺潇洒不羁之致;彝士风骨雄劲,所向空阔,一瞬千里,不可捉搦”[9](20-121)。他自己的文风也带有气势磅礴、雄风逼人的“奇横”特征。陆文霖云:“其文之奇,无所不尽……每出,必哄然不能测其腾骞所至。”[7](499)可见,吕留良所论“奇横”包含文章的奇诡横放的骨气、自由充沛的浩然之气和雄浑开阔的气势。
其三,是平淡自然的审美风格。自宋代开始,文学批评观念中的“奇”与“自然”“平淡”并不构成截然的对立,它们之间的关系成为此后论“奇”的历史与逻辑起点[16](46)。吕留良对这种美学内涵的接受代表了他对“奇横”审美层次的基本认知。他说:“古人谓:‘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予谓:‘必行处要止便止,止处要行便行,方是文章之至。不如此,不足以为奇,不足以为横。’”[7](599)这种随心所欲又不背规矩的“奇横”,其精神实质与苏轼“行云流水”“随物赋形”之论是相通的。钱锺书曾以“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解释苏轼此论,又说:“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这正是苏轼所一再声明的,作文该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的自在活泼,可是同时候很谨严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17](61)可见,诗文之奇横,指向无意为文而老成简淡的风格,正如吕留良所言:“有雄刚之气,而能出以淡远,方奇。”[7](606)“奇”的对立面是平庸或庸俗,不是平淡或平实。他说:“先辈论文必平实。平非庸也,而况可以俗当之乎!”[7](606)奇横与平淡自然犹如诗文的两翼,“念古文之道,亦须有奇横之趣、自然之致,二者并进,乃为成体之文”[18](182)。二者的关系往往体现在作家少时至晚年的创作嬗变中,苏轼在总结自己的诗文创作经验时就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与侄论文书》)吕留良亦云:“老手行文,如书画大家晚年制作,俱从极奇横、秀润、工致中来,故浅浅疏疏数笔,令人玩之不尽之意,即文家所谓‘绚烂之极乃造平淡’也。”[5](2158)他在为吴之振诗集作序时重申:“凡为诗文者,其初必卓荦崖异,继而腾趠绚烂,数变而不可捉搦,久之刊落,愈老愈精,自然而成。”[9](155)于人不经意处忽出异想,令人赏其奇逸与横逆,既能成就文章平淡之美,也含有可以反复涵泳的“不尽之意”,这是一种成熟、苍老、浑成的艺术境界。“浑成者,奇巧之至,若出自然也”[7](619)、“奇藏于拙,巧出于平”[7](590),在看似平淡自然的语言风格下隐匿着一股奇横之气。苏轼“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王安石“看似寻常最奇崛”(《题张司业诗》)即含有此种意味。吕留良对于放墨自如不见法、着笔无意而旨趣十足的奇横风格极为推崇,称道黄庭坚“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非规模唐调者所能梦见也”[9](281)。赞扬陈与义诗“晚年益工,旗亭传舍,摘句题写殆遍,号称新体,体物寓兴,清邃纡余,高举横厉”[9](290)。评价明末文风时云:“崇祯初,一变为古文之学,多以驰骋浩衍、雄深苍劲为胜。惟金正希于简严淡静中自有奇诡,令人一望不易入,久而心为之移,又迷离而不能出,此先生之超越一时者也。”[7](593)
三、师法“奇横”的诗文创作
吕留良不仅以“奇横”品诗衡文,其创作实践也以“奇横”为标的。吕留良自幼作文便语涉怪诞,“八岁善属文,造语奇伟,迥出天表”[7](864)。时人黄周星为吕留良时文集《惭书》作序云:“昨得用晦制义,读之,乃不觉惊叹累日。夫仆所恨者,卑腐庸陋之帖括耳。若用晦所作,雄奇瑰丽,诡势环声,拔地倚天,云垂海立。……何物帖括,有此奇观,真咄咄怪事哉!”[7](498)此为知言。如其《孔子曰才□□□然乎》控诉当时统治者表面惜才实则埋没人才的政策,胸中怀才不遇的郁勃之情肆意横放。又如,其《秋崖族兄六十寿序》不言颂美之辞和祝寿之语,而借生当变乱的彭祖、吕洞宾抒发黍离之悲,痛悼故国山河及衣冠文物的沦落。清人孙学颜评曰:“借荒怪之说,写感愤之情,真古人有数奇文,不独为寿序开生面也。”[9](159)吕留良指出:“惟实发故意态横生。”[7](619)其创作通过警卓新奇之言洗涤俗士鄙情,振奋民族精神人心,笔触中透露出的奇崛之气,率意而亢奋。此种奇横,是吕氏异代之际郁勃之气和个性精神的真实流露,也是他文学观念的彰显和实践。
詹安泰《题吕晚村〈东庄吟稿〉》以“最苍质处最奇横”[19](185)评价吕留良诗歌,可谓独具慧眼。吕留良将家国身世之感寄寓诗作,新奇兀傲之气和横绝俗流的高士风采充溢其间。他弃诸生归家所作《即事》诗句“十年多为汝曹误,今日方容老子狂”[20](508),颇有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狂放与不羁,表现出傲世独立、横而不流的高洁人格。章太炎说:“观其诗,率为故国发愤,时若犷厉(如《人日》诗云:‘鸡狗猪羊马复牛,算来件件压人头。’犷厉之气可见),亦非可以饰为者。”[7](901)吕留良还有“坏我衣冠皆此辈,斩除巢穴在明朝”(《憎鼠》)、“夺朱真可恶,野种亦称王”(《咏牡丹》)[7](907)等风骨铮然的呐喊。这些奇横的诗句可以说是对清廷最强烈的控诉,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卓然不群的人格精神相表里。其《澉湖夜泛》诗云:
万苍楼下小舟横,与客乘风破太清。
俯槛明湖收碧落,举杯孤月伴长庚。
欲倾东海消幽恨,先挽天河洗俗情。
忽发狂歌惊竹裂,四山怪鸟一时鸣。[20](679)
写诗人与朋友月夜泛舟澉湖,面对明湖碧水,他想到了家仇国恨和民族沦丧,胸中一股奇横之气情不自禁地喷薄而出。“消幽恨”“洗俗情”,势不与清廷为伍,浓烈的反清思想挟带一股豪迈奇横之气扑面而来。又如其《题梅次韵》:“遍地繁华不耐看,雨中争发雨中残。若非存雅堂前见,天下梅花改岁寒。”[20](719)以雨后凋零的群芳和傲然挺立的梅花作比,赞叹其孤高绝俗的品质,实乃自比梅花,表露苍坚顽强的铮铮铁骨和孤傲之气,抒写胸中的磊落不平。其《赠巢端明》将坚持民族气节、隐居不仕清的明遗民巢端明比作岩松、野菊,在“冰压”“寒催”的严酷环境中依然老而弥坚,苍劲横放,散发着清香。吕留良诗风多悲壮慷慨,凄楚激越,哀怨却不低沉,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和高亢的豪情,体现了一种阳刚的壮美。正如清代诗人张鸣珂《何求老人残稿跋》评吕留良诗所云:“其豪放如龙门飞瀑,奔腾澎湃,令人三日耳聋;其镵削如奇峰怪石,森然如欲攫拿。”[7](906)
因此,“奇横”在思想内涵上往往异于主流而有意识地追求一种不和谐,是不同于普遍价值的特立取向,在总体风格上要求诗文作品摒弃圆熟软媚的风调而揉入奇崛生硬的刚健之气。
四、“奇横”说的承继与开新
吕留良在重释杜诗艺术经验和承继苏轼文论基础上标举的“奇横”说,对清代及民国诗学和词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吕留良认为杜诗是“奇横”风格的代表,在评杜甫《白帝城最高楼》时更是鲜明地指出“奇壮此格,惟子美胜”[7](751)。清人杨伦品衡此诗继承了吕氏说法,云:“奇气奡兀,此种七律少陵独步。……此尤奇横绝人。”[21](596)此后,以“奇横”品评杜诗成为清代文学批评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如仇兆鳌评杜甫《短歌行》:“一股豪气直贯到结,云:‘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此种奇横,谁为步其后尘者。”[22](1885)宋育仁《三唐诗品》卷二称李颀“七言变离开阖,转接奇横,沉郁之思,出以明秀,运少陵之坚重,合高岑之浑脱,高音古色,冠绝后来”[14](6828)。认为李颀七言古诗具有杜甫诗歌“奇横”与“沉郁”的双重特征。方东树甚至将“奇横”与“沉郁顿挫”并提,作为杜诗最突出最典型的特征,推尊备至。他在评唐代诗人李益名作《盐州过胡儿饮马泉》时云:“此等诗以有兴象、章法作用为佳,若比之杜公沉郁顿挫、恣肆变化、奇横不可当者,则此等止属中平能品而已。”[23](425)又云:“杜公所以冠绝古今诸家,只是沉郁顿挫,奇横恣肆,起结承转,曲折变化,穷极笔势,迥不由人。山谷专于此苦用心。”[23](379)“杜公高华清警兼有王、李;奇横兀傲,兼有山谷;密丽跌宕,兼有白傅、子瞻。”[23](418)杜诗这种思力沉郁,笔势纵横,气魄雄伟,境界恢阔的“奇横”风格,被黄庭坚效仿和推崇,云:“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这与吕留良终身服膺的朱熹所谓的“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逆不可当”[24](3326)相类。清人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曾指出二者的联系:“夫‘横逆不可当’者,风动雷行,神工鬼斧,即山谷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也。”[25](2189)杜甫、韩愈晚年的诗文均已达到奇横之美,即吕留良所谓“随手布置,纵横由我,妙合自然”[5](1972)。
苏轼是继杜甫后吕留良眼中另一个具有“奇横”特色的诗人。吕留良在《宋诗钞·东坡集》诗人小传中称道:“东坡诗气象洪阔,铺叙宛转,子美之后,一人而已。”[9](276)同时,“奇横”说承继苏轼文论之迹甚明,因此,苏轼诗歌也常被清代诗论者称为“奇横”。除前引《神女庙》《荔枝叹》外,方东树评苏轼《雪浪石》:“此诗奇横,以校诸人和作,其大小平奇自有辨。盖他人不能有此笔势,故不能有此雄恣。”[23](306)又评苏轼《宿九仙山》:“后半所谓大家作诗,自吐胸臆,兀傲奇横。”[23](445)又评苏轼《书韩幹牧马图》:“起跳跃而出,如生龙活虎。先生句逆出,金羁三句,提笔再入题。以真事衬、以众工衬、以先生衬、以廐马衬,‘不如’一句入题,笔力奇横,浑雄遒切,放翁折海棠,从此得法。”[23](297)
清代以“奇横”赞誉时人诗歌也常见诸评论。如俞樾称樊芾林“其诗古体有奇横之气……诗虽不多,可以传矣”[26](1686)。吴仰贤《小匏庵诗话》赞黎简“其诗戛戛独造,昌黎所谓‘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庶几近之。……古体各诗,刿目怵心,奇横恣肆”[14](6529-6530)。朱庭珍《筱园诗话》对徐兰边塞诗之“奇横”推崇有加:“徐芝仙塞外诸诗,境奇、语奇、才力横绝,在昭代诗人中,另出一头地。其边塞诗可谓独擅之技,实未易才。稚存、兰泉、荔裳诸君,出塞篇什,并多佳章,然均不能及芝仙之奇横矣。”[25](2372)
“奇横”也广泛出现于清代及民国的词学批评领域,为这一时期词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一般来说,词体以婉约为正宗,以豪放为变体。正如清人顾贞观《古今词选序》所言:“温柔而秀润,艳冶而清华,词之正也;雄奇而磊落,激昂而慷慨,词之变也。”[27]词学批评中的“奇横”兼有词体“正”“变”的格调,浮艳奇丽之外亦有横劲之气、沉雄之魄的意味。
“奇横”是晚清民国著名词人詹安泰论词的重要审美范畴。他评孙光宪词时说:“如有巧妙之意境,则贵出之以拙重之笔,庶不陷于尖纤。巧妙而不尖纤,为孟文(孙光宪)所特擅,但或出之以奇横,不尽拙重耳。”[28](59)他主张融“奇横”于“重拙大”之境,认为“奇横”是一种“巧妙而不尖纤”的气象,它虽未达到“拙重”之境,但趋向和接近生新老辣、苍质淳朴的审美境界。因此,詹氏在花间词派中推尊孙光宪与温庭筠、韦庄鼎足而立,并认为“宋人张子野、贺方回均由孙出”[28](59)。他在论及“奇横”内涵时,就是以张先词为例:“奇横非险巧之谓也,令词最忌纤巧而不妨奇横,如张子野之‘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奇横极矣,然是何等气象,其得谓之险巧耶!”[28](59)张先《醉垂鞭》词描绘了一位酒宴上美丽的歌妓,结句“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将她衣服上的云烟图与天际乱山之云连类相比,极力形容女子起舞时的服饰之美,栩栩如生地刻画出女子的神韵。写至此,词戛然而止,收得极其有力。此句意象新妙,想象出奇,似离题横出,却又情景交融,亦真亦幻,奇境横生,耐人深味,可谓以俊逸精健之笔创造奇横意境的典型代表。
贺铸是这一风格的又一代表。詹安泰说“贺东山词,古艳绝伦,而笔力精健,气韵亦高,读之久久,可以涤除俗秽,引动雄怀”[28](60)。龙榆生则直接以“奇横”评价贺铸词:
依我个人的看法,贺氏在词界的最大贡献,除了小令另有独创,仿佛南朝乐府风味外,他的长调也有很多笔力奇横的作品,可以作为辛弃疾的前导。[29](242-243)
笔力奇横,声调激越;韩退之所谓“横空盘硬语”者,庶几近之。……至于方回长调,反复映射,而又出以奇横之笔,旋转而下,如前录《六州歌头》《宛溪柳》《伴云来》《石州引》诸阙,意态雄杰,辞情精壮,使人神往。[29](341-342)
贺铸既曾为武士又善于作词,其词兼有豪放和婉约两种风格,尤其是他所写的那些声情激壮、雄奇俊伟的长调作品。龙氏评其名作《六州歌头》云:“惟其有英气而又曾为武弁,故其壮烈情感,难自遏抑;惟其好书史,工语言,长于度曲,故能深婉丽密,如比组绣;非特无粗犷之病,亦无纤巧之失。”[29](336)其实,龙氏所谓“奇横”与南宋王灼提出的“奇崛”范畴一脉相承。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乐章集浅近卑俗”条云:“贺《六州歌头》《望湘人》《吴音子》诸曲,周《大酺》《兰陵王》诸曲最奇崛。”[30](84)龙榆生在解读贺、周词艺术经验的基础上接受了“奇崛”范畴。他说:“必欲于苏、辛之外,借助他山,则贺铸之《东山乐府》、周邦彦之《清真集》,兼备刚柔之美,王灼曾以‘奇崛’二字目之。参以二家,亦足化犷悍之习,而免末流之弊矣。”[29](118)他认为贺、周词独有的“奇横”或“奇崛”风格既不同于苏、辛,也有别于柳、秦,而是集两派之长浑化融合而成,既改掉了不谐声律、粗犷豪放的习气,又规避了浅俗纤巧的弊病。
至于周邦彦词,龙榆生指出:“清真词之高者……几全以健笔写柔情,则王灼以‘奇崛’评周词,盖为独具只眼矣。”[29](351)这一论断与清人所谓周邦彦词之“奇横”不谋而合。周济在宋代词人中推举贺、周、苏、辛,曾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以“奇横”二字评论周邦彦《锁窗寒·暗柳啼鸦》在章法结构方面呈现出的腾挪变化、笔力强健的艺术特色[30](1647)。朱庸斋《分春馆词话》亦云:“美成寒食‘暗柳啼鸦’一阕,笔力奇横,气足故也。”[31](61)
当然,以健笔写柔情的宋代词人还有很多,他们的词作同样被清代及民国词论家称为“奇横”。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云:“黄鲁直词,乖僻无理,桀骜不驯,然亦间有佳者。如《望江东》(词略)。笔力奇横无匹,中有一片深情往复不置,故佳。”[32](162)黄庭坚以诗笔填词,其词往往呈现出语言瘦硬而情感深致的特点,这种内柔外刚的特征是“奇横”美学意义在词学领域的贴切表述。因此,陈廷焯又言:“笔力奇横是山谷独绝处。人只见其用笔之奇倔,不知一片深情往复不置,缠绵之至也。”[33](300)另如,万树认为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遒逸之气,如生龙活虎,非描塑可拟。其用字奇横,而不妨音律,故卓绝千古”[34](241)。该词起首连用十四个叠字,下阕又有“点点滴滴”,这种笔法虽破空而来、横放杰出,但清旷雄奇,绝无斧凿之痕。唐圭璋也曾指出吴文英词“深情郁勃,笔力奇横”[35](985),又称赞其名作《八声甘州·灵岩陪庾幕诸公游》“全篇波澜壮阔,笔力奇横”[36](218)。可见,以奇横之笔作词,以奇横之气救纤巧之失,融合阳刚与阴柔的奇横之美已成为清代及民国词学批评的重要趋向和审美标准。
综之,吕留良标举“奇横”的审美风格和艺术境界,以“奇横”论文品诗,其诗文创作也崇尚“奇横”,在明末清初软熟平滑文风之后别开一境。此后,“奇横”被广泛用于清代及民国的诗词批评,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
注释:
① 学界对吕留良文学创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徐正《吕留良诗歌略论》,《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 期;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85—100 页;俞国林、李成晴《吕留良之诗学与诗风》,《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9 期。
② 清人曹鍴辑有《吕晚村先生论文汇钞》,系统地收录了吕留良论文之语,共计302 条,收入王水照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22—3372页。清代车鼎丰云:“吕子之评文,非为评文也,即以评文论,亦自独有千古。近代诸名选家不足论,六朝唐宋以来,论定诗文者夥矣,有一足与之颉颃者乎?有目者试取从来评语,细加对勘,当自得之,实非予阿好也。”参见:俞国林《吕留良全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0 册,第1903 页。清人范尔梅亦云:“国朝论文高出诸家之上者,前有吕晚村,后有陆稼书。”参见:《雪庵文集》,《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九辑22 册,第2 页。钱锺书也曾说:“清初浙中如梨洲、晚村、孟举,颇具诗识而才力不副。”参见:《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7 页。
③ 关于“奇”美学范畴的研究,可参阅郭守运《中国古代文论“奇”范畴研究》,武汉出版社2009年版;陈玉强《古代文论“奇”范畴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④ 清人王应奎云:“本朝时文选家,惟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参见:《柳南续笔》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3 页。
⑤ 《宋诗钞》“从文本上为‘宋诗派’提供了支持,从而自明以来尊唐一统的格局被真正打破,宋风与唐音并存并举,对清诗的发展关系甚巨”。参见: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 页。吕留良对《宋诗钞》贡献最大,参见:蒋寅《清代诗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03—509 页。
⑥ 钱锺书《谈艺录》中云:“《宋诗钞》中小传八十三篇,出于晚村之手者八十二篇。”第14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