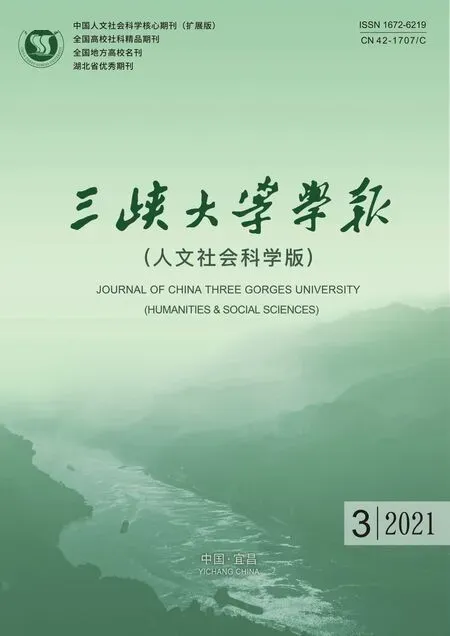从“日本性”到“国际性”的创作转变
——石黑一雄创作思路述评
盛春来, 陈瑞
(三峡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文学创作从来都脱离不了时代的影响,因此考察作家创作思路的流变必定能管中窥豹地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加深对作家的理解。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来自英联邦的拉什迪和奈保尔一起经常被冠以“移民文学三雄”的称号。石黑一雄幼年由日本移民到英国,他在英国文化的滋养下长大,但其亚洲人外表和带有日本特色的英文名字却处处昭示着他与日本剪不断的脐带关系。石黑一雄把混杂着记忆和猜想的日本作为写作的起点,创作了带有浓郁“日本性”的姊妹篇小说《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有人认为把《长日留痕》的英国背景置换成日本同样成立,这“不过是披着英国外衣的日本小说”[1]22,还有人指出“不管石黑一雄如何竭力否认,他的作品中有明显的日本特征”[2]3。以“日本性”出道的石黑一雄却不愿意被冠以“日本作家”的头衔,他后来转向 “国际性”的主题写作,也更愿意被看成是“国际作家”。石黑一雄为什么否认自己的“日本性”特征?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转向“国际性”写作?
基于此,本文将从英国社会时代风貌的变迁,读者接受、出版学和作者本人思想的变化论述石黑一雄创作思路的流变,窥见时代背景和接受美学对石黑一雄的影响。
一、与日本剪不断的脐带关系
“个人文化身份的形成,是从孩童时代开始的。一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首先在儿时的家里,然后在学校里,在与同龄人的交往中形成自己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感觉方式。也就是获得了自己特有的文化身份。”[3]石黑一雄6岁左右被父母从日本带到陌生的英国,由于空间位移导致年幼的石黑一雄遭受了心理和文化创伤的影响。石黑一雄曾回忆说,在上小学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全校唯一一个亚裔孩子,同学们在还未认识他之前就非常清楚他的亚裔身份,因身份差异带来的疏离感无处不在。与此同时,年幼的他对此前陪伴他成长、但仍在日本的祖父有着深深的依恋,这种依恋并没有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减少。石黑一雄后来认为“写作也和我对日本的强烈情感有关,在我形成情感,特别是形成和祖父的情感的年纪的时候,联系突然被切断了……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纽带,(内心里)并没有被切断,因为我总是想着回到日本去。”[4]4石黑一雄的父母开始也以为完成手头的工作后就会返回日本,因此他们在英国有种“旅行”的感觉,为了回国后能跟上日本的学习,石黑一雄总能定期收到祖父寄来的日文学习书籍、日本漫画和日本电影资料等。父母也习惯在家里讲日文,母亲还曾为他朗读过整本日文版《伊凡赫》的故事,年幼的石黑一雄喜欢观看日本电影,因此他的写作题材和写作风格都受到日本文学和日本电影文化的影响。有研究者指出《远山淡影》有《蝴蝶夫人》的影子[1]22;他写作中惯有的隐忍、克制的写作手法有日本文学“物哀”的痕迹;从未到过中国的石黑一雄在《上海孤儿》中,直接把故事的背景设置在上海,书中很多关于上海的详细描述并不完全是作者臆想出来的,而是作者通过早年随日军驻扎在中国的祖父讲述的关于中国的记忆。“石黑一雄在访谈中承认他的日文水平只是处于孩童时期的语言层次,他很可能读过谷崎润一郎或他的译文版的著作。”[5]22他也受到日本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和成濑巳喜男的影响:“日本的这些(电影)视觉影像对我有巨大的痛楚感,特别是小津安二郎和成濑巳喜男的室内电影讲述战后的场景,那就是我记忆中的日本。”[1]30日本导演对他的吸引“部分在于他们迎合了石黑一雄被放逐和怀乡的渴望之情。”[1]30石黑一雄在书写故国的回忆中获得精神的慰藉,抚慰因地域的隔离和时空的变迁导致的不适感。莫言认为“写作就是回故乡”[6]序言3,石黑一雄的写作与日本文学和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密不可分,他始终剪不断与日本文化的脐带联系。
迟至石黑一雄十二三岁,全家才完全放弃重返日本的想法,而他心心念念的祖父直到逝世也未能再见到他。石黑一雄把对祖父和家乡的思念倾注在其初期的小说描写之中,写作于他“是一种慰藉或疗伤,通常,坏的写作来源于这种疗伤,而最好的写作来自于作家和已经迟来的形势和解。”[7]134石黑一雄的处女作《远山淡影》及其姊妹篇《浮世画家》都把故事的背景设置在他离开家乡的记忆截止的战后日本,两部小说都浸透着浓浓的“日本性”:小说中诸多的日本地名,如长崎、东京、核爆纪念碑;富有日本特色的英文名字:二郎、惠子、绪方;美国战后帮助重建带来的西方文化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冲击,军国主义画家(小野)所擅长的日本浮世绘画技;慈祥的绪方先生和孙子一郎温馨的祖孙关系也总是让读者想起作者本人与其祖父,乃至《浮世画家》内含的“羞耻文化”和《远山淡影》对《蝴蝶夫人》的戏仿[1]11,都无处不在地表征着这些小说的日本印记。需要看到的是,这些“日本性”是石黑一雄“混杂着猜想、记忆和想象”建构起来并不完全真实的日本,石黑一雄承认《远山淡影》带有自传色彩:“它直接描写关于我这辈、像我一样的人……如果我把背景置换且拉远距离,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一直做的事情的自述。”[4]41幼年离开日本的石黑一雄对故乡的思念只有在重构日本的记忆里得到满足,于是诉诸笔头的初期作品《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不仅以记忆作为主要的写作方式,而且这两部作品所流露出的浓浓“日本性”折射出作者对故乡最真挚的情感。移民普遍有“故国认同”的情节,在流散者新身份的形成过程中,他们总是渴望再造和重写家乡。由于真实的家乡难以在短期内抵达,因此这种渴望只能在想象和记忆中得到满足,他们的精神家园只能在想象和记忆中重构,以便纠正流散者由于时代变迁和空间位移引起的家乡错位感。时过境迁,人事代谢导致真实的故乡空间图景产生了变化,移民作家的故乡是回望中想象的家园,已变成了难以抵达的文化符号。毫无疑问,石黑一雄早期通过回忆建构的日本就是“想象的精神家园”,他把自己情感的锚系之地——日本作为写作的起点,这既是抚慰包括失去祖父在内的思乡情绪,也是为飘荡在“既非日本也非英国”的“第三空间”中的自我寻找归属感。
二、“求新声于异邦”的英国文学的转变
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现实主义写作在战后后现代主义实验性写作和“着眼于阶级、教育、南北差异、政治和种族”[8]57的愤怒青年作家的冲击下七零八落,英国人逐渐厌弃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各种实验性写作手法,也对愤怒的青年描写的阶级和政治小说失去了兴趣,“当平庸的中产阶级影响渐渐消逝后,对于小说,尤其是严肃小说的智性的态度似乎发生了激进的变化。”[8]58英国人渴望找到反映现实生活、更贴近实际的文学作品。后殖民主义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英国声名渐隆,后殖民文学的兴起和英国战后移民潮密不可分。大英帝国在战后逐渐没落,但来自前殖民地的移民却源源不断地来到英国,自从1948年第一船来自牙买加的移民到达英国后,“移民已经变成了改变‘英国性’面貌的最强的力量”[9]。外来移民导致英国国民身份的多元化,把以白人为主、文化身份相对单一的英国变成了包括黑人和其他移民在内的“杂种”国家。大量移民的到来也催生了移民文学在英国勃然兴起,最突出的莫过于包括奈保尔、拉什迪、毛翔青和石黑一雄等在内的移民作家的诞生。布鲁斯·金注意到,自1983年本土作家威廉·戈尔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英国国内的文学大奖都被移民作家包揽,他认为这和战后大量涌入英国的移民有关。1983年英国《格兰塔》杂志首次推出“20位英国最佳小说家”,包括石黑一雄等新锐作家当选,“这些作家的作品主题多样,风格各异,为英国小说世界带来了崭新的气象”[10]。在拉什迪的《午夜出生的孩子》1981年获得布克奖之后,英国评论界就在寻找下一个带有移民身份的作家。
生逢其时的石黑一雄不仅有着移民身份,而且其处女作《远山淡影》中带有异域风情的日本故事立刻吸引了英国社会的注意。“那时有一种风气——人们寻找年轻、充满异域风情又带有国际风格的作者,我很幸运,刚好生逢其时,那是英国艺术近年来少有的时期:充满情趣的外国名字并写作有趣的外国地方会得到额外的垂青,英国人突然庆祝终于抛弃了英国本土特色。”[7]130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文学审美情趣发生了转向,在一定程度上说,英国读者与其说对《远山淡影》的故事感兴趣,毋宁说他们对石黑的日裔身份更有兴趣。一个有力的佐证是,石黑一雄因《远山淡影》出名后,他生在日本、成长于英国的跨界视角也立刻引起了关注,他被不停地邀请到英国各地作演讲,人们不断地要求他对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发表看法,石黑一雄还被看成日本在英国成功人士的代表,受到访英的日本天皇夫妇的接见。
英国社会看重石黑一雄的族裔身份,还和当时的经济、政治密切相关。在大英帝国强盛的时候,世界的中心就在英国,所以“英国作家写作英国的东西就自然带有世界的意义”[4]27。但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标志着大英帝国地位的彻底衰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偏居欧洲外岛的英国国际地位继续式微,不断被边缘化,这在部分英国作家身上表现出自卑情绪,“年轻一代的作家明显意识到英国现在更像一个世界上小的、偏狭的小镇。”[4]114他们不得不有意识地写作带有世界性的主题,因为如果他们只是写作英国的生活,没有人再感兴趣了。英国年轻作家身上表现出的自卑情结折射出“后帝国”时代英国人不得不面临从帝国中心到世界边缘的身份转变。
几乎与此同时,战后的日本经济发展却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到1968年左右,日本经济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日本工业产品大量销售到世界各地,为日本赢得了世界声誉,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勾起了日渐衰微的英国人的羡慕之情,因此英国渴望了解日本。然而日本在经济上的高歌猛进却没有换来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好感,地域的局限和在二战中与日本分属两个敌对阵营的差异导致英国对日本的了解很有限。日本天皇回避二战责任的态度还激起英国民众的愤慨,丰田公司总裁丰田章一郎和自杀的三岛由纪夫在英国和西方社会最广为人知,大江健三郎认为丰田章一郎和三岛由纪夫都是西方对日本两种极端偏见的认识:“三岛由纪夫的切腹自杀是一种设计好的、展现典型日本形象的表演,而且这种形象并不是日本人自发的心态展示,这是从欧洲视角观看的虚假的日本形象,三岛由纪夫验证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这和实际生活在东方的人毫无关系,但三岛由纪夫以自己的生活和死亡的方式迎合了东方主义对日本的印象。”[4]31
英国对战后的日本混杂着既羡慕又有偏见的复杂情绪,西方社会还未完全接受日本,对东方的日本仍怀有猎奇的心态。在西方的注视下,东方是想象的他者,充满了异国情调。《远山淡影》开篇就以英国丈夫和日本妻子悦子为混血小女儿取名字开始,“真奇怪,是他想取一个日本名字,而我——或许是出于不愿想起过去的私心——反而坚持要英文名。他最终同意妮基(NiKi)这个名字,觉得还是有点东方的味道在里头。”[11]3姓名是一个人身份表征的重要符号,也寄托着命名者的期盼,英国丈夫希望在英国出生的孩子带有东方的味道透露出对异国情调的向往。悦子的大女儿景子移居英国后不久就自缢而亡,“景子是纯血统的日本人,不止一家报纸马上发现了这个事实。英国人有一个奇特的想法,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天生爱自杀,好像无需多解释。因为这就是他们报道的全部内容:她是个日本人,她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自杀。”[11]5日本女孩的自杀牵动了英国人的神经,也符合英国人因此前三岛由纪夫自杀事件引起的对日本人喜欢自杀的已有认知,因此石黑一雄叙述日本女子自杀的故事符合了西方对东方的阅读期待,他自我东方化的写作视角满足了英国人对异国情调的想象,石黑一雄自然就赢得了英国文坛的好评。
石黑一雄善于利用自己的跨国身份,他带有“日本性”特征的早期姊妹篇《远山淡影》和《浮世绘画家》迎合了英国社会“求新声于异邦”的潮流。20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阅读趣味的改变和战后大英帝国的衰落,以及日本经济的腾飞都促成了石黑一雄的脱颖而出,在英国文化浸润中长大的石黑一雄内化了西方的视角,他的域外书写给当时困顿的英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其关于日本性的写作也暗合了西方人对东方固有的文学期待。
三、向“国际性”作家转变
英国社会看重石黑一雄身上和他的作品中的“日本性”,但《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中展现的日本并不被日本读者认同。《浮世画家》里日本画家对二战的反思和一些人为战争谢罪自杀的描写在当时的日本并不多见,石黑一雄笔下的日本更多的是他猜想和记忆的结果,甚至是他在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中捕捉到的模糊的日本意象。他笔下的日本饱含了西方视野对日本的想象,这也导致了石黑一雄的译作早期在日本并不受欢迎。“西方评论者一直把他的写作定义为日本风格,但东方评论者声称他失去了日本性。”[12]刘易斯批评他描写了一个虚假的日本[1]23。在他成名以后,英国社会在涉及日本问题时希望石黑一雄能为日本代言,但除了仅保留其亚裔的自然属性之外,石黑一雄骨子里是英国人的身份使他既不能,也不愿为日本代言。
及至1989年《长日留痕》出版以后,石黑一雄第一次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日本,在访谈中他说:“我意识到我对当代日本缺少了解,我想,正是由于这样迫使我运用想象写作,也使我把自己看作是无家可归的作家。我没有明显的社会角色,我不是一个非常英国的英国人,也不是一个非常日本的日本人。我没有为任何社会或国家代言或写作,没有人的历史能成为我的历史,我想,这促使我必须以国际方式写作。”[4]58回到日本的石黑一雄更习惯用英语而不是以日语和日本读者交流,接受一种语言就是接受一种文化,以英语而不是日语在日本交流暗示了作者本人英国性的文化身份。《长日留痕》出版之后,石黑一雄“不打算以历史的准确方式重现某些过去的时光……通常是我离英国越远,我对我的写作就越满意。”[13]因此在其前期三部带有明显地域特色的小说之后,石黑一雄在此后的四部小说里逐渐远离熟悉的日本和英国,在写作主题上也更关注人类共同的话题,走向国际性写作。
石黑一雄自称是一个国际作家,“他表达了被划分成日本作家的挫败感。一些他近期的小说如《无可慰藉》可能有意把故事背景模糊化,石黑一雄抱怨评论者认为他作品的场景对作品很关键。”[14]77《无可慰藉》的背景是未具名的欧洲小城,主人公瑞德不停地转换空间和流动的生活方式像极了石黑一雄本人的身份特征。《上海孤儿》虽在伦敦和上海之间切换,但两地都是模糊的所指,并且该小说隐喻人类像孤儿般生存的主题,带有很强的哲思含义。《别让我走》是一部科幻小说,故事更是放置在一个虚拟的未来英国学校,探讨了人类如何看待克隆人身份和权利的问题,关注人类的未来,主题也越来越宏大。在2005年《别让我走》出版之后,石黑一雄曾说:“我下一个小说要关注的是整个社会或国家如何记忆和遗忘的问题,何时记忆有利?何时遗忘有利?这是一个大问题,我想我的作品一方面已经关注了国家经历重大的社会变化,另一方面也关注了个体记忆,但我从未把这两件事情并置在一起。”[4]1272015年出版的《被掩埋的巨人》追述人类记忆空白时期的6世纪中古英格兰,揭示了后亚瑟王时代的英格兰如何在记忆和遗忘的两难中抉择的困境。“被掩埋的巨人”喻指当今世界上已经发生和将会发生的民族冲突、大屠杀记忆,以及人类心中的仇恨都难以在短期内消失。作家关注人类普遍的生存状况,描摹了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困境,因此该小说具有了更普适的意义,也帮助作者完成了从关心个人命运的移民作家到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国际作家的转变。
石黑一雄还是一位从读者出发的作家,在其小说中没有晦涩难懂的词语,几乎没有使用双关语等修辞技巧,这样做正是照顾到世界各地的读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免引起小说的误读。从写作之初就希望以“国际作家”写作的石黑一雄早就注意到读者的多样性,同时英国小说和英语的强大世界影响力也注定了他的写作风格和写作主题一定是世界性的。石黑一雄的小说在经历了早期的“日本性”和“英国性”等写作主题后,开始转向后来的克隆人、记忆和遗忘等世界普遍关注和存在也是当今世界焦点的话题,他后来的作品削弱了小说鲜明的地域特色,描摹了人类共同面临和关注的困境,因此也更有普适性。石黑一雄探讨但弱化小说的政治批判性,作者本人虽然遭遇东西方文明的困惑,但不挑战不同文明的价值观。因此石黑一雄的小说在政治批判性上比奈保尔和拉什迪要弱,也不及他们作品的先锋性和战斗力,或者正是因为他的小说兼具政治温和和人性温度的特点,才使他的小说更容易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再者,石黑一雄小说的写作几乎从一开始就受到出版商的巨大影响。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英国作家几乎都是在为本国读者写作,但60年代之后,“具有跨国文化背景的英国作家,如印度裔作家奈保尔,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等自觉地意识到他们自己“不仅是在为英语读者写作,而且是为欧洲、为全球的读者写作”[15]12。所以石黑一雄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的时候,英国出版商就对他争相邀约,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就是要多带些异国风情的东西,就是要突出他的跨国文化背景”[15]13。石黑一雄的很多小说出版后,在出版社的要求下,他本人不断地和读者见面,为读者朗读自己的作品,参加访谈和演讲,为小说的推广和促销不遗余力,他深谙小说出版之道,经常考虑到小说读者的需求。小说创作的商业化趋势和读者群体的世界化也决定了石黑一雄必然以世界主义的视角探讨世界性的话题。作者本人积极参与小说改编成电视和电影形式,在《长日留痕》和《别让我走》等作品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过程中,他本人担任编剧,并且为电影和电视卖力宣传,因此,石黑一雄具备用英语为全球写作的主动性,这无疑会助推他本人成为国际作家的可能。
考察石黑一雄三十余年(1983-2015)的创作流变,我们注意到:他从一个带有明显地域特色的作家走向怀有普世情怀的国际作家,逐渐脱离单一的文化身份,转向多元而混杂的世界公民。在其几十年的创作中,变化的是故事的底色或背景,这些背景从早期有清晰地理指向的特定地域走向后来模糊的欧洲小城和虚构的未来世界,以及回溯历史空白时期的远古时代,故事背景的不断模糊化和写作主题的隐喻化也表征了作者突破地域局限、不断国际化的过程。此外,英国社会阅读兴趣的改变、时代的变迁和出版业的影响也都助推了石黑一雄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