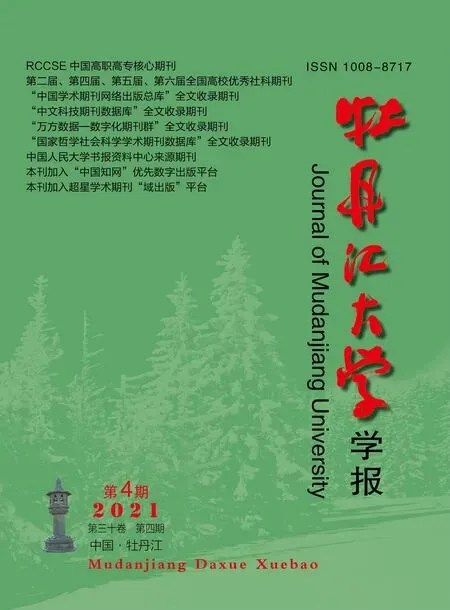清末民初时期“立宪派”概念的形成与演变研究
戴 贺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市 300387)
一、如何定义“立宪派”,“立宪派”概念的复杂之处
“立宪派”是推动清末民初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以来,随着预备立宪研究热潮的兴起,“立宪派”受到了更多的关注。然而谁是“立宪派”,如何界定“立宪派”?随着研究的深入,“立宪派”的概念反而越来越模糊。有学者提出:在当时的情形之下,除了革命派坚决反对立宪外,朝野上下并无立宪与反立宪之争,只有缓立宪与速立宪之分歧。因此,他认为“立宪派”这一概念是一种文化建构。[1]
不可否认,从清末以来,“立宪派”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存在很大程度的文化建构。这是由于“立宪派”三个字本身含义有着不确定性,“立宪派”的“派”字是指“见解、信仰、风格等相同而形成的体系、组织或一些人”,所以“立宪派”的直接含义是“为了追求立宪的而形成的体系、组织或一些人”。“派”字含义的模糊,使得一些概念建构成为了可能。尤其是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区域史、社会史等研究方法引入史学的研究之中。区域社会史研究强调研究对象的社会基础,“立宪派”的概念受此影响,悄然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立宪派”的概念和“立宪党”的概念大致相同,从20 世纪40 年代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可略窥一二:
“各省响应独立,虽由革命党人运动发难,而各省谘议局的立宪党人,无不加入革命动作。除了他们的言论指导者梁启超,尚在海外发‘虚君共和’的议论以外,国内立宪派人物,或任革命政府的民政长(如汤化龙)或任革命政府的都督(如谭延闿),或任其他职务,竟没有一省的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作敌对行动。”[2]
李剑农在书中将“立宪派”与“立宪党”混用,未作具体区分,说明在当时学者的眼中,“立宪派”的概念与“立宪党”并无不同。20 世纪60 年代张朋园在《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中更是直接提出:“所谓派,实际上是‘党’的别称。自来中国的党派不分,党就是派,派也可以说是党。”[3]
20 世纪80 年代,受到区域史、社会史的影响,在学者纪欣提出,应该将“立宪派”的研究引入到清末“绅士阶层”的研究之中,使之适合当时的社会基础。他认为:“绅士阶层是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晚清绅士阶层是在内外环境剧烈变化下而衍生出的新绅士阶层,其中的‘新绅士——立宪派’影响很大。他们以东南地区实业家为骨干,主张实行立宪,强烈要求参与政权。”[4]与此同时,学者王晓秋用区域史的视角,提出了“京城立宪派”的概念。他提出,在清末北京的政治中,有一批“立宪派”人士十分活跃,它们大多是归国的留日学生,多数学过政治、法律,是清政府中央各机关的中层官员,共同主张君主立宪,努力推进宪政改革。[5]王晓秋将这些人士定义为“京城立宪派”。
除了社会史、区域史的角度,学者雷俊还从官员群体的角度,提出了“官僚立宪派”的概念。他认为:“清廷内部存在着一个力量比较强大的官僚‘立宪派’,他们除了地方督抚、驻外使臣、考政大臣及部分满汉大臣外,还应包括一向被人视为思想保守、反对立宪的慈禧、瞿鸿机、铁良、荣庆、孙家卿、载沣等人。”[6]
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所说的“立宪派”概念,已经和传统“立宪派”的概念大不相同。传统“立宪派”的概念与“立宪党”的概念相同,讲求的是政治组织性,而现代“立宪派”的概念更倾向于区域性、社会性与群体性。“立宪党”与“立宪派”的概念之所以走向殊途,很大程度上在于“党”与“派”字的含义不同。“党”的组织性较强,“派”更多的是指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或为思想体系、或为经济体系、或为政治体系,但都具有松散的特征。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者的建构影响了我们对“立宪派”概念的认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立宪派”一词确实存在很大的文化建构。
可是,如果将“立宪派”概念完全说成是文化建构,未免失之偏颇。从清末的历史来看,“立宪派”一词源于“立宪党”,“立宪党”是客观存在的政治实体。我们后人之所以对“立宪派”的概念进行了建构,是因为我们忽视了“立宪党”概念的存在。在清末时期,人们使用“立宪党”的频率远大于“立宪派”,而民国建立之后,“立宪派”的使用频率才逐渐超过“立宪党”,后世遂以“立宪派”来指代这一概念。要想探讨清末时期“立宪派”概念的发展,还需要将“立宪党”纳入研究的维度,“立宪派”一词也将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清末时期,“立宪党”概念的引入与发展
“立宪党”一词,究其源头,属于引进自日本的舶来品。早在1882 年,《申报》介绍日本政治局势时,就提到了“立宪党”:“该处(指日本)两三年来随地创立党会,在会官民为数甚众,东京之自由党尤当首屈一指。其余若大版之立宪党、九洲之改进党皆公然集众会议,饮宴结盟,以敦亲睦为名。”[7]此时中国尚未立宪,“立宪党”无从谈起,所以中国的“立宪党”概念引进于日本,受日本的影响较大。
日本的立宪党人在政治上颇有作为,中国舆论不吝赞美之辞。《大公报》的一篇社论认为,日本之所以兴盛,就是因为国内立宪党人的团结。日本国内原来分为三大党,它们“入主出奴,各不相合”。可是一旦国家面临危机,则“共力维持,以防倾覆”,合并成为新的“立宪党”,不因私人的争端而贻公众国家祸患,共同保卫国家的安全。[8]
不仅日本存在所谓的“立宪党”,东欧、西亚一些诉求改革的国家也存在“立宪党”,它们是国内“立宪党”概念兴起的外部原因。其中报道较多的有俄国“立宪党”,各类报刊对“立宪党”与俄国政府之间的互动尤为关注。比如《大公报》曾对俄国“立宪党”的诉求进行报道:“立宪党致书俄皇声称,伊等满望俄皇大赦天下,并许民人在政界上有自由之权,并改革皇家内阁各事。”[9]同时,《申报》还对俄国“革命党”与“立宪党”之间的不同进行了分析:“俄皇恢复芬兰旧有之自由权之诏敕已在黑尔新福司颁行,立宪党颇为满意,革命党则尚有要求俄皇再须退步之处。”[10]除了俄国的“立宪党”受到关注之外,土耳其[11]、波斯[12]的“立宪党”也获得了一些关注。
对于中国而言,随着预备立宪的呼吁与开始,“立宪党”的概念也开始勃兴。当时“立宪党”的概念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狭义的概念,一种是广义的概念。狭义的概念认为,“立宪党”是指海外鼓吹立宪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是清政府所追查的“党人”中的一种。《大公报》某记者指出:“夫所谓党人者,有二种之派别,其一为革命党,其二为立宪党。”革命党的目的在于“颠覆政府,变更君位”,是“与国体为敌”;立宪党的目的在于“推倒专制,实行宪政”,是“与政体为敌”。一开始,两者的行事手段并无不同,“故皆足以为国家之害,而同入于政治犯罪之列”。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全国提倡预备立宪,朝廷应当对立宪党人进行大赦,正所谓“政治既有变更则犯罪必因而宽免”。[13]作者将“立宪党”和“革命党”都归于“政治犯罪之列”,并认为应当加以宽免,符合条件的只能是康梁等人,并未触及国内。
广义上“立宪党”的概念,则是指所有向清政府诉求立宪的政治团体,与后世“立宪派”的概念颇有相似之处。这种概念在《大公报》文章《革命与立宪党》中也得以体现:
“日前,请愿国会代表团事务长孙君洪伊接得革命党人一函,情殊愤懑,词尤激烈。内有主张宪政,崇载满人殊失救国之道,乃汝持之甚力。碎汝之尸,斩汝之首,亦难蔽汝之辜等。语盖因立宪党与革命党其宗旨向来冲突,故如是之势不两立云。”[14]
除此之外,在《民报》中,笔名为“楚元王”的革命者,也从广义的角度定义了“立宪党”。他认为。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变法失败之后呼吁立宪,一些流亡海外的维新党,可以被称为“立宪党”。而在清政府将立宪提上日程之后,张謇、汤寿潜等人受其影响,开始组建预备立宪组织,也可以称为“立宪党”。[15]随着宪政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立宪改革之中,这种广义上的观点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立宪党”不再被视为是有罪的党人,而是被视为合理请愿的群体。
除此之外,“立宪党”也并非是外人所强加,立宪党人也经常自称“立宪党”。谘议局联合会的立宪党人在请愿反对“皇族内阁”时,曾向全国发布了《为内阁续行请愿通告各团体书》,其中提到:“革命党与立宪党宗旨之差异,全在破坏君主政体与巩固君主政体之一点,惟欲破坏君主政体,方期铲除君主制度,皇族更非其所同。惟欲现固君主政体,期君主之永保其神圣,即不得不望皇族之永保其安荣。”[16]请愿代表将自己归纳进了“立宪党”的范畴,属于广义上对“立宪党”定义。
对于“立宪党”的评价,不同的人群观点并不相同。革命党人因为和立宪党人在政治理念上存在不同,所以对“立宪党”颇有批评之意。革命党人认为立宪党人为清政府上条陈,诉求立宪,是为了通过立宪来稳固自己的权势。[17]士绅和议员们对立宪党人进行附和,则是在做“败德乱群之事”,目的是为了攫取自身利益。[18]除此之外,革命者还从满汉民族矛盾的角度,批评立宪党人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这在《民报》之中数见不鲜。
立宪党人的认识则和革命党人不同。《新民丛报》记者“与之”认为,现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救国问题”。无论“革命党”与“立宪党”,只要“合于救国之前提”,就应该联合起来,以共同的行动来改造政府。[19]同时,他也对革命党人的言论进行了批评。他认为革命党人四处渲染“立宪党”卖国,使得人们犹豫不决,不敢党于立宪,并不利于国家进行改革,实现自强进步。[20]
清末时期“立宪党”一词普遍运用于舆论各界,而 “立宪派”一词则较为罕见,其具体含义的定义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例如《大公报》记者夷齐在讨论清末时局时,就自己定义了“立宪派”。他认为中国国内可以分成几个派别:其一是失望派。清政府腐败至极,亲贵握权,贼臣当路,在上者贿赂公行,在下者苞苴并济,而廉洁才智之士反而没有登进之门。他们目睹时局,愤懑无聊之极,因此成为了失望派。其二是祖洋派,中国危弱,力图自强,于是很多人出洋留学。其中的一些人,仅得西洋皮毛而回国,“以为外洋强大,无所不是,中国弱小,无所不非”,崇洋媚外,可以称为是祖洋派。第三种是立宪派,以前的儒生苦守寒窗、磨穿铁砚,所谓“干谒聚会”俱是例行禁止,所以绝少有谋私利的方法。立宪之后,出现了学堂、自治、谘议与资政等诸多名目,为这些人鱼肉百姓提供了便利。百姓稍有不顺,就会被指为抗捐,被指为聚众。以前政界专制,现在是绅界滥权,朝廷离心离德“半由于此”。第四种是随附派,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像墙头草一样随风而向,不为国家前途着想。第五种是强盗派,趁着国家乱局,烧杀抢掠,危害国民的安全。
夷齐定义的“立宪派”由他自己归纳所得,而非是一个固定词汇,体现了此时“立宪派”这一词汇的运用并不成熟。与此同时,“立宪派”一词在清末时期出现的频率非常低,远没有“立宪党”一词出现的频率高。而在后世我们所探讨的“立宪派”,正是这一时期的“立宪党”。后世研究对“立宪党”一词研究的程度不够,而“立宪派”一词在清末的运用并不成熟,就导致了研究者认为“立宪派”是一种文化建构,而事实并非如此。辛亥革命之后,“立宪派”一词逐渐取代了“立宪党”的地位,一直影响到后世。
三、辛亥革命之后,“立宪派”概念的兴起与各方不同的阐释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立宪党人纷纷加入各种不同的阵营,传统意义上的“立宪党”分崩离析。此时,杨度和汪精卫发起了国事共济会,促进南北和平统一,舆论中有了“君主立宪党”和“民主立宪党”的称谓。“君主立宪党”是指在以保存君主制度的前提之下,南北进行议和,实现立宪政体,以杨度为首。“民主立宪党”则是指以共和制度为前提,实现立宪政体,以汪精卫为首。国事共济会宣言提出:“中国自有立宪问题发生国中,遂分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两党为主。”[21]也就是说,国事共济会将“革命党”也纳入了“立宪党”的范畴之中,将其命名为“民主立宪党”。通过“君主立宪党”和“民主立宪党”的称呼,使得双方具有了共同点——立宪。有了共同之处,就有了谈判的可能。“君主立宪党”与“民主立宪党”概念的产生,与当时的形势息息相关。随着国事共济会的失败以及清帝的退位,这两种称呼昙花一现,不复存在。在此之后,“立宪党”的概念又回归之前,和以往大致相同。即便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辛亥革命之后,随着传统的“立宪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分崩离析,其具体含义越来越受到舆论、政治、学术的影响。
民国成立之后,传统意义上的“立宪党”在政治上更加碎片化。汤化龙、谭延闿、孙洪伊等原立宪党人,此时或植根于国会,或执政于地方;或与北洋政府合作,或与孙中山等人合作。他们各有风云际会,分属不同阵营,不能称作一个政治集团。不过虽然“立宪党”走入历史,但是原“立宪党”人并未走下政治舞台,他们继续在民初政治中发挥着影响力,因此“立宪派”一词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多。“党”的含义具有政治属性,而“派”字的含义具有群体属性,称呼这一群体为“立宪派”,显然更加符合当时语境。最终“立宪派”的使用频率超越了“立宪党”,成为了指代这一群体的名词。不过这些改变属于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一时期“立宪党”和“立宪派”是混用的,词义也并无太大的区别。
除此之外,民国初年各界对“立宪派”范围的界定,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将哪些人划归“立宪派”,将哪些人划出“立宪派”,这一时期颇受政治因素影响。据《申报》报道,唐绍仪内阁时期,由于同盟会在参议院受到其他党派的攻击,“同盟会员且责其参议员之无能,有关系之报纸日惟以空言恫吓,不曰某为立宪党宜处死刑,即曰某为保皇党宜处死刑,并云参议院不足代表全国,宜付之一炬。”[22]可见民初政党政治时期,给政敌定性为“立宪派”,成为了一部分政客获取政治利益的手段,具有政治趋向性。
作为革命党人的章太炎,在从事政党政治时,对“立宪派”的概念有着自己的理解,他在致张继和于右任的书信中指出:
“溥泉、伯循诸君左右,昨承饷食,恳恳以帝制复兴为虑,而言保皇、立宪诸党之不可信,不知此但少数人耳。资政院、谘议局人不可称立宪党,立宪党亦与保皇党殊。保皇党始起也,无过康梁辈数人,本与西太后抗,而非为保其旧君。清景帝殁,名义复无所托,康梁素在神户亦已宣告割辫,渐有转移矣。武昌倡义,汤济武乃为元功,此独非保皇党耶……”[23]
章太炎将“立宪派”与“保皇党”区别开来,而且还将汤化龙等谘议局、资政院成员排除在“立宪派”之外。在我们后世的研究中,汤化龙等谘议局议员请愿要求立宪,属于“立宪派”首领无疑,章太炎却将他们排除在外,说明章太炎眼中的“立宪派”与后世大相径庭。
在章太炎“根本改革团”成立大会的演讲之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佐证。章太炎提出:“现在革命虽成,而政治腐败如昔,其病根实由前清嬗蜕而来。前清末造,亲贵弄权,而为之翼者,即一般脂韦龌龊、机械变诈之立宪党。”民国成立以来,“此种无耻之立宪党又欲乘机而踞要径”,“各政党中如国民党、共和党又为改立宪党人所蛊惑,一变其磊落光明之气”。他还认为,立宪党像“微菌之毒”,最易传染。他成立根本改革团,除了要求五大条件之外,就是为了删除“立宪党”这一祸根,“并非欲破坏大局而推翻政府”[24]。
章太炎将“立宪党”描述成“脂韦龌龊、机械变诈”的形象,并称其为“微菌之毒,最易传染”。从这个范围来看,既要坚持立宪主张,又要给晚清亲贵“助纣为虐”,还要蛊惑国民党、共和党,符合条件的群体不多。章太炎将“立宪党”的危害扩大,实际上缩小了“立宪党”的范围。在演讲中,章太炎还提出:“吾辈所谓根本改革团者,除要求五大条件外,即欲删除此祸根而已,并非欲破坏大局而推翻政府”,可见这是一篇具有妥协性质的演讲,其目的是为了打消政府对“根本改革团”的忧虑。所以在章太炎的观念之中,“立宪派”是一个比较小的范围。
与此同时,作为原“立宪党”人,梁启超、汤化龙、孙洪伊等人也对“立宪派”有着不同的定义。1912 年梁启超回国,从在报界的欢迎会上,可以看出他对立宪派的认识。梁启超指出:清末从事政治的爱国人士分为两派,其中一派是“革命派”,另一派是“立宪派”。“立宪派”不忍生民涂炭,以立宪一词套在清政府头上,使其不得不设立法定民选机关。立宪派凭借民选机关与清政府一战,力图实现政治变革。他认为政治进步是十余年来立宪、革命两派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能忽视“立宪派”在此过程中付出的努力。[25]
梁启超提出“立宪派”凭借民选机关与清政府一战,实际上将清政府内部诉求立宪的大臣——杨度、李家驹等人排除在“立宪派”范围之外。不过相对章太炎等人对“立宪派”的定义,它的范围依旧扩大很多。以此为标准,不论是海外诉求立宪的康梁等人,还是国内请愿立宪的汤化龙、谭延闿、孙洪伊等人,都属于“立宪派”的范畴。
和梁启超相同,作为原“立宪党”人的孙洪伊,也将“似立宪非立宪之官僚派”排除在“立宪派”之外。他在演讲中提到:所谓“革命派”所谓“立宪派”,手段虽有不同,究其最终目的都是希望国家“有真正立宪政治之一日”。两者理念并无冲突,应该更加团结,不应制造对立,否则就会使“似革命非革命之暴烈派乃出而愈肆其凶”,“似立宪非立宪之官僚派乃乘之用其播弄手段而谋逞其私利”[26]。不难看出,梁启超与孙洪伊对“立宪派”的定义,都是企图通过与清末“官僚派”割裂,使自己获得新生共和国的最大认同。
从梁、孙二人的演讲中,我们还可看到,相对于革命党强化“立宪派”的概念,原“立宪派”人士不愿对前清的“立宪派”概念过度强调。立宪党人汤化龙就对革命党强调派系划分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国家初造,政治利害多为国民全体所共同,或有分歧,不过一人一事观察立论之殊,决非全体根本之异。”所以无论前清时期如何从事政治,此时都应当“舍小异而取大同”,“自无旗帜各树之必要”。革命初成,正值人才恐慌,“所谓立宪派者,靡不愿披诚沥胆与革命英俊谋”,希图共济时艰。只有破除壁垒,携手同行,国家才能焕发生机。[27]
除了梁启超、孙洪伊等人,参与到清末政治中的杨度,对“立宪派”也有着自己的定义。杨度宣扬“立宪派”概念,正值其倡行帝制时期。他在《君宪救国论》中提到:
“前清光绪季年,皇室危机已著,排满革命之言充满全国,及立宪党崛起,发挥主义,实际进行,适大总统方掌军机,知清室自救之方无过于立宪者,即以此为其最大方针,隐然为全国立宪党之魁……使清室真能立宪,则辛亥革命之事可以断其必无,盖立宪则皇族政治无自发生故也。乃天祸中国,大总统之计划未行而朝局以变,漳滨归隐之后,立宪党失主持之中坚……立宪党政策不行,失信用于全国,于是革命党代之而起,滔滔进行,所至无阻。”[28]
杨度和汤化龙、梁启超等人不同之处在于,他将诉求立宪的清政府官员归纳进了“立宪派”的概念之中。这些官员不仅包括像杨度这样的底层官员,还包括像袁世凯这样的高层官员。他将袁世凯塑造成立宪派的领导者,无疑会增加他的称帝的声望,也符合杨度一直以来君主立宪的诉求。
由于“立宪派”本身词义的模糊性,使得在不同局势下,不同政治人物的眼中,“立宪派”都有不同的定义。杨度政治理想的失败,梁启超与孙洪伊对“立宪派”的认识颇受各界认同,形成了后世定义“立宪派”的基础,此后几十年立宪派概念的发展,都是基于梁启超与孙洪伊的对“立宪派”的定义,也说明了“立宪派”一词并非完全是文化建构,而是客观存在的政治力量历史研究重视研究对象的时代性,因此探究不同时期我们对“立宪派”概念的认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清末民初“立宪派”概念的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从而以求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