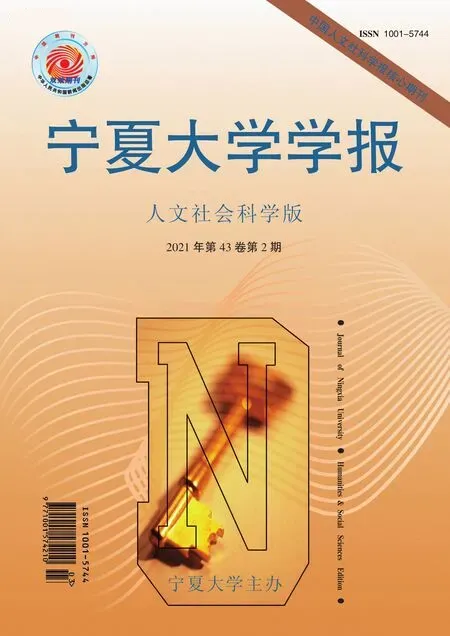宁夏学者吴复安生平及著述述略
行怡帆,田富军
(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吴复安是清末民初宁夏地区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他的生平和著述对研究清末民初宁夏的社会状况及地域文化非常有价值。但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对吴复安的关注度不高。关于吴复安的生平,宁夏地区的期刊有过一些介绍,如《青铜峡文史资料》《银川风物志》等,但总体而言较为简略,缺乏对吴复安生平的整体梳理。关于吴复安的著述,目前仅涉及诗歌的研究,如梁艳的《清末民初宁夏诗人吴复安的诗歌创作探究》及王茜子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宁夏诗人研究》,但未对吴复安著述的传世及散佚情况做分析,也未关注吴复安的文。本文将吴复安的生平划分为四个阶段,相对完整地梳理吴复安的人生轨迹。并对吴复安的著述概况加以分析,探讨其诗文的内容以及各自所蕴含的情感。
一 吴复安的生平
吴复安,字心斋,号静安,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卒于民国九年(1920年)。吴复安孙吴尚贤在《吴复安事略》中载:“先祖父吴复安,字心斋,号静安……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农历十月十六日,殁于民国九年(1920年)农历五月十三日,终年四十九岁。”[1]
吴复安为宁夏宁朔县大坝沙湾村(今青铜峡市大坝乡沙湾村)人。《民国朔方道志》载:“吴复安,字心斋,宁朔县举人。”[2]《青铜峡史话》记载吴复安为“大坝沙湾村人”[3]。《历史银川》《宁夏·银川风物志》与《宁夏五千年》均记载吴复安为今青铜峡市人,而《银川》中载吴复安为今银川市人[4]。《宁夏历史地理考》:“宁朔县,清雍正二年,以宁夏右屯卫改县……辖境相当今银川市、永宁县、青铜峡市、贺兰县部分地区。”[5]宁朔县辖区大坝堡是今青铜峡市大坝乡,因而可以确定吴复安为今青铜峡市大坝乡人。
吴复安之父吴监川,字月照,宁朔县贡生。同治年间,吴监川“督率乡人守其堡寨……以军功赏给蓝翎”[6]。叔父吴盈川、吴巨川、吴在川均为当时的庠生。吴复安之兄吴复兴,字振庭,宁朔县恩贡生。《民国朔方道志》评价吴复兴:“学问优长,课读以勤严著……其培植文风,有足多者。”[7]二兄长吴复太为附生,曾任唐徕渠首事。吴复安之子吴杰,字汉三,曾在沙湾村的私塾任教,之后从事水利工作。吴复安孙吴尚贤一直从事宁夏的水利工作,先后任水利局副局长、宁夏水利协会名誉理事长[8]。吴复安家族在其乡颇有地位,对其乡的教育及水利工作多有贡献。
吴复安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科举应试期、致力新学期、投身革命期、潜心修志期。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之前,即吴复安32岁之前,其主要致力于传统士子应试之路。科举制废除之后,吴复安投身于宁夏地区诸多事业的发展中,主要是实施新式教育,参与宁夏地区的革命以及地方政府的建设,纂修地方志。
(一)求学科考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之前,吴复安主要致力于科考。光绪十九年(1893年),吴复安参加了兰州癸巳科乡试,中举,排名第二十五。《青铜峡史话》中对吴复安的科举年份记载有误,“光绪十九年(1893年),参加兰州癸卯科乡试,考中第二十五名举人”[9],光绪十九年(1893年)是癸巳年,光绪癸卯年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吴复安赶赴北京参加癸卯科考进士的会试,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会试沿途,吴复安拜会名人,游历名胜古迹,并写下了诸多诗作抒发其感慨,如《赴京会试有感》《过潼关雨》等。《赴京会试有感》中载:“不畏风尘苦,驱车向北京。名虽题雁塔,志敢懈鹏程。”[10]既描写了路程的遥远艰辛,又抒发了自己想要建功立业的壮志。
这次会试吴复安并未考中。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科举制废除,乡会试全部停止。吴复安的科考之路也随之结束。
(二)致力新学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到民国元年(1912年),吴复安主要从事教育事业。《民国朔方道志》评价吴复安:“历膺郡城中学师范各校监督,发明科学,训士有方,士子翕然从焉。”[11]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吴复安便在沙湾村吴家庙开办私塾。但吴复安所倡导的新学之路是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开始。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提倡各地兴建新式学堂。但宁夏地处偏远,教育明显落后。吴复安为此多有遗憾:“朝廷下变法之诏,毅然改弦更张,停科举……普建学堂,以育人材。维时我宁僻在边域,士风锢塞。”[12]其他地区校舍林立,生徒莘莘,而宁夏地区却无教书育人之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宁夏知府赵惟熙将银川试院改为宁夏府中学堂。”[13]赵维熙聘任吴复安为副监督,此学堂象征着宁夏新式教育的开始。
吴复安任学堂副监督和正教习,负责学校的行政和教育工作。宁夏府中学堂的课程设置依照1904年颁布的《中学堂章程》,“见有格致即今之物理、化学……统称为格致。勾股即今之数学。舆地即今之地理,国文、军事等课”[14]。宁夏府中学堂是宁夏第一所新式学堂,首次采用了中西结合的教学方式。吴复安感慨:“噫!宁自兵燹以后,元气重伤,旧学半芜,遑问新知,至今世之所为科学者……始渐进而入文明之域,斯固我宁之幸福也!”[15]
然而宁夏地处偏远,近代科学和新思想影响很小,且学校的西式教育并不正规。受时代、地域及经济因素的阻碍,宣统三年(1911年)宁夏府中学堂被迫停办[16]。虽然新式学堂的创办以失败告终,但它开启了宁夏新式教育的先河。
(三)投身革命
吴复安无晚清士大夫的迂腐和保守之气,在新思想新政权萌芽之时,积极地投身到宁夏地区的革命及地方政权的建设中。
1911年11月23日,宁夏成立革命军政府。吴复安为革命军成员之一,“11月21日,‘宁夏革命军同盟会支部’召开扩大善后会议……推举乡绅吴复安等人,为宁夏咨议局筹备委员……11月23日……‘支那宁夏革命军’政府在宁夏府城原道台衙门宣告成立”[17],吴复安为革命军中乡绅阶层的代表。
民国二年(1913年),吴复安被推举为议长。《民国朔方道志》卷十八:“吴复安,正议长,宁朔举人,民国二年推定。”[18]此次选举是依据票数的多寡,“民国肇元,以民情壅闭设县议会、省议会、众议院为人民之代表。其制:投票选举,得票多者为议长,少者为议员”[19]。吴复安当选为宁夏县、宁朔县议长,其在宁夏地区的名望可见一斑。然而,吴复安任职半载,便因与当政者意见相左,辞去议长一职。在这之后,吴复安一直赋闲居家。
(四)潜心修志
民国六年(1917年)到民国九年(1920年),吴复安受马福祥之邀负责《民国朔方道志》的编修。关于吴复安开始修志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为民国六年(1917年),一为民国七年(1918年)。《历史银川》载:“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秋……纂修《朔方道志》。”[20]《吴复安事略》亦载“民国六年(1917年)秋”[21]。《民国朔方道志》载:“民国七年,续修道志,复安充任编辑。”[22]王之臣在序中说:“民国丁巳……聘朔邑举人吴君心斋以主任之。”[23]对修志时间上的异议,胡玉冰在《宁夏旧志研究》中的表述是:“盖民国六年(1917)动议修志,七年(1918)正式修志。”[24]其说是。
吴复安为志书纂修的主要负责人,其他成员有黄光筼等。黄光筼,字润生,宁夏近代著名教育家。然而撰稿进入起步阶段,吴复安身患痢疾,病逝于奎星楼。吴复安去世后,修志的书籍手稿散失很多,修志所用的《乾隆宁夏府志》和一些其他材料由黄光筼保存下来。黄光筼1953年任宁夏文史馆馆长,将这些资料存于宁夏文史馆,即今宁夏文史研究馆。
《青铜峡史话》载:“吴复安病逝后,《朔方道志》编修由王之臣接办,民国十五年(1926年)定稿。”[25]事实上,马福祥并非一开始就任命吴复安主持修志事宜,而是先聘用王之臣。《民国宁夏县长录》中记载马福祥与朔方道尹陈必淮经过筛选之后,选定了盐池县知事王之臣[26]。但当时西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灾荒,王之臣被调往平罗县任知事,修志之事被搁置。民国五年(1916年),马福祥重操修志一事,就选用吴复安主持修志事宜。吴复安病逝之后,民国十三年(1924年),马福祥又任王之臣主持编修《朔方道志》。[27]
民国九年(1920年)五月,吴复安葬于大坝祖茔。吴复安一生为宁夏地区诸多事业的发展不遗余力,在宁夏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名望,“出殡时送葬队伍出银川南门后,有几里路长”[28]。
二 吴复安的著述
吴复安一生潜心经史,著述颇丰。手稿、书籍、碑帖、乡试围墨的木刻板等累计有700余册。但如今,这些著述并未完全留存下来。吴复安的手稿有两本,所存书籍中有《兰河主人书目》。所存碑帖中有《康熙宸翰》,即康熙帝的墨迹,吴尚贤误作“康熙定翰”。雕版所刻内容为吴复安乡试的朱卷。1964年,吴尚贤将吴复安留下的资料悉数捐给宁夏图书馆。1988年,吴尚贤在宁夏图书馆已经查找不到《康熙宸翰》及《兰河主人书目》。今查宁夏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吴复安的手稿、书籍已不见收录。宁夏图书馆目前存吴复安参加兰州癸巳恩科乡试的三块朱卷雕版。该雕版半页十二行,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首先记载的是吴复安的姓名和履历,然后载始祖以下尊属及兄弟叔侄、妻室子女,附载授业、授知师等。
吴复安的手稿有2本,1本收录诗稿、日记等,1本为读书笔记[29]。关于吴复安的手稿出现了3种不同的名称:《集虚斋草编》《集云斋草编》《集墟斋草编》。《吴复安事略》中前文记载“残存手稿《集虚斋草编》两本”[30],后文记载“手稿《集云斋草编》”[31]。《宁夏·银川风物志》记载:“手稿《集墟斋草编》两本”[32]。《青铜峡史话》中记载吴复安的手稿名为《集云斋草编》[33]。吴复安字心斋。“心斋”与“集虚”语出《庄子·人间世》:“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34]。“集虚”多用于书斋名,指主人修身养性之所,清代学者方楘如就将其书斋命名为“集虚斋”。可知,“集虚斋”为吴复安书斋名,吴复安手稿也应为《集虚斋草编》。
(一)吴复安的诗
吴复安的诗歌原收录于《集虚斋草编》第一本。吴尚贤所见诗歌大概有140首:“先祖父遗留诗稿,共捡得一百四十首。”[35]但如今这140首诗歌并未完全留存。《民国朔方道志》收录吴复安3首诗歌:2首《贺兰怀古》和1首《青铜禹迹》。吴复安的诗多为组诗,因而有些刊物在收录的时候将同一题名的2首诗合为了1首,如《银川市志》和《历代诗词咏吴忠》。《银川市志》在附录中收录的《贺兰怀古》是将2首七律合为了1首。《历代诗词咏吴忠》中将2首《杂咏》、2首《书斋有感》分别合为了1首。《青铜峡文史资料》中收录了49首诗歌。杨继国、胡迅雷主编的《宁夏历代诗词集》在第5册中收录了吴复安诗歌54首,此书主要汇集了《银川市志》《历代诗词咏吴忠》《青铜峡文史资料》中收录的诗歌,有个别篇目重复。除去重复的篇目,目前搜集到的吴复安的诗歌共计52首。根据诗歌内容,可以将诗歌分为写景纪行诗、怀古诗、抒怀诗、拟陶诗、咏物诗、田园诗、赠友诗。
第一类写景纪行诗主要描写诗人出游的所见之景,代表作有《三十五日游紫金山》《九日游贺兰山》等。诗中既描写了宁夏地区的自然风光,如紫金山;又涉及了独特的人文景观,如青铜峡一百零八塔。吴复安在描写景物的时候善于从广阔的视野入手,如《三十五日游紫金山》颔联“平看白塔中峰时,俯瞰黄河一带环”[36]。作者运用了两种视角,平视白塔见其立于山峰之中,俯视黄河犹如一条环带,突出了白塔、山峰、黄河的旷远之感。《九日游贺兰山》尾联:“乘兴登高遥望处,山河环抱壮边城”[37],道出自己登高望远,心胸开阔之乐。吴复安有多首登高之作,早期诗歌重在写景纪行,格调欢快;晚期登高之诗感慨自哀,多抒发年华荏苒,锐气消磨之郁。
第二类为怀古诗,作者主要将宁夏古代群雄逐鹿的场面与如今的萧条之景作对比,抒发世事变迁之感。此类诗主要有《贺兰怀古》组诗,其大致内容相似,开篇皆描写贺兰山之景,“贺兰山色望玲珑,虎踞龙盘气象雄”[38],突出贺兰山的雄浑与巍峨。诗的后半部分采用对比的手法,五言中的“或为赫连城,今见沙草寒。或为元昊宫,今只余荒坛”[39],将赫连勃勃与李元昊的宫城与如今的荒凉沙洲作对比,抒发物换星移、世事沧桑之感。同时又以古讽今,暗含对现实的不满与无奈。
第三类诗为抒怀诗,吴复安在诗前小序中写道:“民国癸丑,余赋闲家居,春日无可消遣,偶感成此俚句,非敢问世,聊以自娱。”[40]根据诗歌内容,可将其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作者针对时局而发,另一种是作者即自身之事而发。第一种抒怀诗的代表作有《闲居赋》其五、其六、其七。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动荡,吴复安在诗中感叹“怅望中原似火煎,新亭洒泪空渺然”[41],主要抒发自己对时局的忧虑。第二种抒怀诗有《书斋有感》《闲居漫兴》《春日抒怀》等。民国二年(1913年),吴复安任夏、朔县议长,未及半载,便辞官回乡。作者在诗中说明了自己辞官的原因:“只因性疑难谐俗,到老还耕一砚田。”[42]吴复安耿介的性格难以适应复杂的官场,此类诗主要抒发作者不愿迷失自我,不愿与他人同流的心境。
第四类拟陶诗与第五类咏物诗,在情感上与抒怀诗的第二种有相似之处,作者在诗中主要表达自己淡泊名利、耿介正直的品性。拟陶诗的代表作有《拟归去来兮辞》《拟陶渊明〈读山海经〉》等。“不必羡丘壑,不必入泉林……寰中理乱休闻问,且耕且读终残年”[43],诗人不愿为世俗所累,只愿归隐田园,了此余生。吴复安的咏物诗,重在托物言志,如《寒梅》《秋菊》《老松》等。“不与牡丹争富贵,独摇清影上瑶台”[44],梅花不屑俗世的富贵,在瑶台独自绽放,正如诗人不慕利禄,不弃傲骨。《青铜峡史话》中评价吴复安:“他不容于世俗,为人正直,常以松、菊自比,表现出令人敬慕的品格。”[45]
田园诗以《归田》等诗为代表,如“归来小憩柳荫下,共话桑麻到晚天”[46]。此类诗描写田间的惬意生活以及表现诗人归隐之后娴雅的情致。
最后一类赠友诗数目较少,《宁夏历代诗词集》仅收录《赠赵寿山登科》,此诗是吴复安赠予好友赵尚仁的诗。赵尚仁,字寿山,灵州(今宁夏灵武)人。《赠赵寿山登科》作于赵尚仁中举之后,诗中载:“独步青云舒骥足,杏林先占一枝春”[47],诗人以腾跃青云的良马与秀于杏林的春色来喻友人,表现了对赵尚仁才华的肯定以及对其前程的祝愿。
吴复安诗歌的内容与清末民初宁夏的社会状况以及自身的经历相关。写景,能突出动荡年代宁夏边地的萧瑟与旷远;写情,能展现社会转变阶段传统士人的无奈与悲凉。其诗歌语言典雅质朴,不重修饰,但情感诚挚。诗中多用典,如“钟期不作知音少”[48],用俞伯牙和钟子期的典故来喻自己知音难觅的惆怅。吴复安的诗歌中最突出的一个主题就是“仕与隐”的矛盾。吴复安早期的诗歌格调高昂,“不畏风尘苦”“志敢懈鹏 程”[49],其间充满对“仕”的期待。而后期官场受挫之后,其诗又主要抒发“隐”的思想。但吴复安的“隐”是迫于无奈的“隐”,他自始至终都希望能有所作为,但官场的体制却与他所接受的儒家传统教育及自身的人格境界相悖。吴复安虽选择了“隐”,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希望能“谁扫胡尘障北边”[50]。
(二)吴复安的文
目前搜集到吴复安的文有3篇:评判时局的《庚子之变》,关于宁夏水利的《上高太守禀》以及创办宁夏府中学堂时撰的《新建宁夏中学堂碑记》。
1.《庚子之变》
五路ST188的光电传感器放置在小车的底盘,位置如图3所示。建议三角形排布,把一路传感器放置于小车的最前方,便于提前获取道路信息,及时做出姿态调整。另外的四路分别位于小车的两侧,成三角形形状。五个传感器获取的数据构成一个字节的高5位,经过施密特触发器放大后滤波,反相送入STC12C5A60S2的P0口。
《庚子之变》原收录在《集虚斋草编》第二本,吴尚贤将其摘录于《吴复安事略》中。此篇文章是吴复安读王夫之著述之后,结合时局有感而发。在他的文末记载:“余读王船山之论,因感而记此”[51]。《庚子之变》作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此篇文章中,吴复安批判清政府的腐朽及愚昧,同时也针对国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主战派利用义和团对付外国侵略者,最后以失败告终。吴复安在文章中提出朝廷若用义和团御敌,“必贻误大局,时人多目笑之”[52]。吴复安认为官员党派之间的倾轧加深了清政府的腐朽以及国家内外交困之局面:“我中国至今日贫弱之亟矣,外洋之欺辱中国……庚子之祸,岂尽主战之罪哉,亦有新旧两党相倾相轧,敝之使然也。”[53]针对国家内忧外患的局面,吴复安提出理财、练兵、固邦、御外四个策略,认为朝廷要“修明其政事,激励其人心”[54]。
受时代思想的局限,吴复安对清政府还存有希望,且只看到了造成“庚子之变”表面的原因,即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斗争。但从吴复安对义和团和清政府的批判中能够看出吴复安思想所具有的民主性和先进性。
2.《上高太守禀》
《上高太守禀》原收录在《集虚斋草编》第一本中,民国七年(1918年)《河套水利考察报告》收录此文。之后《宁夏水利志》也收录了此篇文章,将题目更改为《言渠务利弊书》。
《上高太守禀》大约作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之间,是吴复安写给时任宁夏知府的高熙喆。吴复安从六个方面揭示了宁夏地区渠务的积弊,分别为:冗费之敝、购料之敝、修浚之敝、封水之敝、报销之敝、估工之敝。文章开篇就指出了宁夏水利之弊在于人为:“司事者不能实心任事精勤以图治,而局员与局绅亦只奉行故事敷衍了局。”[55]六项积弊的矛头都直指负责渠务的官员,吴复安揭露他们欺上瞒下,牟取私利的恶行,“如彼涸辙之鲋,未得涓涓之润,而反索之枯鱼之肆,以有尽之民膏,填无穷之溪壑,良可悲悯”[56]。
3.《新建宁夏中学堂碑记》
《新建宁夏中学堂碑记》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吴复安为宁夏府中学堂所作,此碑原立于文庙西山墙之旁,原碑已毁,碑文收录在《民国朔方道志》卷二十七《艺文志》中。
此碑文颂扬了赵维熙为中学堂所做的贡献:“夫泰山之云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我公盖宁之泰山也。”[58]亦说明了中学堂的成立于宁夏新学发展的意义:“一洗从前之固陋,而竞进于文明。”[59]碑文情感较为丰富,多赞颂感慨之词,能够体现出吴复安对宁夏新学教育的重视。
吴复安的诗多抒己情,文多抒己见。文针对事件而发,不作敷衍之辞,直切时弊:提出“庚子之变”在于两党倾轧,水利之弊在于官员腐败。语言风格鲜明:在批判清朝当政者及宁夏官绅时,文笔犀利;在评价赵维熙时,又多溢美之词。吴复安的文章多议论,也富含感情,在批判的背后体现的是对国家、对宁夏人民的重视。
吴复安的一生处于清末民初新旧政权交替的阶段,从科考之路结束到参与革命到赋闲居家再至修志,他的生命轨迹也与整个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吴复安的著述虽然留存不多,但对于研究清末民初宁夏地区的社会状况及地域文化而言,是非常珍贵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