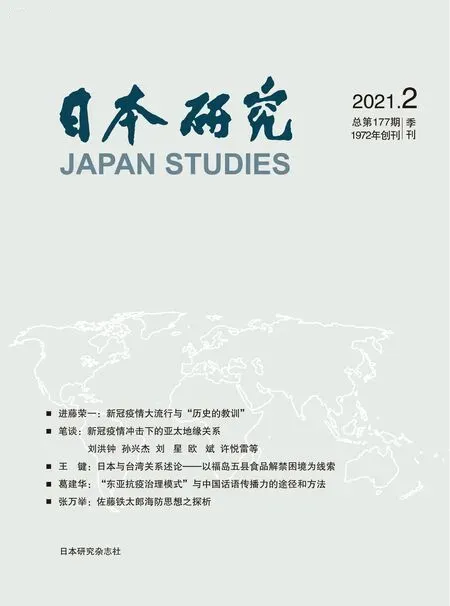“印太”:多重空间及其秩序演化
孙兴杰
进入21 世纪第三个十年,全球地缘政治板块中最热门的一个词无疑是“印太”。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举行了美日澳印四国首脑视频会议,并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首脑联合声明,将四国在“印太”地区的合作追溯到2004 年的印度洋海啸。“印太”从概念变成了地缘政治行动,进而上升为美国这一霸权国的重要战略行动。当媒体和学术界不断追捧“印太”这一概念的时候,不禁要问,“印太”所指代的“事实”到底是什么呢?从美国在2019 年6 月正式出台《印太战略报告》到2021 年拜登召集美日澳印四方首脑会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印太”空间真的形成了吗?作为话语的“印太”在极速膨胀,不仅印太相关国家出台了所谓的印太战略文件,连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也出台了类似的战略文件;作为“空间”的印太并非由话语界定的,而是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相关建构的产物。印太秩序的演化基于多重空间,而多重空间的互动则框定了作为战略话语的印太的限度。
作为战略话语的印太是不是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呢?2006 年安倍晋三在日本国会首次演讲中提出,除了日美同盟之外,日本需要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具有“共享价值观”的国家举行最高级别的战略对话,换句话说,以意识形态划线,推动所谓的价值观外交。2007 年,安倍在印度国会发表题为“两洋交汇”的演讲,他认为,太平洋和印度洋正在作为自由和繁荣之海发生充满活力的联结,一个打破地理疆界的“扩大的亚洲”开始形成了。印度学者库拉纳则以“印度-太平洋”来指代濒临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亚洲和东非国家。2009 年美国著名地缘政治战略专家罗伯特·卡普兰在《21 世纪的中心舞台》中阐述了对“印太”的看法,使得这一概念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关注。2013 年,安倍再度担任首相之后提出“安全菱形”的概念,包括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夏威夷,构建一个新的安全合作机制。在访问华盛顿期间,安倍再次推销印太概念。2016 年,安倍晋三在肯尼亚举行的第六届非洲发展会议上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概念,不仅包括意识形态的维度,还将经济援助和经济发展纳入其中。可以说,安倍晋三是“印太战略”的鼓吹者,但此时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核心战略概念是“亚太再平衡”,与安倍的“印太战略”还是存在差别。作为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的国家,日本更大程度上是“尾随”美国,而不可能以理念去引领美国。
安倍晋三是“印太”战略的倡导者和鼓吹者,在这一概念提出十年之后,美国政府换人,特朗普上台,美国开始接受“印太”的概念,2018 年制定了印太战略框架文件,作为2017 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延续和具体落实,成为特朗普任内美国接受和推进印太战略的纲领性文件。从美国披露的文件中可以看到,美国已经将“印太”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战略博弈空间,“‘印太战略’是美国均势+有限遏制+规制+话语诋毁的混合型战略”。[1]2020 年特朗普败选,在其下台之前居然提前解密了2018 年的印太战略文件,以保持美国政府印太战略的延续性。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并未逆转或者推翻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相反,升级了印太战略,并进一步将印太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支点。印太,已然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空间。“作为国际权势动态转移的发生地和目标场合,当下的‘印太’地区无疑触发了大国间最新一轮关系重组与地缘竞逐。其间的战略博弈态势正显现出鲜明的特征:由陆向海、依海强国已然成为各大国实力、谋略及意志对决的基本战略取向。”[2]作为概念和话语,日本首相安倍是主要的鼓吹者,而特朗普则将印太从概念变成了美国的战略行动,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印太变成了全球地缘政治空间的核心。“印太”话语形成、传播和转化已经成为一种强势话语,也被很多学者所接受,需要反思的问题在于:第一,印太战略的空间基础何在?第二,印太秩序的主体是谁?以何种方式构建新的空间秩序?
作为话语的“印太”和作为秩序的“印太”之间已然存着巨大的鸿沟,换句话说,印太是被制造出来的概念,尤其是作为战略图景、甚至美国战略手段的印太缺乏基础。印太战略空间是日本、美国制造的强势话语,而“印太”的空间是多重和多层的,远远没有成为美国主导的地缘战略空间。事实上,印太是一个多重、多层的空间,只有理解了它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才能避免陷入美国、日本主导的强势的“印太战略”话语陷阱之中。
第一,“印太”的说法源于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弗,他在《太平洋地缘政治》一书中对“印太”空间进行了系统论述。印太,在豪斯霍弗看来是一个与欧洲空间相对立的概念,太平洋和印度洋构成了一个声明的统一体。“太平洋海岸类型经由巽他海峡深入印度洋,正如动物地理学也反对将印度-太平洋的区域范围延伸到大西洋区域。”[3]豪斯霍弗从海洋生物、洋流系统、面积、海岸系统等方面论述了印太作为一个地缘空间成立的条件和因素。他认为,“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演化仍在继续,根据自身的法则,首先趋向于形成由周边国家组成的超国家组织。太平洋的边缘率先形成印度-太平洋的、东亚的、泛美的部分联盟的空间。人类的生命形式在太平洋生存空间变得愈来愈宏大,在欧洲-大西洋生存空间则变得愈来愈逼仄。”[4]豪斯霍弗构建“印太”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应对欧美的海上霸权。德国是个后发国家,错失了卡尔·施密特所说的“空间革命”,[5]也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所形成的海权系统对欧洲大陆形成了挤压和控制。海权所形成的大洋空间承载了新的财富和权力,德国虽然并非海权国家,但是要在未来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也要争取在海洋空间中占据一席之地。“鉴于‘欧美’在南亚、东亚、东南亚深耕已久,德国此时加入耗时耗力必巨。因此,不论他个人观点如何,德国不可能作为传统的殖民帝国与英国争雄。豪斯霍弗提出的解决方式是促使‘印太’地区转变为自主自决的政治体,由德国训练的印度领袖领导反英国殖民斗争,由德国训练的中国军队稳定中国局势。如此一来,看似柔软但实力雄厚的‘印太’海洋带可与德国在欧亚大陆上开辟的政治空间遥相呼应。如果形势大好,‘印太’盟友即可促进德国陆路发展。”[6]豪斯霍弗的思想在日本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并且成为日本在东亚扩张的理论依据。因此,安倍晋三的“印太战略”不过是掸去了豪斯霍弗的“印太”理论的历史尘埃,以新的面貌重新示人。但安倍晋三的“印太”比豪斯霍弗的“印太”更狭隘,也更具有针对性,那就是针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
第二,“印太”背后的“亚洲地中海”的想象。从海洋视角来看,印太形成了广阔的海域,东南亚群岛是印太海洋空间的核心地带,而印太与亚洲大陆相接的地带是一片边缘海,为人类的迁徙和贸易提供了舞台。“马六甲的贸易网络,在每一个节点都与通往印度、波斯、叙利亚、东非和地中海的其他网络相连,最终构成‘当时最大的贸易体系’。它包括从爪哇岛东海岸到巽他海峡的区域,涵盖爪哇中东部,爪哇西部和苏门答腊,同时还链接爪哇与巴厘、龙目岛和松巴哇,连接帝汶岛和松巴岛及摩鹿加群岛。”[7]随着欧洲人的殖民扩张,印度洋、太平洋被卷入到欧洲殖民体系之中。殖民帝国建立在海权基础之上,地中海是海权文明的发源地,从腓尼基到雅典,从威尼斯到英国,地中海成为海权秩序的“原型”。印度洋、太平洋是否存在另外一个“地中海”?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认为,亚洲没有地中海,“东南亚从未成为地中海,我认为东南亚只是个半地中海,因为地中海作为一个权力系统,作为文明的基础,需要从两方施加力量,相互抗衡。这就是一种现实,一种奇怪的动态平衡,各方在和平与战争中保持团结一致,保持统一。”[8]亚洲没有“地中海”,但是印度洋、太平洋,尤其是西北太平洋地区早已形成了一个贸易的世界,“亚太沿岸地区的地图展现的是一个大部分由狭窄水域和宽阔海绵分开的岛屿国家和邻近大陆半岛国家组成的地缘政治区。”[9]在比较“破碎”的地缘空间,商业秩序得以成长。对亚洲海域的“地中海想象”,也激发了欧洲国家对印太的热情。法国和德国先后出台了印太战略文件,其核心原因是印太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极,欧洲大国以及欧盟试图在印太的经济发展中分享红利,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
第三,印太空间的开放性、流动性与裂变性使印太空间难以成为一个封闭的、自我说明的区域单位。作为地理空间的印太早已存在,但是作为政治经济空间的印太依然模糊,人类的互动充实了“空间”,换句话说,互动的频度、广度界定了空间的边界,让空间不再“虚空”,并且具有了政治经济含义。印太是一个广袤的空间,也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其中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一直处于游离状态。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是英国殖民体系的产物,在其独立之后其身份是西方国家还是亚洲国家长期处于模糊之中。因此,印太空间是流动的,是高度异质性的,由此也带来印太空间的裂变性。20 世纪70 年代以来,东亚地区活跃的经济发展带动了西太平洋地区更加绵密的贸易、金融网络的形成,以港口城市为基点形成了一个经济世界,这一发展趋势既激发了东亚国家的自信心,同时也造成了所谓的经济与安全秩序的分离,以中国为主的贸易世界与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之间出现了更大的摩擦。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共同经济发展体系,日本以及美国将“印太”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应空间,遏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势头。而印太的开放性、流变性和内在的裂变性,使之难以成为某一力量主导的战略工具。美日澳印四方只是印太广袤空间中的节点,同时,四方的利益和目标也存在着诸多差异。印太空间过于宽阔广袤,以至于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将其作为“内湖”,印太空间太复杂了,几乎全世界的文化都聚集于此,难以形成具有共同纽带的认同和身份。
第四,印太空间并非纯粹的海洋空间,而是陆海兼备且嵌套在全球体系的空间。豪斯霍弗提出的“印太”概念并非指纯粹的海洋空间,而是一个陆权国家进入世界海洋空间的切入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可以说是海洋国家,但是印度并非海洋国家,而是一个巨型的半岛国家。印太的边界是模糊的,是多个地缘政治板块“交叠”的空间。印太空间可以是陆海二元对立关系的消解之地。英国学者安德鲁·兰伯特认为,英国是最后一个海权国家,但是海权传统留下的市场经济、开放社会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10]21 世纪以来,互联网空间形成,人类经历了又一次“空间革命”,而技术、资本、商品、人员的流动形成了新的经济社会空间,可以说一个全球性空间已然形成,印太是这一单一全球空间的组成部分,已经嵌套其中了。
印太,是一个多重空间叠加的复合体,无论作为自然地理空间,还是作为话语体系,它都不是当下才出现的。美国、日本塑造的关于“印太战略”的强势话语无疑是遮掩了“印太”的本来面目,不是“管中窥豹”而是“盲人摸象”。2019年末,一场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对全球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与此同时,美国、日本推进的印太空间“安全化”也在加速。所谓“安全化”,就是将某项议题或者威胁进行升级和动员,当其变成安全议题时,就可以集中资源予以应对。在2019 年香格里拉对话会议期间,美国推出《印太战略报告》,此后又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印太空间急剧安全化和军事化。新冠疫情之下,美国特朗普政府并未停止印太空间“安全化”的步伐。新冠疫情是对各国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考验,中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恢复经济社会生活,并为世界提供了抗击疫情的物资。
新冠疫情之下,澳大利亚要求对病毒进行溯源调查并甩锅给中国,中澳关系在过去两年中急剧下降至冰点。疫情期间,中印爆发激烈的边境对峙事件,中印关系也出现了大幅度滑坡。在“中国威胁”的话语动员之下,美日澳印四方合作框架形成,其指向越来越明确,即围堵中国。在美日澳印外长会晤机制之下,双边以及小多边的外交、防务合作常态化。2020 年澳大利亚受邀参加“马拉巴尔”联合军事演习。拜登上台之后,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重点外交区域,任命坎贝尔为国安会下设的“印太协调员”,在疫情之下,美国与日韩举行外长、防长“2+2”对话会,美国防长奥斯汀上任首次出访就是印太国家。印太空间的“战略化”力度和速度是空前的,也显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但是,作为战略空间的印太也只是最近一两年才出现的“人造空间”。
印太空间具有多重属性,每一种属性的空间都有其内在的秩序逻辑,多重空间的秩序是“协同演化”,而非人为塑造。印太空间的战略化是当前印太秩序的“热点”,但只是话语的泡沫,真正决定印太秩序演化方向的是“静水深流”的力量。西太平洋“边缘海”地带的国家不愿意“选边站”,而是希望在中美战略平衡之下获得更大的发挥空间,这些中小国家具有浓厚的“海权气质”,而大国间的力量均衡是海权力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前提。二战结束以来,主权国家重塑了印太空间,其情形与豪斯霍弗提出“印太”概念时已大异其趣。东亚地区在过去半个世纪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尤其是中国不断发展,海权与陆权的分野消弭,形成了不断扩大的经济发展空间。“东亚的活力是与跨国资本的大量注入分不开的,本地精英所寻求的并不是一个与其他地区的循环相竞争的地区性积累循环,而是更彻底地融入全球化循环的循环。”[11]2020 年末,全球最大的区域贸易协议RCEP 完成谈判,这既是印太地缘经济空间逻辑的呈现,也是对战略化的印太空间的对冲与平衡。新冠疫情之下,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的经济合作网络的“粘性”更加凸显,中国对外贸易逆势增长,足以说明中国已经嵌入“印太”多重空间,并成为结构性存在。印太的多重空间及其秩序逻辑,框定了美国等国家印太空间“战略化”的限度,同时也为中国积极介入和塑造印太空间提供了诸多选择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