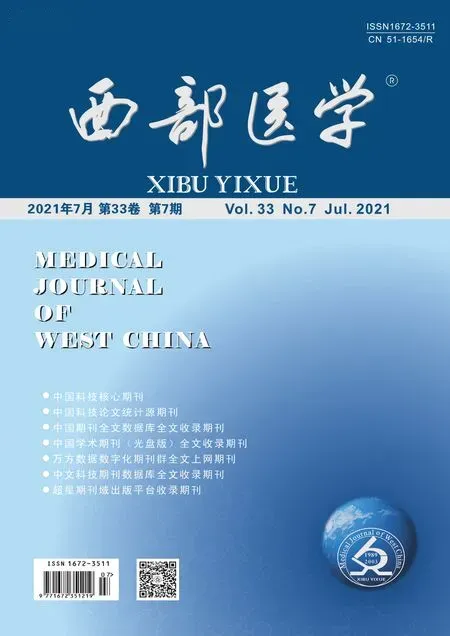肠胶质细胞在炎症性肠病中的作用及变化*
李小青 唐川君 李佳潞 综述 张涛 审校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镜中心·四川大学华西护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2.南充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四川 南充 637000)
克罗恩病(Crohn disease,CD)和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统称为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慢性复发性肠道炎症性疾病。IBD的准确发病机制目前还未研究清楚[1],目前认为其发病与环境、遗传和免疫等相关,其中免疫在IBD的发病机制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IBD也被认为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黏膜免疫系统失衡是导致肠道慢性炎症的主要原因。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仅从黏膜免疫系统层面可能无法完全解释IBD发病过程,因此也开始重视对IBD病理生理学中新成员的研究。许多研究都表明了肠神经系统(enteric nervous system,ENS)在调节肠上皮屏障功能和肠免疫稳态上起着重要作用[2-3]。ENS的改变直接与IBD的发展和症状相关[4-5]。在实验性肠炎和IBD动物模型中也证实ENS,包括神经元和肠胶质细胞(enteric glial cell,EGC)有结构和功能的变化[6]。作为ENS重要组成成分的ECG,其能够调节肠屏障功能和肠道免疫过程,并参与IBD的发生发展过程,其在IBD中的作用也日益受到关注。本文就ENS中EGC在IBD中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1 在IBD中ENS的变化
1.1 ENS的组成 ENS是除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之外最复杂的神经结构,且是仅有的本身能介导反射活动的外周神经系统。ENS能调节和控制肠道结构和功能[6-7]。ENS包含两个主要的神经节神经丛:肌间和黏膜下神经丛。两种神经丛都包含功能不同的神经元和EGC[8]。在人中肠神经元与EGC的比率是1∶7,且肠神经元被EGC包绕[9]。
1.2 在IBD中肠神经元的变化 早在1998年,Geboes等[10]总结了实验性文献中肠神经元的变化情况:有3篇文章报道在CD中肠神经元的损伤较严重,有7篇文献报道CD时肠神经元增生明显;报道在UC中肠神经元轻度损伤和轻度增生的文献各有有一篇[11-12];有一篇文章报道了在CD和UC中肠神经元都肥大,但在CD中,肠神经元的肥大较UC中更明显[13]。Sanovic等[14]在用二硝基苯磺酸的结肠炎模型中,造模24小时后,炎症区域肠神经元大量丢失,在4~6天时仅有49%的肠神经元存活。在肌间神经丛中肠神经节数目保持恒定,但在黏膜下神经丛中肠神经节数目减少了,在平滑肌细胞中轴突的数目不变,在结肠内用布地奈德能导致剂量依赖性的预防神经元损失。 Bassotti等[4]在19例难治性IBD的手术标本(CD患者的回肠和UC患者的结肠)中,证实在CD患者病变回肠的黏膜下和肌间神经丛中,肠神经元凋亡增加了,而在UC中肠神经元凋亡相对较轻,并得出了在IBD中肠神经元的损伤可能是由于凋亡现象,而不是坏死的结论。Gulbransen等[15]使用实验性结肠炎模型证实,炎症导致肠神经元死亡是通过肠神经元上的P2X7受体,Pannexin-1通道,Asc适配体蛋白和caspases通路诱导神经元细胞凋亡的,且氮能神经元首先凋亡。几乎所有关于IBD中肠神经元损伤的研究都证实,在IBD中肠神经元损伤了,且在CD中神经元的损伤较在UC中的要重。
1.3 在IBD中EGC的变化 早在1998年,Geboes等[10]总结了实验性文献中,有一篇文献报道肠CD中EGC增生,对UC中EGC的变化在1998年前无报道。Bassotti等[4]在IBD活体病理标本中证实,在CD患者病变回肠和UC患者病变结肠的黏膜下和肌间神经丛中EGCS的凋亡都明显增加了,但EGCS的凋亡细胞数与IBD中EGC的减少数不平行。Steinkamp等[16]研究表明,炎症因子TNF-α和/或IFN-γ能诱导培养的EGC的凋亡。在一些文献中也报道了在IBD中EGC的数目增加[4]。对IBD中EGC数目的变化还存在不同的研究结果。但EGC在肠道炎症中的作用以及EGC对肠道上皮屏障功能和肠神经元的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且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
目前对EGC的作用的研究认为,EGC已不仅仅是对肠神经元起支持作用的细胞,而是认为EGC是参与调节肠道炎症的关键细胞[9]。Cirillo等[17]研究也证实,EGC对肠道炎症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在两个独立的转基因小鼠模型中,EGC的损失伴随着不可逆的神经元变性和炎症的肠道损伤,而且EGC的功能失调极大地影响了肠神经元的神经化学编码和功能[18]。
2 EGC对肠道屏障的保护作用
2.1 肠上皮屏障的组成 肠上皮屏障(IEB)由单层扩增和分化的肠上皮细胞通过粘附和紧密连接组成。紧密连接由跨膜蛋白组成,通过一个复杂的多种蛋白质(zonula occludens,ZO)与细胞骨架相连,调节细胞间的通透性和细胞极性。许多证据表明,肠上皮屏障(IEB)通透性的改变在IBD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大量的研究观察到IEB通透性的改变先于CD的复发和回肠炎症,且在炎症期间干扰素γ和TNF-α等细胞因子进一步介导了IEB的功能失调[19-21]。这些功能失调其中除了紧密连接改变外,还包括创伤愈合缺陷和或电解质分泌增加。激活肠神经元可通过释放血管活性肠肽(VIP)降低细胞间的通透性,抑制肠上皮细胞扩增,维持肠上皮细胞的完整性;同时增加肠上皮细胞ZO-1 mRNA和蛋白的表达。ENS的神经递质Ach能增加细胞间的通透性[5]。
2.2 EGC对肠上皮屏障的作用 在体实验中,敲除EGC后肠道隐窝增生,说明EGC参与肠上皮增殖的调控。体外共培养模型中,EGC可部分通过TGF-β抑制细胞的增殖[22]。EGC还可通过产生15dPGJ2(15-deoxy-(12,14)-prostaglandin J2 (15dPGJ2)抑制肠上皮细胞的增殖[23]。EGC的功能改变可能通过调节肠上皮的增殖影响肠上皮屏障功能。
Van Landeghem等[24]研究表明,与单纯IEC培养相比,用Genespring分析的方法确定IEC联合EGC培养时,IEC中有116个基因表达与单纯培养的IEC不同,其中70个基因的表达上调了,46个基因的表达下调了。用Ingenuity 通路的方法分析这116个有差别的基因表达时,发现其中92个基因导致了总共10个功能网。这10个功能主要是调节上皮细胞-上皮细胞和上皮细胞-基质粘附,以及上皮细胞分化和细胞运动能力。这表明EGC能使IEC向着能增加IEC细胞粘附和细胞分化的表型方面转化。EGC可能通过此功能影响肠道屏障。在小鼠中敲除EGC可发生暴发性空肠回肠炎[25]。但EGC诱导上皮细胞发生这些变化的机制还不清楚。
EGC可产生多种可溶性介质,胶质细丝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和S-亚硝基谷胱甘肽(S-nitrosoglutathione,GSNO)是EGC分泌的重要的可溶性分子。Costantini等[26]用定量PCR检测发现,在烧伤后早期肠GFAP表达增加,但在损伤24小时后,GFAP的水平又回到了基线。在烧伤之前刺激迷走神经能使GFAP表达的水平增高水平高于单纯烧伤导致的GFAP升高水平。在烧伤后注射GSNO对肠产生的保护作用与刺激迷走神经产生的保护作用相同。这说明刺激迷走神经能增加EGC的活性,从而改善肠屏障功能。胶质源性神经营养因子(glial-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GDNF)也是一类EGC分泌的重要调节因子。GDNF抑制炎症时肠上皮细胞的凋亡,降低肠道通透性,抑制黏膜炎性反应,促进肠屏障的修复[27]。GDNF与RET受体结合招募桥粒结合蛋白(desmoglein 2,DSG2)至细胞边界,增加DSG2介导的细胞间粘附,维持肠屏障的稳定性[28]。吗啡可通过涉及EGC中GDNF表达调控的途径影响肠上皮屏障功能[29]。EGC表达15-脂氧合酶-2,能产生高水平的15-羟基二十碳四烯酸(15-HETE),CD患者EGC的15-HETE产生下降,补充15-HETE的体内外实验显示其可通过抑制AMPK和增加ZO-1的表达调节肠屏障的抵抗性和通透性[30]。EGC通过分泌多种可溶性因子调节肠屏障,在疾病过程中这些改变的重要分泌因子可能是潜在的治疗靶点。
EGC参与抵抗肠道感染入侵的过程。在福氏志贺氏菌感染入侵过程中,EGC通过GSNO降低了Cdc42与p-PAK的表达,且阻止了细菌诱导的ZO-1表达和分布改变,维持肠上皮屏障和抑制细菌移位[31]。同样地,在轮状病毒感染过程中,GDNF和GSNO表达上调,增加ZO-1的表达,抵抗肠上皮屏障破环[32]。但对于艰难梭菌感染,EGC可能与疾病致病机制相关,EGC对艰难梭菌易感,艰难梭菌毒素B(TcdB)可导致EGC细胞周期阻滞和凋亡,但同时也上调GDNF的表达,提示存在一定的自救机制[33]。
2.3 EGC对黏膜免疫屏障的作用 EGC位于肠上皮和黏膜下免疫细胞之间,与周围细胞存在广泛联系。EGC不仅调节肠上皮的增殖、凋亡和肠道通透性等功能,也与免疫调节密切相关。在肠道微生态复杂的环境中,EGC也表达多种与微生物识别相关的受体,这些受体提示EGC一旦被激活可能发挥抗原提呈细胞的功能。EGC上调S100B调节Toll样受体(TLRs)介导的信号转导过程,参与致病菌和共生菌的识别[34]。在炎症情况下,EGC被活化,表达MHC Ⅱ和c-fos,并且发生反应性胶质增生[35]。近期有研究显示氨溴索可作为新型P2X2抑制剂,阻断ATP结合受体P2X2引起神经胶质增生的过程,调节炎症反应[36]。受外界刺激时,EGC可发生形态和功能变化,分泌神经胶质介质和细胞因子,募集免疫细胞,激活粘膜免疫过程[37]。Yang等[38]发现,双歧杆菌和脆弱拟杆菌可通过调节炎性环境下EGC的炎性小体和细胞因子的表达参与炎症过程的调控。EGC的免疫调节过程仍不清楚。Ibiza等[39]研究发现,ILC3与表达神经营养因子的EGC相邻,EGC以MyD88依赖性方式感知微环境变化,调节神经营养因子的分泌,作用于ILC3上的RET受体,导致p38 MAPK/ERK-AKT级联反应和STAT3激活调控IL-22的产生,参与炎症和感染过程。在EGC对T细胞作用的研究中,EGC可以抑制活化T细胞的增殖,而且与对照相比,CD患者来源的EGC细胞具有更强的抑制能力[40]。Pabois等[41]研究发现T细胞有倾向于粘附EGC的特性,在CD患者中也观察道此种特性,但其可能与神经丛炎形成相关,提示EGC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调节局部免疫反应。
3 EGC对肠神经元及EGC本身的作用
研究[39]证实,在ENS损伤,肠神经元受损,EGC被激活,且活化的EGC能促进神经元的生成。von Boyen等[42]研究也证实了,在肠道炎症时,EGC能分泌GDNF。在Hirschsprung病(HSCR)中,GDNF在HSCR患儿的神经节肠培养物中的应用可诱导施旺氏细胞的增殖和新神经元的形成。在HSCR小鼠模型中,GDNF的使用可以延长小鼠的存活时间,诱导其肠神经发生,改善结肠结构和功能[43]。Steinkamp等[16]研究证实,在CD中,EGC通过自分泌的方式分泌GDNF,并通过与自身GFR-a1,2,3结合从而对抗EGC自身的凋亡。
4 炎症刺激后EGC的变化
4.1 炎症刺激后EGC表达蛋白的变化及作用
4.1.1 胶质细丝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 GFAP是分布于神经胶质细胞和神经元细胞的一种中间丝蛋白。GFAP(+)是EGC活化的标志[26]。von Boyen等[44]研究,IL-1B,TNF-α和LPS孵化的EGC中,GFAP(+)EGC表达增加了,IL-4对GFAP的表达无影响,这表明细胞因子在调控GFAP(+)EGC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44]。
4.1.2 胶质源性神经营养因子(glial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GDNF) GFAP和GDNF是活化的EGCs的标志[42]。Von Boyen 等[45]在用IL-1B,TNF-α和LPS刺激培养的EGCs时,发现GFAP(+)EGCs表达了大量的GDNF。由此证明GFAP(+)EGCs是炎症肠段GDNF表达上调的主要细胞来源。与神经元相邻近的平滑肌细胞在TNF-α或IL-1B的刺激下也可产生GDNF[46]。外源性GDNF强烈的促进了神经元的存活。GDNF通过激活神经元的NF-kB通路促进神经元轴突的生长[47]。 von Boyen等[42]采用免疫组化和western blot的方法证实,在UC和感染性结肠炎中GFAP和GDNF在炎症结肠黏膜下神经丛中表达明显增加了;在CD的病变肠段中GFAP和GDNF表达也增加了,但较UC病变肠段明显要少。且与UC未病变肠段和正常对照组相比,CD患者未病变的结肠的GFAP的表达明显减少,而GDNF无表达。在炎症环境中,GDNF通过双重机制发挥发挥抗炎作用:一是以自分泌的方式抑制EGC的凋亡,二是通过旁分泌降低促炎因子的水平[37]。
Hayashi 等[48]研究证实,GDNF与ret受体上GDNF结合的特异性的糖基连接共受体—GFR-a结合形成GDNF复合物,继而GDNF促进细胞内钙库释放Ca2+到细胞质中。Ca2+结合到ret细胞内的钙粘蛋白结构域上。ret细胞内的酪氨酸残基自动磷酸化,结合SHC-GAB1-GAB2形成复合物,吸引各种各样的细胞内信号蛋白: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oinositide 3-kinase,PI3K),Ras和cAMP,进而调节细胞凋亡的抵抗。Meir等[49]的研究显示,GDNF以cAMP/PKA依赖性方式促进伤口愈合,并通过失活p38 MAPK信号传导促进未成熟肠上皮细胞的屏障成熟。Trupp等[50]研究表明,脑胶质细胞分泌的GDNF可通过与含GFR-a的非ret受体结合,不激活ras/ERK通路,而是能激活GFR-a相关的Src相关激酶,从而导致cAMP反应成分相关激酶快速磷酸化,而导致c-fos基因的表达增加,从而启动细胞的增殖与分化。
4.1.3 S100B蛋白 S100B蛋白是小的、弥散的神经营养因子,其位于神经元和非神经元组织的胞浆和/或细胞核中。S100B能进入细胞外空间,特别是在肠道免疫-炎症反应位点。微摩尔浓度的S100B蛋白能够参与炎症反应,甚至是健康的十二指肠中。在脑中,S100B被认为是具有双重作用的神经营养因子。随着在细胞外环境的浓度的变化,S100B能产生两种相反的作用:在纳摩尔浓度时,S100B对神经胶质细胞和羟色胺神经元有促扩增和神经营养作用;然而,在微摩尔浓度时,S100B有神经元变性作用,决定失控的EGC扩增并促进神经元炎症的发生[51]。对S100B特异信号受体的研究证实,这种蛋白可能仅仅在微摩尔浓度时在RAGE(对晚期糖化终产物的受体)位点集聚。这样的相互作用导致mitogen活化蛋白激酶(MAPK)磷酸化和最终的核因子-kB(NF-kB)激活。与CNS中的星型胶质细胞相似,EGC生理上表达S100B蛋白,依据其在细胞外环境中的浓度不一样,起着营养或毒性作用。Cirillo等[9]研究证实,S100B蛋白的表达伴随着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iNOS)蛋白表达的增加和随后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的释放。iNOS蛋白表达的增加和随后NO的释放都是代表CD的关键特征。Cirillo等[52]用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和干扰素γ(interferon γ,IFN-γ)孵化诱导S100B mRNA和蛋白表达增加,iNOS表达和NO产物增加。LPS+IFN-γ诱导的S100B上调不受布地奈德影响,然而,iNOS表达和NO产物被特异性抗RAGE和抗S100B封闭抗体明显抑制。在UC中EGC源性S100B上调,包含RAGE,以一种类固醇不敏感的通路参与NO产生,这说明LPS+IFN-γ刺激EGC通过S100B蛋白介导NO的产生。
4.1.4 神经生长因子(nerve growth factor,NGF) Von Boyen等[53]用促炎细胞因子刺激培养的EGCs后,发现EGCs中神经生长因子(NGF)的mRNA和蛋白表达增加,同时原肌球蛋白受体激酶A(TrkA)的表达也增加。而NGF能增加内脏的敏感性和改善肠道炎症。
4.1.5 proEGF Van Landeghem等[54]用葡聚糖硫酸钠(DSS)诱导黏膜损伤,以研究EGC对黏膜损伤的修复作用。他们发现,在DSS处理的黏膜中,敲出EGC后,黏膜的损伤更加严重了。在离体中发现EGC促进了上皮细胞修复和细胞扩散,进一步他们证实了EGC分泌的的介质——可溶性proEGF激活了肠上皮细胞的EGF受体和focal粘附信号通路。
4.1.6 SOX8/9/10 Hoff等[18]用免疫组化的方法认为SOX8/9/10严格地定位于神经节、神经节间神经纤维链、神经纤维支配肌肉、血管和上皮的EGC的细胞核中,能较清楚地对EGC进行染色和区别不同的EGC。SOX8/9/10是所有EGC共有的标志物。S100B位于EGC的细胞浆和细胞核中,GFAP位于EGC的细胞浆中。因此,他们认为SOX8/9/10是作为EGC定量标记的较好的标记物。
4.2 炎症刺激后EGC释放的细胞因子和化学物质
4.2.1 S-亚硝基谷胱甘肽(S-Nitrosoglutathione,GSNO) S-亚硝基谷胱甘肽 (GSNO)是活化的EGCs释放的一种信号分子,GSNO是还原型谷胱甘肽(GSH)的亚硝基化形式[16]。GSH在铜蓝蛋白的催化作用下被亚硝基化,产物能产生抗氧化的细胞保护作用[31]。Savidge等[55]证实,敲出EGCs的小鼠导致肠黏膜屏障功能紊乱,从而导致炎症。而胶质细胞源性的GSNO可诱导回肠和结肠肠黏膜屏障的修复。而且,他们还发现GSNO调节黏膜屏障功能直接与周围连接factin和紧密连接相关蛋白ZO-1和occludin的表达增加相关。有研究证实EGC和GSNO保护IEB免于福氏痢疾杆菌的入侵是通过降解福氏痢疾杆菌入侵所必需的重要分子Cdc42来实现的。此外,EGC和GSNO还增加了ZO-1的表达,从而也起到了保护IEB的作用[56-57]。事实上,GSNO已经被证实能抑制细胞因子如IL-1B,IL-12P40亚单位,IL-6,IL-8和MAP,并能降低抗炎介质,GSNO的表达。此外,还有研究证实,GSNO能通过使NF-kB的一个保守Cys残基的S-亚硝基化或通过使抑制-kB(I-kB)激酶S-亚硝基化来减弱NF-KB p50-p65的活性[31]。在心肌和骨骼肌中,S-亚硝基谷胱甘肽通过ryanodine 受体(包括RyR1和RyR2)激活肌浆网Ca2+释放[58]。但在肠道中,还未有关于GSNO受体的报道。由于NO的极度不稳定和容易灭活性,Kluge等[59]尝试着检测NO的中间复合物S-亚硝基谷胱甘肽,他们用液相色谱-质谱分析的方法确定和定量分析了大鼠脑组织中的亚硝基谷胱甘肽。
4.2.2 白介素-6(interleukin-6,IL-6) Rühl等[60]从成年大鼠空肠肌间神经丛中提取出EGC并培养,分别用IL-1B,IL-6和TNF-α刺激EGC细胞,并用RT-PCR评价IL-6mRNA的表达和分泌,结果表明IL-1B能刺激EGC中IL-6 mRNA的表达和蛋白的合成且呈浓度依赖的方式,但TNF-α对IL-6 mRNA的表达无影响,IL-6明显抑制了EGC中IL-6 mRNA的表达。
4.2.3 白介素-1B(interleukin-1B,IL-1B) Murakami等[61]研究表明,LPS能增加EGCS释放IL-1B。IL-1B导致EGC的Ca2+浓度增加,激活Ca2+依赖的PLA2,从而导致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 E2,PGE2)从EGC中释放,且IL-1B能增强缓激肽对神经元的作用。Gougeon等[47]研究还证实,IL-1B能通过刺激平滑肌细胞GDNF的产生,从而GDNF作用于神经元的NF-kB通路,导致神经元轴突的生长,以完成对神经元的营养作用。
4.3 炎症刺激后EGC上受体的变化
4.3.1 人类组织相容性复合体(human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是由一群紧密连锁的基因群组成,定位于动物或人某对染色体的特定区域,呈高度多态性,其编码的分子表达于不同细胞表面,参与抗原递呈,制约细胞间相互识别及诱导免疫应答。MHC分成三类:第一型:MHC class I(MHC I)位于一般细胞表面上,可以提供一般细胞内的一些状况,比如该细胞遭受病毒感染,则将病毒外膜碎片之氨基酸链透过MHC提示在细胞外侧,可以供杀伤性T细胞等辨识,以进行扑杀。第二型:MHC class Ⅱ(MHC Ⅱ)只位于抗原提呈细胞上,如巨噬细胞等。这类提供则是细胞外部的情况,像是组织中有细菌侵入,则巨噬细胞进行吞食后,把细菌碎片利用MHC提示给辅助T细胞,启动免疫反应。第三型:MHC class Ⅲ (MHC Ⅲ) 主要编码补体成分,肿瘤坏死因子(TNF),热休克蛋白70(HSP70)和21羟化酶基因(CYP21A和CYP21B)。
EGC生理条件下组成性表达MHCI,但MHCⅡ几乎不可检测。 Cornet等[62]用转基因的方法将一种病毒(neoself)抗原基因传染到EGC细胞中,使EGC产生neoself抗原。绝大多数CD8(+)T细胞能特异的与neoself抗原及EGC上MHCI结合。结果导致EGC细胞凋亡的程度与CD发病中EGC凋亡的程度相当,以及出现在CD进展期出现的特征性标记:肠和肠系膜T细胞浸润,血管炎,Th1细胞因子产生和爆发性肠炎。这些表明免疫介导的EGC损伤可能参与了人类IBD的发生和/或发展。
在1998年,Geboes等[63]总结了实验性文献中有两篇文献报道了在CD时,EGC上MHC Ⅱ表达增加, HLA-DA亚型明显增加HLD-DP/DQ亚型轻度增加。目前关于EGC上MHC的研究相对较少。
4.3.2 P2Y1受体 ATP受体超家族包括G蛋白藕联受体(P2Y受体)和ATP门控离子通道(P2X受体)[64]。P2Y有八种不同的亚型,其中有一些亚型(P2Y1,P2Y12和P2Y13)是选择性与ADP作用的[65]。在中枢神经系统中,激活P2Y1受体(P2Y1R)可抑制P2X3受体的功能,可能导致疼痛[66]。研究[15]证实,炎症导致神经元凋亡,释放ATP的刺激EGC上P2Y1Rs的表达,且通过EGC上的P2Y1Rs/PLC通路激活GFAP(+)EGC的。Neary等[67]研究表明,ATP与星型胶质细胞上的P2Y结合,激活P2Y受体,水解磷脂酰胆碱(PC)和PKC,从而激活ERK。活化的PKC转位到细胞核中,激活或诱导转录因子如Elk和c-fos,参与扩增和基因的分化。
4.3.3 Toll样受体(Toll like receptors,TLRs) Abreu等[68]研究证实,在IBD患者中,TLR和CARD15/NOD2基因存在多形性。在正常的肠道中,TLR和Nod分子维持着控制肠道炎症,但在IBD中炎症与正常的菌群相互反应。TLRs是一种跨膜受体,其细胞外区域为富含亮氨酸重复序列的结构域,然而在IL-1Rs的细胞外区域含3种免疫球蛋白样结构域[69]。细胞内为与IL-1R同源的序列(Toll/IL-1R,TIR)和许多抵抗病害的蛋白[70]。在TIR结构域中,包含3个保守的boxes,在TIR结构域中氨基酸的保守序列大约是20%~30%,且这些结构域大小各异。迄今为止,在人中一发现有10余种亚型[69]。Yang等[70]认为TLR2通过激活NF-kB相关通路诱导基因表达。TLRs/IL-1Rs二聚体招募的下游信号分子有MYD88,IL-1R相关激酶(IRAKs),转化生长因子B(TGF-B)活化激酶(TAK1),TAK1结合蛋白1(TAB1),TAB2和肿瘤坏死因子(TNF)受体相关因子6(TRAF6)[70]。Aliprantis等[71]的研究认为TLRs诱导的信号通路还可分为依赖MYD88和非依赖MYD88的信号通路。
Von Barajon等[44]研究表明,在肠神经系统中,存在TLR3、4和7,TLR3和7识别病毒RNA,TLR4识别LPS。 Murakami等[72]研究证实,肠肌间神经元和非神经元细胞表达TLR-4,而TLR-4是LPS的主要受体。 Brun等[73]研究表明,在IBD时肠神经元和EGC上表达有TLR2,且TLR2与GDNF的表达有关。目前,还缺乏文献报道EGC上的TLRs总的表达情况,以及TLRs与炎症刺激后EGC产生的炎症因子等的关系。
5 小结和展望
大量的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显示,肠胶质细胞在炎症性肠病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IBD中,肠胶质细胞可参与肠上皮屏障稳态的维持和ENS功能的调节以及肠道免疫过程,ECG功能的失调会导致肠道炎症失衡和肠屏障的破坏。对ECG在炎症环境中功能改变和机制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IBD的发病机制,并可能提供新的IBD治疗思路和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