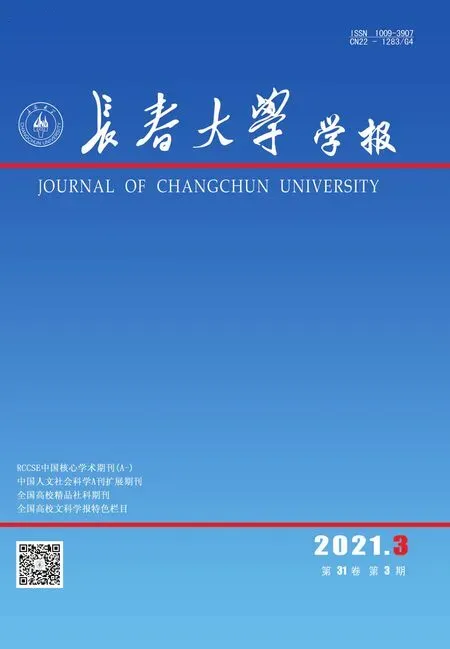青海下弦文化功能探析
苏 娟
(青海民族大学 艺术学院,西宁 810007)
一、青海下弦产生的人文语境
下弦“瞎(音ha)弦”,俗称“曲儿”。关于“下弦”名称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以主要伴奏乐器三弦的定弦法为两个纯五度,习惯上的唱名为1 5 2,艺人们称作“下弦定弦法”,故把采用这种定弦法伴奏并使用这个曲调演唱的曲种形式,称作“下弦”,即曲种名与定弦法同名;还有一种说法是,旧时代人们并不歧视唱曲儿的盲艺人,把他们尊称为“瞎先生”,而把他们表演的“曲儿”统称为“瞎先曲儿”,故改“瞎”为“下”称之为“下弦”。关于青海下弦的形成年代至今没有检索到确切的文献资料记载,据现有下弦演唱艺人的传承关系推测,下弦的演唱活动可上溯到明代孝宗弘治初年。
青海下弦主要流行于省会西宁市及邻近湟中、湟源、互助和平安等县。西宁,位于青海省东北部湟水谷地,东与平安接壤,西南与湟中县毗邻,北与海北藏族自治州、互助县相连,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三川交汇,四周丘陵环抱、山峦重叠,环境优美,是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为西北重镇,素有“西海锁钥”之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有着迷人的自然景观和古朴淳厚的民风民俗。古代为羌戎繁衍生息之地,1946年6月成立西宁市,是一座有2100多年历史的高原古城。优美的自然环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正是这种民间曲艺衍生、发展的良好机缘。正如乔建忠先生说的,民间音乐是特定地区文化的组成部分,它要受到该地地理、地貌、民族、语言和习俗等诸因素的影响,也反过来强化由它们共同组成的文化传统[1]。据史料记载,早在四五千年前,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在秦厉公时期,羌人无弋爰剑,被秦国虏而复归,带来农耕技术并加以传播,中原地区较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开始传入河湟地区。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生存经营方式,为青海下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二、青海下弦的传承功能
(一)文学内容的传承
植根于青海民间的下弦,承载着宋末明初以来河湟谷地人民的群体记忆和审美体验,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首先,青海下弦的词格特殊,尤其是下弦调中主体唱腔的二、二、二结构,可以说是我省地方曲艺音乐中较为独特的词格形式,成为区别地方曲种的一个主要依据,这种词格的独特性和唱腔音韵美,展现了生活在高原的人们以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创造、传承着地方文化。下弦作为地方民间音乐的一种形式,在青海各族人民漫长的历史进程和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内容多与弃恶扬善、忠孝仁义等民族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和人民日常的劳动生活、宗教信仰、礼仪习俗紧密相连,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文化享受和培育人的优秀传统美德和精神食粮。
1.唱词内容的传承
青海下弦的唱词主要以表现历史人物、传说故事为主,新编的曲目较少,其内容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英雄人物的讴歌和对现实生活的感慨,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1)因情取事,借古喻今
下弦的传统曲目《林冲买刀》是通过好汉林冲从八十万禁军教头最后被逼上梁山的故事中几个主要情节作为表演曲目,情节曲折、感人肺腑,歌颂了林冲忠贞不贰、刚直不阿的性格特征。因情取事、借古喻今,字里行间讴歌了人民大众爱憎分明的情感和扶危济困、崇尚自由平等的思想境界。
(2)借景抒情,托物咏怀
下弦的许多传统曲目通过对自然景色的描写,抒发人们对五谷丰登、太平盛世的渴望,借景抒情,托物咏怀。如《观景咏怀》中这样唱道:
苍山古柏,去雾竹林,见牧童斜跨青牛把山歌诵。细雨霖霖下,雾云悠悠生,唱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多福多寿多吉庆。
(3)语言简练,内容丰富
青海下弦的唱词言简意赅、内容丰富,故事的演进通过简单概括的语言,既能够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叙事性的描写,同时也能够结合对人物性格特征和主人公命运进行情感的抒发,将叙述、描写、抒情与议论融为一体,达到情景交融、托物言志的演唱目的。如“西有田虎作乱,南有王庆残员;东有方腊造反,替天行道梁山。”在这短短的四句唱词中,对南宋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生活的简练叙述,表达了人民大众对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英雄主义气概的赞颂之情。
2.唱词语言的地域性传承
下弦的唱词词格特殊、文句典雅精练,演唱时可以根据情绪和情节的需要,加以适当的变化,具有深沉优雅、感人肺腑的艺术魅力。
(1)六言文体的独特性
下弦的主体唱腔下弦调的唱词与青海省其他汉族曲艺音乐的词格大相径庭,讲究平仄相配、音乐和谐,其典型的六言韵文体,根据句式结构,分为二句式、四句式和五句式等,内容可长可短、变化灵活。如:
高俅有语言道,再叫二位年兄。
宣你不为残事,只为少男(的)事情。
(2)唱词语言的地方性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根植于民族灵魂与血液间的文化符号,任何文明语言中的词都真实记录着一个民族文化的踪迹,成为延续历史与未来的血脉。反过来,语言的发展变化又离不开文化的变化和发展[2]。青海下弦使用的语言是西宁方言,西宁方言区属于北方方言区的西北方言,其语言基本采用北方十三辙的辙口押韵。但由于西宁方言的使用,演唱起来更加顺口,其语言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如:
人儿太年轻,说话闯英雄,坐监坐牢什么人。
其中“轻”“人”两字押人辰辙,“雄”字押中东辙,但西宁方言将“雄”字读作xun,如此一来这三个字都归到人辰辙,属于句尾韵。
下弦的语言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地域特征,这一特征是该地域人民心理的情感积淀,尤其是语言性极强的曲艺音乐,与音乐密切结合,二者共同营造出该地域的文化特征。 青海下弦由于受到西宁方言的影响,唱词中有明显的地方语言。如“吹风了嫑(念bao)下雪,下雪了嫑吹风”。这样的语言不仅具有地方特色,还使人有一种亲切和贴近地方生活的感觉,增添了唱词的生动性和亲切感。
(二)音乐文化的传承
1.表现哲学思维的曲式结构
青海下弦音乐主要由下弦调、仿下弦调、软下弦调和下背宫四个腔调组成,它们的音乐风格相互间既有联系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下弦调主要由前奏、曲头(也称起腔)、主体唱腔(也称主腔)和曲尾(也称落腔)四个部分组成;仿下弦调是由前奏曲、主体唱腔和曲尾三部分组成;软下弦调的音乐有前奏曲、曲头、主体唱腔、曲尾四个部分组成;软下弦调和仿下弦调都是在下弦调的基本框架下形成的新腔调形式,这与中国传统音乐追求的“同中求变,变中求同”的曲式结构原则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由混沌、简单的原始状态分化为各有联系又有千差万别的观点不谋而合。
2.融合借鉴的旋法特征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相互借鉴、互相融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地域性民族文化,其音乐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地方性和融合性等特征。下弦作为青海汉族民间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受到青海贤孝、青海平弦、青海越弦及甘肃临夏下弦和藏族、土族、蒙古族等说唱音乐的影响,其音乐形态丰富、腔调多变。其中下背宫是青海平弦艺人以下弦的定弦法,即老、中、子三根弦的关系均为纯五度的关系伴奏,主要曲牌以青海越弦的[背宫]为主体曲牌,演唱某些专用曲目的小型套曲形式,它的传统曲目有《岳母刺字》《三顾茅庐》《出曹营》《盼周郎》《伯牙摔琴》《思夫盼子》《观景咏怀》《游梦》《断弦琵琶》《四季景》等,由前“背宫”、“ 离情”、“ 皂罗”和后“背宫”四个唱腔曲牌组成,其连缀的形式和曲牌的顺序固定不变,它的唱腔曲牌较为独特。[离情]来自青海平弦,前“背宫”、“ 皂罗”和后“背宫”根据青海越弦的曲牌稍加变化构成,旋律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地域特征,它对于探索西北地区曲艺音乐的结构特征、唱腔流派及器乐曲牌等都具有文献研究价值,同时又是青海汉族多元文化特征的有力佐证。
3.精湛高超的表演技巧
下弦的定弦法是两个纯五度的音程关系,这种定弦法在其他曲种中并不多见,它的伴奏音乐、唱腔曲牌丰富而独具特色,不同于青海汉族其他曲种,在内地其他地区也较少见到。它要求演唱者声音圆润柔美、吐字清晰准确、感情真挚深沉;三弦弹奏中必须熟练掌握拈、揉、扣等技法,而对于这些技艺的融会贯通,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需要艺人要有卓越出众的天赋、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甘于奉献的精神,这样才能成为优秀的下弦表演者。笔者在访谈下弦的传承人毛延奎时,他说:“下弦由于词格特殊,曲调不同于其他曲种,所以学习起来难度较大,加之曲目表现戏谑、欢快、愉悦的场景较少,对于一般的‘明眼人’来说,是否能坚持学下去都是一个问题。而对于我这个盲人来说,下弦更与我的思想接近、更能够表达我内心世界,所以无论它的难度多大和要求多高,我愿意用一生的时间研习它。”
(三)中国传统思想的传承
1.忠、义——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
“忠”是封建社会传统思想忠君爱国、忧民正义观念的集中展现,“义”主要指惩恶扬善、维护正义。林冲作为梁山好汉,同情弱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了亲情、友情,也为了正义,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与封建强权势力展开了殊死搏斗。林冲作为八十万禁军教头,他深受封建君主王朝“皇权至上”思想的束缚,对高衙内的行为一直逆来顺受,他将自己的政治意识、政治行为、是非标准,寄托在对君主和皇权的克己奉公和惟君主的利益至上中,这虽有一定的思想局限性,但对其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要继承与弘扬,在现代社会仍然是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林冲买刀》取材古典小说《水浒传》,是青海下弦中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曲目,其语言通俗生动,人物形象逼真细腻,情节曲折感人,有力地鞭挞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残暴,大胆地揭露了当时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和“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通过音乐表达人民大众之心声,通过音乐传承古代思想文化之精华,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又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2.仁、爱——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
所谓“仁者,爱人”,它要求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本着仁爱的宗旨,建立互助友爱、和谐宽松的社会环境。“仁爱”是构建自由公正、安定有序社会的前提条件,它要求与人为善、明礼诚信,把尊重他人、关心他人作为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下弦是青海汉族传统伦理思想宣传的重要媒介之一,无论曲目内容、故事情节还是表现形式,大都与儒家传统文化相关,如《鸿雁稍书》《沧州投朋》《三姐上寿》《岳母刺字》《三顾茅庐》《出曹营》《盼周郎》《伯牙摔琴》《思夫盼子》《观景咏怀》《游梦》《断弦琵琶》《四季景》等作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良好社会风尚等起着十分有益而积极的作用。
三、青海下弦的社会功能
(一)调节功能
音乐能够激起人们的种种情感,平静的、豪迈的、欣喜的、愉悦的等等,一个纯粹的乐音在激发情感方面,胜过几页的文章。弗洛伊德称音乐为“无害的宣泄”方式,他认为音乐能直达人的潜意识,因此最有利于抒发心中情思或宣泄内心积郁[3]。古代时期,盲艺人苦难坎坷的人生道路、凄切悲惨的内心世界,使他们拥有对于与生俱来的生活遭遇的不满和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极其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指尖和演唱中得到自然流露,通过下弦这种音乐形式得到很好的抒发与释放。
青海汉族民间有结婚生子、庆生贺寿邀请曲艺艺人到家中表演的习俗,根据仪式内容、仪式环节的不同,演唱不同的曲种和曲目(主要是青海平弦、青海越弦和贤孝等),有时为了活跃现场气氛,盲艺人也会演唱《林冲买刀》其中的选段,盲艺人在表演中获得了生活的保障、社会的认可和自身价值的体现,而听众获得了身心的调节、精神的放松和人生境界的升华。
(二)娱乐功能
一切文艺形式都有娱乐功能,曲艺音乐自然也不例外,青海下弦无论是在形成之前还是形成之后,其娱乐功能都是不言而喻的,它是青海省地方曲艺音乐中善于表达演唱者内心世界、抒发思想感情的一种音乐艺术形式。其娱乐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下弦的表演一直没有专业的演出团体,主要在民间流行,表演者大多采用自弹自唱或两人结伴的表演形式。演唱者以故事情节为内容,以音乐表现形式为载体,语言通俗易懂,集教育和娱乐为一体,满足了听众的审美需要和精神需要,具有较强的自娱性和娱乐功能。
其二,过去在青海省广大农村囿于交通和经济条件,这种既不需要为演出搭建戏台而耗费更多财力,也不需要演员化妆和角色分工的民间曲艺便成了乡村农民休闲娱乐的主要途径。
其三,曲艺茶社是青海下弦表演的另一重要场所,在这里,曲艺爱好者可以喝茶、谈心,是他们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广大农民及市民在闲暇时节自我消遣、自我娱乐的一种文化形式。
(三)教化功能
青海下弦具有叙述性、描述性及间接形象性的特征,其功能和价值主要体现在认知和教化功能相结合的综合功能上。从这方面来看,民间曲艺发挥着史书、诗文无法替代的社会作用。青海下弦作为地方民间曲艺音乐的一种艺术形式,对于人们认识历史演变、社会变化、人们的道德标准提高和审美情趣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影响,通过认知功能达到戏谑讽喻、传承民德、文以载道助成教化的作用。它的曲目以历史故事居多,情节曲折、寓意深刻、发人深思,通过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历史事件,揭示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通过表演达到寓教于乐、借古喻今、警示世人的目的。
(四)都市民俗功能
我国说唱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汉代的相和歌、南北朝的各种长篇叙事歌、唐代的变文都可以看作是今天说唱音乐的前身。宋元时期,说唱艺术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当时城市繁荣,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城市人民生活的需要,以及说唱音乐本身所具有的容纳长篇故事和表现复杂情节的特点,使说唱音乐成为农民和市民所喜好的艺术形式,在城市里还有了固定演唱场所,即所谓的“勾栏瓦舍”[4]。西宁周边的曲艺茶社是下弦表演的主要场所,它的功能和用途与宋代的勾栏瓦舍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是都市民俗文化的产物,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西宁是春小麦种植的生态区,由于其种植特点春种秋收,一年一熟,生长季节较长,所以这里的农民较之内地的农民则更为闲适,品茶酌酒、唱曲谈心则成为他们打发农闲的首选娱乐消遣活动。青海省民间文艺家谢承华先生在他的一首诗中这样描写民俗传统:“素有踏青野游、笙歌管弦、雅聚豪兴、弹唱歌舞。”下弦无论演唱曲目、表演内容、音乐结构等具有都市民俗的特点。
四、青海下弦的审美功能
(一)审美观念
每一个民族都有显示其独特文化传统的符号和语汇,来源于青海汉族民间的下弦音乐文化,是青海历代社会历史演进、政治制度和文化变迁的产物,是千百年来青海汉族人民群众生产劳动、社会生活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他们精神生活、思想道德、审美情趣等方面具体的体现。下弦以坐唱为表演形式,以西宁方言为载体,以三弦和板胡为主要伴奏乐器,既没有华丽的舞台装饰,也没有角色的分工,他们的身影可在街道巷口、茶园饭店、公园林间,也可在台阶炕头、私家庭院席地而坐,这种表演场所的不固定性,使得青海下弦更加贴近劳动人民日常生活,尤其在媒体不发达的旧社会,甚至成为他们丰富物质文化生活、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手段。即便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文化构成多元化、多样化的今天,它仍然作为精神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真实地、客观地、原生态地反映当地汉族人民独特的审美标准和审美心理。
(二)审美价值
青海下弦无论是唱腔的曲牌、唱词的格律还是音乐伴奏,都有着比较严谨的结构。听众可以借助对故事情节的了解,在脑海中产生剧情画面,较快地进入音乐的情境,在听的过程中感受音乐审美的愉悦。通过故事情节反映广大民众的情感世界、思想意境和精神夙愿,表演艺人通过文学和艺术的形式,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事件、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心理状态,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了美的享受和美的愉悦。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具有它的艺术价值,都必以艺术形象为依托,以表现形式为载体,使得蕴涵在其中深邃的艺术观念和思想境界通过审美对象得到完美体现。青海下弦由于自身独特的定弦法,和子弦与二弦中低把位的应用及前奏、间奏在老弦上使用的演奏技巧,将凄凉、哀怨和忧伤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加之演唱者如泣如诉、深沉委婉的旋律,显示出一种悲剧美,这与青海越弦和西宁贤孝的喜剧美形成鲜明的对比。古人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青海下弦的表演者绝大多数是盲艺人,作为谋生手段,下弦是盲艺人用来维持生计、满足温饱的生存需要;作为艺术的审美功能而言,它是一种精神慰藉、一种生存态度,更是人生价值完美体现的需要。
(三)文化认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数千年历史的记忆和身份的象征,具有显著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2008年,青海下弦进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历史见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作为艺术表演,又是汉族民间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三弦响起,人们不约而至、纷至沓来,围坐在盲艺人的四周,沉浸在故事情节里,时而喃喃自语、时而悲喜交加,这种文化的认同感,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当地人民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思想意识中,成为青海汉族标志性的文化符号。而这种标志性的符号,不仅不会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而销声匿迹,反而随着岁月的更替,显得更加魅力无穷。
五、结语
青海汉族自汉武帝时期,通过从军、屯垦和移民等各种形式,从内地迁到青海定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优秀的文化,青海下弦无论在唱腔词格、唱腔结构和音乐伴奏等方面与江南一带的说唱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中原汉族移民文化的产物,随着它在本土繁荣与发展,不断与青海地方方言、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交流融合,成为中原汉族文化与青海多元民族文化认同、和谐共生的结晶。这些特点在下弦的传统曲目、调式音阶、节奏节拍、伴奏形态、表演风格和表演形式等方面有所体现。根据相关资料和下弦艺人传承谱系推测,青海下弦产生大约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其中《湟中札记》记载:“西宁盲曲,明初自江南跟戊民而至斯地,岁月渺沓,曲韵变异,今多为北韵,间为南云南,牌名则一如旧也。文句典雅,诚非湟中之遗物。然盲人传唱,顺畅自如,缘有师也。府城巷多有卖曲声,老缊少妇尤喜闻。”[5]由此可见,它是移民文化的产物,承载着中原汉族从内地迁移到青海的历史演变进程,再现了青海从远古到现代历史发展轨迹,成为中原文化和本地文化融合的文化见证。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数千年智慧结晶的文化创作和作为历史记忆、文化身份,对促进人类意识与观念、实现人类文化自觉等方面具有宽广而深刻的影响。青海下弦作为非物质遗产的第二项内容——表演艺术,自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青海下弦发展的重要时期,出现了下弦著名的表演艺人文桂贞、王安元、孙有财等近30余名盲艺人,在他们的努力下不断丰富了下弦的唱腔曲调,使之成为唱词优雅、曲调多样、风格独特的地方说唱音乐艺术形式。但是由于曲种自身特点、生存环境的变化和表演群体的特殊性等因素的制约,青海下弦的演唱目前处于青黄不接的局面,不少艺人中的佼佼者相继故去,下弦的传承已经到了濒危状态,亟待保护抢救和保护。如何有效地保护和传承青海下弦音乐文化,如何使其在现代文化和经济背景下健康地生存与发展,作为地方文化研究者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