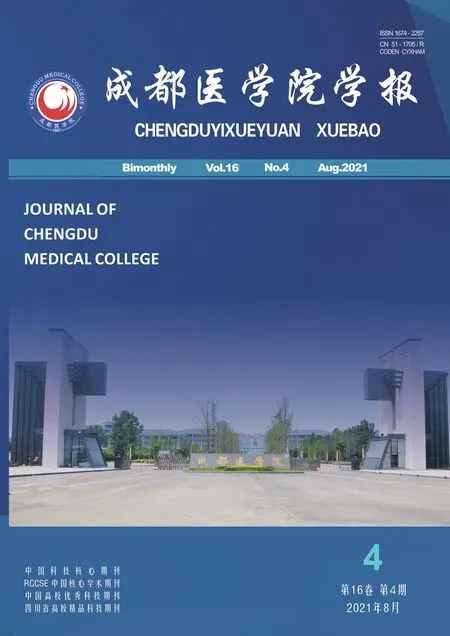安宁缓和医疗下老年恶性肿瘤患者营养治疗的研究进展
闫 翔,郭明阳,宋 辉,唐 微
西部战区总医院 干部病房二科(成都 610083)
近年来恶性肿瘤患者营养不良已成为临床关注热点,营养支持可提高抗肿瘤治疗效果及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已成为共识[1]。但由于对老年恶性肿瘤营养治疗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在营养管理上缺乏或不重视安宁缓和医疗(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HPC)的理念,没有形成与HPC相关的营养目标和措施;临床上重视指标改善,缺乏个体舒适度评价和对患者及家属生活质量、心理状况、预后等综合考量,营养治疗存在支持过度或不良。因此,本文就HPC概况、老年恶性肿瘤营养不良现状和HPC需求,以及HPC下老年恶性肿瘤营养治疗理念等方面进行综述,拟为HPC下老年恶性肿瘤营养不良管理提供新思路,为HPC理念践行于临床提供参考。
1 HPC与老年恶性肿瘤营养不良
1.1 HPC概况
癌症是HPC主要关注的病种之一,近年来随着临床肿瘤学的进展,患者生存率逐年提高,肿瘤已成为慢性病;加之老龄化和疾病谱的变化,全球每年有4 000万人需要HPC服务[2-3]。2008-2016年美国医院HPC项目增长率为91%,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医疗亚专科。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将HPC列为各级卫生系统应向全民提供可负担的优质服务[4]。HPC是对不同年龄段患有严重疾病并因此遭受严重健康损害的个人(主要是生命末期患者)进行积极、全面的照护,为其提供躯体症状管理(包括疼痛和其他不适症状)以及满足心理、灵性和社会需求,以提高个人、家属和照护者的生活质量,包括预防、早期识别和全面评估[5]。
因经济水平、社会文化、医疗服务框架、医疗保险体系不同,全球HPC发展极不平衡,英国、美国、日本等HPC体系较为完整且形成各具特色的HPC模式:英国实行三级分层服务方式[6];美国则分为专科、初级HPC[7],强调初级保健团队是启动和提供有效HPC服务的关键;在日本以立法形式促进HPC开展。HPC体系完善的国家或地区,医疗资源得到合理配置[8],患者生存质量明显改善,实现有质量的“尊严死”。
HPC特点是全人、全程、全家、全队管理,未来发展集中在5个方面:一是将HPC和初级保健整合[9],向社区、家庭推广HPC服务,医院、安宁院、社区及家庭一起构建全方位HPC体系;二是将HPC逐步纳入国民保险体系或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助推HPC发展;三是以患者为“中心”,强调多专业协作、跨学科合作为患者提供帮助[10];四是缓和医疗咨询和医疗咨询团队的组建,提高HPC可行性和效率,并改变护理模式和护理质量[11-12];五是以症状管理为核心,推进疼痛、呼吸困难、乏力、厌食等症状管理规范化及HPC适宜技术专科化。
1.2 老年恶性肿瘤患者营养不良和HPC需求
老年恶性肿瘤特点:1)发病率高且逐年增加,2015年我国癌症新发病例中老年恶性肿瘤患者占总数的64.1%[13];2)老年人恶性肿瘤易与慢性疾病混杂,故被临床明确诊断时多处于中晚期;3)老年肿瘤恶性程度相对较低,惰性生长,带瘤生存期相对较长[14],伴见疼痛、呼吸困难、衰弱等躯体症状和精神、心理异常,生存痛苦随着生存时间的延长而延长,生活质量问题更加突出。研究[15]指出,HPC应整合到肿瘤治疗中,作为常规肿瘤治疗的一部分;而老年恶性肿瘤患者因人数多、症状杂、治疗过程慢、生活质量差、死亡可预期,因此是HPC关注的主要人群。
恶性肿瘤导致机体能量消耗变化和营养代谢异常,加之老年患者胃肠道功能低下,老年综合征和老年慢病叠加,营养不良成为老年恶性肿瘤患者常见和较难解决的问题。研究[16-17]显示,临床上肿瘤患者营养不良的发生率为40%~80%,20%的恶性肿瘤患者直接死因与营养不良有关。在我国老年恶性肿瘤人群中,营养不良发生率达73.8%[18]。厌食、衰弱、疲乏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及家属的生活质量,营养不良是评估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的独立危险因素[19]。预防和治疗肿瘤患者营养不良已成为HPC症状控制的关键环节之一。
2 HPC下的老年恶性肿瘤营养治疗理念
随着肿瘤诊疗技术的发展,恶性肿瘤已成为一种慢性疾病,营养治疗是其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循证依据形成的营养指南,各营养学会对患者不同治疗时期提出了指导意见,如《恶性肿瘤患者的营养治疗指南》[20]分别就肿瘤病人非终末期(预期寿命>3个月)手术、化疗、放疗期间的营养干预指征、路径和终末期营养治疗提出了建议。前期患者通过营养支持可改善营养状况,增加治疗的耐受性和依从性,营养治疗有益于临床结局;而对于终末期患者不主张积极营养治疗获得氮平衡,临终患者只需极少量的水和食物以减轻其饥饿感。但指南未就非终末期未接受手术、放化疗恶性肿瘤患者的营养治疗提出明确建议;指南也未就肿瘤特殊人群如小孩、孕妇、老年人等进行分类指导。事实上,非终末期未接受抗瘤治疗的人群分布与年龄密切相关,大部分是高龄老人(>80岁)。由于老年肿瘤生理特点和诸多非肿瘤因素影响,营养问题突出,营养治疗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必要性。首先,老年患者未行抗瘤治疗,是否从单纯的营养支持中受益?其次,老年肿瘤患者一般体能状况差,现有的营养评定能否准确评估老年肿瘤患者的营养问题?肿瘤营养治疗不仅是医学问题也面临伦理困境,如何协助患者和家属进行营养方案的选择?当老年患者出现失智失能,如何协助代理人做出有利患者的营养抉择?针对非终末期非抗瘤治疗阶段老年恶性肿瘤患者营养治疗的特殊性,HPC理念的介入和HPC相关适宜性技术的应用,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纯医学角度营养治疗的一些困境,满足患者及家属的多元需求。
在HPC以人为中心的理念下,根据老年晚期肿瘤患者病程进展、预期结局、经济状况、个人及家属的感受及意愿,首先确立医学目标,在此基础上全面客观评估营养状况,将营养目标调整为维持和提升生活质量、缓解症状;综合营养评定不仅考虑病史、体格及实验室检查、人体测量等常规评定,还要与生活质量评估、老年综合评估(comprehensive geriatric assessment, CGA)等结合,全面评估老年患者肿瘤及非肿瘤因素、疾病与精神-心理-社会原因对营养的影响。由于营养目标和综合评定的变化,营养疗效在于评估患者及家属生活质量的改善与否。老年期肿瘤患者要得到HPC的帮助以缓解症状、预防和降低痛苦,社会伦理学的支撑非常重要,在制定营养计划时应尊重患者权利,评估风险/效益,与患者和/或家属共同协商做出最有利于患者的营养决策。
3 HPC下老年恶性肿瘤患者营养不良管理措施
3.1 确立医学目标和营养目标
对于老年晚期恶性肿瘤患者而言,当病程进入到HPC占主导地位的症状控制和医疗照护阶段,首先必须通过优良的沟通和交流,与患者或家属就医学目标达成共识:即提高生存质量,减轻患者痛苦,保障患者尊严;然后以医学目标为宗旨确立营养目标:即维持或改善膳食摄入、减轻代谢紊乱、减缓骨骼肌肌量丢失、尽量维持体能状态,并以营养目标作为指引来评估营养介入的时机、程度、途径,以及是否撤出或暂停营养治疗,避免造成医源性伤害。
3.2 遵循营养筛查及评定流程
以HPC医学目标为宗旨,按照营养目标[21],根据恶性肿瘤分三级实施营养诊断(即营养风险筛查、评估和综合评定)、推荐营养风险筛查量表、患者主观整体评估工具等作为营养筛查工具[22-24],依据评定结果按阶梯流程实施营养干预[25]。
3.3 细化营养实施方案
针对老年恶性肿瘤患者营养代谢特点和营养评定进行营养干预,首先确立适当的目标热量(20~25 kcal/kg)和营养素比例,保证蛋白质供给(1.5~2.0 g/kg·d),脂肪供能比例应适当上调;其次,根据老年患者肠道功能及摄入热卡情况分别给予口服营养补充剂、肠内营养支持、肠外营养支持、或部分肠外营养+部分肠内营养,原则上首选途径为胃肠道。老年患者营养路径的选择中应注意动态评估风险和效益,如营养支持的风险和负担超过益处,可以考虑允许性低热卡营养摄入(静息能量代谢值70%左右),以减轻机体的代谢负荷,减少足量喂养的可能并发症。营养治疗过程中注意监测患者营养指标(体重指数、肱三头肌皮褶厚度、握力、骨骼肌量、白蛋白、前白蛋白)和炎性指标(细胞因子、C反应蛋白、肿瘤坏死因子)的变化情况评估营养疗效。
3.4 重视生活质量评估和老年综合征评估
老年恶性肿瘤营养治疗的最终疗效体现在生活质量的改善[26],除了综合评定,应该重视生活质量评估量表、CGA等工具量表的应用,如通过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的生存质量核心量表、Karnofsky 功能状态评分、姑息功能评价量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等评估工具对患者及家属生活质量进行评估,对营养效果进行评定,根据评定结果调整营养治疗的目标、途径。
CGA是老年医学的核心技术,根据CGA可将老年肿瘤患者分为功能自主、功能部分受损、虚弱3种类型[27]。在确定营养方案时将CGA评估结果与其他营养评估相结合,制定的营养决策更符合老年人特点,有利于维持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
3.5 谨守“伦理原则”
营养方案的制定和选择必须尊重患者的权益,尤其是面对老年恶性肿瘤患者,加之尚有部分老年患者失智失能,应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有效沟通,尊重其意愿。在坚持医学伦理学原则下,不但应考虑能量和营养素,还应考虑患者的感受和舒适度,考虑干预措施是否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协助患者和/或家属做出更恰当的选择。
4 展望
营养治疗已成为恶性肿瘤的综合治疗手段之一,但老年晚期恶性肿瘤尤其是非终末期非抗肿瘤治疗人群营养治疗面临困境,建立HPC理念下的营养策略并贯穿于治疗全过程,方能实现以人为中心的营养目标,以期达到减少患者不适、缓解临床症状、提高患者和家属整体生活质量的目的。目前,临床医护人员缺乏HPC相关营养治疗理念,临床应用的相关方法和评估工具亟待进一步规范和标准化,亟需推广HPC理念并加强临床研究,以满足社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