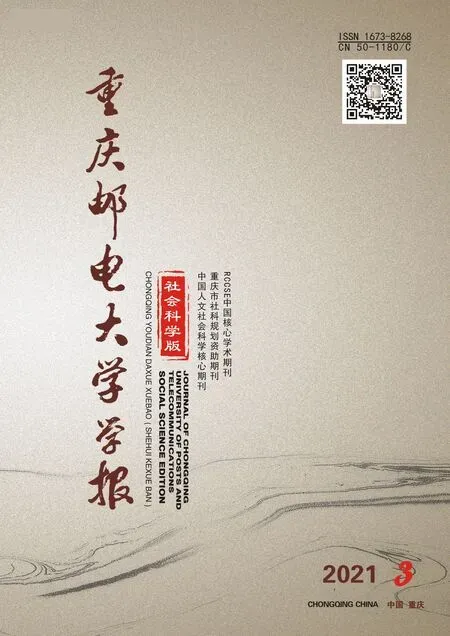从文学家到园艺家:周瘦鹃的身份转型与自我认同
李 斌
(苏州科技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一、观察文人身份转型的心态史视角
心态史是由20世纪20年代法国兴起的年鉴学派在史学革新思潮推动下开拓出的历史研究新领域[1]。近年来,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皮埃尔·诺拉主编的七卷本巨著《记忆的场所》的出版标志着史学领域记忆研究的开始,并推动史学研究向“记忆转向”[2]。在中国,心态史被引入了社会学、电影学、文学等领域的研究中。文学史研究中,学者们认识到“文学史是鲜活的心态史”,重点关注“心态史研究与文学史建构”等问题[3]。方长安认为中国文学文化生态的变化与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作家心态史研究是文学心态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栾梅健从20世纪文化生态的变化与作家心态间的关系考察了文化生态对中国作家创作的影响[4]。杨守森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一书分析了20世纪中国作家的主导心态类型[5]。这些研究比较重视对新文学作家、革命文学作家的心态史研究。相比之下,虽然陈子善探讨了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作家的复杂心态[4],但整体上有关通俗文学作家的心态史研究较少,其中暗含了对通俗文学作家的一贯性误解,如认为他们只不过是爱情故事的创作者,而本人是缺乏真情实意的。更有人因此推导出他们的“人格是低下的、情感是庸俗的、气质是丑恶的”结论。我们认为,“哀情”以及其他种种“情愫”“情怀”“情感”等元素,不仅是通俗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主题,也是他们的人格特征。他们的“情”不是捏造与设计出来的,而是真实存在于他们的心灵之中。他们以多情文学映照多情人生,文学创作与生命体验相伴而行,其心路历程自然值得一探究竟。
20世纪,现代文人普遍经历了身份的第二次转型,然而研究的落脚点却有不同。学者多将目光对准“延安时期”从上海到延安的左翼文人,研究他们在革命知识分子身份转型中的心态。这一时期通俗文学作家们多半居于上海等繁华都市,所以他们没有经历“革命化”的身份转型。他们的第二次转型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分子改造”中,也就是从旧社会的文学市场里孵化出的文人转变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应该说,“劳动者”转型和“革命者”转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通俗文学作家并未担任相关文化部门的要职,没有进入“文学-政治”的核心,他们的转型更接近于“生活化转型”,而不是“政治化转型”。换言之,20世纪现代文人的转型形成了“生活化转型”和“政治化转型”两种范式。在两种范式的比较视野下,作为通俗文学作家代表的周瘦鹃的第二次转型的考察意义就显现出来。
周瘦鹃是民国时期著名的通俗文学作家,对他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学层面,如对其文学、编辑、翻译、电影编剧等成就的梳理,但对其“生活化转型”的关注尚不多见。周瘦鹃与其他通俗文学作家成员的生活美学存在较强的共性。以周瘦鹃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作家们的“志同道合”,不仅表现于文学作品的自成一派,而且表现于生活态度、美学经验、生命旨趣的独具特色上。如周瘦鹃喜欢书画收藏,同为星社成员的赵眠云也爱书法、精篆刻,喜搜罗书画,以藏扇两千多柄而出名。范烟桥喜欢饮茶,茶中偏爱洞庭湖的碧螺春,这和周瘦鹃很像[6]。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多经历了和周瘦鹃一样的“生活化转型”,周瘦鹃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周瘦鹃经历了两次身份转型。一是20世纪20年代从科举入仕的旧文人向依靠现代文学市场谋生的新文人的“生计转型”,“通过对现代性器物的占有和现代意识的演绎,形成市场化的现代传媒和大众娱乐产业主导下的公共空间,参与都市文化建设,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性”[7],从而确立了他的“文学家”身份。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学创作取向协同变化的“生活化转型”,这种将个人生活融入“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生活的转型确立了他的“园艺家”身份,即从文学家向园艺家的转移过渡[8],“园”在周瘦鹃的第二次转型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此处的“园”主要指园林,也包括周瘦鹃自己的“园林化”的家,并由此延伸至“家园”等相关环境。周瘦鹃的青年、中年到老年的生活均离不开“园”的环境,“园”凝聚了他的文艺想象和人格特质,积淀了他的情感范型和思维方式,构成了他的精神家园。“园”既是他的新身份之“名”(园艺家),也是他对变化的身份认同的外显性视镜。伴随着周瘦鹃的人生轨迹与时代环境的变迁,他的园林园艺观及园林生活发生了变化,相应的文学接受审美的社会心理和文学创作主题也发生了变化,他从“文学家”到“园艺家”的身份转型不只是政治环境变化的产物,也是他中晚年时期对“园”的认识逐渐变化的结果。因此本文重点围绕两个问题展开论述:“园”何以成了周瘦鹃的终极归宿?他如何从心理上认同“园艺家”的新身份?
二、游园中的交往:“文学家”的自我认同
周瘦鹃的青年时期大致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此时他约有25~40岁,正是文学上“日臻成熟”与编辑、创作、翻译活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青年周瘦鹃对自己的“文学家”身份较为认同,这可从他的自况看出来,如他虽然多次说自己是“文字劳工”,但言语间对这份工作还是比较认同的:“吾们这笔耕墨耨的生活,委实与苦力人没有甚么分别,不过他们是自食其力,吾们是自食其心罢咧。”[9]287他还写过《小说丛谈》来谈“如何作小说”:“作小说非难事也,多看中西名家之作,即登堂入室之阶梯。一得好材料,便可著笔矣。吾人欲得资料,事亦非难,但须留意社会中一切物状,一切琐事,略为点染,少加穿插,更以生动之笔描写之,则一篇脱稿,未始不成名作。”[10]教大家作小说,一方面适应了小说成为市民茶余饭后消遣的主要文化产品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无形中炫现了他的小说创作特长。若不认同“文学家”的身份是不会写出这等文字的。
这一时期,“园”成了周瘦鹃工作之余的休闲场所与搭建事业人脉、借交游扩大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场所。一次,一位文人在逛半淞园时遇见了周瘦鹃,“五时许觅途出,忽邂逅周君瘦鹃。谓将访张王二君于人群中,第斯日在园中寻友侣,非预约在何许,恐不易找得也”[11],间接看出周瘦鹃是游园的常客。周瘦鹃曾这样回忆自己在徐园的游览情状:“我于文事劳动之暇,常去盘桓,顿觉胸襟一畅”。游玩的内容还是十分雅致的,看昆剧给周瘦鹃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周传瑛、王传淞、朱传茗、张传芳诸名艺人,都还年轻;并且还有一个后来转入商界的名小生顾传玠。他们合伙儿在这里演出,我曾看过不少好戏”[12]63。与周瘦鹃一起游园的人多为文友,园林雅集既增进了朋友间的感情,也从圈层上再次确认了文学身份。这些具有一定文学影响的文友们发表在各大报章里的文字中不断提及周瘦鹃的文学身份,如有人在《申报》上这样形容周瘦鹃:“瘦骨傲霜篱菊白,鹃声啼月海棠红。鹤伴梅花仙骨瘦,鹃啼月夜泪痕多”[13];“弹泪吹花笔一枝,灵心灵肺贮相思。江南金粉胭脂梦,都入周郎绝妙辞”[14]。一位文友应周瘦鹃约稿作游园诗,将周瘦鹃描绘成颇具古典况味的“士子”:“爰有瘦鹃子,感此欲挥涕。知影最纯洁,亲爱非侧媚。知影最正直,坦率绝趋避。相应既同声,相求又同气。乃作弁影图,冷寂诗心慰。”[15]1929年,一位叫章百煦的文人记述了周瘦鹃游梅园的经历,周瘦鹃兴致颇浓,先期一天到了无锡。章百煦可能是无锡当地人,他一路上十分尊敬周瘦鹃,待之以贵客之礼。梅园之游后,他作诗一首遥寄周瘦鹃云:“胜景孤山似,登临绝点埃。琴调新月上,客至万梅开。一酌花邨酒,三更蜡炬灰。明朝挂帆去,极目望苏台。”[16]这些“游园”活动显影着一个对周瘦鹃文学地位高度认可的社会评价系统。
“园”作为背景常现身于周瘦鹃的小说中,如《行再相见》中这样描述:“却说一天是九月的末一日,枫林霜叶,红得像朝霞一般。薄暮时候,斜阳一树,绚烂如锦。玛希儿茀利门……每天出来回去,总经过一家花园。经过时,园里的阳台上,总有一个芳龄十八九的中国女郎,把粉藕般的左臂,倚着碧栏杆亭亭而立。”[9]79借用古典园林的氛围来叙述现代跨国爱情故事也算是周瘦鹃吸引读者的文艺创造吧。深层来看,“园”作为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产生类似《牡丹亭》《西厢记》里记叙的爱情悲剧的背景而存在,暗含了周瘦鹃的“情性冲突”在其间。现实中的他不得不放弃的一场恋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家境不好产生的自卑感,是以他常怀对自己的无能懦弱的喟叹。正如弗洛伊德所说:
被压抑的本能为追求完全的满足而从未停止奋斗,它存在于重复一种满足的原始经验之中:一切代替或反相形成作用和升华作用对于放松持续的紧张用处不大,在那个基础上要求的过量的满足便产生了这种驱动的力量。[17]
不少人认为“哀情”创作象征了周瘦鹃的悲惨无力,我的看法正相反。周瘦鹃像《牡丹亭》《西厢记》里的悲剧男主角一样,骨子里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是敢于抒发情性的大写的“人格主体”。证据之一在他积极进取的文学创作中对“文学家”身份的高度认同。情“哀”的浓度正是他的文学生命力的显性指征。这一点,孙予青也从“本我”和“自我”冲突角度有过类似论述:“‘本我’中本能欲望的释放,是心理的有意识部分,遵循的是现实原则,它根据现实条件和客观环境来调整本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不造成更大的痛苦的前提下满足‘本我’的需要。周瘦鹃的‘本我’指导着其‘自我’的价值追求,他的唯美主义和悲观思想相互发生效应,因此在他的文艺创作风格中,大半生执着于对‘悲美’的追求,不仅热衷于歌颂美,更精于表现‘悲’,倾力打造悲情的文学王国。”[18]52
在上海工作期间,周瘦鹃是租房居住的,但这不妨碍他将出租房装饰成花木葱茏、诗情画意的微型园林。周瘦鹃说自己早年在上海居住时,往往在狭小的庭心放上一二十盆花供养,其中尤以紫罗兰为最动人[19]。周瘦鹃不仅在晒台上种花,还把花搬入宅内,放于床头,“床左右有瓶,各植紫兰,妩媚如好女。盆兰夜发幽馨,与紫兰相氤氲,熏床,香拂拂绕衾枕间。清夜独眠,梦境俱挟香意,虽孤衾如铁,自饶逸韵。昔林和靖要梅,吾欲妻兰矣”[20]。“花”正是周瘦鹃在现实中不可实现之爱情的补偿物,王西神在《紫罗兰曲》说周瘦鹃“周郎二十何堂堂”“三生自是多情种”,这也旁证了“园”之花隐含的生命力补偿之意,这种勃发的情性对周瘦鹃的文学工作起到了一个潜在的“框型”作用,如“花”之造型设计常被周瘦鹃用于刊物编辑中,形成了精美隽永的美学特色。他主编的《紫兰花片》“封面画请诸名画家,专画美人之头及肩而止,用彩色精印,四周以紫兰相衬,并请名人题字”。郑逸梅称《紫兰花片》“成为别开生面的个人杂志……令人咋舌”,无处不求其“精”。其中第三卷,每一号封面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页是镂空硬壳封面,覆盖在第二页软壳上,软壳中女子画像恰从镂空处露出来[21]。周瘦鹃将恋爱失败后所产生的压抑情绪投射到文学创作中,获得了文友好评、市民认同与市场响应的支持。他不但通过稿酬摆脱了童年以来的贫穷恐惧,而且进一步消除了自卑、重建了自尊。
这一时期的周瘦鹃虽然在文学事业上“风生水起”,但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没有心灵阴影的“乐天派”。周瘦鹃虽然游走于夜宴舞场、跻身于满座高朋中,但他仍然是“孤独”的,在他的《写在紫罗兰前头(六)》一文中,开篇第一句就是“笔者生性孤僻”。20世纪20年代,周瘦鹃受过左翼知识分子的批评,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心情低落,他曾这样表述他的态度:“在下本来是个无用的人,一向抱着宁人骂我,我不骂人的宗旨。所以无论是谁用笔墨来骂我,挖苦我,我从来不答辩。”[22]看似洒脱的回应实则满含了无奈。可见,他外在的“合群”与内心的“孤僻”是并存的。对周瘦鹃而言,“园”既可蕴蓄积极进取的生命活力,也可潜藏退隐逃避的消极思想,是具有包容性和多义性的空间。这种“包容性”与“多义性”使“园”十分适合成为周瘦鹃复杂心灵状态的表达载体。在周瘦鹃体认“文学家”身份的这段时期,“园”及“园”的相关元素(如花木)已缓慢渗入他的心灵世界,构成了他的文学自信和情绪健康的支撑系统。对“园”的认可直接影响到他后来对“园艺家”身份的认可,“园艺家”身份并非“外来”身份,而是隐藏和深入他生活的“内在”身份,这可从他游园的常态化、花木供养与私人生活的融合中看出来。因此,我们觉得从“文学家”转向“园艺家”的说法并非完全准确,用“园艺家”的身份在周瘦鹃心灵深处被唤醒的表述似乎更显恰当。
三、逃难中的怀乡:动荡乱世的家园眷恋
如果说青年周瘦鹃仅仅将“园”视为消解忧愁、排遣情伤的“后花园”的话,那么当日寇侵华而致家园破毁时,中年周瘦鹃则切实体会到了“园”与精神体系的深层关联。在那一刻,“园”于他不再只是一己悲欢消遣的场所,而是饱含了民族强大和家园安宁希冀的场所。中华文化的心灵归宿就是家,融合中华文化精华的“园”的最大特点就是宁静和美的家园感。“园”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友爱与亲密建构了抵御喧嚣、危险与骚乱的心灵屏障。
20世纪30年代中期,周瘦鹃在苏州买下紫兰小筑安家。在他眼中,苏州与上海毗邻,有繁华之都傍依,但又无上海之喧嚣,是养身修心的好去处。紫兰小筑前身是一私园,周瘦鹃参照了园林艺术风格对之加以修缮设计,“叠石为山,掘地为池。在山上造梅屋,在池前搭荷轩,山上山下种了不少梅树,池里缸里种了许多荷花”[12]139。周瘦鹃购买紫兰小筑时,日寇尚未全面侵华。孰料日寇的炮火一来,宁静的苏州也成瓦砾,想象中的安宁瞬间瓦解,所以他不得不避难安徽,逃难途中他深深地怀念家园,“苦念苏州,苦念我的故园,因此也常常梦见苏州,并且盘桓于故园万花如海中了”[12]35-36。逃难途中,寄居乡野荒郊的周瘦鹃仍坚守着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花草将草野屋舍点缀得诗情画意,他这样回忆道:“那时我在寄居的园子里,找到一只长方形的紫沙浅盆,向邻家借了一株绿萼梅,再向山中掘得稚松小竹各一,合栽一盆,结成了岁寒三友。儿子铮助我布置,居然绰有画意。”[12]129只是这时的周瘦鹃已不再有青年时期的浪漫悠然状态,而更多地是借眼前的花木种养来表达他遭遇动荡逆境时坚守美好生活的信念,发出他抵抗破坏美、摧毁美的行径的无声宣言。当然,这种抵抗不只停留在内心的追求上,也体现在他现实化的反抗行为中。1938年冬,周瘦鹃参加了有数十年历史的国际性的上海中西莳花会,以古朴、典雅、独具文人意味的中国盆景、盆栽两度夺魁,获得彼得葛兰奖杯,是为华人首奖。“园”及“园艺”成了周瘦鹃向世界展现中国人追求美、捍卫美的不屈意志与民族气节的渠道,他也从“园”那里逐渐感受到了新的人生价值。
变化的时事环境逐渐改变了周瘦鹃对“园”的态度,青年周瘦鹃在文学事业受挫时,将“园”视为精神避难所,短暂休憩之后他要回到文学战场继续厮杀。然而,国难摧毁了这种回去的可能,他作为“文学家”赖以依托的场境消失了,“文学家”的身份渐渐消隐在狞厉的现实中。这时他心头的理想之“园”已不是风雅诗意的古典园林,而更接近于普通中国人生活的安详宁谧的家园。很多学者都提到了周瘦鹃的爱国情怀。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写下不少爱国的文字,如《悼念郑正秋先生》一文开头就对日寇侵华的暴行给予了呼天吁地的感喟:“天哪!这三年以来,毕竟是一个甚么时代?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全体动员的压迫着这可怜的中国,直弄得百孔千疮。焦头烂额国土的损失,经济的损失,人才的损失,文化的损失,都不是表格所能开列,数字所能一一清算的。天哪!这将归咎于天心的不仁呢,或是人谋之不臧?”[23]人到中年本来就有人生苦短的悲思,加上山河破碎,促成了这一时期周瘦鹃沉郁深邃的家园眷恋。没有国,就没有恬静的家园。他以前可以到园林作精神的逃避,而此时他失去了家园,灵魂已无处可依。文学是养家之职业,然而国破城亡,文学有何益?周瘦鹃对侵略者的怒吼与家园的剥夺感是有关的,他坚定的民族气节与他的家园眷恋是相连的。园林、园艺对他而言不再只是身体休闲的场所,而成为其心灵的终极归宿。事业的挫折、时局的动荡、家园的消失进一步唤醒了周瘦鹃的隐逸型人格。这种隐逸型人格逐步推动了一种强烈的回归家园的退隐倾向的生成,“东涂西抹,匆匆三十年,自己觉得不祥文字,无补邦国,很为惭愧!因此起了投笔焚砚之念,打算退藏于密,消磨岁月于千花百草之间,以老圃终了……对日抗战胜利以后,我就……匆匆结束了文字生涯,回到故乡苏州来;又因遭受了亡之痛,更灰了心,只莳花种竹,过我的老圃生活,简直把一枝笔抛到了九霄云外”[24]。
周瘦鹃从安徽逃难回来后仍在上海租界工作,但此时他的心境已大不如昨。他不再或很少创作小说,其中既有文学市场改变的原因,也有他隐逸型人格影响的原因。他更多从事一些编辑类的“幕后”工作,张爱玲正是被他栽培的一株文学奇葩[25]。周瘦鹃甘心“捧得他人百花艳”,不求个人闻达进展,人生状态和艺术状态逐渐遁形到宁静的“园”的境界中。20世纪40年代,周瘦鹃编辑了很多“生活”类文章。在周瘦鹃主编的《乐观》中,他的儿子周铮开了一个“园艺”专栏并翻译了一篇《儿童园艺与良好公民》,文章写道:“每一个儿童的志愿是成为一个园艺家,自然界中,诗词里,催眠歌中,儿童的故事,寓言,文学里……都在颂赞着花的美丽。儿童生长在鲜花和树木丛中,当然有愉快的精神,他们是兴奋,有生气,有幻想,呼吸着花的芳香,熏陶成他们良好的性格。”[26]在这里,“儿童”象征了安详的家园与美好的生活,是周瘦鹃和周铮在乱世里向和平美好的“家园生活”的一种瞩望。周铮后来继承了周瘦鹃的园艺事业,其中少不了周瘦鹃耳提面命的指导,周瘦鹃对“园”的认同从他将之传授给下一代的做法中也可感受到。
不久周瘦鹃就离开上海回苏定居,原因有二。一是日本投降后,周瘦鹃想回《申报》主编副刊,但是国民党接收人员只授之以“设计人员”的虚衔,每月薪金30元,而且不需要到上海的报馆去工作,这相当于让周瘦鹃直接“退休”,这让他十分不满却又无可奈何。“官僚资本已侵入《申报》,将周瘦鹃排挤出编辑的行列”[27]。二是他的妻子胡凤君患上肺病,上海不适合疗养,所以周瘦鹃回苏定居,他说自己“这几年来受尽了种种磨折,种种刺激,弄得意志消沉,了无生人之趣;镇日的不是忧个人,忧一家,便是忧国忧世界,真的变做了一个忧天的杞人了”[28]。民族的磨难、事业的挫折、妻子的疾病等消磨了周瘦鹃曾经的雄心壮志,成为他熄灭逐利之心、回归家园的动力。周瘦鹃的人生观、职业观、事业观在悄然转变的同时,园艺为他赢得了新的国际国内声望,人们对周瘦鹃的园艺美学的认可为他即将到来的“园艺家”身份建构起新的社会评价系统。
四、社会主义“新人”与“园艺家”的产生
周瘦鹃的“园艺家”身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但我们不能说这个过程只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而应该说他从青年时期就已具备了变化的雏形,经历了中间的国难、事业转折、家庭变故后,才正式完成了转型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周瘦鹃对新政权对他的态度还是怀有疑虑的,他的文学事业得到了旧社会评价体系的高度认可,却并不适应高度组织化、强调统一的规范与管理的新中国“文学体制”,他的“文学家”身份是有风险的。与政治环境一起改变的还有新中国的文学市场环境。周瘦鹃擅长的“你侬我侬”的小说类型早已没了市场,“十七年文学”成为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主流文学类型,所以周瘦鹃不敢强调自己的“文学家”身份。
周瘦鹃“园艺家”的身份确立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和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主观要求等原因,积极进行理论探索,逐渐摸索出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群体的改造之路,“要求每一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应该具有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态度,并且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全心全意地站到工人阶级这一边来,以便更好地奉献一切力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29]。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消除了周瘦鹃的恐惧和焦虑。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周瘦鹃甚为尊重、关怀和爱护,鼓励他多写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坛做贡献。依据知识分子改造的要求,周瘦鹃需要重新规划和设计自己的新身份,这个新身份不但要符合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造的政策,而且要体现周瘦鹃的个人风格和气质。要满足这些条件,只有“园艺家”的身份比较适合。正如前文所言,周瘦鹃已比较认可“园艺”作为新的人生价值的标尺,而“园艺家”与社会主义“劳动者”这一形象又非常吻合,是一个安全且合适的新身份。与这种新身份的确立相伴随的是周瘦鹃参加和从事了一系列与园林、园艺有关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如他应邀出任苏州园林整修委员会委员,参与园林的维修工作。谢孝思这样说周瘦鹃的转变: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天翻地覆的震撼,打破了紫罗兰庵的幽静。在胜利红旗的感召下,瘦鹃走出栗里,下了孤山。人民重视他的转变,选他出来参与新中国建设大计。他的《西江月》词:“举国争传胜利,居家应有知闻。红旗竞赛一重重,心志能无所动?早岁出撄尘网,暮年退拥书城。济时也仗老成人,那许巢由隐遁!”道出他感奋的衷情。[30]
这种说法还是比较生动的。对周瘦鹃而言,园林整修既是一项符合他审美取向的文化“活动”,也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劳动”,他对园林艺术的追求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在旧上海长期从事文学、传媒工作的周瘦鹃的手头还是有一定积蓄的。用他的话说,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一个月的租房费就可抵原来母亲当家时的“三年半”的租费[31],但这不是说周瘦鹃完全没有生活压力,他结婚后先后生了七个孩子,妻子没有工作,这和他原来的出生家庭类似,他的妻子扮演了他“母亲”的角色,他扮演了他父亲”的角色。他不但要赡养他的母亲,还时常补贴经济能力较差的哥哥,所以尽管工资不低,但养家的任务还是很重。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境况有较大改善。周瘦鹃与胡凤君生的几个孩子都大了,也各自有了工作和家庭,虽然他与俞文英相继生了四个孩子,但总体而言养家负担已不如以前那么大。虽然旧的文学市场消失了,但新的文学市场正在形成,社会主义新文学有了广阔的市场。文学功底深厚的他1954年起在各大报刊发表了几百篇散文,“沪宁津三个出版社”都向他约稿[32],其中大部分是园艺散文。从创作来看,园艺散文和周瘦鹃之前创作的带有“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33]特点的爱情小说完全不同,园艺散文记录了周瘦鹃“莳花做盆”的园艺劳动,契合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现实,确立了劳动人民的创作立场。园艺散文将园艺视为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代表,抒发周瘦鹃“对生活、自然、社会的真切感悟”[18]54。园艺散文的行文风格简单质朴,显示出“明朗、向上之底蕴”[34]。它的主题、立场和语言都符合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显现了周瘦鹃的“园艺家”身份与“为人民服务”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从而获得了社会主义新文学市场的支持。周瘦鹃借园艺散文宣之世人,他已从旧社会的隐逸消极转变为老当益壮,正在努力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小说向散文的文学转型与他从“小说家”向“园艺家”的身份转型相伴而生。
与之相应的是,周瘦鹃努力将自家花园紫兰小筑开放为公共景观,这与他成为社会主义生活的代言人的身份变化有关。他“接待了来自祖国各地以至国外的无数嘉宾”,“不论是知名人士,还是一般群众,周瘦鹃均一视同仁、以礼相待”[35]。当然,黄恽指出,这个“开放”是“小心翼翼”的,“他不倚老卖老……对每一位来临的贵客都礼貌周至,同时却隐隐保持一点若即若离的距离”[36]。周瘦鹃在紫兰小筑的造园艺术中投注了大量精力,自豪地展现了“园艺家”的新身份。如他在造园时利用花木与不同区位的对应关系来展现花木本身的美丽。他养梅花,就在梅屋东西角的矮几上放置两盆绿梅与婆娑的屋影相映衬,形成一种“疏影横斜”的美。他所居住的凤来仪室窗外,就有意种下素心腊梅,旁边配上天竹,“相偎相依,恰像两个好朋友”[12]281,树、竹、窗和黄花红叶,颜色与位置的协调恰到好处,体现了他造园艺术的借景手法和配景手法。紫兰小筑的公共性使得周瘦鹃的造园艺术获得多数人的赞美,形成对周瘦鹃具有极大精神激励价值的正向社会评价系统。郑逸梅评价说周瘦鹃“是南社的唯一园艺名家”,谢孝思称紫罗兰庵不愧为苏州住家中的“人间天堂”[37]。周瘦鹃还加入盆景艺术研究组织含英社,开办香雪园邀人参观,专门研究栽花技术,他在园艺领域的艺术精进,使他已完全够得上“园艺家”资格了。
人们兴致勃勃地阅读他的园艺散文,津津乐道于他的紫兰小筑的风情万种的园艺设计,让周瘦鹃重新找回了写作的尊严与生活的幸福感。他在很多文章中反复提到自己“性爱花木,终年为花木颠倒,为花木服务”,他也爱屋及乌地偏爱颂花的诗词,在晨书瞑写之余常将写好的诗词在花前三复诵之。而且他常常会提到自身所处的小园里的风景和生活,“我苏州园子里”“吾家紫罗兰庵南窗外”“吾园弄月池畔”,不断向读者展现他的“园艺散文”的来处。在多种因素的促进下,周瘦鹃终于有勇气和信心对外宣称自己的“园艺家”身份,这个新身份是他将个人特长与新时期意识形态需求结合的产物。他不但在现实中从“文学家”变成了“园艺家”,而且从内心认同了这种转型。
五、“生活化转型”与美好生活的建构
心态史研究重视各类主观或人为因素对历史人物精神变化所产生的或浅显或深刻的影响,这决定了心态史研究需要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周瘦鹃的文艺之路可分为前期与后期。前期,他活跃在出版界的各大渠道中,名闻遐迩,在文学创作上侧重于描写缠绵悱恻的爱情和婚姻;后期,则发生了从功利化回归本体的重大转型,由热衷入世转向潜心遁世,希望过陶渊明、林和靖式的隐居生活[18]1。这其中,周瘦鹃的心态也发生了剧烈变化。
在周瘦鹃身份转型的过程中,“园”始终伴随着他,不但构成了他的现实生活环境,而且型塑了对他有重要影响的精神体系。青年时期的周瘦鹃将“园”视作游览对象和交往空间,此时的他体现出明显的儒家进取有为的思想,游园时的潇洒悠游的状态是为明证。“园”既让他的身体得到了休闲,也搭建了他的交往人脉,成了他文学事业蒸蒸日上发展状态的见证者。中年时期的周瘦鹃遭逢国乱,事业也遇挫折。在逃难途中,他对失去家园的悲伤感受及对政府无能的失望,滋生出更偏向于道家的隐逸思想。渴望世外桃源、跳脱尘世苦难的“文人隐逸”的传统在他的身上隐隐浮现。这种隐逸思想通过他的由国及乡再到家的家园情怀得以凸显。老年时期的周瘦鹃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狂喜之中,他在紫兰小筑中朝夕侍弄盆景,将生活美学充分现实化,“园”成了他响应党的号召、投身社会主义建设、认同社会主义劳动者新身份的场所。周瘦鹃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散文中,很少强调自己的文学家身份,而是反复强调自己的“园艺”喜好,这可能与他从前被左翼文人批评后形成的心理警觉有关,这种警惕和焦虑的情绪到了周瘦鹃被接纳进人民的行列进行改造后才慢慢缓解,因此周瘦鹃对“文学家”到“园艺家”的身份转型也非一开始就认同,而是在时代条件、文化环境的改变下通过心理调适完成的。在这种跨越青年、中年、老年的人生摆渡中,他的文学风格也经历了“哀情浓郁”“平实朴素”“清丽明朗”的转变,显现了文学美学和生活美学的呼应。
周瘦鹃的生活化转型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自我改造与发展的新经验,就是回到生活中发现“个人生活”和“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契合点。以周瘦鹃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作家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美好生活的新范型。它既不同于“劳工生活”,也不同于“革命生活”,而是继承了传统江南士子的闲适、清赏、把玩的生活美学特质的“文人生活”。它延续了发自中国古代尤其是在江南地区滥觞绵延的典雅精致的生活美学传统,丰富了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类型,在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容易遭遇物化加剧的现实困境的社会转型期,对于引导人们“走出精神生活的物化困境,转而追求崇高的精神生活,重新领受精神生活的真义”[38],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