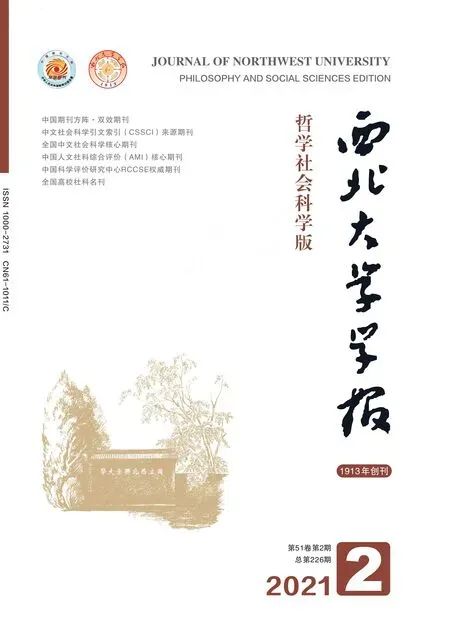元历史罗曼司:21世纪欧美小说理论中的消极理想主义
董雯婷
(1.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2.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提出的编史元小说理论或许是后现代小说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但近年来也不断有学者与其对话并提出批评,如布莱恩·麦克黑尔(Brian McHale)就曾指出,“哈琴的文类如果不是在理论中而是应用在实践里的话,某些程度上有些整体化。”[1](P17)而且在哈琴的理论诞生之后又持续涌现出了许多新的作品,这都为后现代小说理论的进一步探讨与发展提供了可能。美国学者艾米·埃利阿斯(Amy J. Elias)提出很多后现代小说应被称作元历史罗曼司(Metahistorical Romance),“就像司各特的历史罗曼司反映了他自己时代的历史编写,元历史罗曼司反映了后现代的历史转向”[2](P24)。这首先意味着她与哈琴理论关注的焦点相似:即后现代小说所表现出的对历史的强烈兴趣。但是她将哈琴编史元小说中的“编史”换成了“历史的”,同时将“元”这一前缀放在了“历史”而不是“小说”上,这一方面突出了后现代文学内部元史学的影响——对“事件”及建构出的“事实”的区分以及历史的建构性和叙事性的揭示;另一方面正如埃利阿斯所言,元历史罗曼司“强调了这种文类显性的对编史的痴迷,并穿过二十一世纪,直接将这种当代的虚构与更早的历史罗曼司文类联系起来”[3](P160)。与“编史元小说”所指涉的“编纂”和元小说玩弄炫目的叙事手法、完全消解现实本源的倾向不同,元历史罗曼司指出了后现代小说对“历史”——不仅是在文本内部,也在“外在真实”方面的强烈渴望,以及建立在这基础上对于文化原型和人类欲望乃至恐惧的具体想象,而这种渴望和想象完全可以上溯到历史罗曼司甚至更早的中世纪罗曼司上。
埃利阿斯关注和探讨了一系列在哈琴理论成型之后出版的作品,比如《兰皮埃尔的字典》(1991)、《冷山》(1997)、《检疫所》(1998),等等。在许多理论家对后现代小说中所表现出的理性主义信仰的解体和真相与历史的不可知性与不可言说性的认识基础上,埃利阿斯通过元历史罗曼司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她将后现代小说中叙事与真相之间的张力视为其对历史崇高(Historical Sublime)的执着但永不可能成功的追求,它注定只能是一种消极的理想主义,但却真实地作为一种微弱的希冀和欲望而始终存在着。
一、罗曼司:“低级艺术”的原型与传统
埃利阿斯将哈琴术语中重要的用于文类定性的一词“小说(Fiction)”换成了在西方文学史上更为古老的“罗曼司”,她的具体论述则直接从历史罗曼司开始,但对于欧美世界之外的读者来说,从“罗曼司”这个更基础的术语开始理解她的理论是十分必要的,使用“罗曼司”而非“小说”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独特意义:
首先是在后现代小说的研究中突出了文学史的层面。事实上,哈琴对这一点也并非熟视无睹,她曾强调:“我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提出的质疑和自身存在的矛盾首先涉及到了当今艺术与过去艺术之间的关系。”[4](P54)由此观之,埃利阿斯将欧美文学中重要的罗曼司传统引入后现代小说理论,并非是对哈琴的反叛,而是一种更加细化、也更具纵深性的文类理论研究。借由元历史罗曼司,她将欧美世界的后现代小说纳入了整个西方文学发展史,从中世纪的“罗曼司”到近现代的“历史罗曼司”再到后现代的元历史罗曼司,这是一个从未断绝的完整历程。后现代小说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罗曼司的遗产,已有许多学者分析过诸如《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典型的罗曼司模式(1)其中尤其以“宫廷爱情”等中世纪罗曼司所确立的故事和情节模式为代表。可参见Janet E. Lewis and Barry N. Olshen. John Fowles and the medieval romance traditio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Vol. 31, No. 1, Spring 1985. P:14-30.,以及包括A.S.拜厄特、金斯利·艾米斯在内的许多当代欧美作家作品中的罗曼司原型(2)这些作家的作品既可能是遵循罗曼司模式的,也可能是针对性地戏仿甚至颠覆的,参见Suzanne Keen. Romances of the Archive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Book.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1.。后现代小说戏仿罗曼司文本的情节套路和人物设置早已不是新鲜事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就戏仿了中世纪罗曼司《弗洛瑞斯与布兰彻弗勒》(FlorisandBlancheflour)中公主被困、王子从好色者手中将其拯救的情节模式,而库切的小说《福》则改写自经典的帝国罗曼司《鲁滨逊漂流记》。按照库切的说法:“既然世界上只有这么一点冒险故事,如果后来的人不被允许去啃这些旧东西,就只好永远把嘴闭上了。”[5](P54)这已表明以罗曼司为代表的文学史及其经典在后现代小说的创作中难以逃避的影响。而实际上,中世纪罗曼司也是这种依赖于“原型”和非原创的手段、大量吸收前代文学成果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再创作”的始作俑者,埃利阿斯在“元现代(Metamodernity)”一章,特别赞扬了这种“将许多不同的文学材料聚集起来”打造出的魅力。
其次,罗曼司推动了后现代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在这方面,哈琴虽然也充分认识到那种她所谓的“晚期激进元小说”与后现代小说的区别,但她只指出后者在交流层面革除了前者在叙事上过于激进的弊端,并没有详细论及后现代小说又是如何捡起可读性并唤起读者的熟悉感的,这一重要变化与罗曼司及其衍生文类紧密相关。罗曼司对情节的重视胜过一切,弗莱曾在论述罗曼司的叙事模式时指出它属于“后来式”叙事,“在描述人物发生的事情时,它从一个突兀的情节转到另一个情节,”[6](P35)从而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受其影响的后现代小说也表现出对情节的重视,一些作品直接改写了在读者中家喻户晓的罗曼司文本,尤其善于吸收其中的“典范情节(master plot)”,即那些“以各种变异形式在很多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情节,它往往涉及最为人们关切的欲望、焦虑和价值观。”[7](P42-43)尽管小说同时以强烈的自我指涉性、从制作幻象走向了暴露虚构,但与诞生于现代主义晚期的那种“元小说”显然十分不同,比起后者“强调叙事的固有价值,玩弄观众,玩弄现实,玩弄传统的文学成规”[8](P48),后现代小说以“典范情节”收获了取悦读者和唤起他们熟悉感的功效。由此观之,后现代小说与元小说之间的距离远大于它们与罗曼司的距离。
再次,罗曼司在后现代小说上的复兴也再次印证了经典世俗文学在文学史转型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与曾经被视为低级大众读物的罗曼司一样,许多后现代小说因其关于情色、谋杀、科幻、间谍或探案的题材和情节,常常被视为低级艺术。在这方面埃利阿斯与哈琴一样为后现代小说受到的不公待遇而叫屈:“多少次了,早期的后现代小说因为它破坏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的界限而被抨击;一些人简单地责备后现代主义的低级,同时又有一些批评家无可非议地看出,这样的摧毁边界是后现代与资本共谋的一部分。”[2](P121-122)而若我们正视后现代小说的罗曼司传统,这种“低级化”实际上标志着文学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世俗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弗莱所言:“罗曼司的”和“大众的”“之间的联系贯穿整个文学史。”[6](P25)在每一个时代,当作家们不断改变、创新直到不再有发展空间时,“文学就由此进入转型期,历史的包袱被丢弃,以罗曼司为中心的大众文学又重新登上前台”[6](P21)。后现代小说正是丢弃了现代小说的精英意识,以罗曼司式的天真烂漫的魅力、超现实的追求和人类深层欲望的满足来推进当下文学的转型。
需要指出的是,启用“罗曼司”这个术语并不表示埃利阿斯鼓励对可读性的单纯重视,更不意味着一种更加广泛的媚俗化趋势,而是对后现代的主张和诉求更加清醒的认识。正如弗莱所言,以罗曼司为代表的大众文学“对读者以前的言辞训练经历和教育的要求少之又少”[6](P23)。承自罗曼司的大众化、世俗化是后现代小说将读者理解的过程从学识与权威的影响中解脱出来的唯一途径,而并非是目的。事实上,埃利阿斯所言的“历史罗曼司”作为一个文类,“不包括在超市售卖的艳情小说(bodice ripper)和有法比奥插图(3)法比奥(Fabio)是一名男模特,因其为欧美大量不入流的言情小说拍摄封面和插图而广为人知。在这里埃利阿斯是以其名特指那些粗制滥造的当代言情和惊悚小说。的平装惊悚小说之流”[2](P16)。这些声明很明确地表现出了对大众文学淫乱、粗暴的那一面的鄙视和排斥。
最后,注意到“罗曼司”这个传统对于欧美后现代小说的影响,也意味着一种具有特定国族和文化背景的研究视角。在后现代时期,就像建筑一样,文学也与现代时期那种拒绝回顾传统、“过于简单化的,缺乏生活的复杂性以及与过去的连续性”[9](P97)的范式不同,而是与具体的地域和文化传统有特别的联系。具体而言,虽然罗曼司及其所代表的特点在中国常被译为“传奇”,但它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国语境中的传奇,而是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学内部自中世纪以来的罗曼司传统(4)有许多学者都提醒我们注意“罗曼司”与“传奇”的差异,比如浦安迪就有语:“今人或意译romance为‘传奇’,甚易引起误解。”见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页。。这也意味着,埃利阿斯相较于哈琴的整体化风格更加细化,她明确宣布自己关注的重点集中在欧美国家的后现代小说上,反之,第三世界的后殖民小说不是她讨论的重点。尽管她也承认这种分界方法十分粗暴,因为当代后殖民作家作品深受西方传统的影响,比如她提到的麦迪逊·贝尔(Madison Smartt Bell)描写海地反殖民历史的小说《众魂飞升》(All Souls’ Rising)(1996)等,这些小说的作者本人或作品的成功都具有鲜明的欧美文化背景,其上“罗曼司的幽灵”随处可见。总之,罗曼司的原型和传统是我们认识和解析后现代小说的重要切入点。
二、元历史罗曼司:后创伤时期的历史小说
20世纪人类接连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与大屠杀是这个时期历史最浓墨重彩的部分,给整个西方社会留下了“创伤记忆”,在当代欧美小说作者们所处的“后创伤时期”,过去的世界被与深重的苦难联系在一起,“暴力已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意识,而不是历史本身自然而然的或中立的产物”[3](P161)。后现代历史小说迷恋于表现历史的暴力与血腥,尤其倾向以战争文化、恐怖主义,甚至种族灭绝事件为中心来展开叙事,但又超越了幸存者回忆录、照片、影像资料等等经验主义的形式。这一方面是因为“经验主义的呈现使人愤怒。通过照片,一个人感到被不情愿地拖进去参与羞辱那些尸体”[2](P29)。另一方面,后现代作家们受到他们时代的影响,习惯于“质疑历史或感到需要修正它”[2](Pxxxvi)。然而任何对死亡数字和屠杀细节的探究都伴随着令人纠结的道德立场:在大屠杀的问题上保持中立的思考意味着不可理喻的残酷与麻木,有极大的贬低苦难、轻视受害者的嫌疑。于是,在后创伤时期书写历史已然超出了人类理性认知的范围,任何直接叙述或反思过去的尝试都将是失败的。
面对这种情况,后现代作家及理论家们的态度与主张并不是统一的,在埃利阿斯看来,他们主要分为乐观者与悲观者两个阵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现代性的衣钵,“与现代性的价值观相适应,主张后现代主义的总体观念的存在和伦理合法性,常常把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市场文化相结合”[3](P163)。直指理性现代性的破产,在理论界以詹明信为代表。而与之相对的,以哈琴为代表的乐观主义阵营则“庆祝人类的不接地状态,释放囚禁的元主义,进入自由游戏(理性、欲望、语言)的领域”[3](P163)。他们不再试图将真理与语言联系在一起,宣称语言之外没有历史,语言也无法如实传递真理和真相。
而元历史罗曼司的理论则属于晚近出现的第三种主张。它首先承认创伤历史的非理性和不可讲述性,“假设理解是不可能的,那么这样不可言说的残暴也就不会有基本的逻辑原理,或是因果关系的逻辑”[2](P39-40)。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在此被摒弃;但这种文类无论在做什么样的语言实验,都不能说是非叙事或反叙事的,相反,它们重视叙事,以至于看上去与19世纪的历史书写相仿。但是这些小说家很清楚并且一直在证明历史真理和共识真理之间的不同。其文本包含了两种想法:“历史不是真的,但历史是合理的。”[3](P164)而他们采取的方法是“将现实与幻想相融合,为神话和其他所有的可能性、乃至更加丰富的对历史的认知提供存在的空间。”[3](P166)在埃利阿斯看来,这正是曾经的历史罗曼司所做的,即将两种不相容的声音和看待历史的方式融合到一起。
作为一种虚构叙事倾向的代表,罗曼司这一文类自诞生起一直与历史著述相对立,格伦( D.H. Green)在《中世纪罗曼司的起源:事实与虚构1150—1220》一书中就指出,中世纪早期的七十年“欧洲文学传统呈现出一个转向,从明显倾向于历史写作(history writing),转到倾向于虚构叙事,最充分的例证就是罗曼司的模式”[10](P105)。罗曼司基于神话和魔法,是在“原型”基础上有意识虚构的产物。它代表着一种“传奇”(5)罗曼司从中古时期的一个文类名称转向“传奇”这种叙事类型和特点的代名词早已受到广泛认可,如有学者言:“众所周知,中古英语罗曼司研究者们所关注的那些文本是在那个‘roman’或‘romance’仍意味着一个俗语(比如法语)罗曼司文本的时代定型的,但它也可以应用于使用任何语言的一种叙事类型。”——Yin Liu. Middle English Romance as Prototype Genre. The Chaucer Review, (Vol. 40, No. 4, 2006), P335.的倾向,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正如弗莱对它的概括:“(罗曼司)与现实主义(realism)相对,按理想的方向规定内容的固定程式。”[11](P137)它具有一种风格化的特点,对现实进行简单的、缺乏复杂变化和实际考证的主观性处理。英文语境中“罗曼司式的”(romantic)即是指那些“夸饰情感的、不可能发生的、夸张的、不真实的特点”[12](P16),在17世纪的理性时代一直是个贬义词。
同时,罗曼司还代表着一种对历史的基于想象的看法。詹明信就曾指出,在12世纪时,西欧的封建贵族作为一个普遍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时出现了“旧式的、通过武功歌长期存在的善恶立场观念与这种新兴阶级团结之间的矛盾……罗曼司以其强有力的原始形式可以被理解为对这一实际矛盾的想象性解决,是对我的敌人何以能被认为是邪恶的这一问题的象征性回答”[13](P101)。在12、13世纪的发轫、兴盛之后,经过文艺复兴的继承与改良,罗曼司始终保留着这种对过去岁月的蓬勃的想象力以及与当下社会现实紧密捆绑的普适性,并试图通过它的主观想象与有意识虚构传达一种“永恒的、关于人性和世界的真理”[3](P162)。
19世纪后出现的、以司格特的小说为代表的历史罗曼司,正如卢卡奇所言:“提供给读者的是历史和罗曼司的奇怪混合物,其目的是使历史贫瘠化,将其表现得好玩和无害。”[14](P104)此处所谓的“贫瘠化”,即是将特定历史时期复杂多面的、琐碎的现实转化为罗曼司那种永恒的、神话原型式的、一切都“服从于它的辩证的总体结构”的想象性叙事,同时这一切又是建立在历史时间表而不是想象与原型的基础上的。在埃利阿斯看来,司格特的创作表现的是历史与罗曼司两种传统的交锋。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怀特对埃利阿斯的重要影响,怀特在《元史学》中赋予了历史语言学的特质,指出“历史通过从时间顺序表里编出故事的成功正是历史阐释效用的一部分……同一般‘虚构’的方式一模一样”[15](P3)。他将历史著述按照情节模式分为“罗曼司、悲剧、喜剧与讽刺”四种,确定了将一些历史看做罗曼司,或将罗曼司看做历史的主张。而埃利阿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司格特的历史罗曼司最终以历史冰冷残酷的现实的一面压倒了罗曼司神话与想象的一面:被视为神话的高地文化在面对当时转向理性主义现代性的认识时注定要灭亡。
但元历史罗曼司则改变了这种“东风压倒西风”的处理方式,如果说司格特的小说尽管以罗曼司的声调为一种失去的社会结构唱出挽歌,但却从属于一种“科学”地概括历史的方式,那么这种“从属”在后现代的元历史罗曼司中从未发生。这些小说一方面对记述社会现实有着不可否认的兴趣,同时又反复展示理性主义的现代性和认识论是如何在记述历史混乱的暴力时失败的;它们试图以罗曼司的模式理解那些创伤的过去,“从这个世界的压抑中释出想象——那种文化的、性欲的、或是神话的无意识的压抑。”[2](P147)同时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十分明了:这些被编织出来的罗曼司式“神奇故事” (fantastic story)并非认知历史的客观正确的路径,他们更像是进入了某个想象中的神话世界。小说就这样始终维持着罗曼司与历史之间的张力、以此作为后现代认知模式的核心:“同时在两种看待历史的方式中看到真理,而不觉得需要使一个完全从属于另一个。”[3](P162)在1970年后出版的后现代小说里,J.M.库切、扎迪·史密斯、萨尔曼·鲁西迪等人的作品都表现出了这种元历史罗曼司的文类特征。它们不断地推迟与经验主义的历史真相的接触,以至否认其存在;又清醒地感到那些植根于神话和传奇原型的罗曼司故事终究只是想象而已。这也可被视为后现代历史小说对其自身乃至整个文学世界的认识:“它同时怀疑和肯定着创作(poesis)作为一种人文主义的价值。”[3](P163)
三、渴望崇高:后现代的消极理想主义
元历史罗曼司作为一种后现代历史小说,反映出我们的时代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事实上,不仅是在文学创作领域,后现代理论家们同样如此。他们虽然反对以往线性的历史时间观念,但又转向了对历史空间的探索。比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詹明信的“认知地图”,爱德华·苏贾的后现代地理学,等等。在埃利阿斯看来,后现代小说如此频繁地试图去讲述历史,后现代理论家们如此钟情于对历史和时间、空间的讨论,这都是“一种渴望过去的标志,不是渴望过去的某一个非凡的时段或是过去的某种朴素的文化,而是过去本身,作为一种境况,知识与真理的坚实的基础。”[3](P167)其本质是执着地追求在诗学层面上对过去的体验。
然而,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分析的,后现代作家和理论家们已认识到历史书写注定是不准确的甚至伪造的,所以尽管确实感受到了这种对过去的渴望,但他们“没有能力严肃地对待这种渴望,他们甚至无法不带嘲讽地认识它。”[2](P22-23)许多后现代历史小说作者对历史的讲述都是混乱的、非线性的、反阐释的,他们既无法真正地进入历史,又不愿彻底地摒弃历史。这导致了后现代小说“悬停”在基于现实经验的历史和基于想象的罗曼司之间,无法与真实发生任何联系,但又渴望体验一种真实。
埃利阿斯分析了元历史罗曼司中的历史编写手法,与福柯、詹明信、怀特等人的观点相近,她指出它们都表现出对线性现时的怀疑以及一种共同的直觉:“空间可以提供正确的隐喻语言来重新概念化历史”[3](P167)。元历史罗曼司主要通过对多重的现时框架进行两种不同模式的处理来实现这一目标,使历史变得空间化。其一被她称之为“并置历史”(paratactic history),这种范式利用“并列,线性分离(linear disjunction)和非透视空间来迫使叙事中不同现时的面在文本内彼此接近”[2](P123),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的《福楼拜的鹦鹉》是这种模式的代表。另一种模式则被称之为“共时历史”(simultaneous history),“它将不同的历史时间沉凝到一个单独的、真实的平面,继而折叠成一个‘福柯式的异托邦’,历史在这些文本里成为了叙事集合的平台”[2](P124)。代表作品莫马迪(Scott Momaday)的《日诞之地》。这两种策略也常常被合并出现在同一个文本中,以建构一种基于空间意识和隐喻语言的历史编写,它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批评,其理论核心不在于叙事是否呈现了真实的过去,而是读者是否真实感受到了文本所再次概念化的历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历史小说中,重要的不是对伟大历史事件的重述,而是唤起相关人群的诗学觉醒。重要的是我们应再次体验那些引导人们思考、感受和行动的社会性、人性动机,就像他们曾在真实的历史中做过的那样。”[16](P112)
由此可见埃利阿斯与哈琴对历史编写看法的分歧,哈琴和她的编史元小说理论将“历史”视为一种文本化的可及性:后现代小说“把文本的生产和接受过程以及文本本身重新置于整个信息传达的情景之中,置于影响这类互动过程和文本生产的社会、意识形态、历史和美学的背景之中”[4](P40)。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后现代小说与文本之外的真实连接的可能。而埃利阿斯虽然承认对后创伤时期的欧美世界而言,由于对认识论和理性主义彻底失去了信心,“对历史崇高的不敏感性(nonsensibility)和不可知性的认识或许是极少数仅存的世俗信仰之一了”[3](P160)。但另一方面,她又强调后现代小说对过去的渴望并非只是文本性的,历史意味着后现代小说与真实的经验世界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那里不同种类的现实和时间彼此相互影响,或是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平面上,同一个历史性的瞬间。”[2](P147-148)进一步而言,后现代对过去的渴望可被视为一种对历史崇高的渴望,这也正是她的著作《渴望崇高:历史与后1960年代的小说》之核心论点。
何为崇高?“崇高”在西方文化史上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术语,从罗马帝国时期的《论崇高》一书到康德美学中重要的“崇高”理念,都有一个基本的立场,那就是人类天性渴望崇高。崇高基于一种对无限的、极端的从而也是难以概括的事物的敬畏乃至恐惧,“无限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的头脑充满令人欢欣的恐怖,而这种感受就是崇高的最真实的作用,也是检验崇高最可靠的方法”[17](P22)。后现代史学家安克斯密特将人类的历史经验分为三种:客观的历史经验、主观的历史经验和崇高的历史经验。其中,客观的历史经验是指那些笛卡尔式的历史学家基于逻辑论和经验论、对可证实的资料和档案进行放逐了主观性的转换和编辑的结果。而主观的历史经验,顾名思义,是一种基于主观感受、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时间意识及情感体验。至于崇高的历史经验,则是在历史学家考察客观的历史之前所经过的一个阶段:他们认识到历史已经离他们远去了,也只有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才会开始观照历史,而此时他们所面对的是几乎无限的、与自己所处的现时完全断裂的时空,此时,“失去与爱的感受悖论式地交织在一起,一种结合了痛苦和愉悦的感受。历史经验的崇高性正是来自这种结合”[18](P9)。人们一方面对无限的或极端的历史感到恐惧甚至痛苦,另一方面又享受它那令人敬畏的阴影。
在埃利阿斯看来,元历史罗曼司并不指向历史崇高,而是无限地接近它。之所以接近,是因为我们始终有寻找自己身份和位置的需要。正如在18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现代的主体通过对罗曼司英雄的理想化来确立资产阶级的个人观和伦理价值观”[19](P167),而在现代主义时期,我们又通过理想主义式的畅想未来找到自己,获得身份。但是在后创伤时期,西方文化数百年来形成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和对人自身的认知都已崩坏,未来不再值得畅想,理想也令人质疑,我们被迫通过回忆过去来寻找自己。于是元历史罗曼司“试图指明人类生活的经验与过去相遇时的分界或边界,……历史是不可触摸的,最终是不可知的,而且是令人兴奋的诱人和可怕的,因为存在着真理。真理在这个唯心主义意义上与生活体验的物质性相对,或者相反。”[3](P170)换言之,人们对历史崇高的感知正是因为经验主义真理和文本之外的真实世界的存在;但是“历史崇高”这一概念本身又意味着它们的不可知性。因此我们只能无限地、理想主义地渴望接近崇高的历史,同时又深知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触到它。也只有这种消极的理想主义能避免再次伤害那些历史创伤的受害者。
正是基于对后现代“渴望崇高”的认识,埃利阿斯试图与哈琴对后现代小说在政治指涉方面的观点保持距离,甚至提出挑战。众所周知,哈琴理论的一大重心是她对后现代小说政治指涉的审视,她通过对其“戏仿”与“反讽”手法的论述指出,后现代文本“从未逃脱双重编码,它总是意识到处于控制地位的和处于挑战地位的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性”[4](P157)。其再现的是一个没有主叙事的矛盾的共同体。鉴于此,后现代小说无论如何问题化、如何怀疑宏大叙事,它始终不可能到达彻底批判的地步,也不能带来“政治行动”,而是永远处于同谋的和妥协的位置。但埃利阿斯并不这样认为,至少在她看来不是所有的后现代小说都是如此,虽然埃利阿斯也受到德里达延异理论的影响,但她认为元历史罗曼司虽以重复和延缓的方式来处理历史崇高,但并没有压抑它的存在,元历史罗曼司对历史的态度是“可能性的连续体” ,其范围从一个极端的“讽刺甚至虚无主义、解构”到另一个极端的“重构世俗神圣”的信仰,跨越极大,而这种“多重化”和“任意性”,也意味着“历史本身就是如此”[2](P124)。这种理念丰富和扩展了后现代小说编写“历史”的意义,并为“政治行动”提供了可能。
退一步看,后现代小说即使真的导向串通一气的批判,也并非一定意味着同谋或妥协。埃利阿斯引用詹明信的“顶层视角”概念指出,西方第一世界的后现代主义者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削弱理性认识论的特权地位,摆脱其带来的束傅和偏见,“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者们的妥协政治也许是第一世界意识想要摆脱‘唯我主宰论’所必须的第一步”[2](P203)。正是在这方面,第一世界或说欧美国家的元历史罗曼司与第三世界的后殖民小说有所差异,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第一世界的小说家倾向于以“讽刺和解构的集合”的结局收尾,而后殖民小说则更喜欢出现“重构的”结局。埃利阿斯的这些发现都与哈琴那种一体化的后现代小说理论有所区别。
四、结 语
元历史罗曼司是西方学界继哈琴的编史元小说之后很有针对性的理论成果。通过引入“历史罗曼司”这一文类,指出了后现代小说的文学史传承,“罗曼司”的想象性虚构与大众文学特色得以彰显,而“历史罗曼司”将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传统和看待历史的方式结合起来的做法,则被视为后现代历史小说的鼻祖。另外,与哈琴等理论家将讨论聚焦于文本或文本在一定的情境和背景中可供阐释的意义不同,通过提出“历史崇高”和“创伤后想象”,“元历史曼司”对文本和文本以外的“真实”同样看重。这种消极的理想主义特征,是后现代的怀疑主义和罗曼司的想象性虚构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对西方文学内部的罗曼司、历史罗曼司传统不可忽视的国族特性和文化基因的强调,以及对当今世界各国后现代小说创作所面临的不同历史境遇的观照,也提出了研究的本土化问题,这或许能够给我们的后现代小说研究提供经验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