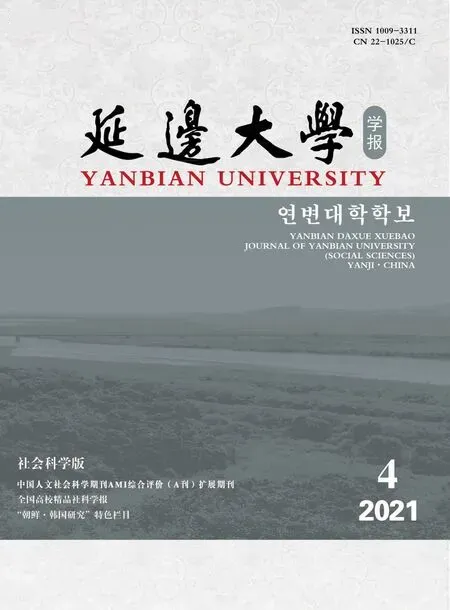汉语量词多重语法功能的类型学分析
崔艳姬 赵 磊
汉语学界对量词的界定比较宽泛,它既包括单位词,又包括分类词,即个体量词,也是汉语语法一般意义上的量词。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看,单位词几乎是人类语言所共有的词类,具有名词的属性特征,归为名词的下位范畴。然而,分类词却不是所有语言的共有词类,如印欧语言中不存在分类词。从词的起源来看,汉语量词的形成晚于单位词,是汉语数量结构表达方式演变过程中,语言结构自身调整的产物。(1)安丰存:《从量词的语法化过程看语言结构的内部调整》,《汉语学习》2009年第4期,第56-60页。从句法分布以及语义功能来看,量词与单位词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量词是特定条件下出现在表层结构中的语素,表达相关名词所指实体的某种特征。(2)Allan,K.,“Classifiers”,Language,Vol.53,No.2(1977),pp.285-311.本文提到的量词均为分类词,即汉语语法中的个体量词。本文将在类型学视角下对量词功能进行研究,可以更加全面地考察数量结构的句法构造和功能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可以通过跨语言的语言事实进一步证明量词功能演变具有语言类型学上的普遍性。
一、人类语言中的量词及汉藏语言数量结构
语言类型学家Craig(1992)、Aikhenvald(2000)等依据量词的形态特征及句法分布将量词划分为如下类型:数量型量词(numeral classifiers)、名量型量词(noun classifiers)、动量型量词(verbal classifiers)、属格型量词(genitive classifiers)等。(3)Craig,C.,Classifiers in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M.Fortescue,P.Harder and L.Kristoffersen(eds.),Layered Structure and Reference in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2,pp.277-301;Aikhenvald,A.,Classifiers: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4.这里数量型量词指的是依据名词的性质、形状或其他内在的属性对该名词的指称进行分类,原则上只能与数词(numeral)或数量词(quantifier)一起使用的特殊语言成分。汉语量词属于数量型量词,这种类型的量词主要出现在汉藏语系及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语言中。
Greenberg(1972)(4)Greenberg, J.,“Numerical classifiers and substantial number: problems in the genesis of a linguistic type”, Working Papers in Language Universals, No.9(1972), pp.1-39.曾指出,语言中数量型量词的存在与其他相关语法范畴关系密切,比如“数”范畴等,并根据数量结构内部成分顺序建立了四种序列可能:(i)数量名:如汉语、越南语、苗语、乌兹别克语、匈牙利语;(ii)名数量:如泰语、高棉语;(iii)量数名:如伊比比奥语;(iv)名量数:如景颇语。Greenberg(1990)(5)Greenberg, J.,Numerical classifiers and substantial number: problems in the genesis of a linguistic type, K.Denning & S. Kemmer (eds.) ,On Language: Selected writings of Joseph H. Greenberg,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66-193.指出,前两种语序比后两种更为常见,很多语言甚至允许前两种语序类型互换使用,但语言中不会存在“量名数”或“数名量”两种语序。
汉藏语系中采用“数量名”语序结构的语言有壮语、布依语、毛南语等;采用“名数量”语序结构的语言有彝语、纳西语、独龙语、载瓦语、傈僳语、阿侬语、基诺语、泰语、临高话、傣语、老挝语、仙岛语、土家语、白语,拉祐语等;采用“名量数”语序结构的语言有景颇语(6)景颇语中量词不是数量结构的必需成分。在表达数量意义时,“名词+数词”就可以表达,只有在需要强调数量或者名词的形状特征时才使用个体量词。因此,这一结构序列构造还有待研究。等。其中,具有“数量名”序列结构的语言,都允许量词重叠使用,这种用法与汉语量词重叠完全相同;而具有“名数量”序列结构的语言,反响型量词(echo classifier)(7)甲骨文中“人十有六人”,即“名数名”这样的语言现象中第二个“人”的功能是第一个“人”的计量单位,由于二者采取了同样的形式,因此,第二个被称为“拷贝型量词”,也称为“反响型量词”或“反身量词”。形式比较发达。
汉语量词属于数量型量词类型,符合语言类型学对量词种类的类型归类。然而,汉语量词的用法及功能已不再局限于在数量结构中辅助表达数量意义,其用法及功能已演变得更加丰富。
二、汉语量词起源的类型学阐释
汉语最早的记录载体甲骨文中并没有出现过量词。这一时期名词的数量结构为“名数”或“数名”结构,其中以“数名”结构为主。例如:
(1)十五犬,十五羊,十五豕。(前2.23.6)(8)“前2.23.6”是甲骨文骨片编号,下同。转引自安丰存、程工:《汉语数量结构演变及量词产生的语言认知机制》,《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03-110页。
(2)获白鹿一,()二。(前2.29.3)
采用5并12串电池组进行锂离子电池安全预警防护系统的功能验证,将电池组中的一个电池单元进行过充直至电池起火冒烟,试验过程中电池电压及火焰传感器、烟气传感器的数据均报送至上位机,这一过程中观察系统能够及时作出预警并采取动作。图5是预警防护系统的预警界面显示的报警信息。
然而,在甲骨文中还出现了如下的“名数名”结构形式。例如:
这种变化体现出“名数量”之间语义一致关系的根源在于量词是相应的名词经过同范畴词语替换而来的。因为量词和名词具有同源关系,因此,可以替代前面的名词。游顺钊(1988)(14)[法]游顺钊:《从认知角度探讨上古汉语名量词的起源》,《中国语文》1988年第5期,第361-365页。指出,“量词的前指替代价值(anaphorical value)来自于它在数量名词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笔者认为,位置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单纯的位置不能解释量词的这种功能是如何而来的。而量词的前指替代价值与反响型数量结构向同范畴词语数量结构演变有密切的关系。
(5)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小盂鼎)
金文中依然存在这类结构,而且数量增多。例如:
(4)俘人十又六人。(137反)
这种用法不是古汉语的特殊用法,在很多汉藏语系语言中也存在这样的结构,被称为反响型量词(echo-classifier)。(9)李宇明:《拷贝型量词及其在汉藏语系量词发展中的地位》,《中国语文》2000年第1期,第27-34、93页。例如:
(6)a.载瓦语 pum51(山) lă21(一) pum51(山) (一座山)
b.基诺语 tso42(房) thi44(一) tso42(房) (一座房子)
c.傈僳语 ko44(山) thi31(一) ko44(山) (一座山)
反响型数量结构带来了语言成分冗余和功能模糊等问题,必然需要进行调整,如“人三人”结构中,其后位的名词“人”逐渐开始被同范畴词语替换,一方面保留了名词的部分语义特征,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了与此前不同的句法语义功能。这种变化带来了后一名词的区分作用,从而量词具有了分类功能。例如:
e.哈尼语 mja33(眼睛) ni31(二) mja33(眼睛) (两只眼睛)
试剂:乙醛(40%,分析纯),购于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乙醛脱氢酶,sigma公司;碘、碘化钾、亚硫酸氢钠、淀粉、草酸铵、结晶紫、番红等试剂均为分析纯,购于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梁敏(1983)(10)梁敏:《壮侗语族量词的产生与发展》,《民族语文》1983年第3期,第8-16页。考察了侗台语族的泰语、傣语、老挝语、临高话等语言,也发现了此类语言现象。例如:
悬臂模板的施工工艺为:(1)安装墩身首节钢筋骨架,安装模板并安装预埋件,埋件通过M30定位螺栓固定在面板上。第一次浇筑混凝土时,用对拉螺栓加固模板;(2)浇筑首节墩柱混凝土;(3)拆除模板及架体;清理模板表面杂物;用塔吊安装三角架,将三角架挂在相应的埋件上,架体卡在支座上,插上安全销;(4)安装模板通过可调斜撑调整模板的垂直度;通过后移装置将模板下沿与上次浇筑完的混凝土结构表面顶紧,确保不漏浆,不错台,浇筑第2节混凝土并养生到可拆模强度;(5)拆除可周转的埋件,清除模板表面杂物,按设计图纸把爬架吊装就位,拆除前一次可周转的预埋件,以备后用;(6)安装本节段钢筋,进行本阶段混凝土浇筑。
(7)a.泰语 khon2(人) sa:m1(三) khon2(人) (三个人)
(3)支护方案。巷道净断面要求6.95 m×7.5 m,断面较大,为保证使用年限内的支护质量,确定采用锚网索+混凝土进行联合支护,硐室毛断面7.95 m×8.0 m。
c.临高话 dun3(树)tam1(三) dun3(树) (三棵树)
一般认为,反响型量词(echo classifiers)是量词的雏形,这一用法在古汉语以及汉藏语系的很多语言中均可以找到证据。(11)戴庆厦、蒋颖:《论藏缅语的反响型名量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124-129页。反响型量词结构,如“人三人”,是在“三人”结构演变为“人三”结构以后,受到单位词表量结构的规范作用而形成的,是结构类推的结果,因此,第二个“人”并不具有表意功能。
反响型量词用名词本身称量,名词如果为单音节,则采取直接复制的形式;如果为多音节,则取其最后一个音节来拷贝,如哈尼语、缅语、阿昌语、载瓦语、浪速语、拉祜语等。徐悉艰(1994)(12)徐悉艰:《彝缅语量词的产生和发展》,《语言研究》1994年第1期,第185-190页。指出,使用名词本身称量,在句中出现时,一般不能脱离名词,否则意义不明确。可见,这种反响型量词在句中主要承担的是语法功能的作用。
语言学家Haugen将语言与所处环境隐喻为特定动植物与其生存环境间的生态关系,生态语言学这一术语应运而生。[3]
通过对古汉语数量结构以及反响型数量结构的观察,发现反响型数量结构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古汉语存在“数名”结构的语言事实说明古汉语可以直接使用数词修饰名词的形式来表达数量意义,这就可以旁证为什么汉语量词出现在数词的后面。一般认为,量词是名词虚化而来的,因此,语言结构必须为量词的产生提供句法机制,包括语序。“数名”序列结构是“数量”序列结构出现的句法基础。二是汉语使用话题优先的语言表达结构,先表达概念,再表达数量,但是,汉语数词不具有替代名词的能力,加上汉语基数词和序数词在使用中分工并不明确,如“马三、牛四、羊五”,数量意义和次序意义模糊。为解决这一矛盾,同时弥补汉语数词缺乏替代名词功能的不足,采用在数词后面重复前面名词的手段实现数量意义的表达。由于“马三马”这个结构是复制了前面同一名词,因此,被复制的名词可以回指前面名词。
反响型数量结构是量词产生的基础,但这只是一种语言表象。量词产生的内部结构原因是汉语数词不具有指代功能,无法回指前面名词;外部原因是汉语话题化表达方式使得“数名”结构转变为“名数”结构,造成“名数”结构后面出现了空位,而这一空位恰好是名词本该出现的位置。通过不可数名词表量结构“名-数-单位”结构的规范及类推作用,促成了反响型数量结构的形成。但是,反响型量词结构造成了语言构造及表达的冗余,对于语言自身来讲是不经济的表现。语言结构自身必然要进行调整,以使冗余成分合理化并合法化。
从古汉语数量结构以及汉藏语系的诸多语言反响型数量结构的用法来看,反响型数量结构是促成量词产生的结构基础。从这方面来看,汉语量词的起源具有语言类型学依据。
三、同范畴词语替换反响型量词
d.拉祐语 tsu31(桥) te53(一) tsu31(桥) (一座桥)
b.他家过年吃了一头猪。
(9)易(赐)女(汝)邦司四白(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赐)尸(夷)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大夫。天子常大量赏赐臣下。(大盂鼎)
将所有可能影响死亡的因素(年龄、性别、肺部疾病史、原患疾病、ILD发生时间、放疗史、化疗史、高剂量激素治疗)作为自变量,以转归为因变量进行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例(8)、例(9)中的“臣”与“鬲”都可以指奴隶,但内涵不同。“臣”指男性奴隶,“家”是“圈养的”意思,这里指没有自由的奴隶;“鬲”指战争俘获的奴隶,与表达个体意义的“人”相通。后来“人”与“鬲”合用,成为奴隶的代称,并用“夫”来表达,“夫”指的是出苦力的劳动者。从而“夫”和“人”都具有了分类作用。同范畴词语替代反响型量词,使替代成分拥有了区分前面名词所指的功能。游顺钊(1988)(13)[法]游顺钊:《从认知角度探讨上古汉语名量词的起源》,《中国语文》1988年第5期,第361-365页。指出,这里“夫”取代“人”,语义的迁移相对说来是微小的。然而,这种替代在上古汉语量词系统的发展中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这种替代不是任意的,必须采用与前面名词相关的同范畴词语,因此,必然与前面名词具有相似或相同的性状特征,进而同范畴词语逐渐趋向于凸显其前面名词的典型性状特征,而失去自身的词汇意义。再如:
(10)车二丙。(36481正)
(11)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马口匹,俘车三十两,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三十八羊。(小盂鼎)
(12)武公乃命禹率公戎车百乘。(禹鼎)
在例(10)、例(11)、例(12)中,“丙”“两”“乘”均为名词,分别指“一马拉车”“两马拉车”“驷马拉车”等概念。因此,这些名词具有区分“车”的作用。后来,统一使用了“辆”来量化“车”。
(3)羌百羌。(32042)
汉语的这种用法在壮语中可以得到印证。壮语的量词可以代替名词单独使用,“量词+修饰语”的结构可以表示那些量词所指代的事物。(15)薄文泽:《壮语量词的语法双重性》,《民族语文》2003年第6期,第7-12页。例如:
(13)tu2bin1(飞的那只)
只 飞
徐悉艰(1994)(16)徐悉艰:《彝缅语量词的产生和发展》,《语言研究》1994年第1期,第185-190页。通过对彝缅语族语言量词的观察发现,名量词除了反响型量词外,还有其他专用的量词。这些量词的使用能力非常强,把名词按照同一属性、类别、性状分成若干小范畴来表量。可见,同范畴词语对量词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们语义功能虚化,而语法功能增强。反响型量词逐渐被同范畴名词替换使用而演化出分类及替代功能,具有类型学发展特征。
四、量词指称功能形成及差异
根据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2006)(17)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中国语文》2006年第5期,第387-400、479页。对汉语数量结构发展历史的考察,发现汉语数量结构在“数词-单位词-名词”格式的类推作用下也由“名数量”向着“数量名”结构转化;伴随着数量结构的变化,量词语义功能也随之出现了变化,演变出个体标记、指称、领属标记等新的功能。安丰存、程工(2014)(18)安丰存、程工:《生成语法视角下汉语量词句法功能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51-58、160-161页。根据量词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功能特征,在生成语法的框架下对“数量名”结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轻名词(light noun)功能语法范畴,从而对量词的句法功能属性进行了定位,并将其句法构造分析为[nP数[n量[NP名]]]。
(一)汉语普通话量词指称功能
汉语“名数量”结构被“数量名”结构替换以后,整体序列又回到了以前“数名”结构,只是中间多了一个成分。由于该成分处于名词之前,因此,不再具有替代功能,只保留了分类功能。随着语言的发展,同范畴词语也产生了竞争关系,只有部分同范畴词语可以出现在“数量名”结构中“量”的位置。“数量名”序列中的“量词”的分类功能也变得越来越弱。除了语义区分特别强的量词可以体现分类功能以外,其他量词分类功能逐渐消失。例如:
(14)a.他家过年吃了一口猪。
(8)姜商(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令簋铭)
(4)为了广纳人才,扩大“带头人”的选择范围,选出能真正改变一村经济面貌的“带头人”作为对农村的人才支援,可以采取与“援藏”一样的政策力度,让来自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大学生、公务员都可回原藉参加选举.大学生胜选者可保留学藉,任职结束后仍可选择继续学习,任职经历视同社会实践;公务员胜选者可保留原职,可连续计算工龄,任职结束后仍可回原单位工作.胜选者作为准公职人员管理,根据任职业绩考核计酬.任职能力与政绩表现突出者可直接招录为县、乡级公务员,以拓展农村经济“带头人”的政治前途,激励这些人为一方村民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鼓励退休公职人员回乡参加竞选,发挥余热,勇当发展农村经济的带头人.
例句(14a)和例(14b)中,不同的量词所表达的“猪”的含义不同。“头”指向猪的个体,即“整体猪”的概念。但是“口”指向屠宰后的“猪”,即“猪肉”的概念。然而,数量结构由“名数量”向“数量名”发生转变后,处于数量名中间的量词就很少体现这种分类功能。
由于量词位置和功能的变化以及量词与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等原因,量词逐渐演化出个标功能,即标示后面名词具有个体特征意义。可以认为,所有的“数量名”结构中,量词均具有个标功能。当量词演化出个体标记功能后,也分化出了形容词的用法,表达“单个的”概念,如“匹马单枪”。数量结构的变化,使得量词语义表达功能逐渐减弱,而发展成为一个功能性成分。
由于数量结构出现的句法位置以及数词“一”缺省,量词开始演变出表达指称意义功能。不同语言间指称功能意义开始分化。有些语言的量词体现定指的指称意义而有些语言(如普通话)的量词体现不定指的指称意义。例如:
理想的发展模式是什么?钟秉枢(2013)认为需要在继续发展传统优势项目的同时,突出发展集体对抗和体能类项目,还要关心运动员的长远利益和全面发展。对竞技体育的发展模式的思考应该不忘初心,回归本质,孙科(2012)认为竞技体育价值导向应回归理性,能真正满足人全面发展的需要,如果忽视了“以人为本”,那么竞技体育就会偏离原本的模样。进入后奥运时代,体育改革是必须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改革究竟怎么改,如何具体实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15)我买了支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是一项极其崇高也非常特殊的事业。城市公立医院需要在提高资源利用率、改善服务可及性和服务质量方面,发挥主导作用[14]。我院在开展医务志愿者服务工作中,通过志愿助人服务、志愿关怀服务、志愿环卫服务为病人提供良好的就诊体验,有利于增加病人医院就诊意向,提高病人就诊满意度;医护人员志愿公益义诊,开展公益活动,有利于提高居民就医可及性[15-16]和健康生活意识和行为;为社区居民提供与其医疗保险计划相关联的综合性健康服务[17],有利于提高服务质量与服务连续性[18]。
例(15)中“量名”结构不用于表达数量意义,而着重表达类别意义。其作用相当于英语不定冠词“a”的用法。例如:
(16)I bought a pen.
在英语中,如例(16)“a pen”的语义重点为类别义,而非数量义。在这一方面,汉语“量名”结构中的“量词”体现出与英语不定冠词“a”类似的句法语义功能。
传统语法学家认为,这里的“量名”结构是“一量名”结构省略了“一”的用法。但是,在普通话中,“量名”和“一量名”结构在句子中分布不同,其中的“量词”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不定指的指称意义,而非数量意义,因此,不能简单地对这一现象下结论。
(二)汉语方言量词指称功能
汉语方言表现出了比普通话更丰富的指称功能,在汉语的一些方言中“量名”结构中的“量词”除了表现出与普通话相似的不定指功能外,还表现出定指的功能。
黄伯荣(1996)(19)黄伯荣: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青岛出版社,1996年,第132-137页。曾对遵义话、苏州话、上海话、闽方言、广东话等地方言中的量词的定指功能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
(17)a.江苏苏州话:杯茶泡得发苦葛哉。(这杯茶沏得发苦啦。)
军工企业作为国防科技工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在技术水平上实际上是比较先进的,但由于很多军工企业的军用产品研发与民用产品研发出于完全割裂的状态,因而这一技术优势并未能够在军民融合发展中体现出来。针对这一问题,军工企业需要加强军民技术间的交流,通过对相关流程与标准的制订来对军民技术传到机制进行完善,使企业在军用领域方面的技术成果能够尽快转为民用技术,并提高现有军用技术的军民两用性。这样一来,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军用领域的技术优势自然也就能够在民用领域的产品研发工作中得到更好的体现。
b.上海话:块黑板挂勒啥地方好?(这块黑板挂在什么地方好?)
c.闽方言:张画雅绝。(这张画很漂亮。)
d.广东潮州话:张纸克来。(那张纸拿来。)
(4)让学生组队进行小组讨论。在课程进行到一定阶段时,组织学生就某一领域的新进展,某一课程重点难点内容,或某个科研成果的案例进行小组讨论,全部过程使用英文,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也提高学生用英文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例如,对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的分子机器研究成果分组讨论,激发了学生发散的充满想象力和创新性的点子和思路,课堂气氛热烈有趣,充满生机。
e.广东汕头话:个人肥肥。(那个人胖胖的。)
f.广东广州话:只狗死咗。(那〈这〉只狗死了或者狗死了。)
例(17)的方言中的量词在句中均可表达有定的指称意义。石汝杰、刘丹青(1985)(20)石汝杰、刘丹青:《苏州方言量词的定指用法及其变调》,《语言研究》1985年第1期,第160-166页。曾对苏州话量词的定指功能进行了研究,发现量词的功能相当于英语中的定冠词。方言的这种用法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量名”结构不是“一量名”省略“一”的结果。因为“一量名”不具备定指意义。Cheng和Sysbema(1998)(21)Cheng,L.& Sybesma, R.,“Yi-wan Tang,Yi-ge Tang:Classifiers and Massifiers”,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Vol.28,No.3(1998),pp.285-412.指出,广东话中的“量名”结构具有有定与无定两种解读,具体依语境决定。黎俊坚(2002)(22)黎俊坚:《陆川客家话的量词》,《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第122-124页。指出,客家话也存在上述用法。但是,“量名”结构既表达有定意义,又表达无定意义两种用法。例如:
10月22日中国复合肥零售价格指数 (CCRI) 为 2499.54点,环比上涨28.24点,涨幅为1.14%;同比上涨211.78点,涨幅为9.26%;比基期上涨52.83点,涨幅为2.16%。
(18)a.条鱼好大。(这条鱼很大。)
b.食了只烟就走。(抽完这支烟就走。)
(19)a.挂幅画落墙根。(挂一幅画在墙壁上。)
b.本书放落台面。(一本书放在桌面上。)
汉语方言中的“量名”结构出现在主语位置上可以表达有定的指称意义,这与汉语普通话中“量名”结构的句法分布和意义完全不同。另外,这种用法还存在于并列结构中的主语位置。例如:
创造性思维可以帮助学生在高中数学学习中,有更多自己的见解和想法,给学生带来数学知识深层次的感受.而不是像以往的数学教学中,学生被动接受数学知识,而不能进行自我的思考和判断,没有凸显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使教师的教学偏离最初的教学目标,达不到自身教学的意义.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教师的方法指引下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可以有效促进学生数学知识的获取和自身能力的提高.
(20)本书同支笔不见了。(那本书和那支笔不见了。)
例(20)的并列“量名”结构说明方言中的量词具备了冠词的功能和用法,但在普通话中尚未出现此类结构。“量名”结构在演变过程中产生了指称意义,在普通话中体现泛指意义,在方言中还可以体现定指意义。句法结构的变化带来新功能的产生,同时,功能的变化也带来了结构上的不同表现。量词在名词短语结构中具有特殊的句法地位,结构赋予了量词以冠词用法。普通话和方言“量名”结构中的量词功能间的差异体现了二者在参数设定上的不同,同时,也体现出二者在量词冠词化程度上的不同。
(三)少数民族语言量词指称功能
(22)a31nu31kh55d33tshu55ja33.(那头牛很肥。)
比工仡佬语“量名”结构中量词在名词前具有定指的功能。(23)李霞:《仡佬语中的一个泛用量词》,《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115-120页。例如:
只 羊 被 只 虎 吃 已行体助词 语气助词
哈尼语“名量”结构中量词可以表达定指意义,具有和定冠词相同的语法功能。(24)李批然:《哈尼语量词研究》,《民族语文》1992年第5期, 第22-27页。例如: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也存在“量名”和“名量”等数量结构,它们也表现出与汉语普通话以及方言相似的指称功能,可以表达定指意义、不定指意义或定指和不定指两种意义。
牛 头 很 肥 (助)
彝语“名量”中量词的用法与汉语普通话相似。在汉语中“一”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数词;另一个是类似于英语“a”的功能,如“一会、一些、一点”等。“名量”结构在彝语中可以表示单个名词的数量。(25)顾阳、巫达:《从景颇语和彝语的量词短语看名词短语的指涉特征》,李锦芳:《汉藏语系量词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89页。例如:
(23)tsho33ma33(一个人)
人 个
例(23)中的“名量”结构之间可以加上数词tshi22“一”,但加上数词后,意义相当于英语的“one”;而不加数词相当于英语不定冠词“a”的意义。
白语的“名量”结构可以表达定指和不定指意义两种功能,具体意义需要结合语境和表达方式来确定。(26)王锋:《浅谈白语的名+量结构》,李锦芳:《汉藏语系量词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4-208页。例如:(27)安丰存、赵磊:《现代汉语“量名”结构类型学分析》,《汉语学习》2016年第3期,第53-63页。
(24)khua33le21pia42l21.(那只狗叫了。)
狗 只 叫 了
(25)pa32t21me44ts31m44tshi55to33l44.(豹子会爬树。)
豹 只 爬 树 爬 好 得 (助)
总之,“量名”结构在仡佬语中表达定指意义,相当于英语定冠词“the”的用法。“名量”结构在彝语、壮语中具有不定指用法,相当于英语不定冠词“a”的用法;在哈尼语中表达定指的用法;在白语中可表达有定和无定两种功能。量词在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诸多语法表现出了类型学一致的规律。由此可见,汉语量词表达指称功能的“特殊”用法并不特殊,具有跨语言的普遍分布规律。
五、量词定语标记功能
刘丹青(2005)(28)刘丹青:《汉语关系从句标记类型初探》,《中国语文》2005年第1期,第3-15页。通过对汉语方言中的领属结构以及关系分句标记所做的调查发现,在普通话中,指示词“这、那”可以作为领属标记,如“我这书”“小王那朋友”“北京这胡同”;而在一些汉语方言中,如在苏州话中,可以使用量词作为领属标记,如“我本书”(我的那本书)、“红颜色件衣裳”(红颜色的那件衣裳)等,并且量词还可以作为关系分句的标记。例如:
(26)a.俚买本书好看。(他买的那本书好看。)
b.生病只猫死脱哉。(生病的那只猫死了。)
量词的定语标记用法来源于其有定意义的冠词用法。Himmelmann(2001)(29)Hemmelmann,N.,Articles,Haspelmath,M.,E.Konig,W.Oesterreicher & W.Raible.(eds.),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Berlin:Walter de Gruyter,2001,pp.834-835.分析出连接性冠词(linking article)就兼有冠词和定语标记两种用法。Mattews & Yip(2001)(30)Matthews, S. & Yip, V.,Aspects of contemporary Cantonese grammar: The structure and stratification of relative clauses, H. Chappell (eds.),Sinitic Grammar: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pp.266-281.发现,香港粤语指量短语作为关系分句标记时,常常省略指示代词。例如:
(27)我写咗(嗰)封信好长嘅。(我写的那封信很长。)
量词可以充当定语标记的语言,必然与其定指的用法有关。有些语言,量词词类可以作定语标记,如安徽绩溪话(31)赵日新:《绩溪方言的结构助词》,《语言研究》2001年第2期,第30-36页。和广东开平话(32)余霭琴:《广东开平方言的“的”字结构——从“者”、“之”分工谈到语法类型分布》,《中国语文》1995年第4期,第289-297页。。例如:
(28)a.担来写对联张红纸。(拿来写对联的那张红纸。)
b.我本书呢?(我的那本书呢?)
(29)a.我件帽。(我的帽子。)
b.我个细佬卷书。(我的弟弟的书。)
量词发展出了定语标记功能,该功能出现的前提是量名结构中所具有的有定指称功能。汉语方言的语言事实说明量词的功能和句法特征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六、结语
量词功能的演变与数量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结构的变化促使量词功能发生变化。量词的这些功能演变在各个阶段均可以在汉藏语系语言以及汉语方言中寻找到依据,因此,量词的功能变化是具有类型学一致的演变。
从量词基本功能以及数量结构来看,汉语与汉藏语系多数语言中的量词具有类型学的一致特征。量词的主要功能都是与数词和名词通过不同的序列组合构成数量结构,以表达可数名词的数量意义。但是,量词在汉藏语系语言中的发展并不平衡,具有“数量名”序列结构的语言,量词比较成熟,而具有“名数量”序列结构的语言,反响型量词比较普遍。汉藏语系一些语言中的量词除了作为数量结构中的必需成分外,还具有一些特殊的用法。概括来讲,功能的演变基本过程如下所示:
量词发展出个体标记功能以后,分化出形容词的用法,表达“单个的”概念;而当量词发展出指称功能时,不同的语言在此发生了分化。有些语言发展出了不定指功能,进而抽象化,朝着“个”化方向发展;而有些语言或方言则发展出了定指功能,进而朝着定语标记功能方向发展。量词功能演变的过程存在突变,但是却具有充分的跨语言分布的语言事实依据,体现了语言类型学一致的发展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