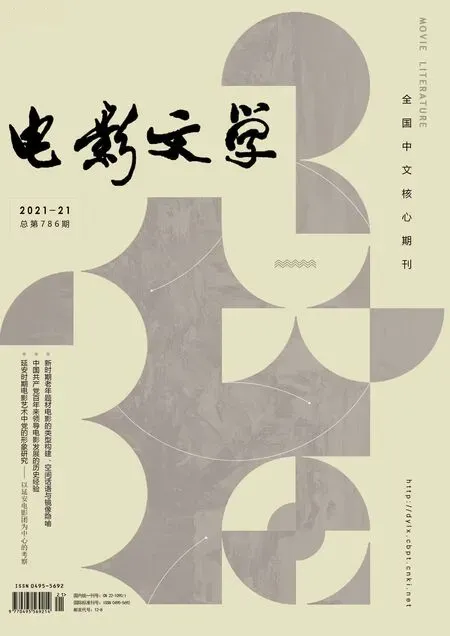论电影色彩对历史重构的表达
孙 伟
(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色彩学本质上属于跨学科领域,其中涉及专业术语、颜料化学、印染技术、服装设计,一些伴随色彩应运而生的各种社会规范,如日常生活中色彩的地位,社会对于特殊色彩的规范,宗教伦理道德的色彩禁忌,以及自然科学(如光学等)和艺术创作。而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色彩首先被定义为一个时代的社会现象,而不是化学颜料,也不是光谱色号,更不是一种主观视觉感知。一个时代的社会构建了色彩,赋予其独特的名称和定义,确定了色彩的规则和价值,组织色彩的实践运用,并制定色彩的等级地位。一言以蔽之,色彩史首先是一部社会史。不承认这点,我们将陷入狭义的神经生物学主义和枯燥乏味的科学主义之中。
鉴于色彩承载了过去历史社会中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信息和资料,历史色彩这一概念应运而生。我们可以将其与色彩本意进行对比分析。色彩本意是色彩专业术语的原初意义,代表每一个色域中的独特色彩,并与其各自所表达的色彩元素相对应。而历史色彩则强调色彩的文化特质。这一专业术语在其象征性运用中则首先被用于阐述18世纪晚期开始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内涵,其能够反映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地区的特有叙事和表征。当我们谈论地域色彩或者历史色彩时,显然其所指代的往往是一种色彩隐喻。历史色彩确切地说并非如同文学作品所描绘的使用某一特殊色彩来指代一个时代,而是通过诸多细节中色彩隐喻映射出时代背景从而给观众营造真实的历史观感。鉴于此,历史色彩的使命在于编织各种时代要素以便于强化历史重现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其中装饰、服装、装扮以及配饰道具等成为重要的时代元素用于重构一段历史。
然而,历史色彩如何在电影中得以应用呢?换言之,电影色彩如何从现实层面或者象征层面来实现对历史重构的表达?在不同影片中如何选择特定历史色彩,而又该赋予其什么含义?本文通过分析电影色彩语言重建时代背景的艺术手法来深入研究电影色彩对于历史重构的表达。电影色彩往往通过图片或者影像的互文效应来强调主色调的使用,其中涉及导演偏好色彩,比如张艺谋很多电影作品中的红色色调,或者一些特殊色系,甚至包括光影的特殊处理等。这些不同的艺术手法赋予影片叙事一种色彩基调,并通过这种色彩基调唤起观众对于影片叙事历史时代背景的感观认知。其中,电影色彩融合服装、装饰、妆扮、配饰道具甚至绘画作品等共同实现了对历史重构的表达。
最后,本文同时也解答电影中特殊色彩运用的问题。此类电影色彩的使用更偏向于象征意义层面,而非现实意义层面。强烈的色彩突兀对影片场景的和谐氛围构成诸多颠覆,这种色彩“刺点”构成了“影像伤痕“,从而以动人心魄的方式触动观众的心灵,引领观众探讨影片潜在的戏剧性冲突,并反思影片故事背后的历史。
一、黑白色调——纪实效果与历史时光重现
营造真实的历史观感是历史题材类电影的重要使命,而黑白色调则有助于电影实现历史时光的重现。通过挖掘分析相关电影素材,我们可以发现在历史题材类电影中常常受到现实主义风格的影响,而这种现实主义风格往往穿插融合虚幻和现实双重场景。比如艾道尔·斯考拉(Ettore Scola)的《不凡之日》便属于此类现实主义电影。这部影片主要讲述德国法西斯入侵时期一个独守空房女人的一天,而影片中现实场景与虚幻场景的衔接几乎天衣无缝。事实上,很多历史题材类电影往往被拍摄成黑白片以便于重现过去时光,其中以吉姆·贾内许(Jim Jarmusch)导演的电影《离魂异客》和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为典型代表。然而此类电影也并不总是局限于黑白两色,有时候也会以单彩色调的方式来呈现。深受英格玛·伯格曼(Bergman)和表现主义电影影响的伍迪·艾伦(Woody Allen)就是以一种水墨色调拍摄影片《开罗紫玫瑰》,从而追求一种美学合法性。这种水墨色调事实上是一种浅褐棕色的单彩色调,用以重现1930年代的时代基调。此外,影片穿插嵌入了另一部电影《礼帽》的一段真实节选内容。无论是黑白色调,抑或是浅褐棕色的单彩色调,色彩的单调便于从一部电影流畅地过渡到另一部电影,从而集中刻画主角人物形象。在电影的叙事框架内嵌套另一部电影让观众见证了一种观影体验的切换,其中的水墨色调背景则淡化了影片间穿插过渡的突兀感。最后,影片的单调色彩同时也被赋予独特的政治寓意和社会内涵,意喻殖民地世界中工人阶级穷困潦倒的生活境遇。
黑白色调除了营造历史时光氛围,便于场景切换之外,还可以强化电影纪实拍摄效果。可以说,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大部分纪实影片拍摄成黑白片。当然这并非是受限于技术发展,而是在那个时代纪录影片中如果加入鲜艳的色彩,容易淡化影片的纪实效果,从而导致纪录片倾向故事片发展的趋势。事实上,即便是早期彩色电影技术尚未成熟之际,人们也经常通过手绘色彩方式制作彩色影片,这从阿尔贝·坎(Albert Khan)基金会的纪录电影中可以得到印证。直到法国《用色彩拍摄战争》这一档纪录电视节目的制作和播放才逐渐改变了观众对于纪实电影观影的习惯,开始接纳彩色纪录片。在面对银幕上血红色渲染的二战战争场面以及解放死亡集中营场景所给人们带来的震撼感和恐惧感则是先前现实主义黑白影像所不能比拟的。
电影的发展总是伴随着色彩和光影的运用,而技术的发展却时常制约着电影的发展。随着电影一步步从黑白影像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在其弥补技术缺陷之后,开始重焕美学的光彩。随着色彩在电影拍摄中的广泛运用,影视色彩成为历史时代的表征。比如库布里克(Kubrick)为其作品《发条橙》配置了未来主义色彩布景,而《2001:星级旅游》中的魔幻色调影像则深受西方20世纪60年代流行艺术和20世纪70年代美学的影响,尤其是绚丽夺目的色调与《黄色潜水艇》影片中的色调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电影致力于呈现其所要拍摄的那个时代,并赋予其特定的历史色彩。其中库布里克的《乱世儿女》则是一部通过色彩和光影来重构18世纪历史的经典影片。
二、冷暖色调与自然光彩——还原历史风貌与强化时代真实感
库布里克于1975年导演的《乱世儿女》凭借对色彩和光影的细致把握和精妙运用,为观众呈现了一帧帧如油画般和谐美丽的电影画面,并通过主人公巴里(Barry)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展示了18世纪欧洲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服饰装扮、建筑风格、情感纠葛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影片中,库布里克主要通过强烈的色彩对比和互补,以及流光溢彩的光影映衬来重构那个时代。
库布里克在影片开头就展现了三种鲜明色彩的强烈对比,从而构成了这部电影的关键元素。这三种颜色分别为爱尔兰便服的绿色、英格兰制服的红色以及少女礼服的白色。来自爱尔兰的男主角巴里深爱着他的表妹,而这位白衣飘飘的美丽迷人少女却倾心于身着红色英格兰制服前来募兵的年轻军官。在此,红色与绿色的鲜明反差凸显了色彩本身的强烈对比,正如瑞士表现主义画家和理论家约翰·伊顿(Itten)在其著作《色彩艺术》中所描述的,是“奔腾不息生命的表达,光芒万丈力量的喷薄”。伊顿认为“橙红色和蓝绿色是最强烈的冷暖对比色”。这种强烈的冷暖色彩对比首先出现在影片开头的大片白昼外景长镜头中,之后表现在两军对垒时英格兰和普鲁士军队制服颜色对比中。然而随着剧情的推进,影片开始不断融入灰色、棕色或者黑色等色彩,以便缓和绿色和红色这组鲜明强烈的冷暖色调对比。这种配色基调一直延续到影片第二部分。而自婚礼仪式那一幕始,棕色和黑色元素的大量介入,红色和绿色要素则退居其次,这也促使影片整体基调开始慢慢变得暗淡。影片最后一幕是主人公巴里和他的养子决斗的场景。这位伯爵夫人和前夫所生的年轻勋贵身穿红色英军官方制服,与穿着绿色爱尔兰便服的巴里展开了生死对决。由此可见,红、绿色两种颜色形成强烈的冷暖色调对比,贯穿这部影片始终,并伴随主人公命运的盛衰荣辱。
此外,库布里克还采用黑色和白色的色彩反差来强调影片后半部的悲剧色彩。这种黑白色彩反差在巴里和伯爵夫人的独子布莱恩(Bryan)的葬礼情节中表现尤为突出。装饰着白色羽毛的羊拉四轮敞篷小车载着英年早逝的小男孩的遗体缓缓驶近,圣洁的白色伴随着哀悼的黑色装点着整个葬礼场景。白色的天空衬映黑色的叶子,神父白色的长袍上佩戴黑色的圣带,黑色葬服镶嵌白色边饰,以及伯爵夫人黑色面纱遮盖下惨白的脸庞。暗淡的色调烘托历经丧子之痛的男主角的沉沦,正好与影片前半部明亮色彩刻画下的人生高光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
除去红绿冷暖色调对比和黑白色彩反差,库布里克在室内场景中精心地运用光影,塑造了一种和谐的暖色调。凭借着影片中大量蜡烛的自然光,库布里克营造了更强的时代真实感,这与其先前历史电影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尤其是在赌场那幕场景中,蜡烛营造了一种幽暗—明亮光影效果,照亮了一部分室内阴影空间。于是粉黛白脸、绅士假发以及服饰装扮等都通过烛光一一映衬出来。在蜡烛光辉的照耀下,每一个场景都沐浴在橘红色的暖色调中,从而营造了类似于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Caravage)和法国画家乔治德拉图尔(Georges de la Tour)绘画中的凝重和谐。其中主色调棕色、红色和橘色在烛火摇曳生辉中烘托出祥和美妙的氛围,而那些阴影区域则反衬出一丝丝焦虑感。故此,伊顿的色彩明暗理论正好印证了这一幕:“我们在油画大师伦勃朗那看到了鲜红色仿佛只有通过与更暗淡的色调进行对比时才显得鲜亮和耀眼。”
事实上,绘画中关于色彩和光影运用的理念不仅体现在库布里克《乱世儿女》这部电影中,为其他影片也提供了创作灵感。一些艺术史学家,诸如龚哈德·安德烈·贝赫利(Conrad André Beerli)和米歇尔·巴斯杜赫(Michel Pastoureau)等关于色彩历史演变的论述为我们展现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各种色彩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偏爱程度,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影视作品对于绘画艺术中色彩元素的借鉴和吸收。其中,法国著名导演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从中世纪的细密画中得到灵感,创作了《高卢人帕希伐尔》这部以中世纪为背景的作品。而卢奇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则从意大利19世纪现实主义画派马基亚伊奥利画派(Macchiaioli)的画作中汲取养料,构思出其作品《豹》中舞会的经典一幕。此外,绘画艺术中的色彩元素和光影运用理念同样影响了中国现代电影的创作。比如2018年上映的影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其导演毕赣在接受采访时直言该片的创作灵感之一来自夏加尔(Marc Chagall)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其海外版的海报则来自夏加尔的名画《散步》。而2017年由陈凯歌导演的《妖猫传》更是吸取了浮世绘、蒙克的画以及中国的青绿山水画三种绘画风格元素,为我们呈现了一派盛唐气象和一段旷世情殇。这部影片让我们从中可以一窥绘画艺术中的色彩元素和光影运用如何重现盛唐荣光和谱写情爱悲歌。
三、绘画色彩元素——历史图景重现与鲜明情感表达
陈凯歌于2017年导演的《妖猫传》用一帧帧极具美学艺术的画面为我们呈现了一派繁华绚丽的盛唐气象和一段凄美苦楚的旷世情殇。影片中的色彩、光影、构图等元素以及人物塑造,无不表现出浓厚的盛唐韵味。奢靡的极乐之宴、金碧辉煌的宫殿、栩栩如生的壁画,向我们展示了大唐开元盛世的华丽辉煌。影片用浓郁的色彩描绘了一幅盛唐画卷,从中我们可以管窥电影艺术对于绘画艺术色彩元素和光影运用的借鉴和吸收。正如影片摄影指导曹郁在专访中坦言,以绘画角度而言,《妖猫传》吸取了浮世绘、蒙克的画以及中国的青绿山水画三种绘画风格元素。其中,蒙克的绘画受到了凡·高等后印象派画家的影响,凡·高的绘画又是在日本浮世绘美术中吸取了经验和灵感,而日本绘画的启蒙又是发源于唐代工笔画。由此可见,这些绘画风格元素具有一脉相承性,同时也很契合大唐盛世图景。
《妖猫传》的色彩运用在一开场便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推进,犹如一幅古代卷轴画,在观众面前缓缓展开。空间层面,影片故事以倭国法师空海前来长安为大唐皇帝驱除邪祟开场。镜头随着空海进宫的马车从市井气息浓郁的西市穿过朱雀廊,直入大唐帝国皇宫,影片用色也从城门口相对朴实无华的色彩开始一路越来越亮丽,直到皇宫中灯火交相辉映下的明艳绚丽。时间主线上,影片在前期胡玉楼、西明寺和陈云樵宅邸等段落大量使用写实色彩来描绘大唐盛景。随着叙事的演进,影片剧情高潮处在美术层面转换了另一种色彩元素表达,以蓝绿色为底色,搭配金黄色,用以呈现一段缘起杨贵妃的凄美绝恋。其中,浮世绘、蒙克绘画以及中国青绿山水画等绘画风格元素大量运用在胡玉楼和花萼相辉楼两处经典场景,勾勒出了大唐盛世的繁华景象。
“大唐风流胡玉楼,长安遍地是诗人。”电影大全景中的胡玉楼掩映在葱郁草木之间,云蒸霞蔚,溪水淙淙,宛如一幅古意盎然、明丽润泽、淡雅俊秀的青绿山水画卷(如图1所示)。

图1 《妖猫传》胡玉楼剧照
华灯初上,在琉璃灯火的交辉映照下,胡玉楼中僧姬共舞,汉胡同乐,一派太平祥和、普天同乐的盛世繁华景象。此刻,胡玉楼俨然成为万邦来朝、天下大同的盛唐气象的象征。其中,云海屏风在精湛的电影技术处理下成为一幅灵动的浮世绘(如图2所示),而胡玉楼中众生相则用了大量的红色和绿色来渲染。在橘黄色的灯光笼罩下,胡姬玉莲身着金丝舞衣,踏着歌声开始翩翩起舞。柔光倾洒在她美丽的脸庞上,犹如蒙上了一层圣洁的光芒,而其绚丽迷人的笙歌乐舞之姿则演绎了一场似真似幻的浮生之梦,邀观众一睹瑰丽盛唐(如图3所示)。整场盛筵沐浴在一片暖色调之中,犹如一幅尘封千年的敦煌壁画重焕光彩,惊艳了时光(如图4所示)。

图2 《妖猫传》云海屏风剧照

图3 《妖猫传》胡姬起舞剧照

图4 《妖猫传》胡玉楼盛筵剧照
事实上,这种红绿配色和侧面光照的手法深受蒙克的绘画色彩元素影响。作为挪威国宝级画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的绘画风格侧重于用光线色彩来表达其内心情感的变化。蒙克的画风主要受到西方风景画派和印象主义画派的绘画理论影响,尤其是19世纪英国风景画家约翰·康斯坦布尔(John Constable)的色彩补色原理。康斯坦布尔在长期户外写生实践中获得了丰富的色彩感受,在局部用细小笔触大胆地并置纯度高的颜色,使观者在后退后能看到较鲜明的色块,画面色彩较古典主义时期褐色调子明亮得多,并总结出了色彩的补色原理,即位处色轮两极的颜色在并置时能提高明度和强度。其后印象主义画派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绘画理论,并进而影响了蒙克。在蒙克画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强烈的色彩对比。“走进一间台球厅,一张张夺目的绿色桌面映入眼帘。然后先抬起头,不久你便会惊奇地发觉这里竟四处充满着奇妙的红色了。……如果你想把刚才那种感受,那耀眼的绿色桌面表现出来,那么你就必须使用深红色。如果有谁想要留住那样一个瞬间即逝的感觉,那么就请这样来做吧!”由此可见,蒙克对于补色原理,尤其是对红绿互补色彩的偏爱。比如蒙克著名的画作《嫉妒》就是用红绿色彩强烈对比来强化人物之间的矛盾。此外,蒙克的绘画中常常用暖色调色彩来表现光源侧照所呈现的画面阴影面和受光面,从而刻画出剪影般的人物形象,并通过映照在人物脸部的光芒来塑造一种美好圣洁的印象。蒙克1883年的画作《坐在摇椅上的卡伦姑姑》便是画家通过色彩表现光线方式来塑造其卡伦姑姑慈祥温柔的模样(如图5所示)。卡伦姑姑在蒙克母亲离世之后一直照顾孩子们的生活,并支持蒙克发展其绘画事业,而蒙克在画作中通过色彩所营造的光线赋予人物肖像一种神圣的光芒,以表达其内心对于卡伦姑姑的感念之情。

图5 《坐在摇椅上的卡伦姑姑》爱德华·蒙克
除了胡玉楼一幕,影片在花萼相辉楼场景中也同样使用了红绿配色和侧面光照的手法。花萼相辉楼中,仙山悬塑,酒池琼浆,寿山福海,宛若仙境,绿色基调中点缀着杨玉环一袭花鸟锦绣的红色长裙,在火树银花一派金碧辉煌的映照下,极乐之宴俨然开元盛世极致辉煌的象征,同时也是大唐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如图6所示)。极乐之宴的高潮处,唐玄宗散发击鼓,亲自为包藏祸心的安禄山伴奏,而安禄山则纵情舞蹈,刀刃相向,将帝国风雨欲来、大限将至的感觉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鼓息舞止之时,镜头使用烛光、LED光和滴度光等多重光彩映照下,贵妇回眸一笑百媚生(如图7所示)。流光溢彩在她美艳动人的容颜上蒙上了一层圣洁的光芒,而此刻她的美丽光芒似乎象征着大唐盛世的最后一抹辉煌。正如剧中阿倍仲麻吕独白所言,“强盛时,她是帝国的象征。危难时,大唐将不再需要她”。极乐之宴的最后一刻,面对贵妃的美丽,唐玄宗是肆无忌惮的占有,安禄山表现出赤裸裸的觊觎,而阿倍仲麻吕则是痴痴的倾慕,这何尝不是他们对大唐盛世的态度?之后贵妃的香消玉殒同时也寓意着盛唐荣光的陨落。

图6 《妖猫传》极乐之宴剧照

图7 《妖猫传》杨贵妃剧照
极乐之宴场景的光影运用与蒙克另一画作《春天》有异曲同工之妙。蒙克于1889年创作的《春天》画作中,一个女孩儿侧着脸躺在躺椅上,一旁的老妇则侧对着观者陪在女孩儿边上,微风轻抚窗帘,阳光透过薄纱帘子洒进房间,照在女孩儿略带苍白的青春脸庞上。画家通过明亮化的色彩运用和具象化的物体描绘来营造一种温馨柔美的绘画风格。然而温馨美好的画面中却暗藏死亡的气息。画作中光源从侧面照入,映显了女孩儿青春美丽却苍白无力的脸庞,此刻美好与即将逝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唏嘘不已(如图8所示)。

图8 蒙克《春天》
这一画面正如《妖猫传》中极乐之宴杨贵妃的美丽有多令人动容,日后香消玉殒就有多令人心碎;大唐帝国繁华昌盛有多令人艳羡,日后帝国倾颓陨落就有多令人慨叹。此外,《妖猫传》还涉及蒙克绘画的其他色彩元素,主要有黑色和红色的使用。蒙克的绘画作品风格属于表现主义,其主观色彩运用具有强烈的画面效果和鲜明的情感表达。“我要描写的是那种触动我心灵、眼睛的线条和色彩。我不是画我所见到的东西,而是画我所经历的东西。”蒙克的作品表达了画家自身的情感和体验,而色彩在其绘画中已经成为一种传递情感和思想的视觉符号。综观蒙克一生,满布坎坷和苦痛。早年丧母丧姐,青年丧父,情路荆棘密布。此外,蒙克还深受虔诚基督徒的父亲的影响,死亡恐惧和宗教迷信一直深埋心底。与这些生活经历、情感历程和文化熏陶伴生而来的恐惧、压抑、孤独、绝望等便常体现在他的绘画作品中,而亲情、死亡和爱欲则成为蒙克作品的主题。基于此,西方艺术文化语境中代表死亡、邪恶、恐惧和悲痛等感情色彩的黑色则成为蒙克绘画中的主要色彩基调。这在画家的《病孩》《母亲之死》和《圣卢克之夜》等作品中多有体现。《妖猫传》中对黑色元素多有借鉴,其中贯穿剧情主线发展的黑色妖猫便是复仇、孤独、绝望和死亡的化身。而影片主角白乐天在获知《长恨歌》的故事是假的时,苦心孤诣书写《长恨歌》的信念在瞬间崩塌,此刻镜头闪回切换到白乐天身穿黑色薄纱长袍痴痴地伫立在一片雪地中(如图9所示)。这一场景中黑色在白茫茫雪地强烈鲜明的映衬下,凸显了白乐天书写唐玄宗、杨玉环爱情和大唐盛世风貌却拙于笔力的苦闷,同时也刻画了其所讴歌的旷世绝恋信念崩塌的落寞和迷茫。此外,在多次表现樱花树下杨贵妃幻象时,影片使用了红色来表达白龙对贵妃的爱慕和痴恋,正如蒙克在其画作《嫉妒》中用红色来渲染爱欲。

图9 《妖猫传》剧照 白乐天伫立雪地
由此可见,电影作为第七艺术,可从绘画这门艺术中广泛汲取营养和灵感,借鉴绘画艺术色彩元素和光影运用,如在《妖猫传》影片中借助绘画艺术重现盛唐繁华和谱写情爱悲歌,让绘画艺术的生命力在影视艺术中重焕光彩。
四、特殊色彩——社会等级的表征与时代偏见的映射
无论是现实主义风格、纪实拍摄效果、鲜明的色彩对比、绘画艺术色彩元素抑或是流光溢彩的光影映衬,电影中的历史色彩总是试图以一种和谐的方式来重构历史时代。然而在这些历史色彩中有时掺杂部分不和谐元素,这些不相搭配的色彩对影片场景的和谐氛围构成诸多颠覆。其中索菲亚·科波拉导演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就是一部巧妙运用历史特殊色彩的经典电影。
索菲亚·科波拉从18世纪的粉彩画和人物肖像画中汲取了灵感,在《玛丽·安托瓦内特》中完美地融合了柔和的色调和美妙的光影。这部影片叙述了法兰西传奇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宿命般的一生,同时也给观众展现了法国18世纪的王室风情和时代风貌。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中,一群绮罗珠履的贵妇和宫廷侍女簇拥着优雅的玛丽王后,而她们色彩斑斓的锦衣华服则衬托出王后塞夫勒蓝裙的雅致。奶白色和象牙白色的主场渲染淡化了场景中色调切换时的突兀感以及色彩绚丽的炫目感。随着玛丽王后在凡尔赛宫中穿梭,快速切换的镜头让观众目不暇接,王后塞夫勒裙的一抹蓝色在不同室内场景中翩翩流转,并将蓝色色调延续承接到宫内布景以及其他人和物中:蓝色瓷器、蓝色箱子、蓝色帷幔、蓝色软座安乐圈椅和奈提埃蓝色首饰盒等。电影巧妙地运用蒙太奇手法,在一帧帧快速切换的室内场景中凸显了蓝色主色调的色彩延续性,生动活泼地展现了18世纪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的日常。镜头画面快速的切换规避了室内场景描述的枯燥乏味,而色彩延续性则使得蓝色主色调不断重现。影片场景中主色调重现了蓝色在18世纪法国社会中的尊崇地位。这种因前工业时代颜料的稀缺性赋予蓝色以其他色彩所不能企及的地位。作为法兰西王室专属色彩,蓝色不但广泛运用于凡尔赛王宫的各种装饰中,玛丽王后的服饰中,甚至还出现在象征法兰西波旁王朝王族族徽的百合花中。故此,影片中蓝色作为法兰西王室专属色彩,彰显了色彩地位的不平等性。这种色彩地位的不平等性恰恰映射出18世纪法国的社会等级秩序。这种因颜料稀缺性而导致的色彩地位不平等性直到颜料工业化生产之后才逐渐消失。事实上,这种颜料稀缺性并不仅限于原材料的稀缺,有时候颜料制作成本的高昂也会导致稀缺性。比如,作为古罗马时代最高贵的色彩,紫色成为古罗马上流社会财富和权势的象征。一时间,众人对紫色视若珍宝,趋之若鹜,无论是国王、领主、祭司,甚或神像皆身披紫袍。任何僭越都被视为挑战王权和亵渎神明,甚至要遭受法律的严惩。苏埃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中就记载了古罗马卡拉古拉皇帝时代一位出身平民的年轻男子因在罗马全身穿戴紫色而遭到逮捕后被处决。然而,古罗马时代紫色颜料主要由地中海海贝和骨螺的汁液萃取而成,而这种原材料在地中海沿岸广泛分布,并不存在稀缺性。但是,紫色颜料提炼所经历的一系列复杂工序(浸泡、蒸煮、浓缩、过滤)和极高的转化耗损比(1/15的转化比率)导致其制作成本十分昂贵。高昂的制作成本打破了色彩地位的平等性,是紫色成为古罗马时代上流社会专属色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影片中金象牙色的壁板、玫瑰色的鲜花和油画以及亮白色的钻石和折扇等构成的淡彩色系布景,搭配舒缓柔和的背景音乐,营造了一种祥和的氛围。总之,索菲亚·科波拉善于用和谐的色系构建电影镜头,即便是影片结尾处色调转为暗淡,也是为了预示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位法兰西王后的悲惨命运。
然而,影片反派角色杜巴利伯爵夫人的出场则颠覆了整部影片的和谐基调。作为玛丽王后的情敌,她的一切似乎都与庸俗联系起来:浓妆艳抹,少条失教。她那绚丽的长裙满是斑驳陆离的色彩搭配,蓝色、天青色、紫色以及朱红色。甚至连她与法国国王通奸的房间也是由大片绯红色色调渲染。这些不和谐元素与凡尔赛宫的精致典雅色调格格不入。事实上,欧洲自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过度绚丽斑斓的色彩常被视为庸俗的象征。新教徒为了反对罗马教会主张的挥霍浪费和炫耀浮夸,开始推动色彩简化运动,尤其是在服饰领域。故而影片中传承了对于绚丽色彩的历史惯例和时代偏见。诚如歌德(Goethe)在其《色彩理论》一书中所言,“……我们应强调那些野蛮民族,那些文明未开化的族群对于五彩斑斓的色彩有种独特的偏爱,而动物看到那些颜色则会显得特别狂躁;反之,受过文明教化的人则通常排斥那些艳丽夺目的服装,以及光怪陆离的环境,并尽可能地规避那些斑驳色彩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我们同样也可以发现化装舞会等场景用更鲜艳的色彩来渲染,那是“用色彩斑斓来呈现面具遮掩下的放浪形骸”。
五、色彩“刺点”——“影像伤痕”和历史反思
事实上,很多历史题材电影都有其一套色彩体系。然而这类电影有时会引入一些不和谐的色彩元素,这些特殊色彩不仅出现在彩色电影中,甚至也出现在黑白片中。正如《玛丽·安托瓦内特》中杜巴利伯爵夫人的出场打破了影片和谐色调,构成了影片的违和颠覆,暗示着玛丽王后婚姻的危机和地位的脆弱。而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辛德勒的名单》则以一抹醒目的红色短暂地嵌入这部黑白电影中。这种强烈的色彩突兀构成了菲利普·杜波瓦(Philippe Dubois)《第七艺术中的影像伤痕》一文中的“影像伤痕”,以震撼人心的方式触动观众的心灵。
这部获得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的著名影片《辛德勒的名单》,是由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根据奥斯卡·辛德勒在二战中救赎犹太人的故事而改编的。作为一位德国商人,同时也是纳粹党成员,奥斯卡·辛德勒散尽家财向纳粹官员贿赂,通过赎买和雇佣的方式,让大批犹太人免于被送进死亡集中营,从而拯救了他们的生命。除了影片开头和结尾,斯皮尔伯格以黑色胶片拍摄这段灭绝人性的至暗时刻。全片令人压抑窒息的黑白色调中,一个穿着红色外套的小女孩儿赫然出现在银幕中。导演特意还原她外衣的一袭红色亮点在黑白色调背景中分外醒目,并深深地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镜头中红色亮点随着小女孩儿的身影跳动着,观众的视线也随之转移。小女孩儿越过街巷,跑上楼梯,藏于床底,双手捂住耳朵,天真地以为这样可以躲避战争的杀戮。当层层堆积的运尸车中那件红色外套赫然在目时,彻底击碎了观众心目中最后一丝希望,而黑白镜头中凸显的红色色调瞬间表现出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刺痛了观众的心。事实上,《辛德勒的名单》中这一抹鲜活的红色与其说是一种“生命的色彩”,毋宁说是一种真实的“影像伤痕”。在黑白影像中划开的这一道鲜红伤痕一直持续到运尸车出现,全程让观众焦心劳思、翻肠搅肚,直到小女孩儿的尸体赫然出现在尸堆中,观众的心瞬间瓦解崩塌。《辛德勒的名单》中“影像伤痕”的运用并非个例。无独有偶,奥利佛·比努埃萨(Olivier Vinuesa)导演的《荣耀战场》一片中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
《荣耀战场》拍摄于2005年,是一部由英法两国合作制作的中长片电影。影片故事发生在索姆河战役期间,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投入战争的英国军队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人员损失,并毫无掩饰地揭露了战争的血腥和残酷。奥利佛·比努埃萨在影片中选择一种独特的色彩淡化处理手法,将肮脏不堪的战场环境和枯燥乏味的战地生活拍摄成近乎黑白片。然而在这暗淡无光的色调中,虞美人花盛开其间,娇艳欲滴的血红色赫然在目。这种虞美人花的色彩同时具有隐喻和提喻的象征性寓意。这种鲜血般的色彩使人联想到战争所造成的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此外,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风俗中,虞美人花寓意为“休战纪念星期日”(Remembrance Sunday),即每年11月11日前的星期日,人们佩戴红色虞美人花,庆祝停战纪念日,并献上花束以缅怀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死难者。影片灰暗色调中虞美人花的鲜红色显得尤为醒目。这种突兀的不和谐色调对观众而言犹如一种警醒。虞美人花在此并非爱国主义的表征,更多是对世界大战残酷和血腥的隐喻。可以说,《荣耀战场》中虞美人花的鲜红色调也是一种“影像伤痕”。
由此可见,无论斑驳陆离的绚丽色彩还是黑白色调中突兀的“影像伤痕”,这些电影历史色彩中的不和谐元素被导演精心安排,以悄无声息的方式潜入影像中,却引人注目。这些色彩元素确切意义上充当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刺点”(Punctum)的角色。“刺点”与“认知点”(Studium)是罗兰·巴特在《明室论摄影》中所创的两个重要概念。简单而言,“刺点”强调的是一张照片中被人忽略,却能在一个主体身上唤醒特殊的审美感知的元素;“认知点”指照片中提供基本的文化背景和知识以便让人可以认出摄影图像中的内容的元素。罗兰·巴特强调了“刺点”对于观众视觉观感的重要意义,认为“次要元素‘刺点’喷薄而出,掩盖‘认知点’的光芒,一举吸引注意力”。这种不经意间的细节元素,诚如《辛德勒的名单》中那位红衣女孩,抑或是《荣耀战争》中的血红虞美人花,顷刻间触动了观众的情绪。而黑白背景色调中的红色则成为色彩“刺点”,让这些“影像伤痕”深深地烙印在观众的心里,令人动容心碎。
结 语
历史题材电影中的色彩表现相当复杂且丰富。出于重构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的考量,人们往往选择各种不同的特定色彩范式。工艺技术、颜料生产、宗教教义以及学术理论观点等要素决定了不同时代色彩独特的意义,而恰恰是这种色彩偏好有助于我们快速定位电影所拍摄的时代,从而能够反映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地区特有的历史叙事和时代表征,管窥当时的社会风貌。此外,电影从绘画艺术中广泛汲取营养和灵感,借鉴了绘画色彩元素和光影运用,尤其是保存了表现主义画派一部分色彩的情感价值和象征意义,从而让绘画艺术生命力在电影艺术中重焕光彩。某些历史题材类电影试图以悲观感伤的基调来描绘一个时代的终结,一段历史的落幕。但是,在影片总体的色彩基调中也可能会催生出一些不和谐的色彩元素。它们貌似在不经意的细节上吸引观众的注意力,犹如影像中的“刺点”唤醒观众视觉观感反应。当然,这些色彩元素的出现从来都不是毫无来由的。通过色彩激发,让观众心潮起伏,情意难平,特殊色彩元素有助于引领观众深入研究影片,探讨影片中所表达的潜在纷争和内在冲突,并在影片所讲述的故事之外,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