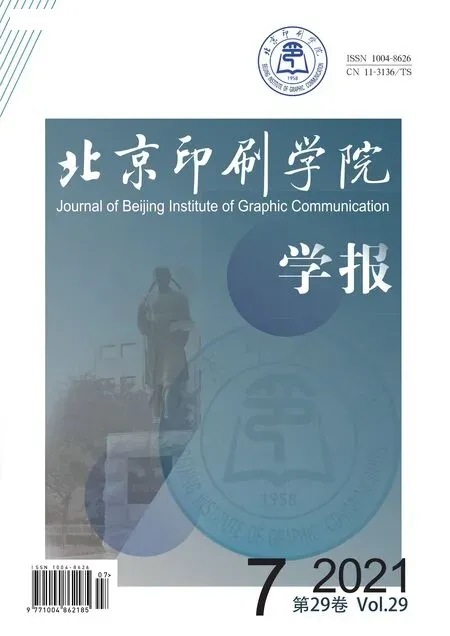美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研究(1921-1936年)
左 晶
(北京印刷学院,北京 102600)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6年斯诺进入延安采访,能够和中国共产党直接接触的外国记者并不多,这些记者大多数来自美国,比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文森特·希恩,雷娜·普罗梅夫妇,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可以看出国际上对早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中国的认识非常有限,他们更多地把报道的目光放到了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以及当时国民党左翼人士身上。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和中国共产党缺乏直接的接触和受当时美国国内反共思潮的影响,他们的报道大都接受了国民党官方舆论将共产党“土匪化”、“妖魔化”的论调,仅有少数记者对此提出质疑。
一、被共产国际和国民党左翼遮蔽下的革命力量(1921—1927年)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古老的中国传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过多外国媒体的关注。只有苏俄《真理报》记者有过少量的报道。
(一)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初露端倪,英美记者敏锐捕捉到布尔什维克的力量
英美记者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报道最早可以追溯到发生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5年2月,上海日本棉纱厂工人为抗议资方无理开除工人而实行罢工,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开枪打死罢工领袖顾正红和打伤十余名工人,继而引发了省港大罢工等全国性的抵制列强在华势力的浪潮。外国媒体对这次运动的报道中,相对于日本媒体,英美记者敏锐地捕捉到布尔什维克在其中的作用。英国在华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在1925年2月18日刊登社论《布尔什维克主义在纱厂》,指出:“罢工的整个过程证明,罢工是煽动分子和狂热分子制造出来的。”[1]英国在上海办的另一家报纸《上海泰晤士报》也进一步指明:“很明显,工人是煽动分子煽动起来的,这些煽动分子一部分据了解是从广州来的具有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中国人,一部分是那个布尔什维克主义温床——所谓上海大学——的学生……”[2}同时,美国的《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在7月25日的一篇报道中承认:“从骚乱开始时起,上海外国报纸曾经指出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在幕后操纵这些骚乱。虽然举不出什么事例来确实证明这一点,但布尔什维克党的势力,在中国,尤其在学生中间,确实有其影响。”[3]
但是,总体来说,“在1927年以前,外国人眼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4]在他们看来,都是受苏俄共产主义影响、试图在古老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力量。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致力于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苏联成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最主要的支持者。在苏俄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重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并于1926年开始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也就是大革命。在外国人看来,中国大革命的布尔什维克色彩是无可置疑的。“国民党处在共产主义强有力的影响之下。”[5]出于意识形态、经济利益等各方面原因,外国媒体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争充满担忧与敌视。驻京的英国名记者辛博森(Putnam Weale)从汉口旅行归来后,写了一组报道,总标题为《扬子江上的赤色波浪》。将北伐战争斥为“受莫斯科控制与指挥”“扬子江上的赤色波浪”。
外国媒体对国民革命军北伐后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担忧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后得以解除。此后,西方记者才将对国民党的报道从共产主义运动中分离。
(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以及国民党左翼领导人成为美国记者报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点
1927年前,很少有西方记者直接接触过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关于共产党人的报道,大都来自于二手资料,而且多半充满了敌意。但是,从1927年4月“四·一二政变”到7月共产党被清除出汪精卫的短命政权期间,仍然有几位美国记者直接观察到中国的共产党人。这其中主要有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Anna Louise Strong),文森特·希恩(Vincent Sheean)和雷娜·普罗梅夫妇(Rayna Prohme)。
斯特朗1925年首次访问中国,之前作为自由作家和流动记者,在美国和莫斯科度过了大部分岁月。由于结识了宋庆龄和苏联驻中国的总顾问鲍罗廷,斯特朗成为省港大罢工委员会允许采访的唯一外国记者。斯特朗在报道中称此次罢工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报道中向外界转达了罢工领导人苏兆征寻求西方工会支持的呼吁。1927年春,斯特朗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夕再次来到中国。她抵达上海不久,就千方百计地去了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汉口。在汉口期间,她采访到了鲍罗廷、陈独秀、李立三等共产党领导人,对劳工领袖以及普通的中国劳动者做了大量采访,并充满自信地预言中国的未来终将掌握在觉醒了的工农大众手中。1928年,斯特朗将在此期间的采访整理出版为《中国大众》(China's Millions),在纽约印刷出版。但是,此书只是以旅行见闻的方式概述了作者的经历,展现了革命紧急关头作者的所见所闻,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充分的展现。
文森特·希恩(Vincent Sheean)1927年受“北美新闻联盟”的派遣来到中国。他于4月中旬到达上海时,刚好是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的几天之后。他当时比较同情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及其中国同志,和鲍罗廷以及国民党左派人物有较多接触,希恩对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和剥削十分震惊。他后来将这段经历写成《个人的历史》,一度成为美国的畅销书。但是在这部著作中,其更多的笔墨仍然放在了以鲍罗廷为首的苏联顾问团、同行的美国记者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身上,而和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少有实际的接触。
雷娜·普罗梅(Rayna Prohme)是美国女记者,1925年夏来到中国,与丈夫威廉·普罗梅(William Prohme)一起投入到中国的大革命中,跟随中国大革命的脚步从北京到广州再到武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雷娜陪伴宋庆龄从上海去莫斯科。1927年11月在莫斯科病逝。
1925年,雷娜夫妇在北京期间,认识了国民党著名左派人物陈友仁,他主持英文日报《人民论坛报》(People's Tribune)。后陈友仁去广州,普罗梅夫妇代办《人民论坛版》在北京的编务工作。“促使普罗梅夫妇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他们是在北京认识的。李大钊因被军阀政府通缉,避居苏联大使馆。雷娜是美国人,所以行动比较自由。她每天去苏联大使馆,成为李大钊同北京的地下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之间的联络员。”[6]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杀后,普罗梅夫妇辗转来到武汉,当时北京的《人民论坛报》已经关闭,雷娜着手在汉口恢复《人民论坛报》,并于3月12日也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忌日这一天在汉口复刊。[7]这份报纸在当时向全世界传递武汉革命中心的声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及1927年7月汪精卫公开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后,宋庆龄发表著名的《七·一四声明——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这篇战斗檄文就是在雷娜帮助下,于7日18日在武汉英文《人民论坛报》及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首先发表。中文稿则印成传单,遍贴武汉大街小巷,并刊登在7月24日的北京《晨报》。宋庆龄声明的及时发表和广为传播,给背叛革命的右派以沉重的打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雷娜负责刊发宋庆龄声明的这期《人民论坛报》,成了最后一期,旋即被没收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写道:“他们的任务是代表国民党用英文进行宣传。他们两人比任何人更负责把新闻发往美国。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就根据这些新闻形成一种发对力量,制止美国政府武装干涉中国。……他们两人虽然都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一直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甚至武汉革命政权崩溃后,他们仍然如此。甚至左派停止活动后,他们还继续经营一家左派报纸。”[8]
从斯特朗、希恩及普罗梅夫妇的新闻活动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外国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更多地集中在来自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和劳工大众身上。
这一点并不难以理解。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新生力量,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听命于来自苏联的共产国际专家的领导。而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处于从属地位,1923年1月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是国民党”。[9]根据国共“党内合作”的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也就是所谓的跨党党员。但是国民党则明确规定国民党党员不能加入共产党。因而在外国记者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报道中,把关注点放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和国民党左翼领导人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当时中国共产党员人数较少,到1925年10月,全国仅有3000余名党员。虽然随着大革命的发展,党员数量有所增加,到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时,党员发展到57967人[10]。但大多数都是新加入的共产党员,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劳苦大众,外国记者由于活动空间有限,很难接触到这些共产党人。
二、被妖魔化、无法触及到的“红色匪军”(1928-1936年)
(一)在国民党严厉封锁下,外国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严重不足而且缺乏真实性
美国研究中国共产党史的学者认为,1927年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是面向城市、受莫斯科指挥、由密谋分子组成的地下小组,其指挥机关秘密地设在上海;二是不那么正统的、面向农民的热情分子,他们在中国东南部山区建立了一些游击根据地。前者执行共产国际城市起义路线,在蒋介石军队的优势力量下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惨重失败。到了1932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一支力量已经被剿杀殆尽,幸存者加入了干得比较成功的另外一部分。”[11]从1927年到1932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农村建立了十几个革命根据地,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等等。这些地方多在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各省交界处的农村地区,共产党在这里发动农民进行武装起义,建立人民军队,进而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渐发展壮大。
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红色政权实行严厉封锁和剿灭政策,在十年间,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开始长征,最终三大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胜利完成跨越十几个省,总行程达数万里的长征。但是对于这些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大事件,外国媒体在当时却知之甚少,几乎没有任何报道。实际上,在安娜·斯特朗随鲍罗廷回到苏联后,外国人(不仅仅是外国记者)同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也就断绝了。在1928—1936年间西方有关中国共产主义发展的报道,不同程度受到国民党官方舆论的影响,即认为处于穷乡僻壤的共产党残余已溃散为流窜的匪帮。这一点从当时对亚洲事务报道的权威杂志《太平洋事务》关于中国的报道中就可以见一斑。
《太平洋事务》是太平洋关系学会出版的一个刊物,在当时是一本研究太平洋问题的很有影响的杂志。1928年5月创刊,总部在美国。该刊物主要是太平洋关系协会的一份新闻简报,同时为读者提供一个就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交换意见的论坛,每月刊登一篇学术性文章。这个刊物有一个固定的新闻概要栏目,名称为“太平洋来讯”,从创刊开始主要由该杂志的编辑伊丽莎白·格林主笔,其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报道极为有限。“太平洋来讯”在1930年7月第一次提到中国共产党,简要提到武汉附近的“红色暴动和土匪活动”。在8月份再次提到了中国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土匪活动,在9月又出现了长沙城遭到“所谓共产党匪帮”的普遍破坏和洗劫的新闻。显然这样报道的消息源来自国民党官方提供的报道,而缺乏和共产党人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接触。
1933年夏,欧文·拉铁摩尔接替格林成为《太平洋事务》的编辑。拉铁摩尔和格林不同,拉铁摩尔有过长期在华的生活经历,对中国有深刻的观察。1921年曾担任《京津泰晤士报》英文版编辑,一年后辞职,开始在中国内蒙、新疆、东北三省等地游历和考察,并完成在中国边疆史研究上很有影响的两部著作《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之路》(1929)和《满洲——冲突的发源地》(1931)。1933年担任《太平洋事务》编辑后,面对动荡的亚洲形势,拉铁摩尔主张“将该杂志办成各种对立意见公开讨论”的场所。虽然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在数量上没有明显增加,但在文章的篇幅和质量上却提高很多,为不同观点间的交叉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这期间,《太平洋事务》发表过伊罗生分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文,尼姆·韦尔斯有关共产党人的介绍以及研究共产党的文献目录,还大量报道了一直被封锁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刊登了很多与此相关的分析论文。其中一篇由拉铁摩尔撰写的分析性文章指出,共产党的真正力量不在于“人数的多寡,而在于他们领导者的质量和他们在自己占领地区赢得支持的能力”。[12]拉铁摩尔这位学者型记者的分析在当时有关中共报道“残匪论”甚嚣尘上的西方新闻界,无疑非常难能可贵。但是显然,拉铁摩尔和中国共产党缺乏直接的接触,他的文章只是突破了单纯从国民党官方获取信息的限制,同时为各种声音的发出提供了一个平台。
(二)史沫特莱转述的关于中国红军的“故事”
当时和共产党有直接接触的外国记者,只有来自美国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928年,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达上海,从一开始她把报道的目光放到了中国劳苦大众身上,先后完成了《沈阳的五位妇女》《献身者》《徐美玲》等文章。史沫特莱到上海后开始关注工农红军的消息。她让秘书兼翻译冯达把报纸上关于红军的消息剪下,译成英文,建立档案。“她对工农红军的了解是如此热衷,以至于她不仅收集关于红军的报道,还粗略统计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消灭红军的人数,以估计报道的真实性。”她说:“有关中国工农红军的卡片就有几盒,不过多一半是官方的报道。头半年总结官方统计数字,我发现国民党官方发表歼灭红军的数字达五十万,但是官方报道始终说‘共匪残部’在追歼中。”[13]
为了进一步了解彼时国共两党的真实情况,史沫特莱同各种朋友保持友好关系,以获取更多的消息来源,并通过各种途径和当时的左翼人士及中国共产党人相识。她说:“我特别喜欢同进步的民主人士和革命的共产党人来往。” 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严重迫害的1932年到1935年期间,史沫特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外国人在当时享有治外法权——经常掩护、救助中共在隐蔽战线的革命者。甚至用自己或朋友的住所藏匿革命者,并护送他们离开上海。赣东北红十军军长周建屏、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等都曾受到史沫特莱的直接帮助。
史沫特莱利用与革命者接触的机会,了解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红军斗争的情况,为撰写关于红军的著作积累了素材。比如从周建屏的口述中了解到红军反“围剿”斗争的情况,1933年,史沫特莱第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国人民的命运》(Chinese Destinies),由纽约前锋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共有三十篇特写文字,除了反映中国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描写中国妇女的不幸命运,揭露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外,也有一些文章歌颂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的诞生。1934年,史沫特莱关于中国的第二本著作《中国红军在前进》(China's Red Army Marches),由纽约前锋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通过22篇报导,向全世界读者介绍了从1927年到三十年代初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和成长的历史(如《在红军中的日子》《井冈山》《红色的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等)。
但是史沫特莱的报道并没有像斯诺后来的报道一样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史沫特莱的作品依然是故事,是通过他人之口转述的关于中国红军的“故事”。正如史沫特莱自己所言,“这本书是由许多根据真实的事件所写的小说编成的”。[14]另外,由于史沫特莱和共产国际以及中国的左翼联系过于密切,她的报道容易让人产生故意“宣传”之嫌疑,而缺乏客观公正性。再者,史沫特莱的报道缺乏对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等方面的报道,借由史沫特莱的文章,外界依然无法对中国共产党做出清晰的判断。但是史沫特莱的报道毕竟提供了一种可以替代国民党宣传的东西。“奋发向上、富于理想的英勇善战的红军战士是她笔下的英雄,腐败无能、烧杀淫掠的蒋介石军队才是土匪”。[15]
其他美国记者,都不像史沫特莱这样和共产党有过直接的接触。而且受到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影响,对共产主义有强烈的排斥和反感。[16]如著名的《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哈雷特·阿班,在报道中不仅使用了大量的负面词汇对中国共产党加以描述,而且还详细列数了共产党人的屠杀、抢劫等不良行为,以便丑化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藉此说明共产主义对中国造成的巨大危害。但是,阿班对于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原因却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在阿班看来,共产主义运动深植于中国政治的高度腐败和人民受到的极端压迫,中国的共产主义是“由于可怕的恶政和可耻的剥削已经将大多数中国人折磨到了与 1917 年的俄国部队一样绝望的程度”[17],因此才成为底层人民进行社会反抗的必然选择。
此外由鲍威尔负责的《密勒氏评论报》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也受到国民党官方舆论的影响,政治倾向明显。以1932年为例,发表于6月18日的《反共剿匪行动》;6月25日的《针对共产党的军事反攻已经开始》;7月9日的《发行五百万债券为反共战争筹措资金》;8月6日的《使用经济压力反对共产党》等文章,虽然在语言表达上不像国民党的党报那样极端,但其政治倾向也非常明显。此后的几年也基本保持这样的政治态度,如1934年10月6日的《黄郛将军计划在北方进行重要改革剿共取得进展》,1935年9月14日的《蒋介石参加反共会议》等。[18]但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步伐的加快,国际形势也在发生转变,《密勒氏评论报》对中共的看法明显在变化。1936年6月至10月,鲍威尔派斯诺前往陕北采访。1936年11月14日、21日,《密勒氏评论报》率先连载斯诺的专访《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引发全世界读者极大的关注。
由此可见,1936年斯诺进入红区采访之前,由于国际上反共思潮的影响和国民党的封锁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在外国媒体笔下,其主流是被土匪化、妖魔化,仅有少数和中国共产党有过直接接触的记者做过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真实的报道,但影响并不大。但是正是因为国民党过于严酷的信息封锁和极端的“匪化”宣传,逐渐引起国际媒体对这种论调的怀疑和对坚持抵抗国民党围剿的中国红色政权的好奇,斯诺随后进入红区的报道才能够在国际社会引发如此大的震动,带动一批外国记者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红区采访,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蓬勃向上、情系中国劳苦大众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