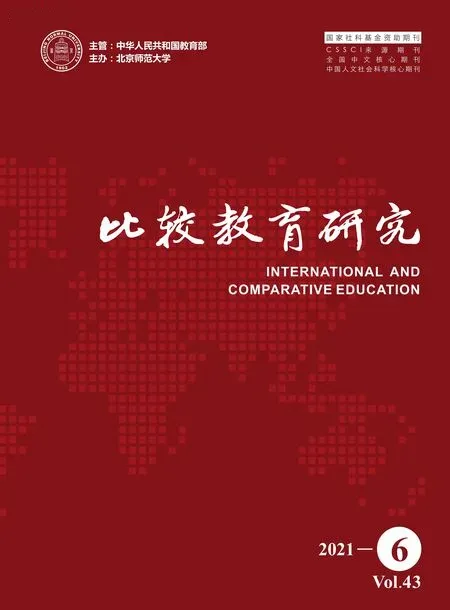全球教育治理的向度与限度
丁瑞常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上,十多年前就有学者开始探讨全球教育治理。但在我国,即便是在五六年前,学界对于这个“舶来品”概念依旧有争议。国际关系学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就较多地开始谈论全球治理问题,然而基本不涉及教育领域。直至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拓展与有关国际组织的教育合作空间,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1],才正式将全球教育治理纳入我国的政策话语。此后,全球教育治理不仅在我国学界获得了“身份合法性”,而且很快就成为热门话题。2019年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重申我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关注全球教育治理的兴趣。
然而,在全球教育治理由边缘话语走向中心的同时,笔者发现这个概念开始出现明显的滥用、错用现象,近乎把凡是涉及国际化元素的教育治理问题,甚至是有关其他国家教育治理的探讨都纳入了全球教育治理范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教育治理无论是作为一个学术术语,还是一个政策话语,外延的过度泛化都将导致它丧失作为一个专有概念存在的价值,也不利于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本文无意对全球教育治理这样一个新兴并且正处于急速发展中的事物下一个规定性的定义,而是试图从其向度和限度探讨一种可能的概念理解思路。笔者认为,我们首先应区分“全球教育治理”这一术语的两种相关却又有所区别的向度。一种是将全球教育治理理解为一种已然存在或正在成为现实的实践,将其视作一种由来已久的,但在全球化时代得到全面发展的特殊现象[2],是国际社会各利益相关方通过协商、合作及博弈等多种方式参与全球教育事务的管理,以维持或确立合理国际秩序的活动。[3]另一种则更多的是将全球教育治理理解为一种理想或理念,视之为一种解释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教育实践,指导解决全球教育问题的重要理论。[4]
二、作为现实的全球教育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和国际教育发展的动态变化,极大地转变了教育治理的格局。这种转变的特点是在主权国家之外出现了多种决策来源,影响和冲击着教育系统的治理方式。全球教育治理被视作一种实然现象时,这意味着教育已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领域。这至少与以下三方面事件和趋势有关。
(一)教育领域出现了需要跨境合作治理的难题
教育对于塑造公民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所以主权国家会高度警惕其教育事业受到外部干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当前依旧有大量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没有参加教育贸易的谈判或对教育服务贸易做出承诺。但是,势不可挡的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使得教育日益跨越主权国家的地理边界,教育领域开始出现超越主权国家的治理范围,需要国际合作乃至超国家力量介入方能得以善治的治理难题,某种意义上的全球教育治理便应运而生了。
首先,跨境教育的发展给主权国家的传统教育质量管理模式带来了诸多挑战,需要跨境教育提供者和接受者共同承担维持质量的职责。[5]与此同时,21世纪以来,旨在增强专业机构合作的国际组织、网络联盟剧增,突出地强调了对质量保障自身可靠性和可信度的关注。[6]例如2000年成立的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网络(European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积极推动各国在高等教育质量保证领域的合作,2004年转型为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2005年,在该协会建议与推动下,欧洲国家通过了《欧洲高等教育区质量保证标准与指南》(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ESG)。[7]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秘书处和经合组织(OECD)也共同制定了《跨境高等教育办学质量指南》(Guidelines for Quality Provision in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为保护学生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免受低质量办学和不良办学机构的侵害提供了一个国际框架。[8]
其次,国际人口流动带来了学历学位、职业资格的国际互认与转换问题。据统计,1990年至2017年,国际移民总量从1.53亿人增长到2.58亿人。这使得技能、经验的可转换性成为这个多样化和流动的世界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9]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机构推动全球相继签署、更新了6个关于高等教育资历跨境认可的地区公约。当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在努力尝试制定高等教育资历跨境认可的全球公约。[10]与国际人口流动相伴随的还有日益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并由此引发了各国对于学生“国际通用能力”的关切,开始努力在核心素养框架开发和相应课程改革中寻求国际合作与共识。
最后,循证教育实践的勃兴,尤其是对于“国际参照系”的重视,对国际教育调查提出了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强调教育实践应当基于证据或至少从证据获取信息的理念极具影响力。[11]通过国际比较寻找规律或备选方案被视为获取这种证据的一种重要途径。实际上,早在19世纪初期,“比较教育之父”马克-安托尼·朱利安(Mare-Antoine Julian)便提出设想,通过国际合作,组建专业团队收集各国教育资料并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推导出若干原理、一定规则,使教育成为近乎实证的科学”[12]。西方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热衷于基于人力资源预测的教育规划活动,在此过程中将朱利安的这一设想付诸了实践,支持并委托多边机构开展国际教育调查,通过信息交换,建立共享的国际教育信息数据库。随着“冷战”和两极格局的终结,世界迎来了一个更加普遍化的多极竞争时代。近乎在同一时期兴起的新公共管理浪潮,则使得人们对于国际比较的兴趣进一步演化为对基于数据的教育问责的狂热。从琳琅满目的世界大学排名到各种跨国成就测试,人们欲罢不能。所以,即便未必所有人都承认“全球教育治理”这一概念,但各国的教育事业正处于地方、国家和超国家层面的多层治理体系之中正在成为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二)教育日益被视作全球共同利益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强调将教育视为“公共利益”(public good,又译作“公共产品”)。尽管对此存在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无论将其解释为人文愿景、政策重点还是治理原则,这一观点都强调对社会集体利益的界定和维护,以及国家在这方面的核心责任。1999年,英奇·科尔(Inge Kaul)等人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思考公共产品的定义,提出“全球公共利益”(global public good,又译作“全球公共产品”)概念,指利益能惠及所有国家、人民和世代的产品。[13]近代以来,教育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接受为国家的公共事业,而全球化的发展则让人们进一步开始关注教育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例如,人们普遍承认,教育的经济外部性(externalities)可以对国家、区域和全球一级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14]当教育的益处突破了主权国家的界限,对于教育的治理也就顺理成章地走向了全球化。因此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问题在教育领域的真正源头是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教育作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的出现,展现了全球治理的另一个方面。[15]
近年来,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发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Rethinking Education: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下称《反思教育》)以后,人们再次对教育的属性与本质作出反思,强调教育作为一种全球共同利益。作为经济学概念的公共利益,被认为是个人利益的附属,《反思教育》认为,在公共利益范畴内,人类的福祉被个人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所框定,而共同利益的概念超越了其工具性,重申了教育作为一种共同的社会努力的集体层面(共同的责任和对团结的承诺)。[16]
无论是将教育视作全球公共利益,还是全球共同利益,都涉及集体行动的缺陷问题,并强调国际社会在教育治理中的角色。但二者强调不同的政策工具,主张不同的治理机制,并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影响。最重要的是,它们对国家、多边组织和国际法的作用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公共产品会导致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在保证此类产品供给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这一概念拓展到全球层面,那意味着构建一个强大的“全球政府”,全球公共产品的治理是“以决策过程的高度集中化为前提……并对所有行为者的合规性进行监督”[17],要求将不同的国际制度整合成一个单一的方案。而当教育成为全球共同利益,则要求发展全球政治机构和治理方法,使各国及其公民在影响其福祉的决策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意味着参与全球一级教育政策制定和实践的政治机构之间的新的合作形式,这种合作应促进“所有人民参与一个多样化和差异化但又团结协作的世界社会”[18]。就现实来看,各种全球教育倡议都是通过全球、地区、国家和地方各级行动者组成的复杂的谈判和影响过程产生的。[19]
(三)国际组织的产生及对教育事务的介入
如果说公共治理难题的出现与全球共同利益观的形成为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了现实需求与动力,那么国际组织的产生及对教育事务的介入便为全球教育治理成为现实创造了重要的制度性条件。乃至有学者认为,全球教育治理是全球化时代在政府间国际组织推动下得到全面发展的一种特殊现象。[20]
为了维系世界和平和促进战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一致同意在基于协商、和平的基础上成立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合作和冲突协商的重要平台,最典型的便是联合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与传播,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不但极大地拓展了国际社会的规模,而且将整个人类的命运扭在了一起,多边主义被推向国际舞台的前沿。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现代国际组织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数目呈爆炸性增长。国际社会从原来以创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主的国际政治、军事类组织的世界体系,转向以创建出一种旨在建立规则互联系统、担当治理全球事务为主的各类国际性组织的世界体系。[21]
相较单一国家,原本就是为处理多边事务、推动全球治理而生的国际组织,以某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内部教育决策的可接受性要大得多。除了身份上的先天优势,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资源优势也是单一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法媲美的。一方面,国际组织通过多渠道融资和捐助体系,获得了雄厚的资金用以支持全球教育公共产品开发和开展国际教育援助。以世界银行为例,仅2020财政年度就投入了约52亿美元用于开展教育项目、技术援助等。[22]而且,国际组织还掌握了丰富的专业资源,汇集了全球范围内的专业精英为其提供专业服务。另外,国际组织借助自己的平台优势,建立了大量国际教育信息数据库,在改善国家间信息不对称的同时,又在其自身与国家之间构造了新的信息鸿沟,使得研究者和决策者对其产生信息依赖。[23]另一方面,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有着强大的协调能力和感召力。可以说,从1990年的《世界全民教育宣言》(World Declaration on Education for All)呼吁普及小学教育,到2000年的《达喀尔行动纲领》(Dakar Framework for Action)设定全民教育六大“千年目标”,再到2015年的《教育2030 行动框架》(Education 2030 Framework for Action)将“确保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增进全民终身学习机会”纳入全球教育面向2030年的总体发展目标,没有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首的众多国际组织的参与、协调和合作,不可能将这些教育行动发展为全球性集体行动,让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就普及教育和提升教育质量向国际社会做出承诺。
三、作为理念的全球教育治理
阅读国内外关于全球教育治理的文献后会发现,“全球教育治理”这一术语有时候也被用以指称一种解释和指导解决全球教育问题的理念。例如,有新近研究将其定义为,“一种方法论和理论框架,强调了目前发生在教育治理中的更广泛的全球空间……这一理论被用来解释教育治理如何蕴含民族国家以外的行为者……从分析上看,它有助于克服方法上的民族主义,寻找教育中的其他权力来源……有助于将研究重点放在不那么正式和非传统的过程和结构上”[24]。就这一向度而言,全球教育治理目前还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因为它尚不具备作为一个成熟理论应有的一整套自洽的术语体系和逻辑框架。当前,部分学者尝试以国际关系学中的全球治理理论为基础衍生全球教育治理理论,但全球治理理论自身就没有形成一个严谨、统一的理论体系。而且,教育所包含的伦理、文化、经济、社会和公民等维度之间的相互交织,使得教育的全球治理比其他领域更加充满争议。[25]这就意味着,全球教育治理不是简单地将教育治理理论向全球层面延伸,也不是简单地将全球治理理论向教育领域分化,而有待学理层面的专门探讨。笔者认为,全球教育治理理论建设至少需要关注以下四方面问题。
(一)超国家行为体与跨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角色
人们往往将治理的话语推至全球层面以界定全球治理。在笔者看来,治理本身所强调的多主体特征其实已在某种意义上内在地蕴含了全球治理这一范畴,也就是说全球治理不应当被视作是治理的派生物,而是属于整个庞杂的治理体系中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如果非要在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做一个区分,那就是当全球治理作为一种多行为体的世界政治研究视角时,除了一般性地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尤为关注超国家行为体与跨国家行为体在治理中的角色。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就是探究这些新生权威决策能力的获得。[26]需要注意的是,全球治理不完全等同于国际治理,后者关心的是主权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治理;而前者还特别强调同时存在于治理进程中的超国家和跨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意义,认为国际治理、超国家治理和跨国家治理共同构成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复合结构。[27]
全球教育治理视野中的超国家体系主要由各种与教育相关的多边组织及相应规制构成,行为体主要包括:联合国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涉足教育事务的经济贸易合作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经合组织;以及区域政府联盟,如欧盟。这些机构通过推动发起教育倡议、制定教育标准与规范、开展教育援助等措施影响各国教育发展。跨国家行为体则既包括活跃在全球层次上的超大规模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全球社会运动,如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也包括活跃在一国范围内但借助国际资源和压力杠杆开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教育治理活动的组织、团体和运动,例如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教育研究部,还包括影响个人和公共教育决策的跨国市场行为体,例如以生产世界大学排名著称的国际高等教育资讯机构QS,等等。
全球治理理论认为,这些超国家行为体和跨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没有等级之别。[28]超国家行为体和跨国家行为体对于世界教育的影响,也因此成为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核心领域。
(二)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全球治理理论认为,世界政治是由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地方的、国家的、地区的和全球的政治进程组成的一个多层次体系。[29]全球教育治理关心超国家行为体和跨国家行为体对于主权国家教育事务的影响,但并不否认国家行为体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首先,“无政府①此处“无政府”意指不存在全球性政府。的治理”是全球治理理论的前提,全球教育治理并不是鼓吹建立一个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全球教育当局来统管全球教育事务。即便是欧盟这种对于成员国教育体制和政策产生了明显实质性影响的政府联盟,其治理权力从本质上来讲也是成员国部分教育主权的让渡,而这种让渡是主权国家的自由选择。其次,国际力量对于主权国家教育事务的介入程度和实际影响,最终取决于国家行为体的选择与解释,绕不开国家否决权行使者和否决点(national veto players and points)②按照克斯廷·马顿斯(Kerstin Martens)等人的表述,否决权行使者是指政治制度中那些有权阻挠或妨碍立法举措的行为者,特别是直接参与政治进程的政治行为者;否决点则是指那些阻碍社会行动者影响政治决策的体制框架,是使这些行为者能够在政治环境中参与的结构。参考文献:MARTENS K, NAGEL A, WINDZIO M, WEYMANN A.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Policy[M]. Palgrave Macmillan,UK,2010:12-13.以及国家意识形态背景的调解。例如,尽管我们意识到经合组织的国际教育指标对世界教育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但同时也会发现,不同国家对于同一份数据或分析可能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甚至作出完全相左的解读。[30]
基于全球治理框架探讨教育治理不仅认识到国家行为体的不可逾越性,而且认为在全球教育治理的事务与活动中,主权国家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31]即便是全球教育倡议,在游说超国家行为体和跨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同时,也强调国家行为体的不可推卸责任。《反思教育》也指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的背景下,国家必须继续保持确保获得和管理共同利益的职能,尤其是教育……国家承担着两项义务:一是改革公共教育并使其专业化,包括利用明确的程序使教育部门接受整个社会的问责,从而打击部门内的腐败;二是对私营部门参与教育予以监管和规范……”。[3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84个成员国通过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也强调,教育2030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各个国家,政府是所有人享有基本教育权利的第一责任人。[33]
(三)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软权力”与“软治理”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Nye, Jr.)把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soft power,又译作“软实力”)两个方面,认为前者通常同诸如军事和经济力量那样的具体资源相关的“硬性命令式权力”(hard command power),后者则指的是与诸如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的、决定他人偏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soft co-optive power)。[34]尽管奈提出软权力理论的初衷是为了重振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但这一观点后来被全球治理研究者所广泛引证。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和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uvall)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力》(Power in Global Governance)一文中提出,在全球治理中,除了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强制性权力(compulsory power),还存在制度性权力( Institutional power),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和生产性权力(productive power)。[35]应该来讲,巴尼特和杜瓦尔所说的强制性权力即奈所说的“硬权力”,后三者则可以看作是对奈的软权力概念的进一步发展与分化。
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制度性权力的概念重点是关注治理主体如何通过界定自己与治理客体之间各种制度的规则和程序,引导和约束后者的行动(或不行动)和生存条件。例如,研究世界贸易组织如何通过“服务贸易总协议”(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GATS),扩大成员国的教育开放。结构性权力则关注的是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之间不对等的社会结构所构成的二者之间不对等的特权和能力。例如,国际教育援助方不仅在金融资本关系上相对受援国家具有绝对主导权,而且在知识和技术意义上的发展能力方面同样占据中心地位。全球教育治理研究中探讨生产性权力的典型例子是分析特定的教育话语如何占据主导地位,此外也会关注某些“全球性教育问题”是如何以它们的方式被建构起来的,哪些知识被授权或合法化。
因此,在全球教育治理视域下,我们除了研究治理主体如何凭借“硬权力”实施正式的、纵向的“硬治理”,还需要关注凭借“软权力”实施的涉及调节社会过程的非正式的、横向的“软治理”。与硬治理模式相比,“软治理”的概念描述了一种依靠自愿形式的公共行动和自律性政治指导的政策执行方式。[36]相比国家政府在各自教育治理中的强硬角色,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角色要“软弱”得多。实际上,全球治理更多时候并非各国决策者被强加这种超国家影响,而是他们自己认为接受所谓的全球标准和政策模式对自己有益。所以有学者指出,全球治理的本质主要是认识论的(epistemic)[37],主要通过知识生产和咨询活动影响人们的认知来发挥作用。
(四)通过“全球教育共治”达成“全球教育善治”
当我们将全球教育治理视作一种应然时,核心关切是它如何在达成全球教育“善治”(good governance)方面发挥优势作用。有学者指出,教育之善治即教育领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教育治理的优势在于以“共治”路径达成“善治”目标。[38]如今我们能看到多种、多层行为体同时在教育决策中产生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理想的全球教育治理已然成为现实,因为这些力量之间究竟是同心合力还是彼此弱化甚至抵消,从根本上决定着能否达成善治。从这一角度来看,全球教育治理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多主体,也不是超国家行为体和跨国家行为体对于教育事务的介入,而是从亚国家到超国家,从公共部门到私营部门,多层教育治理体系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共生。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教育共治,首先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建立起从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的共赢利益观。教育是全球共同利益,全球教育治理的目标就意味着是要保障以及最大化全球共同利益。全球教育治理并非无视不同行为体,尤其是不同主权国家在教育领域的利益冲突,而是呼吁超越狭隘的单一国家优先思想,以国际合作的视野来寻求各国利益合作的契合点和最大公约数,要打造的是“利本国”和“利他国”相统一的“利益共同体”[39]。
其次,全球教育共治的核心是“集思广益”和“平等参与”,建立起共商、共建、共享合作观。全球治理理论假定共存不同形式的治理形式,且这些不同的治理机制之间几乎不存在明显的等级分割。[40]全球教育治理要改变大国主导、强国主导的话语分配格局,尊重并充分听取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保障各国都能就自身教育发展经验和发展需要对多边教育议程产生影响,协力为全球教育公共产品的有效生产与合理分配做出贡献,共享经济全球化与教育国际化红利。
最后,全球教育共治要超越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教育现代化思想,尊重各国教育主权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差异,建立和而不同的发展观。有些国际组织将所谓的教育发达国家和教育欠发达国家置于一个进化的连续统一体中,认为后者向前者学习“最佳实践”可以实现教育的最佳发展。[41]但是,这种单向输入不仅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多样化,而且有着强化“中心—边缘”格局的风险,与寻求共治的全球教育治理思想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由此可以认为,全球教育治理是为了实现主权国家更好地教育自治,而非建立一个抽象的全球大一统教育模式。《反思教育》在论述教育作为全球共同利益的内涵时,也借用塞文琳·德纳林(Severine Deneulin)的观点表达了类似的看法:“鉴于对什么是共同利益的文化解释各不相同,公共政策必须在尊重基本权利的同时,承认和培养这种背景、世界观和知识体系的多样性,这样才能不损害人类的福祉。”[42]
四、全球教育治理的限度
从全民教育宣言、千年发展目标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社会制定了一个又一个雄心勃勃的全球集体行动计划,但实际进展却始终不尽如人意。2020年6月发布的《全球教育监测2020》(Global Education Monitoring 2020)指出,当前全球范围内每5名儿童、青少年和青年中就有1人被完全排斥在教育之外,与此同时还有数百万学生因耻辱感(stigma)、刻板印象和歧视在教室里遭到疏远,而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让世界陷入了教育史上最空前的混乱之中。[43]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这场世界性教育危机,本应是全球教育治理大发展之时,但摆在人类现实面前的却是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的抬头和不信任情绪的蔓延。
笔者认为,国家中心治理对全球教育治理的限制,是其失灵的根本原因,也因此决定了其限度。尽管在全球化影响下,国家中心治理的主导地位受到来自超国家中心治理的挑战,但总体而言,国家中心治理依然保持着相对的优势地位。[44]这意味着,当国家内外力量出现不一致时,来自国家外部的力量在决定教育议程中的优先性绝大多数时候要让位于来自国家内部的力量。典型例子就是全球教育公共产品的外部性无法避免伴随“搭便车”效应,使得各国的纳税人都倾向于拒绝自己的国家为之买单,比如反对本国政府为留学生提供国民待遇(更不用说超国民待遇),反对参与国际教育援助,反对分摊国际组织会费等。而对于大多数国家领导人来说,国内合法性优先于国际合法性,因为真正影响其执政地位的是其国内政治支持者。[45]
即便某些时候看似外部压力战胜了国内阻力,实质可能只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例如,墨西哥政府于2013 年不顾国内反对,遵照经合组织的建议颁布了《教师职业一般服务法》,以至被国内学者讽刺为不是教育政策的制定者,而是经合组织的执行者。但事实上,墨西哥政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借外力在国内施加改革压力,并促进改革中伴随的政治权力重新洗牌的“合法化”。[46]有学者甚至直言:“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外力结果,而是一个本国内由长期政策分歧所产生、旨在施加改革压力和建立政策盟友的修辞而已。”[47]
除了国家中心治理与超国家中心治理之间的力量不对等,国家中心治理的优先性还伴随着国家间的对立与矛盾。一方面,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虽然使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但这并不会从根本上消除国家之间的竞争与防范心理,反而会使主权国家更加敏感自己的自治权,尤其是在教育领域。为此,主权国家出于维护教育主权,尤其是防止外来意识形态入侵的考虑,始终会对国外力量介入其教育事务加以不同程度的抵制。另一方面,全球教育共治要求以和平的方式让传统发达国家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让渡部分既得话语权,这无法避免两股势力的相互拉扯,增大多边教育议程的创建难度,使全球教育治理陷入两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