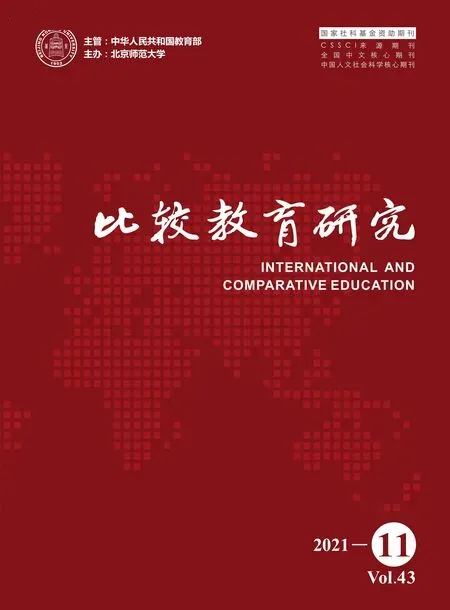在愿景与现实之间
——南非价值观教育与种族平等团结的促进
朱逸
(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 610066)
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教育与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紧密关联。在既定的社会结构的维系与变革中,价值观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自1994年政治转型至今,南非人在拆除种族隔离的制度藩篱的同时,施行了一系列基础教育改革的举措,普及义务教育,提升教育质量,积极融入全球教育的发展潮流,为建设种族平等、社会团结的新南非提供有力支撑。本文旨在探究“后冲突”(рost-сonfliсt)背景下,南非的价值观教育与这个国家实现种族平等团结的进程之间的关系,并从这个国家的历史、法律、教育政策、课程与日常教学实践等多个方面考察。由此呈现教育愿景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一、南非社会不平等与分裂的历史根源:种族隔离政治及其价值观教育
南非学者恩斯林(Р. Еnslin)将南非形容为一个“系统性断裂的社会”,以统称这里存在着的种族、民族、阶级、语言等各种分裂。在他看来,这些分裂主要是由不平等的种族隔离政治及其反抗斗争造成的。[1]南非的种族不平等问题源自17世纪以来荷兰和英国的殖民侵略。这个国家经历了长达300年的少数白人对多数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的种族压迫。南非荷兰裔白人民族主义党(Аfrikаnеr Nаtionаlist Раrtу)1948年当政后,南非殖民当局逐步推行一套按照白人、有色人、印裔人和黑人四个种族群体分而治之的系统全面的种族隔离制度。1959年和1970年颁布的《促进班图人自治法案》和《黑人领地的公民资格法案》,将黑人迁移和圈禁在特定区域(主要是南非的边境地带)施行所谓“自治”,实则完全剥夺了南非黑人的公民权。殖民当局还严酷地镇压南非人民对种族隔离政治的反抗。正如有学者评论的:“整个种族隔离时期流血惨案、暴力冲突频繁发生,人权遭受践踏,严重的社会不公正与不平等以及暴力恐怖给受害者身体和心灵都留下了深深的疼痛的烙印。”[2]
为维持白人的统治地位与种族隔离,南非殖民当局推行针对白人特别是荷兰裔白人儿童的“基督教民族教育”(Сhristiаn-Nаtionаl Еduсаtion)和针对黑人儿童的“班图教育”(Ваntu Еduсаtion)政策,通过各自分离的学校系统灌输种族等级的观念和“白人至上”的价值观。种族隔离与班图教育的“设计师”维沃尔德(Н. F. Vеrwoеrd)认为:“对土著人的教育将使之从小意识到他们与欧洲人是不平等的。”[3]因此,学校教给白人学生是加尔文教的教义,以及扮演未来社会的管理者、督导者角色的思想观念与知识技能。其他的种族尤其是黑人,则被置于“供养白人”的奴役地位,学校提供了大量的手工训练和低水平的文化课程,要求他们“学习服从”、接受“历史事实”和尊奉“既存秩序”——“每一种人必须在成长中理解国家分配给他的角色。必须毫无疑问地接受由南非白人的领导权力和非白人的服务义务所确立的白种人的优越性”[4]。南非学者瑟若塔(J. Sеroto)指出:“班图教育部”(Dераrtmеnt of Ваntu Еduсаtion)于1957年在小学开设的“社会研究”与历史课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在种族隔离时代,尽管存在针对不同种族的学校教育系统,但“历史”一类课程并没有太大的差别。[5]历史课竭力鼓吹“殖民英雄史”,将种族隔离制度的建立“自然化”。如三年级的历史课教给儿童的是“导致不同的族群迁入南非的历史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与南非的现状联系起来——如何影响南非人发展成为相互分离的社群”[6]。瑟若塔认为,这种教育的本质,是培养白人公民和黑人奴隶。同时,这种教育也戕害了南非黑人的身心发展。南非学者、政治活动家塔巴塔(I.В. Таbаtа)指出,班图教育是使人“野蛮化”的教育,它使黑人回到了原始分散的部落主义,与现代国家的民族统一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班图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制造驯良的、无法理解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黑人劳动力”[7]。南非学者阿克尔-科巴(А. Аrko-Сobbаh)指出,种族主义的价值观教育导致南非人普遍缺乏“文明性”,丧失了对人的生命的神圣性的尊重。[8]南非学者斯科曼(S. Sсhoеmаn)则认为,由于在种族隔离时期现代民主价值观教育的长期缺失,人们普遍对政府制度、政治进程和其他公共议题感到无知。[9]
种族隔离制度及其价值观教育造成了南非不同种族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导致了激烈的社会矛盾与种族冲突,但这并未阻挡南非人民为实现平等团结而不懈探索与抗争。1955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等组织召开“南非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自由宪章》宣告南非属于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全体黑人和白人,提出“教育与文化应该面向所有人”[10]。同年,南非黑人学生对《班图教育法案》发起抵制。1960年,“教育与我们拓展的视界”国际会议在南非召开。这一南非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发出了反种族隔离的强有力的呼声——“我们的教育不要分离,而要接触和社会交往,尤其要通过教育弥合特权者与无权者之间的间隙”[11]。20世纪70年代,保罗·弗莱雷(Р. Frеirе)的批判教育学为当时的“黑人意识”等斗争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与方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南非社会掀起了“人民教育”运动,不仅为受压迫和受歧视的黑人争取平等的受教育权,而且主张教育要服务南非全体人民的发展,避免教育从狭隘的白人民族主义滑向狭隘的黑人民族主义,坚持通过多方参与协商达成关于教育决策的广泛共识。这场进步运动为后来新南非的教育改革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2]
二、南非的政治转型与价值观教育的目标与内容
1994年南非历史上第一次普选,它标志着曾经建立在种族主义之上的压迫性政治的终结。1996年,南非制定和颁布了《南非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为新南非指明了进步的方向:既保证每个南非人,无论其种族,都作为该国的公民平等地享有生存发展的权利;强调“多元一体”,呼吁各种族和解、团结以及共同对新南非的繁荣发展承担责任。[13]
学校教育是新南非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颁布的宪法是新南非教育特别是课程与教学法领域改革的行动指南。在社会成员特别是作为国家公民的青少年学生中培育以宪法为依据的新的核心价值观,促进种族平等、团结,就成为新南非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南非人已经进入了一场旨在建立一个统一体而奋争的新斗争中,这场斗争将弥合曾经的分裂,消解过去的冲突。这些目标包含在植根于宪法及其《权利法案》的价值观中。”[14]2001年,南非教育部依据宪法颁布了《价值观、教育和民主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是新南非价值观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它规定了要培育的核心价值观包括以下十项:民主、社会正义与平等、教育平等、反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人性尊严(“乌班图”,Ubuntu,祖鲁语)、开放社会、问责性(责任)、法治、尊重与和解。[15]这些价值观展现了新南非不同种族的人们平等团结的愿景。
(一)培养体现共同的公民身份的价值观
新南非的价值观教育首先需要在青少年学生中缔造一种超越种族对立的“公民身份”,由此,他们能够意识到他们是普遍享有法定权利、共同承担法定义务的社会成员。《宣言》强调,新南非的青少年学生应当具备与实现权利相应的知识与能力:不同种族的学生应当知悉和理解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同种族的学生应当获得民主协商的能力。[16]同时,青少年学生还应当了解并积极履行对国家和其他同胞的义务。南非教育部于1996年颁布的《教育政策法案》要求学生把个人的成长与国家整体发展相结合——任何南非公民,无论其种族,均应当推动“国家在道德、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发展”,实现社会在“民主、人权以及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进步”[17]。2015年的《南非青少年责任法案》明确规定了南非青少年的12种公民责任,其中直接关涉种族平等团结的责任是:保障人性尊严;平等待人;公民参与。[18]
总之,《宣言》突出了共享、共建、共荣的“国家共同体”观念以及不同种族的学生作为人和国家公民在法律上的共通性,力图改变过去的政治冷漠与种族敌视,要求学生学习如何通过民主、法治、尊重的方式解决争端。
(二)培养体现包容种族差异的价值观
随着南非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价值观建构的关键是从“宽恕”到“宽容”。[19]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宽恕是对罪行的饶恕,宽容是对差异的包容。唯有学会包容差异,欣赏各种族在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才能克服偏见、实现长期的平等团结。正如英国学者温特霍尔特(Е.Untеrhаltеr)评论的:“南非共和国宪法包含了一个承认多样性的公民身份观。”[20]据此,《权利法案》和《宣言》肯定了多种差异,要求尊重、保障和促进种族之间的“积极的差异性”,并将这些差异转变为教育的资源。《南非青少年责任法案》表达了通过尊重差异实现种族平等团结的要求:“南非是一个多元的国家,平等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相同;我们国家的口号是‘多样的人民团结在一起’,这号召我们共享国家的荣耀,以及使我们成为不同族群的多样性。”[21]
第一,“积极的差异性”包括南非人使用的语言的多样性,特别是支持南非黑人民族语言的保存。语言是传递文化的媒介,新南非的种族团结和多元文化的发展无不受到语言的影响。《南非共和国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权选择一种或多种官方语言在公共教育机构中接受教育。针对(黑人)民族语言地位的降低和使用的减少,国家必须采取实际而积极的措施,提高它们的地位,推广它们的使用。”[22]2012年的《国家课程声明R-12》规定的语言科目包括了除英语和南非荷兰语(Аfrikааns)以外的同等的11种语言,如祖鲁语、科萨语等。在南非公立学校,双语教学以及在学校课外生活中使用多种语言的倡议逐步得到推行。此外,也有南非学校致力于探索如何让不同种族的学生突破语言的限制,通过其他的交流方式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23]
第二,“积极的差异性”包括在种族隔离时期受到歧视的土著黑人的文化传统。《宣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包含了体现非洲文化传统的概念“乌班图”。依据南非大主教图图(D. Тutu)等人所述,这是一种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哲学,它的基本含义是“通过他人,一个人才能成为人”,核心精神是号召人们应当“团结一致”“结合为一体”。这种观念突出了人作为社群成员的身份意识,要求在社会交往中关切他人和集体的福祉,“帮助他人,关怀年老的、无家可归的人和患艾滋病的孤儿,急人所需,让任何人食宿无虞,有所依靠”[24]等。其引入价值观教育中,对于重拾非洲传统的教育智慧、挑战西方教育的话语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乌班图”既是增强黑人社群内聚力的传统价值观,也包含了爱心、平等、正义、尊严等人性善的观念,因此能被其他的族群认同和分享。图图认为,“乌班图”体现了人类的本质,“是非洲人贡献给世界的礼物之一”[25]。
第三,对种族差异的包容还涉及对待差异的正确态度。《权利法案》禁止种族歧视,规定对种族的特殊性的强调不得超出《权利法案》的条款规定。《宣言》要求学生认识和尊重那些有利于新南非文化发展多样性的差异,同时警惕和克服那些“特别有害的态度”[26],如种族偏见、歧视和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种族特权意识等。
三、新南非价值观教育在学校课程中的实施
《宣言》提供了16种在学校进行价值观教育的策略:在学校培育一种交流和参与的文化,使学生能通过对话建立共识、理解差异;角色示范,促进教师与管理者在践行价值观方面的承诺与能力;确保每一位南非人都能阅读、写作、计数和思考;确保平等的受教育权;使艺术与文化成为课程的一部分;让历史科重回课程;将宗教教育引入学校;在学校推行多种语言;发挥体育运动在凝聚社会和缔造国家统一体方面的作用;反对学校中的种族主义;使女孩的潜力同男孩一样得到释放;应对青少年艾滋病问题,培育一种有关性的与社会责任的文化;使学校成为安全的教学场所;确保依法治校;生态环境教育;弘扬新爱国主义,即以对宪法价值观的承诺为根基的爱国主义,确证我们共同的公民身份。[27]以上价值观教育策略广泛地涉及课程与教学改革以及校园环境、管理制度和校园文化的建设,无不体现了将不同种族的南非青少年学生导向平等团结的主旨。这里主要聚焦课程展开论述。
学校课程是培育新价值观的主渠道——“新南非国家建构进程中,国家课程的首要目标是通过灌输自由民主价值观培养完全脱离种族主义的国民,从而达到去种族化和实现民主过渡的目的。”[28]宪法价值观融入了国家课程标准。《国家课程声明R-12》涵盖了南非公立学校从学前到高中的所有课程。培育“人权、包容、环境和社会正义”的价值观作为课程的一般目标,被写入了所有学科配套的《课程与评估方针声明》的“背景综述”部分。可见,尽管有培养价值观的重点课程,但一种“全面主义”的策略被采用,即价值观教育的要求包含在一个学习领域,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方式。价值观教育也渗透到学校的日常管理和校园生活中。
道德与社会科学是进行价值观教育的主要领域,包括从学前到6年级的《生活技能》,7年级到12年级的《人生取向》, 4年级到9年级的《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和“地理”),以及在10年级到12年级分科开设的《历史》《地理》《经济学》等科目。
其中,《人生取向》是价值观教育的核心课程,初中的《人生取向》目标是“教给学生个人与社会方面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促进学生身心成长,使学生能够自我激励,学会设定目标、解决问题和确定决策,为民主社会服务”。与种族平等团结的主题和价值观教育最直接相关的部分是“宪法的权利与义务”,包含《南非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人权、公平参与、性别平等、公民义务、文化多样性等议题,三年总计有23个课时。9年级的课程专门将宪法价值观设置为一个议题,具体的学习内容包括“在弘扬宪法价值观方面的积极和消极的角色典型:社区/社会中的父母和领导者”;“将这些价值观运用到生活中”。[29]高中的《人生取向》则要求学生“为民主和公正的社会作出贡献”。“民主和人权”是该课程的六大主题之一,要求教给学生“宪法的权利和义务,懂得他人的权利和社会多样性的问题”[30]。三年总计有18个课时。
社会科学课程要求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和责任心,为学生将来建设民主公正、文化繁荣的新南非做准备。例如,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社会科学》的“历史”部分的目标是“阐释和宣扬南非宪法的价值观”“加强青少年的公民责任”以及“通过挑战种族、性别等偏见而促进人权与和平”[31]等。
其他学科课程也承担着价值观教育的任务。它们“不是文化中立和没有价值导向的”;数学、自然科学、技术领域要求学生除了掌握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外,还要能够“作为一个整体,以一种民主的、非种族主义的、去性别歧视的方式,参与他们的社区和南非社会,能够批判地讨论科学问题,以一种明智的方式参与民主决策的过程”。[32]
课程教学是价值观养成的重要途径。南非教育部于1996年引入了一种“以结果为本”的课程教学与评价模式。这一模式以学生为中心,以活动为基础,“围绕学习者学到了什么以及在学习过程结束时能够做什么展开”[33],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就价值观教育而言,这一模式重视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展现民主和包容精神,预演作为未来政治参与者和社区服务者的角色。[34]例如,在开普敦的沙丘高中(Dunе Нigh)的一堂《人生取向》课上,教师没有拘泥于课本中的论述,而是根据学校所在社区物质条件差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有关“环境正义”主题的教学。教师注意到煤在教材中被说成是主要的环境污染物,但也是该社区贫困家庭生活的主要能源。因此,这堂课围绕“公民如何能够要求政府确保基本服务的供给以改善社区条件”的议题讨论展开,要求学生描述其生活境况和社区状况,由此明确其中存在的主要社会问题与环境问题,学习有关政府结构的知识与公民参与的机制。[35]这堂课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紧密相关,采用了多种价值观教育的策略,涉及的价值观包括民主、平等与责任等。并且,这里的责任不仅指学生作为公民保护环境的责任,而且批判地指向了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可问责性”。
学生参与学校治理以及校园文化环境,是新南非价值观教育的“隐性课程”。《南非学校法案》要求建立由国家、省、地区、学校四个层面构成的“学校治理团体”体系,每隔三年换届选举;“尊重每个儿童的权利、宣扬平等和无种族主义的价值观、与种族主义等其他形式的歧视和不公正作斗争”是学校治理团体承担的重要职责之一。[36]南非教育部鼓励家长和学生参与治理团体,规定学校一级的治理团体必须有两名学生以平等的、完全的成员身份加入。这在学校管理制度方面为价值观教育提供了支持。此外,价值观教育也渗透在校园文化中。南非教育部给新生发放的宣传单“同伴价值观”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一名来自马里的黑人新生因为肤色和口音而受到几名白人学生的嘲笑,另外一名女生则出面制止这种行为,理由是“他与我们不同,但并非意味着我们与他是不平等的”,这几名白人学生最终意识到了自己错误的种族偏见和仇外心理。[37]
四、新南非价值观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
1994年以来,南非社会总体上朝着种族平等团结的方向迈进,犯罪率下降,对不同种族群体的尊重以及政府的合法性逐渐增强。价值观教育是这一进程的助推器,从中可以看到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与学校教师不同方式的努力。通过《宣言》和相关法案,政府的教育政策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宪法蕴含的价值观,表达了在南非公民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中培育这些价值观的普遍要求。学校课程依据教育政策设置,将教育要求转化为承载价值观的学习目标与内容。作为课程教学的执行者,教师更加关心实践策略的特殊问题;他们是价值观教育从愿景通往现实的桥梁——“在将这些理想转化为与学习者相关的并为之接受的概念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38]。指向未来的愿景给予了人们生命与行动的意义;对于教育,正如彭正梅所言,它们是必要的、“高贵的幻象”;否则,教育将会失去丰沛的内蕴与深沉的创造力。[39]南非共和国宪法勾勒了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确立民主、平等、团结的新价值体系,为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基本指南。从实际的教育行动看,南非人将新价值观全面地渗透在课程和学校生活中,让学生参与课堂、学校和社会,发掘有利于涵养新价值观的传统文化资源等,这些做法值得肯定。然而,当前南非的价值观教育也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对种族平等团结的实现进程构成了挑战。
首先,课程设置、教育内容与方式不完善。第一,价值观教育的核心课程内容烦冗。作为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人生取向》的主题庞杂,包含大量诸如“体育运动”“职业规划”等可设置为单独课程的主题,而涉及“宪法与法律”“政治与公民”等与价值观教育直接相关的主题的课时量很有限,无法充分满足培养具有宪法价值观的公民的需要。第二,历史课的重新开设是《宣言》倡导的价值观教育策略之一,但将种族隔离的罪恶引入历史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无辜的白人学生的“负罪感”。今日南非的许多年轻白人感到,种族隔离似乎已经构成了他们的“原罪”,即使自己不曾迫害过任何人,仍需要替他们的祖辈犯下的错误“赎罪”。[40]与此同时,许多教师也面临既要讨论历史上的种族不平等问题,又要避免在学生中制造疏远与敌对的教学难题。[41]第三,教育方式存在简单化与形式化倾向,教育的实际成效遭受质疑。例如,恩斯林和瓦格西德均对《宣言》倡导的第十六种价值观教育策略“培育新爱国主义”提出了批评,认为“新爱国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教育策略,毋宁说是一种类似于尤尔根·哈贝马斯(J. Наbеrmаs)所谓的“宪法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并且认为其所建议的“通过唱民族国家赞歌、展示国旗、高声宣誓效忠和朗诵《宪法》序文”等会使教育流于表面,与民主价值观的培育形成扦格,不利于学生批判的、协商的能力的养成。[42][43]
其次,教育资源在不同学校分配不平衡。在种族隔离时期,不同种族的儿童所享有的教育资源就存在着严重的差距。如依据1949年南非参议院援引的数据,政府给白人儿童的财政支出为每位50英镑,给非洲儿童的仅为每位7英镑。这稀少的支出还只是针对实际在校的非洲学生,并未涵盖大量辍学的非洲儿童。[44]在今日南非,这一问题并未完全得到解决。为实现学校治理的民主化,南非教育部采取了“去中心化”的政策。这保证了地方学校的自主权,使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但也导致了背离平等的后果,即种族隔离时期白人学校的特权被保留,学费高昂,黑人学校仍旧处于劣势地位,经济与种族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被延续和固化。哈米特(D. Наmmеt)和斯戴海利(L. А. Stаеhеli)对开普敦、彼得马里茨堡和威廉王城三地的12所中学进行了实地调研,指出由于资金不充分和政府职责的缺位,教室拥挤破旧,教职员工不足,教学设施、教学材料和学校供餐缺乏等问题,在贫困地区原先的黑人学校,仍旧特别明显。[45]福格勒-唐摩尔(А. Foglе-Donmoуеr)博士在南非的杜尔班选取了三所历史上的白人学校、印裔学校和黑人学校进行了质性案例比较研究。根据她的记述,学校的物质条件、周边环境、经费、师生比、师生种族多样性等状况的优劣程度是依次递减的。[46]可见,打破种族隔离造成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的历史格局,仍需要较长时间。
再次,相关课程的教师教学活动不规范。有学者指出,《宣言》中的价值观所代表的教育理想的传递,既受到延续至今的教育资源分配差别的影响,也受到教育者自身的态度和期望的塑造。[47]教师群体不同的生活史和生存境况,都积极或消极地影响了宪法确立的价值观从教育政策向教学实践转化的实际成效。福格勒-唐摩尔的调研揭示了上述三所学校的《历史》《人生取向》课程教师不一致的教学风格:原先的黑人学校的教师注重准确清晰地呈现法定内容,而白人学校的教师更注重引导学生批判地介入这些内容。尽管后者或许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在具体的操作中,这些教师所谓的批判更多地指向了当今的南非政府,甚至刻意地采取与官方的历史叙事敌对的立场。例如,一位名叫菲尔(Рhil)的历史课教师倾向于引导学生从消极的角度认识曼德拉等南非历史上的英雄,而从积极的角度认识种族隔离时期的恶棍。他为此辩护的理由是“避免简单化、标签化和注重观点的平衡性”[48]。福格勒-唐摩尔对这种做法的评论是公允的:“尽管教授多样的观点不可或缺,但给予所有的观点同等的权重是危险的。”[49]在实现种族平等团结的进程中,历史教育不能没有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正确导向。这里显露的问题是,南非政府的相关政策与课程方案尽管声明了教育必须基于民主、平等、团结等价值观,但并未明确具体地规定教师在教学中应当如何遵循这些原则、处理相关主题。对相关课程教师进行规范系统的培训,是决定价值观教育与课程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最后,正如英国比较教育学先驱萨德勒(М. Sаdlеr)所说:“学校外的事情甚至比学校内的事情更加重要,学校外的事情制约并且说明了学校内的事情。”[50]他强调了一个国家教育的改革发展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于南非,种族平等团结的愿景无法仅仅通过学校教育实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有效应对当前南非社会面临的经济增长缓慢、人才外流、贫富分化加剧和政治腐败等现实挑战,才能为价值观教育化解种族矛盾、弥合社会分裂创造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