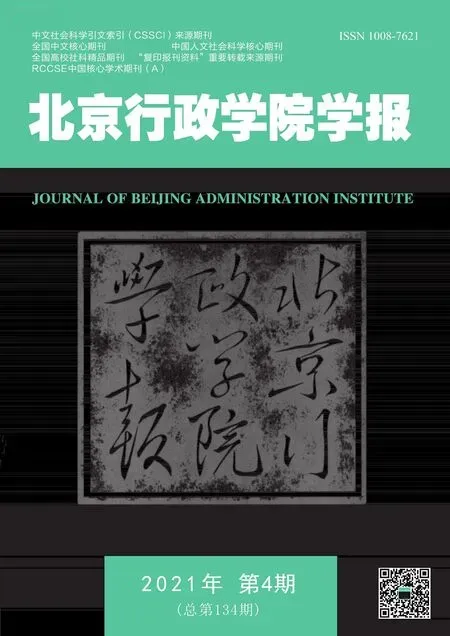体认与呈现:中国传统史学话语及其内在逻辑
□王振红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一、认识论的阴影与理性的魔力
西学东渐以来,包括中国史学在内的中国学术,日益被规范于西方的学术分类以及理性分析论证为主导的话语系统之中。“我们总是想当然地把西方的、直到19世纪才形成的学科分类,看作是永恒自明的东西,并以之来规范所有的学问,包括古典的及非西方的学问。眼下种种提升‘传统学问’(‘传统’似乎不经现代转化便与‘过时’同义)的好意与努力,多倾向于使之附就于现代西方学术之框架,使之概念化、理论化,这样做的结果,徒然使真正的尚富活力的传统支离破碎,离我们越来越远,而不这样做,在今天的学术化大潮中又未免内心不安”[1]46。究其根源,中国近现代学术之所以主动或被动“附就于现代西方学术之框架,使之概念化、理论化”,主要原因在于学术界普遍接受了西方的认识论,尤其是对西方科学与理性的膜拜。
世界近代文明史上,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西方的学术分类及其背后的认识论,作为认识、分析、解释,以及建构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学术利器,推动各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因而也就具有无限的魔力。因此,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自觉不自觉地浸润其中而无法自拔。就中国史学研究而言,无论是关于历史事实的科学考据,还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层面分析与阐释历史,或是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划分与探究,抑或是历史的叙事、书写、编纂,无一例外,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自发或自觉地在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下开展研究,匍匐在理性的魔力之下,在各个领域从各个层面进行着概念化、理论化、体系化的努力。
当然,伴随着学术界对科学崇拜与理性宰制之极端状态的批判与反思①何兆武先生曾言:“理性或科学是人类文明(尤其是近代文明)中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没有它,人类文明不仅不可能进步,而且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但它决不是唯一在起作用的因素。人类的文明史永远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或理性的一统天下。崇拜理性或科学过了头,就成为理性崇拜或科学崇拜,其结果就会走火入魔而成为和传统各色迷信一样的另一种迷信。”相关论述参见何兆武:《历史学两重性片论》,《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史学研究也遭遇了后现代反理性、非理性以及拒斥宏大叙事等方面的“反动”。在此情形下,中国史学界一方面开始重视主体间性,提倡“感觉主义”,倡导叙事转向,理论上试图突破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另一方面眼光向下,在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开展具体而微的研究,诸如开辟社会史、新文化史、情感史、概念史、妇女史、环境史等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理论层面的众声喧哗与实践层面的五彩缤纷,无论是正向继承还是反向而动,实际上依然以近现代以来形成的学术分科及其背后的科学、理性和认识论为基点。
主客二分的认识论以及科学理性的精神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魔力,一是因为它源于元气淋漓的古希腊文化传统,根基深厚,源远流长;二是因为近现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相结合所形成的无比巨大的合力,从而在制度、思想、精神以及经济、科技等领域遥遥领先并宰制了整个世界。古今相辅相成,西方近现代的话语系统、思维范式酝酿出无比强大的力量,成为整个世界学术认知、理解、阐释与建构的全局性的系统性的范式①托马斯·库恩指出,范式是“实际科学的公认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是“团体承诺的集合”。参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9页、第158页、第163页。我们认为,近现代西方学术在科学、理性、认识论等根本层面呈现出整体性、全局性的范式,同时与西方近代的民主制度、工业革命紧密结合,形成了融学术、政治、经济为一体的主导世界的力量与范式。。因此,即便它们遭遇到后现代的全面“反动”,其地位至今也无法撼动。
在西方近现代话语系统、思维方式笼罩下的今天,我们如何研究与西方学术皆无交涉的中国传统史学呢?本文认为,中国传统史学记载的是中国古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以,研究中国传统史学,首要的是要借助历史记忆与史家技艺“重返”中国古人的生活世界,即“重返”中国古代的具体历史场景、中国古人的精神情感世界。当然,这里的“重返”既是客观的“还原”,也是主观的“建构”,其最为适切的路径当是“体认”基础上的“呈现”。
二、作为认识方式、思维模式的“体认”
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先秦史学主要围绕着华夏民族在中原地区及其周边生存、繁衍、发展的具体历史活动而展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系统。与以西方世界为历史舞台,渊源于古希腊文化且以科学实证、理性分析话语系统为主导的近现代西方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氛围之下,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在记载内容、认识方式、思维模式等方面自然存在着诸多差异。
中国古人对于自身拥有的历史认识能力,以及“鉴往知来”的认识目标都非常自信,正如《论语·八佾》所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2]186-187又如《为政》曰:“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2]148不仅如此,孔子修《春秋》,又明言其修史之法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3]孔子认为,立足文献、运用损益之法就可以征知夏礼、殷礼,其具体方法是“见之于行事”,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将夏礼、殷礼当作客观对象进行认识,但与近现代历史认识论把历史当作客观对象进行分析认识、阐释建构的方法当有本质之别。
实际上,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史学家一方面重视立足文献、运用损益之法而“见之于行事”,另一方面,他们更强调史学家要置身历史、体认历史。比如,《论语》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郑玄注:“逝,往也,凡言往者如川之流也。”[2]704-705孔子把历史(“逝者”)比作奔腾不息的河流,其对历史的情感体验浓郁而深沉。李泽厚认为,《论语》此句“大概是全书最重要一句哲学话语”,认为“作为时间现象的历史,只有在情感体验中才成为本体”[4]。其实,这更是一句历史哲学话语,它足以表明孔子认识历史往往采取“体认”之法,将向往、感怀、忧愁、希冀等情感充溢其中,诸如对文王、周公之德的尊崇与感怀,对伯夷、叔齐遭际的同情,对管仲、子产功业的恳认,对礼乐崩坏的感伤。这种“体认”历史之法,得到后代学者尤其是史学家的继承与发扬。比如,《左传》所载晋灵公命鉏麑杀赵盾,而鉏麑为赵盾的品德所感动,自己陷入“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的绝境,最终触槐而死。鉏麑临死前的内心独白无人知晓,《左传》作者显然是通过设身处地的“体认”而获得的。再如,司马迁之所以能栩栩如生地描述荆轲刺秦王、鸿门宴、霸王别姬等历史场景,他本人总结的原因在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这其实就是“体认”。当然,司马迁的“体认”不仅限于具体的历史场景,而且对时代精神、历史发展趋势皆“成一家之言”。
此外,这种对人事、时代、历史的感悟与体认还深深地影响着历代的文学作品,最为著名的应为咏史诗。诸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中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王安石的《叠题乌江亭》中有“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杨慎的《临江仙》中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屈大均的《鲁连台》中有“一笑无秦帝,飘然向海东。谁能排大难?不屑计奇功。古戍三秋雁,高台万木风。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这些咏史抒情的诗句饱含着对历史人事的感怀之情,正是作者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基于对历史的深切“体认”而形成的。
“体认”作为认识方式与思维模式,与认识论将认识主体与客体彼此分离对立迥然有异,它强调历史认识者与客观历史本身的同质性、一体性,强调历史认识者将自己的身体感受、情绪、心理、情感、意志乃至潜意识、非理性等融入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认识与体验。在美学研究领域已有学者指出,“感情认识”是与“理智认识”相对立的认识方式。胡家瑞认为,理智认识与感情认识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人们认识世界存在着两种认识形式:理智认识和感情认识。理智认识是对某一事物在特定范围内的运动规律的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两个有着因果联系的阶段;理智认识的核心特点是要排除主观情感的干扰,它的唯一出发点是客观存在,唯一归宿是实践的结果。人们对客观事物还有一种与此相异的认识形式,这就是感情认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感情认识,还伴随着人类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即感情思维[5],这种感情反应不是诉诸理智,也不是依靠分析。中国古人“体认”历史,今人或可以认为这是将“理智认识”与“感情认识”合为一体,但其实传统史学并未有意识地区分理智与感情,而是使两者浑然一体,进而形成了独特的认识方式与思维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人设身处地“体认历史”与柯林伍德的“历史重演论”貌同而心异。根据何兆武先生阐释,柯林伍德的“历史重演论”主要主张是:其一,“史家所研究的过去并非是死掉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目前依然活着的过去”[6]20,这是因为“今天由昨天而来,今天里面就包括昨天,而昨天里面复有前天,由此上溯以至于远古;过去的历史今天依然存在着,它并没有死去”[6]21。其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每一桩历史事件都是人的产物,是人的思想的产物,所以不通过人的思想就无由加以理解或说明。要了解前人,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前人的想法;只有了解了事实背后的思想,才能算是真正了解了历史”[6]27。所以,“史学研究对象,确切说来,不外是人类思想活动的历史而已”[6]28。“历史思想总是反思,因为反思是对思想的行为进行思想”,“一切历史思想都属于这种性质”[6]28。其三,“根据历史即思想史的原则,便可以得出另一条原则,即历史知识就是史学家在自己的心灵里重演(re-enact)他所要研究的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6]29。其四,史家如何重演他人的思想呢?柯林伍德说:“这一重演只有在史学家使问题赋予他本人心灵全部能力和全部的知识时,才告完成”[6]29;“它是一项积极的、因而是批判思维的工作”[6]29;“他之重演它,是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进行的,因而重演它也就是批判它并形成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6]29。众所周知,柯林伍德关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重演论”的论断,具有强烈的对科学史学与实证主义进行革命的意图,然而他的“思想”内涵依然来源于科学史学与实证主义。所谓“批判”“反思”,狭义上是指“推理的思想”,广义上也就是“康德所称的‘全部的心灵能力’,即知、情、意均包括在内”[6]43。甚至,他特别强调“历史重演”所凭借的“心灵能力”截然有别于自然科学思想指导下的“心理学”,其理论深处或许包裹着一套特殊形式的“客观心理学”[7]。这就是说,柯林伍德的“思想”与“心灵”几乎完全忽视了对历史起到巨大作用的“非思想的物质力量”以及“人们的本能和各种潜意识”[6]178。简而言之,柯林伍德的“历史重演论”总体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突破西方认识论的笼罩,也没有真正摆脱科学与实证主义的语境;其“思想”依然注重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对于非理性的情感、意志乃至潜意识对个人行为的重要作用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①柯林伍德在论述心理学特别是关于心灵问题时指出:“(心理学)在认识到它自身的合理性时,心灵也就认识到它本身之中有着各种不是理性的成分。它们不是肉体,它们是心灵,但不是理性的心灵或思想。……这些非理性的成分都是心理学的题材。它们是我们慎重的盲目力量和活动,而它们是人生的一部分,因为人生是在有意识地经历着它自己的;但它们却不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而是与思想不同的感知、与概念不同的感受、与意志不同的嗜欲。它们对我们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形成了我们的理性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最贴近的环境这一事实,……它们是我们的理性生活的基础,尽管并不是它的一部分。”参见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第323页。;着意于个人行为背后的思想,对寓于个人行为之中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及其背后的巨大物质力量却不屑一顾。
自从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传入中国之后,余英时、张文杰等学者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重演论”之说与中国传统史学颇有相通之处。余英时指出,章学诚“别识心裁”之说“重史事之内在面”,一方面与柯林伍德的“重演”说比较相似,另一方面与柯林伍德之“先验的想象”可以互通,是指史学家的一种整体性的直觉[8]。张文杰则认为王船山“设身于古”之说①王夫之尝谓:“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岳麓书社,2011,第1184页。,与柯林伍德之“反思”以“重演古人心思”之论是相通的[9]。本研究以为,如果把王夫之、章学诚以及柯林伍德都共同置于现代认识论的视域之下,可以说他们有互通之处,但如果置于各自的文化语境之下,两者互通之说确属牵强。究其根源,在中国传统语境之下,中国古人“不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而把两者看成浑然一体”,“甚少专门的、明显的关于主体如何认识客体、自我对象的认识问题”,所以中国古人往往重“为道”的思想以提升高远的境界,但轻“为学”的思想,轻认识论、方法论、轻理性认识[10]。在思维模式上也体现出一种经验综合型的历史思维,即“极端重视个人的实践经验而不重视普遍的理论原理,强调在个人的亲身实践中求知,而不重视一般的理论分析和逻辑推导”[11]。在此思想文化语境之下,中国古代史学强调的“设身处地”足以说明“历史体认”是一种独特的认识方式与思维模式:它在文献层面强调“信而好古”“无征不信”,即立足文献考证人事;从叙事层面注重典型场景、典范人物及其背后的道德、情感、意志乃至于非理性、反理性、潜意识的表达与渲染,载述内容上既关注个体的历史,又凸显时代的演变及其发展趋势,具体方法则往往采取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或以心印心的方式以获取对历史的“通感”,在总体宗旨上又表现为浑然一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或“承百代之流而汇乎当今之变”。
三、传统史学的叙事“呈现”
列奥·斯特劳斯曾指出:“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人的思维方式都是很不相同的。”在不同的话语系统、认识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之下,其历史叙事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景象。亦即,不同历史背景、文化语境下历史叙事呈现的关切点、呈现的方式方法以及呈现的目的意义各不相同。比如,在古希腊历史文化中,无论是政治、哲学还是神话、历史等领域,其叙事的关切点总体上都离不开言说(修辞、演说、悲剧等)与城邦(民主、政治实践)[1]47;与之不同,中国上古时期的历史文化主要的关切点则集中于德行(天人演变、祖先崇拜、制礼作乐)与通变(古今、变常)。本质而言,历史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由于地理环境、生存生活方式、历史思想文化的差异,使得不同地区的历史叙事呈现也颇为不同。
在中国古代社会环境与文化语境以及“体认”的认识方式与思维模式之下,中国传统史学的叙事呈现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中国传统史学叙事的核心关切点之一是德行、典范与秩序
根据先秦史学者的研究,“德”的内涵大体经历了宗教之德到祖先之德,再到礼仪之德,最后发展为内心修养之德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不少学者指出,甲骨卜辞中“德”有“顺从祖先神、上帝神的旨意之义,因此其实为一种祖先崇拜与上帝崇拜的宗教观,并无后世伦理道德之义”[12]。到了周文王、武王以“德”典祀神天,其宗教性依然相当浓厚;不过,文王把积极主动的恭敬与敬天保民的行为典范纳入到“德”的内涵之中,从而形成了具有制度属性的“文王之典(德)”,故《诗经》《左传》反复赞颂文王之德,所谓“仪刑文王”[13]504“仪式型文王之德”[14]1276。到了周公“则以观德”,虽然继承文王之德的某些宗教因素,但更多的是把待人敬天的礼数以及行礼当中的威仪充实到“德”之中。所以,西周春秋间人们往往以德代礼,以威仪与礼并举。比如,《诗经·大雅》中有“敬慎威仪,以近有德。”[13]548《左传·桓公二年》中有:“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14]89很明显,这里的度数、文物、声教都是周公所制作的礼乐典制的进一步发展,春秋时期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地把它们作为日常行为规范。到了孔子的思想形成时,终于将这种外在的日常行为规范内化为人的内在修养之“德”,“德”终于从宗教图腾、赫赫威仪进入人的内心世界。
其实,不论是宗教之“德”还是文王之“德”,抑或制度之“德”与伦理道“德”,“德”的本质与功能都包含着外在或内在的典范与秩序之意,而“德型”到“德行”再到“德性”内涵的发展演变,皆对中国古代史学形成重人的传统,褒善贬恶、品评人物的传统以及注重教化、世风的传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与之相应,历代史著注重人物取舍、分类载述,本纪载皇帝(皇后)、世家记诸侯、载记霸史述割据称雄者、列传著贤明功勋等,更有班固《古今人表》以德行功业分人为三六九等;又有将人物分为若干类别的,诸如德行、言语、政事、文章、逸民、高士、文苑、隐逸、独行、党锢等。这些分类,且不说对具体人物行事的描述评论,单从篇章称谓都可以看出褒善贬恶的著述宗旨。不仅如此,历史叙事通过叙述各色人物,从正、反两面为世人树立了典型,影响着世风的形成、时势的变迁。近代刘咸炘等学者特别注重从世风、时风、土风、风俗等方面揭示人事与历史的发展演变,其根源即在于此。
(二)中国传统史学的核心关切点之二是天人关系、古今通变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重视“天人关系”,而“天人关系”的内涵丰厚而驳杂:自然之“天”作为历史人事及其发展演变的环境与舞台,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事的成败、历史的发展演变。这表现在两方面,一者遵守“天”行之常,即遵守四季变化、山陵川泽等的客观性及其运行规律,制天命而用之;一者偶然性的“天”,诸如地震海啸、旱涝霜雪、蝗螟瘟疫等都不期然地参与着人类的历史进程。而上古时期,宗教神灵之“天”不但能够干预个人的命运、祸福、吉凶,甚至还左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这从三代帝王虔敬上天、甲骨卜辞事事占卜的记载中可见一斑。
伴随着人之力量的增强,人逐渐以其自身的能力、品德而掌握自身的命运甚至历史的发展演变(“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人之“德”足与天相参(“天道远,人道迩;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接着,人类不仅认识到人之“德”对于历史的发展演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认识到人的感情、欲望、意志等在历史活动中的巨大作用,从而认识到历史的发展演变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又寓于人的欲望之中的历史发展趋势,此之谓时势之“天”。
然而,无论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之中,人总是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更不能完全掌握历史的发展演变,历史总有自身独立运行的轨迹。正如刘咸炘对“究天人之际”的解释,曰:“古今大变有不可全以人力解者。势之成也,天人参焉,故曰际也。”[15]24由此而言,无论是个人的历史还是群体的历史,个人或群体的努力、意志、欲望等对个人或群体的成功与失败起着重要作用;但也总有某种偶然性或必然性参与其间,甚至起到决定作用。
“变”是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一个永恒主题。在中国传统史学家看来,历史充满着变化:人事变幻、制度因革、礼乐损益、朝代兴替、质文递变、三统五德等等,所有这些无不揭示了“变”的永恒性。既然如此,历史如何把握呢?中国史学给予一个解决的办法即“通变”。那么,“变”如何才能“通”呢?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方法是见盛观衰、承弊通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郭象的办法则为“承百代之流而汇乎当今之变”,近人刘咸炘的办法为“察势观风”①刘咸炘尝谓:“事势与风气相为表里,事势显而风气隐,故察势易而观风难。常人所谓风俗,专指闾巷日用习惯之事,与学术政治并立,不知一切皆有风气。后史偏于政治,并学术亦不能详,故不能表现耳。风之小者,止一事,如装饰之变是也。风之大者,兼众事,如治术之缓急,士气之刚柔是也。”参见刘咸炘:《刘咸炘论史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第237页。,而今人王家范则谓“历史的通感”[16]。无论是中国古代史家还是近现代史家,其具体的通“变”之法各不相同,但无一例外的是,其“通变”之法都必然以“历史的通感”为基础。所谓“历史的通感”,就是对时代的精神气韵与历史的脉搏有着深切的感受与准确的体认。这种感受与体认,不是单纯通过史料文献的收集、整理以及对历史人事的理性分析就能获得,它是史家设身处地地贯通历史与现实,把自身的认识情感、意志融入到历史之中,使得情、境、识、意交融,从而洞悉历史与现实。
(三)中国传统史学的呈现方式之一是以“典”带“面”,即通过典型的人物、事件、场景描写展现时代脉搏、历史精神
中国传统史学体例有编年体、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等形式。编年体以时间为经、人事为纬,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中心,外在形式虽有所差异,但记载的中心皆集中于人事。事由人做,人因事丰,中国传统史学无论以哪种体例记载人事,其人与事的记载都集中在典范人物、典型事件与经典场景的叙述。
关于典范性的人物,钱穆曾反复强调:“孟子书里有所谓‘名世者’,在一个时代出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就可用来代表此一时代,所以称之为‘名世者’。”[17]柳诒徵亦曾指出:“史之为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中心人物。而各方面与之联系,又各有其特色,或与之对抗,或为之赞助,而赞助者于武功文事内务外交之关系又各不同。……故其妙在每一事俱有纵贯横通之联络,每一人又各有个性共性之表现。”[18]诸如,文王、周公是西周时代精神的化身,这一时期武王伐纣、周公制礼作乐等则为典型性的事件;春秋时期,五霸迭兴,尊王攘夷、挟天子以令诸侯、争霸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旋律,代表人物即齐桓晋文等;到了战国,变法图强、合纵连横则为这一时期的典型性事件,而代表人物则有吴起、商鞅、苏秦、张仪等;到了秦汉之际,伴随着贵族的衰败以及平民的崛起,刘邦、樊哙、韩信等市井小民则成为时代精神的代表,形成了布衣将相之局。而且,“这些内容又融行事与行事者及其时代背景、历史场景为一体;显然,从如此繁复的任务行事中揭示历史真相,单纯的理论分析是很难奏效的。抑或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古典史家在记述历史的过程中没有按照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去分析历史事实,而是采取设身处地的方法来再现历史的场景”[19]。当然,历史场景的再现,绝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历史场景完整全部地再现,只能采取细节或经典场景的描绘,由此揭示人物个性或时代精神。诸如,司马迁撰写的《李斯列传》,其开端首先描写了“厕中鼠”与“仓中鼠”,而文中的典型场景则是描写其子李由结婚。宾客车水马龙,李斯站在门楼之上不由地感叹自己布衣而登相位,此时虽然他有“物禁太盛”“吾不知税驾也”的隐忧,但没有真正引以为戒,最终被腰斩于市。司马迁描写的这些细节与场景,不仅揭示了李斯为贪图富贵而不顾性命的冒险个性,而且也展现了战国时期整个时代尚军功、崇势力、汲汲于功名的时代之风。总之,诸如此类的典型人物、事件、场景纵横联络,既呈现了人物个性,又揭示了时代精神。
(四)中国传统史学的呈现方式之二是感悟体味、情景交融
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在论述“史德”时就曾指出历史叙事“非区区之明可恃也”,其意就是指史学家认识历史不能单纯依靠智力(区区之“明”),而“情感”可以出入“人事”“是非”之中。所谓: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然而心术不可不虑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于阳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于阴矣。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20]
在章学诚看来,事有“得失是非”“盛衰消息”,而人之性情会“因事生感”,故人对事会“出入予夺”“流连不已”。凡此足以说明古人对于历史,强调投入性情的体认,而非主体对客体的认识。靳西平在翻译吕迪格尔《海德格尔传》的译后记里,引用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的话语:“爱与亲密无间、心心相印与携手共进,才是人生在世最深沉的基础结构。”[21]实际上,以“爱”为代表的人类情感才是历史或人类社会的基本面。因此,认识历史就不能单纯依靠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更需要从人文和情感的角度乃至于将全部身心置身其间。故中国古代史学家称赞“良史”,“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22]万事之“理”、天下之“用”、难知之“意”、难显之“情”等等,显然不是单纯的认识论问题,更需要对历史现实的感悟与体味,没有这种真切的感悟与体味,很难知其奥、解其味。这也就是说,历史叙事既要呈现人物、事件、场景的真相,也要史学家探骊得珠、体解其韵味。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说:“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不要以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动感情的,无论如何,他还是有感情的。实际上,‘理解’一词既孕育着困难,又包含着希望,同时,又使人感到亲切。”[23]这里的“理解”自然属于西方的学术话语,在中国传统学术语境下“体味”“体认”“品味”或许更为合适。
四、余论:突破“对象化”,置身历史中
近现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历史认识论的传入,中国史学界已普遍把历史看作了认识的对象,即通过分析批判史料文献而认识、建构历史,这正如近现代科学“以拷问的方式对待自然”。吴国盛指出,“以拷问的方式对待自然,成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态度”,“实验室作为一个自然拷打室,发现了无数的自然规律,使人类得以有效地征服和控制自然,但同时也造成了人类和自然的紧张关系。长久待在实验室的人容易生长出一颗‘无情’的心,因为实验室内在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你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客观的立场,不能夹杂情绪和主观臆想,不能对研究对象有任何同情之心,否则,你就拷问不出自然的秘密来”[24]168。非常明显,近现代历史学家对待历史、研究历史同样遵循着近现代科学研究的基本逻辑,甚至使用了同样的研究方法。
在将外在世界乃至于内在世界对象化之后,人类把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都设置为自己的对立面进行拷问,这造成了现实世界以至于历史世界的图景化、对象化。“从前人与世界并不是一个表象关系,因而世界并不表现为图景,只是在现代,世界成为人的表象,被图景化、对象化”[24]170。近现代以来的实证史学、科学史学,实质上就是把历史研究对象化、图景化。然而,“世界不是外在于人的东西,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视界。图景化的世界对应的是主体的人。以求力意志为标志的现代人类必定把世界表象为一个图景”[24]170。近现代的历史学研究,正是把人类的历史活动乃至人自身不断地予以对象化,从而把内在于人的“历史”构造为一个又一个外在的知识“图景”,诸如实证主义史学、社会史学、心理史学,甚至后现代史学莫不如是。
然而,包括中国传统史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上古特有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产物,它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上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它自始至终就没有把客观的历史活动与主观的历史认识者(史学家)对立起来,即没有把人的历史活动对象化;相反,而是把历史与现实、历史活动与人的思维、思想、情感融为一体,亦即把历史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来体认。不仅如此,包括中国传统史学在内的传统思想文化也因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话语系统与思维模式,例如先秦时期的《庄子》特别重视“体道”、《易经》有“体仁”之说,《中庸》则有“体物”之论,这里的“‘体’,作为经验方式与认知方式,‘体’不是外在的观看,不是旁观,而是整个的人进入到对象的内部。对象与人始终处于“零距离”,这是‘体’的基本特征”[25]。这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人与对象融为一体即物我一体、天人合一的文化,其话语系统与思维方式自然与此匹配。
由此可知,研究中国传统史学的学者理应首先置身于中国古代特有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形态之中,最大限度地破除近现代以来由认识论与科学思维主导的话语系统与思维模式,尽可能地回归到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语境以及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应当探究历史以把握概念,而不要以概念勾连历史,注意物事和概念渊源流变的错综复杂,通过梳理所有的史事,把握概念的发生衍化以及约定俗成,切忌假定古今中外能够一以贯之,而由名词连缀史事[26]。因为,历史研究不仅仅是理性认识与历史叙事,同时也是感情认识,是传统思想文化意义上的“体认”。这与当今史学的历史叙事转向、倡导感觉主义、概念史与情感史的研究虽相通,却有本质的不同①杨念群先生倡导“感觉主义”注意到了历史研究中“感觉”的重要性;方维规先生认为“概念史”涉及“范畴史”(描述特定术语所关涉的事物起始以来的场域与情状)的研究,但认为“概念史”重在“阐释”即说明基于历史的定义、基本问题及其运用范式,以及“词语史”即论述相关词语的来源(词源),以及它的古今词义的研究;而西方学者所倡导的“情感史”逐渐朝跨学科方向发展,不断加强理论研究、更新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野,并就“情感”在史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达成了共识(参见查理斯·齐卡:《当代西方关于情感史的研究:概念与理论》,《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0期),但依然是把历史中的“情感”进行对象化的研究。这些与古今一体、设身局中的“体认”在认识方式与思维方式上还是迥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