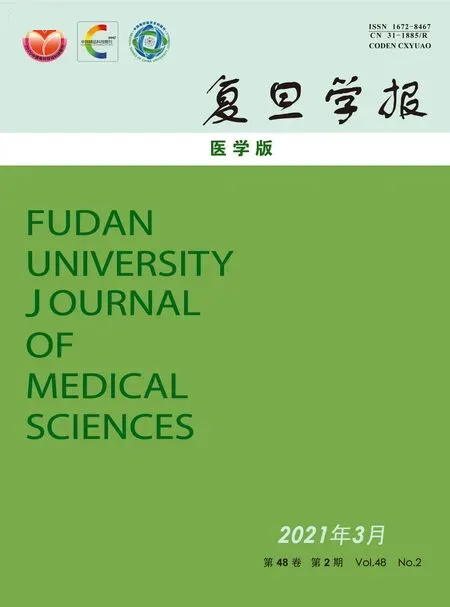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中瓣中瓣技术的应用进展
金沁纯(综述) 潘文志 张晓春 张 蕾 周达新(审校)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 上海200032)
随着人口老龄化,主动脉瓣狭窄的发病率不断增 高[1]。经 导 管 主 动 脉 瓣 置 换 术(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TAVR)已成为外科禁忌、高危、中危症状性主动脉瓣重度狭窄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案,并逐渐向低危人群推广[2]。TAVR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手术,术前精确的评估、术中精准的定位及释放缺一不可。目前国内临床上市使用的瓣膜均为不可回收、无法重新定位的装置,一旦术中瓣膜释放位置不理想,在原有瓣膜中再次经导管植入一个全新的瓣膜,即瓣中瓣技术,就成为一种新的治疗策略。本文对TAVR术中瓣中瓣技术的应用现状进行回顾。
TAVR中需要瓣中瓣置入的危险因素
主动脉瓣反流既往研究显示TAVR术后主动脉瓣反流的发生率大于50%[3-5]。一项纳入45项研究、12 926例患者 的Meta分析显 示TAVR术后 中重度瓣周漏的发生率达11.7%[6]。随着TAVR器械的不断更新和技术的不断进步,2016年PARTNER2研究显示TAVR术后中重度瓣周漏发生率仅为3.7%[7]。
瓣中漏TAVR术中瓣膜释放后的中央型主动脉瓣反流与瓣膜释放位置不理想、型号不恰当或操作时人工瓣叶受损引起的瓣叶开闭失衡有关。显著的瓣中漏无法通过球囊后扩张缓解,其继发的血流动力学改变可能加重患者心衰进程,同时损伤瓣叶的持续暴露也大大增加并发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可能[8],因而往往需要再次置入新的瓣膜。
瓣周漏因瓣膜型号选择不佳引起的患者-瓣膜不匹配、自身瓣膜/瓣环严重钙化、植入瓣膜支架展开不完全、瓣膜植入位置不恰当等原因引起的瓣周漏在各种型号的瓣膜类型中都有报道。轻中度的瓣周反流一般对预后无明显影响,但多项研究显示中重度的瓣周漏是TAVR术后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9]。5年随访发现,TAVR组患者14%合并中重度瓣周漏[10],5年死亡风险高达72.4%[6,11]。一项多中心研究纳入了2 434例接受Edwards sapien瓣膜置入的患者,TAVR术后9.1%的患者合并有中重度瓣周漏,这部分患者随访期间左心室内径明显增加、左心室射血分数、左室质量指数明显下降,而1年死亡风险及心衰再住院率较其他患者明显升高[12]。临床上一般认为,TAVR术后若合并中重度瓣周漏需要及时干预。对于瓣膜扩张不充分或形态欠佳者,球囊后扩张可明显改善人工瓣-自体瓣的贴合以减少瓣周漏。对于瓣膜位置过深或过浅者,除对可回收瓣膜重新调整再释放及对局限性瓣周漏进行经皮器械封堵外,目前常在术中进行瓣中瓣置换术。
瓣膜移位人工瓣稳定是TAVR成功的必要前提,自膨胀瓣膜释放后的最佳置入深度为4~6 mm[13],但是瓣膜尺寸不合适、释放位置不理想、植入瓣膜时心室起搏不充分或面对水平型主动脉挤压影响输送系统与左室流出道同轴性,均可能引起植入瓣膜缓慢向心室侧或主动脉瓣侧移动,这在自膨 胀瓣 膜 多 见[14]。Piazza等[15]在 首 次提 出 瓣 中瓣“俄罗斯套娃”概念时报道1例由于过早停止心室快速起搏引起的CoreValve瓣膜向上移位。及时再次植入瓣膜作为补救措施有利于及时挽救血流动力学,并减少瓣周漏风险。
其他并发症TAVR术中其他灾难性的并发症包括瓣环撕裂、左心室穿孔、主动脉根部撕裂等,瓣中瓣技术能够在最短时间进行干预并稳定血流动力学,故被认为是一种潜在可行的抢救策略。TAVR术中依次嵌套释放两个瓣膜的技术用于处理术中瓣环撕裂、室间隔穿孔均有成功案例[16-17]。针对外科瓣衰败,也有急症下TAVR瓣中瓣应用的报道[18-19]。
瓣中瓣的预后既往研究显示,术中应用瓣中瓣技术治疗急性TAVR失败(最常见于主动脉瓣反流)的发生率为1.4%~6.7%[20],且在瓣环较大的患者 中 比 例 更 高[21]。VitaFlow与Venus-A两 款 国 产瓣膜术中瓣中瓣的发生率相较稍高,分别为10%[22]和13.3%[23]。但 自2008年Ruiz等[24]首 次 报 道TAVR术中瓣中瓣技术以来,针对该手段的随访研究仍然有限。
意大利一项纳入663例患者的CoreValve注册研究显示,24例(3.6%)患者因严重瓣周漏接受了第二个人工瓣置入,术后即刻及1年随访时跨瓣压差与单个瓣置入组相似,30天内及1年的全因死亡率(0vs.5.6%,P=0.238;13.7%vs.4.5%,P=0.230)较普通患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其中1例瓣中瓣患者的随访病例报道显示3年随访期内未见瓣膜血栓/栓塞事件[25]。但是,该研究结果同时显示术后30天内,瓣中瓣组患者接受永久起搏器植入率更高(33.3%vs.14.5%,P=0.020)。Toggweiler等[26]对760例接受Sapien/Sapien XT瓣膜置入的TAVR患者的分析发现,21例因瓣膜功能不佳或移位而接受瓣中瓣置入,术中瓣中瓣技术成功率达90%,另2例患者因瓣膜栓塞失败。术后30天及1年随访瓣中瓣组患者死亡率与非瓣中瓣组相似(14.3%vs.7.3%,P=0.23;24%vs.22%,P=0.37),但是两组患者的瓣膜功能参数在术后1年随访时出现明显差异,瓣中瓣组患者平均跨瓣压差更高[(15±4)mmHgvs.(11±4)mmHg,P=0.02],左心室射血分数 降 低(46%±12%vs.58%±12%,P<0.01)。Makkar等[27]对PARTNER研 究(2 554例,sapien瓣膜)中63例接受瓣中瓣植入的患者进行统计分析,其中62例因此避免了急诊外科手术。但与既往研究不同是该研究中主动脉瓣中瓣反流是进行瓣中瓣置入主要原因(49.2%)。该研究随访结果显示瓣中瓣组主动脉瓣跨瓣压差、瓣口面积等瓣膜功能参数在术后及1年随访时与单瓣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瓣中瓣组1年全因死亡率(33.3%vs.21.0%,P=0.02)、心血管相关死亡率(24.4%vs.9.1%,P=0.0005)明显高于非瓣中瓣组,且再住院率达25.5%,但卒中发生率及NYHA心功能分级未见明显差异,进一步的多因素回归显示瓣中瓣是心血管相关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子(HR=1.86,95%CI:1.03~3.38,P=0.041)。
虽然目前的小样本研究数据均提示瓣中瓣技术作为避免急诊外科手术,即刻干预TAVR瓣周漏的手段是安全且可行的,但研究样本量仍很小,且观察期最长为1年,瓣中瓣技术的远期预后仍不明确,有待进一步的大规模临床研究证明。
瓣中瓣的技术难点因需要依次嵌套置入两个瓣膜,如何保持嵌套瓣膜的位置稳定及形态正常、避免冠脉阻塞和术后主动脉瓣跨瓣压差异常升高成为了TAVR术中瓣中瓣技术的三大挑战。
瓣中瓣位置稳定及形态正常既往大部分文献报道TAVR术中置入第二个瓣膜时往往选择与第一次瓣膜型号相同的瓣膜,但是目前尚无关于TAVR术中瓣中瓣型号选择及释放定位的官方指南。Midha等[28]进行的一项体外模拟瓣中瓣的研究结果显示,术中第二次若置入自膨胀瓣膜,其最优位置仍然是主动脉瓣环平面最低点,且建议选择大一号的瓣膜尺寸;但是若二次置入的是球囊扩张式瓣膜,则优选瓣环上方6 mm处释放。该研究在模拟体内已置入瓣膜环境的基础上,综合不同二次瓣膜类型、型号和展开位置对瓣膜功能参数、瓣膜栓塞及瓣周漏的风险,给实际确定TAVR瓣中瓣的部署位置提供了依据。虽然文献支持瓣中瓣二次植入的瓣膜理想位置仍然是主动脉瓣环平面最低点,但是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对于瓣膜植入过深导致瓣周漏的患者,即使是二次植入的瓣膜和原来瓣膜位置相同,也是具有缓解瓣周漏的作用。这是因为二次植入的瓣膜可使首次植入瓣膜的人工生物瓣外翻贴合在二次植入瓣膜的支架外面,使其外包裙边明显加长,从而阻止瓣周漏的发生。Edelman等[20]进一步提出,若一次释放不佳的瓣膜为自膨胀瓣膜,则推荐后续选择球囊扩张瓣膜完成瓣中瓣置入,这是由于球囊扩张缓慢,瓣膜位置移动可能性小,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同时球囊扩张瓣膜较高的径向支撑力有利于进一步充分扩张先前的自膨胀瓣膜以利于自身瓣膜支架的完整展开。随着瓣中瓣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定适用于瓣中瓣置入、具有较小交叉轮廓与强大复位能力的新型瓣膜可能问世。
冠脉阻塞冠脉阻塞及心肌梗死是TAVR的严重并发症,因此术前CT精确评估冠脉高度且术中实时进行主动脉根部造影以确认冠脉血流通畅度是预防该并发症的前提。瓣膜的理学特点及解剖学参数(内径、小叶高度等)对手术成功至关重要。有高危冠脉栓塞风险的患者,一旦使用瓣中瓣置入,两层瓣膜支架相互交错的网眼进一步增加了TAVR术后导管寻找冠脉开口的难度。对此,有学者提出可预防性置入支架。Maggio等[29]曾报道1例外科衰败患者进行TAVR瓣中瓣时,预先置入未展开的支架于冠脉,在快速起搏下球囊扩张瓣膜时出现一过性心动过缓和严重低血压,迅速将冠脉预置支架拉回并部署在冠脉开口部位,及时解除了血流动力学压迫并成功释放瓣膜,提示TAVR瓣中瓣技术中冠脉保护支架的潜在可行性。
跨瓣压差恶化一般认为,瓣中瓣置入后的主动脉瓣跨瓣压差不能高于手术最初获得的压差。瓣中瓣植入技术是在原有首次植入瓣膜的基础上再植入一个瓣膜,二次植入瓣膜可能面临受到首个植入瓣膜的限制导致膨胀不全,进而产生跨瓣压差恶化的风险。目前大部分研究显示瓣中瓣置入后的主动脉瓣跨瓣压差并没有明显恶化或仅有轻度升高[24-26],但仍不能排除极少数患者植入瓣中瓣后跨瓣压差明显恶化的情况。在排除必须选择小型号瓣膜或特殊主动脉根部结构的特殊条件下,跨瓣压差的不明原因增高可能提示后选的瓣膜型号与患者不匹配。
PARTNER 2瓣中瓣注册研究[30]显示,平均压>20 mmHg的患者1年生存率明显低于平均压<20 mmHg的患者(7.7%vs.16.7%)。但此研究纳入的人群是外科生物瓣衰败人群,并非TAVR术中瓣中瓣人群。TAVR术中瓣中瓣技术可能引起的跨瓣压差增加对预后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其他问题瓣中瓣置入后,残余瓣周漏仍然是TAVR术中关注的焦点。大部分TAVR术中超声心动图随访结果均显示瓣中瓣技术对瓣周漏的解除作用,少数瓣周漏未明显缓解的病例可能与治疗策略的错误选择有关。TAVR术中术者仍需要根据手术最初瓣周漏形成的原因及分布来选择瓣中瓣置入还是经导管器械封堵处理瓣周漏。
起搏器植入率增加也是TAVR瓣中瓣研究的重要发现[27,31]。因此,在瓣中瓣术中谨慎选择瓣膜尺寸,避免型号过大及默契配合稳定二次瓣膜释放位置及置入深度对术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由于两个或多个瓣膜嵌套置入,目前常规的TAVR术后抗血小板策略是否合适这类特殊人群仍不明朗。Eitan等[32]通过MRI筛查发现,瓣中瓣置入组患者出现术后微栓塞的比例低于非瓣中瓣组(73.2%vs.51.2%,P=0.005),这可能与研究中瓣中瓣组患者年龄更低及后扩张少有关。
结语虽然瓣中瓣技术的即刻安全性及有效性在多组小规模TAVR人群中得到证实,且多项研究显示对外科衰败的生物瓣进行经导管二次人工主动脉瓣置入术较再次外科干预患者预后良好[33],但目前尚无指南推荐瓣中瓣置入术为TAVR术中处理TAVR失败的首选治疗手段,同时TAVR术中即刻瓣中瓣技术的长期随访结果仍待完善。
作者贡献声明金沁纯、潘文志课题设计,论文构思、撰写和修订。张晓春,张蕾文献调研,论文修订。周达新论文终审。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