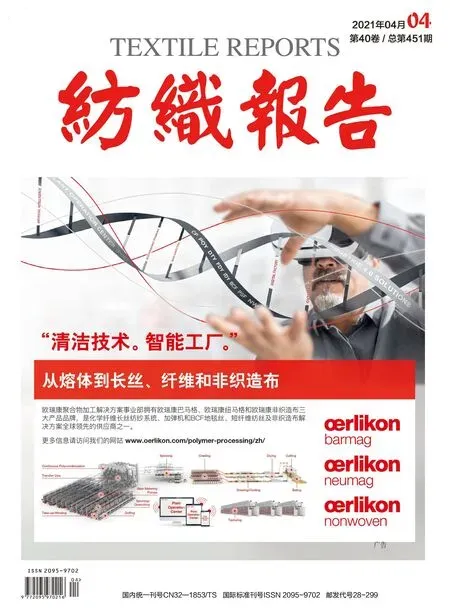东西方“繁复风格”服饰对比研究
——以拜占庭时期与唐代时期对比为例
冯晓桐
(沈阳师范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处于盛世的大唐(618—907年)可以用很多词语来形容,如疆域辽阔、经济繁荣,对外来文化不过分排斥和抵触,兼收并蓄,凭借自身的文化自信迎接各国使者,如胡商来大唐交流和贸易。不论是经济还是思想,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唐朝开放最明显的表现之一为唐朝女性的服饰。
拜占庭帝国(395—1453年)是指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后的东部改为拜占庭帝国。拜占庭时期的艺术,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地跨欧亚两洲的君士坦丁堡为首都,既继承和发扬了古罗马、古希腊古典艺术的自然主义,又融合了东方艺术的抽象装饰特质,形成了西方史上独特的艺术形式。
在丝绸之路贸易背景下,拜占庭帝国作为丝绸之路亚洲部分的最终抵达地,使得看似不相干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两个帝国,服饰风格既有艺术表达上的共性,也有各自国家影响下的个性[1]。
1 服装风格形成的原因
服饰是受社会、环境、政治影响的外化表现。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也是版图面积最大的国家,声誉远扬海外。唐朝的疆域在极盛时期东起朝鲜半岛,南抵越南顺化,西达中亚,北包括贝加尔湖至叶尼塞河下游。唐朝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有很多,如突厥、回鹘、室韦、契丹等。唐代的多民族文化融合是唐代兴盛的原因之一,也为接纳外来民族和外来国家的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唐代开放包容的政治制度在允许胡商来唐进行贸易的同时,还允许周边国家如新罗、日本的使者前来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和手工艺等。在此社会背景下,唐代文化在丝绸之路的影响下还吸纳了许多西亚文化,在服饰图案上有具体的体现。因此,在与少数民族和他国使者的不断融合中,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抑或是服饰,都同之前的朝代有了较大不同。拜占庭服饰继承了古罗马、古希腊的特点,神性优先人性,艺术风格上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由于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优越的地理位置,领土也曾包括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极盛时领土还包括意大利、巴勒斯坦、高加索、西班牙南部沿海和北非的地中海沿岸,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君主制国家,其地理位置为融合东方传统文化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和便利性,服饰风格也受到了建筑的影响。当时,拜占庭将基督教作为国家唯一的宗教信仰,艺术是为教会服务。基督教堂内部的镶嵌画装饰色彩缤纷绚烂,这种色彩表达也在服饰上有所体现[2]。
2 拜占庭服饰与唐代服饰“繁复”的成因及表现形式
2.1 “繁复”与物质基础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充满活力且大胆的时代。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生产和纺织技术的进步以及对外交往的频繁等,促使服饰空前繁荣,“丝绸之路”也为唐朝不断地注入生命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社会物质丰富极大的基础上,人们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尤其是对美的定义。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打破了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固有形态,倾向于“大”“多”和“富贵”的感觉,追求个性、妩媚、潇洒之美。唐朝帝王如玄宗、德宗、宣宗三帝追求美色声乐而好宴,对奢侈的社会风尚影响深远,分别扮演初始、复兴与推波助澜的角色,影响到世人对“美”的看法,进而自然地多元化、开放化、享乐化,逐渐导致唐朝的女性日常服饰从一开始的小袖短襦到盛唐晚唐时期的大袖宽襦,下配曳地长裙,双臂搭一披帛,着刺绣锦履,多数妇女的裙子集六幅而成。据《旧唐书》记载,六幅相当于今天的3 m以上。除六幅以外,还有用七幅、八幅制裙者,不仅影响活动,还浪费衣料,因此受到了朝廷的干涉。由此看来,唐代的经济发达不仅存在于皇室,社会上也是从上至下的富裕。蓬勃发展的经济与奢侈华丽的社会风气,将“服饰美”的理想境界推到大胆的追求,对女性的伦理纲常、礼教观念影响较弱,如盛唐时期,贵族女子着露出半个胸脯的袒领服以及晚唐时期流行的仅以轻纱蔽体、不着内衣的纱罗衫,“蝉翼罗衣白玉人”正是对纱罗衫的写照,当时还流行一种散幅裙,多幅纱绢遮蔽下体而不缝合,由此可以看出唐朝纺织业技术的高超水平。女子着戎装,模仿男子装束,爱好胡服骑射,这些都是在物质基础极大丰富后形成的开放的审美现象[3]。
在遥远的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是丝绸之路亚洲部分的终点,以“奢华时代”著称。此时的服装款式却与唐朝相左,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使服装款式厚重、呆板、僵硬,皇室与平民服装款式基本相似,差异在于面料的质地及皇室会以刺绣、珍珠和红绿宝石等在衣身排出图案装饰(来源于镶贴艺术),也是富贵和权力的象征。凯撒大帝曾穿着丝绸长袍看戏,导致罗马贵族男女都以穿着丝绸为荣。拜占庭的纺织业发达,但不具备中国丝绸的制作方法,早期进口的丝绸有限且价格昂贵,曾有一磅紫色丝绸可以换一磅黄金的说法。丝绸也在一时间成为身份的象征,从上至下狂热地追求丝绸制品,需求量巨大。拜占庭设法学习了养蚕缫丝,还将其作为外交礼品,可以说是拜占庭帝国将中国丝绸传向了西方诸国。在整体服装形象上,还是保留了欧洲尚武的服饰形象,主要穿着窄袖贯头式长袍,外配一块长方形织物,从左肩绕至右肩用别针固定,男女均如此穿着,女子在长袍腰部系带以示身形。男子腿部会配以长筒袜、短袜或缠腿布,依然是具备战服特色的样式,搭配具有东方风格的矮帮尖头鞋,虽款式呆板,斗篷与长袍不如古罗马、古希腊那般自然垂下而营造出自然褶皱美,但动态下衣裾边缘的曲线随意而又具有层次感,穿着者的行动不受限,重装饰下又尽显华贵。这些情形有别于同时期欧洲地区的服饰,创造出一种融合东西方又充满华丽感的服饰美。
2.2 “繁复”与服饰色彩
唐朝服饰在色彩上远超前代,可以用绮丽多姿来形容。中国人对穿衣颜色历来有诸多讲究,除朝廷规定外,百姓的服色也表现了生活水平、心理状态以及情绪。唐朝的年轻妇女最喜爱红、绿、黄等鲜艳颜色,刺激视觉感受,以鲜亮的颜色绣出精美的图案来追求富贵、华美的服饰形象。唐朝染红裙的颜料主要是从石榴花中提取而成,因此,也被称为“石榴裙”。与红裙相比,绿裙也极受妇女青睐,又被称为“翡翠裙”。黄裙以郁金香根为染料,郁金香根又是香料,染成裙后穿着于身芳香诱人,很受年轻妇女的欢迎。最具特点的是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曾有一条百鸟裙,是由多种鸟毛和丝制成,从各个角度观看,此裙均呈现不同色彩,该裙据《旧唐书·五行志》记载计价百万。可见当时女子为追求美,不惜一掷千金。
拜占庭艺术为宗教服务,宗教性的建筑感染了服装色彩,融合了教堂内部的镶贴艺术。色彩的象征性也十分明显,如白色象征纯洁、蓝色象征神圣、红色象征基督的血和神的爱、紫色象征高贵和威严、绿色象征青春、黄色象征财富,而皇室犹爱紫色。一件衣服表现多种色彩是拜占庭时期女式服装的特点之一。宫廷中最喜爱的色彩搭配是红紫色的底上刺以金色绣品,红色和紫色只有皇室成员可用,富贵华美的风格尽数体现在色彩上。
两国对于着装的色彩有共同性,即喜好鲜艳色彩。从服饰心理学上来说,服饰色彩对情绪的影响是直接的,选用的着装配色反映出唐代和拜占庭帝国着装者对于当下的生存环境是否满意以及前途是否光明。笔者认为,着装行为的审美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从小的教育、生长环境、家庭氛围的影响,不是因为一时的兴趣而着装,而是糅合了生长经历的着装形象,是基于客观与主观的碰撞产生的审美心理和着装形象。
3 结语
中西方传统文化、价值观、审美特征以及宗教信仰的差异性形成了不同的服装文化。通过对比发现,中西方服装相似的风格、不同的内涵正是现代服装缺失的部分。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中西方服装逐渐融合为单一样式,是抛弃了传统文化的表现。因此,应在中西方服装融合的过程中,提取传统元素与现代服装相结合,呈现出新时代的服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