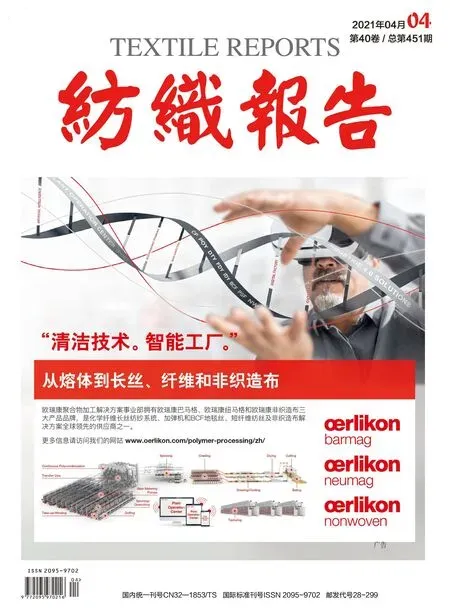唐代儿童服饰文化与形制特征
刘 欢
(岭南师范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广东 湛江 524000)
在中国古代绘画中,以儿童为入画题材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画像可以推测出古代儿童服饰特征与文化,为当代儿童服饰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在两宋时期,婴戏题材较为丰富,而唐代以前的图像不多,从唐代开始清晰易辨。画像中呈现的服饰一方面反映了开放经济影响下成人对孩童的成长与关怀,另一方面蕴含了当时的宗教思想。描绘孩童的画家有张萱,虽然在唐代还未形成独立的儿童绘画,但张萱画孩童既有童稚形貌,又有活泼神采,从宋摹本的张萱《捣练图》中可窥见一斑。
1 唐代儿童服饰的文化属性
通过梳理唐代儿童图像发现,唐代儿童服饰大体上呈现简洁、实用的特征,同时受胡服的影响,唐代儿童服饰独具特色,唐代经济的发达、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唐人对儿童的包容及人性化、至美至善的成长观,在服装上则更多体现其合理、科学的功能性和美观装饰作用。唐代儿童服饰的审美趣味及其受到的影响出发,本研究认为唐代儿童服饰受到3种文化的重要影响,分别是儒家文化、胡风和佛教的影响。
首先,以儒家文化为基础。李唐立国之后,延续了隋代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度,对后世中华文化影响极深。儒家的兴盛使得对孝行的提倡再次成为社会的普遍认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儿童成为社会关注的对象,也反映在唐代诗歌中。据统计,《全唐诗》收录了73首儿童诗,包括“儿童自己创作的诗、描写儿童的诗、寄赠儿童的诗”等[1]。如白居易的“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贾岛的“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都是千古名句。此外,还出现了天才儿童诗人,如晏殊八岁就被誉为神童,《新唐书》载:“玄宗封泰山,晏始八岁,献颂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张说试之,说曰:‘国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请旁午,号神童,名震一时。”唐代美术考古实物中丰富的儿童图像及其反映出的服饰文化,正是在唐代儒家文化流行的背景下,人们追求“子孙昌盛”和重视儿童教育社会现实的缩影。
其次,胡风的浸润。唐代,开疆拓土版图达到了历史巅峰,在唐朝统治下,有很多胡人把“胡风”带入了长安,带入了唐代社会。尤其是在盛唐文化中,以“胡风”为审美的社会尺度,在长安街头流行胡食、胡服、胡语、胡坐等,上层统治阶级使用“葡萄美酒夜光杯”,李白笔下有“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当安归”。胡服、胡妆在社会中广泛流行,元稹写道“女为胡妇学胡妆”,对社会习俗影响深远。在这种背景下,儿童服饰也受到了胡风的浸润。如前文提到的儿童所穿的皮靴就是来自胡风,童子的披帛更是受到印度的影响。敦煌莫高窟第361窟中唐时期化生童子的腰鼓是来自西域诸国的乐器。莫高窟第12窟中晚唐时期化生童子的服饰是“交领窄袖”的胡服,其抱持的“筚篥”等乐器也是来自西域地区。《太平御览》卷五百四引《乐府杂录》云:“筚篥者,本龟兹国乐也,亦名悲篥,有类于笳也。”
最后,佛教的影响。童子与莲的组合受佛教的影响较大,亦体现了唐代人赋予儿童服饰的寓意,并增添了神秘的色彩。较多例子表明,佛教石窟壁画是唐代儿童服饰图像的重要载体,表明二者之间的关联。如敦煌壁画中,儿童图像非常丰富。又如在佛教故事绘画中,童子本身就是“化生童子”和“诞生佛”内容绘制所必需的题材。在唐代“净土宗”流行的背景下,在壁画或绢画描绘的佛国世界里,童子形象又是千变万化的佛国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童子们或披帛舞蹈,或攀登莲花;或双手合十,虔诚礼佛;或演奏胡乐,令人陶醉。佛教的悲悯之心和童子的天真无邪形成了对应,影响了石窟观赏者的宗教体验。
总之,唐代儿童服饰呈现出以上3种文化的综合影响,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兼容并蓄的艺术特色,成为中华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们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悠久灿烂的文化、实施“文化自信”战略、为当代儿童服饰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2 唐代儿童服饰形制
通过唐代儿童图像及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可窥见中国唐代儿童服饰的基本形态。唐代儿童服饰形制包括首饰、帽子、围涎、披帛、襁褓、兜肚、裲裆、圆领袍衫、短衫、襦裙服等,既满足了儿童身体发育的需求,简洁、实用,又体现了多民族服饰文化融合的影响,款式上丰富多彩且独具特点。
2.1 饰品
头部、身体各部位佩戴的装饰品,大致可以分为首饰、帽子、围涎、披帛,具有实用功能或装饰功能。璎珞和虎头帽可作为唐代儿童饰品的代表,在考古资料中时有发现。现有的儿童图像资料显示,唐代儿童佩戴的首饰主要有项圈、手镯、脚镯、长命锁和项链等[2]。项圈有金属素圈,另在儿童和女性之中广为流行的是镶饰珠宝的璎珞。缨络,即璎珞,可佩戴在不同部位,戴在脖子上的叫“璎”,戴在手臂、小腿等处的叫“珞”,源于佛像颈脖间的装饰。在敦煌莫高窟第361窟中唐时期的伽陵频迦伎乐与化生童子画像中,人首鸟身的伽陵频迦头梳发髻,半身赤裸,张开翅膀,身上佩戴璎珞,双手作举高状态,敲击圆形铜钹,而右侧上方童子亦全身佩戴璎珞,有项饰、胸饰、臂钏和腕钏,童子腰间一鼓,画像呈现出精致、丰富多彩的唐代菩萨装饰风格。同时,唐代儿童有佩戴长命锁的习俗,是对子女健康长寿、驱邪消灾的祈愿,展现了唐人对孩童的关怀呵护。
帽子在唐代时期已成为中原汉族传统的儿童服饰之一,具有御寒的功能性和装饰性。唐代儿童所戴帽式均无帽沿,有多种帽式,如尖顶、圆顶瓜皮帽及虎头帽。在扬州唐城和1978年常州劳动路分别出土了两名手抱球且头戴圆顶瓜皮帽式的童子俑,童子手上均抱有一圆球作戏耍状态。西安韩森寨唐墓出土的婴儿俑头戴虎头帽,此帽源于佛教中的护法天王形象,可见虎头帽是一种广受唐代儿童喜爱的帽式,亦可窥见唐人借神灵来庇佑儿童健康成长。虎的形象具有丰富的民俗意蕴,形象威武又憨态可爱,既可辟邪镇宅,又可祈福保佑,虎头帽倾注了唐代成人对儿童的深情呵护,又寄予了对儿童茁壮成长的祝福。亦有学者认为,唐墓中的虎头襁褓俑、童子杂技俑、童子洗澡俑都属于戏弄俑,是唐代生活丰富多彩的表现[3]。
围涎也叫“围嘴”,最早可追溯至汉代,是婴幼儿服饰中最常见的一种功能性强的服饰品。西汉扬雄所著《方言校笺》卷四提及“繄袼”一词,晋代郭璞标注:“即小儿涎衣也。”[4]围涎早期以实用功能为主,至唐代以造型多样、实用美观并存,围涎上的装饰纹样变化丰富,题材多样,不仅给人们带来视觉上的愉悦和精神上的享受,亦有较强的文化传递和风俗体现,为当代设计留下了珍贵的参考资料。据资料分析,唐代围涎纹样装饰有单一或重复的几何形、植物形、动物形和人物形,色彩大胆,对比性强。初唐第329窟西龛外侧中的化生童子,下方童子颈部戴橙色围涎,绣有装饰花样,右手抓握莲茎,左手则随意朝下,双脚穿同色柔靴,左脚悬空,右脚踩莲,画面生机勃勃,突显孩童天真可爱的性格。晚唐第173窟化生童子画像中,有一赤裸上身、肩部饰披帛、下身着裤的莲花童子形象,即化生童子。在佛教中,化生是生命的诞生方式之一,指无所依托,借业力而生。童子与莲的画面组合,或手持莲花、或脚踏莲花、或处于莲花之上,莲花是佛教的象征,是儿童纯真圣洁的象征,是对新生命的祝福和对往生者的轮回。
2.2 服饰
古代“衣”的服装形制,一般指上衣或上下相连的款式,唐代儿童所着襁褓、兜肚、裲裆、圆领袍衫、短衫、襦裙服等皆属童衣范畴。婴儿从一出生便穿襁褓,是唐代育儿习俗。“襁”指背婴儿用的布幅或宽带,长一尺二寸至二尺,宽度为八寸左右。“褓”指用以包裹小儿的被子,襁褓婴儿也指未满周岁的孩儿。在画圣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画面第三段《释迦牟尼降生图》画面中,可看到净饭王怀抱的婴儿清晰而完整的襁褓形象,画面以佛教题材表现人物形态和服饰。在西安韩森寨唐墓出土的长约10 cm的婴儿陶俑中亦有发现,此婴儿俑头戴虎头形帽子,身着一层宽带圆领襁褓,身前系成蝴蝶结状于中间,婴儿睁着双眼安静地被包裹在襁褓中。经梳理可知,唐代襁褓是具有保暖功能和人性化的服装形制,将婴儿包裹在襁褓中,可使其产生安全感并易入睡,促进婴儿身体的生长,还可使得腿部保持平直生长,保证身体健康,亦有学者把此俑归纳为戏弄俑,认为是多姿多彩的唐人生活的体现。
兜肚,即“肚兜”,是一种贴身穿着、护住胸部至腹部的布块,具有保温、护腹、裹肚的实用功能,用一条或两条带子系在脖子上,从腰处将两条带子系于后背。基于成熟的唐代丝织工艺技术,肚兜不但品种多样且绣有精美的图案。最早发现的唐代儿童所着兜肚画像,是在湖南长沙出土的童子执莲纹执壶中,壶上绘有面庞丰满、活泼可爱的童子腰围兜肚,童子手持一支莲花,多条彩带绕臂部随风飘扬。唐代儿童所着兜肚形状多样,有圆形、半圆形、方形和菱形,肩部分有带和无带系连,虽有形态之别,但都只见前身裁片而无后身裁片,穿时后背裸露,仅以细带系之。与兜肚形制接近的还有裲裆,类似现代的背心、马甲,前后各有一裁片,两者的区别在于兜肚为贴身穿着,裲裆贴身穿或穿在贴身衣物外层皆可。法国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馆藏的唐莲花化生童子图[5],画面中七童子分别露出生殖器站在莲花台上,其中,六童子上身穿裲裆衫,而另一童子则赤裸身体,这就是卵生而非胎生的超自然“莲花生”。在敦煌壁画第126窟的方形覆斗藻井中亦出现莲花童子的形象,两孩童身穿白色裲裆衫在中心方井举手并舞,莲花环绕童子,童子贴身衣物、裤子颜色与莲花相呼应,共五色。卷草纹、联珠纹、龟背纹、鱼鳞纹等环绕藻井四周,形成清新典雅的藻井。童子与莲的组合明显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并增添了神秘的宗教色彩。
在唐代,不同年龄段的孩童穿着略有差异,如4岁以内的幼童活泼好动,着装较为随意,有时直接赤裸上身,或只穿下装,或只穿贴身衣物。当孩童逐渐长大时,穿戴呈现大人服装的特征,即缩小版的成人服装,服饰形制有交领袍、圆领袍、短衫和襦裙服等。其中,男童穿圆领袍、交领袍、短衫,女童则多穿襦裙服。受唐代成人女性穿男装的影响,亦有女童穿男童袍服的现象。袍服的袖身多为窄袖,增强了儿童活动的便捷性,带有人性关爱的情怀。圆领袍的服饰形制为圆型领子、窄身袖子、衣身长及腰,下着裤装和衣身及膝盖处上下,衣侧开衩,属上衣下裳连属的深衣制。在何家村孔雀纹银方盒画像中发现,右侧童子穿着交领花纹短袍,袍边装饰细带,下穿简单裤子;左侧童子穿着素色短款上衣,下着短裤,双手上举,身后一只小狗(古人称为猧)。画面所绘的是两童子与猧共同玩耍的场景,儿童的衣着较为华丽,应该是出自贵族家庭,可见是对贵族儿童日常生活的一种描述。在长安南里王村韦氏家族墓墓室东壁北侧宴饮图中,右侧童子穿着圆领窄袖长袍,左侧童子穿着短上衣,下着裤装,右臂弯曲上举,意欲扑蝶。另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在《祭小侄女寄文》中道:“侄辈数人,竹马玉环,绣襜文褓,堂前阶下,日里风中,弄药争花,纷吾左右。”[6]其中,“襜”指短衣,“绣襜文褓”指穿绣花的短衣襁褓。
在儿童竹马游戏的图像资料中,穿着袍服游戏的儿童较为常见,如在莫高窟晚唐第9窟西侧出现了身穿赤色为主、花饰袍服的儿童,显得充满活力。在敦煌佛爷庙湾36号墓中也出现了一名儿童上身着红白圆领短袖衣,下身全裸骑竹马嬉戏,身旁妇人则身着红袍白裙的图像,这些均说明唐代儿童穿着袍服广为盛行。在敦煌莫高窟晚唐第138窟的《仕女童子图》中,仕女怀中的幼童身穿黑绿色花卉点缀的襦裙服,仕女身边的两个幼童亦穿着同色襦裙服,一起游玩嬉戏,展现了欢乐气氛。儿童与仕女一同出现在画像中的资料较为常见,两者相处融洽、亲密无间,从服饰上看,该形象为当时贵族家庭妇女,其服饰与孩童服饰色彩呼应,孩童身上的花色图案与贵妇身上的素衣繁简对比,协调其中,表现了贵妇怜爱子女之情。以上图像中儿童所着服饰与成人服饰形制相同,男童均为圆领、交领窄袖袍;女童则多穿襦裙装,亦有穿胡服、男童服饰的现象,如在画家张萱《捣药图》(宋代摹本)中有一名脸型、身形圆胖,上身穿着桔黄大翻领胡服,下身穿着白色长裤的小女孩在练习穿梭,画面充满活泼的生活气息,由此可见,唐代女性着胡服、穿男装的服饰形制已然在儿童服饰中转化,也正是受到了唐代包容、开放的社会风尚影响。
裤子的形制在唐代盛行受胡服的影响较为明显,其中,以背带裤为特色的服饰形制简洁、方便,实用功能性显著,裤腰上装有挎肩背带的裤子,背带可满足儿童成长中身体的发育需求,裤口紧窄。目前发现唐代画像中身着背带裤的童子较多,如在敦煌莫高窟第119窟《七童子采花图》中绘有7名身穿赤红、绿色及黑色服饰的孩童,穿着窄身袍服、短衫及不同长度的裤子形制。在丁卯桥童子文三足银壶中,两名童子身着宽松背带裤,背带短,裤子腰线高,裤身遮住胸腹部,壶底部装饰一层浮雕状的莲瓣纹饰。新疆阿斯塔纳唐墓出土中发现身穿背带波斯间色竖条纹裤子的孩童图像,小脚裤口式样,脚穿红色靴子,左边童子右手高举,左手抱猧子,这种间色条纹窄口裤从波斯传入新疆至中原内地,并在女性和儿童间流行。从以上画像中的儿童形象来看,唐代儿童不论性别,多穿长裤且裤筒舒适,夏季的裤子是长及膝处的短裤,春秋冬裤则长及脚部。在敦煌壁画中亦发现了许多赤裸身体和穿短裤的孩童,如晚唐第196窟南壁《阿弥陀经变》中,正是数名上身穿着短袖衫、圆领袍衫和交领窄袖袍衫,下身穿着中裤、长裤的孩童在戏水嬉闹,或骑栏杆,或伸手拉水中其他童子,或扶栏杆,画面纯真,充满童趣。再比如,盛唐第148窟《药师经变》中见3名童子在水中游玩,下方右侧童子身着背带长裤、脚欲踩荷叶,左侧童子和上方童子下身均穿着绿色短裤,共同嬉闹,画面充满生机。在敦煌壁画中,可发现儿童较喜爱戏水。无拘无束是孩童的天性,从中也可看出唐代成人健康、宽容的孩童成长观,这与当时的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风尚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这种变化反映在儿童服饰上,则体现为轻松、简便、舒适、洒脱。
3 结语
对绘画、器物及纺织物中的儿童画像进行研究是一项长远而有意义的工作,分析古代儿童家庭的关系、宗教的象征意义及儿童生活游戏等,可窥见中国古代不同历史阶段的儿童服饰,亦是一种研究尝试。本研究对唐代儿童服饰进行综合研究,力图发掘唐代儿童图像中所体现的服饰及装饰品特征,探究其服饰的基本形态特征,为中国古代儿童服饰文化增添一抹重要的色彩。通过对唐代儿童图像的梳理,可窥见唐代儿童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的背景,发掘这些图像中所体现的儿童服饰面貌及唐人的育儿观。一方面,受成人服饰形制的影响,唐代儿童服饰在造型、面料、图案、色彩及工艺装饰上,一定程度地借鉴了成人服饰的特点,尤其是在礼制严谨的场合;又因年龄、生理特征、心理特征、生活环境等特殊性以及唐代开放进步的文化,影响了成人对孩童成长观念包容的态度,其服饰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人性关怀和呵护。如根据其自身生长特点进行调整,具有儿童服饰特有的功能属性,唐代儿童服饰有着与成人服饰相同又不同的发展规律和特征。同时,在唐代多民族文化习俗的碰撞、大环境相融合的影响下,各民族儿童服饰的交流与融合反映了一种社会文化和对儿童的关爱以及传递美好生活的状态。此外,汉至唐代认为的儿童是狭义上处于低龄的孩子,男子二十“及冠”和女子十五“及笄”是古人对“儿童”的界定。“儿童”的称谓,多使用“小儿”或“童子”,为将研究明确化,本研究中儿童的年龄范畴定为0到12岁。画像中儿童形象的确定可根据画面的主题场景、人物组合、道具搭配、发型与身体比例等推测。由于“重男轻女”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上相当多的儿童图像性别区分不明显,儿童图像以男童造型为主,因此,本研究侧重于解读男童服饰。结合唐代儿童的生活背景,如宗教思想、家庭观念和儿童游戏,并借鉴唐诗中对儿童及服饰的描述,对唐代儿童服饰及特点进行相对全面、系统的考证分析,对唐代儿童的首饰、帽子、围涎、披帛、襁褓、兜肚、裲裆、圆领袍衫、短衫、襦裙服等进行具体探究,从中领略唐代儿童服饰的多民族杂糅特征,对当代童装设计及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方的儿童史研究走过了近50年的历程,其儿童服饰文化亦有较长的历史。我国古代儿童服饰文化的研究则少之又少,现有对服饰的研究以成人服饰为主,面向儿童服饰的研究尚待拓展。唐代儿童图像实物的大量出土,为研究儿童服饰文化带来了新的机会,同时也对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外,受画像清晰度和敦煌壁画等文物保护的限制,加上儿童题材的绘画尺寸一般较小,往往居于画面一隅,不易发现,对唐代儿童服饰具体纹样的研究存在一定难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