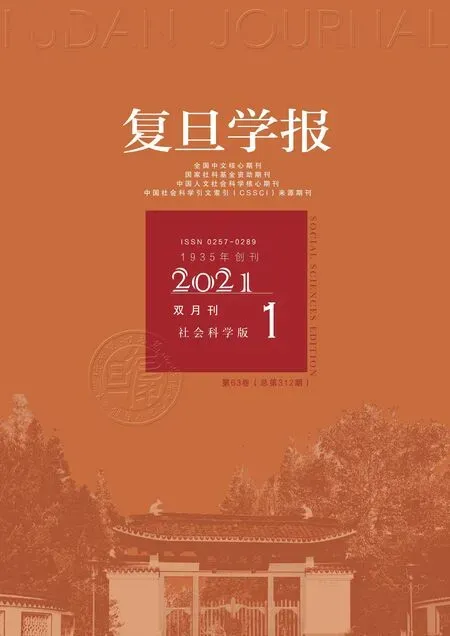阳明《中庸》首章诠释及其意义
许家星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作为朱子四书学的内在继承者和批判者(1)唐君毅先生倾向阳明是朱子的继承者,“然自细处看,则阳明之学,虽归宗近象山,其学之问题则皆承朱子而来;其立义精处,正多由朱子义, 转进一层而致”(《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87页)。陈来先生则认为阳明相对于朱子兼具继承者与反动者两重身份,似更强调后者,“无论如何,阳明哲学整体上是对朱学的反动,而不是调和”。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页。,阳明的《四书》诠释在方法、义理上皆提出诸多与朱子不同的看法,体现了《四书》诠释的新面目。学界多关注阳明《大学》之学,对其《中庸》学相对忽略。(2)有学者认为,“从《传习录》来看,阳明与学生以及道友所讨论的问题,多源自《大学》,几乎没有关于《中庸》话题的讨论,即便偶尔提及《中庸》,也是讨论其他话题时顺便提到而已。这些现象似乎隐含了一个事实,即阳明实际上不是重视《中庸》而是重视《大学》”。蒋国保:《王阳明“〈大学〉古本”说生成考》,《贵阳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事实上,阳明的《中庸》诠释颇为新颖,翻转了程朱所主张的《中庸》多言形上本体的明道性质,将其定性为与《大学》同一的修道工夫之作。“《中庸》为诚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阳明紧扣《中庸》首章,认为仅此就足以囊括《大学》全书之义,提出“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并将此理念落实于《大学古本旁释》中。针对朱子以戒惧、慎独分指未发和已发两层工夫的做法,阳明合两者为已发一层工夫,并从本体与工夫的关系视角诠释不睹不闻与戒惧,“不睹不闻,即是本体;戒慎恐惧,即是功夫”。在中和的认识上,阳明对朱子思想有继承和发展,既从本体角度主张“良知是未发之中,人人所同具”,又从境界立场提出“常人未有未发之中”说,进而探究了中和与天理、存气的关系。故深入理解阳明的《中庸》诠释,对从经典学的角度准确把握阳明心学,领会朱、王学术异同,推进对《中庸》学的认识皆有一定学术意义。(3)关于阳明《中庸》首章解的研究,吴伯曜的《王阳明四书学研究》(高雄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第五章,2007 年)有所论述,郭亮的《释经与治疗:王阳明的中庸首章解》(《现代哲学》2015年第2期)从解经方法的角度讨论了阳明解经的得失。
一、 “《中庸》为诚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
1. “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阳明对《中庸》首章评价甚高,提出子思将《大学》要义皆浓缩于《中庸》首章,实为《大学》精华所在,此解突出了《学》、《庸》内在义理上的高度同一性,这与程朱强调两者之别迥然不同。“澄问《学》、《庸》同异。先生曰:‘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4)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6页。陈荣捷先生认为朱子有括《中庸》一书之义为《大学》首章之意,见《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年,第63页。《言行录汇辑上》:“子思撮一部《大学》作《中庸》首章,圣学脉络,通一无二,净洗后世支离异同之窟”,第1627页。《中庸》与《大学》确是风格有别的著作,朱子给予《学》、《庸》不同定性:《大学》多言心,侧重为学工夫次第,确立了圣学纲领,亲切可行,以为《四书》之首;《中庸》多言性,侧重形上本体,阐明儒学高远之境,最为难读,置于《四书》之末。阳明主张“括《大学》一书之义”的《中庸》首章,在朱子看来包含了本体、工夫、境界三层含义,《中庸章句》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页。可参拙稿:《朱熹〈中庸章句〉首章“三位一体”的诠释特色》,《中州学刊》2010年第5期。阳明则认为首章性质实如《大学》,以为学之方为主而非论本体境界,揭示出为学用力之要,由此入手终可达于道之体悟。《中庸》首章于阳明具有指示圣学工夫、为学路径的根本意义,当在龙场遭遇诽谤之时,阳明即以该章之中和说来克治化除内心不宁,对悟道产生了工夫印证作用。“既归遭谤,则以其语置诸《中庸》中和章,并观以克化之。”(6)黄宗羲:《江右王门学案》七,《明儒学案》卷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7页。正因该章具有重要工夫意义,故阳明将之与《大学》首章一并作为接引初学的“入德之门”。钱德洪《大学问序》言:“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学》《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入之路。”(7)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967页。
2. 以《庸》注《学》。在刊于1518年的《大学古本旁释》中,阳明展示了如何“括《大学》之义为《中庸》首章”,以《中庸》首章范畴贯穿于《大学》全篇训释,通过《庸》、《学》互训的方式,极大强化了两书在工夫层面的内在联系,突出了《中庸》首章所具有的工夫意义。如以《中庸》首章之戒惧对应格物诚意,未发之中对应正心,已发之和对应修身,显示了《中庸》首章统领《大学》一篇之义的可能性。(8)《大学古本旁释》目前有百陵学山本和函海本不同版本,陈来先生认为后者是定本,前者是初本。本文据《丛书集成》函海本。具体言之:一是以戒惧解诚意、格物。指出修身在诚意,诚意就是慎独,是在格物上的慎独,正如《中庸》之戒惧。戒惧、慎独、格物、诚意四者在阳明看来,皆是在意念上用功。“诚中形外”则相当于《中庸》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大学古本旁释》所谓诚其意句旁注:“诚意只是慎独,工夫只在格物上用,犹《中庸》之‘戒惧’也。”此谓诚于中句旁注:“犹《中庸》之‘莫见莫显’。” 二是以“未发之中”对应正心,强调心不可堕于有无,而应处于不偏不倚之中。正其心章旁注:“正心之功,既不可滞于有,亦不可堕于无。犹《中庸》‘未发之中’。”三是以“中节之和”对应修身,强调心体当廓然大公,以实现情之所发无所偏颇而中节之和。修其身章旁注:“人之心体不能廓然大公,是以随其情之所向而辟,亲爱五者无辟,犹《中庸》‘已发之和’。”阳明还以《中庸》其他部分对应《大学》,如切磋之道学对应《中庸》道问学、尊德性,“赫兮喧兮”之威仪对应《中庸》之“齐明盛服”。
3. “修道之谓教,诚之者也”的修道工夫义。阳明《中庸》的新诠,首要者在于将该书由形上本体之作转变为修道工夫之作,认为其非言“天道之诚”,而是论“人道诚之”工夫。故在对首章首层“性道教”的阐发中,有意忽视为郑玄、朱子所重视的关乎形上层面的“天命之谓性”,而尤着意于对“修道”的诠释,视此为首章核心,体现出与朱子从宇宙创生、形上本体角度阐发“天、性”范畴的不同旨趣。在刊刻《大学古本旁释》的同年,阳明著《修道说》阐发对首章看法:(9)《王阳明全集》,第263页。
率性之谓道,诚者也;修道之谓教,诚之者也。故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中庸》为诚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微之显,诚之不可掩也。修道之功若是其无间,诚之也夫!然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道修而性复矣。致中和,则大本立而达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诚尽性,其孰能与于此哉!是修道之极功也。而世之言修道者,离矣,故特著其说。(10)孔颖达似亦有此意:“谓人君在上修行此道以教于下。”(阮元刻:《礼记正义》卷五十二,《十三经注疏》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25页)如此则“教”成为与“修道”并列而表进一层递进行为之动词。
其次,以“修道”作为《中庸》首章宗旨,以“诚”贯注其中,以《中庸》二十一章“诚明”章“诚”与“诚之”这组范畴解释“道”、“教”,认为两者具有等同关系:率性之道即诚,修道之教即诚之,分指本体与工夫。阳明极注意将“诚之”与“修道”并提,指出《中庸》就是“为诚之者而作”,是“修道之事也”。修道之功针对道之偏离而发,戒惧工夫体现了修道之功的绵密无间,不睹不闻正是诚之不可掩的体现;位育中和之境则是修道工夫之极致,是唯有至诚才能达到之境界。充分体现出阳明以“修道”贯穿首章乃至全书的宗旨。朱子则将“诚”与“诚之”分别解为天道本体与人道工夫,并反对与首章关联,认为此“性”、“教”不等于首章“性”、“教”。(11)朱子早期采用侯师圣说,主修道之教与明诚之教同义,“修道之谓教,疑只与自明诚谓之教之教皆同,言由教而入者耳。所谓以失其性,故修而求复。(先生自注云:此说非是)。”(《答吕伯恭》,《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23页)此后则反对此说,《语类》卷六十二言:“‘修道之谓教’一句,如今人要合后面‘自明诚谓之教’,却说作自修。盖‘天命谓性’之‘性’与‘自诚明’之性,‘修道谓教’之‘教’与‘自明诚’之教,各自不同。”同上,《朱子全书》第十六册,第2023页。阳明直接将道、教与性、教等同,越过首句“天命之谓性”,主张道即性,二者没有区别,似弱化了“性”的超越意义。朱子区分性与道是所以然与所当然之别,是本体与流行、全体与分有的关系。阳明以过与不及来阐发道之偏离,正因为存在偏离道的可能,故修道之功顺理成章导出作为工夫内涵的戒惧慎独,并将之与末章“微之显”关联,反复以“诚之”来突出工夫之“诚”。“微之显”乃是有诸内必形于外之必然,表明诚体彰显之不可遏止。
复次,阳明认为,在戒惧工夫基础上方有中和之境,此即“道修而性复”的修道以复性过程。此道修、性复说意在回应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体现由工夫复归本体之义。致中和实现了立大本、行达道、“知天地之化育”的效果。阳明用“知化育”而非“赞化育”,强调致中和所达之境乃是自我契悟,而非作用天地,有针对朱注之意。(12)《中庸章句》解“知”为“其极诚无妄者有默契焉,非但闻见之知而已”,“赞”则为“助也”。致中和与“至诚尽性”相应,唯有实现至诚尽性者方能做到致中和,这是修道工夫所达的极致功效。朱子亦认为此是“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阳明道出本文意在批评朱子修道说的支离务外,偏离本旨,以正视听。阳明将修道、中和与诚之、诚关联,实质是以“诚”的工夫、境界之两义解首章道、教,故亦可谓以“诚”概括作为《大学》全书之义的《中庸》首章,这与阳明主张《大学》之要即在“诚意”的观点是一致的。反观朱子首章之解,则有意避用“诚”,着眼于性道、体用说,将致中和视为“圣神功化之极”,以圣论而不以诚论,更强调首章形上、境界义。
再次,阳明集中批评了朱子以“品节”解“修道之教”。“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何须要圣人品节?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礼乐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谓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修道而学,则道便谓之教……人能修道,然后能不违于道,以复其性之本体,则亦是圣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惧’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复其性之本体。”(13)王守仁: 《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37~38页。朱子解意在表明教是道的现实展开,如礼乐刑政之教化,故有“品节”这一强调差异性的表述。而在阳明看来,此种理解则是对道的分裂和碎片化,破坏了道的整全性,故提出“道即性即命”,强调以命为性、性为道、道为教的三者一体说。“率性”、“修道”分指圣、贤境界,虽程度有别,但却不可对立而论,实互有交叉,如圣人亦修道,常人亦率性,圣人亦要做下学工夫,常人亦能上达本体之道。针对“道即教”的疑问,阳明以良知解之,认为“道即是良知”,从良知的角度理解道,良知之完完全全,正如道之完全。良知之是非自明,正如道之无过不及,故良知正是自家明师。阳明强调了道的整全、自足、完满、绝对,若道尚须圣人加以品节完善,则乃成为一残缺有待的“不完全”之物了。故《章句》“治天下之法”说非《中庸》宗旨,与下文戒惧慎独之修道工夫亦不合,导致“教、道”落空。阳明的“修道”是指修道者戒惧慎独的体道工夫,而非就布道者礼乐刑政教化言。其诠释视角较朱子明显发生了变化,他以“学”解“教”,使道的教化义转变为己的自我修学义,如此则经文当为“修道之谓学”方可。阳明是采用增字为训的方法以插入“学”的概念,以修学为教,行性为道。他认为教、学一义,视为修道为教、为学皆可,取决于所面对的对象,如于自我工夫修习则为学,于道之示人无隐则为教。教、学皆是作为道之显现、实践义,本无需训释,意在消除以学解修道之教带来的语义问题。(14)阳明说:“率性而行,则性谓之道;修道而学,则道谓之教。谓修道之为教,可也;谓修道之为学,亦可也。 ”丙戌《答季明德》,《王阳明全集》卷六,第214页。阳明提出修道的实质就是循无过不及之中道,在此意义上道即是教。此“教”近乎《礼记》所言“风雨霜露无非教”,朱子引此解“吾无隐章”,指天道无时无刻不自然显露流行于天地之间,示以为教。在这个意义上,阳明同于朱子,皆认为“教”是“道”的流行展开。阳明又提出此“修道”同于“修道以仁”之修道,后者指以仁作为修习道的根本,由修道方可至于不违道,方能复性之本,最终实现圣人率性之道的境界。修道之教对应贤人戒慎恐惧,率性之道对应圣人中和,中和又对应《易》“穷理尽性至命”之境界。阳明“修道而学为道”的宗旨意在阐明修道工夫义,阐明《中庸》首章及全书的工夫意义。此关乎他对《学》、《庸》关系的判定,故反复论之。他将“《中庸》一书,大抵皆是说修道的事”作为全书主旨,此后或从正面论能修道之人,如君子、颜渊等,或反面论不能修道之人,如小人、庶民等;至于舜、文武、至诚至圣等,其要亦在于能自主修道,故《中庸》主旨是学者修道工夫,而非程朱所强调的明道之体。由此证成“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说。(15)朱子弟子黄榦则特重“哀公问政”章,认为其义囊括《大学》一书。“哀公问政一章,当一部《大学》,须着反复看,榦旧时越看越好。”(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802页)此外,勉斋以道之体用作为《中庸》框架的同时,亦特别突出了《中庸》的工夫义,认为“戒惧慎独知仁勇诚”八字是实现中庸之道的工夫,也是全书大旨所在。“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体用者,则戒惧谨独与夫智仁勇三者,及夫诚之一言而已,是则一篇之大旨也。”(同上,第548页)且勉斋如阳明一般,尤重戒惧工夫,“《中庸》一书,第一是戒谨恐惧”。在强调《中庸》的工夫义上,他与阳明确有相通之处。
二、 “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工夫”
阳明从其良知学出发,居于本体与工夫说,以致良知统摄戒惧与不睹不闻,阐明戒惧与慎独、戒惧与洒落的关系,突出了戒惧在良知学中所具有的工夫意义。
1. 戒慎恐惧与不睹不闻。阳明从本体与工夫的角度对戒惧与不睹不闻关系作出了不同于程朱的新解。他说:“人之心神只在有睹有闻上驰骛,不在不睹不闻上着实用功。盖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工夫。”(16)《王阳明全集》,第123页。批评世人用心于睹闻外物,用错方向,应用力于不睹不闻之处,不睹不闻为良知本体,戒惧是致良知工夫。戒慎恐惧是本体与工夫的统一,工夫当由所睹所闻转向睹所不睹闻所不闻,在良知本体上用功,如此工夫方有着落。工夫成熟后即达到自然无为,无意防检之境,而真实性体自然健健不息,如此虽外在闻见亦将为心所用而不为心累。此不同于朱子以敬畏工夫而论。阳明对戒惧与不睹不闻的本体工夫关系存在角度不一的表述,如不可执著两者本体工夫之分说,即不睹不闻、戒慎恐惧虽然分指本体与工夫,存在本体与工夫有别,但不可拘执于此,本体既是不睹不闻,亦是戒惧不睹。如能有真知之见,洞见良知,则说戒惧是本体,不睹不闻为工夫亦无不可,以此见出工夫、本体皆是名称而已,两者本来为一。即本体即工夫,即工夫即本体。“此处须信得本体原是不睹不闻的,亦原是戒慎恐惧的……见得真时,便谓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功夫,亦得。”(17)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第105页。戒惧则为致良知的根本工夫,它具有通贯其他工夫的统贯性,据此可反省己过。“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者,时时自见己过之功。”(戊寅《寄诸弟》)它内在容纳了道教养身之说。“果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专志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矣。”(辛巳《与陆原静》)
阳明讨论了如何区别戒惧不睹不闻与所睹所闻的思、为关系,即工夫动静关系,凸显了儒学特有的天理动静观。指出周公虽终夜在思,然而却只是戒惧工夫。此看似与戒惧“不睹不闻”有所冲突,但却合于阳明“睹闻思为一于理,而未尝有所睹闻思为”说。所知所思如以理为主宰,即是不睹不闻、无思无为。判定见闻、思虑、行为未发已发之动静与否的标准不在知觉、行为的是否发出,而是知觉行为所指之内涵,即睹闻是否“一于理”(此极似朱子诚意之解“一于善”)。如“一于理”,则虽有所睹闻思为而实未尝睹闻思为,即动而未动,动静皆定之意。此一于天理之见闻思行乃是顺应心体之自然而发,是人所应行当行者,非造作、背逆之行,故心虽实有所动而未尝动。此体现了阳明对动静概念的理解并不在动静之分,而在乎在此两种不同状态中心的道德价值取向,是以心性道德论动静,是天理动静论,而非物理、心理意义上的物理动静论,并以此否定了佛老之动静观,如庄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的木石不动之形态殊不可取。此亦是宋儒本色,阳明所追求者,即是明道提出的“动亦定,静亦定”的动静一如观。“‘常知常存常主于理’,即‘不睹不闻、无思无为’之谓也。不睹不闻、无思无为,非槁木死灰之谓也。睹闻思为一于理,而未尝有所睹闻思为,即是动而未尝动也;所谓‘动亦定,静亦定,体用一原’者也。”(18)《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第63页。
2. 戒惧与慎独。朱子据自身工夫体会和上下文本用语,提出戒惧与慎独当分为未发、已发两层工夫的新说。阳明反对朱子二分说,主张戒惧慎独为一。当然,在对“慎独”的理解上,阳明认可朱子“人所不知己所独知”的独知义。阳明对慎独评价甚高,认为是为己之学的根基,是独知之学,是致良知工夫。“从来为己学,慎独乃其基。”(《守文弟归省携其手歌以别之》)“慎独是致知工夫”。慎独与格致、精一、集义是同一工夫,“《大学》谓之‘致知格物’,在《书》谓之‘精一’,在《中庸》谓之‘慎独’,在《孟子》谓之‘集义’,其工夫一也。”(《答陆清伯》)批评弟子慎独为格物之一事说,认为“格物即慎独,即戒惧”,二者实为同义。盖阳明格物义近乎“正念头”,慎独、戒惧亦是在独知之念上用功,故可谓之同。阳明进一步将慎独视为礼乐之本,颜子之乐之基,颜子一切为学工夫皆立根于慎独,由此方有克己、不贰过、三月不违之功,实现自得从容之乐。“盖箪瓢之乐,其要在于穷理,其功始于慎独。”韩愈缺乏格致、穷理慎独之功,此为最大缺陷。阳明对戒惧慎独给予充分认可:
只是一个工夫,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此处不论善念恶念,更无虚假,一是百是,一错百错,正是王霸义利诚伪善恶界头。于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诚。古人许多诚身的工夫,精神命脉全体只在此处……今若又分戒惧为己所不知,即工夫便支离,亦有间断。
戒惧亦是念。戒惧之念无时可息……若要无念,即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19)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34~35页。
阳明首先否定了朱子戒惧、慎独分未发已发说,提出工夫只有一个,无事有事皆是在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之处用功,若在人所共知之处用功,则是陷入小人自欺作伪。此慎独独知是诚的萌芽,于独知之时,一切念头无论善恶,皆是真实不虚。独知构成所有行为如王霸、义利、诚伪之起点,是源头、分界所在。若能于此源头立定根本,则是端本澄源,是诚身工夫精神命脉全体所在。慎独工夫贯穿一切时空、状态而永无止息,朱子之分过于支离,导致工夫间断。其次,戒惧并非无知,戒惧自身即是知。若认戒惧是“无”之意识状态,则将陷入佛教离弃世间的断灭见、禅定见。阳明从念的角度论戒惧亦是念,此念须永恒无息,一旦有息,则生出昏沉之念、邪恶之念。批评无念无知说,认为只有在昏睡或枯木死灰状态下才可能。事实上,昏睡中意识亦在流动,只不过未明显觉知而已,今称为潜意识。阳明根据工夫的持续性、普遍性、真诚性反对割裂戒惧与慎独,突出慎独作为一切工夫之始的根源性。(20)朱子划分戒惧与慎独为二的思想,是其新解,提出之初即遭到吕祖谦等质疑,朱子据文本“是故”等予以回应。此后朱子后学对此亦不乏非议。阳明悟道前亦取朱子此说。如1504年秋主考山东乡试,主朱子戒惧与慎独分两层说,尽管有学者考证试录非出自阳明之手(彭鹏:《山东乡试录非出于王阳明之手辨》,《孔子研究》,2015年第4期)然作为主考官的阳明之评语“题意正如此”亦流露其态度。阳明将《学》、《庸》视为孔门传心之要法,提出《大学》之要在“本末兼该,体用一致”,《中庸》则是中和为一,不睹不闻为本体,戒慎恐惧是工夫,慎独即独知,由此贯通内在天德与世间王道,此即明道“有天德乃可语王道,其要只在慎独”说,故不应将戒惧存养与慎独工夫分而为二。“其后因悟《大学》、《中庸》二书,乃孔门传心要法。……论《中庸》则谓‘中和原是一个,不睹不闻即是本体,戒慎恐惧即是功夫。’”(21)黄宗羲:《江右王门学案》九,《明儒学案》卷二十四,第554页。在反对二分的基础上,阳明认为就中和体用、未发已发、本体与工夫关系而论,戒惧是在发用之和上的致和功夫,之所以不在致中上用功,盖本体无形无影,无从下手,只有在中之发用处才能下手。中和本为一体,未发不偏不倚,则已发无所乖戾,故“致和便是致中”,由万物得育之和,正见出天地得位之中。告诫弟子不应拘泥文义,当明乎“中和是离不得底”,如火之体与火之照本无可离,此是以体用解中和,“故中和一也”。阳明进一步提出“致中和只在谨独”。他发挥象山“人情事变做工夫”说,提出所有工夫皆可归纳为“人情事变”,事变又只在人情中,做好人情的根本在于致中和,致中和的要领又在慎独,慎独是实现情感中和之工夫根本。故慎独与戒惧都是在已发之和用功,从而相契于阳明的“事上磨练”精神。“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22)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15页。阳明“致中和”说不同于朱子致中、致和的两分说,取消了朱子存养未发工夫,皆视为已发戒惧、慎独致和工夫,并将二者进一步收归为致良知工夫,而致良知工夫是无间动静、不分未发已发的。
3. 戒惧与洒落。戒惧工夫与自得洒落密切相关。敬畏与洒落这一对概念被视为充分体现了阳明哲学“有无合一”精神(23)参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一、九、十相关章节。。而阳明之敬畏不同于程朱的以敬为畏,实则是以戒惧为敬畏。除《答舒国用》涉及敬畏一语外,阳明似乎未见使用“敬畏”,且他极为反对朱子“敬”论,而最喜“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他说:
夫君子之所谓敬畏者,非有所恐惧忧患之谓也,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纵情肆意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惧,惟恐其昭明灵觉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于非僻邪妄而失其本体之正耳。戒慎恐惧之功无时或间,则天理常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无所亏蔽……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孰谓“敬畏之增,乃反为洒落之累”耶?惟夫不知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歧为二物而分用其心……是国用之所谓“敬畏”者,乃《大学》之“恐惧忧患”,非《中庸》“戒慎恐惧”之谓矣。(《答舒国用》)(24)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190页。
针对敬畏为洒落之累,敬畏本有心而不可无心说,阳明批评此乃源于“欲速助长之为病”。进而对敬畏、洒落之义加以说明,强调“敬畏”非《大学》有所恐惧忧患之义,而是《中庸》戒惧义;洒落亦非放荡纵情,而是心体不为欲望所累所达到的无入不得之状态。指出对敬畏的错误认识是导致工夫陷于困境的根本原因。进而将戒惧工夫与天理、良知本体结合起来,指出心体即天理,天理之明觉即良知。戒惧作为致良知工夫,意在防止此昭明灵觉的良知被物欲所昏沉、遮蔽、隐昧,流向邪恶妄念之中,导致本体不正。克服此弊关键在于当以持续不断的戒惧工夫来存养天理,保持昭明灵觉的本体廓然大公,不偏不倚,无所染着,由此达到无过不及,从容中道,从心所欲,而为真洒落。阳明着重从“无”的方面形容“洒落”是彻底摆脱了亏、蔽、牵、扰、喜惧忧乐、意必固我、内疚悔恨等负面意识、情绪、烦扰所带来的心体不正,而达至的圆成饱满、自足自适、祥和安宁之境。故洒落与敬畏非对立关系,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之常存则生于戒惧之不息,洒落境界本于敬畏工夫,洒落为心之体,敬畏为心之工,两者是工夫与本体、境界的关系。不可将敬畏与洒落分为二物,而造成抵牾,流于助长。阳明引程子说指出“无心非无心”,而是“无私心”。《中庸》之戒惧正表明心之不可无,否则即陷入释老之断灭空;《大学》有所恐惧之心是不可有之偏私心,否则就流于执着见。戒惧与有所恐惧之心是性质截然对立之心,一无私,一有私。即便圣如尧舜文王,亦不离兢业、翼翼的敬畏工夫,可见戒惧工夫之普遍高明。此戒惧敬畏工夫看似严肃拘谨,实则出乎心体自然,非造作强迫,而是无所为而为之自然,不可视为对人心的拘执。敬畏工夫无间动静而贯穿意识一切过程,此即敬内义外之学,由此通达乎天道而行之无疑。就此看来,阳明将戒惧与敬畏等同之,同于朱子“常存敬畏”,但阳明将不睹不闻视为本体,朱子则视为知觉状态,朱子“常存敬畏”工夫指向“存天理之本然”这一目标,阳明则以敬畏直接作用于不睹不闻之本体,突出本体与工夫的一体性。
三 、 “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与“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
“中和”说是影响朱子思想形成转变的重要论题,以致良知为宗旨的阳明,对中和问题亦给予高度关注,而且提出了貌似相互矛盾的两种看法,即未发之中究竟是否为人所普遍具有?这一问题其实已潜藏于朱子学中。
1. 朱子的未发之中与未发之不中。朱子的未发已发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体用论,二是思虑论。(25)田智忠指出朱子未发之中具有三个视角:理本论、天理浑然论、成圣功夫论。阳明的未发之中具有“体用一如”的特质,且从个体性原则出发,讨论了“未发或不中”的问题。参《从未发无不中到未发或有不中——论理学对未发之中的讨论》,《吉林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或者说一偏重于性,一偏重于心。一方面,朱子从性本体的观点看待“中”,认为“未发,则性也。”“中者状性之体”。提出众人与圣人一般,皆有未发之中,反对以心之昏沉与光明来区分圣凡之未发,以“未发只做得未发”的强势语气表明圣凡未发皆同,不容置疑,此未发是人生大本、天命之性,为一切人生义理之根源,故若常人无此,则“是无大本,道理绝了”。(26)《朱子语类》卷六十二,《朱子全书》第十六,第2038、2046页。至于圣凡之别,则体现在已发之后能否做到感而遂通,发而中节。凡人之所以不能中节者,其因在于对自身本有的“未发之中”未有自觉,“有而不觉”的原因是缺乏静养心体工夫。“此大本虽庸、圣皆同,但庸则愦愦,圣则湛然。”(27)《朱子语类》卷六十二,《朱子全书》第十六,第2038、2046页。另一方面,朱子亦从心的立场论中,提出“未发之不中”说。指出心之思虑未发之不中的情况普遍存在,就常人而言,已发之时远多于未发之时,未发不中的原因是受到昏沉浑浊之气质及私欲影响。此心之未发如顽石之状态而无法开其窍,一旦发出则是乖戾不中。朱子以不开之顽石比喻心之未发,甚为罕见,其义当指心虽未有思虑,但亦未通乎义理,故劈斫不开,处于昏昧不醒之状态。对治此未发不中的工夫不在察识,而在主一涵养。(28)“喜怒哀乐未发而不中者,如何?”曰:“此却是气质昏浊,为私欲所胜,客來為主。其未发时,只是块然如顽石相似,劈斫不开;发来便只是那乖底。”又曰:“看来人逐日未发时少,已发时多。”曰:“然。”《朱子语类》卷六十二,第2039页。这是因为此心“未发时已自汩乱”。他说:“某看来,‘寂然不动’,众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圣人能之,众人却不然。盖众人虽具此心,未发时已自汩乱了,思虑纷扰,梦寐颠倒,曾无操存之道,至感发处,如何得会如圣人中节!”(29)《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第3179页。心可分为寂然不动和感而遂通之未发、已发两层,寂然不动之心为圣凡同具,感而遂通之心圣所独具,众所不能。不能感通的根源在于心之未发时,已处于思虑纷扰、神魂颠倒状态,毫无操存工夫,故发而不中。据此未发已发的定义,似乎有矛盾,既是“寂然不动”之心,又在“未发时已自汩乱了”,变成“不动已乱了”。朱子之未发已发除指性情体用关系外,还指心之所处动静状态,即思虑之萌发与否。通常把“未发”与“思虑未萌”等同起来。朱子既认为才思即是已发说,未发则是三无:无思虑、无私欲、无偏倚,即寂然不动之中。但据此,则朱子之已发不是从思虑萌发立论,而是就心是否受到外物感应,与外物交感作用立论,“感发”才是已发,正如《乐记》“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朱子确有“无事是未发,才感便是已发”说,“方其未有事时,便是未发;才有所感,便是已发,却不要泥着。”此是从意识之外感论,与就意识自思论明显有别。朱子以《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论未发已发,亦是强调一个“感”字,二者之分,可视为“无感之思”(意识的自我反思)和“有感之思”(因物而思)。朱子在评论伊川“既思即是已发”说时明确反对“思为已发”说:“故以为静中有物则可,而便以才思即是己发为比,则未可。”(30)《四书或问》,《朱子全书》第六册,第562页。朱子早年亦主此说,认为“才涉思,即是已发动”。《朱子语类》,第2038页。认为正如不能说复卦之一阳即是阳,亦批评伊川“祭祀时无所见闻”说不合情理,而赞其“无事时须见须闻之说”精当,主张静中有物,反对静中无物说,有堕入佛老虚空之嫌疑,(31)《四书或问》基于此批评吕大临等说。“其曰‘由空而后见夫中’,是又前章虚心以求之说也,其不陷而入浮屠者,几希矣!”第563页。提出未发之静仍是有喜怒哀乐,只不过未发而已,即“有而未发”。在此意义上,未发不是无喜怒哀乐,而是喜怒哀乐之有而未偏,即不偏不倚之中。在此状态下,人之知觉能力较已发时更为精明专注。以此否定伊川的未发乃知觉不用,耳目无闻见说。“盖未发之时,但为未有喜怒哀乐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见,耳之有闻,则当愈益精明而不可乱”。其三,朱子在此问题上极重儒佛之别,特别强调不可割裂未发已发为两段不相干工夫,否则堕入佛教离弃人事,块然独居之断灭,而应贯通未发已发,批评半日静坐之见,即犯此病。此体现朱子对佛学静坐所可能带来的弊病之警惕。(32)“然不是截然作二截,如僧家块然之谓。只是这个心自有那未发时节,自有那已发时节。……若以为截然有一时是未发时,一时是已发时,亦不成道理。今学者或谓每日将半日来静做工夫,即是有此病也。”《朱子语类》,第2039页。在诠释未发已发时,他始终绷紧着儒佛之辨之弦,提出判定儒佛在未发之中的原则是“当论其中否,不当论其有无”。体现了他与阳明在诠释未发之中上的一个差异:他更关注如何严辨佛老,以保证儒学道德原则的实现;阳明则关注如何容纳佛老,以在有无合一之中如何实现人的存在自由。其四,需要提出的是,除朱子外,朱子再传饶鲁提出的“众人有性而无中”说明确将中与性区别开来,观点极为清晰。“鲁尝谓众人有性而无中,人以为怪。众心(当为“人”字)之心,纷纷扰扰,无须刻宁息,何由有中? ”(33)史伯璇:《四书管窥》卷六,第865页。胡宏提出未发之中指性,故圣凡同;已发指心,独圣人能做到“感而静”的心之体段,凡人则是“感而动”。胡宏的已发包含寂然不动和感而遂通两面。这与程子、朱子的寂感分体用、中和说不同。“未发之时,圣人与众生同一性; 已发则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圣人之所独。”《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5页。“性”为先天固有,“中”则是后天修为之境界、状态,非常人所能及,盖众人之心时时刻刻处于纷扰不停状态,无片刻之安宁,其心之未发已是不中。未发只是人心皆有的一种自然生理状态,中则是需要经过修炼才能达到心的道德境界,具有很强的境界意味,此合乎中之意义。
2. 阳明的“良知未发之中”与“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
(1) “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人人之所同具者也”。阳明又以未发之中、天理和良知等同之,认为性本无不善、知本无不良,良知就是未发之中,由此自然推出未发之中是“人人之所同具”的大公本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阳明既言“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又言“未发之中即良知”,将此二者等同,从动静角度论未发已发的一体性,二者乃体用一源,即体即用关系。未发之体在已发之用中,已发之用亦不离未发之体。反之,用在体中,未发再无已发,浑然一体。是有体用而不分体用,有动静而不别动静。“‘未发之中’即良知也,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者也。……未发在已发之中,而已发之中未尝别有未发者在。已发在未发之中,而未发之中未尝别有已发者存。是未尝无动静,而不可以动静分者也。”(34)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64页。无论如何,阳明将良知与未发之中等同,在此意义上,当是人人皆有未发之中。阳明的良知即是未发之中,自能发而中节说,采用了体用一源、寂然感通的理论模式,同于程朱,只不过阳明还以两个“自能”突出了良知发用的必然性和自发能动性。“良知是未发之中,寂然大公的本体,便自能发而中节,便自能感而遂通。”(35)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二,第268页。
关于未发已发关系,阳明在辛未1511年《答汪石潭内翰》中基本站在朱子立场以体用、性情论述两者。未发指本体之性,已发指发用之情。喜怒哀乐之情与思虑、知觉皆是心之所发,即情、思、觉三面。阳明亦认可横渠提出、朱子倡导的心统性情说,赞赏以伊川寂感体用论心之性情,采用体用一源之论,主张体用相互一体。知体即知用,知用即知体。体难知而用易见。批评人心未有寂然不动之时说是见用而未见体,为学之要在于“因用以见体”,伊川“既思”、“既有知觉”是针对求中于未发者而言,并非否认心有未发。认可朱子《章句》以性情解未发已发。告诫学者不可专于寻求静处工夫,动处用功同样可以达到中和效果。凡所已发,若能做到无不中节,则必有一无所偏倚之中在。此“动无不和,即静无不中”,即用而见寂然不动之体也(似可由此反推,动有不和,则静有不中,可见常人无未发之中)。批评朱子“有知觉者在而未有知觉”说割裂了能所关系。阳明后来又针对朱子,主张无未发已发说,认为如说有未发已发,则无以别于宋儒。如说无,则有助于跳出朱子之见。对于真正认识到本无未发已发者,则说有未发已发亦不妨害原有之分。阳明之意,在从本体与现实两层分说,从本原论,确乎并无未发已发之分,未发已发只是动静状态之表述语、形容心体之两种存在状态,故就本视之,并无其分。然就用视之,确有其分。故此分合有无,端在观者之视角。在中和关系上亦然,未发即有和,已发则有中,未发已发、有无本为一体两面。故阳明言未扣是惊动天地之响动,既扣是寂寞无声之天地。
只缘后儒将未发已发分说了,只得劈头说个无未发已发,使人自思得之。若说有个已发未发,听者依旧落在后儒见解。若真见得无未发已发,说个有未发已发,原不妨原有个未发已发在……未扣时原是惊天动地,既扣时也只是寂天寞地。(36)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第115页。
(2) “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阳明据体用一如之论,提出“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盖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发之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37)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17页。学界近来论阳明未发已发思想的论文有:杨少涵《王阳明论“未发已发”》(《理论界》2008年第6期)提出阳明之未发有本体与境界两义,阳明关于未发之中两种看法存在严格与宽泛、同质与异质之别。孙占卿《王阳明论未发已发》(《孔子研究》2011年第6期)提出阳明认为“无未发时”、强调在“已发”上用功。朱卫平:《从王阳明“未发之中” 看阳明心学特质》(《湖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从有、无两面论阳明未发之中。袭业超:《王阳明“未发之中”说新解》(《衡水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认为王阳明首次提出“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说,其未发之中的“中”存在就性言与就气言两种情况。他采取逆推形式,认为有体有用,有未发之中,自然有未发之和。但“中”不可见,可见者乃“已发之和”,故据常人所发之未和,可推出所存之非中。阳明此是从人之实际修为状态论“未发”之“不中”,此“未发”不再是指良知本体。此推论粗看亦有个问题,体是普遍同一的(如儒家设定的人性之善),并不因用之无(现实人性之恶)而产生差异。儒家对性善论大体持圣凡同体异用论,理学解为理(性)同气异,如照此常人无已发之和,则必无未发之中的推论,则圣凡关系变成异体异用。这显然是与性善论相违背的,断然非阳明之意。此中关键在于阳明是从工夫角度立论,性体本不存在有无,阳明此处的未发之中则成为一个获得、实现问题。他从现实修养境界论“中”,“未发”不等于中。与此相应,王龙溪认为阳明的“‘人有未发之中,而后有发而中节之和’”说,乃针对朱子主张的未发之中人皆有之,和则常人并无说而发,即圣凡同中异和,将不中节归于流弊。阳明强调有中而后有和,无和必无中,中和正如镜之明体照用关系。“人有未发之中,而后有发而中节之和。此先师之言,为注《中庸》者说也。”(38)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 第235页。黄宗羲则将阳明“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说视为阳明为教三变之一,在龙场大悟格物,知行合一宗旨之后,阳明于滁阳以默坐澄心教学,强调了未发体上用功。如能体悟良知本体,则明乎本无所谓未发已发。“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39)《王阳明全集》,第1544页。
“其全体常人固不能有”的中和之大本与事为之分。阳明对中和作出了全体与局部、必然与偶然的区分,以此区别圣人之大体之中与常人事为之中,这一对中和属性的两层切分,亦证明阳明“众人无未发之中”是从修为境界效用论“中”。“在一时一事,固亦可谓之中和,然未可谓之大本达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岂可谓无?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则其本体虽亦时时发见,终是暂明暂灭,非其全体大用矣。”(40)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23页。
阳明的回答表明他对中和的本体与境界的两种认识。从境界论,存在圣人全体持续之中和与常人一时一事之中和之分,偶然短暂的中和不能作为大本达道之中,此即圣凡在中和实践上的客观差异。从本体论,他从性善的角度提出既然人性皆善,故皆具有中和,不能说常人就无中和(此显与“未发之中非常人有”矛盾)。故他又立即指出,常人之心经常昏沉遮蔽,导致作为本体发用之和不能得到保障,表现为明灭不定,不能持久,不能实现心之全体大用。所谓大本之中,达道之和,乃是时时之中和,处处之中和,只有能做到至诚无伪者,方能树立此作为大本之中和。可见此中具有普遍性、必然性,与常人偶然、局部之中截然不同。阳明这种区分,与其对人之根器及相应的从体用两面入手的教法相关。利根之人在现实层面有未发之中,故可从本源上悟,悟彻本体即是工夫,本体工夫、人我内外通体透彻浑然无隔。“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41)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第117页。阳明还以未发、已发区别正心、修身,正心近乎未发,修身则近乎已发,心之不偏不倚即是中,身之修是发而中节之和。“修身是已发边,正心是未发边。心正则中,身修则和。” 《大学古本旁释》中,阳明以未发已发之中和解正心、修身。如颜子即是此利根之典范,颜子能做到不迁怒不贰过,正因其心体已实现未发之中。这是由颜子已发之和,推出其具有未发之中。“颜子不迁怒,不贰过,亦是有未发之中始能。”(42)王守仁:《传习录》上,第32页。此以中和境界论述颜子似有拔高之嫌疑。他还主张“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有中方有和,有体才有用。故工夫不在积累讲求,物上穷理,而在“成就自家心体”,养得心体,则自然达于未发之中。如能做到心体未发之中,则事上之用自然中节,由此反对讲求名物。“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43)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21页。
(3) 中和与天理。 陆澄被阳明两种说法所混淆,感到阳明对“中”之定义有所不同,追问之:“澄于‘中’字之义尚未明。”曰:“此须自心体认出来,非言语所能喻。中只是天理。” 阳明的答复是:“中”义无法言传,只能自心体认,并以“天理”解中。阳明之意并非将中与天理等同,而是认为二者在无私欲、无偏倚、无染着上相似,最大共同点是“无所偏倚”。“中只是天理”,则人皆有天理,皆有中。阳明反复强调未发之中与纯乎天理的同一性,它实质是戒惧工夫所实现的此心“纯是天理”所呈现的心体状态。“汝但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养得此心纯是天理,便自然见。”对未发之中伤害最大的是“着意”,盖喜怒哀乐之情的本体,本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和,如稍一着意,则偏离了中和之体,流于过与不及,而为私欲束缚。“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自家着些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 阳明以明镜为譬,突出“中”的莹彻无染,以“无”的否定性表述来阐发中无偏倚、无染着。并以疟疾为譬,从根源与现象、无(隐藏)与有(显现)的关系论述未发与已发。私欲未发(未著于相)不等于无,而是私欲之心始终存有,一旦欲心扎根,则人心早已偏倚不中。可见在已发之先的未发之时,心已丧失其中。此可谓有私欲即不中,不在于发之与否,也即“常人无有未发之中”。正如犯疟疾之病者,病虽未发而实已为非健康之人。此处的未发之中非指先天皆具的天命之性,而是后天修养工夫极致之境界,可谓是“性复”之境。
“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阳明将中和与良知、天理贯通论述,尤其分析了天理与良知的关系,提出“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天理本体自有分限”说。此实为处理情、理及度的关系。 阳明向陆澄指出,忧儿病危最是用功之时,实践之地。父子之爱是人间至情,是人之天性,是合乎天理之举。但即便此合乎天理之事,亦不可过。因“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强调天理自带中和,中和为天理固有属性,当以中和来审视天理、人情,若过其中,则流于私,突出“中”为儒家最高之标准。(44)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传习录》上,第17页。这种表述从语义分析看,似有问题。“天理过中”是与天理的定义相违背的,天理的定义内涵了中,一旦过中,即非天理,而是私意。故阳明的真实用法应是指“天理发用过中”,阳明实质是以“中和”来化解理与情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强调即便是合乎天理之事,亦有个“度”的问题,如有所偏,走向过与不及,则事情会由合理走向不合理之“质变”。比如当忧则忧,如忧而无度,则陷溺于《大学》“有所忧患”之中,已丧失其本有的“正当性”;如俗语“得理饶人”,如不依不饶,则过而非理。陆澄之案例涉及情理关系,合理之情亦不可流而须节制。阳明强调,人情易犯“过情”之病,“多只是过”,一过即伤害“心之本体”,主张“毁不灭性”,“必须调停适中始得”。他以“天理本体自有分限”说表达此“中和”思想,天理、本体、善亦有其分限,不可过不可不及。工夫在“识心体”,若能识得心体,则自然合中。此“识心体”近乎明道《识仁篇》的“识仁”说,而其“调停适中”、不可“一向忧苦”之论,近乎明道《定性书》对于情的处理,“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亦与伊川《颜子所好何学论》主张的“约其情使合于中”相通。
阳明还讨论了中和与定气的关系,认为不可混淆定气与存中,气之宁静的心理状态不等于不偏不倚的心之道德状态。“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批评时人存心工夫并未做到心存,而只是平伏其气,可谓定气,而非存心,平心静气非未发之中,亦非求中工夫。求中功夫在于存天理、灭人欲,此工夫不间动静,只是一念在此,而无关宁静。未发之中指一种道德修养的极高境界,有强烈的价值指向,非同于泛泛的无指向的心气之宁静。(45)“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不管宁静不宁静。”《传习录》上,第13页。阳明将古代礼乐制作归结为中和,古人具中和之体以作乐,自家中和本与天地之气相应,候天地之气即是验自家之和气。故礼乐实根源于自家心体中和。
总之,未发已发之中和问题于阳明学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体用论、心性论、本体工夫、天人关系等重要论题。据邹守益所记阳明言:“中和者,礼乐之则也;戒慎者,中和之功也;位育者,中和之敷也。”(46)邹守益:《赠宗伯西玄马子北上序》,《邹守益集》卷三,南京:凤凰出版集团,2007年,第148页。我们或可在阳明“子思括《大学》全书之义为《中庸》首章”的基础上推进一步,认为“子思括《中庸》首章为中和”。总之,阳明《中庸》首章之解,内涵丰富,意义深刻,对阳明思想乃至宋明理学的研究,对《中庸》诠释史的阐发,皆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值得作出更深入的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