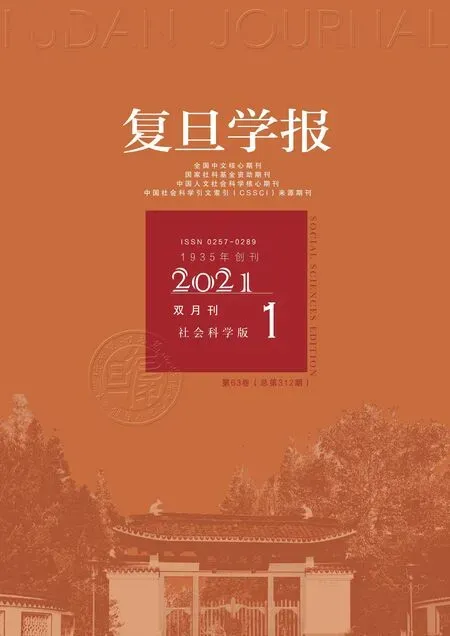世本无圣:明清常州舜山地区乡村士子的耕读实践
马俊亚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南京 210023)
舜山地区主要包括清代阳湖县(1724年以前及民国以后属武进)大宁乡及江阴县申港镇。舜山又称“高山”,在清代江苏常州府城东北25公里处。舜山南约4公里为顺塘河,顺塘河东行5公里至三河口北达长江。(1)顾世登等修:《毗陵高山志》卷2,丙子年(1876)刻本,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1~7页、第23页b。境内有申港(申浦)、焦溪(焦店)、下垫、三河口等村镇。同治时期,大宁乡有平田、沙田、山塘荡地41144亩;(2)顾世登等修:《毗陵高山志》卷2,丙子年(1876)刻本,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1~7页、第23页b。1928年测量的全乡面积为31.2平方公里(124.782平方里),人口26097人。(3)陈思修:《江阴县续志》卷5,民国九年刻本,第4页a。民国初年,申港人口15803人,(4)《申港志》编审委员会编:《申港志》,内部资料,2013年,第157页。1948年为19401人,(5)据《申港志》编审委员会编:《申港志》,第398页资料计算。耕地面积有25700余亩。(6)《焦溪乡志》编写组:《焦溪乡志》,1984年打印本,第32页。
舜山境内地势平坦,属长江下游冲积平原,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据1954~1978年的连续记录,年降水量在537.6~1466.6毫米之间,全年无霜期225天左右,年均气温约15摄氏度。(7)潜厂:《耕读说》,《钱业月报》1928年第8卷第6期。从自然条件来看,舜山地区的气候、土质比较适合农耕。
本文研究的区域比较微观。总的说来,学界对舜山地区研究较少。但学界对耕读文化的论述几汗牛充栋。1949年以前,文士们论及耕读,多视为田园诗般的世外桃源生活。如,有人认为耕读就是“春雨一犁,秋风万亩,田家风味,至乐存也”。(8)武进县建设局编:《武进年鉴》,“地理·各市乡面积街村一览表”,1928年,无页码。《耕读渔樵》图更是中国传统画家的常见之作。
现有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文化层面。如邹德秀认为,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耕读传家,形成了“耕读文化”。(9)邹德秀:《中国的“耕读文化”》,《中国农史》1996年第4期。徐雁认为,“耕读传家”观念不仅由来已久,且曾经深远地影响了农业中国的乡村社会。(10)徐雁:《“耕读传家”:一种经典观念的民间传统》,《江海学刊》2003年第2期。刘加洪指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是客家人的优良传统之一。(11)刘加洪:《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教育评论》2009年第1期。杨茜研究了张履祥如何在躬耕和处馆训蒙中坚守文人的理想。(12)杨茜:《明遗民生计图景——以耕读处馆的张履祥为中心》,《历史档案》2015年第3期。李任等认为,在科举制创立后的上千年时间里,耕读传家成为很多村落家族的家训家风。(13)李任等:《传统村落视域下耕读文化发展初探——以黄陂大余湾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17年第4期。李存山指出,农业文明加上以“明人伦”为主的学校教育, 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耕读传统。(14)李存山:《中华民族的耕读传统及其现代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1期。本文的研究着重于耕读士人与明清政治和传统社会观念的关系,与学界已有的研究并不构成冲突,可视为互相补充。
有些学者的研究从不同侧面帮助本文在更广泛的时空范畴中理解所涉事件的来龙去脉。渡边信一郎厘清了唐宋时代小农耕作方式的兴起,(15)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社会论》,东京:青木书店,1986年,第283~293页。有助于解释宋以后耕读家庭的普遍出现。宫崎市定认为,五代以前,中国兵与士是一体的,属于贵族阶层;宋代以后,兵农分离,士人不再负有从军的义务。(16)佐伯富等编:《宫崎市定全集》(2),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第93~94页。说明宋以后,士人无需习练武技,更加专致地耕种读书。这可与刘培的研究结合起来。刘培根据对南宋文学作品的解析,认为耕读传家的兴起和发展与理学的塑造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关联。(17)刘培:《耕读传家观念的重塑与强化——以南宋中后期辞赋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他还指出,南宋文学书写中的岩桂意象承载着耕读传家观念的种种内涵和意趣,调和了金榜题名与敬德修业的两种人生追求。(18)刘培:《耕读传家观念与士绅文化形态——以南宋文学中岩桂意象的生成为中心》,《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另外,陈杰克对中国古代“读”的本义作了细致的辨析。(19)Jack W. Chen, “On the Act and Representation of Reading in Medieval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9.1 (January-March 2009): 57-71.魏希德(Hilde De Weerdt)通过考察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在宋至清代的影响,分析人们对科举制度的不满。(20)Hilde De Weerdt, “Changing Minds through Examinations: Examination Cr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6.3 (July-September, 2006): 367-377.葛瑞汉(A. C. Graham)指出,春秋战国时,重农学派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农民乌托邦的起源。(21)A. C. Graham, “The ‘Nung-chia’農家‘School of the Tillers’ and the Origins of Peasant Utopianism in Chin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42.1 (1979): 66-100.这些学者的研究均在一定程度上对本文具有启发意义。
(一)
舜山地区的耕读历史极为悠久。舜山下有舜田8亩,传说为舜躬耕之处。(22)顾世登等修:《毗陵高山志》卷1,第4页a。春秋时,季札最初弃室耕读之地即在舜山,(23)《申港志》编审委员会编:《申港志》,第197页。此处后来成为季札延陵封地的核心地区,并且是季札的归葬地。(24)顾世登等修:《毗陵高山志》卷2,第3页a。
季札是吴地学识宏富、不求君位、礼让天下的名士。《汉书》载:“后二世而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其少子则季札,有贤材。兄弟欲传国,札让而不受。”(25)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667页。据顾野王《舆地志》:“季子名札,吴太伯十九世孙,……退耕于延陵,即其采邑。士人怀德,为之立庙。”(26)董诰等编:《全唐文》卷29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84页上。
传说舜山季札的碑文“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为孔子亲题。崇宁元年(1102),常州太守朱彥“表识其墓,谨樵牧耕凿之禁,又摹取孔子所书十字刻碑墓上,设像祠之学中,以时率吏士诸生拜焉,所以示邦人贵一德也。”(27)顾世登等修:《毗陵高山志》卷4,第4页b。
尽管春秋时代贵族与乡民之间有着相当大的礼法距离,(28)参见增淵龍夫:《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第488~514页。季札仍被视为吴地耕读的楷模。西晋左思《吴都赋》盛赞季札的影响:“且有吴之开国也,造自太伯,宣于延陵。盖端委之所彰,高节之所兴。建至德以创洪业,世无得而显称。由克让以立风俗,轻脱躧于千乘。”(29)萧统编:《文选》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1页。东晋殷仲堪《季子庙记》有言:“英风澡俗,遗德在民。虽复世经五代,年积千祀,而坟陇勿剪,庙宇常存。”(30)杨棨:《京口山水志》卷14,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619页。
季札对待君主僭位、王朝更替,采取自然而现实的态度:“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幸,乃吾君也。”(31)司马迁:《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465页。这也是南朝至唐统治者轮番登位且有合法性的依据。建元元年(公元479年),齐高祖萧道成甫即位,南齐君臣编造在季子庙掘得沸泉,得一银木简,向齐高祖献祥瑞,(32)萧子显:《南齐书》卷18,“祥瑞志”,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54页。为萧齐取代刘宋正名。于此可见季札在南朝士民中的影响力。(33)唐鹤徴:《(万历)常州府志》卷17,万历四十六年刻本,第79页b。在唐代,关陇集团创立的朝廷对江南人物崇拜多视为“淫祠”而予禁止,但仍承认对夏禹、太伯、季札、伍员祭祀的合法性,视四人为正神。唐代季札庙屡次得到维修,并被士民拜祀。
季札退耕延陵,显然不像中原地区的农家那样受到儒家强烈的抵制和批判。(34)农家与儒家的关系,详见A. C. Graham, “The ‘Nung-chia’農家‘School of the Tillers’ and the Origins of Peasant Utopianism in Chin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42.1 (1979): 66-100.2500多年来,季札的仁义、道德、学识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文化风俗有着相当的影响,影响的核心显然是舜山地区。季札的信念使吴地民众能非常理性地对待君主政治,致力于求田问舍,不愿参与皇权争斗。一位本地人写道:“邑中人皆诚谨忠实,不喜作伪,循循犹有让国之遗风焉。”(35)清华癸亥级编:《癸亥级刊·风土志》,1919年刊印,第 11页。这里的精英和普通民众很少做着帝王美梦,更倾向于务实性的耕读生活,与一江之隔、开业帝王辈出的苏北风尚有着极大的区别。
“耕”意味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满足物质生活的必要条件;“读”则是为了满足精神需求和追求高成就动机。清代大学士张英写道:“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虽至寒苦之人但能读书为文,必使人钦敬,不敢忽视。其人德性亦必温和,行事决不颠倒,不在功名之得失,遇合之迟速也。”(36)张英:《恒产琐言》,见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卷36,《魏源全集》第15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32页。
与季札同时代的舜地人披裘公,见道路上有遗金而不顾。季札怪而问之,披裘公曰:“反裘负薪,岂拾遗金者哉?何吾子貌君子而言之野也。”不与言姓名而去。(37)顾世登等修:《毗陵高山志》卷3,第5页a。显示了自尊的人格。
唐代常居舜山的陆龟蒙写道:“余在田野间,一日呼耕甿,就而数其目,恍若登农黄之庭,受播种之法。淳风泠泠,耸竖毛发。然后知圣人之旨趣朴乎其深哉。”(38)陆龟蒙:《耒耜经》,载董诰等编:《全唐文》卷801,第8417页。据陆龟蒙自述,他“有地数亩,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万步,有牛不减四十蹄,有耕夫百馀指。……乃躬负畚锸,率耕夫以为具”。(39)陆龟蒙:《甫里先生传》,傅云龙、吴可主编:《唐宋明清文集》第1辑《唐人文集》卷4,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71页。他是一位亲身参与耕作的读书人。
舜地人魏璞(字不琢),以琴书、诗文自娱,不攀权贵,与陆龟蒙、皮日休为知交。“当夏秋芙蕖香艳,鲈蒪荐美,偕二契,乘短,一觞一咏,尽水月湖天之兴。”皮日休曾向魏璞赠送五件礼物,并与陆龟蒙作《五贶诗》以纪其事。(40)顾世登等修:《毗陵高山志》卷3,第5页b~6页a。皮日休《五贶诗序》:“毗陵处士魏君不琢,气真而志放,居毗陵凡二纪,闭门穷学。……君子处乎进退而全者,由此道乎。”(41)顾世登等修:《毗陵高山志》卷4,第1页a。
唐代舜地人顾悰为饱学之士,有人劝他入仕,他回答:“祖父世守高洁,不愿与浊乱同朝。吾敬媕婀随群事女主,岂不重忝所生哉。”(42)顾世登等修:《毗陵高山志》卷3,第5页b、6页a、6页b、8页a、15页a。平时读书耕种,终老于舜山林泉。
宋代舜地人顾克明为政和年间进士,在金人入侵后,“遂绝仕进。名山古刹,随兴所之。悉捐产归嗣子,而寄迹于先人所建福山香火院,时偕二三老衲,讲楞严以逃诸漏”。(43)顾世登等修:《毗陵高山志》卷3,第5页b、6页a、6页b、8页a、15页a。舜地人翟献可,一心耕读,曾被征为兴国教授不就。绍定年间进士翟梦龙,博学能文,后“悬车归隐”。顾孺履隐居武进政成,与弟孺俊“博涉群书”。(44)顾世登等修:《毗陵高山志》卷3,第5页b、6页a、6页b、8页a、15页a。
明代江南虽然漕赋等各项征收极重,但普通之家基本能维持温饱水平。明人写道:“丰亨豫大,金瓯晏然。吴越为东南财赋地,家给户殷,民生乐业,靡兵革供饷之扰。”(45)孙鏊:《松菊堂集》卷21,万历三十八年刻本,第12页b~13页a。大部分家庭有余财供给读书生活。
原籍江阴虞门的焦丙,系朱元璋幼年出家时的蒙师。朱元璋定鼎南京,曾诏见焦丙,赐以金玉角三带,授千户之职。焦丙不久即辞归焦溪,时人把他比作东汉的严子陵。(46)顾世登等修:《毗陵高山志》卷3,第5页b、6页a、6页b、8页a、15页a。
明代画家、诗人卞荣《舜田春雨》一诗描写了舜山非常和谐的乡村农耕生活:“象耕遗迹自东西,又喜东风雨一犁。二月绿蓑行处湿,重华翠辇望中迷。若教百亩年年熟,不负双鸠日日啼。”(47)顾世登等修:《毗陵高山志》卷4,第37页b、39页b。学者桑悦《观插秧口占》一诗则叙述了在舜地乡村亲自参加农业活动的经历:“手把禾苗去插田,低头便见水中天。”(48)顾世登等修:《毗陵高山志》卷4,第37页b、39页b。从上述两首诗概可推见明代舜山一带的人们安守乡村,对农耕生活非常认同和重视。
明朝常州人孟栻《惠麓小隐记》称:“府君即信州录事,年甫六十慨然叹曰:故山榛莽,田园日芜。遂引年谢事而归,闭门不出十余载,日与高人幽士吟啸自娱,教子耕读,优游泉石,将终身焉。”(49)裴大中修:《无锡金匮县志》卷36,光绪七年刊本,第18页b~19页a。常州诸生李逊之,其父李应昇为万历丙辰(1616)进士,官至御史。李逊之“嘱子孙耕读传家,不必应试,自是遂无闻人”。(50)陈思修:《江阴县续志》卷10,民国九年刊本,第8页a。“三吴先进”贺承宗游江阴,“薛伯润怜其才,妻以女,授以田庐。承宗耕读,无斯须自佚”。(51)牛若麟修:《吴县志》卷49,崇祯年间刻本,第9页a。
耕读之家比较崇尚礼节,喜周贫济困,有些人更看淡财利。常州江阴李氏“世守耕读二百余载,藉祖诒谷,……拨田赡族”。(52)陈思修:《江阴县续志》卷23,民国九年刊本,第71页b。大宁乡人方炳昭,事母至孝,终身如赤子。叔父议析产,方炳昭把腴田美宅均让与叔父,自己只求温饱。“见人讷讷不轻发,至论古今成败、诗文得失,则详辩不已。家多藏书,经史艺术,靡不宣究。而尤溺于诗,寒暑坐卧一楼,吟讽不绝。”(53)汪其淦修:《武进阳湖县志》卷25,光绪己卯年(1879)刻本,第33页b。舜地人丁域,有道人疾病将死,留赠丁域30两银子。丁域加以拒绝,认为“此不耕之获,胡为来哉?”(54)顾世登等修:《毗陵高山志》卷3,第5页b、6页a、6页b、8页a、15页a。于此可见,丁域与披裘公一样,遵守从农耕中获取财富的原则,以砥砺品行。
清末舜地人吴镛(字卓铭)所写的《山人》诗:“山人自分老江乡,手种溪南十亩桑。”另一首诗称:“安得水田三十亩,倚门闲看舜山云。”(55)《焦溪乡志》编写组:《焦溪乡志》,第276页。表现了对耕读的憧憬。
缪氏于嘉靖年间迁入申港。入清后,“以耕读起家,代有科名,同族翰林、进士、举人、拔贡均有多人”。(56)《申港志》编审委员会编:《申港志》,第786页。晚清学者缪荃孙即是其一。焦溪邻村郑陆桥许家的厅堂悬挂着“耕读传家”的匾额。中国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的设计者许学彥就出自这个家庭。(57)张毅:《远望情怀——许学彦传》,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7页。
在清末数十年里,仅焦溪文秀才即有丁少泉、丁纯曾、丁绍千、丁义秀、刘寿春、徐谦、承乃韶、汪雪祺、沈国文、奚鸿诩、奚锦昌、奚廷选、徐沁芳、是汝庸、仇可德、徐恩荣、奚晓峰、徐廼馨、奚锡三、承钟岳、承钟隽、承隽尊、承泰宇、承继绍、承梦绍、承恩诏、潘友庆、潘堂、苏裕勳、徐伯明等30人。这些人在乡村除业农外,多是当塾师或行医。如丁绍千,“曾设塾授徒于西石桥、蓉湖、柳荡、本村等地,兼行医”;刘寿春,“早年设塾授徒,晚年行医”;徐廼馨,“中年设帐授徒,……晚年息影家园,读书颐志”;奚锡三,“年十七授徒镇之北乡”;承钟岳,“光绪十年考授予岁进士,以训导铨选。其后在家授徒,兼业医。其子槐卿为当时名医”;承钟隽,“平时手不释卷,从游者甚众”;承隽尊,“穷究医理,有炙手生春之效。光绪元年创建高山书院”;潘友庆,“常州史有良曾聘其为西席”;苏裕勳,“入泮后坐馆,学生较多”。(58)《焦溪乡志》编写组:《焦溪乡志》,第281~282、282页。显然,教书、行医均需读书。
即使武秀才,也回归耕读。焦溪查家湾人武秀才朱国范,在洞庭东山做过旗牌官,“后回乡以耕为业”,(59)《焦溪乡志》编写组:《焦溪乡志》,第281~282、282页。读书教子。
游牧民族的人也被融入耕读习俗中。江阴赤岸李氏本为色目人,定居申港后,走上耕读之路。明代撰写《戒庵老人漫笔》的李诩即是这个家族成员,其孙李如一以藏书名闻江南,曾孙李应昇为东林党人。(60)徐华根:《江阴地区著姓望族述略》,江阴市暨阳名贤研究院、江阴市谱牒文化研究会编:《谱牒研究文选》,2015年,第299页。
舜地一些家庭中,女子织布成为主要或重要收入,从而使得男子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读书。常州府无锡县“耕读桥”上联语:“沃壤植桑麻,抱布贸丝人利涉;佳名易耕读,高车驷马客留题。”(61)张伟振编注:《吴地古今桥联》,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205页。把纺织与耕读结合到了一起。常州监生朱广寿妻何氏,夫殁后家赤贫,“氏日夕纺绩以为生,历数十年,生计充裕,督两儿耕读,兼营商业,率儿妇习勤不稍懈”。(62)陈善谟、祖福广修:《宜荆续志》卷9下,民国十年刻本,第60页a。舜山翟云举妻梅氏29岁守节,家贫子幼,梅氏躬纺绩,亲井臼,以养舅姑,抚育三子。(63)顾世登等修:《毗陵高山志》卷4,第8页b。顾可充妻李氏,夫早卒,李氏依靠蚕织养抚孤子。(64)顾世登等修:《毗陵高山志》卷3,第17页b,19页b、20页b。丁某妻李氏、顾大节妻陈氏,均年青而寡,靠纺绩养育家人,抚子读书。(65)顾世登等修:《毗陵高山志》卷3,第17页b,19页b、20页b。守节妇女能独自养育家庭,尽管是夫殁不得已而为之,但从侧面说明纺织的收入较高,某种程度上可以减轻男子的家庭负担,使之有余力用于读书。
科大卫(David Faure)认为华南地区母亲的形象多是食物的供给者、温柔的典范以及家庭和地产的管理者。(66)David Faure, “Images of Mother: The Place of Women in South China,” Helen F. Siu, Merchants’ Daughters: Women, Commerce,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South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57.而苏南士人的记忆中,常有母亲辛勤织布的背影。妇女日夜守家织布,本身就给家中读书的孩子提供了最好的陪伴和专心致志的榜样;使孩童极具安全感,并使其直观地理解母亲的辛劳,激发其读书潜能。曾在舜山各书院授业的李兆洛甚至主张妇女也应该读书,以更好地学习和培养女德。(67)Clara Wing-Chung Ho, “The Cultivation of Female Talent: Views on Women’s Educ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and High Qing Period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38.2 Women’s History (1995): 193.
安乐哲(Mary Evelyn Tucker)写道,对儒者而言,一个有效的社会秩序和运转的政治制度有赖于生产性的农业。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人们的生活和生计依靠与土地的联系。如何在一个可持续的社会政治秩序中养育土地,与在人类伦常中提升道德的实践紧密相联。更准确地说,耕种土地与自我修炼是构建和谐的儒家社会并由此完成上天的旨意同源的。(68)Mary Evelyn Tucker, “Religious Dimensions of Confucianism: Cosmology and Cultivatio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8. 1,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 Confucianism in Japan (January, 1998): 19-20.
耕读传统使一般民众安于求田问舍、读书教子,过着相对平静的田园生活;使淡出官场者远离了许多不经之事,其精神方面的幸福指数显然极大地得以提高。封建统治者多视耕读为政权延续之福音、国家稳固之本,以保证民众免于饥寒、享受不同程度的教育,显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相对务实的一面。
(二)
耕读传家是中国传统家庭非常普遍的生活方式,且不仅仅限于汉民族。达斡尔人《耕读赞》:“神农皇帝开始,轩辕神仙传下,耕读二事从来没有错。……如果没有农耕,有谁养活他们;若说读书荒唐,他们怎能升官。”(69)奥登挂、呼思乐译:《达斡尔族传统诗歌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页。有学者指出:“对白族而言,耕与读是不能分离的。……耕是读的基础,读则是耕的补充。读书博不到功名,只有好好耕作,积攒得一笔钱后,为了子孙后代考虑,就应当让他们读书,从而以耕养文,以文传家,形成耕、读之间的良性循环。”(70)张金鹏、寸云激:《民居与村落——白族聚居形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91页。
谷川道雄从政治层面研究了古代贵族居住在乡村、经营田园,从而达到控御城市的目的。(71)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07~313页。从经济层面来看,放弃乡村生活进城居住,需要丰厚的收入方能保证不影响生活质量。张英写道:“人家富贵,暂时荣宠耳。所恃以长子孙者毕竟是耕读者。子弟有二三千金之产,方能城居。盖薪炭、蔬菜、鸡豚、鱼虾、醯醢之属,亲戚人情应酬宴会之事,种种皆取办于钱。”(72)张英:《恒产琐言》,见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卷36,《魏源全集》第15册,第131、132页。这种城居水平的收入绝非中小田主所奢望。可以想见,中等以下的人家移居城市后,大部分精力不得不忙于生计,极大地压缩了读书的空间。
是以张英告诫:“果其读书有成,策名仕宦,可以城居,则再入城居。一二世而后,宜于乡居,则再往乡居。乡城耕读相为循环,可久可大,岂非吉祥善事哉?”(73)张英:《恒产琐言》,见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卷36,《魏源全集》第15册,第131、132页。在这里,耕读与科举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超然的耕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人的本性,回归自然的生活。科举制度几乎从诞生之时,就遭受批评。(74)Hilde De Weerdt, “Changing Minds through Examinations: Examination Cr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6.3 (July-September, 2006): 367.有些潜心耕读者认识到科举之弊,试图回归教育的本义。清代常州学者张亮采(张太雷之父)认为:“科举时代,以有唐为开始,故唐代之风俗,可以科举代表之。天下人心所注射,不离乎科举也。唐代之科举,又可以文词代表之,无所谓实学也。……君子观于唐之风俗,而始知科举之害烈也。”(75)张亮采:《中国风俗史》,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2页。
至明清,以科举应试为导向的中国教育彻底走上歧途,教育理念以维护封建政体为根本宗旨,客观上导致应试教育成为扼杀常识的工具。常州邻邑学者顾炎武写道:“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76)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6,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46页。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也认为:“有清一代科举之毒甚于明代。盖文网日紧,士非由八股以作进身之阶,其道无由。故莘莘学子终日埋首斗室,咿唔吟哦,所希冀者,博得一领青衿,归以娇妻子耀乡里耳。”(77)怀恩选编:《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4页。宫崎市定认为,科举制使得学问竞技化、游戏化,让人死心塌地地上演着滑稽剧,一本正经地从事着荒唐戏。(78)佐伯富等编:《宫崎市定全集》(2),第99~100页。
即使科举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和进入国家权力阶层的通道,但永远无法消弭人性与常识力量的反作用。寻求耕读,甚至学而不仕,在一定意义上是人们摆脱传统畸化教育的束缚,对教育回复正轨的渴求。这些人中,既包括科举失意者,也包括科举成功者。
一些耕读者认识到传统官场的种种弊病,希望保持做人的本色,维持相对独立的人格,过着平静的日常生活。《儒林外史》首篇:“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思,总把流光误。”(79)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第一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1页。道出了传统官场的诡谲莫测。王冕之母曾言:“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么好收场。”耕读者中不乏王母式的认知,不再视做官为终极选择。甚至有朝廷官员开始认识到明代政体的反理性。辅臣王锡爵对常州人顾宪成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则认为:“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80)查继佐:《罪惟录》卷10,“顾宪成”,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18页。
士人看淡官场,致力于学术,是常州学派的重要成因。传统中国的显学是阐经、释经。梁启超评价清代学术史称:“大江下游南北岸及夹浙水之东西,实近代人文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81)梁启超著:《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264、4266页。他注意到:“旧常州府,与苏接境,而学风又分二支:迤东无锡、江阴一带,其学大类昆熟;迤西阳湖、武进,自为风气,卒乃别产所谓‘常州学派’者。”其实,常州学派更像是海上冰山的一角,其不为人见的下层是乡村无数耕读为业的家庭,它们构成了常州学派的社会基础。而士人耕田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儒家的君子观相冲突。(82)关于儒家的君子观,参见Erica Brindley, “‘Why Use an Ox-Cleaver to Carve a Chicken? ’The Sociology of the Junzi Ideal in the Lunyu,”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9. 1 (January, 2009): 50.
但在传统中国,正如马克思所说,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83)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63页。以国家名义占据着各类资源。朱元璋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当杀身灭家”,(84)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63,万历四十四年刻本,第55页。使明朝以后的耕读者无不囿于专制罗网。不与朝廷合作者不但生活举步维艰,生存都会非常危险,更不可能过上丰裕体面的生活。因此,把耕读作为科举阶梯的做法仍是明清各类家庭的主流思维。
更重要的是,耕读者同样为凡夫俗子,有望有欲,有私有疵。他们求田问舍,致力于自身和家人的饱食足衣;他们多喻利明理,甚至孜孜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客观地说,舜山地区绝大多数、甚至全部耕读不仕者并非天生鄙视官场,精神也没有升华到冰清玉洁、仙风道骨、高雅脱俗的圣贤境界,从而耻为五斗米折腰。耕读不仕、粪土王侯者多是经历无数的科举挫折和官场坎坷才修炼出的超脱心态;许多耕读者是希望维持温饱以上的物质生活,读书以待时机,一旦机缘来临,就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在多数人的语境中,“耕”为本业,其反面是被污名为末业的商业。“读”的目标不是追求真理性的知识和常识;相反,“读”多是为科举做准备,读那些“圣贤”注解的经书。甚至有耕读者是以退为进地寻求终南捷径。广义而言,在传统社会,任何耕读者均无法完全脱离官权的影响,相反只要有资源,每位耕读者与官权均保持若即若离、流转顾盼的关系。也只有官权的背书,耕读者的身价才会暴涨。
阳湖赵氏自康熙至同治年间,从赵申乔至赵烈文,每代即画一幅《耕读图》,“世各一图,图其事之大者”。共有《力田肇绪》《服畴贻谷》《庄桥施赈》《艺兰肯构》《蓬门教授》《整旅格苗》《玉堂校书》7幅。(85)黄彭年著,黄益整理:《陶楼诗文集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15年,第365页。但致力于科举一直是赵氏的追求,且科举人才辈出。
不少人把曾国藩家族视为耕读传家的典型。曾家恰恰数代致力于科场,宦者盈途。祖父曾玉屏(字星冈)曾曰:“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姓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音尘,常愿通材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礼不怠。”(8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要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2页。曾国藩本人致诸弟书称:“吾来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至要至要,千嘱万嘱。”(87)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上),第146页。曾国藩殁后谥“文正”,被视为官场楷模。
左宗棠致长子孝威:“尔年已渐长,读书最为要事。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若徒然写一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究竟是甚么人物?尔父二十七岁以后即不赴会试,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作一个好人,留些榜样与后辈看而已。”(88)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19页。左宗棠后来虽没有参加会试,但结交陶澍、贺长龄、林则徐等官场要人,对日后进入仕途极有助益。
康熙帝《示江南大小诸吏》诗称:“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民者国之本,生计在畎亩。六府既孔修,三事安可后?教民默转移,各须尽官守。户使敦诗书,人知崇孝友。”(89)黄之隽等纂修:《江南通志》卷202之2,乾隆四十四年刊本,第16页a~b。江南地方官,不少以兴文教为责,仅书院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乾隆年间,是镜在舜山之麓创办舜山学所,讲学授徒,四方慕名而来的学者络绎不绝。咸丰年间,焦溪创设鹤峰书院,举人承越任山长,学者名士群集其中,切磋琢磨,堪称盛事。(90)《焦溪乡志》编写组:《焦溪乡志》,第220页。
1875年,高山书院在大宁乡三河口文昌阁附近建成。书院由阳湖县令吴寿康选址。前五楹为门、塾,复进5楹为听事,东西号舍各3楹。后5楹为讲堂。房舍及各项器具共计花费2400缗。每年20次官师讲学、肄业生膏火、山长束修及文卷手力庸值300余缗。吴寿康出私钱850缗,焦溪等地乡绅捐集2390余缗。余钱1000缗存入焦塾典当,月息12缗。吴寿康每年另助膏火钱60缗。乾嘉年间李兆洛居三河口,“其经学文章政事为天下式,其天官、舆地诸书,至今风行海内,生徒于治经之暇旁通诸学”。(91)庄毓鋐等修:《武阳县志》卷3之1,光绪十四年刊本,第33页b ~34页b。
不少人把书院与教育划等号。其实,书院固然培养了大量读书人才,但与教育、甚至与学校教育有着极大的区别。晚清状元张謇指出:“譬如科举时代,其城乡书院遍设,而课士较勤者,则科第必盛。其仅读高头讲章,除时文八股外,一无所课者,则获隽者且阒如焉。况学堂性质,与书院全然不同:书院则人人意中皆功名利禄之思想,学校则人人意中有生存竞争之思想;书院则人人意中有服从依赖之思想,学校则人人意中有奋起独立之思想。”(92)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 ”(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164页。可以说,书院基本是为科举服务,为培养朝廷所需的没有自己思想的人才。
明清时代的道德伦常与现实生活常常脱节。作为必须经过科举,然后走向官场的知识分子,表面所言皆朝廷百姓,忧先天下,乐居人后。事实上,他们多作个人前途和利益算计,少言是非曲直。即使未走入官场者也耳濡目染了明清官场的习尚和思维,遂使整个民族的思辨能力和道德素养每况愈下。尽管绝大多数耕读者无法摆脱现实世界的枷锁,把读书→科举→做官视为人生的成功之路,但耕读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科举的影响,使部分士人看轻官场的诱惑,耕读生活甚至成为他们自重自高的心理优势。更为重要的是,耕读传统塑造和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理性基因,培养出了一部分具有自主思考能力和独立人格的人,成为这个民族的精神中坚和思想峰脊。
(三)
舜山地区耕读的典型人物较多,季札、魏璞、焦丙、李诩等均厕身其间,但以清代是镜(字仲明)最具争议,是以最值得研究。
是镜之父为是奎,焦溪人,县学生。方志称其“博雅有声,讲求正学,立日录记言动得失,自警省性,坦夷温厚,衣冠朴率。问以学者,随其浅深,反复曲畅而止”。是奎“著述甚多,尤以易象元音为心得云”。(93)汪其淦:《武进阳湖县志》卷23,光绪己卯年(1879)刻本,第27页a~b。说明是镜具有一定的家学渊源。
是镜48岁时父卒,奉柩与母合葬于舜山,在父母墓旁结庐而居。(94)汪其淦:《武进阳湖县志》卷25,第21页b、第21页a~b。常州知府黄永年《草庐记》载:“阳湖是君仲明抱道而耕于野庐,其先人之墓于舜山,始也毁甚。其问业弟子即山起书屋为就学之地,复以君庐草茨不足蔽风雨,即书屋之余材为墓庐以居,君有年矣。”(95)顾世登等:《毗陵高山志》续一卷,第5页a、7页a、25页b。柳商贤《是仲明先生传》:“[是镜]师事澄江杨太素先生斐文,教以静坐读书,专心为己之学,遂弃举业。”(96)顾世登等:《毗陵高山志》续一卷,第5页a、7页a、25页b。
文渊阁大学士陈世倌、江苏学政尹会一、河督高斌等对是镜非常赏识。“学政尹会一屏驺从造庐访之,镜潜心学问,不求闻达。总督高斌、河督顾琮与会一各疏论荐镜,力辞不出。”(97)汪其淦:《武进阳湖县志》卷25,第21页b、第21页a~b。尹会一疏:“布衣是镜者,品端学邃,居于江阴接界之舜山,教授生徒,安贫乐志,不务声华。”(98)顾世登等:《毗陵高山志》续一卷,第5页a、7页a、25页b。
然而,与是镜同时代的袁枚、阮葵生、戴震等则对他多有诋讽。曾任刑部侍郎的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专列“是镜丑态”一目,称:“江阴是镜,诡谲诞妄人也,胸无点墨,好自矜饰。”(99)阮葵生:《茶余客话》卷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2、183页。阮葵生列举是镜邪恶之事有:1.“辟书院,招生徒,与当事守令往还,冠盖络绎。”2.在书院静室中,供奉陈世倌、高斌、尹会一、黄永年四个木主(长生禄位)。3.遇雨时从小沟跳过,被童子发现,出钱堵其口。(100)阮葵生:《茶余客话》卷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2、183页。
袁枚危言耸听地致书直斥是镜:“以子之名,考子之行,吾为子之危之也!虽然,庐墓近孝,可行;不应试近高,亦可行;惟讲学近伪,且大妄,断不可行。……幸三思毋悔。”(101)李汉秋编撰:《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93页。
江瀚《石翁山房札记》“是仲明”条记载别人转述的是镜所做的另一件不道之事:“尝闻溧阳强赓廷言其为同邑史、刘二家相墓事,祸刘败史,设心阴险,强极非之。”(102)李汉秋编撰:《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第194、194页。
不难看出,阮葵生所述的是镜丑恶诸事,更像是强人所难的鸡毛蒜皮之事;称是镜“胸无点墨”尤为过分,显然是毫无依据的恶意中伤,且阮葵生连是镜的籍贯都不清楚。袁枚视是镜断不可行之事竟是讲学,而不问其讲学的效果,更是苛责于人。江瀚记述的是镜为人相墓传闻,实属无稽。堪舆之“学”本极玄乎,人言人殊。若有人拨弄,更易引发各种邻人盗式的猜测和杯弓蛇影式的疑惧。
董潮《东皋杂钞》载是镜为其胞弟告发,共30余款。罪状之多,骇人听闻;又因胞弟比一般人更了解其隐私,对认识是镜极具参考作用。考30余款罪名,竟无一条具体事实,只是泛泛称其“多有不法事”。令人震惊的是,仅凭无实据、莫须有之罪,常州知府宋楚望,不但毁掉了是镜的庐舍书院,更对其大肆羞辱:“时适有奸僧某,拥巨资,亦为宋公所恶,畲田八百亩,尽入书院为膏火费。院中告示,首举事。所谓‘经明行修’之儒,乃与淫恶不法之僧并提而论,可为浩叹!”(103)李汉秋编撰:《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第194、194页。这种羞辱对视声名重于生命的学人而言,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官员污人清誉,最擅长捏造两性疵垢。鲁迅注意到,乾隆时审理道学先生尹嘉铨的三宝等人用两性问题轻易地搞臭了被审者。(104)《鲁迅文集》第2卷,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张敬立《是仲明先生传》对胞弟告发是镜之事作了说明:时常州境内有江阴克复会、锡山复七会、靖江躬行会,“三大会赴者恒数百人;学会赴者亦数十人,先生往来讲习,无虚月。自此名日盛,忌者亦日盛。邑令圣贤,以无行不见答于先生,令恨之。先是,季弟鋐,嗜博,与伯兄戒之,不悛。……至是,令诱之,列款诬先生,守令至山,移所著书去,卒无以罪先生”。(105)朱一玄、刘毓忱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页。无论如何,若是镜有真实罪恶的话,对其恨之入骨的常州知府宋楚望绝不会让他全身而退。
段玉裁所编《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条写道:“[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当亦其时所作。仲明名镜,是姓,江阴人,客游于扬者,欲索先生诗补传观之。先生答:此书平生所志所加,功全见于此,亦以讽仲明之学非所学也。仲明筑室于江阴舜过山讲学,其人不为先生所重,故讽之。”(106)段玉裁编:《东原集·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壬子(1792)年刊本,第6页b~7页a。
览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首称:“仆所谓《经考》,未尝敢以闻于人,恐闻之而惊顾狂惑者众。昨遇明贤枉驾,望德盛之容,令人整肃,不待加以诲语也。又欲观末学所事得失,仆敢以《诗补传序》并辨郑卫之音一条,检出呈览。今程某奉其师命来取《诗补传》,仆此书尚俟改正,未可遽进。请进一二言,惟明贤教之。”(107)戴震研究会等编纂:《戴震全集》第5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87、2588页。末尾则云:“群经六艺之未达,儒者所耻。仆用是戒其颓惰,据所察知,特惧忘失,笔之于书,识见稍定,敬进于前不晚。名贤幸谅。”(108)戴震研究会等编纂:《戴震全集》第5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87、2588页。确实语含讥讽。即使戴震鄙视是镜学问,但与是镜品行无涉。
同治八年(1869),上元(今南京)人金和的《〈儒林外史〉跋》称:“权勿用之为是镜。”(109)吴敬梓:《儒林外史》附录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552页。后世学者多袭其说,视是镜为伪君子的典型。
陈汝衡称:“《外史》还十分成功地刻划了一些伪道学和假名士,就中主要反面人物应该说是权勿用吧。……他是是镜(字仲明)这个真人的化身。他表面上是奉行孔孟之道的通儒、真儒,是‘治国平天下’需要的人,是古代伊、吕类型的王佐之才。在他多次科举考试失败后,便放弃功名,一意在家守孝讲学,以道学家的面貌出现在当时社会上。实际上,他以讲学为幌子,欺世盗名,并非真正的隐逸之流。”(110)陈汝衡:《吴敬梓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35页。
曹聚仁写道:“权勿用在《外史》中是一个有趣的人物:他是清初雍正乾隆年间大怪物是镜(仲明)的影子,……是镜,江苏江阴人,生前可真是名动公卿,煊赫一时,简直是高卧南阳的诸葛孔明。可是,其人是伪君子、伪道学,给吴敬梓写成了权勿用,欺世盜名的人物。”(111)曹聚仁编著:《书林三话》,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30页。
在申士垚、傅美琳主编的《中国风俗大辞典》“假名士”条中,是镜被作为代表:“清人是镜(字仲明),‘胸无点墨,好自矜饰’,以隐居自视高洁。……这正是散曲家所申斥的‘貌衣冠,行市井’的‘卖狗悬羊’之辈。”(112)申士垚、傅美琳主编:《中国风俗大辞典》,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第601页。
何泽翰更称:“我们对于是镜的‘怪模怪样’、欺世盗名的伪装手段,可以总结为三大特点:首先造成隐居讲学的烟幕,在社会上取得‘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的空头名望;继之利用父母的丧事,拿庐墓守孝作为幌子,表现他的道德品行,建立有‘程朱的学问’的道学家的招牌,名望和道德都伪装好了,最后的目的当然可以达到,那就是和当朝宰相以及地方官吏往来交结。”(113)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9~10页。
上述学者全部是讽骂式的价值判断,而非辨析式的事实判断;就算道德可以作假,名望岂可伪装?
来新夏认为:“是镜不仅为社会所指摘,就连他的亲人也憎恶他的丑行。”“他的欺世盗名的种种手段一一被戳穿而只能留给后世诡诈作伪的无耻骂名!”(114)来新夏:《来新夏自选文集——邃谷文录》下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18页。这种说法则有违事实。直到1943年,是镜后人是贻永借焦溪南下塘是氏宗祠和徐氏宗祠的房屋,创办私立仲明初级中学,由是氏族人是贻勤任校长。“中学之取名‘仲明’,是纪念是氏祖先清乾隆时著名经学家是镜(字仲明)的。”(115)承浩如:《是贻永先生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武进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进文史资料》第15辑,1993年,第124页。说明是镜的亲人、乃至乡人非常崇敬他。
金和《〈儒林外史〉跋》断言权勿用原型为是镜,本来就带有极大的主观成分。金和母亲虽为吴敬梓堂侄女,但金和出生时,吴敬梓早已去世60余年,即便其母也未必尽知吴敬梓的真实想法。据章培恒考证:是镜由于杨太素之教而弃举业,权勿用由于杨执中之教而弃举业,金和既言权勿用的原型为是镜,则杨执中的原型自当为杨太素,但金和却称杨太素的原型本姓汤。(116)章培恒:《不京不海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0页。可见金和并不完全了解《儒林外史》的创作本意,更不了解是镜本人。叶楚炎则认为权勿用的原型为全祖望。(117)李汉秋编撰:《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94页。
退一步说,小说家言非同正史;即便正史所载也不等于事实。史不辨不用为学人通则。学者不应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行事简单地视为现实生活中某位具体人物的作为,并武断地予以褒贬。波兰学者史罗甫(Zbigniew Slupski)指出,《儒林外史》中的权勿用甚至被指控为诱拐和奸淫尼姑。(118)Zbigniew Slupski, “Three Levels of Composition of the Rulin Waish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9.1 (June, 1989): 37.同治甲戌(1874)十月开雕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例言》:“窃谓古人寓言十九。……只论有益世教人心与否,空中楼阁,正复可观,必欲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且传奇小说,往往移名换姓,即使果有其人,而百年后亦已茫然莫识,阅者姑存其说,仍作镜花水月之可耳。”(119)杜云编:《明清小说序跋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9页。也就是说,不论“权勿用”的原型是谁,他都不是真实的是镜。
事实上,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的学者对是镜的评价与态度,甚至不及当时朝廷公正与理性。乾隆十二年(1747)六月,谕军机大臣等:“朕闻江苏华亭县生员姚培谦、江阴县布衣是镜,此二人皆力学有素,闭户著书,不求闻达。尹继善、安宁既为江苏督、抚,谅必知二人之梗概,可寄信询问之。或其人才具可用,或学问可膺师儒之任,据实奏闻,候朕降旨,俟奏折之便寄去。”(120)《清实录·高宗实录》卷293,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37页上。据江苏巡抚安宁奏:“布衣是镜实阳湖人,在江阴开有讲堂,闻学臣尹会一造其庐,与谈理学,称为先生,时论迂之。访知该生向谈道学,亲没庐墓三年。”两江总督尹继善则奏称:“至江阴布衣是镜,曾究心儒先诸书,聚徒讲学,著有《孝经图颂》,词多肤浅;性醇谨,不竞声利。考其言论,识见虽近迂拘,尚能自立。”乾隆帝认为:“所奏甚公。”(121)《清实录·高宗实录》卷293,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37页上。
恩格斯谈到英国的乡绅(country-gentlemen)时指出:“他们住在自己的田庄里,出租土地,在租佃者和其他邻近居民的心目中,他们享有贵族的威望,但在城市里,由于他们出身低微、缺乏教养、土里土气,则得不到这种尊敬。”(1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清代君臣对是镜的评价,多少带有“城市里”高层人物对乡鄙之人的轻视。但就学术水平而言,拿是镜与全国一流经史学者相比,是镜显然无过人之处,清代君臣的评价还是相对公允的。学贯中西的梁启超也以当时最高的学术标准对是镜作了评析:“江阴是仲明(镜),治程朱学,然不能光大。”(12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7册,第4267页。
反过来说,清代那些学术水平高于是镜者,又有几人固守乡村,安然在底层社会课徒著述?尽管是镜学术水平未臻化境,做村师谅亦有余。充其量,在当时的社会中,是镜是一位人畜无害、循规蹈矩、自食其力的小民百姓。但为什么当时及后来的多位学者罔顾事实,以空穴来风之事对是镜极尽中伤诋毁呢?
人们首诋是镜崇尚程朱理学。无论时人,还是今人,多有不屑程朱理学者。康熙帝对道学家们的言行不一、表里霄壤的本性洞若观火:“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124)《清实录·圣祖实录》卷112,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8页上。是镜信从理学,以现在标准来看无疑是其缺憾。但理学是当时最神圣的意识形态,有学者指出,清中期礼、经之学的盛行,“就连放浪形骸的袁枚,也对西周的宗庙布局发生了兴趣,或假装有兴趣”。(125)Wei Shang, “Ritual, Ritual Manuals, and the Crisis of the Confucian World: An Interpretation of Rulinwaish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8. 2 (December, 1998): 378.更何况,庙堂之上,终日讲求理学之人如恒河沙数,他们以此获得的利益何啻千百倍于是镜。
批评者处处以中国传统的完人、圣人标准要求是镜,而理学所定各类道德准则绝非正常人类所能达到,往往需要献生殉命才算完美。简言之,理学的虚高标准,使多数理学家、甚至儒者事实上沦为自欺欺人者,包括那些批评者本人。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非常奇特的现象,不少人责他人以圣贤标准,待自己则行市侩伎略。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学而优则仕”,从而导致人们逆推出:未仕则学不优。一般说来,学问的优劣无刚性的评判依据。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在潜意识和显意识里均会把官职的高低视为与学术水平成正比。明清时代,一个人只要登上高职显爵,立雪投谒之人即如过江之鲫,许多窳陋不堪之作常有洛阳纸贵之效,即便粗鄙至俗之语也被奉为纶音格言。反之,没有爵职的布衣白徒纵使才高八斗,也常为人鄙弃讥讽。
显而易见,在中国传统社会,对人的学术评价无法避免权势的影响。居高位者无需真才实学也可获得较高的学术声望;有学术成就而没有官场资源的平民,不但难以获得公正的社会评价,反而易受中伤,贻害自身。平民学者免于位高者讥讽的生活方式无疑是箪食瓢饮、瓮牖绳枢,足不出户、安贫乐道,枵腹力学、弃利喻义,恂恂讷讷,如履薄冰。像是镜这样的学者绝非学界翘楚,更非圣贤,但学问应远优于众多高官,其遭遇应与其未得官职、尤其是与没有高位有关。
时人独仇是镜、对是镜中伤,至少中伤者清楚自己安全无后患。相反,若是镜在乡村揭橥反理学大旗,诋毁者恐同样不屑于是镜,视其为跳梁小丑,甚至置其于死地;若是镜位居极品,原来不少中伤者或唯恐奉迎阿谀而不速。
综上所述,舜山地区耕读典型人物是镜无论在当时,还是当代均有极大的争议。时人以理学的虚高标准衡量是镜,无疑是求全责备;后世学者奉金和之言为成说,视是镜等同于权勿用,以小说家言为信史,对是镜的评价更乏公允。充其量,是镜式的耕读者没有完全摆脱名利意识,他们同样是求饱思安的凡夫俗子。
(四)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的全部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126)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页。明清时代的教育、官场已极度畸形。教育不再具有开启民智、增加学识的功能;学者不再究天人之际、研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而是一成不变地阐释官方的教条和理学的成说,以维持反理性、反常识的思维惯性。但即使韬晦玲珑的官员的前途也随时随地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躬行耕读者在不同层面上看到传统体制下的教育、官场之弊,有的试图摆脱,有的试图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人性。但由于传统体制中行政权力主导社会的本质,耕读者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耕读既符合重农的国家意识形态,也在客观上为科举做准备。俗世本无圣!他们大多是传统体制的合作者,而不构成对传统体制的反动和破坏。
耕读者与体制保持一定的距离,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从是镜式的耕读者身上得以体现出来。本来,耕读者的道德要求应低于各级官员。吊诡的是,他们所承受的道德审视甚至比官员们更苛刻,充分体现了明清官场对道德话语权的垄断,揭示了封建朝廷不可能真正践行以民为本的理念,只能始终以权为本。
是镜的遭遇,可与当今社会一个极为奇怪的价值判断相类比:真小人好于伪君子。若以事实判断析之,则可见其荒谬:某人一生干尽恶事,但偶尔为一施舍小财于嗟食者之类的小善,概可属“真小人”;相反,某人一生行善,散尽家财,但若风传有两性、甚至邻里方面的小疵,基本可断定其为“伪君子”。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舆论责人之偏,几使人乐为“真小人”而惧为“伪君子”。
允许耕读者的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提倡,就在于耕读生活营造和延续了没有社会联系的无数小农家庭,让他们饱食足衣、安居乐业,比任何空洞的封建教化更有功效,比把他们折腾得朝不保夕、饥寒交迫更有利于政权的稳定。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也算体现了一定的理性和让步,并使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得以维持。从最积极的意义来看,耕读传统塑造和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理性基因,培养出了一部分具有自主思考能力和独立人格的人,成为这个民族的精神柱石和思想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