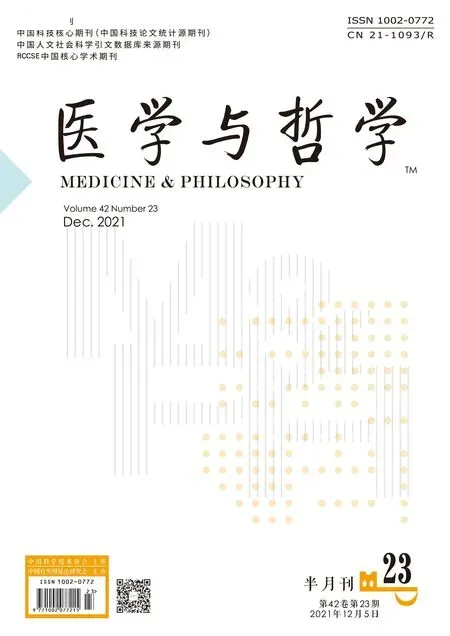国内外患者尊严研究进展*
许宝惠 李凤侠 孙 丽 胡成文
近几十年来,随着临终关怀、安宁疗护理念的蓬勃发展,患者的死亡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患者面临死亡命题时,不仅躯体上承受折磨,更多的是无法摆脱恐惧、焦虑、无助、绝望等心理痛苦,巨大的心理痛苦和认知能力下降剥夺了患者的价值感和意义感,从而患者的尊严感逐渐丧失[1]。安宁疗护的原则以患者为中心,不再以治疗疾病为焦点,接受不可避免的死亡,不加速也不延缓死亡,核心宗旨是帮助患者有尊严的逝世[2]。有文献报道患者缺乏尊严严重损害了患者的价值感,同时加速了患者对死亡的渴望[3]。生命末期患者一般会通过安乐死、自杀、安宁疗护来维护自己的尊严[4]。文献报道维护尊严是生命末期患者的核心需求之一[5],同时也是医疗护理人员的责任和价值体现。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姑息治疗建议,应该促进有尊严和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事业的发展[6]。让每一位患者能够安详而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是我们每个医务人员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本文将对尊严相关概念、尊严的起源、国内外患者尊严的研究现状等进行综述,以期为我国患者尊严照护的临床实践提供指导。
1 相关概念
1.1 尊严
尊严是有关生命终结问题中最具争议性但也是最常用的术语之一,在伦理和政治辩论中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含义,对其概念和含义尚未达成共识[7]。20世纪70年代,尊严是姑息护理和临终关怀发展的核心概念[8]。哲学家、伦理学家和法学学者认为尊严是人类固有的,原则上是抽象的、普遍的;然而,在实际护理实践中,尊严是指特定情况下的特定价值观[9]。在英国,尊严被理解为对个人自主权利的尊重,患者有权利决定和掌握自己的生活;在法国,尊严被理解为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尊重,强调的是社会所有成员的平等权利,而不是个人权利[7]。德国学者认为尊严是医疗和护理的精髓,是人权、政策和专业中的一项基本价值[10]。Rodríguez-Prat等[11]则认为尊严是一个复杂、多方面和动态的概念,它与个人身份概念密切相关。国外有学者认为尊严在生命伦理学领域是一个无用的概念。我国学者也考察无行为能力患者的尊严问题。在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中,尊严是指人和具有人性特征的事物,拥有被其他人和具有人性特征性的事物尊重的权利,换言之权利和人格被尊重。总而言之,尊严是人固有的价值属性,是一种值得被尊重、重视或尊敬的品质。正确理解尊严概念可以促进安宁疗护事业的发展,提升人们对维护患者尊严的理解和认知,确保临终患者能够平静而有尊严地落幕。
1.2 尊严死
尊严死(death with dignity)的概念不同于安乐死,安乐死即辅助死亡。尊严死是对“优逝”的追求:身无痛苦、心无牵挂、人有尊严、灵无恐惧,是理性、理想的死亡方式。尊严死即自然死,是指临终患者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让患者自然、平静、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的尽头[12]。我国学者罗点点于2006年创建的“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提倡填写生前预嘱——我的五个愿望,让患者可以自主选择临终时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统从而维护自己的尊严,开创我国大陆提倡尊严死的先河。在西方国家,尊严死已经通过立法并被广泛接受[13]。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基于本土文化倡导预立照护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ACP),确保患者在无法表达意愿的情况下,濒死患者得到的照护和治疗能够符合个人的价值观与意愿,以减少不必要的抢救带来痛苦的延续,维护濒死患者的尊严。
2 尊严的起源
尊严一词大多来源于拉丁文dignitus(功绩)和dignus(价值),但尊严最早是源于希伯来语Kavod HaBriyot(上帝创造的荣耀)翻译而来,在《圣经》《诗篇》或《先知》中没有发现尊严,而后希腊词axioprepia、semnotes被翻译成尊严使用[14]。意大利神学家(Aquinas)在《神学概要》中经常使用尊严及其同源词,尊严表明某物强大的生物链地位而具有的价值,例如,植物比岩石更有尊严;天使比人类更有尊严。在欧洲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把尊严(semnotes)定义为一种美德,重视荣誉、善良、无所欲求、拥有各种德性。Griffin在文章中提到,对罗马人来说,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值得”,在其共同的政治意义上意味着一个人的“名誉或地位”,没有地位就没有尊严[15]。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说一个公民由于其社会地位和责任,可以被视为比另一个公民更有尊严[9]。1948年文艺复兴时期的皮科·德拉·米兰德拉(Pico della Mirandola)是第一个将人的自由和尊严联系起来的作家,他在“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讲中指出,人的尊严在于选择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的能力。英国哲学家霍布斯(Hobbes)把尊严与人的权利联系到一起,他定义尊严是一个人的公共价值,就是人们通常称之为尊严的价值。德国哲学家康德(Kant)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尊严,他在《道德的形而上学》中写道“我对他人的尊重,或别人可以向我要求的尊重,是对另一个人尊严的承认”。康德的尊严观念最终与意大利神学家安东尼奥·罗斯米尼(Antonio Rosmini)以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类观念相结合,“尊严”这个词的概念性用法后来进入了正式的天主教神学,并首先被教会在社会百科全书《新纪元》中明确使用。在近代学者“世俗智慧”的话语中,普遍的人类尊严是从一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神学要求,转变为“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人平等”的世俗要求。当代尊严观念实际上是20世纪以后才发展流行起来的,总体来说,近代学者继承基于较高地位的尊严观念,并且在不同路径上发展处于不同的形态。随着尊严的发展,2002年Chochinov等[15]通过扎根理论开发出尊严模型,该模型由三个主要类别组成:疾病相关因素、尊严维护条目、社会尊严条目。2005年Nordenfelt等提出了一个有四个组成部分的尊严模型:人类的尊严、功绩的尊严、道德地位的尊严、个人身份的尊严[16]。美国学者2015年针对重症监护室患者提出尊严的概念模型:共同的人性、个人叙述、自主权利,该模型可以帮助识别这些类型的对重症监护室患者尊严的威胁[17]。随着“尊严革命”工作的开展,尊严在医疗保健中的重要性变得日益突出。
3 国内外患者尊严研究现状
3.1 国外患者尊严研究现状
3.1.1 尊严疗法
2002年尊严疗法(dignity therapy,DT)得到了发展,这是一种基于尊严的经验模型的简短、个体化心理干预方法,提供患者思考对自己人生重要的问题或回忆、传递重要事件的机会[18]。DT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国外已经成熟应用。DT适用于处于生命末期、患有威胁生命疾病的患者,如痴呆、运动神经元疾病、老年人和癌症患者。在英国,一项针对早期老年痴呆患者实施DT,使用框架分析法对生成性文档进行分析,分析出四大主题:价值观的起源、自我的本质与肯定、宽恕与决断、生命的存在意义,为DT对未来护理的价值提供了证据[19]。Rodriguez等[20]利用结构回顾法对青少年姑息治疗中应用DT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需要发展针对青少年患者的DT的评估方法。西班牙学者对DT进行系统评价,结果显示:首先,DT提高了尊严感、希望感和目标感;其次,提示未来的研究应该着重于哪些患者能够从DT中获益最大;最后,有必要对高度抑郁患者进行深入研究[18]。葡萄牙学者Julião等[21]于2013年、2017年研究DT在临终患者中的应用,研究表明DT对临终患者的抑郁和焦虑症状有良好效果,降低了患者的心理困扰;同时提出DT应该被纳入临床护理计划中,可以帮助更多的患者处理他们的临终体验。然而美国学者Dose等[22]对18名晚期胰腺癌/肺癌的患者进行DT,在抑郁评分有改善外,生活质量、痛苦、尊严、灵性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这可能与两种癌症的严重性、样本量的限制有关。加拿大学者对560名老年癌症患者进行前后试验、随机、对照、四部阶梯式楔形设计DT试验[23],该试验从2017年开始招募,研究结果将于2021年产生,这项严格的DT设计将成为老年癌症患者姑息治疗里程碑式的一步。综上所述,由于不同国家文化的差异,学者对尊严的认知、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在DT运用的过程中有不同的研究设计。然而,国外学者研究一致认为DT能够提升患者的尊严感、缓解患者的心理痛苦,最终提升患者的生命质量。
3.1.2 尊严护理干预
尊严护理干预(dignity care intervention,DCI)是一种环形封闭五个步骤干预模式,旨在指导社区护士识别并提供适当的护理,关注患者主要的身体、情感、精神或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困扰姑息护理需求的患者及家属[24]。DCI的发展基于Chochinov等[15]的尊严理论模型,目的是帮助尊严服务机构在社区护理环境中开展工作,可以为维护患者尊严提供指导。英国学者Johnston等[6]对姑息护理中维护尊严护理进行文献系统评价,对符合要求的31篇文献进行分析,确定了护理行为可以根据尊严模型主题进行分类:独立程度、症状困扰、尊严维护观点、尊严维护实践、隐私界限、社会支持、护理基调、他人负担、善后问题九大主题。根据尊严维护护理证据,确定循证护理行动,并为护士在临床实践中照顾临终患者提供指导。2017年McIlfatrick等[25]招募24名社区护士对临终患者实施DCI,研究表明社区护士发现DCI的有效性,它帮助护士提供全面的临终关怀,并协助对姑息护理患者进行全面评估,确定患者尊严相关的需求。Östlund等[26]基于DCI构建了适用于本土文化的瑞士版DCI(Switzerland dignity care intervention,DCI-SWE),提高护士的知识水平,保证姑息护理的循证质量。其他领域的护士对临终患者实施DCI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3.1.3 其他干预形式
瑞士一项研究通过将Newman的扩展意识的健康(health as expanding consciousness,HEC)理论[27]与Shaha的癌症无所不在(omnipresence of cancer,OC)的中程理论[28]联系起来,采用综合理论方法,提出了一个名为Revie⊕的干预措施。旨在让患者发现自己的潜力,确定应对事件的策略,更好地了解自己,并讨论最终生活目标或项目。通过对41名晚期癌症患者进行干预,研究结果表明Revie⊕干预措施是可行有效的,能够提高临终患者的尊严和满意度[29]。
3.2 国内患者尊严研究现状
我国对尊严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近两年来尊严的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内对患者的尊严研究主要集中在疾病晚期患者,对其他人群患者研究鲜有报道。2007年有学者研究表明生活在我国香港地区和北京的老年人的尊严感与他们的孩子关心和欣赏有关[30-31]。近几年国内多位学者研究了DT在肺癌、胃癌、肝癌、胰腺癌、乳腺癌患者中的应用,结果表明DT对患者产生了积极影响[32-34]。2011年Lin等[35]研究指出在我国台湾地区,患者的尊严在医院环境中被探讨,涉及到尊重、关怀、身体形象、控制感、自主性、隐私和保密,但还没有研究在临终关怀的背景下调查患者的尊严。2014年Li 等[36]探讨了在临终关怀背景下,采用现象学方法对9名晚期癌症患者进行半结构化的深入访谈。研究结果提供了临终尊严的概念,它表明尊严的核心含义包括重视自己和被他人重视,尊严的外在因素与内在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为护士和临床工作者提供了指南,指导他们在实施尊严护理时应注意的因素。吴梅利洋等[37]对21例晚期癌症患者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探讨西方尊严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尊严的三大因素得到证据支持,提示护理人员在工作中要重视家庭支持,规范自己的操作和言行,考虑患者的隐私和社会关系。陈丹等[38]探讨了家庭尊严干预在老年轻度认知障碍的主要照顾者应用,结果表明该方法明显缓解老年痴呆患者主要照顾者的负性情绪和照顾负担,提高希望水平。刘小红等[39]应用安心卡的尊严照护模式应用于恶性肿瘤临终患者,有效地减轻了患者的抑郁和焦虑情绪,增强了患者的尊严感。2019年Xiao 等[40]对DT在姑息治疗癌症患者尊严、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进行荟萃分析,研究表明,DT对患者的尊严、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有积极的影响。相反,Li 等[41]对10项试验的904例晚期癌症患者(对照组449例,试验组455例)进行DT有效性的荟萃分析,结果表明DT降低晚期癌症患者的焦虑和抑郁,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ang 等[42]基于中国文化背景建立以DT为基础的沟通促进机制,初步探讨了家庭参与性尊严治疗(family participatory dignity therapy,FPDT)的益处和挑战。来自国内的11位专家对FPDT草案经过两轮的修改,使之适应中国人的表达方式。研究者运用FPDT对招募的10对血液肿瘤患者及家属进行干预,初步评估了FPDF在目标人群中的可行性。FPDT对促进家庭沟通、增进家庭联系和人际关系、提高患者的希望和精神健康水平可能具有重要价值。为了进一步研究FPDT的有效性和价值,需要大样本量进行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
4 启示
4.1 我国患者尊严的思考
随着我国老年化趋势的加重、全球化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品质和需求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视生命的尊严。现阶段国内患者的尊严研究主要集中于肿瘤患者,而对于其他慢性疾病、老年痴呆、精神障碍等患者的尊严研究涉及较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要求为人民群众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健康服务。《患者权利典章》中提到患者有权利被尊重、接受关怀和照顾,尊严维护是患者的核心需求。因此,研究者需更多地关注不同患者群体的尊严研究,挖掘出患者尊严的影响因素,以便探索出提升患者尊严的干预策略。
4.2 开展我国患者尊严照护系列研究
尊严是影响患者死亡质量的重要因素,护士是促进和维护患者尊严的重要力量[43]。美国护士协会强调,维护患者的尊严是护理专业的基本核心价值。护士的行为、态度、同理心、沟通交流方式、尊重患者自主权利是维护患者尊严的重要部分。目前,我国患者尊严护理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首先,我国教育机构应该加强对护士高水平的教育和培训,借鉴和学习国外尊严护理研究干预模式。其次,开展尊严照护课程体系的研究,提高护理人员对患者尊严的认知,强化专业知识、技能和人文素养。最后,国家应加大对尊严照护的投入力度,采用多学科团队合作模式,将尊严照护灵活地运用到不同群体患者中,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
4.3 构建适合我国患者本土化的DT势在必行
DT在西方社会姑息治疗实践和政策的发展中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深刻的影响。DT虽然在我国有一定的适用性,但由于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家属和患者难以全部接受[44]。因此,构建适合我国患者本土化的DT势在必行,研究者应完善DT问题提纲、干预方式和干预流程,使得DT的用语和问题适用于我国患者。
4.4 鼓励家庭参与,构建家庭参与式尊严照护模式
有研究表明通过加强家庭完整性,包括与亲人的公开交流、互相支持、利他主义,可以增强患者的尊严感[45]。因此,为了维护和提升生命最后边缘的尊严,需要通过帮助患者在痛苦中找到意义,在家人的关爱和支持下建立道德超越,增强患者的精神可塑性;通过创造一个表达感激、实现和解、履行家庭义务和与后代建立持续联系的平台,帮助患者增强家庭联系感。家庭参与的尊严干预模式,可以减少临终患者及家人的痛苦,在死亡临近时实现希望。积极的家庭沟通可以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提高家庭凝聚力,缓解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家庭参与式的干预模式在国内已有少量的涉及,但这种研究方法仍是探索阶段,需要进一步的大样本的研究。为此,我们应该重视家庭在患者尊严照护中的重要性,倡导家庭参与患者尊严照护的行列。这也要求研究者需探索出家庭参与式的尊严照护模式,结合患者和家庭的建议和需求,提升患者的尊严和生活质量。
5 展望
维护患者尊严是临终关怀的核心价值和哲学基础。目前,随着国内安宁疗护的推行,维护患者的尊严和提高患者的尊严照护亟待更多安宁疗护人员参与。我们需要不断探讨患者尊严的内涵,深入研究患者尊严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尊严理论模型,构建出本土化的DT和尊严评估工具。维护患者尊严是死亡教育的必修课程,它能够提高患者的希望水平,缓解患者的负性情绪,最终让患者安详、平静、有尊严地走完生命最后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