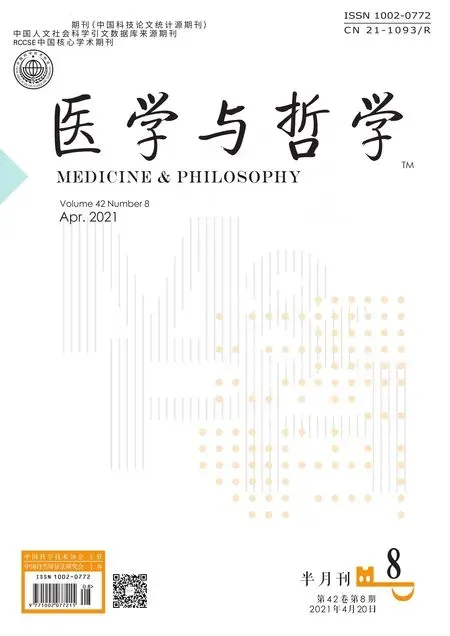《医说》中佛医医案的治疗特色探析
李亚婧 梁玲君 李良松
《医说》一书,作者为南宋张杲,自成书后,历代公私多有刊行,后世医书也常见引用,甚至远播日本、朝鲜,其医学价值与影响力不言而喻。张杲“三世授受,相传一脉”,其伯祖张扩(子充)先从学于庞安时,后又向王朴学习太素脉,尽得其妙,医显京洛,名噪江东[1],后传医术于其弟张挥(子发)和其子张师孟,张挥之子张彦仁继承家学,并传其孙张杲,为“三世之医”[2]。作为一名医者,张杲潜心五十余载编纂《医说》,是为了“弘畅其道”(书前罗序言),使传统医学发扬光大,故搜集各类书籍中的“涉医内容”,材料丰富详实,实数医书中罕见[3]。当今学者多注重其文献价值,但本书所反映的南宋及以前的医疗情况也很值得探讨研究。宋代三教合流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医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以书中也包含许多佛医内容,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佛医状况提供了依据。
实现校地共建可以使“周恩来研究专题数据库”在经费和资源建设上获得突破,特别是本土特色资源收集渠道的扩展将使“周恩来研究专题数据库”的价值得到快速提升。这一方面有助于其远期目标的实现,从而带动提升淮阴师范学院在全国周恩来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共享数据库可以有效满足淮安市社会各界对周恩来相关资源的需求,并且可以通过数据库平台将淮安市周恩来相关的本土特色资源向外推介,提升以周恩来总理为核心的旅游资源品牌,吸引游客来访,促进淮安市旅游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宣传展示淮安市以周恩来精神建市的城市形像。
佛医是以古印度“医方明”为基础,以佛教理论为指导,与中国传统医药理论与临床经验相结合,形成的独特的传统医药学体系[4]。通过对《医说》中佛医内容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知晓当时的佛医发展现状,探究佛医治疗特色,充实我国古代医学临床经验,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1 佛医疗法
《医说》有10卷,分49门类,共收录925条,其中与佛医治疗相关的内容42条,散见于各卷各门,可见当时佛医应用领域的广泛程度,归纳来说,主要包含方药、咒语、艾灸、针灸四种佛医治疗方法。
1.1 方药
佛医治病所用方药,多分为单方和复方两种形式,如《杂譬喻经·第207部》中第三十二卷所载“以一草治众病,或以众草治一病”。单方是仅用一味药物为方,多专攻一症,《医说》中就有相关的医案,如卷三《观音治痢》一文中,就是单用木香一味药物治疗久痢。单方药精力专,疗效十分迅猛。卷五中《桑叶止汗》一则中,监寺僧只用桑叶一味药,三天治好了游僧二十年的盗汗,效果立竿见影,并详细说明了桑叶采摘时间不同对药效的影响。这样的医案并不是个例,卷六《天蛇毒》一则描述了西溪寺的僧人主动为田家治天蛇毒,用秦皮一药,令通身溃烂的患者“初日疾减半,两三日顿愈”,医僧主动为百姓拔除痛苦,尽心尽力为患者医治,体现出佛医“慈航济世”的仁心善念。复方是以多种药物组合为方,如卷三载观音治眼熊胆丸方有《药用十七品》,含南熊胆、黄连、密蒙花、羌活、防己、草龙胆、蛇蜕、地骨皮、大木贼、仙灵脾、瞿麦、旋复花、甘菊花、蕤仁、麒麟竭、蔓菁子、羯羊肝,药物众多,详述用量,服药二十余日,“药尽眼明”,使医巫都束手无策的失明患者重见光明[5]。南宋佛医发展相对成熟,并不断发挥其特长,对传统中医的遣方用药亦产生深刻的影响,医僧善治妇科可追溯至晋朝,卷九中《四物汤之功》记载了医僧惠海,用四物汤治好了妇人牙痛,目前此方最早见于唐代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其作者蔺道人,相传为少林寺僧,此方经过后世医家不断地临床验证,亦被传统中医吸纳接受[6]。
为达到更快更好的疗效,医僧有时候也会多种治疗方法合用,《医说》卷六中《解蛊毒咒并方》前文已有简要介绍,咒后附解毒方“用豆豉七粒,巴豆去皮二粒,入百草霜,一处研细,滴水丸绿豆大,以茅香汤吞下七丸”,百草霜即锅底灰,对付神秘蛊毒的方子,药物十分的简单易得,服用便利,与咒合用,更加万无一失。
《医说》中涉及的佛医药物剂型也十分丰富,像丸剂有观音治眼熊胆丸方、牛黄金虎丹,散剂有獭掌散,汤剂有人参胡桃汤、四物汤,膏剂有接骨膏,洗剂有浓盐汤等,采用剂型主要与所患疾病的发病情况和病因有关。并分有内服和外用,像丹剂、汤剂多为内服,亦有涂抹、浸洗等外用方法。药物使用方式的差异,取决于药物剂型与发病部位,主要依据简便有效的治疗原则,使药物能够直达病所,尽快解除患者的痛苦。
艾灸是借助热源的温通作用达到治病效果,卷六《痔肠风脏毒》一则就展示了医僧如何运用艾灸治病,文中先提到僧人患肠风脏毒的原因是“饱食久坐”,有人提供“柏叶”一方,道场慧禅师认为“释子恐难用此”,“灼艾最妙”,并详细讲述了艾灸的位置与方法,“平直,量骨脊与脐平处椎上,灸七壮,或年深,更于椎骨两傍各一寸,灸如上数”,方法简单易行,并考虑到年长体衰的僧人,可以在肾区多灸七壮,以壮肾阳,疗效显著,“无不除根”。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方面,僧人生活习惯方面的特异性,诊治时应给予考虑,不能盲从;另一方面,医僧们身处这个群体之中,会对其病因与适用治疗方法把握得更为精准。
1.2 咒语
在对两组产妇阴道分娩结束后,分别对两组产妇的会阴损伤情况进行统计,对照组会阴完好人数为31人,会阴损伤者为31人,其中轻度损伤为20人,严重损伤为11人,完好率为50.00%;观察组会阴完好人数为52人,会阴损伤者为10人,其中轻度损伤为6人,严重损伤为4人,完好率为83.87%。(P<0.05)数据之间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大乘佛教本着慈悲心,受“不杀生”戒,是不食用肉食的,但在为人治病时,人命当前,并不否认动物药的疗效,只是较少使用。例如,卷三《梦药愈眼疾》中观音治眼熊胆丸方,就包含南熊胆、蛇蜕、羯羊肝这三味动物药。可见,在拔除病患痛苦的时候,医僧并不会完全拘泥于戒律,仍会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少量使用动物药。
1.3 艾灸
成都东郊龙泉驿片区原主要为坡地场地,地形起伏较大,原建筑物(构筑物)主要集中于较为平坦地区。随着成都市城市发展,东扩进程的推进,大量山区土地得到使用,但因地形起伏大,建筑场地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场地大挖大填工作,建(构)筑物建造前需对场地边坡进行稳定性评价及相应的治理设计。边坡问题作为拟建物地基基础设计前的主要问题摆在了工程勘察设计人员面前。
1.4 针灸
《佛说长阿含经》第十三卷言:“或为医方、针灸、药石,疗治众病。”可见针灸也是佛医常用的方法之一。卷二《工针》一则记录了僧人海渊的事迹,“僧海渊,阆人也,工针砭”,现今四川人,擅长针灸砭石治病,“天禧中,入吴楚,游京师,寓相国寺。中书令张士逊疾,国医拱手,渊一针而愈,由是知名”。医僧海渊一针治愈了中书令的疾病,因此享誉京师,可见其技艺精湛,“既老归蜀”时,还有众多士大夫作诗饯行,反映出其德行高迈,医术高超,深得众人的爱戴与尊敬。
2 治疗特色
《医说》中佛医医案涉及疾病种类甚广,包括伤寒、癥瘕、眼疾、鬲噎、泄痢、肠风、中毒、脚气等,反映出当时佛医在医疗生活中较为普及,从中可以归纳出以下五点特色。
佛医中,持诵咒语也是治疗疾病的一种常用方法,像《佛说咒时气病经》《佛说咒齿经》《佛说咒目经》等,早在宋以前就出现了,可见佛医早就把咒语作为重要治法之一[7]。《医说》中自然也体现出了这一点,卷四《观音洗眼偈》中详细记述了咒文、用法与疗效,偈曰:“救苦观世音,施我大安乐。赐我大方便,灭我愚痴暗。贤劫诸障碍,无明诸罪恶。出我眼室中,使我视物光。我今说是偈,洗忏眼识罪。普放净光明,愿睹微妙相。”患眼疾的患者需要“每旦咒水七遍或四十九遍”用咒水洗眼,眼部疾病就都能痊愈,“凡积年障翳,近患赤目,无不获痊”,效果令人惊异。在卷六《解蛊毒咒并方》也有一段咒语,“姑苏啄,摩耶啄,吾知蛊毒生四角,父是穹窿穷,母是舍耶女,眷属百万千,吾今悉知汝,摩诃萨摩诃”,是高僧用来帮助同行者避免被蛊所害,“竞传其本,所至无恙”,保障了同行众人的安全。有时也会用咒语配合药物、针灸等方法,达到快速有效的目的。
2.1 万物皆药
北凉昙无谶译《大集经》卷九,有言“天下所有,无非是药”,这一观点对佛医影响深远,《医说》中的许多佛医医案,也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卷七中汤火金疮门下《治金疮》后又一则,讲述了医僧道光用塳尘治脚伤的事迹,匠人造屋过程中不小心坠落,被一旁的锄头伤及脚痃,出血不止,但苦于村中没有药物,道光就“于门扇上撮得塳尘掩定”。“血止痛定,两日便靥坚”,效果神奇,有人就问道光“塳尘如何治得金疮?”回答说:“古人用门桯尘者,此也。”可见是参照古人的治病方法,并举一反三,灵活运用,才使工匠得到及时医治,不至于留下病根。灰尘治疮的原理,或许与草木灰止血类似,附着在伤口上的灰尘可以隔离外界空气,防止进一步感染,同时吸附血液,帮助形成软痂,起到止血的作用。卷五《米瘕》一则,记录了蜀僧道广用动物粪便治愈了“众医不辨”的米瘕之病,患者症见肌肉消瘦、神思忧虑、不吃米就会口吐清水,处方“以鸡屎及白米各半合,共炒如末,以水一中盏调,顿服”,服后患者吐出像米一样的东西,随后才痊愈。卷六中《地浆治菌毒》,四明温台间的山谷之中,有很多野生菌,有些不认识的人误食之后,轻者中毒,重者丧命,“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搅之令浊,少顷取饮,皆得全活”。以地浆为药,可治菌毒,山中居住的人“不可不知此法”。如此常见的医案可以证明,佛医用寻常物品为药,不是偶然,而是其特有的用药理念指导下的必然现象。
在沥青混凝土路面正式施工前,应先铺筑试验段。通过铺筑试验段,可以达到以下几个目的:验证目标、生产配合比;优化人员组织;确定最佳机械组合;确定各项施工数据,指导正式施工。
除了以食为药,在日常生活中,僧人也有一套独特的“以食养生”的理念,例如,卷七中《粥能畅胃生津液》一文,妙齐和尚就详细论述了饮粥养生的原理,山中僧人每日天快亮时,会饮粥以畅胃生津,不饮就会“终日觉脏腑燥渴”,并劝诫到“每日食粥,以为养生之要”,晨起之时,胃中空虚,用软糯香甜的粥来唤醒肠胃,更有利于下一步的营养吸收。妙齐和尚亦言“大抵养生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寝食之间耳”。可见感悟颇深,通过调节平日的饮食起居,达到养生祛病的效果,正是我们当下需要学习的。
2.2 以食为药
在医僧眼中,食物不仅会被用来治病,还可以用来验证是否中毒。卷六《解蛊毒咒并方》后面记载了泉州一名僧人,用白矾和生豆来验证是否中金蚕毒,“先吮白矾,味甘而不涩,次嚼生豆不腥者,是也”,通过咀嚼生豆看味觉是否正常,就可以判断出,此人是否中毒,方法简便易行,利于操作。
从以上医案中,可知佛医治病用药,并不拘泥于常见的草木,而是世间万物皆可入药,这种观点亦被后世诸多医家所接受,崇佛医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加以认可:“有天竺大医者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灰尘、动物粪便、地浆在普通人眼中都是污秽之物,而医僧却可以变废为宝,灵活地用来治病,这种万物皆药的用药理念,亦给传统中医带来许多启发,丰富了药物种类,拓展了中药学的范畴。
电网企业数据中心UPS系统往往同时也在为其他数据中心以外的重要负载供电,将这些负载完全分离出来测量有一定难度。因此可直接测量向IT负载供电的配电列头柜(精密母线)的输出功率,并累加起来作为IT负载的参考值。这样做不但考虑了UPS输出至列头柜(精密母线)输出之间的开关及电缆的损耗,也将不属于数据中心的负载分离出来了。
医僧以食为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万物皆药”特色的一个具体体现,这不仅便于寻找合适的药物,无需去药房购买,厨房即能找到,亦可在日常生活之中,就将疾病消解于无形。
2.3 多种方法合用
佛医在药物炮制方面,也有独特的认识。卷八《人气粉犀》一则,讲述了犀角非常难处理,常常所有药物都研磨好后,“而犀独在”,但医僧元达有一套处理犀角的特殊方法,“解犀为小块,方半寸许,以极薄纸裹置怀中,使近肉,以人气蒸之,候气蒸熏浃洽,乘热投臼中急捣,应手如粉”,此法十分简单易学,可以推广应用,但“今医工莫有知者”。由此可知,医僧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出一些独特便捷的药物炮制方法,丰富了药物的炮制经验。
佛医重视心法,以医治人心见长,在治病的同时,也会关注心理因素。例如,卷九《妇人》一则,提及佛医对治妇人病的看法,就认为摄心养性,才是治病的关键,“诚以情想内结,自无而生有,是以释氏称:谈说酢梅,口中水出。想踏悬崖,足心酸涩。心忆前人,或怜或恨,眼中泪盈。贪求财宝,心发爱涎,举体光润,大率是此。若非宽缓情意,则虽服金丹大药,则亦不能已。法当令病者先存想以摄心,抑情意以养性”。佛医认为心身不二,心理上产生的种种贪嗔痴,导致情想郁结于内,都会造成身心失调,引发疾病,在这种情况下,治病时必须注意调节患者的情思,重视摄心养性,只有宽心缓念才能根治,不然用药疗效也会大打折扣。
14年前,我从一所中学调进四川省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成为一名小学语文教研员。十多年来,我时时提醒自己多读书,读好书,做一个清醒的读书人。
2.4 贵人命,不拘泥于戒律
佛医中的咒语,甚至还对民间俚巫治病产生了影响,例如,卷七《治汤火咒》的咒语融合了佛道两家的用语,但对于治疗手足被火烧伤成疮颇有疗效,咒云:“龙树王如来,授吾行持北方壬癸禁火大法。龙树王如来,吾是北方壬癸水,收斩天下火星辰,千里火星辰必降。急急如律令。”其中“龙树王如来”即龙树菩萨,是南印度僧人,中观派创始者,大乘佛教论师。从咒语的意思来看,是说龙树菩萨有禁火法术,但最后一句“急急如律令”却是道教符咒常用结尾,如此佛道混杂,形成了民间巫医的特色。
此外,不饮酒也是佛教五条基本戒律之一,认为饮酒会使人昏迷沉醉,但佛医重视为众生拔除痛苦,《法苑珠林·第三十九卷》中认为“酒虽是戒禁,有患通开”,在治疗疾病时考虑到酒可以温经散寒、行气活血的独特药性,并不会完全摒弃使用酒类。卷七《被毒蛇伤》中,有人被毒蛇咬伤昏迷,老僧“以酒调药二钱”,灌入口中,将其救醒,并用药滓涂抹咬伤处,过了许久再服用一次,才算救活。《素问·厥论》言“酒气盛而慓悍”,这等危急关头,借用酒的“慓悍”之气,快速行气活血,祛除体内的蛇毒,救人性命。
佛教“五戒”是一切佛戒的基础,佛门在家弟子,便应受持,应该说要求相当严格,包括“不杀,不盗,不邪淫,不欺,不饮酒”[10]。使用动物药与以酒调药,自然是不符合戒律的,但人命当前,权衡性命与戒律孰重孰轻,医僧还是本着医者之心,体察病苦,解除疾厄,真正的大医精诚。
2.5 崇尚医德
佛教认为一切事物皆是有因有果,信奉因果论,因果业报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根本地位,许多思想的理论根基都来源于此,佛医理论自然也受到这部分理念影响,形成独特的逻辑体系,塑造了医僧高标准的医德,约束了信众们的医事行为。《医说》中的某些医案就能看出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奖励善者,惩罚作恶之人,尤其对行医之人,提出更高标准的要求。卷十《医以救人为心》云:“人身疾苦,与我无异,凡来请召,急去无迟,或止求药,宜即发付,勿问贵贱,勿择贫富,专以救人为心,冥冥中自有佑之者。乘人之急,故意求财,用心不仁,冥冥中自有祸之者。”这种崇尚医德的行为,至今依旧有借鉴价值。
全书49门,最后专列一门类为“医功报应”,反映出佛教宗教文化向医学领域的渗透,书末用典型的“因果业报”案例来强调医德的重要性,亦是作者的良苦用心。《梵网经·菩萨心地戒品》云:“若佛子!见一切疾病人,常应供养,如佛无异。八福田中,看病福田,第一福田。”作为医僧更应该高标准地要求自身,卷十《医僧瞽报》亦反映出这种观念,医僧法程少时目盲,原因前世为灸师时“误灸损人眼”,但今生勤勤恳恳十五年,诵观音名号,怜其诚心善念,不仅眼疾得愈,亦医道大行,衣钵甚富。除了医僧,这种观念对民间医生也有鞭策意义,卷十《聂医善士》一文,讲述了医士聂从志为邑丞妻李氏治病,“李氏美而淫,慕聂之貌”,几荐枕席,聂医士都没有动心,只是拒绝后速速离开,也“未尝与人言”,保住了李氏的声誉。后其好友黄靖国梦游冥间,见证了李氏的因果业报,僧人告知“此乃子同官某之妻也,欲与医者聂生通,聂不许,可谓善士。其人寿止六十,以此阴德,遂延一纪,仍世世赐子孙一人官。妇人减算如聂所增之数,所以荡涤肠胃者,除其淫也”。醒后遂告之,聂医士听闻非常震惊,其子孙后世亦果如僧言,可谓善恶有报。佛医认为善恶面前,各自的选择都会给命运带来影响,产生相应的善恶报应,应弃恶从善。
印度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BARC)近日宣布,在停堆9年并完成重大升级改造后,印度最老研究堆Apsara已重新启动。
医功报应的理念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古人对于公平公正、赏罚无误的理想医事制度的期盼和向往。对当下现实生活中医疗方面,有利于勉励约束医生的医德,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维护良好的医疗秩序,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结语
《医说》中保留的佛医医案,反映了南宋及以前佛医临床治疗的基本情况,可见当时佛医发展已经相当成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与高超的医疗技术,通过这些医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医学思想发展情况与医疗水平,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11]。从这些史料还可以看出,佛医为传统中医注入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带来不一样的医学知识与治疗手段,丰富了祖国医学宝库,对中国医学发展史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佛医对医德的重视,为促进和谐的医患关系树立了榜样,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加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