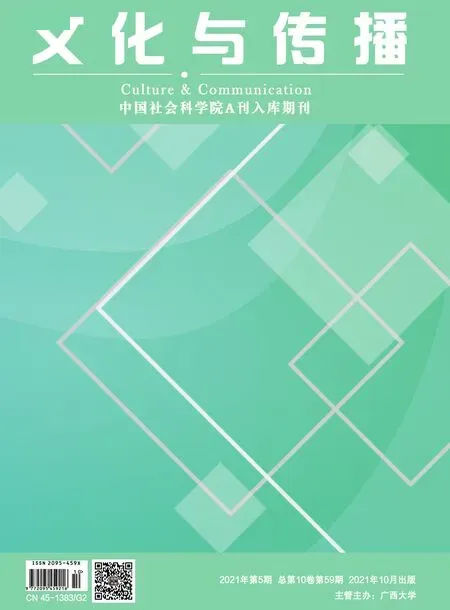刘伯承军事翻译研究综述(1981—2021)
——基于CNKI检索文献的统计分析
刘紫瑶
一、引言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两条主线,战争时期存在和平的期盼与因素,和平时期也有战争的阴影与威胁,国防安全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统治者都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1]。而今,我们虽身处和平年代,但国际风云变幻,暗流涌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
以史为鉴,可以开创未来。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共产党党史,提到国防安全与军事时,刘伯承就进入了我们的视线。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刘伯承戎马一生,战功卓著,以其军事才能与军事理论而彪炳史册。
然而,刘伯承在军事翻译及翻译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却鲜有人关注。刘伯承一生著述丰硕,留下390多万字的军事著作及190万字的翻译作品,他的军事翻译成就对中国革命及其军事斗争,特别是对中共早期军事翻译人才的培养意义重大。即使在今天,刘伯承军事思想的翻译作品依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目前,已有诸多学者对刘伯承军事翻译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本文基于CNKI知网数据库(截至2021年9月),对1981年至今的刘伯承军事翻译研究进行梳理与分析。选择近40年的数据是考虑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望本研究能为今后致力于研究刘伯承军事翻译的学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并为我国新时代的军事翻译人才培养事业做出微薄贡献。
二、刘伯承军事翻译的实践及成就
刘伯承的绝大多数军事翻译著作完成于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因而研究刘伯承军事翻译的成就及思想必须结合作品诞生的历史时代背景,也应注意到刘伯承的军事翻译成就与其军旅生涯的实践密切相关。刘伯承的军事翻译生涯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受中共中央指派,刘伯承、左权等同志前往苏联进行军事方面的学习。期间,刘伯承向周恩来同志表明,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期间,他会认真筛选一批可以为我军所用的军事教材。他在翻译军事教材的时候,特意选取了与中国国情相符的科目和教材,并根据中国实情在翻译中作了相应改动。1930年,刘伯承结束在苏联的学习后秘密回国,投入国内的革命战斗,不仅参加和主持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还在最紧张的前线指挥工作间隙完成了《苏联山地战斗》《战斗胜利的基本原则》等军事论著的编译。1932年,他前往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主持军事教育和军事翻译工作,后又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同年8月,他和左权等共同翻译了苏联红军的《军语解释》,该著作是我军首部译自外军的军语专著。刘伯承的军事翻译成就不仅仅是中国革命军事斗争的客观实践需要,也是他凭借个人军事经验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中国革命及军事斗争实践的总结。
具体的翻译行为体现了刘伯承深厚的翻译素养与极高的道德涵养。在翻译中他能很好地依据俄语本身的词义及含义,结合中国语言的文化内涵巧妙地进行跨语种翻译,在专门术语的翻译中体现了娴熟的技巧与创新。如,他在翻译中特别注意并纠正传统旧军队中各种不平等的称呼,以体现工农红军革命队伍的性质:把旧军队的军官改称为指挥员,士兵则改称为战斗员,马夫改称为饲养员等。刘伯承即使身居高位,也能够考虑到普罗大众的感受,这便是他个人的道德涵养与深厚的翻译素养的体现。
刘伯承的军事翻译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教育学理论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其军事著作的翻译和出版,适应了当时中国革命战争形势的需要,填补了国内军事战争教材翻译的欠缺,为人民军队翻译人才与军事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国内研究现状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计量统计、定量分析以及定性分析的方法,以“篇”作为分析单位,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数量特征的非介入性研究。文献的数量特征主要包括文献发表的时间及数量、每篇文献占用期刊版面的情况,以及刊载文献的期刊类别、学科分布等[2]。通过统计这些文献所包含的数量特征,可以分析和总结国内研究刘伯承军事翻译的现状。
(一)文献发表时间及数量统计
首先,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输入关键词“刘伯承翻译”,限定时间为1981年1月至2021年9月16日,发现研究始于1983年,但仅有1篇论文。截至2021年9月16日,仅有39篇文献涉及该项研究。该研究从1983年开始小幅缓慢增长,于2007年达到峰值,而后出现明显的波动,在2017年又出现了一个小高峰,而后呈下降趋势。这些数据表明关于刘伯承翻译的研究数量偏少。
笔者于39篇文献中遴选出29篇“有效文献”,10篇“无效文献”,区分的标准在于是否与刘伯承的军事翻译有“直接相关性”。如2008年胡兆才发表的《刘伯承三次历险记》,其主要内容为刘伯承军事生涯中惊心动魄的历险故事,没有任何与军事翻译相关的内容,缺乏直接相关性,故为“无效文献”。因涉密已经无法下载阅读的也视作“无效文献”,重复发表的文献只取发表时间在前的为“有效文献”。统计分析“有效文献”,得出结论:在目前所找到的39篇刘伯承军事翻译的研究中,有效文献的数量仅有29篇,约占总篇数的75%。该数据反映出刘伯承军事翻译方面有效研究的匮乏。
(二)文献占用版面统计
从文献占用版面的情况来看,除硕士论文2篇和发表于网络的文献1篇外,仅占1个版面的文献共有8篇,占用最多版面的1篇是刊载于《党史博览》2017年第4期的《刘伯承在“反教条运动”中》,共占6个版面。其余文献占用2到5个版面,共有17篇。
(三)刊载文献的期刊类别
笔者按照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进行来源期刊分类,将文献的来源分为“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来源于核心期刊的仅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S2期的《论刘伯承军事教育思想的用人艺术》1篇。从刊载文献的期刊类别看,该领域的论文尚未受到国内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关注,论文质量仍有提高的空间。
(四)学科分布
刘伯承军事翻译的研究学科分布不均,所涉及的学科多集中于中国共产党、人物传记、军事、外国语言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五大学科。刘伯承第一本军事编译著作发表于1930年,而关于它的研究直到1983年才出现,该项研究滞后了半个多世纪。与其他同等军事著作相比,刘伯承的军事翻译研究起步较晚。
总之,国内对于刘伯承军事翻译的研究有着起步晚、数量少、研究发展缓慢、学科分布不均、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仍有提升的空间等特点。
四、现有研究的主要成就及其观点综述
(一)最为全面与观点最突显的主要研究
在1981年至今的“刘伯承翻译”研究中,最为全面与观点最突显的当属王树森和陈石平、成英的研究。
王树森最早提出刘伯承军事翻译具有研究价值。他于1983年在《中国翻译》上发表《元帅与翻译》一文,提到“早在三十年代初,刘伯承就开始从事翻译和著述了”。王树森认为,“当时国内战争形势变化无常,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刘伯承在紧张的战争环境里,译校了许多军事著作,作为培训军事干部的教材,为革命战争服务”[3]9。作为被刘伯承亲手培养出来的军事翻译干部,王树森从其作为受训者自身的感受出发,主要描述了他与刘伯承之间受训、学习的故事,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刘伯承关爱下属、对待军事翻译工作一丝不苟的形象及严谨、踏实的翻译作风。
此外,王树森总结了刘伯承在军事翻译工作上的几大特点[3]10-11:第一,重视教材编译。如先翻译《苏沃洛夫十项军事法则》,再修订《苏联红军野战条令》,撰写《中文译本说明》,刘伯承认为好的翻译和好的教材资料是环环紧扣的。第二,重视外语运用和中文修养。刘伯承会亲自检查翻译人员的译文,如发现翻译不到位之处则要求立即改正,力求在翻译时能尽量做到客观准确地反映原文的意思。同时刘伯承结合中文语词及用语的属性与习惯,兼顾工农革命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实际,强调译文与原文的贴合,从而使翻译既准确地反映外文的原意,又与中文语词的属性、习惯相吻合,即翻译结果呈现出通俗易懂的特色。为了配合刘伯承的军事翻译与人才培养工作,红军大学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如订阅外文书刊、开办译员训练班等,旨在提高译员的翻译水平。第三,规范军事术语的翻译。刘伯承规定了三条术语翻译的原则,即根据实质命名、表意清晰不混淆、尽量结合并引用中国已有的军事用语等。第四,重视军事院校的开办、军事及翻译人才的培养工作。第五,重视翻译工作,特别强调译文的正确性。在翻译工作中要求刘伯承在源头上杜绝漏译错译等现象,原文如有拿捏不准的地方不能凭空翻译,必须查字典或者向专业人士请教。
王树森是研究刘伯承军事翻译的先驱之一,他肯定了刘伯承在军事翻译上的突出贡献,并在文末附录了刘伯承军事翻译实践的总结表,以翔实的数据和自身见闻证明了刘伯承军事翻译及其实践活动的深远影响。
距王树森论文发表5年后,书海出版社出版了陈石平和成英著述的《军事翻译家刘伯承》。该书基于大量历史资料,首次将刘伯承的军事翻译理论整理出来,并深入研究与肯定刘伯承的学习态度、翻译主张以及贡献。刘伯承的学习态度主要体现在其口语练习与对生词的攻克上。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刘伯承总是起早贪黑,在空旷无人的操场处练习俄语[4]14-15。由于四川口音和年纪偏大,刘伯承深感俄语学习的困难。为了取得锻炼口语的机会,他还主动帮助清洁员打扫校园。对于不懂的地方,他要么虚心请教老师或同学,要么自己死磕到底直到问题解决。勤奋苦练数月后,刘伯承就能够流畅阅读俄语书籍。刘伯承学成回国后的贡献包括首次在我国确立了军事翻译的工作地位、开创我国的军事翻译事业,如创建地下翻译所、创办中央第一所“红校”、编译出版著作《合同战术》《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等。陈石平和成英认为:“刘伯承是我国军事翻译理论的奠基人。”[4]43
《军事翻译家刘伯承》是刘伯承军事翻译研究的里程碑之一,其丰富的史料及将译文、论著与时代背景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堪称是历史学、军事学与翻译相结合的优秀案例,对后续刘伯承军事翻译的研究方法与思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具有价值的其他研究
40年来,对刘伯承军事翻译研究作出贡献的学者还有萧珊、顾育豹、陈瑞、杨柳、郭显彬、卢蓉、艾书周、杨鲁等。按照研究内容的侧重点,可以将这些研究划分为三类。
1.研究刘伯承军事翻译中体现的品质
一些学者主要围绕刘伯承军事翻译中的轶事进行研究,如:萧珊记载了刘伯承酷爱读书的故事[5],顾育豹讲述了刘伯承将他人直译的“杂种旅”修订为“混成旅”的故事[6]。该类论文多侧重于展现刘伯承的优秀品质,如勤奋好学、博闻强识、有勇有谋、一丝不苟等。然而,除了彰显人物个性,并没有形成更有深度的研究。该类论文只强调文学性,仅具有一定的了解价值,对研究其军事翻译贡献不大。
2.研究刘伯承的军事翻译中体现的教育理念
一些学者独辟蹊径,将刘伯承的军事教育学与军事翻译联系在一起研究。如:陈瑞和杨柳归纳了刘伯承的选人用人原则,其原则包括不拘一格选取人才、尊重人才爱才惜才、育才与放手相结合。刘伯承建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支军事翻译队伍,并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军事翻译风格[7]。郭显彬从军事教育学与军事翻译的跨学科视角出发,高度概括了刘伯承翻译过程中军事教育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主要特征和现实指导意义。“刘伯承在军事教育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军事教育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科学性、创造性和民族性等主要特征。”郭显彬认为,刘伯承的军旅生涯贯穿我军发展的重大阶段,他在相应阶段的军事斗争中总结出了军事理论和军事翻译理论,是我国现代军事翻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8]。艾书周则提出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以史为鉴,用刘伯承军事人才培育思想中的精华指引我军军事翻译人才的培育工作[9]。
该类研究对于我国现在的军事教育人才、军事翻译人才培养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研究刘伯承的军事翻译活动
近年来,学界也涌现了一批着眼于总结刘伯承丰富的军事翻译实践的研究。如,卢蓉从刘伯承的翻译活动入手[10],结合刘伯承的译著从“如何成为军事译者”“翻译工作关键作用”“军事律令翻译标准”“军事教材翻译标准”四个方面总结刘伯承的军事翻译思想,首次归纳出刘伯承的翻译活动具有政治性、灵活性、艰难性和权威性等特点。杨鲁总结并肯定了刘伯承军事翻译活动中体现的军事翻译思想,认为包括军语翻译在内的军事翻译应当遵循三条原则:一是应注意学习借鉴外军军语,二是应紧密联系实际为我所用,三是应编纂具有人民军队特色的军语[11]。
该类研究将刘伯承的军事翻译活动与时代背景相结合,为刘伯承的军事翻译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史料与参考价值。
五、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及解决方法
(一)不足之处
综上,所列学者的研究填补了刘伯承军事翻译的部分空白,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已经很难搜寻到刘伯承翻译、编译的底本和译本等相关资料。由于一手资料的欠缺,相关学者在具体的研究中,出现研究内容同质化的现象,这反映出刘伯承军事翻译研究内容的丰富性尚存在不足之处。
其次,很多研究者的视野与眼光仍停留或侧重于刘伯承军事翻译的某一方面上,尚未有研究者全面关注刘伯承军事翻译的整体性,因而,在研究的视野上尚有整体性研究的拓展空间。
再者,对刘伯承军事翻译研究的层次脉络稍有欠缺,具体体现在对刘伯承军事翻译的思想理论研究与翻译人才培养实践研究的时代阶段性的发展脉络与层次,尚有待相关专家廓清与梳理。
(二)解决方法
为使刘伯承军事翻译的研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现代化军事建设,服务于“强军梦”和“强国梦”的伟大实践,本文提出以下解决方法。
首先,丰富刘伯承军事翻译资料的研究。进一步拓宽刘伯承军事翻译各类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及整理,为刘伯承军事翻译研究的深化提供可靠的资料,解决刘伯承译作的底本和翻译手稿原始资料缺乏的问题。
其次,关注刘伯承军事翻译家的身份和主体性。通过编纂军事翻译史研究军事译者,可构建军事译者的身份和主体性[12]38。研究者需要拓宽并深化刘伯承军事翻译的内容,全面关注、梳理与研究刘伯承军事翻译的相关领域,解决当前研究内容同质化的问题,丰富刘伯承军事翻译研究的内容。
再次,转换研究的视角和创新研究的方法,将刘伯承军事翻译研究上升至学科的高度,基于多角度、多层面、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视野,全面考察刘伯承军事翻译。同时打破学科研究的界限,从历史学与翻译、历史学与政治学、历史学与军事学等跨学科展开研究。创新研究的方法,提倡综合运用文献阅读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田野调查法、语料库等具体的研究方法对刘伯承军事翻译进行深入研究,使其更具系统性与整体性。
六、结语
和平与发展一直都是新时代发展的主题,但居安仍需思危,国防与军事安全始终是国家安全体系中十分重要的支柱与保障。穆雷教授与王祥兵教授近年一直在呼吁译界关注军事翻译、构建中国军事翻译史研究体系。其指出,翻译乃至语言服务已成为现代战争中一种重要的战斗力,军事翻译研究引起越来越多学者和机构的关注[12]33。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翻译室主任彭天洋也聚焦军事翻译标准,从军事翻译通用标准、军事术语译写规范、语言服务采购标准、语言服务保障标准以及军事翻译分领域标准方面对军事翻译标准化建设提出了构想[13]。由此可见,军事翻译研究在我国国防安全事业中的地位与日俱增。本文以CNKI文献为例,总结了1981年以来的刘伯承军事翻译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拓宽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关注刘伯承军事翻译家的身份和主体性,转换研究的视角和创新研究的方法的建议。将刘伯承军事翻译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我国军队翻译事业与人才培养之中,立足时代发展及军事斗争的现实问题,让珍贵的刘伯承军事翻译思想再次焕发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