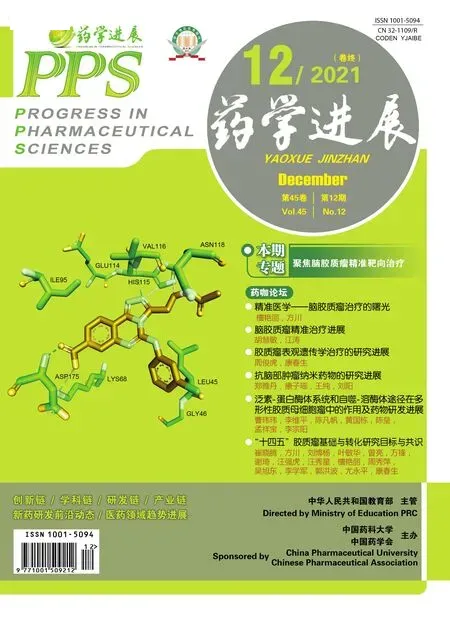KRAS突变与肿瘤代谢重编程的研究进展
李优云,柳晓泉
(中国药科大学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09)
RAS致癌基因在确定其潜在的转化能力后已成为数十年来研究的热点,实际上,3种RAS基因(HRAS、NRAS和KRAS)是肿瘤中最常见的致癌突变基因,其中KRAS突变最常见。RAS蛋白充当细胞内信号分子,将细胞外信号从受体酪氨酸激酶转导至下游效应器。KRAS突变发生在约30%的人类肿瘤中,能导致KRAS及其下游信号通路处于持续的激活状态[1-2]。尽管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KRAS突变与增殖相关的信号转导上,但现有的研究发现,致癌KRAS基因对于肿瘤转化具有广泛的作用[3]。
研究发现,在肿瘤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癌细胞需要重新编程其分解和合成代谢过程从而合成生物物质以维持细胞的存活和生长[3]。约100年前,Warburg观察到癌细胞倾向于通过有氧糖酵解代谢体内的葡萄糖[4]。在过去的20年中,对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确定了代谢重编程在肿瘤发生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葡萄糖和谷氨酰胺是癌细胞存活和增殖的主要营养来源,它们能够促进糖酵解和三羧酸循环过程。同时,细胞生长过程所产生的废物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无用的代谢产物,例如乳酸、乙酸盐、酮体和其他外源蛋白质,然而过去几年的研究已发现这些代谢产物的各种新功能,它们可作为非常规营养物质来源用于体内ATP的生成以及其他物质的生物合成[5-6]。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KRAS在肿瘤发生中具有协调肿瘤代谢重编程的关键作用。这些代谢改变对于KRAS突变肿瘤的生长至关重要,且取决于致癌基因KRAS的存在,这也提示了潜在治疗靶标的存在;此外,参与代谢途径的酶可适用于靶向抑制[7]。
来自KRAS驱动的胰腺肿瘤发生的小鼠模型的数据显示,突变激活的KRAS不仅能够驱动胰腺癌的发生,也能够促进肿瘤的增殖,因此开发出针对KRAS的疗法非常必要[8-9]。然而迄今为止针对KRAS突变肿瘤的治疗尚在临床研究阶段,以往的研究重点是针对KRAS下游信号通路的抑制,特别是针对磷脂酰肌醇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PI3K)-蛋白激酶 B(protein kinase B,Akt)-哺乳动物雷帕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和有丝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EK)-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ERK)通路,包括PI3K、Akt和MEK抑制剂的研究[10]。然而,由于不同信号通路之间存在复杂的串扰机制,对于MEK蛋白的抑制可导致KRAS突变肿瘤中ERK的代偿性激活从而导致治疗无效[11-12];而直接靶向作用于KRAS蛋白从而抑制KRAS激活的化合物如SCH-53239和SCH-54292却因为缺乏有效性而被终止研究。尽管最近开发了抑制KRASG12C的药物,但其对于大部分KRAS致癌基因仍然无效[13-14]。此外,由于KRAS已被证明可以驱动肿瘤细胞代谢重编程,针对肿瘤代谢改变或是其伴随的氧化还原电位变化也被认为是KRAS驱动肿瘤的一种潜在的治疗策略[15]。
本文旨在讨论KRAS致癌基因驱动肿瘤代谢改变的新兴作用,而不是对肿瘤代谢的全面综述;着重于总结KRAS突变在促进肿瘤代谢改变的最新研究,包括对葡萄糖、谷氨酰胺、补救合成以及脂质代谢改变的最新发现,强调了其中的某些代谢改变可能是肿瘤潜在的治疗靶标,并总结了针对这些代谢途径相关靶点的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进展。
1 靶向葡萄糖代谢
KRAS致癌基因参与代谢重编程过程最初是通过其促进糖酵解的能力揭示的,KRAS对于维持肿瘤生长至关重要,许多研究表明其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对中央碳代谢的各个方面进行重编程。在胰腺癌中,KRAS突变最先在胰腺上皮内瘤病变(pancreatic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s,PanIN)中检测到,在小鼠模型中,当KRAS突变结合P53基因缺失时,PanIN便迅速发展为侵袭性胰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PDAC)[16-17]。
在胰腺癌细胞系和转基因小鼠模型中发现KRAS突变能够增加糖酵解作用,同时也可导致糖酵解中间代谢产物分流至特定的合成代谢途径中,KRAS调控代谢改变的主要机制之一就是调节代谢途径中所涉及酶的表达[18-19]。已有研究证明KRAS可通过MEK/ERK途径的激活来上调转录因子MYC的表达从而增强糖酵解代谢过程;KRAS还能增强己糖胺生物合成途径(hexosaminebiosynthesis pathway,HBP),HBP可产生糖基化所需的前体物质,糖基化则是一种重要的翻译后修饰过程,在肿瘤发生中具有关键作用[20]。KRAS可以将糖酵解中间代谢产物分流到磷酸戊糖途径(pentose phosphate pathway,PPP)的非氧化臂从而促进核糖生物合成[18]。KRAS可介导核酮糖-5-磷酸3-差向异构酶(ribulose-5-phosphate-3-epimerase,RPE)和核糖-5-磷酸异构酶A(ribose-5-phosphate isomerase A,RPIA)的上调,导致进入非氧化臂的PPP通量增加[18]。实验证明,抑制RPIA或RPE的上调将减少葡萄糖衍生的核糖进入DNA/RNA合成,从而抑制KRAS驱动胰腺癌的体内外生长,且补充核苷可逆转其对KRAS驱动胰腺癌的生长抑制作用[18,21]。在KRAS驱动的结直肠癌(carcinoma of the rectum,CRC)中,有研究发现葡萄糖转运蛋白1(glucose transporter 1,GLUT1)表达和葡萄糖摄取的增加主要取决于KRAS突变,这种代谢改变具有明显的生存优势,可使得KRAS驱动的CRC细胞能够长期存活在低糖环境中[22-23]。研究还发现,肿瘤的遗传环境能够与KRAS突变协同作用于糖酵解活动从而促进肿瘤的生长和扩散,在胰腺癌中,已发现对氧磷酶-2(paraoxonase 2,PON2)的过表达能够与KRAS突变共同促进糖酵解,PON2可通过与GLUT1结合来增加葡萄糖摄取[24-25]。
尽管以上讨论的相关靶点在临床前研究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但是其特异性抑制剂的开发以及临床应用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如GLUT1抑制剂在体外虽能够选择性杀伤肿瘤细胞,但是由于GLUT1在众多正常哺乳动物细胞中广泛表达,这些药物的临床应用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虽然以上讨论的有关葡萄糖代谢的酶尚无特异性抑制剂进入临床,但MEK/ERK途径能够调控这些酶的表达已是事实,这也为MEK抑制剂抑制葡萄糖代谢提供了机会[18]。然而临床试验显示无论是单独还是联合用药,MEK抑制剂对于KRAS驱动的肿瘤都不是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也有可能是代偿机制作用的结果,该机制通过上调上游通路如活化酪氨酸激酶(tyrosine kinase,TK)或KRAS从而导致ERK的重新激活[26-27]。因此,鉴于ERK是有丝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信号通路的最终下游激酶,靶向抑制ERK可能在KRAS突变肿瘤中有效,这也得到了临床前数据的支持[27]。各种ERK抑制剂,包括LY321496、BVD-523、MK-8353和KO-947等目前也处于单独或联合使用的临床开发早期阶段[2,28]。
2 靶向谷氨酰胺代谢
KRAS能够维持肿瘤细胞的氧化还原平衡,且可以通过多种机制来实现。其中最重要的机制之一是其能够控制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phate,NADPH)的生物合成,NADPH能够维持氧化还原平衡且与肿瘤的生长有关。前文提到KRAS突变可通过PPP途径分流葡萄糖通量,这也说明KRAS驱动肿瘤使用了其他的碳源生成NADPH。在胰腺癌中,谷氨酰胺已被证明是肿瘤细胞中产生NADPH的关键碳源,它作为能源物质可使肿瘤细胞产生NADPH从而维持氧化还原平衡[29-30]。研究发现KRAS可通过一种新的代谢途径消耗谷氨酰胺,谷氨酰胺首先在谷氨酰胺酶(glutaminase,GLS)的作用下分解为谷氨酸,谷氨酸在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2(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2,GOT2)的作用下转化为天门冬氨酸,天门冬氨酸在细胞质中被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1(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1,GOT1)转化为草酰乙酸,草酰乙酸在苹果酸脱氢酶(malate dehydrogenase1,MDH1)的作用下转化为苹果酸和丙酮酸,苹果酸在苹果酸酶(malic enzyme,ME1)的作用下最终生成NADPH和丙酮酸[19,31]。这与正常细胞通过谷氨酸脱氢酶(glutamate dehydrogenases,GDH)代谢的途径完全不同,通过此途径生成的NADPH对于维持肿瘤细胞氧化还原平衡至关重要。已有研究证明,KRAS突变可增加GOT1的表达,并抑制GDH的表达,从而使得谷氨酰胺代谢生成的NADPH增加[31-32]。参与这一代谢改变的下游信号通路仍在研究中,重要的是,研究发现在任何水平上抑制这一途径都会导致氧化还原失衡从而抑制KRAS驱动胰腺癌的增殖[32-33]。KRAS除了能够在谷氨酰胺代谢中发挥作用,还可以通过上调核转录因子红系2相关因子2(nuclear factor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Nrf2)来维持氧化还原平衡,Nrf2能够调控活性氧清除相关基因的表达,如可溶性ME1[34]。
目前已有的研究表明上述谷氨酰胺代谢通路对胰腺癌是特异性的,并不存在于所有具有KRAS突变的肿瘤中,这提示了KRAS驱动的代谢重编程具有组织特异性,不过仍需更多的研究来评估该途径在多种肿瘤类型中的作用[35]。
在谷氨酰胺代谢方面,现有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可能的治疗方法,如在KRAS驱动的胰腺癌中,任何水平的谷氨酰胺代谢抑制都会导致氧化还原失衡从而抑制肿瘤生长[36-37]。这也说明抑制谷氨酰胺代谢与增加ROS的疗法联用具有可行性,胰腺癌模型的临床前研究数据也支持这一观点,该数据显示增加ROS和抑制谷氨酰胺代谢的疗法具有协同作用[31]。
3 靶向补救合成途径
肿瘤细胞对于代谢需求的增加使得某些肿瘤开始同时利用细胞外和细胞内来源的营养物质,其中KRAS驱动的肿瘤存在几种不同的代谢适应,这使得该类肿瘤细胞能够摄取各种代谢产物,从而为细胞新陈代谢提供了各种能源物质[38-39]。重要的是,这些清除途径已成为促进KRAS驱动肿瘤生长的关键代谢途径,从而为肿瘤的治疗提供了潜在的靶点。
3.1 靶向自噬
自噬是一种分解代谢过程,它通过降解细胞内成分来支持细胞在应激条件下的生存。该过程首先将受损的蛋白质、细胞器和大量的细胞质等包被到囊泡中,然后与溶酶体融合形成自噬溶酶体,紧接着其中的内容物被降解。降解的产物被循环至细胞质中,并参与生物合成代谢[40-41]。尽管最初认为该过程是非选择性的降解途径,但最近的研究发现在细胞中存在多种形式的选择性自噬过程[42-43]。
自噬存在于所有组织中且具有稳态功能,研究表明在KRAS驱动肿瘤中存在较强的自噬活动,且对其生长至关重要,研究发现无论是使用药物氯喹(CQ)或羟氯喹(HCQ),还是通过基因敲除抑制肿瘤细胞的自噬均表现出对肿瘤生长的抑制作用[44]。这些研究中最常见的现象之一就是自噬丧失可导致肿瘤细胞代谢功能障碍,尤其是线粒体代谢功能严重受损。CQ和HCQ在多种适应证患者中已使用了数十年,因此在患者中测试这种治疗方法具有可行性。CQ和HCQ能够通过抑制溶酶体酸化从而作用于溶酶体,能够在自噬体降解水平上抑制自噬的晚期阶段。
目前已有30多个开放的临床试验在多种癌症中使用HCQ,这些试验包括在具有高KRAS突变频率的癌症如PDAC(90%)、肺癌(30%)和CRC(40%)进行。HCQ在各种癌症类型中的疗效已有一些早期报道,结果喜忧参半。一些已完成的临床试验表明,单独使用自噬抑制剂的疗法在抑制肿瘤生长方面的疗效可以忽略,与其他疗法/药物如化疗或紫杉醇等的联合用药则有效[44-45]。然而药效学研究结果表明,HCQ的剂量即使高达1 200 mg · d-1也只在体内产生轻微的自噬抑制作用且存在个体间差异,故不能确定临床疗效由HCQ抑制自噬而产生[44]。
鉴于HCQ在体内抑制自噬的作用尚不明确,研究人员致力于开发更有效的自噬抑制剂。例如,SBI-0206965是自噬激酶ULK1的小分子抑制剂,其能抑制ULK1介导的磷酸化过程从而抑制自噬作用[46-47],SBI-0206965因此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自噬抑制剂。Spautin-1是目前正在开发的一种新型的自噬抑制剂,其可以通过增加PI3K的降解从而抑制去泛素化酶USP10和USP13的表达[48-49],这也证明了Spautin-1潜在的自噬抑制作用。与HCQ相比,HCQ二聚体化合物ROC325是水溶性的,其溶酶体自噬抑制作用更强。肾细胞癌的体内外研究表明,ROC325可诱导含有未降解代谢废物的自噬体的积累和溶酶体脱酸,对于自噬的抑制作用明显优于HCQ[50-51]。以上这些更具特异性的自噬抑制剂正在开发中,有望在临床上产生更好的治疗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自噬在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中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自噬产生的细胞死亡程序可以抑制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另一方面,自噬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可在癌症进展阶段保证肿瘤细胞生存。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噬抑制剂的临床疗效,未来的研究方向还需关注自噬在肿瘤生长中的双重作用,并开发人类自噬流(autophagic flux,指一定时间内自噬过程发生的强度,主要与自噬被诱导的强度和自噬体被溶酶体融合消化的速率相关[52])的分子标志物以及确定易感人群等。
3.2 靶向胞饮作用
KRAS突变肿瘤也可以利用细胞外能源物质,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开创性工作确定了KRAS基因的表达可以促进大胞饮过程[53]。在此内吞过程中,大部分细胞外物质被吞入称为大包囊的大囊泡中,这些囊泡最终与溶酶体融合[54-55]。有研究表明KRAS驱动的肿瘤细胞需要大胞饮过程才能生长,细胞可通过胞饮作用吸收细胞外白蛋白并将其降解为氨基酸然后进入三羧酸循环[56]。目前尚未发现控制大胞饮过程的蛋白质,但该过程可被抑制Na+/H+交换的药物EIPA阻断。研究发现,EIPA可抑制KRAS驱动的胰腺癌的生长,对野生型胰腺癌则无作用[57]。尽管目前尚无特异性的胞饮抑制剂进入临床,但溶酶体抑制剂(如HCQ)能够抑制自噬和大胞饮作用,因此有理由认为,在溶酶体水平上抑制大胞饮对于KRAS驱动的肿瘤具有抗肿瘤作用。有报道称临床上使用结合型紫杉醇(nab-paclitaxel)药物在胰腺癌患者中取得成功的一部分原因是其能够抑制大胞饮[58]。
4 靶向脂质代谢
脂质代谢,特别是脂肪酸的合成,是膜生物合成、信号分子的产生和能量储存所必需的生物过程[59]。已有研究发现KRAS突变可以调控非小细胞肺癌中脂肪酸的β-氧化和从头合成过程。KRAS能够增加小鼠模型中的脂肪酸氧化作用,它可导致调控脂质代谢的酶如长链酰基辅酶A合成酶3和 4(acyl-coenzyme A synthetase long chain family member 3 and 4,Acsl3 and Acsl4)表达显著增加。Acsl3能够促进脂肪酸吸收、保留和β-氧化,并将其转化为酰基辅酶A。研究发现无论是在发育中还是成年阶段的小鼠中,Acsl3基因缺失都不会引起小鼠任何形态的缺陷,但会抑制KRAS突变肿瘤的生长。Acsl3沉默可能具有与脂肪酸合酶抑制剂类似的作用,这也为肿瘤的治疗提供了一个潜在的靶点。最近又有研究发现,在肺癌细胞中KRAS还可以通过上调脂肪酸代谢酶如ATP柠檬酸裂解酶、脂肪酸合酶和乙酰辅酶A羧化酶从而调控脂肪酸的生成[60-61]。
KRAS突变还可以与基因改变协同作用于脂质代谢的重编程,研究发现在PDCA中,KRAS突变与信号转导GNAS基因突变具有协同作用,GNAS基因可以通过诱导盐诱导型激酶(salt-inducible kinases,SIKs)从而支持PDAC生长;蛋白质组学研究结果显示这一途径与脂质代谢和过氧化物酶体的含量增加相关,过氧化物酶体是长链脂肪酸加工和醚脂类脂质生成所必需的细胞器,这也说明KRAS突变与脂质的代谢重编程有关[62]。
临床前研究发现抗生素cerulenin通过抑制脂肪酸合成酶(fatty acid synthase,FAS)来抑制肺癌细胞的增殖,虽然目前尚未进入临床,但FAS有望成为一个潜在的治疗靶点[63]。
5 结语
与正常细胞相比,肿瘤细胞具有更旺盛的代谢活动,这与代谢途径以及能量物质来源的不同有关,这种代谢重编程作用为肿瘤治疗提供了潜在的靶点。各项研究已证明KRAS在肿瘤的代谢重编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但要充分利用这些潜在的靶点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首先,KRAS突变对代谢的改变具有组织特异性,这是肿瘤起源组织的内在代谢通路与KRAS相互作用的结果,未来的研究也需要考虑到KRAS对于代谢改变的组织特异性。其次,需研究肿瘤微环境对于KRAS驱动的代谢通路改变的影响,包括缺氧、营养物质有限情况下的代谢变化[64]。要了解这些复杂的关系,需要使用复杂的肿瘤模型以及在体内进行代谢追踪研究的能力。
本文讨论的许多相关代谢途径均尚无特异性抑制剂,目前的研究仍处于靶向代谢重编程的初级阶段,预计将有更多的抑制剂能够靶向相关代谢通路。同时,了解如何更好地将相关代谢途径的抑制剂与现有的化学治疗药物联合使用也至关重要,这需要进行大量的临床前研究。随着代谢重编程研究的进展,科研人员势必对KRAS驱动肿瘤的代谢重编程有进一步的理解,其有望通过识别和抑制KRAS突变肿瘤中所产生的代谢改变开发出有效且耐受良好的治疗方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