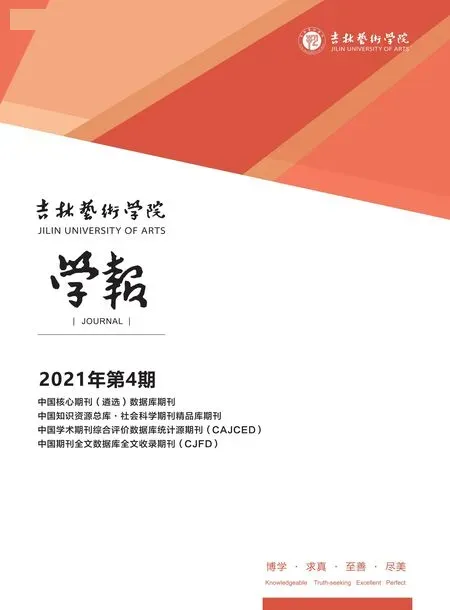蔡楚生“向左转”时期电影中的地理意象
张文毓 赵宜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234)
蔡楚生是一个受到左翼进步人士的帮助而思想观念发生巨大转变的电影创作者。在初任导演时,他所拍摄的影片即使涉及社会生活,却沉溺在富人阶层的幻想中。1932年拍摄的《南国之春》和《粉红色的梦》正是他此时思想的见证——“局限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不触及真正的社会问题”[1]。但随着“九·一八”和“一·二八”的相继发生,左翼思想涌入文艺界并占据主流,使得“一九三二年”成为“中国电影‘向左转’的一年”[2]。在这样的背景下,蔡楚生开始“向左转”——秉持左翼思想创作具有进步倾向的影片。
在这里有必要对“向左转”做进一步的说明。这里的“左”,即其作品不再局限于富人阶层的个人生活中,而是反映与时代贴合的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暴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毒害,从而唤醒大众。而“转”既是身份的转变,也是创作倾向的转变。前者又可分为创作者的身份和影片主人公的身份,创作者从做“白日梦”的艺术家,转变为具有进步要求的艺术家;影片主人公则从花花公子和摩登女郎,转变为革命者或受压迫的贫困百姓。在创作倾向方面,则是“从纯粹商业化的电影工业向政治机制的转型”[3]365,从单纯地展现喜怒哀乐,转变为将其与社会时代生活相联系,暴露现实的黑暗与不合理,从而渴望推动社会进步。
蔡楚生在受到左翼思想的影响后开始“向左转”,于1933年拍摄《都会的早晨》,这是其创作风格发生转变的第一部影片。于1934年拍摄《渔光曲》,标志着其左翼电影创作走向成熟,并为其带来巨大声誉。于1935年拍摄《新女性》,较之前更具有希望和信心,其“思想又向前发展了一步”[4]340,并最终完成了“向左转”。自此,“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下,在政治上他从来不曾动摇,在创作上也从未走过弯路”[4]259。
综上所述,可以对蔡楚生“向左转”时期的作品做一个大致的定位说明:从《南国之春》到《粉红色的梦》为蔡楚生“向左转”之前的时期;从《都会的早晨》到《新女性》为蔡楚生“向左转”的时期。本文以地理意象为切入点,对这两个时期进行对比研究。首先,应当关注这些影片中的地理意象所具有的不同意义。其次,需要阐明身份对形成地理意义的影响。最后,应当注重观众的层面,即地理意义对于不同的接受者而言有着不同的效果。
一、地理意象的建构与转变
蔡楚生在“向左转”之前和“向左转”时期的电影作品中,对地理意象的描述及赋予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城市可以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令人神往的现代化摩登之地,也可以是此时令人感到厌恶的邪恶之地。乡村也同样如此,既可以为人们提供栖身之所,又可以剥夺人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与此同时,不同的地理意象背后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也大相径庭。城乡的美好意象否认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这符合富人阶层的意识形态观念;而城乡的消极意象则深入表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面貌,这与具有进步观念的人士和底层民众的意识形态观念相吻合。
1.城市的地理意象
蔡楚生“向左转”之前的影片中的城市意象多是积极的和令人向往的。在《南国之春》中,大学生前往巴黎,城市使其流连忘返,赞叹不已。一同去往巴黎的同学搂着女伴,说道:“巴黎的月色照在你的脸上,格外的漂亮。”在此,城市不仅仅被塑造为充满机遇之地,更是一个神话之地。更为积极的城市意象则是体现在《粉红色的梦》中。在这部影片中,有一天夜里,罗文打开窗门,望向那灯火通明的夜上海。在夜色的映照下,他翻动手里的杂志,看到一张写有“交际之花,李慧兰”的照片。在这里,上海的现代性被电力和通俗杂志所建构,成为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之后,当罗文外出“交际”时,其妻子在家苦苦等待丈夫的归来,而当交际花李慧兰外出寻乐时,其丈夫罗文在家扮演等待者的形象。在影片的结尾,在罗文一无所有之际,妻子回到城市的家中,重新给予罗文家的温暖。从中也可以发现,不论谁是等待者或是归家者,城市中的家始终承载着剧中人物的希望与幸福。此外,影片还使用较多的篇幅展现罗文与李慧兰幽会的场面。二人在高档餐厅跳舞之余,又共饮红酒。李慧兰在补完妆之后,又邀请罗文来家中做客,周围的其他男人不免投来羡慕的眼光。城市在此被营造为一个摩登世界,充满着五光十色的夜生活。可以说,在蔡楚生“向左转”之前的影片中,城市意象的建构多是伴随着一种正面态度。
而蔡楚生“向左转”时期影片中的城市意象则多是消极的和令人恐惧的。在《都会的早晨》中,“蔡楚生强调了环境对人的身心的影响,既合情合理,又在一正一反之间接触到深刻的社会问题”[5]。影片中同父异母的兄弟命运差别巨大。同样在城市中,自幼被遗弃的哥哥生活贫寒,与穷车夫相依为命、艰苦度日,而养尊处优的弟弟却道德败坏、贪恋女色,企图采用卑贱的手段来占有兰儿。在这里,城市不仅使穷人的生活雪上加霜,同时也是滋生富人罪恶的温床。在《渔光曲》中,小猫和小猴因乡下生活贫困,打算去上海投奔舅舅。可城市的失业问题也相当严重,为数不多的工作机会却有一大群人争抢。当富人在脸上涂胭脂粉时,小猫、小猴为了捡垃圾不受欺负和排挤,则往脸上涂黑泥。在《新女性》中,韦明被各种不怀好意的男人骚扰着,在吃安眠药却未死之际,被报纸大肆宣扬“女作家自杀”。上海的摩登在此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性别歧视和人身依附。尤为重要的是,曾经参与城市现代性构建的出版业,在此时则成为消费生命的罪魁祸首。可以说,在蔡楚生“向左转”时期的影片中,城市意象的建构多是伴随着一种负面态度。
差别巨大的城市意象既代表着蔡楚生不同的创作思想,也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受到左翼思想影响之前,蔡楚生站在富人阶层的立场上,多展现小资情趣,将城市营造成为一个充满现代性以及光明未来的地方。之后,其思想则是站在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士和劳动群众的立场上,多展现贫苦的生活,将城市塑造为一个贫富差距巨大并且充满危险的地方。这两种不同的立场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前者渴望活在“粉红色的梦”中不愿离去,拒绝求新求变;后者则要求从“粉红色的梦”中醒来,深入现实生活,关注底层民众的利益。
2.乡村的地理意象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意象的意义不仅是由其自身所建构的,也是由乡村所赋予的。对城市的积极或消极的理解,依赖于乡村的肯定或否定性意象。同上述一样,任何一个地理意象都是复杂和矛盾的,这背后隐藏着不同的意识形态。
在蔡楚生“向左转”之前的影片中,对于城市意象的塑造多是正面的,与此同时,对乡村意象的塑造也是正面的。在《南国之春》中,大学生与少女在江南水乡结识之际,楼宅上的阳台成了二人传情达意的场所。大学生的同学在起哄中说道:“最好是有个女人讲讲爱情,是吗?”之后,在同学的帮助下,大学生借用唱歌和写信等方式,向少女表达了自己的爱意。在阳台的另一侧,在月色的笼罩下,少女也憧憬着即将到来的爱情。在影片结尾,大学生得知少女重病,从巴黎飞奔而来,二人在水乡终获重逢,爱情再一次显得弥足珍贵。在《粉红色的梦》中,妻子被罗文赶出家门,无处可去的她来到乡下。在这里,妻子继续给小孩教课,孩子们在房前玩耍着,妻子时不时还用余粮喂飞来的鸽子,乡亲邻里间也充满了关怀。在蔡楚生“向左转”之前的电影中,乡村与城市一起被建构为积极之地。
在蔡楚生“向左转”时期的影片中,对于城市与乡村的意象塑造则都是负面的。在《渔光曲》的开篇字幕中就提到“东海,……不同的人,对它作不同的看法”。小猫与小猴自幼在乡村生活,极其艰难,暴风雨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母亲为了生计只好去何家做奶妈,小猴则因为没奶吃而变得体弱多病,再加上严苛的税收与新渔船的影响,更是使乡村的渔民叫苦不迭。满怀抱负的何家少爷子英,海外学成归来后渴望改良渔业,但以失败告终。小猫与小猴在城市历经磨难,碰巧得到子英的资助,却被诬为抢劫而入狱。出狱后,乡下的房子却遇到火灾,妈妈和舅舅葬身火海。在急需接纳与包容的时候,乡村没有如过往一样,而是与城市共同被建构为消极之地。
蔡楚生“向左转”之前和“向左转”时期影片中所提供的关于城市和乡村的意象是截然不同的,与此同时,其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也大为不同。在“向左转”之前的影片中,城市与乡村都是从积极的方面得到表征的,隐藏在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未受到进步思想影响时,蔡楚生倾向于用一种积极美好的眼光来看待城市与乡村,忽略了其中的矛盾,似乎要否认冲突存在的证据,这与富人阶层的思想立场相联系,即拒绝深入生活、关注底层大众,拒绝求新求变。在“向左转”时期的影片中,乡村与城市都是从消极的方面得到表征的,隐藏在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则可以理解为:蔡楚生在转变之后,倾向于以一种进步的思想来考察城市与乡村,在积极求变的心态中暴露出城市与乡村的种种不合理,强调冲突的存在与剧烈,这与始终站在劳动群众立场的进步人士相联系,即真实展现底层生活,推动开展社会改革。
二、身份对地理意象的影响
地理意象的建构是与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身份相联系的,这些身份是由阶层、性别等来定义。阶层与性别的身份可以将城乡塑造为富人阶层眼中的积极意象,也可以将其塑造为具有进步观念的人士和底层民众眼中的消极意象。
1.阶层身份
在蔡楚生“向左转”之前的影片中,阶层身份促成了积极的乡村与城市意象。在《南国之春》中,大学生与银行家之女都属于富人阶层,少女拥有阔气的豪宅和精心打扮的妆容,大学生回家成婚后去往巴黎留学,少女则积郁成疾,二人之后又在水乡重逢,最终少女因病去世。在这些属于富人阶层的人物及其事件中,城市与乡村都得到了美好的表述。同样在《粉红色的梦》中,作家罗文、教师妻子和交际花李慧兰,同样都是富人阶层。罗文的醒悟、妻子的忠贞、交际花的放荡,也同样都是从积极的角度构建了城市与乡村的意象。罗文与交际花的恋情证明了城市所具有的吸引力;妻子在城市或者乡村教书,其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在乡村还有余粮喂飞来的鸟),即使在城市被丈夫抛弃,也依旧在城市与丈夫团聚;交际花不论结婚与否,身边总是有男人追求。从中可以发现,在城市或乡村中生活的富人阶层,对他们造成烦扰的源头似乎只是情感问题。与此对应,这背后隐藏了另一层面的现实——在城市或乡村中生活的其他阶层(主要指底层民众),对他们造成烦扰的源头是否也同富人阶层一样仅仅是因为情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些影片借由展现富人阶层的生活状况,在城市与乡村的表征中展现了一幅歌舞升平的景象,而使景象产生涟漪的,也仅仅是情感波折罢了。
在蔡楚生“向左转”时期的影片中,阶层身份则促成了消极的乡村与城市意象。在《都会的早晨》中,哥哥自幼被生父抛弃,被穷车夫收养,长大后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工人。而弟弟则是在富人的生活中长大,成为一个道德败坏、为私欲而不择手段的人。哥哥的生活十分困苦,之后又被弟弟从中作祟关进监狱,同是属于底层的兰儿因拒绝富家公子的求爱而被软禁起来。在此,城市的地理意象被两个不同的阶层共同建构为消极之地——不仅使富人堕落并滋生其罪恶,也使穷人饱受贫穷与欺凌。在《渔光曲》中,小猫、小猴属于底层贫苦民众,而何子英则属于富人阶层,但都以悲剧收尾。
在这里,影片似乎传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在城市或乡村中生活的人们,不论是富人阶层还是底层民众,生活多少是不尽人意的。这样的设置暴露出城市与乡村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如贫富差距、失业现象等等,城市与乡村也就被建构成消极的意象。而这样设置所渴望得到的反馈是唤醒了包含各个阶层的大众,使其认清城市与乡村的真面目。
2.性别身份
身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于性别,“我们不能将称为‘性别’的东西与生活体验的其他方面隔离开来”[6]。性别也参与了城市与乡村的意象建构,并且同阶层一起,混杂在意识形态之中。
在蔡楚生“向左转”之前的影片中,女性仍是作为男性欲望的载体,继续扮演着传统的性别角色。在《南国之春》中,少女因情人回家成婚而变得郁郁寡欢,在水乡的家中长卧病床,最终含恨离世。大学生同学的女伴,在巴黎求学途中,也依旧迷恋在男人的怀抱与城市的月色中。在此,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的地理意象中,女性作为男性和爱情的附属品,只能活在富人阶层的情感世界中。在《粉红色的梦》中,罗文的妻子不论是在城市中被抛弃,还是重新回归城市中的家庭,亦或是在乡村著书《弃妇泪史》(稿费有助于罗文的生活),仍然依附于男性并以男性为中心而存在,而男性则是两性关系的主导者。与此相对应,交际花李慧兰也在扮演着传统的性别角色——“作为图符被展示给男人——这些观看的主动控制者——用于凝视和享受的女人”[7]。将这种性别关系与地理相联系,可以发现女性仍在扮演着传统的性别角色,强化了主流性别秩序,也参与了城市与乡村积极意象的建构。在这种积极意象之中,传统女性与富人阶层相联系,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富人阶层的、美好的城市和乡村存在的前提在于,女性仍是传统的女性。
在蔡楚生“向左转”时期的影片中,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女性仍是男性欲望的投射,更为关键的是,在阶层的“观照”下,女性“解放”了。在《都会的早晨》中,兰儿属于底层民众。一方面,她成为富家公子欲望投射的对象,但是她的泼辣大胆、疾恶如仇,拒绝富人的求爱与奢侈的生活,放弃跨越阶层并坚定地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女性在此不再是男性或物质的附庸,而是在阶层的压迫下与男性作斗争,夺回自己的阶层与性别的尊严。在《新女性》中,韦明属于富人阶层,而李阿英则属于劳动阶层。不论是影片中韦明照片的大量出现,还是在汽车上裸露的双腿,在此女性仍属于传统的性别定位。而李阿英则打破了这种性别划分——她极具进步观念,为了保护韦明,与男人大打出手,并占得上风。在这里,女性不再是依靠男性而存在,甚至有足够的力量去反抗来自男性的压迫。将此与地理相联系,背后的意识形态显而易见——城市是黑暗且动荡的,富人阶层女性韦明受到各种男性的侮辱最终自杀,而正确的做法显然是像进步女性李阿英那样奋起反抗。
但是在这里,性别的概念被模糊了,“这种论调的言下之意无非是阶级问题更为‘适时’和紧迫,相比之下性别问题则明显过时了,它早已在现代性的进程中被解决了”[3]422-423。但实际上,在“向左转”时期具有左翼思想的电影中,传统的性别秩序仅仅是受到了挑战,并没有被完全颠覆,性别问题也只是被阶层问题悄然置换。身份由多重变为单一,由涉及性别、年龄等变为只涉及阶层,从而使得意识形态的传达也由隐蔽变为直白。而这样以阶层代替性别来传达意识形态的表述方式在日后得到了延续,例如,蔡楚生在1947年与郑君里合作拍摄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影片虽然是围绕一个男性与三个女性的命运来展开,但其身份问题的核心仍是将性别属性替换为阶层属性——三个女性代表了两种阶层。正如戴锦华所言:“在百年中国电影的绝大部分里,占据绝对主角位置的女性形象不仅是为召唤男性主体而生的结构性暂存,而且始终是五四时代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中的激进性载体。”[8]
三、城乡意象所形成的道德恐慌及其反作用
在蔡楚生“向左转”之前和“向左转”时期的电影中,地理和身份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社会价值与意识形态是借助包含道德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地理范畴来发挥影响的”[9],也就是说,地理意义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要想发挥其作用,离不开道德方面的助力。此外,也应当注意接受者形成不同解读的情况。“不同的观察者或读者基于不同的位置也就会提出对于这些意象不同的解读”[10]。这些影片中的城乡意象,可能会在观影公众中形成一种与进步人士和底层民众愿景相反的一种解读,从而使这些城乡意象产生一种反作用。
1.道德恐慌
蔡楚生“向左转”之前和“向左转”时期影片中的地理形象及意义可被视为一种道德的陈述。正如李欧梵所言:“左翼剧作家对中国观众的思想影响不是通过直截了当地向他们灌输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因为审片制度),而是在故事层面上带给观众一种新的叙事模式,描写那些或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中的小市民,以此来折射社会等级,并用善、恶世界之间的比较来隐喻城市和乡村。”[11]
在蔡楚生“向左转”之前的影片中,城市与乡村的意义都是与正面态度相联系的。与此同时,影片中人物的身份也在促成这一美好意象的建构,从而得到这样一种道德图景——在女性仍然作为传统的女性而存在的作用下,富人阶层在城市与乡村的生活十分美好。在蔡楚生“向左转”时期的影片中,这种美好的道德图景被颠覆,从而形成一种道德恐慌。传统的城市与乡村的美好意义不复存在,二者都与消极态度相联系,不论是富人阶层还是底层大众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女性作为传统的女性而存在也无济于事。这种“道德恐慌”可视作由以下三方面构成。
首先,影片将城乡的消极之处和生活在其中的各个阶层的异常行为放大。在《都会的早晨》中,弟弟道德低下、欲壑难填,在翻动情色连环画时产生幻觉,竟忍不住捧画亲吻起来。之后,弟弟企图勾引兰儿,被断然拒绝。他为了达到此目的,不惜将贫穷的哥哥诬陷入狱,还将兰儿软禁在自己家中。而且,影片会进行一种“预言”——相同的问题会再次发生且有可能变得更糟,所指涉的人群将会扩大到所有人身上。在《渔光曲》中,何子英学成归国,看到小猫、小猴的悲惨生活于心不忍,便将他们带回自己家,然而富有的何父却将其赶出去。之后,何父因公司破产而选择自杀,何子英也放弃了自己对渔业的改良计划。
其次,影片用负面话语来描述城乡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从而将其变成一种寓言,最终形成一种道德恐慌。在《渔光曲》中,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也不论是富人阶层还是贫苦大众,最终都是以悲剧而告终。何父的公司破产,何子英的船业计划也无法实现,小猴又因捕鱼受重伤而死。影片通过对城乡中不同阶层、不同经历的描述,形成了一桩桩悲剧寓言,最终对大众造成一种道德恐慌。
最后,城乡的负面形象与富人阶层和底层民众生活中的腐朽或贫穷,皆被视为由社会颓败所导致。在《都会的早晨》中,致使哥哥遭受贫困的原因在于,其父亲为和富家女结婚而抛弃了他和母亲。弟弟则由于生活极度奢靡,恃富纵欲,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又如,在《新女性》中,学校的校董为占有韦明而将其辞退,并以钻石相诱惑。而韦明服毒后,又被新闻记者进行炒作,悲痛欲绝,直至死亡。影片通过将个人的悲剧与更大的背景相联系,将营造道德恐慌的矛头直指社会层面。
“许多意义重大的社会伦理在电影这个公共空间中被‘循循善诱’地传授给民众,最后通过道德感化——而非意识形态建构——的形式达到启蒙和改革之功效”[3]231,使这种道德恐慌所产生的意义十分深刻。它号召生活在城乡中的富人阶层脱离传统的束缚,如女性对男性的依赖,放弃腐朽的生活和对现实的幻想,重新选择一条光明之路。同时也号召被黑暗所压迫的劳动人民积极反抗,拒绝走上堕落之路,从而驱逐城乡意象中的黑暗。
具有左翼进步思想的电影通过将意识形态置换为道德,对大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的手法在谢晋的电影中得到传承。“谢晋电影完成的是双重的置换:不仅将政治置换为道德,也将悲剧置换为正剧”[12]。正是这种置换,避免了这类影片成为令人容易遗忘的单纯说教,而是历久弥新,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依旧被无数人所关注、所留恋。
2.道德恐慌的反作用
然而,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并不确定更广大的观影公众实际上是否同意影片中所营造的这种道德恐慌。在这里,更广大的观影公众主要指的是小市民。“小市民……中的大多数从事低或中低层的工作,之所以被冠上一个‘小’字,是因为他们非精英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年轻、有限的教育背景和眼界”[3]122。事实上,在小市民的眼中,这种道德恐慌可能并不会被过分认同。
从这样的视角来看,蔡楚生“向左转”之前和“向左转”时期的影片所形成的道德恐慌,可能会违反营造道德恐慌所渴望最初的目标,在其接受者中可能会产生一种反作用。很多群体实际上会欢迎媒体通过负面表述对其所创造的道德恐慌,因为这有助于宣传该群体及其文化。观影群众对于这些影片中积极或消极的城乡意象,可能都是持有一种认同的态度。他们可能尤其欢迎对于城乡的负面描述,因为它可以更广泛地宣传该地理及身份的意义。
在“向左转”之前的影片中,观影公众中的小市民对于城市与乡村的积极意象可能会是一种相当认同的姿态。在《南国之春》中,借由大学生与少女的相识和重逢,以及大学生与同伴出国求学,共同将城乡营造为美好世界。在《粉红色的梦》中,罗文在魅力十足的夜上海中的种种遭遇,以及其妻子在乡下田园诗般的生活,同样将城乡营造为积极意象。在这些影片中,不论是将城市与乡村的属性归结为积极美好,还是将富人阶层中的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归为传统范畴,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十分符合当时小市民生活中所渴望出现的景象——女性仍是传统的女性,富人阶层的生活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是美好的。影片借由建构地理和身份的意义,对这种富人阶层意义下的美好生活起到了宣传作用,在当时受到了广大小市民的欢迎。而正是这种富人阶层对城乡地理意义的态度与描述方式,遭到当时左翼进步人士的反对与批评,使得接下来的影片开始“向左转”,但其效果可能与左翼进步人士的期冀产生了出入。
在“向左转”时期的影片中,小市民对于城市与乡村的消极意象可能也会是一种相当欢迎的姿态。在《都会的早晨》中,城市使同父异母的哥哥自幼贫寒、饱经磨难,同时也滋生了娇生惯养的弟弟道德败坏。在《渔光曲》中,小猫、小猴挣扎的生活建构了消极的乡村意象,也通过何家在城市中的腐朽生活对城市意象进行了负面描述。在《新女性》中,韦明不但继续在城市中扮演着男性欲望的载体,也被城市中代表着现代性的出版业消费生命。这些对城乡意象所作的消极描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迎合了小市民的心理。这些影片在起到教化作用——展现城乡黑暗、号召人们反抗——之余,也同时呈现了小市民所渴望的生活的残影——城乡中阶层的鸿沟无法逾越,女性继续臣服于男性,并且对这种左翼进步人士意义下的落后又腐朽的生活作了一定程度的宣传。“向左转”时期影片中所呈现的城乡消极意象,从“反作用”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它违背了影片所企图形成的道德恐慌,对左翼进步人士眼中的负面城乡意象做了宣扬,进一步建构了小市民对于所谓现代生活的想象。
四、结论
在蔡楚生“向左转”之前和“向左转”时期的影片中,地理意义、身份属性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向左转”之前,城乡的意象均是积极的,富人阶层在其中的生活十分美好,女性仍是扮演着传统的角色,这体现了此阶层活在“银幕之梦”中不愿离去和拒绝求新求变的意识形态;在“向左转”时期中,城乡的意象均是消极的,无论何种阶层在其中的生活都是不尽如人意的,富人阶层的女性受到男性的侮辱最终自杀,而正确的做法是像具有进步观念的女性那样奋起反抗,这体现了要求深入现实生活并关注底层大众利益的意识形态。如果将这种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道德,违背它就意味着形成了道德恐慌,那么结果则是促成社会变革。但从小市民的接受层面来看,这种道德恐慌可能会形成一种反作用——恰好对左翼进步人士眼中的破败景象进行了符合小市民口味的宣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