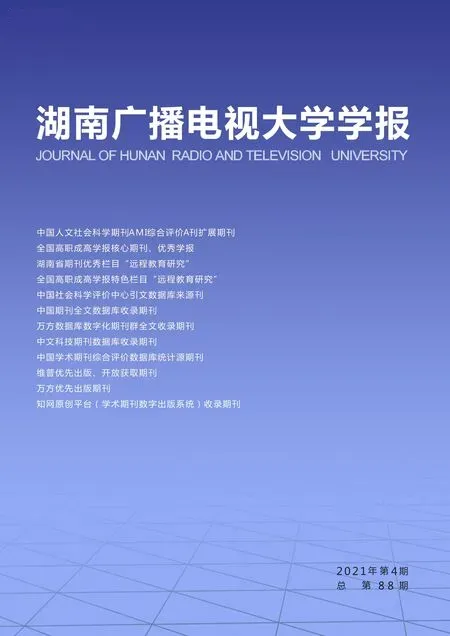亲亲相互规正是儒家伦理的要则炯戒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考辩
杜纯梓
(湖南开放大学,湖南长沙 417000)
一、父子相互隐过的训释与儒家一贯倡导的持直守正道德原则相忤
《论语·子路》有这样一段记载: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177
对其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学者们大都感到疑惑。古代经师作了很多疏证辩说,力图在亲情和公义之间寻求一种合理解释。但按亲亲相互匿过隐恶的故训,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孝义两难、情理相悖的矛盾。非但如此,且将儒家所确立、恪守的“义以为上”[1]244的道德伦理体系轰然摧毁,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都蒙上了一层难以抹去的尘垢。“文革”中有些人借此大加挞伐,批判说:“这充分暴露了孔老二是一个两面三刀、惯于说假话的政治骗子。”“孔子鼓吹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为历代反动阶级所继承,成了一切反动派大搞宗派、结党营私、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的信条。”[2]有的学者现在仍坚持认为“父子相隐”是一种违法悖德、亲情至上的狭隘落后观念,危害了法律正义与社会秩序,并提出:“对于现实生活中某些屡见不鲜的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儒家的血亲情理精神也应该说是难辞其咎,……我们也不应该低估它在诱发这些腐败现象方面所具有的温床效应。”[3]网络上更有人称孔子是“虚伪家的祖师爷”[4],指责“儒家文化虚伪到了令人发指”[5]。
真的是这样吗?“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该如何训释,才符合经文原意和孔子思想,这是关系到儒家伦理乃至中华文化本根本源的问题,确有必要利用今天所能掌握的全部材料(含出土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取科学方法,破解文字密码,拨开千年迷雾,揭示其真正内涵。
古今解经者普遍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隐”作“隐匿”“隐讳”“容隐”理解。桓宽《盐铁论·周秦》:“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岂不欲服罪尔?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之相坐也。”[6]66皇侃《论语义疏》引范宁云:“若父子不相隐讳,则伤教破义,长不孝之风,焉以为直哉?”[7]925邢昺《论语注疏》:“子苟有过,父为隐之,则慈也;父苟有过,子为隐之,则孝也。孝慈则忠,忠则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隐,告言父祖者入十恶,则典礼亦尔。”[1]177-178钱穆直接将“隐”解作“掩藏”,认为父子相互掩藏其恶“亦人道之直”,“此乃人情,而理即寓焉”[8]。父亲犯了罪过,儿子替他隐瞒;儿子犯了罪过,父亲替他隐瞒;而且将这种相互隐瞒包庇纳入正义合理的范畴,这与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相违背,也与孔子本人大力提倡且一直信守的道德箴戒不一致。众所周知,中国古代长期处于以血亲为联系纽带的宗法社会,为了社会稳定、国祚恒久,很早就形成了崇德尚义、趋仁向善的文化传统,注重培养持直守正、著诚重信的君子人格。北京大学哲学系郑开教授指出,在诸子百家之前很明确是一个德的时代,儒家的思想脱胎于之前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9]。
《尚书》作为古代政事之纪,其中“德”字凡203见[10]。圣圣相受的先王贤臣们反复强调:“克明俊德,以亲九族”[11]27、“皇天无亲,惟德是辅”[11]453、“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11]206。商王盘庚郑重告诫臣民若心存邪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11]239。福善祸淫乃天之恒道,“凡犯禁绝理,天诛必至”[12]。由此,历代圣贤对人的行为操守提出了一系列严格、明确的规范约敕,最主要的是立公心、行仁道、遵礼义、守诚信、明是非、止邪僻。《尚书·周官》:“以公灭私,民其允怀。”[11]486《逸周书·武纪解》:“本之以礼,动之以时,正之以度,师之以法,成之以仁。”[13]《墨子·贵义》:“万事莫贵于义。”[14]《刘子·履信》:“人非行无以成,行非信无以立。”[15]荀子还响亮地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16]385种种明训炯戒,形成了内圣外王的德性伦理。
孔子“之谓集大成”[17]447。他忠实继承并光大了自尧舜以来所形成的道德传统,在礼崩乐坏的周季竭尽全力弘道救世。他仁善笃诚,恪守直道,力主改过归正,鄙弃邪佞奸伪,旗帜鲜明地反对愚忠愚孝。《论语》里记载孔子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1]229“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1]165“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1]213“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1]52《孝经·谏诤章》记载,当曾子问:“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18]47孔子回答说:“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18]48在《孝经·事君章》中,孔子明确表示:“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18]54在孔子看来,不义则谏,补过救恶,这才是大孝大忠。孔子这种思想主张在《左传》《荀子》《孔子家语》等典籍中也有记载,如《左传·昭公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19]1542又如《孔子家语·六本第十五》:“孔子曰:‘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君无争臣,父无争子,兄无争弟,士无争友,无其过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国无危亡之兆,家无悖乱之恶。父子兄弟无失,而交友无绝也。’”[20]121再如《荀子·子道》: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孔子趋出,以语子贡曰:“乡者君问丘也,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何如?”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有奚对焉?”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16]386
孔子的这些言论清楚阐明了父子亲情上的道义原则,“当不义则争之”,不能盲目顺从,不能偏私遮掩。所谓“父失之,子得之”,是说父亲犯了错,儿子得以补察纠正。这里的“得”相对“失”而言,不单是察知,且包含有帮助改正、促使改正的意思。孔子历来十分重视改过。人之过失在所难免,孔子的认识和态度是“过则勿惮改”[1]121,“过而不改,是谓过矣”[1]216。他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1]84深为忧虑,期勉人们“能见其过而内自讼”[1]68,勇于徙义迁善。孔子清醒地看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1]49。立公心、去私情则寡过。他庆幸自己“苟有过,人必知之”[1]96。他对弟子们坦诚表白:“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尔乎。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1]93他为人坦荡正大,从不隐讳掩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小人之过也必文”[1]257,只有小人才文过饰非。
基于这样的理性认知、道德主张和君子素行,“吾道一以贯之”[1]51的孔子怎么可能在听到叶公夸耀他们那里有个躬行直道的人,“其父攘羊,而子证之”[1]177,就说出父子要相互隐瞒的话来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孔子对叶公说的这段话里前后两次提到“直”,一为“吾党之直者异于是”,一为“直在其中矣”。何谓直?直即正直,行道践义,无偏无党,不阿私,去邪恶。它是德性伦理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命题,是儒家理想人格的主要支撑。战国楚系文字“德”从直从心,鲜明而典型地体现了古人以“直”为德的本质属性这一伦理观念。《尚书·舜典》有“直哉惟清”[11]78,《尚书·洪范》有“无反无侧,王道正直”[11]311。《韩非子·解老》释义甚明:“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21]《论语》中22处论及“直”,其中18处表示正直,4处指具有正直品德的人,足以看出孔子对正直之德、正直之人极其推崇。《论语·颜渊》有“质直而好义”[1]167,“质直”与“好义”对应,“直”与“义”相通。《论语·卫灵公》有“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1]214,朱熹注:“直道,无私曲也。”[22]67孔子将“直”提到了人的生存法则高度,他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1]78人的生存在于正直,不正直的人能够生存下来,那是他侥幸逃避了本该降临其身的祸殃。孔子极力主张“举直错诸枉”[1]21,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置于邪曲的人之上。他对“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1]209的子鱼十分赞赏,由衷叹曰:“直哉,史鱼!”[1]209孔子对直德的肯定与提倡,在中国古代社会无以复加。
考察古代道德规范和伦理哲学,“直”还有“正人曲”的意蕴与功能。《左传·襄公七年》:“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孔颖达疏:“能以己正正人之曲,是为直也。”[19]978这一义项古时常用。《诗经·小雅·小明》有“正直是与”,《毛传》:“正直为正,能正人之曲曰直。”[23]939《鄘风·定之方中》有“匪直也人”[23]238,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直当读如正曲为直之直。”[24]俞樾《群经平议·尚书三》:“正直者,以正道相切直也。”[25]孔子这位杰出的思想家对此自然熟知,他所说的“直在其中矣”与“正人曲”不无关系。
父子相互隐瞒过错,与“直”完全悖反。朱熹说:“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22]56朱熹的这个观点影响很大,直到现在仍为学术界的倾向性看法。被列入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的《论语》(钱逊解读)同样认为:“父子相隐,是人之常情。孔子说父子相隐,直在其中,是从人情的角度,肯定这是人间真情的表现,没有矫饰。”[26]这种人情说从基本逻辑和义理上都经不起推究。子隐父过,让其陷于不义,而不予匡救,终受大辱;父隐子过,任其滑向深渊,罹难遭祸。这样既悖天理,又害人情,何直之有?既然孔子用“直在其中”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行为初衷与效果进行解释,认定施为者为“吾党之直者”,说明父子相隐的实际所指也在道义范畴之内,它和“直”存在合乎逻辑的内在联系。只是这种“直”与直躬证父之“直”在行为表现和效果上有所不同。这样一来,破解“隐”字的密码就成为我们探求经文真义的关键。
古代一些经学家已经觉察到隐恶瞒过之说难通,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隐”并不是全无是非、悖逆义理,而蕴含有是非不枉、几谏自讼的内容。何焯《义门读书记》:“何故隐?正谓其事于理有未安耳。则就其隐时,义理昭然自在,是非之理,即在恻隐羞恶之中,并行不悖。在中之解如是,原无所枉也。苟有过,人必知之,直之至矣。”[27]何焯认为“隐”的本身就体现了是非之理。王夫之承认父子相互隐过为“德之偏长”,他为之辩说:“凡一德之成,皆必顺乎性之所安,而不任其情之所流与气之所激。惟中国为礼义之邦,先王之风教陶镕其气质,而士君子以学术正其性情,故人咸有以喻其天性自然之理,则虽偏有一德者,亦不碍于大中至和之道。”[28]750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这种亲亲相隐不是简单、孤立地隐匿其过。“有几谏教诲以善之于先,特不济恶文奸以求逞于后。……礼以养之,义以裁之,不期然而自然。”[28]751王夫之将几谏教诲、礼养、义裁引进“隐”的义域。当代也有学者意识到父子相互隐恶的训解与儒家的德性伦理、孔子的一贯思想主张不相吻合,而对“隐”的真旨实义有不同的推测和领悟。有人说:“孔子所谓的‘子为父隐’并不否认儿子有持义劝谏父亲过错的义务,毋宁说持义谏亲是孔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29]有人说:“‘隐’不是包庇过错,而是为了启发觉悟,让他自己‘见其过而内自讼’,更好地认识改正。”[30]由于受“隐”的本义所牵,这些论述总是闪闪烁烁、遮遮掩掩、弯来绕去、扑朔迷离,未能直接、透彻达旨明理。《说文解字》:“隐,蔽也。”[31]305就“蔽”而论,无论如何辗转引申,它与恻隐羞恶、几谏教诲、礼以养之、义以裁之、持义谏亲、启发觉悟、认识改正等都是扯不到一起的。因而,这类添加于隐匿之上的“应有之义”只是一种推测附会之辞,不能信人,同样未能揭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真正涵义。
在前些年儒家伦理争鸣中,王弘治发表的《〈论语〉“亲亲相隐”章重读——兼论刘清平、郭齐勇诸先生之失》一文指出:“‘隐’一般也可以被认为是‘檃’的假借字”,“隐为‘矫正’是古代经师未曾注意发现的一个义项”[32]。廖名春先生对这一训解非常赞赏,并进一步补充新证,力挺其论[33]。由于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误读已久,自汉末开始多个朝代又将“亲亲相匿”纳入律例,以致人们普遍将亲亲相互隐匿过错看作儒家亲族伦理的固有内容。加之王弘治、廖名春等学者的疏证论析还不够充分,个别地方存有罅漏,辩驳诘难之声不断,矫正之说并没有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延续至今的儒家伦理争鸣,无论持哪一种观点的学者仍袭从旧训,偏执其理,曲为辩说,讼争依然未息。
二、“隐”读为“檃”是破解“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本旨的关捩确诂
联系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儒家伦理的价值取向,遵循古汉语文字的表意特征和发展演变规律,全面考察、深入分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中“隐”的确切所指及其所承载的思想意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断定“隐”通“檃”、表矫正是完全站得住脚的。父亲帮助儿子改正错误、儿子帮助父亲改正错误应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本旨确诂。
(一)“檃”是出现较早的古语词,它与“栝”“檃栝”名异而事同
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檃”在春秋时期就存在于古汉语文字体系之中,并广为应用。《说文解字》收录了‘檃’字。虽然《说文解字》出自东汉,但许慎基于前人成果和当时的语言事实,对所收录的文字作了认真而广泛深入的考证稽验。许慎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覩,靡不兼载。”[31]316《说文解字》探源稽古,有根有据,确凿可信,当时世间万事万物都能从这本书里看到。许慎还特别提到编著《说文解字》时参阅查核了《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等古文版本。录入其中的“檃”是远古先贤适应生产生活需要而创造的、具有特定含义并应用于语言交际实践的文化符号和信息载体。与其他古语词一样,它同样具备“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31]316的特性和效用。
何为“檃”?许慎的解释是:“檃,栝也。”紧接着训“桰”(“栝”的异体字):“檃也”[31]123。按照《说文解字》训释体例,“檃”与“栝”属于绝对互训词(又称标准式互训词、狭义互训词)。许慎采取这种以物释物、称名互易的方式解说字义,今人看起来虽有些茫然,但他已清楚表明“檃”和“栝”意义相同,所指称的是具有同样性质和功用的事物。据统计,《说文解字》中这类绝对互训词有200多组[34],其中的名词如:“匏,瓠也”[31]18、“瓠,匏也”[31]150;“甑,甗也”、“甗,甑也”[31]269;“袂,袖也”、“褎(袖),袂也”[31]171;“棚,栈也”、“栈,棚也”[31]124;“箝,籋也”、“籋,箝也”[31]97;“辕,輈也”、“輈,辕也”[31]302。这类绝对互训词绝大多数指称同一事物,只是名称不一样,少数有细微差别,其核心字义和基本所指则完全一致。由于时代久远,“檃”“栝”到底是哪一种物件,有何功用,典籍中没有见到对其单个字所作的具体描述和阐释,后人渐感生疏。值得注意的是,南唐徐锴将“檃”与“檃栝”相联系,释云:“此即正邪曲之器也。”[35]117传世文献中对“檃栝”的性质与用处阐述甚明,如《荀子·大略》:“乘舆之轮,太山之木也,示诸櫽栝,三月五月,为帱菜敝而不反其常。”杨倞注:“櫽栝,矫煣木之器也。”[16]369《荀子·性恶》有“故枸木必将待櫽栝、烝、矫然后直”,杨倞注:“櫽栝,正曲木之木也。”[16]315-316《荀子·法行》:“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櫽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16]391《尚书大传》:“夫檃栝之旁多枉木,良医之门多疾人,砥砺之旁多顽钝。”[36]《盐铁论·大论》:“俗非唐、虞之时,而世非许由之民,而欲废法以治,是犹不用隐括斧斤欲挠曲直,枉也。”[6]69
“檃栝”是用来矫正曲木、使之平直或成型的器具。将不规则的竹木置于檃栝之中,经过蒸煣,达到挠曲直枉的功效。现在湖南乡村竹艺匠人仍使用此类工具,其做法是在一根粗大的树干上横着凿出若干对穿的圆洞,洞与洞相隔一定距离,然后竖立起来,装置稳固。如果要把竹子弄弯,就将竹子穿过木洞(木洞起固定作用),再用火烧烤,待竹子烤到有一定柔性后慢慢用力下压,使之达到所需的弧度,冷却后即成曲形。如果要把弯曲的竹子弄直,同样将竹子的一头伸进木洞套牢,用火烤煣后按水平线拉压使直。这种工具也可用于矫正曲木。原湖南广播电视大学(现湖南开放大学)制作的《益阳小郁竹艺》专题片中有这种工具的实物展示,其功用与古书上所记载的“檃栝”一致。农耕文明的器具有着较为稳定的传承特性,从古至今无大的变化。这也可以证明,古代“矫煣木之器”确实存在。
“檃栝”是由“檃”和“栝”这两个绝对互训词组成的复合词。既然“檃栝”为“矫煣木之器”“正曲木之木”,其构词成分必然与之紧密相关。王筠《说文句读》:“古书多檃栝连言,许君则二字转注,以见其为一事而两名,群书连用之为复语也。”[37]766本文列举的绝对互训词大多都有连言用例,有些后来已经固定为复合词。再如“栊”和“槛”单用,字义为关养禽兽的栅栏,“栊”和“槛”连用亦指关禽兽的笼槛。祢衡《鹦鹉赋》:“顺栊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38]“薪”和“荛”单用表示柴火、柴草,复合词“薪荛”同样指柴草。《孙膑兵法·十陈》:“薪荛既积,营窟未谨。”[39]“檃栝”与此类似,“檃栝”即“檃”,“檃”即“檃栝”。古代经学家就常以“檃栝”(櫽栝、隐括)释“檃”(隐)。如《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有“君子慎隐煣”[40]160,孙星衍注:“隐与檃通,谓檃栝。”[40]161《汉书·刑法志》有“劫之以势,隐之以厄”[41]922,臣瓒注曰:“秦政急峻,隐括其民于隘狭之法。”[41]923
南宋毛晃、毛居正父子所著《増修互注礼部韵略》指出:“揉曲者曰檃,正方者曰栝。”将“檃”“栝”二字的词义范围作了具体区分。王筠认为:“分为两义,盖非许意也。”[37]766按照《说文解字》释义通例,凡同类事物有明显差异的都带附加成分予以说明。如:“疾,病也”、“病,疾加也”[31]154;“桎,足械也”、“梏,手械也”[31]125。
许慎对“檃”和“栝”的解释未带任何附加成分,相互为训。周秉钧先生审校的《说文解字今释》直接点明:“檃又名栝。”[42]如果二者确有揉曲、正方之迥异,许慎断不会如此训释。例如“规”“矩”,“规”是正圆之器,“矩”是正方之器。《说文解字》所作解释是:“规,有法度也”[31]216,“巨,规矩也,从工象手持之”[31]216。而没有以“规”释“矩”,也没有以“矩”释“规”。
从以上分析可以推定,“檃”“栝”“檃栝”所指一也,都是矫正竹木邪曲的工具。
(二)“隐”通“檃”是本有其字的通假,先秦时期这一通假已成为语用常例
“正邪曲之器”的“檃”字从木,隐省声。字形两体相叠,笔画繁多,难于书写契刻。由于古代书写工具和承载媒介落后,古人用字有从简求易的习惯。春秋时期,“櫽”就常常省作“隐”。战国以后“檃”字渐而不用,凡表“櫽”义都以“隐”代之。对这种用字现象,古代学者早有察识。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古今皆借隐字为之。”[35]116王筠《说文句读》:“亦省作隐。”[37]767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檃,亦作櫽,亦假借作隐。”[43]这种用字现象在古典文献中屡见不鲜,桂馥就列举了多个例证:
《书·盘庚》:“尚皆隐哉。”传云:“言当庶几相隐括共为善政。”《大戴礼·卫将军文子篇》:“自设于隐括之中。”注云:“孔子曰:‘隐栝之旁多曲木也。’”《鬼谷子·飞箝篇》:“其有隐栝。”注云:“施隐栝以辅其曲直。”《韩非·难势篇》:“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显学篇》:“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圆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括之道用也。”蔡邕《郭有道碑》:“隐括足以矫时。”《公羊解诂叙》:“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后汉书·邓训传》:“训考量隐栝。”[44]
“隐”借作“檃”,字形上是简省,语义上属通假。徐灏《说文解字注笺》:“隐之本义盖谓隔阜不相见,引申为凡隐蔽之称。”[45]《故训汇纂》中所汇集的“幽蔽也”“翳也”“塞也”“匿也”“伏也”“藏也”“避也”“私也”“微也”“不见也”等义项[46],都是由“蔽”引申而来。很明显,“隐”的词义与“檃”迥然有别,它们之间不存在转注关系。至于有的学者将“审度”认作“隐”的本来意义,也是经不起推究的,“审度”跟“隐蔽”没什么关联。《尔雅》郭璞注和《广雅·释诂》中提到的“隐,度也”[47],是“隐”的假借义,这一意义来自“檃”(檃栝)。将曲木置于檃栝中蒸煣矫正,就引申有量度、审度之义,前人常以“隐审”“隐度”连称。故而,“隐审”“隐实”“隐校”“隐核”中的“隐”都应读为“檃”。凡古注为“度”的“隐”通常都通“檃”。
这种本有其字的通假,被通假字往往易于忽略,而将通假字误作本字。“隐”通“檃”并无形式上的标志,文本里只看到“隐”。若从“隐”的本义去理解,必然造成误读。只有从义理、文情、逻辑等方面悉心体会,加以分辨,弄清哪些是“隐”的本意本用,哪些是通假,才能正确理解文意。
(三)“檃”表纠正之意是有理据、合逻辑的直接引申,这一意义的“檃”(隐)在典籍中的应用并不少见
“檃”本是矫曲木之器,表名物之词,它能将弯曲、不规则的竹木矫正或使之成形。《荀子·性恶》《荀子·大略》《淮南子·修务》《韩非子·显学》《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盐铁论·申韩》对“檃”(檃栝、隐括)这一功用都有介绍和描述。
由矫正竹木之邪曲比况、转指纠正、规正人的错误言行,理据非常充分,极为自然顺当。可以说规正、纠正是“檃”(檃栝)的本然之性、应有之义。在古代文献中“檃”借“隐”表达审度、纠正意义的语例屡有所见。如学者们经常所举的《尚书·盘庚》“尚皆隐哉”,整段话是:“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11]244-245这是盘庚完成迁殷大业后,对各位诸侯、公卿和吏属的儆戒之辞。对其中的“隐”,孔安国传:“言当庶几相隐括共为善政。”[11]244孔颖达疏:“幸翼相与隐审检括,共为善政。”[11]245孔传以“隐括”释“隐”,孔疏将“隐括”解释为“隐审检括”,十分切合文意。盘庚迁殷遭到来自多方面的抵触和反对,盘庚既迁,敕令各级官吏严格约束、规正自己的行为。盘庚要求他们照顾怜恤民众,对民众施与恩惠,不要贪婪、聚敛财宝,并表明自己不会任用自私贪财的人,只敬重选用帮助民众谋生、养育民众并能使他们安居的人,强调对这些提倡和禁止的意见必须遵从勿违。这段话没有涉及如何对待迁殷的问题,而是希望官员们纠正过去不正确的思想认识和举止行为,回到公廉恤民的正道上来。因而前面的“隐”字绝对不是一般的省度、考虑,它表达了隐审检括、使就绳墨的意义。这是汉儒最早指出的“隐”“檃”相通、表矫正的典型用例。《熹平石经》中“隐”作“乘”[48],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乘之本义为升为登。”[49]《国语·周语》有“从善如登,从恶如崩”[50]145的说法。尚皆乘矣,意谓要抛弃狭隘自私的成见旧习,登临善政之境。这与纠正意义相通。
古籍中“檃”(隐)表纠正用法的语例还有不少。《管子·禁藏》:“是故君子上观绝理者以自恐也,下观不及者以自隐也。”[51]360尹知章注:“隐,度也。度己有不及之事当效之也。”[51]362这正是“檃”所能表达的意义。“檃”可用以审度而矫正。“自隐”同“自檃”,即自我审度,努力改正。姜涛《管子新注》径解为“自我纠正”[52],得其本旨。
崔瑗《座右铭》:“世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李善注:“刘熙《孟子注》曰:“隐,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吕氏春秋》曰:‘内反于心不惭,然后动也。’”[53]李善采纳“隐,度也”的故训,又引《周易》《吕氏春秋》以申实义。这两句话中的安身、易心在传统文化中都有特定含义。晋潘尼说:“盖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进而指出:“故君子不妄动也,动必适其道;不徒语也,语必经于理;不苟求也,求必造于义;不虚行也,行必由于正。”[54]998“内反于心而不惭”出自《吕氏春秋·高义》,整段文字是:“君子之自行也,动必缘义,行必诚义,俗虽谓之穷,通也。行不诚义,动不缘义,俗虽谓之通,穷也。然则君子之穷通,有异乎俗者也。故当功以受赏,当罪以受罚。赏不当,虽与之必辞;罚诚当,虽赦之不外。度之于国,必利长久。长久之于主,必宜内反于心不惭然后动。”[55]无论安身、易心,还是内反于心,都突出一个“正”字,表明君子要适道缘义才能行动。从而准确揭示了“隐心”的真实内涵和价值意义。“隐心”当读为“檃心”,“檃心”就是正心,用道义规正其心。
廖名春所列举的《后汉书·安帝纪》中的“隐亲悉心”[56]157、《后汉书·孔融传》中的“隐核官僚之贪浊者”[56]1529、《晋书·宣帝纪》中的“欲加隐实”[54]4、《晋书·张辅传》中的“隐核名检”[54]1087等例,其中的“隐”都通“檃”,分别表达审度、核查、审察诸义。
古籍中还有一些用“隐”的语句,前人多以“隐”的本义训释,明显不洽文意,而用“纠正”释义,则怡然理顺,意切神通。如《中庸》:“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57]1425对其中的“隐恶而扬善”,《礼记正义》无注无疏。朱熹解释说:“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则隐而不宣;其善者,则播而不匿。”[22]3后人多将“隐恶”理解为“隐瞒恶事”[58],“把别人不好之处隐藏起来”[59]。隐瞒恶事和人的不好之处,这与守死善道、鄙弃邪恶的道德传统完全背离。无论贤与愚、君与臣,这种背德行为都不可取。对善恶应采取何种态度,自古以来就有鲜明的主导倾向和道义原则。《国语·楚语》有“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50]528。《荀子·臣道》有“扬其善,违其恶”[16]184。《荀子·不苟》有“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16]30。《孝经·事君章》有“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18]54。《鹖冠子·天则》:“举善不以窅窅,拾过不以冥冥。”[60]徐干《中论·谴交》:“故民不得有遗善,亦不得有隐恶。”[61]《大戴礼记·文王官人》将“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饰其美,不隐其恶,不防其过”作为“有质者”[62]的优秀品德和应秉持的操守。《晏子春秋》以有无直辞衡量政治是否清明。晏子说:“臣闻下无直辞,上有隐恶;民多讳言,君有骄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辞;君上好善,民无讳言。”[40]148《贞观政要·贡赋第十三》深刻揭示了虚美隐恶的严重危害:“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63]遍检中华元典,未见有以隐瞒恶事劣行为美德而予以赞赏的。《中庸》里的“隐恶”也应读作“檃恶”,矫正过错的意思。它与古代文献中的抑恶、违恶、匡救其恶的语义指向和伦理规范是一致的。《中庸》论舜这段话实际上是肯定、赞美舜三个方面的德行:“好问而好察迩言”,言舜善于调查考察,从百姓浅近的俚言俗语里了解政风民情;“隐恶而扬善”,言舜对不好的加以约束、矫正,对美的善的努力发扬光大;“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言舜治理天下力避过与不及,允执中正之道。有此三德,舜就可称得上有大智慧的圣君。将“隐恶”作“檃恶”训解并不值得惊异,“檃”是古代习见常用之物,矫曲正枉之效为当时人所共知,用它来表达舜对人们不好的言行予以纠正,使之合乎规范,是十分自然合理的,也符合舜的帝王身份。有些学者以舜帝隐恶扬善作为父子相互隐恶的论据,完全是一种误解。
另外,《礼记·檀弓》中提到“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事师无犯无隐”,郑玄注:“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无犯,不犯颜而谏。”[57]169若依此训,把父母亲的错误、缺点都隐瞒起来,当然就不存在“犯颜而谏”了。为什么后面还用转折连词“而”,要求做到“无犯”呢?同样,对君王敢冒天威、竭诚谏诤,当然就不会隐匿其过了。再说“无隐”岂不多余?对师长既不犯颜直谏,又不替其隐瞒过失,岂不矛盾?这三个句子里的“隐”同样可读为“檃”。“事亲有隐”类同于“事父母几谏”。发现父母有违礼悖义之处要诚恳、委婉劝谏,并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其绳愆纠谬。“无犯”指不能贸然冲撞,粗鲁冒犯。事君则不同,可以犯颜直谏,语其得失,但只能补察时政,建言献策,劝其救失纠偏,而不能僭越擅为,代君发令,搅动天下。韩愈《过鸿沟》诗:“龙疲虎困割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64]在我国封建社会,朝廷无论面临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危机,臣僚忠肝义胆、尽力规谏,君王开诚纳言、革弊兴利,就能臻于清明强盛之境。事师与之亲密接触,相与切磋,教学相长,不会冒犯,也无须专意帮助老师纠正过失。正人之过犹如矫揉曲木,主要靠外力作用而成。因所事对象不同,“有隐”“无隐”各殊,合情合理。
“隐”(檃)由纠正过失又引申为“正”。《易经·系辞下》:“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王弼以“微”训“隐”,将后一句解释为“事显而理微”[65]。这是不确切的。肆者陈也,纵也,并无显义。“隐”与“中”相对应,也非幽微义,而是“正确”的意思。“事肆而隐”是说陈述的事情很多,涉及面甚广,而道理中正,不偏不倚。
“隐”通“檃”的纠正、规正用法后来为“檃栝”(隐括)所代替,这种例子在古书中不胜枚举。如《韩诗外传》卷一:“磏仁虽下,然圣人不废者,匡民隐括,有在是中者也。”[66]何休《春秋公羊传》序:“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67]7刘勰《文心雕龙·指瑕》:“若能隐括于一朝,可以无惭于千载也。”[68]孙绰《桓宣城碑》有“隐括真伪,擢奇取异,不轨常流”[69]。董逌《广川书跋·蔡邕石经》:“独蔡邕镌刻七经,著于石碑,有所检据,隐括其失。”[70]葛洪《抱朴子·酒戒》:“是以智者严檃括于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检之以恬愉,增之以长算。”[71]
大量的语言事实证明,“檃”(隐)、“檃栝”(隐括)用作动词,表纠正、规正,是古代习语常训,其应用较为广泛而频繁。有学者认为“直”或“矫正”之义是在“隐栝”“檃括”的用法中才有的[72]。这既不符合语言事实,也颠倒了源流。
(四)“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读为“父为子檃,子为父檃”,既通于训诂,又切于义理
通过深入考察分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应读为“父为子檃,子为父檃”。即当父或子犯错时,应相互规谏,主动帮助对方予以纠正。这在文字训诂上完全讲得通,更重要的是与自五帝三王以来就已形成具有主导倾向的崇德尚义、著诚重信传统,以及早期儒家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163、“事父母几谏”、“义以为上”、“敬而无失”[1]159、“身不陷于不义”[18]48等亲族伦理思想和直道精神相吻合。父亲帮助儿子纠正错误,出于父之严慈与絜矩之道;儿子帮助父亲纠正错误,出于子之孝诚和道义担当。
孔子态度鲜明地反对直躬证父,不赞成亲族内部采用谒吏告官的方式处理“其父攘羊”这类过错,而主张在公门、法律未介入之前,在事情还未形成最后定局,还没有到无可挽回、无法弥补的地步时,父子之间要尽力规劝和帮助对方纠正错误、弥补过失,并主动承担可承担的责任,以减轻或消除危害与祸患。所谓“门内之治恩掩义”[57]1673,就是在宗法亲族的帷幕下,出于真孝至爱和感恩报恩心理,通过血缘亲情的感化和推动,着力于相互规正,以消灾弭祸。各人都视亲过为己过,将改亲过当己责。这就实际上履践了公义原则和直道精神,实现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价值。有人称之为第三种公正。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楚竹书《内豊》篇就明确阐述:“君子事父母,亡私乐,亡私忧。父母所乐乐之,父母所忧忧之。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止之而不可,隐而任之,如从己起。”[73]这段文字为“亲亲相隐”的正确训解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佐证。其中“隐而任之”的“隐”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隐”字同义通。有的整理者将此字读为“憐”[73]。“憐”与“檃”音近,可通假,亦表纠正之意。“任”就是担负责任。父母有不好的地方要努力谏止,谏诤未被接受,就自行替父母纠正,主动担责,如同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正是“父为子檃,子为父檃”的真意所在。
在儒家伦理争鸣中,有学者举出“《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及相关例证,说明汉以前有为君主隐恶饰过的倾向,用以为亲亲相互隐恶之论张本。实则“讳”与“隐”是有区别的。 “讳”即有所顾忌不敢说、不忍说、不愿说,或改换说法。“隐”则是有意隐瞒事实。讳言所涉及的并不全是劣行恶事,如“避其名”“死曰讳”,而要隐瞒的必定是不好的事情。王四达先生在《也谈“亲亲相隐”之本义》一文中所列举的几个例子都不能看作替君王匿恶。《春秋·宣公元年》:“晋放其大夫胥甲父于卫。”[19]586《公羊传》以“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67]320-321为由,认为此处“放”有“近正”用意。我国台湾学者傅隶朴指出,胥甲父是否待放三年不离,晋侯是否限令其三年不得擅离,都未有交代,所以这一解释无论是经义或是史实都极含糊不清[74]。由此表明《公羊传》对“放”义有所误解。《说文解字》:“放,逐也。”[31]84将犯罪的人放逐到边远地区,这是一种从宽惩罚措施,杜预释之为“宥之以远”[19]586。《左传·宣公元年》:“晋人讨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卫,而立胥克。”[19]588据《左传·文公十二年》记载,秦晋河曲之战,臾骈发觉秦军有逃跑企图,提出急速进攻。主帅赵宣子纳臾骈之谋,而胥甲父与赵穿挡住营门,阻止出击,使秦师夜遁。因胥甲父有不用命的罪过,而遭到晋侯放逐。《春秋》实录其事,根本就没有隐讳,这哪里谈得上是“因为大夫本无罪而去,又不可扬君之恶,故假出奔之例而言‘放’,引罪于己,若为君所放”[72]呢?《礼记·坊记》有“善则称君,过则称己”[57]1407,这是一种公忠自厉、敢于担当的为政之德。不但贤臣如此,明君亦如此。《尚书·汤诰》:“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11]201《尚书·泰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11]277《尚书·冏命》有“惟予一人无良”[11]531。这难道是君王为臣属、为百姓隐恶吗?在《坊记》里孔子还说:“善则称人,过则称已,则民不争。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怨益亡。……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57]1407这与“隐恶”有本质不同。至于孔子说昭公知礼与事实不符,明显不是有意隐瞒。经人指出后,孔子自知其错,叹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1]96言不副实即为过,孔子深为自责。无可讳言,古代也不乏隐恶匿愆的伪言劣行,但都是受主流意识排斥和鄙弃的。我国古代历朝历代都设立言官,选拔公廉介直之士察失规过、补偏救弊。直言谏诤,不避亲嫌,一直是明君圣主所倡导和鼔励的。
还有一些学者以舜窃负而逃、石奢私父伏罪为例,以证子为父隐恶自有由来。舜窃负而逃出于《孟子·尽心上》,并无说服力。一则这是虚拟之事,无可稽考,不能据以论理。二则孟子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生活时代与孔子相距近两百年,其思想体系一脉相承,却存在较大差异。在人伦关系上,孔子总是先君臣而后父子,先公义而后亲情,他明确指出“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20]120,认为“义”是大原则大前提,“孝”是“义”的根本。孟子则把“父子有亲”置于“君臣有义”之先[17]243,提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17]355。舜窃负而逃、乐忘天下就是孟子依其伦理思想所构拟的理想范式。三则在《论语》中孔子5次论舜,极为赞赏舜举贤任能、无为而治、勤苦为民、正直无私。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1]106“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1]208这跟孟子所说的其父杀人窃负而逃、弃天下如敝屣的行为与境界大相径庭,说明孟子论舜恰恰是对早期儒家亲族伦理的偏离。而石奢之例反而与“子为父檃”“如从已起”在精神实质上具有一致性。据《韩诗外传》卷二记载:“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为理。于是道有杀人者,石奢追之,则父也,还返于廷。曰:‘杀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废法,而代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锧,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义也。’遂不去铁锧,刎颈而死乎廷。君子闻之曰:‘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诗》曰:‘彼己(其)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谓也。”[75]此事又见于《吕氏春状·高义》《史记·循吏列传》《新序·节士》等典籍,流传广远。石奢将其父杀人、自己“私其父”之事当廷禀报,没有一丝隐瞒。虽在前徇情失法,而后为守职践义自伏斧锧而死,显示法不容情,公义不可违背。时人将石奢的行为与“子为子隐,父为子隐”“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相联系,这就说明“子为父隐”并不是隐匿放纵父恶,而包含有勇担其责、毫不含糊地维护法度和坚守道义的内容,“邦之司直”也就体现在这里。
三、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误读误解的原因探究
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误读误解肇自汉儒。出现这一情况有其复杂而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一则自周迄汉时隔数百年,其间战乱频仍,暴秦焚坑,华夏文化惨遭摧残,《论语》的传播也受到很大影响,《古论语》《鲁论语》《齐论语》已失其二。因无丰富的原始材料相资,学者们传抄文本解经,忽略了“隐”为“檃”的借字,而作了蹈常袭故、有忤原意的理解。二则汉武帝为巩固中央集权,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奉儒家学说为正统思想。儒家崇尚孝悌、畅行仁道,形成了仁孝统一、富于深刻内涵的宗法伦理体系。孔子曾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3汉儒偏颇地将顺亲之孝作了绝对强调和极度张扬,视父子相互隐恶为“天理人情之至”,指出“父为子隐者,欲求子孝也”[7]925。在亲亲的旗幡下赋予隐恶说以合理性,掩翳、摒弃了规正大义。三则汉承秦制,汉武帝铁腕治国,不避亲贵。为解决当时的流民问题,颁布了舍匿法,又称首匿相坐法,严禁容止、藏隐流民。首匿相坐法的执行很严酷,凡藏纳流民、不予举报者,亲朋邻里一律连坐伏法,杀人无算。《盐铁论·周秦》记载:“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废,而刑罪多闻。”[6]66首匿相坐法的施行加剧了社会矛盾,引发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此时的执政者以误读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作为矫枉的理论依据,将亲亲相隐匿援引入律。汉宣帝于地节四年下达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41]176自此,后世司法实践多予效从,以亲亲的诚爱容忍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根基。
质其实,“子首匿父母”“父母匿子”与“子为父檃,父为子檃”,其行为的性质、效果完全不同。只强调亲亲相匿,以遂自然之人情、天伦之诚爱,是不长久、不稳固的。即使就其隐时,义理昭然自在,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总是存在危险。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王夫之所言:“执法在国家,公论在天下,而究未尝枉也。”[28]751一旦恶事暴露,就会受到惩罚制裁。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也并没有真正、全面施行过亲亲相匿之法,谋反、谋大逆、叛、降等大罪从来都排除在外。汉献帝的诏令规定,犯了死罪时父母为儿子隐瞒、丈夫为妻子隐瞒、大父母为孙子隐瞒的,要上报廷尉,以决定是否追究首匿者罪责,而并没有一律免于治罪。不少朝代都施行连坐法,甚至株连九族。我国现行刑法中还设置有窝藏、包庇罪。联系古代的司法实际,更显示儒家提倡“义以为上”“父为子檃,子为父檃”之可贵。另外,这种亲人之间相互规过矫错与现代法律中的亲属容忍规定并不矛盾,法律上容忍并不排斥帮助亲人悔过改错。存心隐恶护短、包庇纵容与不强制父母、子女、配偶到庭作证也是有原则性区别的。因而,用亲亲相匿入律来证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父子相互隐恶,也是说不通的,且有很大危害。
四、正确释读“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重要意义
在《论语·子路》里,孔子并没有对直躬证父这一具体事件直接进行评议,而是以“吾党之直者异于是”转换拓展,将“父为子櫽,子为父櫽”作为具有普遍规范、约束和导引作用的伦理原则提出来。这种亲亲之间缘于情、重于恩、准于义、括于礼的相互规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大踏步向法治社会迈进的今天,仍具有积极进步意义。如果每个家庭的成员都确立明确的是非观、善恶观和荣辱观,知道哪些事可为、哪些事不可为,当亲人出现犯错苗头,或误入歧途时,相互规谏劝止,相互矫枉纠错,就会减少过错、恶行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铲除腐败和违法犯罪的土壤和根基,净化社会环境。
长期以来由于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深度误读,让孔子一直蒙受冤屈,成了伦理思想史上实实在在的“冤大头”。所谓“孔子哲学的主导精神实质上是一种不仅赋予血缘亲情以本根地位,而且赋予它以至上意义,强调它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76];所谓孔子“将‘父子相隐’的血亲规范置于‘诚实正直’的普遍准则之上”[77],“希望人们不惜牺牲诚实正直的社会公德,通过‘父子相隐’来维系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从而明确地将家庭私德凌驾于社会公德之上”[78]。这些完全是人为强加的。另有一些人援引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容隐制度(西方国家法律中则有亲属拒证权等),将亲人之间平时的相互隐恶匿过视为金规铁律,认为这是“个体的一种不可让渡的基本权利”[79]14,“是符合人性的、具有普遍性的观念”[79]18,“对于正常时代一切正常的人来说,‘亲亲互隐’的合情合理性无疑是不言而喻的”[80]。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简单比附和在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文本误读前提下的发挥,同样偏离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支撑的儒家伦理基本精神,是用自己的观点对孔子言论的主观诠释和曲意辩解。为何亲亲之间只有相互隐匿其过才是符合人性的?难道父子兄弟相互规过纠错就不是基本权利?难道亲情与公义必定完全对立、水火不容?一字之误训,一语之错解,对中国哲学思想乃至整个传统文化产生的不好影响至今未能肃清,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尤为深重。正如老舍所说:“以前,中国人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于是隐来隐去,就把真理、正义全隐得没有影儿了。”[81]
在新时代,我们以科学求真、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儒家伦理刮垢磨光,还原本真,发掘其中的积极因素,剔除有明显时代局限性的落后成分,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整治和预防塌方式腐败、家族性腐败,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绵邈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