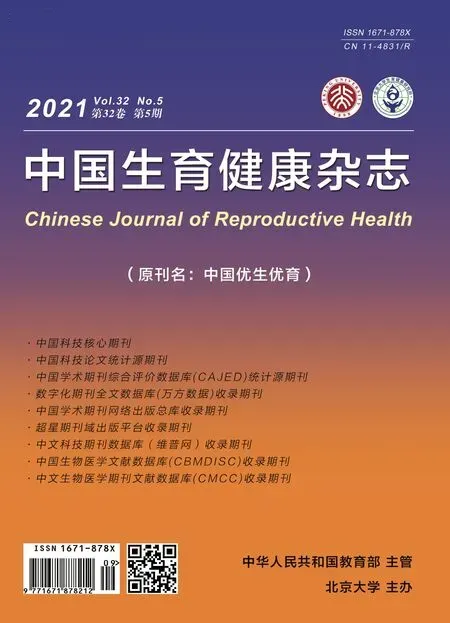妊娠期卵巢透明细胞癌相关研究进展
韩杰霞 孙欣 黄明莉
卵巢透明细胞癌(ovarian clear cell carcinoma,OCCC)是一种罕见的卵巢恶性肿瘤,妊娠期OCCC更是极为罕见。妊娠期新出现的卵巢恶性肿瘤的发生率为1/万[1],其以上皮性卵巢恶性肿瘤(epithelial ovarian malignancy,EOC)为主,约占妊娠期卵巢恶性肿瘤的25%~50%[2]。EOC组织学分型为浆液性癌(70%~75%),粘液性癌(5%~10%),透明细胞癌(10%)和子宫内膜样癌(10%)[3]。OCCC属于EOC预后最差的一类,其发生率占卵巢上皮源性恶性肿瘤的5%~11%[4]。OCCC恶性程度高,对传统化疗药物不敏感,复发率高,预后较差。制定合理的诊疗方案对提高活产率、提高患者生存率、改善预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免疫表型及分子生物学特征
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卵巢非典型腺纤维瘤都被认为是OCCC的癌前病变[5]。部分学者认为OCCC由子宫内膜异位病灶恶变而来,K-ras基因突变可能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恶变的诱因之一[5-6]。研究发现在子宫内膜病灶癌变的过程中雌激素受体ERa表达逐渐减少,透明细胞癌多数表现为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和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阴性,卵巢癌中PR功能丧失可能是卵巢癌进展的标志[7]。
基因层面上,OCCC与富含AT相互作用结构域1A基因(AT-rich interaction domain 1A,ARID1A)的功能频繁丧失有关[8-9]。ARID1A的作用类似于肿瘤抑制因子。根据文献报道,ARID1A直接抑制OCCC中的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HDAC),HDAC6诱导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 1α,HIF-1α)蛋白表达。HIF-1α是与OCCC的化疗耐药及不利的预后密切相关的关键因素之一[10]。
蛋白途径上,OCCC存在5种蛋白激活途径:HIF-1α/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途径,肝细胞核因子1β(hepatocyte nuclear factor 1β,HNF-1β)途径,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3(STAT3)途径,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 AKT /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途径和甲硫氨酸(methionine,MET)途径[11-12]。大多数透明细胞癌患者中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程序性死亡 - 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HNF-1β、天冬氨酸蛋白酶A (napsin A)表达上调,而ER、PR和p53表达下调,这些可用于辅助鉴别其他类型的卵巢癌如子宫内膜样癌和浆液性癌[11,13]。
HNF1β和napsin A是诊断OCCC的敏感的标志物[13]。HNF1β在90%~95%的OCCC中呈阳性表达,而其他上皮来源的卵巢癌的表达率低于10%。HNF1β过表达可能与OCCC病理生理学中ARID1A缺失有关,但尚无确切证据[9]。
MET是一种受体酪氨酸激酶,在与HNF-1β 结合后,激活Raf/Ras/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和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oinositide 3-kinase,PI3K)/ Akt或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PKB)/ mTOR信号通路并刺激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12]。
研究也发现了其它分子生物学特征。OCCC中核苷酸切除修复(nucleotide excision repair,NER)的活性高于任何其他组织学亚型。NER活性的增加与卵巢癌对铂类药物的耐药性有关,相反,NER缺乏与OCCC对铂类药物的敏感性增加有关[12]。L型氨基酸转运蛋白1(l-amino acid transporter 1,LAT1)是Na+非依赖性中性氨基酸转运蛋白,其在癌细胞生长和存活中起关键作用。与其他组织学亚型相比,LAT1在OCCC中高表达,与化疗耐药及较差的预后相关[14]。解整合素和金属蛋白酶(metalloproteinase,ADAM)参与细胞粘附,迁移和侵袭等生物学过程。Ueno等人发现ADAM9m在透明细胞癌中高表达,且在顺铂耐药中起关键作用[15]。分子生物学标志物中的极光激酶A,PD-L1与OCCC患者对铂类化疗药物的耐药相关[11]。
文献报道,接受促排卵患者卵巢癌的发病率较高,在体外研究中雌激素和促性腺激素均能刺激ER(+)卵巢癌的生长,高水平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促进卵巢癌进展[16,7]。
二、妊娠期OCCC的诊断思路
1.临床特征:不同种族人群的OCCC发病率存在显著差异。美国最近一项报告显示,OCCC的发病率白人为4.8%,黑人为3.1%,亚洲人为11.1%[5]。OCCC临床表现可能为腹痛、腹胀、恶心、呕吐、盆腔肿块生长迅速等,但症状往往不典型[4]。OCCC患者高钙血症或高凝状态甚至血栓相关并发症的风险增加[6,17-18]。
2.病理特点:卵巢恶性肿瘤在宏观上通常表现为具有实性成分的较大单侧肿块,肿块呈囊实性、实性、伴乳头状突起,呈多房样、分页状不规则结节等,部分病灶伴钙化[19-20]。镜下发现OCCC细胞分为含糖原及丰富透明细胞质的细胞和鞋钉样细胞[5]。
3.肿瘤标记物:妇产科超声检查发现可疑附件肿瘤时,建议立即检测肿瘤标记物如碳水化合物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125,CA125)、CA199、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铁蛋白、癌胚抗原等。但肿瘤标记物水平作为辅助诊断妊娠期卵巢癌的价值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妊娠期肿瘤标记物较非妊娠期有所变化,妊娠期CA125有所增加,有时可高达550 U/mL,重度子痫前期的孕妇AFP可达肿瘤临界值的13倍[2],其它如发生HELLP综合征,先兆子痫或流产时也可能出现CA125升高的情况[21]。附睾蛋白4不受妊娠影响,可作为妊娠期附件肿瘤的检测指标[22]。
4.影像学检查:OCCC无特异性超声表现,超声主要用于发现卵巢肿物并初步判断肿物的良恶性质,OCCC和子宫内膜样卵巢癌具有相似的超声特征,大多数是具有固体成分的大的单侧肿瘤,且常见乳头状突起,许多透明细胞癌和子宫内膜样卵巢癌被误诊为交界性肿瘤。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中出现的透明细胞癌常表现为囊液玻璃样回声[23]。
妊娠中晚期可进行盆腔核磁共振检查,进一步明确肿物浸润的范围及深度[21]。卵巢透明细胞癌在T1WI呈等信号,T2WI呈稍高、等信号。增强扫描在妊娠期的应用需要谨慎,增强剂中的钆元素可能对胎儿有致畸作用,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归为C类药物[22],需要与患方做好充分沟通。
三、妊娠期OCCC的治疗策略
考虑到OCCC的恶性程度及治疗的复杂性,需要肿瘤科、妇科、病理科、影像科等多学科团队协同制定诊疗方案。EOC的治疗方式一般为手术联合化疗,手术是EOC的主要治疗方式[24],OCCC的治疗尚无国际标准。OCCC对治疗EOC的一线化疗药并不敏感,靶向治疗已取得一定研究进展。
1.手术治疗:医生需要根据妊娠阶段和肿瘤分期等评估手术时机,手术方式及手术范围,同时结合孕妇及家属意愿进行个体化治疗。妊娠期非产科手术可能导致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早期新生儿死亡[20]。手术途径包括开腹和腹腔镜。开腹手术建议沿垂直中线切口,以满足最大可视化要求[20];Webb等认为腹腔镜手术与开腹手术相比,早产风险降低[25]。腹腔镜手术术后恢复时间短,损伤小,缺点是CO2气腹可能致胎儿酸中毒,腹腔压力增加导致胎盘循环受阻,穿刺针损伤妊娠子宫等,建议使用可视穿刺器械减少损伤,术中使患者左侧卧位,术中实时检测CO2压力,术后早期下床活动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22]。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指南建议妊娠前三个月避免手术治疗,如果可能的话择期手术应推迟到妊娠中晚期进行[26]。Zhou等建议,对于无症状的卵巢肿块,手术干预时间为妊娠16~24周[27];袁江静等报道对于II~IV期卵巢上皮源性恶性肿瘤,妊娠24周前倾向于选择全面手术终止妊娠;妊娠24周后可化疗3~4周后终止妊娠,剖宫产手术同时或术后进行全面手术[22]。Cordeiro等报道卵巢癌III~IV期妊娠早期由于化疗风险需要终止妊娠;妊娠中期根据情况进行根治性卵巢切除术,盆腔淋巴结取样活检,阑尾切除术,随后进行化疗,至妊娠足月进行剖宫产术,子宫切除术;在妊娠晚期,进行剖宫产子宫切除术和分期手术,术后给予化疗[26]。
2.化疗:妊娠中晚期化疗安全性的循证医学证据已有报道,同时提出化疗与胎膜早破、低出生体重儿等的发生有一定关联[22]。妊娠期化疗相关的先天性畸形率在妊娠早、中、晚孕期分别为16%、8%和6%。上皮性卵巢癌的标准治疗方法是标准手术后进行6个周期的紫杉醇加卡铂化疗[26]。关于OCCC的化疗尚无标准方案,研究表明OCCC对基于铂的一线化疗较不敏感,预后较差[4]。有学者认为紫杉醇加铂类仍然是OCCC患者的标准化疗药物[5,9]。另外,在铂类化疗的一线治疗后,复发性疾病缺乏有效的化疗[9]。
3.靶向治疗及内分泌治疗:内分泌治疗对GnRHR阳性或对GnRHa敏感的OCCC有效,靶向治疗副作用小,靶向治疗联合内分泌治疗,提高药物功效,减少副作用,具有广阔应用前景[28]。OCCC相关蛋白表达信号通路可能是OCCC的重要研究方向,并且这些途径中的一些靶向抑制剂正在临床开发中[12]。
PI3K/Akt/mTOR途径是OCCC重要的治疗靶标。研究发现,PI3K/Akt/mTOR抑制剂在AKT/mTORC1活性较高的卵巢癌细胞中具有显著的抗肿瘤作用,但在AKT/mTORC1活性低的卵巢癌细胞中作用最小。曲贝替定加 mTORC1抑制剂和/或伊立替康在治疗OCCC方面值得研究。VEGF或VEGF受体(VEGFR)的部分抑制剂现已被批准用于治疗卵巢癌[12]。HDAC6选择性抑制剂在临床上也被用作抗肿瘤药物[13]。
在前临床试验成功的基础上,研究这些靶向抑制剂作为OCCC的治疗策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四、OCCC的预后
OCCC在卵巢上皮源性恶性肿瘤中预后最差,对传统化疗药物不敏感,复发率高。合并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在预后、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等方面较单独OCCC均有所改善[16,29]。妊娠胎次的增加与卵巢癌生存率提高有关,而BMI和吸烟与生存率降低有关[30]。与PR(+)肿瘤患者相比,PR(-)肿瘤患者的生存率更低。OCCC的预后与FIGO分期和手术残余肿瘤之间存在显著关联[10],而 Zhou等人认为残留的肿瘤大小不是粘液性和透明细胞癌的预后因素[27]。HIF-1α和LAT1是与0CCC不良预后相关的重要标志物[10,14]。
五、结论
妊娠期OCCC是产科极为罕见的疾病。OCCC恶性程度高,肿瘤生长速度高,妊娠期更是加速了疾病进展,由于对传统化疗药物不敏感,复发率高,其诊疗相对于非孕妇具有很强的局限性及特殊性。研究有效的治疗策略,提高OCCC孕妇的生存率、胎儿存活率,改善预后十分必要的。关于OCCC的治疗缺乏一定的研究,目前尚无国际标准指南,需要妇科、产科、肿瘤科、病理科、影像科等多学科团队结合患方意愿综合制定诊疗方案,应向患方详细告知治疗过程中的益处、风险及预后。在手术时机、手术途径、手术范围的选择上综合各种因素,进行个体化治疗。靶向治疗OCCC具有广泛研究前景,相关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