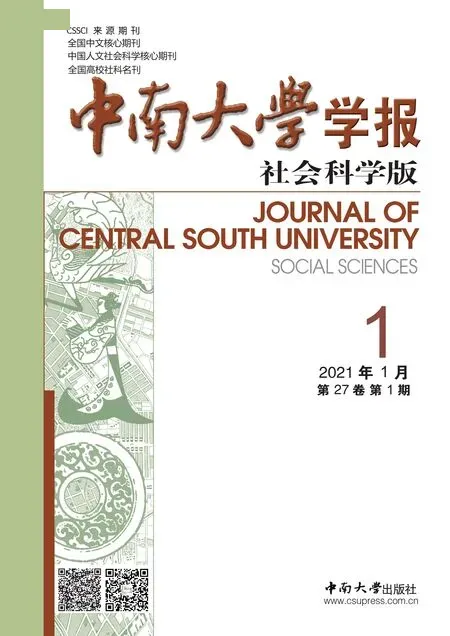1990年代中国实验艺术的社会介入与审美转向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一、1990年代的实验艺术:对“实验性”的追问
实验艺术是一个看似明确实则有很大暧昧性的概念。广义来讲,不论什么方面什么程度上的创新,任何一种新的艺术在被大多数人接受和熟悉之前都可以说是“实验性”的。而当我们在中国20世纪艺术史的语境下谈实验艺术,它又指向了具有历史特殊性的艺术范式与社会情境。通常认为,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实验艺术,主要是指’85 新潮美术运动以来对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更新,这种更新突出表现在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大量引进、模仿和挪用。而1989年以后,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着一个更加复杂且剧烈变化着的现实环境,1990年代的实验艺术也从对西方的简单模仿和借用转向对当下经历着的中国问题的思考和表达,从相对单纯的对艺术形式与艺术风格的更新转向探索更广阔的当代艺术和当下社会变革的关系,即艺术与社会的互动。
正是因为这种互动,我们无法把1990年代的实验艺术简单地称为“前卫艺术”或“先锋艺术”,也因此在21世纪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的今天,它的“实验性”仍旧对当代语境产生意义,值得我们回望和追问。以一些重要展览作为标志性的节点可以勾勒这段历史的一个直观轮廓。1989年北京的现代艺术展作为第一次全国性的现代艺术展览,是对’85 新潮美术运动中涌现的种种尝试(包括北方艺术群体、西南艺术群体、杭州“池社”、厦门达达等)的一次大总结,但它更重要的意义或许是开启了1990年代艺术面向中国问题的新方向。此次展览上最具影响力和冲击力的行为艺术和装置作品都与政治、经济、社会议题密切相关,比如肖鲁的《对话》、张念的《孵》、李山的《洗脚》、吴山专的《大生意》等。艺术史家巫鸿指出:“90年代实验艺术的一个新方向,即从80年代的大规模吸收西方现代艺术转到‘面向国内’,从而使实验艺术成为社会批评的一个有力工具。”[1](82)在巫鸿的定义中,实验艺术不取决于艺术内部或艺术外部的任何单个因素,而是由它和中国当代艺术当中的四种主流体系的关系决定的,即:一、直接在政府资助和指导下的高度政治化的官方艺术;二、与政治宣传拉开距离而更强调技术训练,并具有较高美学标准的学院派艺术;三、不断吸收日韩及西方时尚图像的大众都市视觉文化;四、源于实验艺术但最终迎合国际艺术市场的“全球”商品艺术[2]。这样一种界定从整体的视野为实验艺术划定了一个共时的边界,提示这个边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实验艺术和艺术家与官方、学院派、大众文化、商品市场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
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就从侧面反映出在这种动态关系之下1990年代前期实验艺术被商品和市场分化的处境:在自由经济和权力管控的双重作用下,1980年代先锋艺术的主流样式被市场意识形态和利益逻辑所主导,成为一种迎合意识形态期待的商品艺术,于是其先锋性、实验性也就不再显现,不再属于实验艺术。因此批评家易英说:“虽然广州双年展也同样为前卫艺术家所关注,但其效果完全不同于89 现代艺术展,不具备那种影响力和冲击力,但却为后来的大型美展提供了一种商业化的操作模式。无论这些样式化的前卫艺术是否真正推向了市场,这届展览都标志着前卫艺术被市场的招安,亦即85 运动的主要艺术样式在前卫意义上的完结。而85 运动的另一翼,观念艺术则可能作为85 的遗产,作为9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的样式,把85 的精神和理想继续推向前进。”[3]
大型美展对前卫艺术的主流化和商业化,不论是在意识形态、市场经济、学院标准的主导下,还是为了迎合西方想象,都致使实验艺术转向寻求差异化和异质性的“私人叙事”。如果说1990年代前期的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新生代艺术等还活跃于大型国际展览(比如1993年的“后89”中国新艺术展、威尼斯国际双年展等),那么1990年代中后期以观念艺术为代表的实验艺术则更多以公开、半公开乃至地下个展的方式保持其精神的独立性。批评家黄专指出:“从媒介上看,它开始广泛使用诸如文字、装置、身体、影像、网络、图片及其他图像媒介,尽其可能地发掘这些媒介在文化、历史、心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意义潜能,从而有效地拓展着中国先锋艺术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内涵……这种运动从一开始就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的‘宏大叙事’的特征,而与自身具体的社会和私人课题密切相关。”[4](908)这种倾向在20世纪末的实验艺术展览中愈发明显,比如,1997年宋冬、郭世锐等人策划的“野生”在全国不同地区进行了“非展览空间、非展览形式”的艺术实验,“非展览”包含了“去中心”的意图,27 位艺术家以各自的原生语境进行不同形式的艺术“展示”来重新定义与观众的关系;1999年吴美纯、邱志杰策划的“后感性——异形与妄想”活动在北京芍药居202 楼地下室举办,他们关注视觉、心理和身体感受在艺术中的关系,对身体材料的使用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同时也将“闭门展览”的概念推至极端。
我们可以对1990年代实验艺术的“实验性”做如下概括和总结:其一,从历时的角度来说,相较于1980年代的实验艺术,1990年代实验艺术的“实验性”是伴随着对西方艺术范式和思想资源的“本土化”过程而发展的,对中国经验的发掘和表达成为其实验特质中真正具有重量和厚度的原因。其二,从共时的角度来说,1990年代实验艺术的“实验性”并不取决于单个的内部或外部因素,而是在市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和艺术自身传统等多重关系作用下动态形塑了一个边缘空间,因此组成其“实验性”的也是处于互动之中的多重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三,相比于当代其他艺术种类而言,实验艺术与中国社会之间有着更加紧密而直接的互动,因此批评家更强调从社会学角度切入艺术,强调实验艺术的社会考察、社会批评功能。也就是说,更关注实验艺术“表达了什么”和“为什么表达”,肯定实验艺术的“社会性”价值。相对而言,在“如何表达”方面,由于实验艺术具有“反艺术”“反美学”的先锋特性,这就造成经典美学和传统的形式分析无法有效解释实验艺术,其“艺术性”往往遭到质疑。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实验艺术的“能指”(表达形式)与“所指”(观念目的)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造成实验艺术“艺术性”和“社会性”的失衡。
然而,这也把我们引向了对“实验性”的进一步反思:实验艺术自我边缘化的“实验性”恰恰在于其“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张力。也就是说,用公众所不能接受和认同的表达方式来表达社会观察和社会批评。这样一来,单纯从外部的社会文化环境来谈“所指”,或是单纯从艺术内部的视觉形式、审美经验来谈“能指”,都不能有效地解释其“实验性”。这就要求我们以一种不只是将外部和内部简单相加的方法论视角来重新审视实验艺术的意义潜能,即不仅仅将社会外部因素作为问题情境,而是进入艺术内部的语义运行机制中,探究社会因素如何参与到实验艺术的生成与观看机制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对实验艺术展开一系列的追问:社会历史的特殊时刻是如何呈现于具体作品之中的?经验的内容如何演变为一种形式?情绪和事件如何被表达?……借助这些具体问题,我们拟进一步探讨“实验性”背后内在的文化逻辑与美学逻辑。
二、社会介入:“背景”如何成为“前景”
(一)“反映”的语法重塑
实验艺术聚焦的首个问题就是对艺术“反映”现实的重新思考。受苏联文艺观点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准则,提倡“艺术家要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去描写现实”[6]。文学、艺术界以此为指导思想创作了一大批各门类的艺术作品。而在美术界,艺术家们面向生活,把握新的人物、新的事件和历史面貌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写生”。比如以上海地区的数据为例,“自1955年以来,上海画家有组织地深入生活计27 次,人数达589 人次,先后到达内蒙、闽西、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浙江渔区、云南、江浙农村、黄山、富春江、市郊及市区工厂”[7]。在“写生”方式指导下反映现实的作品,在题材上直接描绘国家建设的新风貌、人民群众的劳动场景,或将更多新生事物如长江大桥、盘山公路、汽车等融入传统绘画中;在技法上多以写实风格呈现;在情感表现上力求朴素、易懂。
可以说,直到1990年代,现实主义仍旧是官方艺术的指导原则。然而历史是变化的,历史中的个人是具体的,而个体境遇是多样化的,艺术家对创作环境的感受、回应和表达也不可能如出一辙,尤其对于实验艺术家来说,“写生”式的反映模式已经不能真实有效地呈现他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艺术家徐冰曾在访谈中表达过这种感受:“我一直在做作品,《天书》之前就做了很多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其实基本上是老式社会主义创作思路过来的,直接反映生活现象的。那个时候的反映生活,其实我感觉是和我们的时代生活本质没有太多关系的,到边远农村去画那些东西回来,我发现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好像离我们时代变革核心的部分很远:那种反映成为一种民俗考察式的,中国实际上已经在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可是整天去农村画一些老乡的棉袄之类的,跟现实的深刻变化越来越远,这只能是一类,不存在好不好。”[8]而要反映“我们时代的生活本质”和“变革核心”,并不是改变创作的内容就能够解决的,关键在于改变创作的“语法”。因为,“你是一个有感觉的人,你是一个对人类命运关注的人,所以你一定会有问题意识,能感受到现实的问题,而这问题一定是表现为当下特有的,与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同的,这个时候你就要用一种新的语法来说,这种不同才能说得到位”[8]。也就是说,正是每个艺术家现实境遇的不同,促使他们生发出不同的时代思考,并给他们在创作上的不同实验提供可能性。就这一点而言,1990年代的实验艺术绝不是独立、自足的“为艺术而艺术”,而是“有问题”才“有艺术”。
“语法”的改变会使得社会历史的具体时刻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进入艺术作品之中。例如,同样是负载“文革”记忆,1980年代的伤痕美术,以悲情现实主义的笔法直接描写“文革”期间的戏剧性事件,表现出沉重的历史反思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怀,尽管着眼于大时代命运下的普通个体,却仍然具有某种“宏大叙事”的特征。而1990年代具有实验性的政治波普同样是从“文革”衍生出的特定视觉因素出发,却解构了它们原本具有的政治含义,与其他视觉元素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比如“商标和广告(王广义),纺织物图案(余友涵),性符号(李山)以及电子游戏影像(冯梦波)”。巫鸿指出:“他们的目的是要使政治符号非政治化,而不是赋予它们新的政治意义。”[1](91)一方面,这些元素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1990年代商品经济的兴起、大众消费的热潮、电子游戏等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这些元素又表达了具有个体特殊性和偶然性的遭遇和情绪。比如说,周宪教授在分析王广义的《大批判——可口可乐》时就指出,王广义对于“文革”报头图案与可口可乐商标拼贴的选择,是一种包含时代深刻必然性的偶然。虽然艺术家在介绍自己创造过程时说可乐是偶然摆放在画布旁才入画的,但是“如果一个画面只有被复制的‘文革’报头图案,就会因失去与当代语境的关联而索然无趣,所以需要一些与‘文革’图像具有参照性功能的当代符号,由此形成一种对照性的当代图像结构”[9](143)。而1980年代后期的对外开放使得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外国品牌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象,“所以可口可乐商标标识成为当时情境中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只不过王广义作画时,正巧瞥见了一罐可口可乐而已,这就是偶然中有必然”[9](143)。进一步说,“与‘文革’十年相比,1990年代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负载痛苦记忆的‘文革’报头图像再次进入人们的视觉时,不同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感触。深受‘文革’迫害的艺术家会远离甚至拒斥这些图像,因为那会唤起许多痛苦记忆;而王广义出身于工人家庭,在‘文革’中并没有遭受因为出身而降临的诸多灾祸,所以这样的图像对他来说并无特别的抵制情绪”[9](144)。
因此,当作为“背景”的历史事件与集体记忆转化成作为“前景”的视觉样式时,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个转变过程中的复杂语法。而对于实验艺术家来说,以往的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传统的艺术样式由于人类经验的长期积淀,已经有很成熟的程式化表达,语法自由度相对来说就比较小,所以转向材料与媒介上的融合与创新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
(二)“材料”的意义潜能
在西方20世纪早期的前卫艺术运动中,“现成品”艺术成为一种重要样式,尤其以1917年杜尚将小便器命名为《泉》的艺术作品为代表。这种艺术样式在作品中部分或全部使用现成品作为材料,引起了巨大的质疑和争论。使用现成品作为材料的目的通常在于:其一,打破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向艺术体制发出挑战,表达反叛性和先锋性;其二,作为一种观念艺术,排除艺术家“技艺”的干扰,表达纯粹的“观念”。
在中国,’85 新潮美术运动以来追求革新的艺术家们也开始使用现成品进行创作。吕澎指出:“80年代末期,更为激进的艺术家为了保持前进的动力和方向,开始把艺术探索向反艺术的方向推进,他们——吴山专、谷文达、黄永砯、张培力、徐冰——开始拆卸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桥梁,或者任意添加非表达的材料。”[4](903)这里即认为现成品作为“非表达的材料”打破了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
然而,在1990年代许多与现实环境密切相关的现成品艺术中,我们却可以观察到作为现成品的“材料”非但不是“非表达”的,反而作为“表达”特定情感、记忆和经验的不可取代的载体成为构成艺术品存在的关键要素,发挥出巨大的意义潜能。在这里仅举尹秀珍的装置艺术《变化》一例加以说明。在尹秀珍的作品里,各种最私人又最公共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物料”成为艺术表达的关键词,“特别是那些与女性记忆欲望有关联的私人物件:衣服、鞋子、家具、照片,与被拆毁建筑的残余物、水泥瓦砾对峙。在折叠与开展、凝结与溶化的静默无声中,年轻女性的梦想世界与急剧变异社会——即是今日的中国——的粗莽现实之间的交战发生……对活在每日,发现物质改善的喜悦,又缅怀失去了安宁、感性、简朴生活的一代人来说,这种状态普遍存在”[10]。而《变化》的关键“物料”——“瓦片”,则缘起于1997 到1998年间她和丈夫宋冬在平安大街沿途的建筑工地上收集各种拆迁过程中的废弃物。这个人口密集的路段上原有的房子、街道、胡同,在短短几个月内消失殆尽。尹秀珍把从拆迁现场收集来的原来屋顶上的瓦片排列成一个方阵,每片瓦上都贴着拆迁场地的一幅黑白照片,取名《变化》,放置在工地不远处的美院附中的院子里进行展览。
以RNA含量最高的a型单倍体为出发菌株进行ARTP诱变,致死率和诱变处理时间关系如图 4。选择诱变效应最强即致死率90%~95%的55 s进行反复诱变[23],最终得到一株RNA含量比原始出发菌株Y17高39%突变菌株Y17aM3(如图5)。将Y17aM3在糖蜜培养基中培养,从第6 h开始每隔2 h取一次样,得到Y17aM3生长及产RNA曲线如图6。由图6可知,发酵培养至12 h之前,酵母生长和RNA含量都随着培养时间增加而增加;12~18 h酵母生长处于稳定期,而RNA含量在18 h时最高;18 h之后,酵母生长处于衰亡期,RNA含量随着培养时间增加而降低。
在这里最有意思的是对于“瓦片”的使用,并非由于它们呈现出特殊的视觉效果,而是由于其负载了特殊的经验与意义,并且这种经验与意义无法通过直接的视觉性来呈现,只能依靠真实的行为与过程,伴随解释性的图片或文字,最终凝结在材料之中。尹秀珍出生于1960年代的北京,对于她来说,旧北京城的一砖一瓦组成了生活的安定感与记忆的连续性,然而1990年代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改造摧毁了原有的视觉图式,代之以新的、现代化的景观神话。在这个过程中,也造成了城市和它的旧有居民之间的疏离与断裂。在巫鸿对尹秀珍的访谈中,她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自己和北京的关系:“我的感觉就像一粒小种子,已经发了芽,但还没有破土。我想象当这个种子成长的时候,一定会去挤压周围的泥土,而周围的泥土也会反过来挤压这个正在发芽的种子。我觉得这就是我和我周围环境的关系——一种挤和压的关系。”[11]巫鸿补充道:“在现实中,包围和‘挤压’着她的是北京各种或存在着或正在消失的空间:低矮房屋和院落组成破烂不堪的街区,拆毁的民宅向大街上的过客展开自己的内部。”[11]从拆迁现场“抢救”下来的“瓦片”成为一种艺术意象,这既是对这些消失的空间的一种记录,也是对随着这些空间的消失而消亡的记忆的一种保存。艺术家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发掘和定义了自身与空间的关系。
在这些向现实环境敞开的材料中,积淀着真实的本土经验,而实验艺术家所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说,使得这些原本不可见的经验获得了一种“可见性”,成为可感知的审美对象。
(三)作为“事件”的艺术
上述所涉及的实验艺术尽管在观念、材料、媒介等方面进行了实验,但总的来说,其艺术形态仍是以“物”的姿态呈现,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与作品本身相分离,艺术与社会的互动最后凝结于作品的“物性”之中,作为一个客体对象被欣赏。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是,以行为艺术为代表的很多实验艺术不再以“物”的姿态而是以“事件”的姿态进入观众的视野。以“事件”形态展开意味着艺术不是作为“物品”而是作为“过程”和“活动”而存在。举例来说,邱志杰在1992年创作的一项行为艺术是在一张纸上反复书写一千遍《兰亭序》,直到整张纸被字迹覆盖成完全的黑色,构成这件作品的不是作为“结果”的黑色纸张,而是反复书写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艺术家创作和表演的行为,也是观众观看发生的过程。
以“事件性”取代“物性”意味着更关注作品发生、发展、与外部的关系及其产生的效应。在这个过程中将艺术家、观众和世界都纳入事件的要素之中,而不是按照传统的观看模式只关注孤立的作品本身的形式与品质。作为事件的艺术进一步打破了艺术的边界,也将1990年代的许多社会问题以一种更加极端的方式置入艺术界域之中。从1989年肖鲁在“中国现代艺术展”上的枪击事件开始,1990年代的许多行为艺术以一种新闻性质模糊了本质上是虚构的“艺术事件”与真实发生的“政治事件”“社会事件”之间的边界。肖鲁在展览上当众向自己的装置艺术《对话》开了两枪之后,即因扰乱治安罪被行政拘留,枪击事件也引起了中外媒体的争相报道,成为名留当代艺术史的标志性事件。尽管事后艺术家发表声明称枪击行为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一次纯艺术的事件”,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行为还是以很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姿态强硬地迫使社会与艺术进行对话。再如,1994年5月,朱发东开始实施为期一年的行为艺术《此人出售,价格面议》。他身穿背后缝有“此人出售,价格面议”字样的中山装,行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直接出售自己的身体。将商品交易行为直接置换到艺术行为当中,现实中没有完成的社会与个人价值的交换,索性以反讽的方式在艺术中寻找一个象征性的补偿。在这些事件化的艺术背后,存在着既是艺术家个人也是艺术界对自身社会存在与文化属性的困惑与探索。必须承认的是,大多数尝试是不成功的,既没能产生艺术价值,也没能产生社会影响力,最后仅仅是博人眼球的戏谑性事件。
19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历着一个急速的现代化的过程,作为个体存在的实验艺术家们往往体验到的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交织在一起的不均质的社会生活状态。这种状态“介入”艺术当中的种种尝试也往往是离散而多样化、不成熟、不完善甚至是混乱的。这也使得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在一种破碎的视界之中勾勒实验艺术的方向和变化。但我们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在这个破碎的视界之中,实验艺术家们自身所处的历史传统、时代情境、地域环境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又确乎显现成一股“合力”,内化为1990年代实验艺术讲述中国问题时独特的本土立场。
三、审美转向:实验艺术的观看机制及其困境
实验艺术的社会介入不可避免地带来审美方式的转变。西方前卫艺术带来的诸多变革,如艺术对“美”的颠覆,对“感性”的颠覆,与经典美学观念相悖的种种实践,都打破了传统艺术的审美方式,带来审美经验上的巨变。而在中国,这个问题又尤为复杂。
自康德以来的西方经典美学将审美限定为无利害的、对艺术感性形式的静观,由此建立起艺术的自律性观点,强调审美对象的独立性与自足性,即审美主体与外部世界相分离,艺术本身作为独立的、自足的、意义自我封闭的对象呈现。与经典美学相符合的是传统画廊、博物馆、美术馆中对于艺术作品的观看方式:作品被剥离了它的原生语境,以“对象化”和“客体化”的姿态被观看,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审美距离,往往造成审美主体的独白式观看,而无法与艺术作品和艺术家形成真正的对话。可以说,艺术的博物馆化建构了一种剥离外部语境的纯净视觉。
而当代的种种艺术实践很显然已使得这种静观理论之下的纯净视觉越来越无法满足艺术创作与艺术接受的需要,甚至造成阻碍和误导。因此当我们面对以“反艺术”“反美学”等极端姿态登场的实验艺术时,并不代表审美需要的消失,而是审美机制与诉求发生了变化,呼唤一种迥异于传统的观看方式。单就1990年代中国实验艺术而言,首先,很多实验艺术脱离了结构化的、正式的展览空间,代之以地下室、工厂、私人住宅甚至广场等开放性的公共空间。比如1998年冯博一策划的“生存痕迹”作为“内部观摩展”在北京郊区一个废弃的厂房中举办,1999年徐震、杨振中和飞苹果策划的“超市”展使用了一个公共商业空间(上海广场购物中心)进行展览。实验艺术在“反博物馆化”的努力中试图进入日常生活经验的中心,提供一种与艺术所思考的问题紧密相连的原生“情境”。其次,在这种“情境”中,“对象”不再清晰地凸显,不再呈现纯净的视觉性,而是以“情境化”的方式,常常是多感官、多维度地被体验和被思考。以“超市”展为例,30 多个艺术家的作品被包装成有完整标签和售价的“商品”摆放在“自选商场”的门口,有专门的售货员,观众可以自行挑选并到收银台结账,“超市空间”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装置空间”,其中有录像、装置、行为、绘画、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交织,共同营造出当代生活空间的一个“情境”。在这个超市情境中,并不只有包装定价的“商品”是体现展览意图的艺术品,而是整个空间、整个展览行为都可以视为一件艺术作品。同时,实验艺术也往往呼唤一种直接的现场性,从主客体分离转变为一种主体间性的共在,艺术家与观众之间寻求一种直接在场的对话与互动,最为典型的就是行为艺术。艺术家本人的行为与观众的回应和反馈都是艺术现场的一部分,而像尹秀珍《变化》这样的装置作品看似也使用展览陈列的方式,但并不是艺术家个人独白式的展览,而是在“墓地”式的沉默中邀请参观者共同进入艺术材料的情感记忆之中,在参观者与消失的空间之间重新建立起联系。
首先,我们应该重新定义的就是“审美”这个概念,而不仅仅把审美限于纯形式的感性之中。借用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审美“指一种鉴别、知觉、欣赏的经验”[12]。杜威认为日常经验与审美经验之间并不存在康德式的截然二分的界限,审美经验是更加完满、连续、具备内在整体性的日常经验,即他所谓的“一个经验”。因此,“审美经验的包容度很大,极具弹性,是一种缺乏明确内涵和确定外延的心理感受,它有时涉及感性,有时涉及理性,有时涉及自然,有时涉及艺术,有时涉及感觉,有时涉及知识,有时涉及评价,有时涉及意愿,包含了无数的东西”[13]。
其次,实验艺术的现场性和互动性,也要求我们将注意力更多地从艺术创作方面转向艺术欣赏和艺术接受的层面。20世纪的理论大多倡导一种和审美静观、艺术自律相对立的广泛意义上的“介入”美学。比如美学家阿诺德·贝林特就在杜威经验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审美介入”(aesthetic engagement)的理论。他在《艺术与介入》一书中指出欣赏当代艺术最为重要的一个观念是:“欣赏者以参与的姿态介入艺术对象或环境。”[14](2)他用“审美场”这个概念把“审美情境的四个主要方面——创造性的、客观性的、欣赏性的和表演性的——结合成一个整体”[14](13),从而用“审美介入”代替“审美无利害”,用参与代替静观。
简而言之,实验艺术的社会介入所追求的是从传统的独白式观看转向主体间性的情境现场,从纯粹、独立、自足、自我封闭的审美感受转向开放、混合、意义交织的复杂经验。
然而,由社会介入所造就的追求“现场性”的观看机制,却因为缺乏社会的关注度和影响力而陷入一种“现场性”缺席的困境。1995年,批评界针对1990年代的行为艺术举办了一场学术性的讨论会,与会者中,冷林指出:“在没有有效传媒对行为艺术进行传播的情况下,行为艺术采用摄影照片和录像的形式来记录,人们对行为艺术活动过程的了解,只是通过图像材料,那么行为艺术现场的感染力无法让人体会到,而且图像材料本身的真与伪也尚有待判定。”[4](925)岛子也指出:“行为艺术的理念既然是对架上绘画的革命,扩大视知觉的媒介和语言,那么再刻意制作成图像材料用来传播,本身就成了问题。”[4](925)张栩则认为:“图文资料与行为本身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4](925)总之,“行为艺术或观念艺术在中国的生存土壤,似乎不容许艺术家追求直接的现场性。艺术即时的反叛和挑战特征,它的社会性和公众性,一句话,它的当场影响力统统成为问题”[4](925)。
而这一针对行为艺术所指出的困境,同样也存在于装置、录像等其他非架上绘画的艺术形式,为了保持实验艺术的独立性,相应地往往就要牺牲大众市场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持。除了上述原因以外,大部分观众仍被传统的审美方式所影响而无法以“介入”的方式欣赏实验艺术的情景现场,这也是“现场性”缺席的一个客观原因。总之,由于社会影响力有限,实验艺术实际上无法通过在场的观看机制实现其社会性诉求,而更多的是通过图文资料作为“当代艺术史”而非“当代艺术”进入观者的视野,成为一种“档案化”的观看。这种“表达机制”与“观看机制”之间的错位关系,而非社会批评的艺术诉求,其实才是实验艺术自我边缘化的真正困境。
尽管如此,当我们时隔二三十年回望1990年代的实验艺术,其中的种种尝试虽然已经失去即时的公众效应,但仍然具有作为“社会文本”和“艺术文本”的双重价值与历史意义。就像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社会’从来不只是一个束缚个人和社会实现的‘死的外壳’,同时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构成过程。其强制力既有 政治、经济、文化形式表现,又被内化为个人意愿从而充分实现其‘作为一种构成要素的性质’。”[15]本文所探讨的社会介入与审美转向,正是在社会“作为一种构成要素的性质”上,对实验艺术与当代中国社会关系的一种勾勒和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