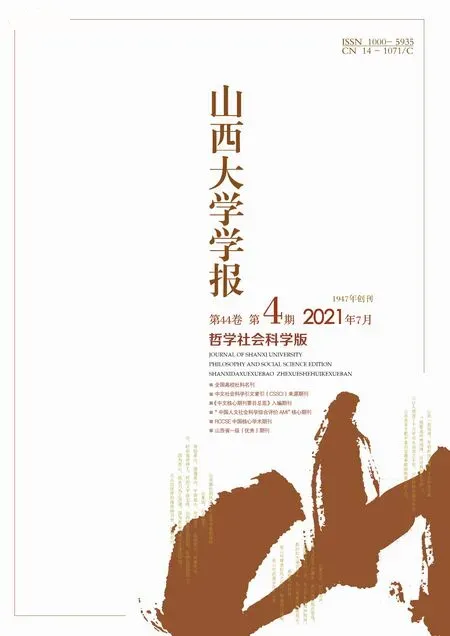论五四“诗意体小说”的文体价值
王爱军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后,小说的叙事文体迎来了全新的面貌,尤其是小说的“文体互渗”[1]现象刷新并发展了小说的“杂”质特征。有学者认为:“就中国现代小说来说,已经产生了两次明显的交融互渗:一次在20世纪20年代,另一次在80年代。”[2]20年代即五四时期,主要表现为诗歌、日记、书信等诗化文体与现代中短篇小说互渗融合而生成诗意体小说(1)“诗意体小说”并非“诗体小说”,后者是指具有小说特点的一种叙事诗,但篇幅比一般叙事诗长,像小说般地描绘人物性格和构建故事情节,如拜伦的《唐璜》、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的《芒果街上的小屋》等。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诗体小说”文本较少,如《王贵与李香香》等有限的几篇(尚丽清,高月梅.中国的“诗体小说”[J].内蒙古电大学刊,2002(6):59-60.),而“诗意体小说”文本极多,其文体特征主要表现为篇章结构穿插诗词歌赋而寓于诗情画意,故事情节弱化而诗情特征凸显,这类小说也被视为“诗化小说”范畴(吴晓东.现代“诗化小说”探索[J].文学评论,1997(1):118-127.)。至于那些抒情气息浓郁、意象意蕴丰盈而无诗词歌赋穿插的“诗化小说”则不属于本文探讨对象。、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等。诗意体小说文本如:冰心的《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郁达夫的《南迁》《茑萝行》,郭沫若的《牧羊哀话》《残春》,陈翔鹤的《断筝》《茫然》,许地山的《换巢鸾凤》《缀网劳蛛》,王统照的《春雨之夜》《一栏之隔》,杨振声的《玉君》,庐隐的《海滨故人》,李霁野的《露珠》,韦丛芜的《校长》,林如稷的《狂奔》,冯至的《蝉与晚祷》,等等。这些文本不仅植入诗词歌赋的外在形式,而且汲取诗词歌赋的内面精神,凸显了生命主体的至真性情和自由个性,标识了现代生命意识的觉醒与丰盈。五四小说的“诗意体”现象表征了五四时期生命个体对于诗性生存的强烈诉求与美好憧憬,这正是五四小说“诗文互渗”形式的重要价值功能,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
一、生命审美:现代小说诗文互渗溯源
传统的“诗化小说”之谓并非指小说被化成诗,而是指小说借鉴和吸收诗词歌赋的文体形式,如文辞、格式、情调、韵律、意象等抒情表意元素,创造出“不以叙述故事或塑造人物形象而以表达某种情绪感受或营造意境为中心的小说”[3]。中国现代小说的“诗化”审美发端于清末,“诗意体”形态兴盛于五四时期。
1907年,觉我著文认为:“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4]“美之究竟,在具象理想,不在于抽象理想。”[4]“其言美的快感,谓对于实体形象而起。”[4]即小说的价值在于“审美”的有无,“审美”来自具象而非抽象,而具象连缀着感情,是为“感情美学”,尤其认为女性所阅的小说应当“加入弹词一类,诗歌、灯谜、酒令、图画、音乐趋重于美的诸事”[5]。可见,此一时期小说诉求的诗意形式已然标识了自觉的趣味和美育功能,然而个性至真情感还不够凸显。时至五四,现代小说的诗化形态与价值功能超越以往,没有停留在仅仅将诗词、赋赞、韵语穿插于小说以呼应阅读之趣,而是将诗词歌赋中的“文体情景”扩展至小说全篇,比如融入小说语言、文本结构或表现方式之中,在更大程度上汲取诗词歌赋的内面精神,以“突出故事情节以外的‘情调’、‘风韵’或‘意境’”[6],从而彰显了主体的至真性情和生命意识,其理所当然地属于生命的文学,犹如诗情勃发的青年郭沫若所言:“生命地文学是必真、必善、必美的文学:纯是自主自律底必然的表示故真,永为人类底Energy底源泉故善,自见光明,谐乐,感激,故美。”[7]
生命的文学源于主体对生命的沉思、礼赞和审美。五四作家的生命之思不仅受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歌德的泛神论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8],而且还受到欧西“抒情型”文学的文体影响。萧乾说:“晚近三十年来,在英美被捧为文学杰作的小说中,泰半是以诗为形式,以心理透视为内容的‘试验’作品。”[9]这种“诗形”的“试验”也在五四文坛流行着,郁达夫、冰心、郭沫若、庐隐等作家的五四小说莫不如此。1920年,周作人激切地向中国读者介绍国外的“抒情诗的小说”:“小说不仅是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10]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五四文坛的抒情旋风,郁达夫的《茑萝行》、郭沫若的《残春》、冰心的《秋风秋雨愁煞人》、王统照的《春雨之夜》、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作品无不性情十足且情意绵绵。未名社作家韦素园很是欣赏俄国现代文学的“诗形美质”,认为“他们从事创作的人,仅只歌咏刹那,赞颂美,死和女性;音韵特别讲究,读时仿佛如悠扬的,音乐的鸣声似的”[11]。“歌咏”与“音韵”的诗意形式深深影响了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如小说《两封信》《我的朋友叶素》和散文《“窄狭”》《端午节的邀请》等作品皆弱化“叙事质”而强调“情绪质”。宗白华于五四时期著文亦表示“湖山的清景在我的童心里有着莫大的势力。……我仿佛和那窗外的月光雾光溶化为一,飘浮在树杪林间,随着箫声、笛声孤寂而远引——这时我的心最快乐”[12],处处景语皆情语,生命的审美和快乐是与月雾林籁等恒性的自然相映生辉的。宗白华的诗意心声与五四作家的生命礼赞实相一致。
总之,五四小说的“诗意体”主要表现为诗词歌赋的穿插融合,既有古典诗词的植入,也有现代诗歌的穿插,还有民间歌谣的融合,形成了诗文互渗的繁荣格局。这类小说文本以“诗”为维,以“情”为经,“诗意”为表而“诗性”为里[13],映现着物我相合的情感力、想象力、生命力和审美力。
二、性灵觉醒:以“诗”为文的诗意语体
诗词穿插形式被称为“插入体”叙事。著名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认为,“插入体”叙事即“打破小说中语言单一线条的实例——卷首(或章首)引语、前言、插入信件、脚注、所引文件、各章标题”[14],从而创造小说的结构和意义。这类“插入体”叙事在欧西现代小说中颇为流行,如博尔赫斯、乔伊斯、托马斯·哈代等人的作品。我国现代文学批评家高明曾于20世纪30年代著文述及:“小说里不时插入诗歌这件事,就在哈代的作品里也是很多的。而同时,在菩特娄的作品里,在赫克斯莱的作品里,也可以看到很多。”[15]可见这类“插入体”叙事形式已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涌进我国现代文坛,并被中国现代作家们巧妙运用而赋予现代小说以独特的意义。
冰心小说的“插入体”叙事形式甚为典型。1932年,现代作家赵景深等人著文认为冰心小说“巧妙地融合了古代的诗词和散文”[16],“与其称她的小说为小说,无宁称它为诗更合适些”,是“诗人的小说”。[17]可见冰心小说“诗词”穿插的普遍与繁复。小说《斯人独憔悴》以“诗语”开端勾勒自适之境:“一个黄昏,一片极目无际绒绒的青草,映着半天的晚霞,恰如一幅图画。忽然一缕黑烟,津浦路的晚车,从地平线边蜿蜒而来。”[18]此情此景容易勾连到王维《使至塞上》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小说结尾穿插杜甫《梦李白》的诗句“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以抒发青春生命之隐忧。小说《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标题源自清代诗人陶澹人《秋暮遣怀》诗句:“篱前黄菊未开花,寂寞清樽冷怀抱。秋风秋雨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该诗意境很是契合小说主人公“我”与英云等同学少年的心境,所谓“更何处相逢,残更听雁,落日呼鸥”[19]的生命情怀。尤其开篇和结尾反复写到“秋风不住的飒飒地吹着,秋雨不住滴沥滴沥地下着,窗外的梧桐和芭蕉叶子一声声地响着,做出十分的秋意”[19],诗语“秋意”更“秋语”,与“秋又暮。更窗外萧萧,几阵芭蕉雨”[20]的心绪相合,处处是“秋”字字“愁”。小说《遗书》以黄仲则之词寓景:“晚霞一抹影池塘,那有这般颜色作衣裳?”以欧阳修、苏东坡诗文抒情:“这是晚餐后,灯光如昼时,炉火很暖,窗户微敞,清风徐来。”[21]151古之佳句“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欧阳修《生查子》)、“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苏轼《前赤壁赋》)被化用其间,性灵情愫熠熠生辉。女主人公宛折花赠友的心境这般:“窗内两盆淡黄的蔷薇,已开满了。在强烈的灯光下,临风微颤,竟是画中诗中的花朵!一枝折得,想寄与你,奈无人可作使者。”[21]152花语人情,诗画一体,诗心满怀空寂寞。文学史家杨义评说:“‘一枝折得’,是古诗词中常见的倒装句法,欲寄无人可使,便用一个‘奈’字,衬出惆怅的情绪,珠联璧合,传达了一种类似婉约词人笔下的凄淑怨怼的韵味。”[22]可见冰心小说“插入体”叙事形式能从婉约词人李清照那儿觅得踪迹,如《六一姊》汲取《声声慢》之意境:“乍暖还寒时候常使幼稚无知的我,起无名的怅惘”[21]185,这是青春的纯情弹奏,没有生命的休止符。
郁达夫开创了现代小说的“主情”模式,诗意绵长。小说《沉沦》穿插了华兹华斯和海涅的诗歌,《银灰色的死》穿插了《坦好直》中的诗句,《南迁》穿插了歌德的《迷娘的歌》,《采石矶》穿插了黄仲则的旧体诗,《茑萝行》穿插了Housman的诗歌AShropshireLad(A·E·霍斯曼《什罗浦郡的浪荡儿》),等等。郁达夫诗意体小说形式的繁复首先得益于作家自身的诗学素养,“在预备班时代他就已经会做一首很好的旧诗”[23]。郁达夫不仅会做旧诗新诗,而且崇尚那些个性率真自然的浪漫主义诗人。如《银灰色的死》中穿插的现代诗篇《坦好直》便颇有意味,其汉译十分巧妙,因为“坦”和“直”表征了浪漫主义诗人Tannhaeuser的率直个性,也同时暗合作家郁达夫、小说叙述人和主人公的性灵特征和情感期待。当主人公“他”得知女孩静儿即将嫁人时,很想做些事情以表达自己的爱意,此处便穿插德文《坦好直》唱句:“你且去她的裙边,去清算你们的相思旧债!”[24]“可怜我一生孤冷!你看那镜里的名花,成了泡影!”[24]他将古人之爱与自己的爱情相比照,寄寓了冲出现实荆棘以追求生命自由的心境。小说《南迁》穿插了德语诗歌《迷娘的歌》:“那柠檬正开的南乡,你可知道?/金黄的橙子,在绿叶的阴中光耀/柔软的微风,吹落自苍穹昊昊/长春松静,月桂枝高/那多情的南国,你可知道?/我的亲爱的情人,你也去,我亦愿去南方,与你终老!”(2)汉译诗句是作者于文末附译的。参见: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1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37.这是歌德长篇散文体小说《威廉·麦斯特学习时代》第三卷的插曲,其与郁达夫小说《南迁》的主体情怀实相一致,即对于生命自由和诗性生存的眷恋与向往。《采石矶》是郁达夫所有小说中穿插诗歌最多的文本,共有15首古典诗词植入小说文本,它们皆是“内倾型”生命意识的感怀之作,映现了五四时期个性觉醒和自由自适的生命意志。
此外,郭沫若、陈翔鹤、杨振声、王统照、许地山、冯沅君等现代作家的小说中也植入了不同类型的诗词歌赋形式,彰显了生命个体的情感之真和理想之切。郭沫若的《牧羊哀话》穿插了忧伤的民歌——“太阳迎我上山来/太阳送我下山去/太阳下山有上时/牧羊郎去无时归”,流露了牧羊人生命无依的忧伤之情。《未央》穿插了感伤的童谣——“鱼儿呀!鱼儿!你请跳出水面来,飞向空中游戏!”呈现了生命个体的孤寂之情。《残春》穿插了忧郁的现代诗:“谢了的蔷薇花儿/一片两片三片/我们别来才不过三两天/你怎么便这般憔悴?”睹花思人问归期,生命易逝情何堪。陈翔鹤的《断筝》穿插了两首现代诗以表达对父亲的命运追思和对自己的生存沉思:“游子何时归来/可还有衣锦返乡时候?/父亲,鲁德罗高塔已毁/这除非是在梦中/我昨夜也曾魂绕你左右。”生命中的亲情父爱始终是游子的心灵港湾。杨振声的小说《玉君》由于浓郁的“诗意”语体而在当时就备受关注,如吴宓认为“《玉君》一书之词句文体,亦深得熟读《石头记》之益,而有圆融流畅之致。《玉君》作者,又曾诵读中国诗词,故常有修琢完整之句法”[25],即《玉君》的诗意语体显然借鉴了诗词歌赋的文体元素,比如穿插了屠格涅夫的《春流》和中国渔歌“打鱼乐”[26],穿插的“诗语”不仅连缀了小说叙事的情感线,而且暗合着主人公“我”的生命活力和自适情怀。许地山的《换巢鸾凤》穿插了四首现代诗歌,构建了有意味的“诗境”,超越了现实人生而进入诗性之界,如沈从文所言:“落花生的创作,同‘人生’实境远离,却与艺术中的‘诗’非常接近。”[27]冯沅君的小说也是一篇篇充满着“诗气息的文字”[27],《隔绝》穿插了一首篇幅较长的现代诗,以“就在这样的夜里”为首的四节诗歌烛照了“你我”诗意盎然的心灵世界。王统照的《春雨之夜》《一栏之隔》,未名社作家李霁野的《露珠》,韦丛芜的《校长》,“浅草—沉钟社”作家林如稷的《狂奔》,冯至的《蝉与晚祷》等,皆穿插了形式各异的诗词歌赋以凸显个体性灵觉醒的生命姿态。
三、诗性生存:以“情”结构的文体功能
诗词歌赋不仅仅从语体层面为五四小说穿上了一件“诗意的外衣”,而且从叙事结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情景融合。五四作家虽然“在解脱着旧诗词的窠臼”,但“不曾把那抒情的成分完全抛弃”,[28]从而使得五四诗意体小说回荡着至情至性的音符,并且以现代诗歌为中心形成了绵长厚重的“情绪链”,映现着物我相合的情感力、想象力、生命力和审美力,构建了一片情感炽热和生命自适的诗性生存空间。
田汉认为“诗人把他心中歌天地泣鬼神的情感,创造为歌天地泣鬼神的诗歌”[29],诗歌是情意的载体;郭沫若呼唤“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醇底美酿,慰安底天国”[30],诗歌是灵魂的呐喊;郑振铎强调诗是“包含情绪更为丰富而感人”[31],诗歌是人性的烛照;叶圣陶认为好诗的必要条件为“情感是深浓热烈的”[32],诗歌是深情的呼应;成仿吾追求“诗的全体要以它所传达的情绪之深浅决定它的优势,而且一句一字亦必以情感的贫富为选择的标准”[33],诗歌是情感的伴侣;冰心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是充满了情绪的”[34],文学是情感的见证;郁达夫坚信“艺术的第二要素,就是情感”[35],艺术是情感的表征。甚至到了30年代初期,诗歌诉求战斗功能的同时也必须“更能挑拨人们的心弦,激发人们的情绪”[36]。显而易见,现代诗歌“至情至性”的质素迫切地融入了现代小说创作之中。茅盾于1922年著文呼吁:“出于真情的文学才是有生气的文学,中国文人一向就缺少真挚的情感;所以此时应该提倡那以情绪为主的浪漫主义。”[37]茅盾作为现代文学文艺批评的开创者,相继撰写了《徐志摩论》《庐隐论》《冰心论》《落花生论》《女作家丁玲》《〈呼兰河传〉序》等作家作品论,而这些作家的五四文学创作无不秉持着“以情绪为主的浪漫主义”标准。五四作家郑伯奇宣称“身边小说”的吸引力就在于作者是在“强烈的冲动之下”的写作,“这种情感的作用和抒情诗是同性质的”,[38]其等同于“抒情诗”的情绪或情感要求革新了现代小说的文体面貌,即诗意为表,诗性为里,节奏鲜明,律动强烈。正如现代作家张资平所言:“不是以言语文字上之外的韵律为表现,而是以内在的意义,即文学内容的律动(Melody)为表现。”[39]张资平的五四小说践行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如《冲击期化石》《约檀河之水》等,与郁达夫早期小说的文体风格有着相同之处。
郭沫若的小说《残春》《Lobenicht的塔》《喀尔美萝姑娘》等篇章皆可视为浪漫主义诗学的小说实践。《喀尔美萝姑娘》的整篇结构“诗意”盎然,比如诗语般的人物对话:
——“唉,唉,是的,是的。我对不起你。”
——“倒是我对不起你呢。但是……只要……”
——“只要甚么呢?只要我爱你么?”
——“唉,那样时,我便死也心甘情愿。”
——“啊,姑娘!啊,姑娘,姑娘!”[40]
若去掉“破折号”和“引号”,这些语句近似于五四时期的白话“抒情诗”,充满强烈的节奏感,呈现回旋上升的波浪状,映现着至情至性的情感激流。郭沫若在《论节奏》中说:“抒情诗是情绪的直写。情绪的进行自有它的一种波状的形式,或者先抑而扬,或者先扬而后抑,或者抑扬相间,这发现出来便成了诗的节奏。节奏之于诗是她的外形,也是她的生命。”[41]节奏就是生命,实质上就是主体的情感力、生命力和审美力的形象表现。小说里除了准诗句还有标识“情感力”的词汇符号——“啊、嗳、唉、哦、哟”等语气词以及感叹号(!)、问号(?)的叠加运用,如《残春》中主人公“我”的梦境独白:“啊啊!啊啊!这种惨剧是人所能经受的吗?我为甚么不疯了去!死了去哟!”[42]小说《Lobenicht的塔》的第八节重复了四次“啊,Lobenicht的塔!”[43],以此表征康德教授冲出内外藩篱而抵近生命生存的诗性之境。以上诗句语段和词汇符号皆可与郭沫若的诗歌《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进行比照:
啊啊!我眼前来了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44]
它们不属于现实人间,而是超越现实的生命彼岸。郭氏小说与诗歌的文体互文性共同建构了一方庇佑此生的诗性生存空间。
庐隐虽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但其小说却有强烈的“情感”音符,结构了庐隐小说的叙事空间。庐隐认为:“艺术的结晶,便是主观——个性的情感。创作者当时的情感的冲动,异常神秘,此时即就其本色描写出来。”[45]这“本色”即是以庐隐式的“泪水”作为至情至性的形象呈现,释放的快感构筑了庐隐的诗性大厦。《或人的悲哀》以“泪诗”结构全篇:“假若智慧之神不光顾我/苦闷的眼泪/永远不会从我心里流出来呵!……我禁不住坐在她往日常坐的那张椅子上,痛哭了!”[46]痛哭流涕呼应了小说的标题——“或人的悲哀”,结构的情感力显而易见。《海滨故人》的主人公宗莹吟唱赋体“泪诗”:“叩海神久不应兮/唯漫歌以代哭!”宗莹同时流出一连串的泪珠儿,还有玲玉“扑朔朔滚了下来”的泪水,露沙“痛痛快快流了半天眼泪”,莲裳“哀哀地哭”,云青“眼泪便不禁夺眶而出”,等等,真情之泪贯穿全篇,映现了现实感怀与诗性诉求的交织缠绕。
郁达夫于五四时期创作的小说更是唯“情”至上,诗性昭然。郑伯奇于20年代中后期评论郁达夫的《寒灰集》说:“凡一翻读《寒灰集》的人,总会觉到有一种清新的诗趣,从纸面扑出来,这是当然的。作者的主观的抒情的态度,当然使他的作品,带有多量的诗的情调来。……怎样能不唤起读者的诗情来呢?”[47]“诗趣”和“诗的情调”彰显着主体的诗性精神,这是郁达夫诗意体小说结构的独特标识。文学研究会作家王以仁的小说创作风格“颇和创造社同人相近”[48],且“带有达夫的色彩”[49],“诗情”比之郁达夫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小说《流浪》《落魄》《还乡》《沉缅》《殂落》等全篇回旋着“凄苦之情”[50]的激越音符。未名社作家韦丛芜的《在伊尔蒂希河岸上》、台静农的《负伤的鸟》等皆“有较强的浪漫抒情色彩”[51],情感至真,诗意盎然。“浅草—沉钟社”作家陈炜谟呼吁“要捉住的是一种情调”[52],创作了《轻雾》《甜水》《寻梦的人》等浓情烈意之作;该社同仁陈翔鹤的《幸运》《断筝》等小说篇章也多小诗结构而流泻“真情”,词句反复、意象寄寓、旋律回荡和情绪宣泄是其小说结尾的共性,比如《茫然》的结尾:“——哦!哦!幸运!幸运!无穷而可以赞美的长久——十年——幸运,今日已实现吗?”[53]不无交织着现实感怀与诗性诉求的复杂情愫。正如鲁迅所言:“向外,在摄取异域营养;向内,挖掘自己的灵魂,将真和美唱给寂寞的人们。”[54]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五四时期的中短篇小说是“最美的情感之最经济的记录”[55],“常有抒情诗的元素在内”[56]。这些中短篇小说吸纳诗词、赋赞、韵语等文体质素而生成“诗意体”小说,其结构全篇的诗情画意往往与五四白话“抒情诗”有着呼应关系,烛照了五四时期生命意识的觉醒和丰盈,指涉了生命个体对于诗性生存的诉求与憧憬,屡屡试图超越现实悲苦而抵向真善美之境,以期得到诗性王国的庇护。此谓五四小说“诗文互渗”的真实镜像和价值功能,既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也对于新世纪的文学书写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