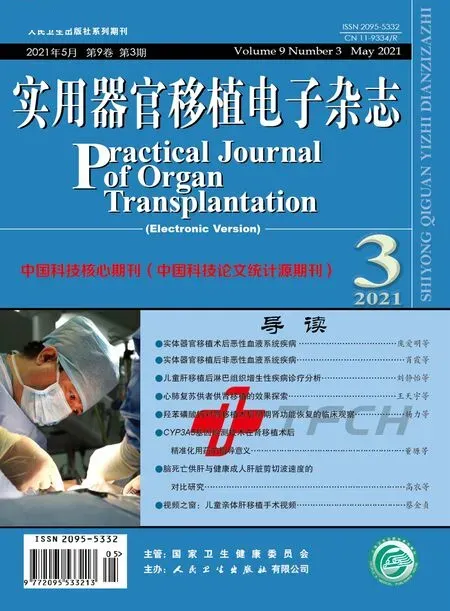实体器官移植术后恶性血液系统疾病
庞爱明,韩明哲〔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实验血液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 300020〕
经过60 多年的发展,目前,实体器官移植已经发展为终末期疾病患者标准的治疗手段之一,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1-2]。中国器官移植志愿者网络数据库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大约进行1 万例器官移植手术。在器官移植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移植质量亦稳步提升,以心脏移植为例,2016-2018 年数据显示,我国心脏移植1 年存活率均超过92.5%[3]。随着实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器官移植例数逐年增加且移植后患者生存时间明显延长。由于移植后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以防治排斥反应,患者血液系统肿瘤发生的风险明显增加[4]。因此,提高对实体器官移植后常见血液系统肿瘤的认识,早期诊断、合理治疗,对提高实体器官移植疗效十分重要。
1 实体器官移植后血液系统肿瘤发病率及相关机制
实体器官移植后血液系统肿瘤发病率在不同的研究及不同器官移植中不尽相同。2018 年,Dharnidharka 等[5]报道在所有器官移植受者中,霍奇金淋巴瘤(hodgkin lymphoma,HL)发病率为11/10 万人年,浆细胞肿瘤发病率为15.2/10 万人年, 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AML)发病率为13.2/10 万人年,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ALL)发病率为2.2/10 万人年。发病机制中的关键问题如下:① 应用外源性和非特异性免疫抑制剂防治同种异体移植排斥反应,使肿瘤细胞的免疫监视受损;② 硫唑嘌呤等药物可能对细胞具有直接的DNA 损伤作用;③ EB 病毒(EB virus,EBV)对移植后淋巴增殖性疾病(posttranspl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PTLD)发病具有关键作用。
2 实体器官移植后常见血液系统肿瘤
2.1 实体器官移植后淋巴系统肿瘤:实体器官移植后淋巴系统肿瘤以PTLD 报道最为多见,最常见的是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s lymphoma,NHL)。Quinlan 等[6]报道156740 例肾移植患者中,诊断PTLD 762 例。移植后5 年和10 年PTLD 累积发生率分别为0.7%和1.4%。PTLD 的发病率随移植后的时间呈“U”形变化,移植后不久PTLD 发病率较高,移植后2~4 年发病率呈下降趋势,之后又呈上升趋势。早发性PTLD 以B 细胞为主(72.3%为B 细胞,4.2%为T 细胞,23.6%原因不明)。晚发性PTLD 中T 细胞PTLD 的比例略高(B 细胞64.3%,T 细胞9.7%,不明原因25.9%)。年轻与早发性PTLD风险的相关性更强(移植时0~19 岁与20~50 岁的HRR 值分别为6.59%和2.98%,P <0.0001),而高龄(>50 岁)仅与晚发性PTLD 风险显著相关。EBV 血清阴性与早发性和晚发性PTLD 风险均显著相关(P <0.0001)。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血清阴性与迟发性PTLD 风险相关性更强。类固醇维持治疗并不影响早发性PTLD 的风险,但显著降低了晚发性PTLD 风险(HR 0.64)。
Engels 等[4]报道了美国175732 例实体器官移植患者,包括肾移植(58.4%)、肝移植(21.6%)、心脏移植(10.0%)、肺移植(4.0%)等。移植后最常见的高危恶性肿瘤是NHL〔n =1504,标准化发病率(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s,SIR) 7.54,95%CI 7.17~7.93〕。最常见的NHL 亚型是弥漫性大B 细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DLBCL),大多数病例是EBV 阳性。NHL 在年轻和老年受者中(0~34 岁或移植时50 岁以上)发病率均高于中年受者(35~49 岁)。NHL 在肺移植受者中发病率最高(SIR 18.73,95%CI 15.59 ~22.32)。在所有受者中,移植后第一年NHL 的风险最高,然后下降,在移植后4~5 年开始再次上升到平台期。
在178785 例次成人实体器官移植中,移植后1617 例诊断为NHL,48 例诊断为HL。在已报道的特定亚型的NHL 中,85.5%是B 细胞淋巴瘤,6.2%是T 细胞淋巴瘤。风险最高的NHL 亚型是肝脾T 细胞淋巴瘤,其风险是普通人群的100 倍,其最常见的亚型是DLBCL,约占移植后NHL 的2/3,风险是普通人群的13 倍以上。在常见的NHL 亚型第二位的是Burkitt 淋巴瘤,发生风险是普通人群25 倍[7]。在儿童实体器官移植受者中, NHL 发病危险性比正常儿童明显增高,其危险性比成年人更为显著。 DLBCL 的发病率是一般人群的451 倍,免疫母细胞型DLBCL 的发病率是一般人群的1027 倍[8]。
2.2 实体器官移植后髓系肿瘤:Morton 等[9]分析了美国1987-2009 年共207859 例实体器官移植后髓系肿瘤SIRs 分别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MDS)4.6(95%CI 3.8~5.6;n =101)、AML 2.7(95%CI 2.2~3.2;n =125)、 慢 性 粒 细 胞 白 血 病(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CML)2.3(95% CI 1.6~3.2;n =36)、真性红细胞增多症7.2(95% CI 5.4~9.3;n =57)。AML 和MDS 的发病率随着移植时年龄的增加而增高,与发病率模式不同的是,除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外,所有髓系肿瘤的SIR 在年轻受者中最高,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从发病时间上看,AML 发生风险在移植后第一年增加了2.0 倍,在移植后的1~1.9 年达到了4.6%的峰值,此后风险降低。相比之下,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的风险在移植后的第一年增加了22 倍,此后急剧下降,但仍高达2.9 ~ 6.7 倍。从器官移植类型来看,心肺移植受者MDS 和AML 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脏器移植(SIR 分别为14.3 和6.5)。肾移植受者患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的风险增至9.0 倍,其他/多器官移植受者是21.7 倍。硫唑嘌呤用于早期维持免疫抑制增加了MDS 和AML 发生风险(P =0.0002)。
另一项研究报道了31691 例心/肺移植受者中37 例发生AML,153528 例肾移植患者中56 例发生AML。大多数患者(90%的心/肺移植和60%的肾移植)接受了硫唑嘌呤为基础的免疫抑制剂防治排异。AML/MDS 的发生率与移植后1 年硫唑嘌呤的用量相关,硫唑嘌呤每日剂量2.0~3.0 mg/kg组AML/MDS 发生率显著高于每日剂量<1.0 mg/kg组(P =0.031)[10]。移植到AML 发病中位间隔为3.8 年,70%以上的移植后AML 病例发生在器官移植后的5 年内。预后普遍较差,中位生存期仅为3 个月[11]。
2.3 实体器官移植后浆细胞肿瘤(plasmacytoma,PCN):Engels 等[12]对1987-2009 年202600 例实体器官移植受者(其中肾移植58%,肝移植22%、心/肺移植14%)进行研究,随访期间共发生140 例PCN,发病率15.4/10 万人年,是一般人群的1.8 倍(SIR 为1.80,95%CI 为1.51~2.12)。以多发性骨髓瘤为主,发病率为11.2/10 万人年。移植后PCN 的中位发病时间为3.8 年。PCN 发病率在移植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肾移植受者(SIR 1.88)和心脏移植受者(SIR 2.27)发生PCN 风险较高。EBV 血清阴性的受试者发生PCN 风险显著升高(SIR 3.93)。使用单克隆抗体预防排斥反应的实体器官移植受者发生PCN 风险较高(SIR 为21.0,95%CI 为9.05-41.3),而使用霉酚酸酯的风险较低(SIR 为4.00,95%CI 为1.92~7.36)。
3 小 结
实体器官移植术后血液系统肿瘤是实体器官移植术后的重要并发症,与免疫抑制剂、导致DNA 损伤药物应用及EBV 感染等因素相关。实体器官移植后常见血液系统肿瘤包括PTLD、NHL、HL、急性和慢性髓系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及实体器官移植后多发性骨髓瘤和浆细胞瘤等。其中以PTLD和NHL 最为常见。实体器官移植术后一旦发生血液系统肿瘤,往往提示预后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