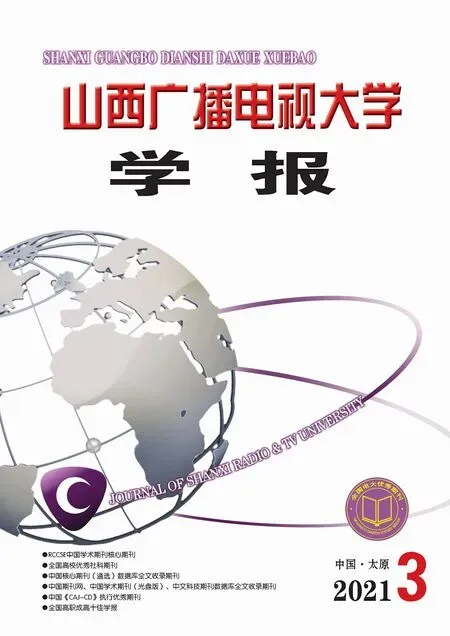《革命者》:新主流大片的创新性探索
杨宇婷 延保全
(1.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学院,山西 晋中 030600;2.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近几年,主旋律电影在电影市场上有着相对稳定的输出和表现。无论是在实践领域还是理论探讨中,有关主旋律电影的讨论和探索一直十分热络。《当代电影》在2017年第1期中关于新主流大片进行过一次研讨。编者指出,“经过多年探索之后,新主流大片呈现出来的某种结果或者新的特征:它们表现出更加成熟的叙事技巧和市场号召力,表现出更易让人接受的主流价值观表达方式,表现出对现实和历史更新角度的切入,表现出对更具普通意义的人类情感的关注。”[1]新主流电影在市场号召力和艺术表现力上的不俗表现,得益于越来越多的新主流电影懂得如何更好的在影片中缝合商业和艺术的裂隙。在近期上映的电影《1921》和《革命者》两部影片中,创作人员无独有偶地都关注到了商业和艺术的统一,对于片段类型化的呈现和艺术化的渲染都体现的十分突出。在观影的受众呈现多样化、年轻化的今天,新主流电影无疑在努力的探索中,走出了一条更加适应市场、符合艺术创作规律,同时兼具政治宣传目的的道路。
电影《革命者》聚焦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不同于传统的人物传记影片,《革命者》选取了李大钊被执行绞刑前的38个小时为时间主线,采用倒计时的方式,通过李大钊生命最后的38个小时串联起他生命中的多个重要时刻,同时也将当时风云诡谲的政治环境铺陈了出来。影片以一种极具艺术化的手法呈现了李大钊革命和生活的过往,采用非线性叙事、浪漫诗意化的意境呈现和杂糅的多元化类型表现等手法,传递革命价值观的同时,更多维度地丰满了李大钊的人物形象。
一、非线性叙事——非典型结构塑造典型人物
“对非线性叙事结构我们可以人为地分为三类:散点式、环扣式、复调式。其中散点式采用一种发散的思维方式来组织电影,整部电影的进展都围绕某个导火索,只要导火索触发,电影就铺开了。散点式的电影通过采用多条叙事线索,叙事空间比较复杂,呈现多维度,以第一人称叙事为主,其他叙事为辅。在横向时间呈现非连续性、片断性,各片断之间互不关联,自成一体。”[2]影片《革命者》以李大钊临刑前的38个小时为叙事焦点,通过倒计时的方式,串联起影片的主线。但影片内部的时间线又是完全打乱的,借助李大钊的回忆、其他人物的引出、具体的物像关联等方式,将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家人、报童徐阿晨、庆子、张学良、蒋介石、革命同志、学生、工人等这些人物群像与李大钊串联在一起。通过这些人物与李大钊的过往经历,铺展开了李大钊短暂生命中的重要时刻,充实了故事的情节,丰满了人物的血肉。影片中,主线是李大钊在被执行绞刑前的38个小时。在狱中所发生的事情,又引出了影片的其他分支。比如庆子这个人物的出场,以搭救李大钊为目的进入审讯室,在与李大钊的短暂交流中,影片以闪回的形式呈现了庆子与李大钊认识的过往。在吃饺子、教识字、唱大鼓书等等一系列细碎却重要的细节铺陈中,李大钊的人物形象渐渐立体丰满起来,他的共产主义的坚定理想以及这种精神对孩童庆子的影响绵长而深远。当镜头又跳回到现在时,观众更好的理解了庆子眼中噙着的热泪和李大钊舍生取义的坚定信念。类似于这样的呈现手法,在剧中俯拾皆是,每个出场的人物都由这种反传统的叙事方式与李大钊进行连接,全方位地还原了一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革命者形象。非线性的叙事方式,让人物的情感得到了更好的释放和渲染,同时这种打破常规的叙事方式,也可以引导观众关注除故事主线以外的更多其他细节,而这些往往是打通剧中人物与观众情感桥梁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由李大钊为主体生发出来的这些散点之间并没有关联性,每个散点内部通过表意化的剪辑呈现非线性的结构特点。正如导演徐展雄在访谈中谈到的,“……我们首先是按照剧本逻辑剪辑出了第一版,但我觉得这一版的情感浓度不够强烈,虽然影片整体的大结构是具有特殊性的,但是不同段落的结构,仍然是一种平铺直叙式的,而我希望影片的结构是跟着情绪进行的,要更偏向意识流风格一些……我的确是想追求诗意化的风格,从传统的角度来说,影片或许不能称之为‘史实片’,而应该是‘史诗片’,换句话说,它不是《史记》,而是《楚辞》。是一种像叙事诗一样的电影,而非纯叙事的影片。这也是我对影片最初的构想。”[3]在影片中,借由张学良的回忆,引出了李大钊带领底层民众为报童徐阿晨向俄罗斯列强讨说法的片段,但影片并不是平铺直叙地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依次讲清,而是先叙述张学良的片段式回忆,将最触动张学良内心的一幕先呈现了出来,进而通过非线性的几个段落,包括李大钊自己的回忆穿插其中,才将李大钊与报童徐阿晨的关系以及张学良为何要为李大钊向父亲张作霖求情的前因后果讲明白。在这个完整的大段落中,导演将线性故事打破重组,以一种片段式、重复式、间断式、多重视角介入的方式重新进行布局,营造了一种类似于意识流氛围的影片风格,同时导演也兼顾了非线性叙事中的叙事技巧,制造了悬念,给观众以观影期待。这样的例子在电影中还有多处,非典型结构既避免了影片流于常俗,又恰如其分地为观众呈现出了一个熟悉的典型人物形象。
二、诗意化意境——革命浪漫主义的渲染
《革命者》的监制管虎在谈到电影如何体现李大钊先生身上的浪漫感和诗人气质时说到,“李大钊身上一定是有诗人气质的,电影如果拍得太实,就会削弱这种气质。所以在跟剧组各部门沟通的时候,我会特别强调意境的呈现,所谓的浪漫我认为就是营造一种意境,在这种意境当中,呈现人物的人格魅力,有一种将生命挥洒于理想当中的浪漫主义……”[4]这也恰恰是《革命者》这部聚焦于李大钊先生的人物传记片的主要影像风格特点。诗意化的意境渲染,在影片中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突出李大钊本人的浪漫化和诗意性。作为众所周知的伟大革命者,他不再是被供之于高台的神话人物,而是走下神坛,有着坚定信仰、顽强意志和优秀才干的革命者。他也有失落感,会恐惧,会无助,有着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和难以割舍的情感纽带。影片对于李大钊的日常生活有更多的细节展示,比如在表现李大钊如何认识庆子这个段落时,展现了李大钊为澡堂的人们在大年三十团圆夜表演了一段大鼓书《桃符换了是新年》;李大钊与妻子、孩子们在草地上嬉戏玩耍;李大钊教妻子赵纫兰弹琴;“三一八事件”时面对无辜被枪杀的学生,受伤的李大钊在赶来医院看望他的妻子的怀中奔溃哭泣等等。这些场景多采用艺术化的诗意手法呈现,李大钊这个人物跳出了脸谱式的塑造窠臼,呈现出更加立体丰满的多面性。对于新主流电影的探索,无论在创作层面还是理论层面,近几年都在不断尝试着革新和深化。尤其是在创作层面,主创们也在尝试用更多样化的创作手法去呈现自己的作品,更好地面向电影市场,寻找与观众对话的不同契机。不难发现,作为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片,《1921》也同样在影像呈现上进行了革新尝试。影片中在塑造青年毛泽东的形象时,展现了两段奔跑戏。在这个段落中,先是在上海租界毛泽东偶遇庆祝法国国庆日的外国人而被阻隔在欢庆人群之外,而后在五味杂陈的情绪中掉头,释然地奔跑在街边,抬头看夜空中满是绽放的绚烂烟花。闪回段落中,毛泽东奔跑在老家的乡间小路上,身后追赶的是愤怒的父亲和叮咛的母亲。两段奔跑的场景,通过浪漫诗意化呈现,突破时空的限制串联在一起,凸显了毛泽东鲜活的人物性格和对革命理想的坚守。
诗意化的意境渲染的另一个层面是影片整体的氛围渲染。这也是《革命者》这部影片对于主旋律电影的创新性尝试,为新主流大片的影像呈现注入了更多新的可能性。影片中处处体现着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氛围,李大钊本人是具有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而围绕着他的人或事也都被渲染上了一层革命的浪漫气息。无论是电影开篇声音先入画,于虚实之间拉开影片的帷幕,李大钊墓碑上被雨水冲刷的红色颜料如革命的鲜血般流淌下来,还是李大钊在狱中被刑讯逼供时,幻想中握住革命同志的手和伸向光亮处的手等等片段,诗意地呈现于逐帧的画面之上。在影片《1921》中,同样有多处片段以浪漫诗意化方式呈现。在展现共产党人在嘉兴南湖开会的场景时,作品同样使用了充满意象化的镜头语言。开会时,外边下着雨,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时,雨过天晴,共产党人在船上一起朗诵《共产党宣言》、歌唱《国际歌》。这时候画面切换,电路用平行蒙太奇将六个不同时空的共产党人串联在了一起、陈独秀被抓、李大钊就义、李汉俊被枪决、邓恩铭被杀害、杨开慧被行刑、何叔衡英勇跳崖就义。发生在不同时空的革命志士对革命的无悔奉献,通过打破物理时空的限制和诗意化的渲染,突显了革命的不易,调动了观众的情感共鸣,观众在激昂的情绪中接受了革命精神的洗礼,完成了对革命先烈的深情缅怀。无论是《革命者》还是《1921》,在电影市场更加开放和多元化的今天,新主流电影在大浪淘沙中不断地找寻更适合自己的道路,发展更适应市场、观众并更具艺术价值的作品。
三、多元化类型——杂糅风格的呈现
导演徐展雄在回答关于影片结构的问题时,谈到自己对于影片叙事取舍的想法,他指出:“……其实这个“镣铐”反而成为影片叙事的推动因素,让它能够与类型片的模式相结合,提高观众对叙事时间的感知度,营造紧张的叙事氛围。”[5]在上文中提到导演希望影片更偏向意识流风格一些,从这些有关导演对影片的整体考量上,可以看出《革命者》的影像风格呈现出一种杂糅性、多元化的特点。我们既可以看到特征明显的类型片痕迹,又可以感受到浪漫诗意氛围烘托下的艺术片气质。多种创作手法的交叠杂糅,不同影片类型的交响和鸣,使得影片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叙事场域和结构风格。前一段落还在诗意化氛围中酝酿情绪,后一段落就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发生了因陈独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引发的戏院追逐戏,惊险紧张刺激的影像呈现了典型的类型片风格。学者赵卫防在评论电影《1921》时说到,“新主流大片在形式层面的主要特色是类型书写和类型创新,而《1921》的类型书写遵循了这样的美学赓续。在国际视野表现上采用了类型化叙事,类型叙事成为其主体叙事之一,其中悬疑类型是影片的主要类型。”[6]在电影《1921》中,也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与黄金荣手下程子卿惊险的追逐戏片段。日本共产党人被跟踪和日本人之间的谋杀这个段落同样也注入了很多悬疑惊险的元素,表现了跟踪与被跟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紧张氛围。这些都使得严肃的党史题材融入了类型片的风格,影片节奏更加多变,故事内容更加灵动,观影体验更加独特。同样都是新主流电影,同样都是关注党的革命发家史,不同的创作团队都在探索在现有的影像风格基础上更多影像叙事方式的可能性。
最后,需要提到的一点是,有关影像符码的使用,电影《革命者》与电影《1921》形成了有趣的互文现象。在影片《革命者》和《1921》中都反复出现了火苗的影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火苗象征着共产党永不熄灭的革命之火。在影片《1921》中,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光脚独自站在自己住所的屋顶上,迎着清晨的朝阳,露出无比喜悦的笑容;在电影《革命者》中,李大钊与毛泽东在景山迎着日出,畅谈和憧憬着新中国的未来。这两个片段中,太阳代表着希望,共产党人迎着太阳,象征着共产党人就如太阳一般,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发光发热,共产党人一定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黑暗、走向光明。在电影《1921》和《革命者》中,都出现了儿童的符号化指称,《1921》中的小女孩,是住在李达和王会悟家对面的小女孩,也是在新世纪的中国,排队参观纪念馆的小学生中的一员。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是导演安排两个女孩由同一个演员扮演,不难看出其意图。两个女孩都露出纯真的微笑,眼睛里充满着希望,实现了跨越时空的连接,她们代表着初生的新中国,代表着充满希望和无限可能的未来;在《革命者》中报童徐阿晨和他的妹妹以及小伙伴们、童年庆子、李大钊的子女等孩童除了承担相应的叙事任务外,也象征着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在影片的结尾,通过旁白的形式李大钊提出“共产主义”,而向他提问“共产主义”的是一个孩子。孩子是花蕾,充满着朝气和希望,中国共产党就如孩子一般,是一个年轻的党,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党。
四、结语
电影《革命者》以非典型的创作手法塑造典型人物,打破传统人物传记类电影的影像呈现方式。通过非线性叙事、诗意化意境渲染、多元化类型杂糅等手法组接架构电影,为未来新主流电影的创作提供了较好的借鉴经验和蓝本。李大钊先生一生为革命事业奔走呼号,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带领中国走向光明的未来。在影片中,李大钊先生和其他被捕的革命志士们被押赴刑场的一幕是压抑悲壮的,囚车的栅栏、监狱的大门层层锁住了他们,紧接着下一幕是一群飞鸟飞过天空,李大钊抬头望向天空,正如李大钊在监狱中做飞鸟的手影一般。人间地狱无法抹杀李大钊等革命者们向往自由的心,也无法抹杀革命者们为新中国的建立奋斗不息的精神,更无法抹杀初生的共产主义者们带领中国民众向着自由、民主、文明展翅高飞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