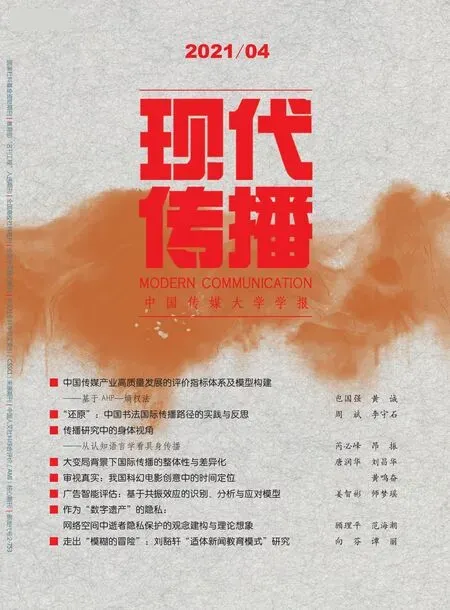他者伦理下的主体性:民族IP动画中的成长寓言*
■ 赵 敏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一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9.56亿元的最终票房,让国产动画电影扬眉吐气,随后国产动画电影沿民族化之路狂飙突进:2019年一部《哪吒之魔童降世》拿下50亿票房,创造了国产动画电影票房神话;2020年中国电影再次奉上一部史诗级动画《姜子牙》。我们可能更多地将这三部电影的巨大成功归功于国产动画制作水平的突破与故事讲述能力的提高。技术维度与叙事维度这两个向度的考量即是从动画电影内里层面寻找原因。然而,我们可能忽视了一个重要外部向度,即观影受众的情感维度。
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首次打破国产动画电影票房纪录,不得不感谢一批“自来水军”的贡献。就连导演田晓鹏接受访谈时也袒露:“国人可能压抑得太久,看到一个还凑合的东西,就过分褒奖。”①而《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同样依靠“群情激昂”的人口相传而成功出圈。这里,票房成功可归因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国人对迟来的民族动画电影的惊喜与期许,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三部电影的同一主题对位了当下受众的情感结构。
三部动画或是“不约而同”或是“有意为之”,而趋向了同一主题“成长”。说是“不约而同”,是因为电影主题可选项之多,不必在一个问题上死磕,这种同一可能是来自创作者对大众情感体认的潜意识;说是“有意为之”,则是这一“成长”主题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票房的情感保障,那么,后来者自然有意取道仿之。无论是意识还是潜意识,总之,电影的共享成功与“成长”主题的同一并非“巧合”,而是“耦合”。
“耦合”是物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能量从一个介质,传递到另一个介质中。国产民族动画电影的成功,就是借助一股以“成长”叙事结构为载体的情感流,从一部电影传递到下一步电影中。而《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三部电影取材民族IP,因此赋予了自身同一的介质体征,从而能够在民族IP这一文化共同体场域中,激发伦理情感,勾连情怀,快速促成情感共同体。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成长”在三部的电影中的面孔各有何特点?各自又有着怎样的表征?它们是如何关联当下受众的情感现实,又如何旨向意义功能的?
二、“成长”的三副面孔
世界动画电影已经摆脱低幼面向的低水平制作阶段,上升到面向全年龄段制作层次。国产动画电影正在追随世界电影的脚步,而本文所提的三部电影正是这一努力的成果展现。因此它们不再局限于低龄段的“成长”的烦脑,而是面向全龄段,徐徐展开人生不同阶段的“成长”的困惑。“成长”一词用之于个体是指人走向成熟的过程,这里既有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发育长大之意,亦有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智能成熟之意。如果说生物学层面的“成长”是阶段性的,是针对从出生到青年这一特定时期,并且是可停滞的,那么,第二个层面精神的“成长”则是适用于人生的每一阶段。人精神“成长”是全过程的,是全年龄段都将面临的人生命题,是可持续的。
为了阐释影片中的“成长”寓言问题,我们引入“感觉结构”这一术语。这是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提出的重要概念。威廉斯把“感觉结构”描述为是“一种现时在场的,处于活跃着的、正相互关联着的连续性之中的实践意识”。威廉斯阐释道:“‘感觉结构’是一种文化假设”,是对“一代人或一个时期中的关联作出理解的意图”。在威廉斯看来,“感觉结构”与文本之间存在着一种对位关系,“感觉结构的观念可以同形式和惯例的种种例证-语义形象-发生特殊关系,而在艺术和文学种这种语义形象又常常是这种新的结构正在形成的首要标志”②。
纵观三部动画电影的成功,或许正是指向了“成长”的精神层面,才能无缝对接不同代际人们的内心“感觉结构”,唤起多代人的“成长”记忆。全年龄段的定位实质是面向观影主体即13~50岁这个大年龄段。这个大年龄段是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猛发展实践一同“成长”的不同代际,细分为80后、90后和00后。他们在中国现代性发展框架内具有各自显著的特征,是同时被冠以不同文化标签的三代人。他们各自经历着不同断代的人生遭际,有着各自不同的心路历程,在中国现代性发展的阵痛中,面对着各自不同代际“成长”的困惑。那么,上述三部动画电影中的三个主人公形象“大圣孙悟空”“姜子牙”“哪吒”,正对应着这三代人,分别是80后、90后、00后的隐喻符号,呈现着中国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三张代际面孔。
80后是中国独生子女的第一代,曾经是家庭中两代甚至三代成员的“中心”,是中国“小霸王”“小皇帝”“小公主”等话语的第一代缔造者。当年的他们,那股舍我其谁的“自我中心”主义与谁与争锋的“盲目自信”,像极了大闹天空时期那个初出茅庐妄自尊大的孙悟空。80后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如今已经步入中年,即将步入人生的不惑期。他们是亲历改革开放40年的一代,当年的他们,在豪迈的改革浪潮应召下,从唯我独尊的温室中跳脱出来,携带着零社会经验勇闯天涯,一路跌跌撞撞。他们亲历改革开放40年社会巨变后,现实磨平了身上的棱角,也抹去了当年的锐气与霸气。建功立业的梦想不再,剩下的只有满身疲惫,还有那只容得下与自我对话的一隅之地。这不正是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那个被镇压在五行山下,终日自怨自艾、颓废不堪的孙悟空吗?影片彻底打破了传统孙悟空意气风发、活灵活现的形象,而是塑造了历史上第一个富有“沧桑感”的孙悟空形象。无论是脸部肌肉略显塌陷和松弛,还是身形略驼,这些形象上的修辞都一再指示着年龄:这是一个中年的孙悟空。显然,形象上的变化还是有意制造的某种“陌生化”的效果。观影的“陌生化”一再提醒着观众,应从传统的孙悟空“英雄”话语中挣脱出来,去领会现实的旨向:那个封印的五行山,那个困住孙悟空的锁链,不正是现实中“自我”的困境吗?无论是对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农民工,还是在城市打拼的外地大学毕业生而言,户口、住房、编制等难题就像一道道困住自身的魔障,让他们在城市里从青年打拼到中年,却始终游离在城市的边缘。当下,“屌丝”一词是80后常用的自我称谓,透露着点辛酸又傲娇的味道。影片中的孙大圣多少带了点“屌丝”感,而片尾“大圣归来”的最后升华或许就是给现实屌丝逆袭的一点点期许吧。
90后是当下正处于青年期到而立之年的一代,是中国社会的生力军。他们成长在中国改革开放成果初成的时期,尤其是95后,一部分人生活条件相对优渥,“官二代”“富二代”主要产生于这一代。中国青年报曾公布了一项来自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对中国各个代际群体特征的调查报告。此报告对不同代际特征给予了概括,称90后是“轻松、乐观的‘社交一代’”。在不同代际群体当中,“90后社会心态相对轻松,诸如‘社会不安全感’‘不公平感’、对‘官、富、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等负面情绪在90后中出现的频率均是五大群体最低”③。如果说80后因为背负诸多“历史先行者”的文化负累而初显未老早衰的迹象,那么,90后则是一群仍有梦想的前行者。影片《姜子牙》同样打破传统姜子牙银发白髯的老年形象,颠覆性打造了一个高颜值的帅叔叔形象。这番偶像化的包装正是娱乐时代成长起来的90后的自画像。年轻、梦想、初心是影片中姜子牙形象的关键词,也是当下90后群体特征的投影。
00后是指处于11~20岁的青少年,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哪吒显然是00后孩子们的写照。哪吒是上述三部电影中唯一一个没有进行年龄创改的形象。影片保留了哪吒的传统孩童面孔,并在高潮部分让镜头在幼儿与少年间切换,指示着00后这一群体的年龄跨度。00后被称为网生一代,是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下成长的一群人,是极富个体主权意识的一代。他们多数人个性张扬,民主意识强烈,现实中正处于青春期,自我意识高涨。影片中哪吒顽劣叛逆的举动,是少年期独立意识萌生,意欲获得关注的潜意识作祟。影片中哪吒的“魔童”身份正是对00后这一群体个性特征的委婉表达。影片不忘与社会热点的互动,哪吒来自心底的呼唤“爸爸、妈妈陪陪我”,是中国当下众多“留守儿童“的心声。
三部代表着中国最高制作水平的动画电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民族IP进行现代性改造。孙悟空、姜子牙、哪吒这三个民族符号分别表征三张代际面孔,巧合般地共同形构了中国国民的代际谱系。或许是当前国产动画民族化的共识,达成的力量同盟,彼此互动借鉴,不谋而合共谱了这样的时间序列,并共享国人的精神寓言。80后、90后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而00后则是中国社会未来的希望。他们无疑构成了中国社会力量的主体,也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建设主体。他们的精神“成长”正与中国现代性发展形成共振。某种意义上,现代性本身孕育着一个“成长”的命题。
三、“成长”的表征意图:启蒙与主体性求证
在当下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场域内,启蒙仍然是主流叙事话语的追求。民族IP的题材性质与动画电影的属性,更使得三部电影负载启蒙的担当。“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提出,使得主体性成为现代性的重要追求,主体性是现代性最主要的启蒙话语。在中国急速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同代际在启蒙话语的询唤下,都有一种自我的主体性追求。这个追求伴随人的一生,体现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也实现在不同社会关系之中。换言之,主体性的求证是个体历史化的过程。福柯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人们从未停止构建他们自己,也就是从未停滞变动他们的主体性,从未停止在无限众多的系列主体性当中构建自己,这些主体性永远不会结束,也从不会让我们面对某种叫做人这样的东西”④。
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性的求证过程,便是“成长”性的,主体性的求证过程是“成长”的逻辑展开——“主体如何在他和自身关系的真理游戏中体验他自己”⑤。而“成长”则表征着自我认同的追寻过程,是自我主体的求证过程。上述三部电影一致旨向了“成长”的命题,底色便是启蒙叙事。
当然,落实到不同的代际,这一自我主体的实现过程不尽相同,所遭遇的困境也千差万别,三部电影立足于叙述三代的“成长”困惑,解码不同代际的主体确证过程。
小说《西游记》存在一个五百年前与五百年后的时空转换,两个部分也构成了叙事上的断裂,这就为现代重构提供了空间。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正是从这一时间断裂点上开始书写:曾经大闹天宫心比天高的齐天大圣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出山后的他,心路历程将出现怎样的拐点?他是否能够心怀初心,砥砺前行?此时摆在大圣面前的是如何看待“过去的自我”“现在的自我”“未来的自我”这样一个命题。这提供了一个人生回望与展望的契机,在回望/展望中获得“成长”。因此,电影的创意呼应了当下80后老男孩们的心态,反映了当下80后男性“成长”的精神模式,即映照了当下中国中年男性群体的主体生成模式。中国的现代性发展有自身的特点,当下社会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话语并存。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中国男性是一群受过传统价值话语与现代价值话语共同规训的群体。“功成名就”是他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价值追求,也是作为社会主体获得自我认同的依据与标准。而80后男性正处于如此的焦虑与自我期许之中。对于观看群体尤其是80后男性受众来说,那个还压在五行山下或只是刑满释放的孙大圣不就是已届不惑,却还未能功成名就的自己吗?可是这并不重要。影片带领着观众寻找过去的自我——过去的自我就是现在的自我的镜像。影片开头“回顾”了孙悟空身披战甲、脚踏红云、叱咤风云的过往,又几次闪回再次“回望”了曾经的赫赫战绩。这些“回望”并不是为了驻足停留,而是积蓄过往的力量重新踏上征程。更重要的是“过去的自我”缓解了“现在的自我”的尴尬和压力。当然,影片还必须努力为“现在的自我”的认同探求路径,即“过去的自我”“现在的自我”“未来的自我”三者位移,发生重叠,最后形成同一。因此,在电影的最后,孙悟空终于能够在江流儿的精神感召下,找回“过去的自我”,手刃妖魔。影片象征性地让孙悟空重新披上铠甲,在万丈光芒中重返巅峰。孙悟空形象从布衣到铠甲的返回,也宣告了“过去的自我”“现在的自我”“未来的自我”的最终同一。影片这一结尾仪式某种意义上是为中年男性观众加冕,是对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恢复的庆典,也是为中年男性主体地位确证的庆典。以80后为主体的中年男性在这具有象征性的仪式中获得宣泄的快感与启蒙的“力量”。
如果说80后中年男性能够在影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重拾“过去的自我”,那么90后观众则在影片《姜子牙》中反躬“当下的自我”。人生的青年期是正式离开安全舒适的“温室”,步入复杂社会的阶段。面临各种诱惑、压力、考验,“选择”就成了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影片《姜子牙》正是以“两难选择”的叙事展开了对人生“选择”命题的思考。年轻的姜子牙以拯救苍生为使命立志追随昆仑,映射着90后刚刚步入社会时怀揣青春梦想的样子。然而,拯救苍生的初心却遭遇“天命”之抵牾,“斩的是善不是恶”违背了姜子牙“一人也是苍生”的理念。姜子牙所面对的“天命”与“初心”两难选择,则是90后奔赴梦想之路上“现实”与“初心”的龃龉。正如吉登斯指出:“生活在这个世界——晚期现代性世界——在自我层面上涉及了各种各样独特的张力和艰辛。我们若把这些张力和艰辛理解成一系列两难困境,便能很容易地对它们加以分析。进一步讲,无论在何种层面上,这样的两难困境都必须加以解决,从而保持一种条理清楚的有关自我身份认同的叙事。”⑥这种“两难困境”便成为了当下现代性社会中个体的心理结构。而电影的叙事形式“为自我叙事的构建提供了一定的蓝本”⑦。在现代性进程中,作为社会主体的90后深刻感受到这一结构性的困境。姜子牙最终选择保持“初心”,走上了反抗天道之路,在“做自己的神”的宣言中完成自我认同。影片对叙事的设置,一方面是对当下意识形态“守望初心”话语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对个体主体性建构的启蒙。影片中的“初心”是90后理想主义的影射。姜子牙守望初心,最后得到天道认同,也完成了自我认同。这种对个体理想主义的极大肯定,正是现代性寓言,即现代性的主体需要这样的理想主义色彩。
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与前两部电影慢进式叙事节奏不同,影片开头便揭示了戏剧冲突:太乙真人宿醉误事,错混了灵珠与魔丸,导致两物未能各尽其用,而使得本该是灵珠天神的哪吒成了混世魔王。这一戏剧性的开头预设了哪吒身份的两重性即“魔”/“神”,哪吒从一出生就必须面对是魔还是神的身份认同问题。哪吒一方面必须在面对“自我”的关系中进行“自我”认识与“自我”的确认,另一方面又必须在“他者”的观照中完成身份的确认。“自我”与“他者”是哪吒的主体性确证的两个维度。00后由于尚未独立步入社会,主要面临与原生家庭及周邻、学校的关系以及与自我关系问题。“成长”的小圈子就构成确证自我的“他者”。于是影片也在这两个维度展开叙事。哪吒在身份认同之路上,首先遭遇的是“他者”凝视中的自我镜像,这里分为家庭的父母凝视中的“自我”镜像与村民凝视中的“自我”镜像。而哪吒最早获得的身份认知并非来自家庭,而是来自村民极尽夸张的情绪反应。影片使用了大量无厘头的夸张叙事塑造了村民眼中的“魔童”镜像。这一“魔童”镜像是导致哪吒无法完成自我认同的根源。同时,由于知晓哪吒的身世之谜,李靖与殷夫人夫妇为了安慰哪吒,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即哪吒的灵珠天神身份。这一谎言暂时缓解了哪吒对自身身份认同的焦虑。此时,哪吒的自我镜像是分裂的:魔童的哪吒/天神的哪吒。然而,父母谎言的败露,加速了哪吒自我认同的崩塌,认同的危机导致哪吒在“魔”与“神”两极中走向了“魔”这一极。哪吒的“魔”童身份通过“长大的身体”这一形象得以表征,这一象征性的长大的身体,也隐喻着叛逆的青春期的到来。此时,即将降临的天劫与被开启的惊世之谜将影片推向了高潮。哪吒真实身份的揭晓,改变了“他者”眼中的哪吒镜像,哪吒也完成了与自己的和解——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影片最后,天劫降临,将哪吒的主体生成之路推向了更高一个层次,即自我与世界关系。在哪吒的“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神我自己说了算”的呼喊中,认同再次升华。独立于客体世界,为自我掌控的主体由此完成了最终的确证。哪吒的呼喊旗帜鲜明地标识着现代性立场,在“我”与“天”二元对立的关系中,完成“我”的主体立场。
综上,尽管不同代际主体面对不同的“成长”困境,但实质仍是共同的命题,即如何完成自我的认同,在人生不同阶段,完成各自阶段性的主体求证。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共享的“成长”叙事主题下,不同的代际主体是如何被建构起来,或者说是基于怎样的建构逻辑而生成主体性的?
四、“成长”的表征逻辑:“他者”伦理下的主体建构
我们不难发现,三部电影在叙事上走着相同的情绪线,开场轻松搞笑,结局悲情壮烈。影片前置笑点,后伏泪点,引导观众的情绪缓缓上升,最终走向至高点。同场观众在影片高潮中形成情感共同体,在结局的悲壮美中获得情感宣泄与共鸣。这种强烈的情感体验,将暂时屏蔽理性机制的运作,而直接开启认同环节,由情感认同带动价值认同。而引发这种情感共振的“刺激物”便是影片的伦理维度,即不同代际主体性在“他者伦理”下生成。三部电影共享着相同的表征逻辑。
“从‘他者’理论的视角来看,西方哲学关于主体性问题的变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以主体性哲学为代表的自我对他者的认识与同一阶段;以主体间性哲学为代表的自我与他者的交流与沟通阶段;以伦理主体为代表的他者对自我的超越阶段。”⑧勒维纳斯则是第三个阶段主体理论的主要建树者,将主体性建构在“为他者”的伦理向度上,他认为:“人类在他们的终极本质上不仅是‘为己者’,而且是‘为他者’,并且这种‘为他者’必须敏锐地进行反思。……从我到我自己终极地内在,在于时时刻刻都为所有他人负责,我是所有他人的人质。”⑨
显然,影片的主体建构是在自我与他者关系框架内进行的,“他者”是自我重要的维度。影片虽然设置了与自我二元对立的客体“他者”,例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的妖魔、《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龙族与申公豹的反派同盟、《姜子牙》中的姜子牙与小九。然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并不以“同一性”为绝对要求,它没有拘囿于西方现代性哲学的主体本位的基本立场,将主体性的生成置于与自我截然对立的“他者”关系中实现,而是构置了“为他者”的主体面向,从而实现“为他者”的主体建构逻辑。
首先,在影片的“自我”与“他者”的第一组关系即对立关系中,主体性并不以战胜或者打败作为客体的“他者”而得到实现。自我个体的价值、主体的叙事功能并没有因为绝对对立的“他者”得到说明。孙悟空的主体性生成于打败妖魔之前,哪吒的主体性生成与打败反派无甚关系,姜子牙的主体性也同样不在于战败狐妖。
其次,影片通过从与“他者”的对立逻辑转向“为他者”的逻辑实现主体性。三部影片设置了不同的“他者”镜像。在影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下五百年,孙悟空法力尽失,光环尽褪,这时候的他对自我认同与未来前景充满迷茫。如何完成自我认同这一现代性寓言,影片自然需要一个符合现代性要求的设置来作为孙悟空最重要的“他者”镜像,而重新进行现代化改编的江流儿便出场了。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的命运错位,逆天改命的勇气,则出自于同为“他者”镜像的父母。《姜子牙》中姜子牙的主体性同样生成于“他者”小九。
影片还必须架构起“为他者”的主体建构逻辑。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进行了最大胆的改编,将小说的青年唐僧形象切换成了孩童版的江流儿。小说中唐僧的身世也成为影片改编浓墨重彩的一笔。孩童化的改编符合动画电影的人物分配,满足了观影人群中的低幼受众的欣赏需要。同时,江流儿的身世敷衍生发,则为其人设增添了一重浓重的悲情色彩,为叙事的悲情走向蓄势。江流儿的天真、执着、无畏的“强者”形象,与中年的孙悟空的颓废、感伤、自弃的“弱者”形象形成巨大反差:江流儿年龄的小与孙悟空的大,江流儿精神上的“强”与孙悟空的“弱”。在这一大一小、一“强”一“弱”的比对与互动中,江流儿成了孙悟空精神的引领者。在妖魔幻化成的巨兽这一巨大威胁面前,江流儿仅凭孩童的一己之力,殊死抵抗,最终“殒命”。影片借用中国传统美学“留白”与“写意”手法塑造“死亡”意象:乱石之中一只小手将悲情气氛点染到极致,引爆了放映现场的全场恸哭。面对巨大的对立力量,如何冲破自身局限,江流儿给孙悟空作了最好的示范。江流儿的“舍生取义”真正激发了孙悟空斗志。为江流儿复仇,拯救所有被妖魔俘虏的孩童成为了孙悟空的使命与责任。从江流儿的“为他者”激发了孙悟空的“为他者”,在“为他者”的逻辑中孙悟空实现了其自我主体的建构。如果说影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为他者”实现的是社会伦理,那么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为他者”则是基于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影片结局对立型“他者”向“为他者”逻辑转换。敖丙在哪吒的朋友情义感召下,赴死相救囚于天劫的哪吒,在“为他者”精神涤荡中,自我升华,释怀了身份危机。影片所有对立型“他者”在“为他者”的伦理中达成最后的和解。而影片《姜子牙》这一“为他者”的逻辑则更加简单明了,“为他者”直接承担了影片的叙事框架。姜子牙这一人物的行动逻辑都来自守护小九,他在展开守护“他者”小九的反抗天道之路上,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五、结语
当然,启蒙神话的完成仍然要置于启蒙话语生产与传播场域中进行考量。20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发生了巨大的转向,现代性及其启蒙的合理性遭到质疑与批判,被称为“一场具有‘反启蒙’意义的‘后启蒙’……不仅是对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历史审判,而且也是人类跨入新世纪后对整个文化的重建的‘第二次启蒙’”⑩。这一股西方思潮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当下中国社会的话语语境也具有明显的“后启蒙”特征。当下的后启蒙的语境便是民族IP的启蒙神话的文化场域,这显然是启蒙话语的表述困境。
然而,三部民族IP动画电影不约而同归入“成长”的这一启蒙叙事的大旗下,共谱了中国代际主体的面孔,而三部影片的票房无疑宣告了其启蒙神话的成功。这不得不归功于创意者是将不同代际主体的启蒙神话嵌合进观众的情感结构,从而使其获得对启蒙话语的认同。
这一方面说明了民族IP的大有可为。在中国民族复兴与现代性之未尽的道路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IP与启蒙神话天然同盟。民族IP数百年的经典化过程,赋予了自身传统价值内核,承担了传统伦理的意义表征,其一出场自然勾起民族伦理情怀。
如果说三部影片的取材为启蒙叙事奠定了情感基础,那么更为重要的情感认同则来自于伦理主体的建构。影片营造的“他者”的困境,带来了深刻的命运弄人的悲恸情绪体验,影片角色“为他者”的“献身”又引领观众对“悲壮”意义的获得,一种崇高感油然而生。因此,伦理主体生成之时,也是观众抵达“悲壮”情绪的巅峰之时,又是“悲壮”美感的巅峰之时。影片伦理主体的镜像激发受众自我主体的生成,一种“在场”的情感共同体结盟成价值共同体,伦理美学为政治赋能,打通了由伦理到美学再到政治的通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启蒙的语境与启蒙话语并不绝对矛盾,现代性主体建构在获得伦理的观照后,是能够打动中国观众,“他者”伦理下的启蒙叙事才符合中国动画观影受众情感结构的内在要求。或许,三部民族IP动画电影的成功正昭示着伦理中国对伦理主体的询唤吧。
注释:
① 材料来源:http://news.sina.com.cn/c/zg/jpm/2015-07-14/15261244.html,2015年7月14日。
② [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143页。
③ 周凯:《复旦报告详解中国代际群体特征》,《中国青年报》,2014年10月22日,第3版。
④⑤ [法]朱迪特·勒薇尔:《福柯思想辞典》,潘培庆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
⑥⑦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7、186页。
⑧ 孙庆斌:《他者视域中的主体性向度》,《光明日报》,2009年8月28日,第12 版。
⑨ [法]埃马纽埃尔·勒维纳斯:《塔木德四讲》,关宝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1页。
⑩ 高宣扬:《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上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论代际批评的“有效”“有限”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