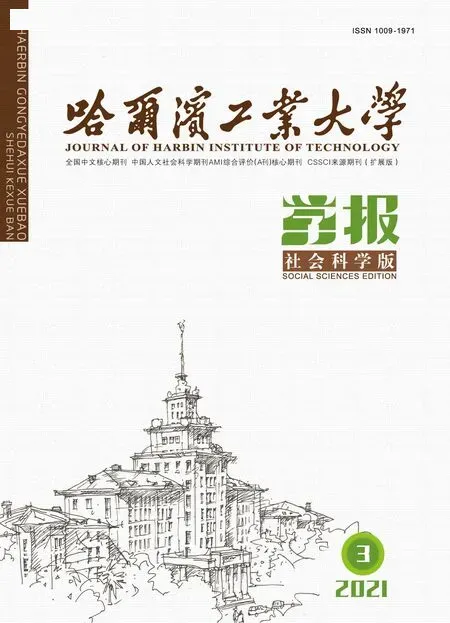风险情境中的情感涌现和生活流变
薛亚利,王雅林
(1.上海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上海200020;2.哈尔滨工程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哈尔滨150001)
在一个巨型风险事件中,身临其境的我们情感到底是如何体验的?我们的情感会有何不同和变化?与此同时,经历风险的我们生活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这些都是风险情境之中异常活跃的情感思想和行为活动,本文就尝试揭示情感现象和生活流变的突兀发生及其多元样态。
一、风险的情境特征
所谓情境构成了特定时空环境和具体背景,它对其中的人们情感、意识与行为方式的变化,有直接的刺激作用,而突发大型风险则构成一种特殊情境,它所产生的刺激乃是强度更高且范围更广的大型冲击。从作为参与主体的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大冲击效应,会唤醒多种情感。为了辨析这些情感,我们需要理解风险的情境特征及其具有强制性的影响力。
(一)身份即时赋予
风险情境不同于日常环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带有“身份即时赋予”能力。一个突发的大规模风险事件以一种不易觉察的方式,更以“身份即时赋予”的强制方式,把“风险经历者”的身份叠加在我们原有的身份之上,以身份之间的差异甚至冲突来警示我们身处风险之中,从而形成形塑力量,为生活流变埋下伏笔。
“风险经历者”就是风险情境下诞生的首要身份。如今出行,每个人都伴随着一个健康码,这个健康码就成为这个“风险经历者”身份的可见表征,这种身份的诞生和来临是突兀的,初始接触时我们是毫无准备和缺乏经验的,当初引发的各种情绪反应,如惊讶、好奇、焦虑、恐惧、愤怒等已被遗忘,我们现在对健康码习以为常并操作熟练。其实,在“风险经历者”身份之下,还有更细致的身份划分,可进一步划分为“受难者”“接触者”“预警者”和“肇事者”等,只不过这些身份都隐含在“风险经历者”这一首要先赋身份中需审慎辨析,正如“健康码”会随情境的危险等级发生绿、黄和红的色变一样,这些身份也会因距风险源远近发生变化。无论是哪种身份,风险经历者的身份与我们原有的身份系统进行交错拟合,然而这一过程并不能自动自洽。
(二)身份排序变化
风险情境中人的身份赋予,不仅表现为新增身份的叠加,还表现为身份之间的排序调整。“风险经历者”身份借助风险情境潜入日常生活之中,这种危险情境中的身份赋予,是新生身份叠加在已有身份基础之上,这种双重或多重身份现象,进一步引发了多重身份之间的排序变化,甚至导致排序倒置。一个风险事件发生,本质上是与日常生活的叠加、交汇和融合的过程,它以危害和干扰的面目侵入日常生活,打破了它的主流状态甚至将其下沉为底层潜流,让其行进状态发生变形。正如2020年疫情防控初期的封城措施,暂时的社会停摆直接导致日常生活及相关既定身份的排序变化,大众化的居家隔离防疫,显然让正式身份和非正式身份的关系发生倒置,正式组织机构暂停转让正式职业身份,正式职业身份突遭削弱,而深居幕后的私人非正式身份被不断强化,教育体系暂停和学生居家网络上课,无疑让家长监护人成为被时刻检验的身份存在。其实,表面看起来家庭成员身份在身份序列上不断前移,只是反映了风险情境中身份平衡被打破势必带来的一个现象,即必然出现某些身份重要性的降低而某些身份重要性的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身份调整可能引发新的身份冲突,因非正式身份突然负载不堪负重的消极后果,如亲子冲突悲剧和婚姻解体现象的一时增多,无疑说明了这种家庭照顾者的身份被突然过度强化会超越社会成员的承受能力。由此来说,风险情境中风险身份赋予隐含的身份系统张力及冲突问题,不仅仅是个体应对问题,还是社会干预问题。
二、风险情境中的情感涌现
风险经历者,风险情境之下的身份即时赋予,作为一种隐性存在,与现实身份之间构成一种张力甚至冲突。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情感唤起和情感涌现的现象。
情感唤起,其前提是现实情境和心理预期的不一致或悬殊落差,在常态社会中这两者之间维持相对一致或稳定的平衡关系,但在突发风险情境中,这种现实和预期的差距骤然出现,此时缺乏充足的理性思考和沉淀过程,因此,大型风险情境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超出心理预期的客观存在,这会引发出不同的情感反应,如恐慌,忌惮于疫情形势的严峻可怕;如愤怒,因对疫情防控措施偏差的不满意;如轻视,则对疫情形势乃常态化的误判。无论哪种,它都代表了疫情唤起了不同的情感反应。
(一)情感论说
在理解一般的情感现象上,最为实用且为人所熟知的有四种典型。关于情感研究有诸多理论解说,如最概化的两种论说是情感的有机模式(代表人物如达尔文、威廉·詹姆斯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情感的互动模式(代表人物如约翰·杜威、汉斯·格斯和C.赖特·米尔斯、欧文·戈夫曼)等[1]248-266。但是,由于情感的抽象性,反倒是更为通俗和更易理解的四种论说最常见,即情感的“信号论”“工具论”“压迫论”和“反思论”。
1.一般情感的四论说
情感的这四种论说具有内在的亲和或排斥关系。相比较而言,“信号论”和“工具论”具有相似性,因两者更关注情感的积极意义,而“压抑论”和“反思论”具有相似性,因两者更关注情感的消极作用。
“信号论”,常见于心理学领域,往往偏重于个体视角分析,关注个体在环境中的调适表现,它认为情感能促进个体认知及促发后续行为,它更关注情感对即时信息的迅速捕捉、快速反应和不受控制,如面对突发危险时拔腿就跑,听闻好消息后的手舞足蹈。“工具论”则常见于社会学领域,它偏重于群体维度分析,关注群体关系的凝聚和维持。涂尔干认为,周期性仪式所激发的集体感情,还会延续到仪式之外,起着社会团结的作用,那些用于激发和维持这种情感的符号如图腾会被保留下来甚至神圣化,情感是群体关系凝聚的一种周期性能量[2]286。这成为情感研究的一大传统,被后来的情感研究所继承,如特纳认为感情是创建和维持社会关系,及对较大社会规模的社会文化结构形式承诺的关键力量[3]142。由此来看,“信号论”和“工具论”皆关注情感的积极作用,它们被重视和强调乃是为了其能发挥建设作用。
“压抑论”被视为“工具论”的对立性解释。“压抑论”认为,现代社会中情感已无法正常释放,因为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压制及资本主义的强势理性霸权最终导致情感的受控和压抑。这种情感压抑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整体性的压抑,如韦伯理性化去魅社会进程,导致宗教信仰中的神圣和崇敬感情地位被工具理性所强势取代[4]137-139;另一类则是商业化的情感劳动或情感剥削,某类特质的情感,如温和亲切,会被作为一种典型或标准化的劳动形式,被严格规训用于经济效益的获得,这种情感利用,损害劳动者的健康,致使他们情感压抑和自我观念受损[1]165-170。情感的“反思论”认为,现实中情感状态的呈现类型取决于具体情境,不确定的情境比静态情境更能激发情感,情感的本质特征可发生改变,情感能发挥其反思作用。在情感和反思性关系上,米尔斯和克莱恩曼提出一个类型学。他们认为它有四种存在状态,即“无反思情感”“有反思的情感”“纯粹反思”和“反思和情感皆无”。人的情感状态到底是何种类型则要取决于具体情境,正如“麻木不仁是压抑环境的合理反应”[5]。无论如何,正是通过情感认同、情感展示和情感体验等多种形式,情感可以从其作为个体的属性恢复到社会互动属性之上[6]。
2.风险情境中的情感缺乏论
关于情感的各种论说已相当丰富,远不止以上这四种。如诺尔曼曾总结已有情感论说,具体如认知理论、认知情感理论、心理分析理论、交互作用—心理分析理论、社会结构理论、结构—交互与固结理论、符号交互作用理论、结构心理学理论、交叉文化和非文字理论、情感—动机理论等[7]6。
遗憾的是,大型风险危机形成的非常态情境中的情感却较少被研究。所谓的非常态情境下的情感,在我们所熟知的典型类型中,莫过于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对其研究会关注受害者经历风险活动后的情感状态。不过,这种研究焦点多放在受害者的诊治方案及人际关系修复上,因此受害者是否发生器质性病变的药物干预,以及人际关系恢复程度多是研究重点,而不会把风险本身及风险中的情感体验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更为局限的是,这种研究的关注对象多是个体,由于这种病症多来自个体的特殊经历如车祸等,研究难以上升到对整个社会情感状态的考察上。
大型风险中的情感研究往往需要时机,尽管情感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但少有机会研究风险情境中的情感,这是因为二战之后尚未遭遇全球规模的风险危机,又由于风险危机总是暂时性和过渡性的,而情感看似捉摸不定甚至是转瞬即逝的,即使与风险相关的各种议题纷起,情感现象总被附载其他议题中较少被持续关注。情感对人本身和社会本身极其重要,因为情感不但创建和维持社会关系,而且是大规模社会结构承诺的支持力量[3]142。我们需要审视风险之中的情感现象,因为情感是带有行动倾向的,面对一场大型风险,人们总是期待尽快恢复社会常态,那么,这就意味着情感可以为风险后的社会恢复和重建提供启示方向。
(二)情感涌现
结合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试图来理解风险情境之下的情感现象。围绕着情感关注的高度注意,它有三个典型表现:沟通作用的情感符号现象,多类型情感一并涌现的现象,情感极化现象。
1.情感符号
在风险情境中诞生的情感符号,发挥着有效的认知沟通作用。在中国抗疫行动中出现了一种明晰的情感符号,它呈现出脉络性的演变特征。风险疫情暴发之初,各种身着白色防护服的医务人员形象符号可谓是应运而生,从诞生之初就持续存在,成为解读疫情进程的特殊符号,其中医务人员的面部表情则成为解读疫情形势的核心密码,如疫情暴发时广为流传的一张医生自拍照,这是一张面部特写照,神情严肃,医生的面庞被口罩勒出两道血色深痕,这透视了医务工作者的超常工作强度,也传递了抗疫形势危急的信息。就情感符号而言,人的形体、人的身态、人的动作、人的手势、人的面部表情等,皆是表达情感和传递信息的符号,但相比较而言,人的感情更容易通过面部表情识别,即使可以借助其他方式手段如身体或声音来表达,但面部表情却是人类情感最重要的表达方式[3]13。我们可以看到最醒目的感情符号总是结合具体人的面部表情,因此,就不难理解在疫情暴发初期,疫情形势正处于最险峻时刻,全身防护的抗疫工作者,通过一双传神眼睛——严肃且疲惫,透露出当前疫情形势尚处于不确定、不可控和不容放松的时刻,它也要求我们要有坚忍的情感态度。
随着防疫形势好转,我们看到了对应性的情感符号变化,医务人员的面部表情有了更丰富的表达。当疫情被认为是可防可控时,我们看到了医务人员略有放松的神情。当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就,全国各地疫情得以有效控制,这可以从医务人员的积极表情如微笑上得到印证。有些医务人员会摘掉口罩,面部表情自然甚至略带喜意,这种表情符号传递出疫情的整体可控,而那些病人向救治医护人员道谢的温馨,以及援助医务工作者撤离武汉时受到当地民众夹道欢送的感动,都在印证着一场防疫战斗的阶段性告捷。因此,医务工作者的情感状态代表着人们对风险认知的微妙转变,疫情性质转变背后乃是防疫工程的系统支持,如防疫策略的有效调整、医疗物资的八方援助、医护人员的各地纷至等,这些都是医护工作者的稳定工作模式以情感表达的外在系统支持。因此,医务人员的情感状态从惊慌应对到从容面对,展现了宏观抗疫工作从混乱失序到重整有序。情感符号是在风险情境中诞生的新型集体符号,它作为符号取自疫情风险中的代表性群体——医务人员的形象,通过他们的情感状态和行为特征来传递疫情冲击之下的社会秩序恢复和重建过程。情感符号从诞生就有整体性,承担着表达整体性社会事实的基本作用。
2.多类型情感反应
在不确定性的风险面前,情感反应除了产生凸显的情感符号之外,还有多种多样的情感镜像。风险突如其来,会让社会以一种突兀的面目呈现,这会引发多种情感反应,在混乱无序的暂时性过渡阶段中,多样化的情感反应自动涌现,由风险的各种不确定性引发的焦虑不安和将信将疑,有着更加细致化的类型呈现,具体有焦虑、不满、团结、好奇和反思等。
(1)焦虑恐慌
新冠肺炎疫情一暴发,其社会危害性就引发了群体性的焦虑和恐慌情绪[8]。风险情境中的焦虑感受具有普遍性,而且离风险越近这种焦虑感越明显。对自身安全的过度担忧及对病毒危害的过高估计,是风险情境中的特定情感反应[9]。对于靠近风险中心者来说,他们会首先受到冲击因而焦虑感最明显。疫情早期,湖北省一半居民有中度恐惧心理,超过一成的居民有高度恐惧。2020年2月10—12日,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在湖北省抽取1157名居民进行心理健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1.51%的居民有中度恐惧心理,13.74%的居民有高度恐惧心理[10]660。有些城市的调查显示:有超过2/3的被调查者担心被病毒感染,约1/3的人认为病毒感染死亡率较高。有93.8%的被调查者受疫情的影响,其中67.1%的人担心会被病毒感染[11]。
相比较而言,处于风险风暴中心的人,其情感消极程度远超过远处的外围人群。最新全国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群焦虑患病率为7.6%[12],疫情期间湖北省有16.51%的居民有焦虑症状[7]6,其焦虑状态和抑郁状态明显超全国水平两倍多,当时武汉和昆明省会城市的被调查者的焦虑和抑郁状态接近1/3。这种心理恐慌的情绪可谓达到了应激水平,适度刺激能增强体质和提高适应能力,但过量刺激则对身体有害及导致心身疾病,遭受重大创伤的高危人群其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发病率为3%~58%,心理问题的比例远高于一般人群[13]。其实,不只是身处风险中心的人会有消极情感,那些疫情中心之外的人群,也存在普遍性相似但程度不同的情感反应。尽管防疫的最有效办法是物理空间上的隔离,但在长时间的普遍居家隔离中,人们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焦虑感和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焦虑紧张等[14]。正是这种焦虑恐慌情感,内在地促动人们自身及社会对疫情防控的快速应对和不断调适。
(2)歧视排斥
此次疫情之中还存在一种令人关注的消极社会情感,即歧视和排斥。公共卫生风险中传染性风险引发歧视和排斥问题由来已久,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也是如此。湖北武汉是国内最先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地方,坊间出现了针对武汉乃至湖北人猜测甚至怀疑,曾有诗作公开使用针对湖北人的歧视字眼,典型案例莫过于云南彝良县文联主席陈衍强。作为中国作协会员,陈衍强在疫情期间撰诗《仰望天空》传播于网络上,诗文中用词“湖北佬”和“九头鸟”指代和歧视湖北人,被批评缺乏同情心和人文关怀[15]。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歧视情感还蔓延到社会流动和劳动用工上。如武汉解禁后湖北籍车辆被禁止进入其他省市,不少企业半公开地排斥湖北劳动者。在心理层面,湖北尤其是武汉人会被视为一种风险源,这种歧视和排斥造成该地方人的情感压力和负担。在对湖北千人的调查中,发现超过1/3的被访者“对遭受歧视”有中等程度的担忧,约1/4的被访者有重度担忧[10]658。这种歧视和排斥需由正式组织及行动干预才能消除,无疑说明这种情感态度的严重性。2020年5月中旬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倡导用人单位不得歧视湖北及武汉外出务工人员,要一视同仁[16]。与此同时,武汉开展了约两周的全员式全覆盖的病毒感染筛查,筛查人群超过九百万,查验结果并未发现确诊患者,无症状感染者检出率极低,仅为万分位的超低比例,且未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传染他人的情况:从5月14日0时至6月1日24时,武汉核酸检测已实现“全覆盖”,除6岁以下儿童,共计9 899 828人接受集中核酸检测,发现确诊患者为零,5月31日起,新增无症状感染者为零,无症状感染者检出率仅为0.303/万[17]。这说明,对于武汉和湖北人的传染威胁歧视,既无事实基础也无科学依据。这也暗示了风险情境中歧视情感的消除,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协同干预。
(3)情感团结
在大型风险危机中受风险冲击而乍现的情感鼓励具有积极性和开放性。在中国这次疫情中,有一句流行口号“武汉,加油!”它见诸各种场合且被广泛传播,这反映了群体内部或群体之间的情感支持。这句抗疫口号,情感表达简洁有力,它以城市名称指代当地居民,兼做宾语和主语,让其既是情感鼓励的突出主体也是客体对象,借助灵活语法,从而传递多层次的积极情感,如同情、理解、承认及期待等。“加油”,作为一种最直白的情感鼓励,尽管带有旁观者的情感特点,但它的情感支持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在一场巨型疫情危机之中,湖北武汉被迫封城,当医疗资源不足和物资筹备不够时,风险前沿的市民群体要首先经受冲击考验,这会引发他们的克制、忍受、悲伤甚至怨恨等情感,这些情感反应中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无论哪种情感状态都需要被承认和包容。在风险前端的受冲击者是一个广泛的社会群体,不仅包括忙碌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还包括进行疫情防控的政府工作者,还有宅在家中的普通市民,无论哪类群体都应被理解和尊重,因此在情感加油的模糊指认和鼓励意愿中,在者皆受之无人被遗忘。
情感团结所召唤的情感支持在跨群体间广为流传,具有抵制歧视排斥的作用。针对网上流传的歧视湖北的那篇诗作,其作者陈衍强及作品立即受到同行反对,而且对其批评从个人举动转变为集体行动:先是原云南省作协副主席、湖北籍作家汤世杰在其个人微博上发文《声明》,指出陈衍强公然拿同胞的灾难恶意调侃,该批文很快被文学圈人士在网络上转发,随后来自湖南、湖北、青海、山东、河南、河北等省份的作家联名写信,公开《联名建议中国作协尽快撤销陈衍强会员资格的公开信》,要求撤销陈衍强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格及给予其必要惩处。在舆论声势之下,歧视诗的作者陈衍强,公开发文致歉并主动辞去彝良县文联主席和昭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18]。大型风险是群体性的集体苦难,它只能在社会成员之间心怀悲悯和满怀善意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到齐心协力。那些极端的排斥和歧视言行因违背当下的迫切需求、因大难当头显然难容。
(4)好奇探究
在风险情境中人们还试图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风险事发突然,风险打破常规停顿惯例,风险引发的改变促发情感上的惊讶、错愕和好奇,这其中最为动力性的情感则是好奇,它在试图理解当下到底是什么状态。在风险情境中,人们很容易被激发出好奇情感,它由知识上的不确定性、认知缺口所引发[19],当个体的知识库存与想要获得的知识信息存在差距,而个体对此有所意识时就会产生好奇情感和探索意愿,以弥补信息缺口[20][21]诱发的不确定感。疫情防控时,全国范围内各地各级政府在探索积极措施时,普通人同样为此忙碌,他们花大量时间来了解疫情。针对湖北某些城市的调查中,发现有超半数的被调查者每天花大量时间关注疫情相关信息,不过其中正负信息皆有,如有2/5者(40.2%)每日接受疫情信息中超半数(50%)是负面的;1/4者(25.16%)认为接受疫情信息为不实信息,如谣言、断章取义或歪解等[10]658。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早期个体被各种信息包围以至对疫情认识不够科学。疫情后期个体认识提升,受众对病毒防护知识及死亡率的认识相对客观。可见,好奇情感在驱使人们认识走向客观的过程中发挥促进作用。
风险期间的好奇情感,并不仅限于探索风险本身,还有更具超越性的认知。情境特殊催生反思,当一个流动的世界被割裂、被禁止,包括学校、博物馆、餐饮和娱乐场所,体育场馆大面积和长时间被关闭,人类不得不接受“封国”“封城”“封航”和“蛰居”的现实,这将急速改变以往通过聚集和直接交流的生活方式[22]26,特别是当复工复产为固定场所所困时,通勤为外界地理隔离环境所限时,好奇和尝试带来的技术探索和创新,无疑同步成为社会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如各种居家办公、网预约、云会议和线上会面等,从疫情之前的偶尔为之变成惯常行为。
(5)情感反思
在此次疫情中,一直都存在批判的声音,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批判的方式和批判对象都是情感性的。中国疫情暴发并很快得以有效控制,然而全球范围内疫情却快速蔓延,对于疫情风险的这种不确定性及严重态势,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府及民众并没有充分认识,针对这种疫情风险危机形势与对其浅显认识上的落差现象,被批评为人类情感态度问题所致,正是因为人类自身的傲慢无知、肤浅轻蔑、自私自利和缺乏担当等,才会导致对疫情危机认识的迟缓和滞后。因此,疫情危机警醒当下人们应该回归尊重自然、宽容诚恳、包容团结等。目前,这种关于情感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它视疫情危机是一面镜子,它引发对人类情感傲慢及常规认知偏差的反思,而这种反思评判继而被深挖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弊端及文明视野的盲区上。
3.情感极化
在一场大型风险的形势不断演化且充满不确定性时,对风险的群体性高度注意中,也会随着时间推进及正负情感的积累,自动演化出情感的极化现象。
人类情感不但类型各异,而且强度不同且能动态演化。人类的每类情感都具有高中低三种强度。特纳将情感分为四种维度和三种强度:四个维度是满意—高兴(satisfaction-happiness)、厌恶—恐惧(aversion-fear)、强硬—愤怒(assertion-anger)和失望—悲伤(disappointment-sadness);三种强度则是高、中和低[3]13;而且,不同种类的情感之间还存在进阶关系。特纳在总结前人的情感研究时,特意提到了普拉契克和肯珀的情感模型,后两者的情感类型划分带有演化关系,前者将情感分为基本、次级和三级,后者将情感分为基本情感、基本情感上的依附情感、基本情感的组合形式[3]10-17。情感间的进阶关系,预示其会在某些情境之中发生强化趋势。如涂尔干研究的仪式中的群体情感会有非常规的激情如癫狂[2]285-294,勒庞在突发事件中发现了群体情感的某些特征,如受无意识驱动的群体情感具有易传染和受暗示会强烈得如同暴风骤雨难以控制,从而理性人变成了“乌合之众”。群体的人际聚合及视觉感知造成的心理壮大感受效应,会让情感状态昂奋却不稳定[23]15-43。
风险中的情感极化现象,表现为消极情感和积极情感的各自强化和趋向对立。在风险暴发之后,多种情感涌现也是变动不居的过程,它会据情感性质的积极和消极进行自动聚拢强化。人类的基本情感中天生具有积极和消极这两种对立的情感,值得注意的是,消极情感在基本情感中占比更多,正如“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在四大情感分类中,有满意—高兴、厌恶—恐惧、强硬—愤怒和失望—悲伤[3]13,积极情感仅为一类。即使积极情感占比不高,但也能韧性存在。对湖北千人调查发现,尽管有超过一半和一成多的居民分别有中度和高度恐惧,同时,也有超过两成和接近3/4的居民对战胜疫情有中度和高度信心[10]658。这种积极和消极情感的对立性存在,会在风险情境中各自强化,继而引发对立性的互动,典型如情感的撕裂现象,疫情议题如疫情日记或其他记录等中的情感倾向成为大众关注和争议的焦点。人们既看到如失望、悲伤、不满和愤怒等消极情感的竭力申诉,也看到对如感动、鼓励、感恩和团结等积极情感的强势动员,疫情中的情感极化对峙成为社会成员之间相互确认群体边界的重要依据。
论及风险情境中突现的情感符号、涌现多类情感和情感的极化,作为风险社会中人类情感世界的真实写照,也未能详列全部。人类的情感世界极其丰富,除了基本情感及其变化形式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情感,如羞愧、内疚、好奇、怀恨等情感[3]13。关怀人类自身情况,尤其要关注情感的积极与消极对立,乃是包含着对消极情感的警惕,如果消极情感持续时间越长强度越大且未被承认,就会致使人们参与社会水平的攻击运动,对平稳社会形成干扰[3]142。
三、生活流变情势分析
风险情境中伴随着人们情感上的变化,是同步发生的生活流变。生活是由个体所承载的人的特有生命形态的社会性存在、展开、实现形式及意义追寻的行动体系,对其我们可以从人的生命认知、价值观念、社会性包容三个向度加以考量[24]7。但由于风险情境造成的冲击并不足以构成整体性的颠覆,它以细小、微量、局部但重要甚至关键性的变化,在生活的不同层面上展现出来,如从认知观念上的偏差纠错,到深层狭隘价值观的包容性修正,再到群体层面上的生活共同体的开放性增强等。
(一)科学认知的纠错
风险情境提供了一种检验机会,用于检验那些流行于日常生活中的科学认识和观念。以动物为宿主的病毒对人类没有直接伤害,这作为一种科学定论已流行很久,然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却推翻了这种观念,它以大规模伤害后果证实这种所谓的科学定论的错误。与此错误的科学定论相伴的还有更深的错误观念,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原本被认为是病毒入侵了人类社会,但从漫长的演化史来看,这种认识不过是人类的傲慢和臆断。它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在人类形成与进化的过程中,病毒所具有的终极性微观地位早已形成,在生命的本源探讨上,植物、动物和人的灵魂有贯通之处,三大生物体系只是有着不同的生命表现形式[25]。因此,必须修正狭隘的科学认知,即并不是病毒入侵人类,而是人类“嵌入”已存在的病毒和微生物等自然系统中。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以其情感震慑提醒我们,病毒系统已经构成现实经济的真实微观基础。这也警示我们,我们正确地从更为长远和整体的视角去认识病毒,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人类生存环境的演变[22]18。
风险情境中的新情况继续考验和挑战着现有科学认知能力。新冠病毒Convid-19的演变和传播能力考验着当下的科学认识水平,譬如2020年6月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的疫情调查结果显示,该新冠病毒经检测为L基因型欧洲家系分支Ⅰ,该毒株比此前欧洲流行的同型毒株更“老”,而且该病毒既不是此前北京本地传播毒株,也不是武汉流行毒株。疫情在新发地批发市场的传染模式,主要为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传播,还有或经物品表面污染的间接接触传播[26]。在国内疫情防控局面较好的情况下,2020年10月新疆2天突发164例无症状感染者,人们从地缘关系推测它与中亚东欧国家毒株的疑似;而11月份内蒙古满洲里市病例的新冠病毒属于L基因型欧洲家系分支,与俄罗斯流行株高度同源[27];11月上海浦东机场工作人员2例确诊病例,都曾在未佩戴口罩时清理过北美地区返沪的航空集装器,经基因测序2例病例基因高度同源且与北美流行毒株高度相似[28]。到目前为止,尽管我们知道新冠肺炎病毒传播对环境封闭和温度敏感,尽管已有多种疫苗投入生产和应用,但对病毒变异能力及传播路径我们尚无有效的根治办法。
(二)价值观的包容性修正
疫情病毒作为一种看不见的破坏力量乍现,也突显了现有的科学认知的被动和傲慢,这就暴露了人们对科学理性的盲目自负,这也敦促人们认真反思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的负面作用,需要重新回归价值理性与社会理性。在疫情风险情境之中,关于风险议题的价值观辨析和修正议题慢慢凸显出来,一方面我们开始警惕那些让风险扩大的傲慢价值观,另一方面我们开始重申有利于化解风险的文化价值。有学者明确指出关于风险文化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它基于西方现代社会发展及其文化脉络,缺乏非西方经验的总结,西方文化传统强调“人对物”的征服和开发的对立文化,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传统不是西方的对抗文化,注重“人对人”关系的德行文化和和谐文化[29]。面对风险,中国应有基于自身文化价值的文明建构。
在抗击疫情风险之中,积极包容性的价值观起到有效的支持作用。家国情怀作为一种包容性更大的群体情感凝聚力量,是民众接受和形成新型防疫生活方式的纽带工具,这其中关于生命价值的积极导向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和不畏艰难等,从源远流长的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刑天舞干戚等传统故事中游离出来,在风险情境中重组为一种活生生的情感支撑力量,在抗击疫情的现实困境中起着精神补给和支撑作用[30]。因此,在疫情风险中,我们应重新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助于群体团结的德性价值和和谐价值,内外兼修地提升应对现代风险的能力。
(三)生活共同体的开放性增强
广泛的社会参与是生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24]9,风险情境中群体层面出现了这种进步的面向。由于人群密度的差异,城市疫情比农村严重,而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城市社区的社会参与达到了前所未有之广度和深度,出现了所谓的“超级网络”现象[31]。一直以来,城市社区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内在张力,基于国家政策和知识精英所倡导的秩序性社区,它追求一致化和理想化的目标,与居民日常生活意义上的体验性社区存在差距甚至冲突,后者追求个性化和地方性目标。但是,疫情风险却让这两者目标接近且达成多种合作关系,如疫情风险中,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大量下沉到街居成为抗疫的“主网”力量,而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物业公司等参与互动则成为抗疫的“辅网”力量,社区在抗疫行动中出现了多方治理主体群策群力的局面,合力维持社区安全感和归属感。疫情风险中社区衍生恐慌气氛,作为生活共同体的社区面临健康威胁,而其中的弱势群体则可能面临生存危机,社区管理与社会组织联动,把社会工作和心理咨询等专业化的服务融入抗疫行动中,有助于缓解社区居民的恐慌情绪。值得注意的是,社区抗疫让驻区单位也参与进来,这种潜在资源的再组织利用和整合,直接补给和扩充了社区的抗疫力量。由此可见,国家目标建设的社区与每个居民情感体验中的社区在风险情境中融合起来,疫情风险突出和强化了群体共同体的深层团结,这与社区内在发展的本质性需求是暗合关系,这种团结直接提升社区抗击风险的韧性和抗逆力,系统性地增强了社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结 语
一场大型风险危机会自动展现它独有的历史维度,会衍生出一种纵向认知感,让连续的时间发生断裂,从而让风险前后的社会事实相应地分时段呈现,正如流行的“后疫情时代”说法,乃是它默认了疫情风险对时代的分水岭效应,这种风险分段是外在客观环境的强行改变形成一种外在冲击力量,它会带来改变。
风险情境冲击带来的一大悄然改变,就是情感涌现现象。何以要关注风险情境中的情感现象,是因为它有型塑社会的作用。“人类情感是身体和社会的语言”[3]217,它的变化可以反映社会的变化。一些情感表达的出现及流行意味着社会情感的某些共同性形成,如“很嗨”“不爽”和“找不到北”等描述精神状态的新型说法,最早来自20世纪60年代的毒品文化,后来却被广大的中产阶层所采纳,它说明了群体之间的相似性,关注释放压力的中产阶层与亚文化群体之间有着情感上的共鸣[1]217。“情感具有感染性,因为情感能够唤醒他人情感及同样的或交互的情感,从而增强社会联结关系。”[3]216正如怜悯情感,它随着基督教的援助系统得以在社会上广泛推开,更为重要的是,施助者群体和受助者群体如寡妇、孤儿和老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社会纽带,“实际上,情感是人类智慧的基础,因为情感使文化以及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成为可能”[1]217。
风险情境,即使是特殊的,也是建立在常态社会和既定生活基础之上,它与后两者保持着贯通关系,但风险危机会挑战常态社会及日常生活,最典型的乃是风险会搅动某些既定安排和想当然之处,并让重新调整成为被接受的,这种暂时的合理化也为长久合理化提供契机,即出现风险情境催生的一系列“合理化”现象,正是这一细微的改变现象,撬动了惯性常态社会及生活方式的改变之道,在诞生一些美好生活方式的期盼中思想逐步解放。疫情风险发生在中国的新时代发展的转折期,由它应激而生的生活流变正好与当前我们追求更美好生活[32]的集体愿望恰巧汇合,这为让每个个体能生活美好的社会实践注入了新型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