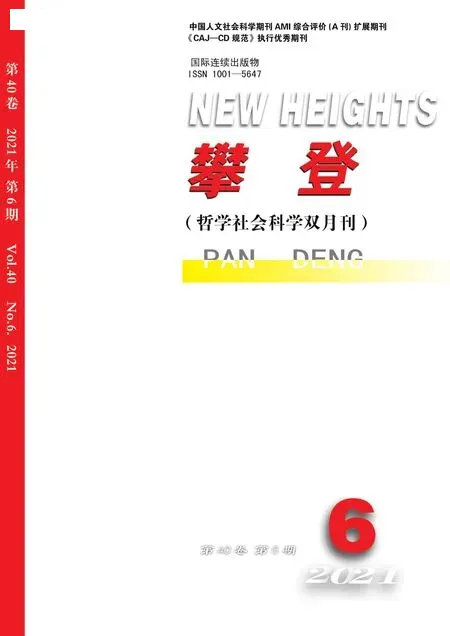再论毛泽东关于权利与制度的思想
王甄玺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如果说西方政治哲学“古今之争”由追求“至善”的“高贵谎言”让渡为“知性真诚”的公共权利与政制设计,[1]那么,中国人民民族解放的政治哲学则由理论上的守卫“旧体与传统伦理”让位为吸纳“异质性与改造”,毛泽东政治哲学关于权利与制度思想的构建则是改造“异质性学说”的理论典范。即使当代西方左翼沉醉于政治和身份之争,但只要资本主义作为历史时代的基因尚存,追求解放、独立、民主、和平友好、人类进步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事业便永不会止步。诚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人类解放不会从天而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既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新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征程的新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程证明,毛泽东对公共权利与社会制度理论的建构有着极为科学和系统的判断,他提出的“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三条基本外交方针、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等政治实践的实现,既有指导着中华民族政治解放的远见,又兼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指向。可以说,毛泽东的权利与制度理论不仅回答了在中国如何完成政治解放的问题,更科学地回答了如何实现“人类解放”的长远理想。
一、从西方人权走向人民权利的实践
在西方政治哲学中,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口号“裹挟”着大量非自觉主体的“泥沙”默化于“时局图”时代的中国,各派阶层的知识分子尝试西方式权利与制度的政治哲学设计,在每一次的政治行动中携有大量的“过敏”症状与不适警醒着中国各派人士必须选择马克思主义。高举自由、民主的改良派激进地要求“消化”所有西方人权与政体,并以“猛药”警醒“麻木的中国”。反对“猛药”的保守派则坚守传统“孔孟之道”下的民本权利与旧体制,甚至翘首以望“均田免赋”的大同世界,在喜剧与悲剧夹杂的变革景观中,二者纷纷倒在了革命的“血泊之中”,这不仅无法为行动主体作出正确的指导,反而背道而驰地成为恶化主体性的力量。在中国近代以来各式的“变革与守旧”冲突中,如何解决权利与制度的关系无疑是每次政治行动的焦点。而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唯有毛泽东思想站在了中国政治解放的高光灯塔中,指导中华人民争取实质性的公共权利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早已批判了西方资产阶级构筑的法权虚伪景象,自由、平等、民主等权利不过是附属于财产所有权,并以各式法典加以明确。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毛泽东所指向的是“人民的权利”而非西方式“人权”。部分学者认为,毛泽东所指的权利思想与制度建构,其理论不过是苏俄模式的照搬套用,这一观点实为荒谬。毛泽东的权利与制度思想并非无法证伪的宗教路子,对其中蕴含的政治哲学需要在历史逻辑和革命实践的具体工作中进行解析。
首先,在于传统性。从《尚书》《孟子》乃至清初王夫之等人均有丰富的民本思想论述,“安民利民”“民贵君轻”“以百姓心为心”等思想无不具有传统文化人文关怀属性。毛泽东权利与制度思想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从东山学堂至长沙高师乃至在北京大学学习,在袁仲谦与杨昌济等传统知识分子的熏陶下,毛泽东所萌发的公共权利与社会制度思想无疑厚植于传统理论规范。譬如:“群众路线”“一心为公”“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等政治理念就源于中国传统文化。
其次,在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公共权力的实现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仅滞于观念是无法完成的。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时,他还未转化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提倡“无血革命”。“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2]“认为无政府主义的温和主张比马克思的激烈主张更科学和深远。”[3]事实上,“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或是期冀“不消灭哲学本身,就可以使哲学变成现实”的怪语,或是仅以和平手段就可让封建官僚主义、资产阶级、西方买办臣服于“人类解放”事业的思想,是永远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权利的虚伪与封建专制对人民的压迫“囚笼”。只有无产阶级坚持“武器的批判”才有观念的物质载体,才能完成自身的解放任务。无政府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失效后,毛泽东认识到“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需要开辟新的道路。“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4]。要改造旧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政治解放、行使公共权利、健全社会制度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
最后,在于中国社会现实性。在旧时代,解决老百姓吃饭穿衣的生存权与摆脱外来压迫,建立独立的国家社会制度是最为首要的。旧压迫体系不消除便无法实现最基本的权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任何拒绝民族解放、政治解放或者召唤“旧体制”的政治行为均要被客观的历史规律所否定。在这一历史运动中,抵御外敌、扳倒“三座大山”、保障人民生产与生活的权利与制度问题被上升为首要任务。“怎么办?”成为毛泽东权利与制度思想切入中国社会现实性的入口。“政治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行为,成为具有公共权利与社会规范的价值诉求,需要民族、民众的联合与自我牺牲,需要依靠“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组成“镰与锤”敲碎“链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5]正如毛泽东所说:“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6]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中国,各种矛盾交织复杂,需要“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7],革命的高潮终将不可避免。
以上三点思想的“历史叠合”促成了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式抽象的公共权利的鄙夷,认清了西方资产阶级式权利学说的本质,为毛泽东将资产阶级式人权及资本主义制度范式转换为“人民的权利”与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毛泽东权利与制度思想的语境中,只有符合社会现实性的革命实践才能实现公共权利与变革社会制度,实事求是地回答了理论有效性与否。与其说毛泽东权利与制度思想是指导实践的“天才般”创建,不如说革命者是以革命探索的方式,由经验上升到理论并具有现实性的发展成果。僵化而教条式的近代异质性理论及革命中的本本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水土不服”,甚至成为了阻碍中国民族进行政治解放的绊脚石,原因就在于脱离实际,异化为历史和人民的对立面。
不可否认,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德赛二先生”与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民主革命纲领振奋人心,对依然故步自封的守旧派是“一剂猛药”。但是,其理论终究在完成自身使命的节点上无法实现最终的解放任务。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卢梭已经反思着“布尔乔亚”式的政治解放所支持的畸形式公共权利与社会制度,富有激情的法国大革命迎来的却是雅各宾派专政和拿破仑荒谬般复辟。实质上,平等、自由、民主等公共权利与公正的社会制度依然败在了以《法国民法典》所推崇的财产所有权上。当真正的公共权利也已异化为资产阶级法权,人类所探求的解放愿景只能是法制式“强迫”,从霍布斯、卢梭乃至萨维尼以理性所“设计”的“契约论”“公意”和“民族精神”,呈现的依然是不彻底的政治改造。对中国而言,唯有不断地探索新民主主义主义革命的政治解放、社会主义建设的人类解放,才能真正实现人民权利。
二、毛泽东关于权利与制度思想的实质建构
毛泽东关于公共权利与社会制度思想的建构面临着尖锐而复杂的压迫环境,既有由自由竞争脱胎为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阶级双重压迫,又有新兴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联合。当马克思从对市民社会的一般批判转向试图由西欧已完成的“政治解放”尝试进行“人类解放”,寻找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切入点时,列宁则以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双重路线来实践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是将二者理论与实践的普遍性纳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加以具体化和现实化。在中国进行权利与制度的改造中,一是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批判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滥觞于精英派的幼稚政治解放幻想,提出必须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实现“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8]。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解放的条件下,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保障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并确立了以“政治解放”迈入“人类解放”的长远目标。相比中国近代以来的各式“主义”,或是选择片面、孤立地看待中国革命问题,摒弃革命投降资产阶级,或是选择脱离社会实际,以超现实的政治观点实现直接迈入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关于权利与制度的思想建构不仅坚持以无产阶级革命方式争取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更以具体的现实战略构建了迈向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制度,真正地为实现公共权利指明了方向。
第一,以人民群众为社会革命的主体。当西方资产阶级虚假地宣称权利具有不容置疑的普遍性和其制度的“历史终结”时,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每个人似乎“被赋予了同等的权利,但实际上人们之间并不是平等的。”[9]资产阶级公共权利的背谬性不过是“布尔乔亚”式对旧统治者的模仿。马克思指出,在“一部分的市民社会”政治解放中“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框框里。……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10]资产阶级完成了“半截子”解放,废除等级身份特权的各式资产阶级民法典却以私有财产构筑了实质不平等。[11]当西方政治“药水”以“立宪”“新政”“新约”的形式出现在我国时,孙中山便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12]经历了近代中国革命挫折的毛泽东认识到,无产阶级与农民才是人民群众主体,要赋予人民权利自然不是抽象的资产阶级权利。投降派在革命的进程中误读了我国无产阶级属性,并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13]且农民“私有观念极其严重”“共产的社会革命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14]只有资产阶级才“负着历史的使命”[15]可领导中国革命,无产阶级只是追随者。毛泽东则坚持人民群众是社会革命的动力和主体,将受剥削、受压迫和受穷受苦的老百姓置于权利保障的中心。土地革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新中国识字扫盲运动、推动妇女解放等等都表明了“人民群众有无限创造力”。毛泽东始终努力探索着一条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权利的道路,克服了西方式人权的抽象性与虚伪性。从西方人权到保障人民的权利,毛泽东为“政治解放”转向彻底的“人类解放”理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以中国社会现实作为权利与制度的理论之根。长期以来,无论是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还是齐泽克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毛泽东的权利与制度思想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站起来”的理论法宝就在于其中所涵盖的辩证法,以辩证法为阐述路径方法的确更凸显毛泽东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马克思中国化基于中国社会现实性,毛泽东权利与制度思想着眼于服务社会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并非仅依赖于主观形式的辩证法。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若无中国现实性的考察、研究和斗争,毛泽东的权利与制度思想则失去了实事求是这一灵魂。
近代以来,改良派或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法在中国取得实质有效的成果是因为无法现实地认清民族危机的根源,在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获得和保障生存权利时,他们竟幻想以器物、实业、移风易俗等西式思维改造中国。无法认清社会主要矛盾,脱离社会现实性必然无法为中国带来新生,更遑论实现实质的公共权利与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而毛泽东权利与制度思想则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工农联盟、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三制”、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等均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挽救民族危亡。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目标是让老百姓真正获得平等、自由、民主,“有尊严”地“站起来”。然而,囿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必须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第三,以无产阶级专政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毛泽东关于权利与制度的思想指向是解放人民群众主体,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人类解放”,要赋予所有被压迫阶级当家作主的权利,致力于中华民族和社会生产力的解放,这远远超越了各种“布尔乔亚”式拙劣政制与“弥赛亚”布道般的各式资本主义革命。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管理国家、军队、各种企业、文化教育的权利是人民群众基本权利,以上公共权利是劳动者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的保证。[16]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优越就在于人民性的基础,始终视人民群众为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不可否认,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要实现“人类解放”还须作出巨大的努力。但是,中国人民是有夺取斗争胜利的坚韧性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已证明这一点。
当然,毛泽东关于权利与制度的思想并非否定权利的普遍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进步性,与之相反,毛泽东坚信所有人均享受同等权利是有可能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是在无产阶级消灭自己作为阶级存在之后,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后。而西方资产阶级正以资本主义制度规则本身遮蔽了无产阶级的权利,认为“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17],剥削无产阶级剩余价值,奉私有财产特权为圭臬。过去旧统治者与采纳西方人权的文化知识分子,即使也高呼人民权利和健全社会制度,但在政治行动中幼稚地幻想再造让人民群众俯首帖耳的阶级社会。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断改革的历史证明,人民群众才能当家作主,以强迫、恫吓和欺骗的统治手段视人民群众为草芥的政治路线,只能是“自掘坟墓”。历经波折磨难的中国不能走资本式剥削的步伐,而是致力以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个体利益和共同体利益的内在一致,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属性,只有这样,中华人民才能“站起来”且“有尊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使“解放了的人民为自己而工作,所以具有无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8]。这种以实现真正公共权利和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既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注入了新鲜的生命力,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宝贵的发展空间。
三、毛泽东权利与制度思想的时代指向
当前,我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启了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仍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目标。一些人认为,21世纪已是一个后革命的时代,所谓的“人类解放”早已划归理论考古学;或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实现公共权利与健全社会主义制度全部完成,无产阶级已经完成了解放自身和人民的任务,无需再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创新;或是认为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中国内部进行改革创新足以,不需要迈入全球化轨道进行不合时宜的“输出革命”或冒进。事实上,上述观点形而上学地误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性与斗争性,更缺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判断历史的方法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由革命走向建设,从苏俄开始便有修正主义式的解放观,试图回避矛盾,以“鸵鸟法”面对社会现实。毛泽东早在革命时期就对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进行了批判,这些思想汇聚于毛泽东科学性、系统性和革命性统一的“人类解放”观中。
第一,把握社会历史现实性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鲜活生命力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弥赛亚”式布道成为信徒“供奉”的圭臬或永恒真理,更不是简单公式可以被直接“剪裁现实”的工具。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其理论科学性与系统性之所以能够指导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法宝,就在于它能够精准把握社会历史现实性,可以将一般原理和客观现实有机结合。所谓的权威式、真理式、箴言式理论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因为教条化与本本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恰恰是“过多的侮辱”[19]。视马克思理论为工具式背书,不仅在脱离社会现实性中消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更妨碍了真正实现公共权利与建设公平正义的制度。毛泽东一生的政治活动是在中国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度过,从不离开理论的批判,他孜孜追求着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矛盾具有普遍性,具体化于社会历史中则意味社会制度革命不存在福山式的“历史终结”,只要资本主义的历史基因还存于社会运行机制中,变革社会制度、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批判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式唯意志论,他以中国社会现实为基点,将理论的批判转化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奋斗目标。因此,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以唯物辩证法强调了“不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尚存的社会经济矛盾,警示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只把握矛盾运动的“相对的同一性”,更要注重矛盾的特殊性。一方面,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揭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仍是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阶级斗争没有完全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毛泽东开展的批判首当其冲便是“泥沙俱下”的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0]无论是巴黎公社抑或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新经济政策双向式过渡政策,其正反经验早已证明了把握社会历史现实性才是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所在,必须对客观事物进行具体化、现实化、实际化分析。毛泽东指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21]需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必须结合着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
第二,人民群众是健全公共权利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体。1944年,英国记者斯坦曾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22]毛泽东的回答蕴含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人民性特征。无论是“人民子弟兵”的亲切称呼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体现了毛泽东对“人民创造历史”唯物史观的确信。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权利的实现与制度的建设必须围绕人民群众,在权利与制度的建设中逐步消灭“城乡”“工农”“脑体”三大差别。那么在独立的新中国如何实现?
首先,大力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是实现公共权利与健全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23]要吃饭、要民众联合、要健全权利与制度就得大力发展社会经济。马克思指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4]因此,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朝着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发展,才能构建出一个更加平等、正义、文明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完善的公共权利。
其次,社会利益大于个人功利主义。马克思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5]他强调以集体权利价值消解个人功利主义造成的个体与共同体矛盾。毛泽东权利与制度建设保障的是社会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毛泽东生活的时代,人民群众苦于旧社会的盘剥与压迫,经济破败,人格尊严受到肆意践踏,独立的个体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需要以集体主义消解个人功利主义,通过公有制经济、集体经济建设国家经济,将个人权利统一于集体利益之中。毛泽东以“大仁政”和“小仁政”的辩证关系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即“大仁政”要优于“小仁政”,即社会制度的建设和公共利益的提升优先于个人利益;“小仁政”的实现要依赖于“大仁政”的保障。个人利益的获取依赖于社会制度和社会建设的发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只有建立起强大的国家经济基础,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国家各方面的平稳运行和个人权利的实现。
最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相较欧洲、俄国,中国社会的现状更为复杂,既没有欧洲那样强大的物质生产力,也没有俄国那样拥有相对强大的革命力量和较为成熟的工人阶级。中国有的仅是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和战后破败凋敝的社会经济。那么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和完善人民权利?虽然十月革命证明了落后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列宁也认为,落后的国家在完成民族独立解放后,可以建立“农民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26]。但是,此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事实上,在落后的国家要保障人民权利和实现制度的完善,靠等、靠要、靠乞讨是徒劳的。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27]中国人民要争取权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必须靠自身。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成功不仅在于国家有计划地进行指导,更在于中国人民自身的奋斗,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祖国的力量。
第三,完善公共权利与健全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不在于被人供奉为永恒真理,而在于指引无产阶级政党通向“人类解放”,实现真正的权利和“自由人的联合体”制度。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经验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完成由“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带领人民“告别”虚伪的公共权利与资本主义式腐朽式共同体,即剥削人民的自由和生产领域的“无政府状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肩负着人类解放的使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扳倒“三座大山”的民族解放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一方面肩负着中国人民继续摆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新压迫重任,另一方面承担着引导受剥削与恫吓的世界无产阶级迈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从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到甩掉“绝对式贫困”旧帽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一致、攻坚克难、帮扶他国的事实雄辩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实现。如果说《资本论》的问世,如雷鸣电闪般驳倒了资产阶级经济学,[28]那么毛泽东政治哲学权利与制度思想则是以实践的方式瓦解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式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