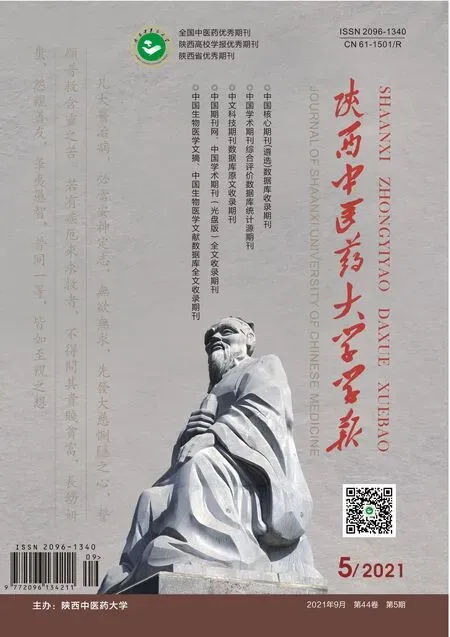从一气周流到五行脏腑气机气化*
王振国 余楠楠 王凌立 刘华为
(1.西安中医脑病医院,陕西 西安 700032;2.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 西安 710068;3.陕西省中医医院,陕西 西安 710003)
黄元御,清代著名医家,曾为乾隆御医,黄师晚年学医而致大成,著有《四圣心源》等流传医书十一种[1]。黄老认为五行是一个以土为轴,以木、火、金、水为边运动的“轮”,五行之土化五脏,其中《天人解·脏腑生成》曰:“己土上行,阴升而化阳,阳升于左,则为肝,升于上,则为心;戊土下行,阳降而化阴,阴降于右,则为肺,降于下,则为肾”,文中强调土在五脏生成中的主导作用,而且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中土健则精气化生无穷,从而维持健康,《劳伤解·中气》指出“胃主受盛,脾主消化,中气旺则胃降而善纳,脾升而善磨,水谷腐熟,精气滋生,所以无病”,可见,脾胃中气是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根本,治疗上应注意调护中气[2],恢复脾胃升降的中轴作用,使一气周流往复无阻而达到防病治病之目的。
刘华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一级主任医师、二级教授,陕西省名中医。刘华为教授以木、火、土、金、水为中介,以中医五脏六腑为基础,加入中医气化理论,构建了“人体五行脏腑气机气化系统”,简称“五行气化”[3]。他指出:人体内时刻存在着升降出入的运动,这些运动以五行及脏腑为中心周流循环,从而维持机体稳态。饮食物通过气化才能变成气、血、津液、精以供养身体;如若气化不彻底,一部分饮食物就变成中间代谢产物(痰、湿、水、瘀)成为人体及继发致病因子[4]。内科疾病的产生都与“升降失调、气化失司”有关,而诸多疑难杂症,均与气化不彻底的代谢产物“痰、湿、水、瘀”等互相结聚有关。而用药的目的,就是加强气化,把这些中间产物重新分化的过程。因此治病需以损有余而补不足之法,使阴阳平衡、气机和顺,恢复人体正常的升降出入变化,保持合理的气化状态。
笔者有幸师从刘华为教授,结合前期经典学习,认为五行脏腑气机气化理论与黄氏一气周流理论皆植根于传统中医理论,而后者是前者的一种传承与发展,需要进一步融合创新,以指导临床实践。兹浅述如下:
1 生理观——脾胃升降、肝胆斡旋,五脏气机气化
黄元御以“一气周流变化于五行之间”来概括人体的正常生理特点,而“气”是五行相生相克的媒介,正如《四圣心源·五行生克》云:“五行之理……其相生相克,皆以气而不以质,成质则不能生克矣”,因此,气的运动贯穿五行的生克过程,是五行运转的动力[5]。刘华为教授则重新认识了气机和气化的概念,认为气在机体内运行而形成气机,概而言之气机是五行脏腑之气的运行规律,可概括为升、降、出、入四种基本形式或状态[6]。而气化则是人体生命活动中的新陈代谢过程,这与现代医学的“细胞氧化”类似,如同三羧酸循环将饮食无生化为糖类、脂类和蛋白质,中医则认为气化使经口进入的饮食化生为人体必需的精微物质而维持正常生命活动。
黄元御氏着重强调中土是“气化”的动力源泉,认为四象合而言之不过阴阳,阴阳合而言之不过中气,脾胃之气是机体脏腑阴阳环周变化的枢轴和动力[7]。《天人解·气血原本》云:“肾水温升而化木者……脾为生血之本;心火清降而化金者……胃为化气之原。”中土冲和则肝木升发而化心火,肺气肃降而化肾水,从而水火既济、动态平衡。中气是阴阳、脏腑、气血津液、精神形体等化生的源泉。黄元御之理论固然圆融,为治本之法,以之论治疾病却易陷入独重脾胃的怪圈,为缓图治本之法。而刘华为教授扩大了“气化”的内涵,认为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但气机调节在于肝,而气化之总司则在胆[8]。脾胃与肝胆作为人体的两大枢纽站,共同调节人体气机的升、降、出、入。《素问·六节脏象论》言:“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李东垣《脾胃论》亦言:“胆者,少阳春生之气,春气升则万化安。故胆气春升,则余脏从之;胆气不升,则飧泄肠澼,不一而起矣。”在此基础上刘华为教授扩大了升降的内涵[9],在传统的“脏升,腑降”基础上,更渗透脏腑、经络之间的升降关系,其中包括五脏中的心火降肾水升,水火既济;肺气降肝血升,气血调畅;肺气降肾水升,气水互化。脏腑间包括肝气升,胆气降,疏泄有制;脾气升,胃气降,纳磨有权。六腑中的小肠降、膀胱升,清浊有别;胆、胃、大肠之气主降,浊气下流。经络之督脉升、任脉降而阴阳循环等等。刘华为教授认为脏腑气机的升降是维持“气化”功能的原动力,论治疾病应恢复脏腑气机的正常升降与气化,着重强调脾胃、肝胆为主,其余脏腑兼顾的升降气化观。
2 病机观——阳衰土湿,三焦阳化不足、阴化太过
关于疾病病机,《四圣心源·六气解》开宗明义地指出“内伤外感,百变不穷,溯委穷源,不过六气。”“内伤者,病于人气之偏,外感者,因天地之气偏,而人气感之。”黄元御认为六气五行,皆内现于人体本身,平人六气之间生克制化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一旦六气的平衡被打破,某一气即会亢旺而致病[10],正所谓“病则或风、或火、或湿、或燥、或寒、或热,六气不相交济,是以一气独见。”对于内伤病人气之偏,黄元御认为疾病以阳虚为主,《四圣心源·阳虚》云:“病于阴虚者,千百之一;病于阳虚者,尽人皆是也。”也批判了后世典籍耗伐阳气的错误医疗行为,指出“医书不解,滋阴泻火,伐削中气,故病不皆死,而药不一生。”对于外感之天地之气偏,则独重湿邪,在《四圣心源·劳伤解》中指出“阳明之燥,不敌太阴之湿……其病也,胃阳衰而脾阴旺,十人之中,湿居八九。”湿邪为患,阻滞脾胃升降而百病由生,“胃主降浊,脾主升清,湿则中气不运,升降反作,清阳下陷,浊阴上逆”[11]。由此,进一步制定疾病论治大法,即“泻水补火,扶阳抑阴,使中气轮转,清浊复位”,此为却病延年之不二法门也。
刘华为教授理论则继承了内伤疾病阳虚者多的理论,指出病态的气化是致病之因,包括“阳化”和“阴化”的太过与不及,而其中阳化不及也阴化太过占绝对优势;而且丰富了六淫理论,提出内生六淫致病内涵[12],更强调复杂疾病多病理因素联合作用。刘华为教授认为脏腑之间的气化失调,会使得机体正常的气、血、津、液、精等生理物质的化生、布散、转化和排泄受到影响,当生成不足时就会出现气虚、血虚等证候,而产生太过则会产生诸如痰、饮、水、湿、瘀等代谢产物,成为内生六淫,损害脏腑气化功能,影响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因此,临床内科疾病的产生多因三焦阳化不足,以致阴化太过,产生痰饮内盛、痰湿阻滞、痰瘀互结、水湿浸渍等复杂病机,使得上、中、下三焦气机逆乱,气化失常,从而百病滋生。刘华为教授临床中始终强调固护阳气在疾病防治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体中的阳气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具有温煦、防御,推动脏腑气化的功能[13],并根据自己临床经验提出“护阳、卫阳,养阳”的观点。因此治疗上应时刻注重扶正祛邪,高度重视人体的阳气,遣方用药不可峻烈猛浪,尤其在清热解毒、活血破血、消积散结等药物使用时尤应小心谨慎,需攻补兼施、寒温相配,恢复人体三焦正常气化功能,避免过伤阳气而变证锋起,此医者之大过也。
3 治法观——从黄芽汤到黄连温胆汤、柴桂龙牡汤、调中益气汤、五苓散等
黄元御认为“阳衰土湿”为诸劳伤病、内外科杂病、妇人病之根源,治病之法当以“培升降之用,拨转运之机”为原则,重在脾胃。黄元御在《四圣心源》中的用药处方处处体现了这一思路,以中焦培土设立大法,或拨动左路之木、火,或拨动右路之金、水,以轴带轮,恢复正常的一气周流,正所谓“中气轮转,清浊复位”[14]。黄元御以此为准绳,创制了基本方黄芽汤,该方被认为等同于伤寒论之桂枝汤,为黄元御“诸方之祖”,为一元论治本之方。方含人参、炙甘草、茯苓、干姜,即为伤寒方理中汤易白术为茯苓,其中崇阳补火则用参、姜,培土泄水则宜甘、苓,药味虽少,而配伍严谨,效专力宏,非结合数十年临床经验所不能拟定[15]。而视其药味加减,更能体会其一气周流理论之圆融,“其有心火上炎……加黄连、白芍,肾水下寒……加附子、川椒,肝血左郁……加桂枝、丹皮,肺气右滞……加陈皮、杏仁。”观其临证用药之梗概,明黄元御一气周流之深意,在中州立法的前提下,兼顾上下左右四旁,思维周密,并无以偏概全之嫌,反而力求面面俱到。黄元御以阳衰土湿为内伤杂病的基本病机,所以立方遣药,注重培中焦泄水湿[16],但临证亦不忘清心、温肾、疏肝、理肺等诸法的融会贯通,不悖辨证论治之精髓。
刘华为教授则强调脾胃肝胆对于五脏气机气化的综合作用,强调人体阳气对气化的推动作用,病理因素也则着眼于内生之痰湿水饮之邪。刘华为教授认为:气机升降失常,则导致“气化”不彻底,从而产生痰、饮、水、湿、瘀等代谢产物,成为致病因素而滋生疾病,其中痰、饮、水、湿往往是气和津液代谢失常的产物,瘀是血代谢失常的产物[17]。还指出升降失调、气化失司、体内代谢产物(痰、湿、水、瘀)停聚是诸多内科杂病的实质[18]。临床每遇到胁痛、胃痛、焦虑、失眠等患者,属于肝脾不调、中焦气化失司者多选方(丹栀)逍遥散、柴桂龙牡蛎汤(小柴胡汤合桂枝白药龙骨牡蛎汤)合五苓散、逍遥散合调中益气汤等;若见心下痞满、呃逆返酸、肝胃不和者多选用逍遥散合半夏泻心汤、小柴胡合半夏泻心汤等,胆胃不和时予黄连温胆汤合半夏泻心汤;若上升为神志异常,出现肝胆不调、痰热内生、气机逆乱病机者则予柴桂龙牡汤、四逆散或丹栀逍遥散合黄连温胆汤等;若因此影响下焦气化,小便不利,肝肾不调者则酌用柴桂龙牡、逍遥散合猪苓汤或金匮肾气丸等,用药法度严谨,旨在恢复人体正常气机气化。根据经验总结,临证往往选用诸如黄连温胆汤、柴桂龙牡汤、逍遥散、调中益气汤、五苓散、藿香正气散、大小柴胡承气等一类具有调节脏腑气机升降,恢复气化功能的方剂,经方、时方并用,且常常进行联合使用或巧妙灵活化裁,屡起沉疴。刘华为教授治病每每强调阳气的作用,认为阳气就是人生、长、壮、老、已和气化功能实现的动力。阳气不足,则气的升降出入不利,津液的输布代谢失常,气化不彻底而内生水、湿、痰、饮,甚或水泛为肿,尤其是肿瘤患者,阳气不足往往传变迅速,损伤正气往往使病情迅速恶变[19]。而痰、饮、水、湿等阴性的病理产物往往容易损伤阳气,形成恶性循环。临床中教授往往佐少量附子(3~6 g)以少火生气[20],且善于半夏与附子同用,前者降逆气,后者升阳气,一升一降,气机调畅,使气化归于正常。
笔者业医以来,初学一气周流理论,思四象合阴阳,阴阳合一气,而土枢四象实为中医道家一元论之至理,从此摒弃各家学说,独尊脾胃之学,辨证立法皆遵水寒土湿论,遣方用药不外黄芽理中、金匮肾气、五苓散、三仁汤、枳术丸之辈,疗效缓半,甚为苦恼。后旁学诸家,皆无法跳出脏腑、六经论治之藩篱,法伤寒方证对应,始遇速效。自跟师刘华为教授以来,深明脏腑六经皆有赖气化,每于方中加入促进气机气化之方,如黄连温胆汤、逍遥散、柴桂龙牡、半夏泻心等,且时时顾护阳气,以阳气带动周身气化论治诸病,方柳暗花明,十效七八。自此深知中医理论之博大精深,明了仲景先师之语,慨叹“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以一驭万,寻师所集,思过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