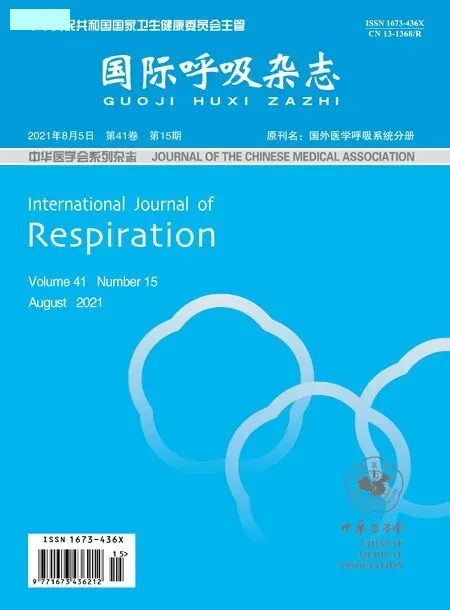糖皮质激素对病毒性肺炎的辅助治疗价值
邢夏 邢丽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ICU 450052
社区获得性肺炎是一种常见的感染性疾病,在世界范围内是导致住院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1]。随着分子诊断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呼吸道病毒在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学中的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2-3],部分病毒性肺炎可快速进展为重症肺炎、ARDS、脓毒症[4-6]。病毒的快速复制以及免疫失控引起的细胞因子风暴可能是导致其不良预后的重要原因[7]。糖皮质激素 (glucocorticoids,GCs)具有强大的免疫调节作用,但同时存在使病毒清除延迟、继发感染等风险,因此在病毒性肺炎的治疗中备受关注,也饱受争议。为进一步梳理GCs对病毒性肺炎的辅助治疗价值,现作如下综述。
1 病毒性肺炎的炎症反应机制
机体对病毒感染的免疫反应可分为3 个连续阶段[8]。(1)启动阶段:病毒入侵后,固有免疫应答即刻被启动。首先气道上皮细胞及固有免疫细胞 (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等)直接通过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识别病毒,从而诱导Ⅰ型干扰素 (interferon,IFN) (IFN-α、IFN-β等)、Ⅲ型干扰素 [IL-29 (IFN-λ1)、IL-28A (IFNλ2)、IL-28B (IFN-λ3)]、IL-1β及其他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的表达,并激活炎症小体。Ⅰ型干扰素及Ⅲ型干扰素主要介导早期抗病毒反应[9-10]。除此之外,病毒感染细胞及损伤细胞产生的损伤相关分子模式,被抗原提呈细胞识别,核转录因子κB 活化,导致IL-1β前体等炎性介质的转录,同时,炎症小体组装完成,激活caspase-1,活化的caspase-1催化了IL-1β和IL-18等的成熟和释放,而IL-1β进一步促进肿瘤坏死因子α、IL-6等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这一阶段建立了炎症环境,也参与启动了后续的适应性免疫应答。(2)缓解阶段:在该阶段中,适应性免疫细胞被募集至受感染部位,适应性免疫反应启动。病毒清除及对再感染的抵抗力主要由适应性免疫应答介导。其中,以产生特异性抗病毒抗体的B 淋巴细胞为主的体液免疫通过中和病毒防止病毒扩散,介导吞噬细胞高效杀伤病毒,而细胞免疫 (由CD8+T 细胞介导)则主要负责清除病毒感染细胞。(3)修复阶段:病毒清除及炎症反应控制后,便开始了肺的 “重塑”。在这一阶段,肺屏障的完整性及基本功能 (气体交换等)逐渐得到恢复,与感染相关的细胞碎片也得以清除。
然而,部分高致病性病毒株 (如甲型H5N1、H1N1、SARS-Co V、SARS-Co V-2、MERS-Co V 等)的感染会导致宿主免疫反应失调,使得促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过度释放,引发 “细胞因子风暴”。其机制可能在于: (1)拮抗IFN 反应。IFN 反应为早期固有免疫抗病毒效应的关键途径,而高致病性病毒可编码多种拮抗IFN 反应的结构和非结构蛋白 (如甲型H5N1 编码的NS-1 蛋白[11]、SARSCo V 的nsp1 蛋 白 等[12]、MERS-Co V 的M 蛋 白 等[13]),IFN 的早期拮抗可能会使病毒延迟或逃逸固有免疫,使得病毒复制不受限制,大量致病性炎性单核巨噬细胞涌入,累积的炎性单核巨噬细胞产生更多促炎细胞因子及趋化因子 (肿瘤坏死因子、IL-6、IL-1β、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等),进一步放大炎症反应[14]。 (2)快速病毒复制。病毒(如SARS-Co V、MERS-Co V 等)在感染后能快速复制达到高滴度水平[15-16],这种高复制导致病毒PAMP增加、细胞病变效应增强,受感染的上皮细胞产生更高水平的促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 (CCL3、CCL5、CCL2、CXCL10等),它们又使炎症细胞大量渗入肺部。(3)促进炎症因子的转录与释放。一些病毒可以在转录水平促进炎性细胞因子表达,例如SARS-Co V 的E 蛋白和ORF3a可激活核转录因子κB,导致IL-1β 前体转录,然后两者通过促进NLRP3炎性小体的组装和激活,使成熟IL-1β释放,进而诱导促炎性细胞因子风暴[17-18]。 (4)不良的T 细胞应答[7]:病毒特异性T 细胞对于病毒的清除和限制对机体进一步的损伤至关重要。同时,T 细胞反应也能抑制过度的固有免疫应答[19]。直接感染或因促炎细胞因子导致的T 细胞凋亡以及淋巴细胞耗竭,使得炎症反应失控,并阻碍了进一步的病毒清除[14]。
2 GCs的免疫调节机制
2.1 GCs的信号传导机制 循环GCs大部分与皮质类固醇结合球蛋白结合,小部分以游离形式存在,游离GCs具有生物活性。GCs介导的免疫调节被经典地归因于糖皮质激素受体 (glucocorticoid receptor,GR)诱导的基因表达的改变。GCs与细胞质GR 结合,GC-GR 复合物通过3种机制调节基因转录:(1)GC-GR 二聚体作为转录因子直接与基因组糖皮质激素反应元件结合而诱导或抑制靶基因表达; (2)GR 与其他转录因子发生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它们的转录活性,例如通过与核转录因子κB 和激活蛋白-1发生物理相互作用,抑制它们诱导促炎基因转录的能力,从而抑制促炎细胞因子 (IL-1、TNF-α、IFN-γ等)的合成及一氧化氮合酶的表达和NO 的产生,下调转化生长因子β的表达;(3)GC-GR 直接与包含糖皮质激素反应元件和另一转录因子的反应元件的DNA 片段结合 (复合调控)[20-22]。除了基因组机制外,GCs的抗炎活性也可能通过与膜成分非特异性相互作用、与膜结合GR 相互作用或者激活激酶途径等非基因组机制引起。该机制涉及多种第二信使、激酶和离子跨膜转运等,起效快 (秒至分钟),作用持续时间短 (60~90 min)[23]。但是,目前仍普遍认为核转录因子κB和激活蛋白-1转录活性的抑制在介导GCs的抗炎作用中起重要作用。
除上述抗炎机制外,GCs的作用也受到了GR 不同亚型的影响。GR 由基因NR3C1转录而来,该基因的可变剪接产生GRα和GRβ亚型。与GCs转录调控相关的典型受体是GRα。而GRβ主要位于细胞核中,它不与配体结合,并且拮抗GRα的活性[20]。研究表明,炎症影响GR 亚型的表达谱,在一些疾病中,GRβ 的表达增强与GCs 抵抗有关[24]。
2.2 GCs的免疫调节作用 GCs在转录和细胞水平上调节免疫应答。机体暴露于病原体后,会导致免疫应答的快速激活,GCs可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等的产生;同时,GCs通过抑制黏附分子的表达防止中性粒细胞滚动、黏附和向炎症部位募集,通过诱导膜联蛋白-1的表达促进中性粒细胞凋亡。长期暴露于GCs会使巨噬细胞基因表达谱从促炎性转变为抗炎性,并增加其吞噬活性[25]。GCs还可通过抑制淋巴细胞活化和促进其凋亡来调节适应性免疫,高浓度下,GCs也会抑制B细胞和T 细胞产生[20]。
然而,GCs不仅有抗炎作用,也会增强固有免疫应答。研究表明,GCs的作用与给药剂量和时机有关[26-27]。有学者认为,低浓度GCs通过上调模式识别受体、细胞因子受体和补体来提高固有免疫系统的敏感性,从而对危险信号做出快速反应;高浓度GCs则抑制模式识别受体和细胞因子受体介导的信号,从而防止过度或延长的免疫反应[20]。
3 GCs辅助治疗病毒性肺炎的临床研究
虽然目前关于GCs 对病毒性肺炎的疗效仍存在争议[28-29],但其仍常被用来辅助治疗重症病毒性肺炎以及所引起的严重并发症。在对浙江省45 家医院ICU 的问卷调查中,44.74%的医师支持在重症病毒性肺炎中常规使用GCs[30]。由于GCs对病毒性肺炎辅助治疗价值的研究多聚焦于引起大流行的病毒上,故在此将流感病毒及高致病性冠状病毒 (SARS-Co V、MERS-Co V、SARS-Co V-2)的相关临床研究综述如下。
3.1 GCs对病毒性肺炎预后的影响
3.1.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一项纳入31例普通型COVID-19 患者的观察性研究表明,GCs治疗与病毒清除时间、住院时间或症状持续时间无关[31]。而一项纳入201例患者的回顾性研究对发生ARDS的84例重症COVID-19患者进行分析,发现GCs可降低病死率[32]。无独有偶,美国的一项多中心研究表明,对于中重度COVID-19患者早期小剂量短疗程使用GCs(甲泼尼龙0.5~1 mg·kg-1·d-1,分2次静脉使用,连续3~7 d)能够改善患者的临床结局[33]。另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将2 104例应用GCs 的患者 (地塞米松6 mg/d×10 d,中位时间为7 d)与标准治疗组 (4 321例)进行比较,发现地塞米松的使用降低了接受有创机械通气或非有创氧疗患者的28 d病死率,却对病情较轻 (无需呼吸支持)患者的28 d病死率无影响[34]。
3.1.2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及中东呼吸综合征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 Auyeung等[35]对78例非重症成年SARS患者的回顾性研究提示,GCs的应用显著增加了不良事件 (入ICU 或者死亡)的发生率。一项纳入401例SARS患者的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GCs治疗并未改善患者病死率和住院时间,但只关注该队列中的152例重症SARS,并对混杂因素调整后,发现GCs治疗有助于降低病死率、缩短住院时间[36]。在一项关于入住ICU 的重症MERS患者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中 (n=309),在调整了混杂因素后发现,GCs治疗并不增加90 d病死率[37]。
3.1.3 流感病毒性肺炎 Diaz等[38]对372 例甲型H1N1病毒性肺炎患者的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使用GCs治疗不能改善生存率,Moreno等[39]对2009年6月至2014年4月之间招募的1 846例入住ICU 的流感肺炎重症患者的前瞻性观察性队列进行了二次分析,结果显示GCs的使用 [甲泼尼龙,中位剂量80 (60,120)mg/d,中位持续时间7(5,10)d]会增加ICU 病死率。而另一项纳入中国407家医院的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则分别对不同严重程度的患者进行分析,发现GCs(25~150 mg/d甲泼尼龙或同等剂量)可降低PaO2/FiO2<300 mm Hg(1 mm Hg=0.133 kPa)的甲型H1N1流感pdm09病毒性肺炎患者的30 d和60 d病死率,而轻症患者 (PaO2/FiO2≥300 mm Hg)不能从GCs治疗中获益,甚至增加了60 d病死率[40]。
虽然目前关于GCs对病毒性肺炎预后的研究结论差异较大,但从有限的证据中可以发现:GCs对于轻症患者未表现出明显的生存受益,而部分危重患者更可能从GCs治疗中获益。其原因可能在于: (1)研究发现,相比于轻中度患者而言,重症患者的促炎细胞因子水平更高,提示炎症风暴与疾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41-43]。合理应用GCs可有效抑制炎症风暴,对防止继发多脏器损伤可能具有潜在益处[44]。(2)在危重患者中,皮质醇的调节变得更加复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失调、皮质醇代谢改变及组织对GCs的抵抗会使部分重症患者出现危重症相关性皮质醇缺乏[45]。在这种情况下,应用GCs以补充相对不足的皮质醇,可能会使患者受益。但是最近研究也指出,重症患者皮质醇的清除能力明显降低,较大剂量的GCs可能反馈抑制中枢而进一步增加对肾上腺皮质功能抑制[46]。另外,近期研究认为,相较于最初的过度炎症反应,随后的免疫抑制状态更容易引起预后不良[47]。GCs剂量及应用时机选择不当可能是某些重症患者使用GCs后仍预后不良的主要原因。
3.2 GCs对于病毒性肺炎治疗的时机探讨 重症病毒性肺炎病理结果显示,其肺部主要表现为弥漫性肺泡损伤和肺透明膜形成,符合ARDS表现[48]。研究发现,在ARDS起病14 d后应用GCs会显著增加病死率[49]。目前建议早期中重度ARDS (<7 d,PaO2/FiO2≤200 mm Hg)患者应用甲泼尼龙,剂量为1 mg·kg-1·d-1,晚期ARDS (≥7 d)剂量为2 mg·kg-1·d-1,在13 d内缓慢逐渐减量[50]。最近的研究也表明,对于ARDS患者,在首次满足中重度ARDS诊断标准 [FiO2≥0.5,呼气末正压≥10 cm H2O(1 cm H2O=0.098 kPa),PaO2/FiO2≤200 mm Hg]后30 h内应用GCs (地塞米松20 mg/d,第1~5 天;10 mg/d,第6~10 天)能够缩短机械通气时间,并降低60 d病死率,且并不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51]。然而,既往研究包含了相当大比例非感染原因所致的ARDS,因此该治疗方案可能不完全适用于重症病毒性肺炎患者。
既往研究表明,重症病毒性肺炎的临床病程分为3个阶段:病毒复制期、病情进展期和ARDS期[7,52]。第二阶段接近尾声时病毒滴度逐渐下降[52]。因此,病程后期主要由宿主免疫功能失调引起。虽然动物模型显示,GCs与抗病毒的联合治疗可显著减轻棉鼠在H3N2感染期间的组织损伤,且不延长病毒清除[53];但在临床研究中,绝大多数患者在应用GCs的同时也联合了抗病毒治疗,研究结果却大相径庭。在一项纳入16例SARS患者的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试验中,“早期”(<7 d)氢化可的松治疗与随后更高的血浆病毒载量相关[54];关于甲型H7N9 禽流感病毒及MERS的研究也同样显示GCs 应用与病毒清除延迟有关[37,55]。而2项针对甲型H1N1 病毒感染的研究均显示,早期 (症状出现或者机械通气3 d内)GCs治疗的患者发展为重症的风险及病死率更高[56-57]。因此,在重症病毒性肺炎中,GCs的使用可能并非 “越早越好”,而需要对患者的一般情况、病毒载量、免疫功能、炎症程度等方面综合分析。关于重症病毒性肺炎患者GCs最佳治疗时机的选择仍需大规模的随机对照研究去摸索。
3.3 GCs治疗病毒性肺炎的剂量与疗程 由于病毒性肺炎的爆发性,用药初期并无完善的指南指导,而多由临床医师根据病情经验性治疗,导致了回顾性研究中GCs用法的异质性。中国的大型问卷调查结果显示,ICU 医师对于GCs剂量、剂型及疗程的选择差异较大[30]。一项针对7例重症COVID-19的病例系列报告表明,在呼吸衰竭的早期进行大剂量、短疗程GCs治疗 (甲泼尼龙1 000 mg/d 或500 mg/d静脉输注3 d,之后改为1 mg·kg-1·d-1,2~4 d,并逐步减量,总疗程中位时间为13 d)可能会使患者受益,而不增加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58]。然而,既往多数临床研究表明,大剂量、长疗程的GCs与不良预后及长期并发症密切相关。一项对甲型H7N9重症患者的回顾性研究显示,高剂量GCs组 [>150 mg/d甲泼尼龙或等效剂量,中位时间为7 (4,11.3)d]的30 d和60 d病死率及病毒清除时间显著增加,而低中剂量GCs(25~150 mg/d甲泼尼龙)对病死率无影响[59]。这一现象在SARS研究中更为明显。虽然研究表明,早期大剂量规律使用GCs(甲泼尼龙,平均用量240 mg/d,疗程3~4 周)对于重症SARS有明显疗效[60],但后续研究发现,GCs的累积剂量、冲击疗法的持续时间等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61]、精神病[62]的发生密切相关;而类固醇性糖尿病发生率在甲泼尼龙最大剂量>160 mg/d组为最大剂量≤80 mg/d组的5倍,疗程≥3周组为疗程<2周组的3.6倍[63]。
GCs剂量及疗程选择不当可能为患者带来严重并发症,甚至影响其长期生活质量。因此,目前针对COVID-19患者的GCs建议较为谨慎,国内指南或专家共识普遍建议对于进展较快的重症患者可酌情采取短疗程 (不超过10 d)、中小剂量 (0.5~2 mg·kg-1·d-1)甲泼尼龙辅助治疗[64-65]。尽管已有研究表明GCs 应用可能会改善重症COVID-19患者的短期预后[32-34],但对于其长期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考证。
4 总结
综上,目前关于GCs对病毒性肺炎应用的研究仍存在较多争议,但从有限证据来看,部分重症患者似乎能从GCs治疗中获益,而过早、大剂量、长疗程应用GCs可能会使病毒清除延长,甚至增加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影响患者预后及长期生活质量。目前临床研究由于患者及GCs用法选择的异质性较大,得出很多相互矛盾的结论。未来仍需要进一步探索病毒性肺炎的病理生理机制,同时也需更多更严谨的大规模随机对照研究和临床观察性研究去进一步探讨在病毒性肺炎中应用GCs的有效性、安全性、适用人群、最佳治疗方案,以期指导临床实践,最大程度上改善病毒性肺炎患者的预后。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