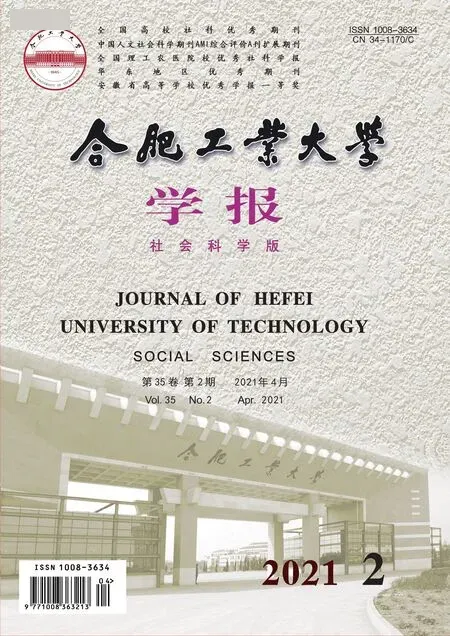林纾译作书名的批评话语分析
胡萍英
(福建工程学院 a.人文学院;b.福建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福州 350118)
一、引 言
林纾(1852-1924),是我国近代伟大的翻译家和文学家,以翻译和诗画著称于世。尽管不谙外文,林纾以大无畏精神,与他人合作,跻身近代译坛,其一生共译介184种外域小说,涉及十几个国家近百名作家。林纾是中西文学交流的先行者,“林译小说”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早的西洋文学的代名词。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虽然享有“译界之王”和“译才并世数严、林”的赞誉,林纾却是一位颇有争议的翻译家。文献显示,学界从多元视角对林纾、林译作品及其翻译方法进行研究和评价。有的从翻译理论与方法的角度进行评价和论述[1-2];有的基于文学理论视角,从译著的文学性、忠实性、创造性和现代性方面进行评价[3-4];有的从语言学角度肯定其文言译作的语言研究价值和文化意义[5-6]。十多年来,学界越来越关注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从话语分析角度解析社会文化与林纾翻译的互动关系[7-8];通过考察林纾译著及序跋等,研究林纾的翻译爱国思想及现代意义[9]。但是,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林纾翻译意识形态及其社会价值研究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因此,本研究试图运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从林译小说书名翻译及其表达的文体特征两个维度,探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林纾翻译意识形态和翻译思想对其翻译实践的影响。重点考察译者如何在小说书名翻译过程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识形态,从而揭示林纾意识形态对其翻译思想和小说书名翻译的影响;解释林译书名的潜在社会文化意义。
二、批评话语分析方法论
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是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权力和话语是不可分割的,权力通过话语来实现,话语不仅是传播知识和实施权力的工具,也是获得权力的关键[10]。Foucault对话语的看法让我们重新思考语言、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他推翻了很多人把语言视为传达或表述知识的透明工具这种一厢情愿的看法,让我们认识到语言是意识形态的载体、话语运作的原材料[7]15;“话语”是“或明或暗地流露着意识形态的语言或文本”[11]。20世纪70年代,Fowler等在《语言与控制》(LanguageandControl)一书中首次提出“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概念,把语言和社会权力联系起来,旨在探究权力和意识形态对语言的影响以及语言如何去反映这些不平等的现实[12]。Fairclough在《语言与权力》(LanguageandPower)一书中提出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概念[13];创建了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话语分析体系,以语言学为主体,以系统功能语言学分析方法为工具,将语言实践活动中的特定文本与话语的社会文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旨在通过语言分析,透过语言形式探索话语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从而揭示语言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应用语言学的发展,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基础上,话语分析被应用于翻译研究,探讨语言传达意义及社会与权力关系的方式[14],主要研究话语运用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语境。Fairclough提出的话语分析框架(a framework for discourse analysis),从文本(text)、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和社会实践(discourse as social practice) 三个维度,分析话语、理解话语的潜在意义[15]。在此基础上,Fairclough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三个层次:“描述(describe)”文本的语言结构特征;“阐释(interpret)”文本与话语实践的关系,分析文本的生成(production)、传播(distribution)和接受(consumption)过程;“解释(explain)”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16],即读者应结合社会文化背景,解析权力和意识形态在话语实践中是如何产生作用的。本研究主要从林译原著的选择、译作书名的创译和书名文体的选用三个维度出发,探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林纾翻译思想的渗透,阐释林纾翻译意识形态对源语文本的介入和对翻译行为的操纵;从意识形态操控下的林译书名对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的指向性,以及对当时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挑战性,阐释林译话语对当时社会文化的建构意义。
三、林译书名的生成过程
翻译是涉及两种语言及文化的话语实践活动过程。话语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语言表达具有意识形态的力量[17]。这就意味着一切为意义所做的选择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动因,林纾的翻译与当时政治和社会改良运动紧密配合,他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寻找先进的精神武器,以警醒同胞爱国保种、维新救国;其次,西方文学中对于人之自然情感的推崇是让林纾动心的另一个因素。他认为翻译西方小说是介绍新思想、启蒙开化国民的重要途径。因此,林译小说的选题广泛,而且大多基于爱国醒世、维新图强的思想内容,他对小说情节的考虑超出了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他甚至不介意原著是否出自名家之手。另外,林纾采用“以中化西”的归化策略“创译”书名,以满足当时读者和社会需要,达到警醒和教育国人的目的。林纾选用古雅的文言译介外域小说,体现他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和抵御强势文化殖民的思想意识。
1.林译原著的选择
由于林纾不懂西文,林译小说采用与他人合译的方式,故学界通常认为林译小说原著的选择完全由合译者操纵[18-19]。这一论断忽略了“合译模式”下每个译者作为社会个体,彼此可能存在的协商过程。由于受当时许多具体社会因素的影响,林纾合译模式下的译本选择,应是以林纾为主导,在其文学追求与社会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整个翻译团队经过潜在的“协商”,最终达成的“一致选择”[20]。如果说林纾在翻译其处女作《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时候,尚无明确的意识形态和翻译目的,那么,在其后为《译林》杂志社所作的序(1901)中,林纾显示了他已经将翻译实践与启蒙话语联系在一起了[21]。林纾看到了启蒙、教育、译书与小说之间的密切联系,意识到“翻译”就是他今后的战斗武器和救国实业。林纾希望通过翻译域外“政治小说”来惊醒国人、宣扬变革思想、开通风气。他将与当时中国时局密切相关的外国名家作品都翻译过来[22]。林译小说的类型以言情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政治小说以及冒险小说居多,这些作品向国人传播了民族、民主、女权、实业等西方先进思想。
2.林译书名的创译
林译小说体现为口译笔述的合译方式,林译小说书名的独特翻译方式往往基于林纾的翻译目的和意识形态。林纾依据自己对原著核心内容的理解及诠释,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将外国小说书名进行中国式改写,体现其翻译救国目的和动机。这既是对西方异域文化的一种抵制和排斥,又是为了吸引和鞭策受众,以利于读者借助书名所传达的含义,领会和感悟小说的核心内容。例如,法国作家沛那(Bruno)的小说LetourdelaFrancepardeuxenfants(两孩童的环法之旅)讲述了战败后的法国国民实业自强、实业报国的故事。林纾以《爱国二童子传》命名,凸显实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俄国杰出作家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 Л.Н.)的小说集Детство отрочество и юность(童年·少年·青年)是自传体小说,叙述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讲述了俄罗斯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反映了19世纪俄罗斯社会的真实生活及尖锐的社会问题,宣扬人道主义精神。林纾将书名Детство отрочество и юность创译为《现身说法》,希望托尔斯泰伟大的人格能够感动读者的心,呼吁国人清醒地认识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为灾难深重的国家和民族顽强抗争。不言而喻,书名《现身说法》比《童年·少年·青年》更直接呈现原著作者的创作意图,更符合当时国内读者的阅读期待。英国小说家哈葛德(Haggard)的Montezuma’sDaughter(蒙特祖玛的女儿)叙述了专制统治下,墨西哥亡国的始末,揭露墨西哥无民主的黑暗现实。出于宣扬民主民权,又囿于其封建忠孝观,林纾把Montezuma’sDaughter译为《英孝子火山报仇录》,警醒国人专制与愚昧终将导致国家灭亡的结局。哈葛德(Haggard)的另一部作品NadatheLily(百合娜达)写一位苏噜酋长的故事,其中夹杂许多的神怪内容,体现西方民族的“尚武精神”。林纾把NadatheLily创译为《鬼山狼侠传》,呼吁怯懦的国民向西方民族学习,激励了国人奋起爱国保种。法国作家森彼得(Saint-Pierre)的代表作PauletVirginie(保尔和薇绮尼)通过对人物命运的动人肺腑的描写,歌颂了保尔和薇绮尼的纯真爱情,谴责了世俗的金钱观和等级观念。林纾将其翻译为《离恨天》,“离恨天”寓愁恨悲戚之意,译者以此暗示小说主角保尔和薇绮尼的爱情悲剧,也呈现出林纾阐扬爱情伦理,“倡导女权和妇女解放”的翻译目的和新思想[23]。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林译小说书名的“创译”顺应了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自然能够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
3.书名文体的选用
林纾以“仿古文”[24]译介外域小说,传播西方文化和先进思想,体现他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和反抗殖民文化侵略的思想意识。林纾自幼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古文造诣深厚,把语言文字看作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所在:“吾中国百不如人,独文字一门,差足自立,今又以新名辞尽夺其故,是并文字而亡矣。”[25]他始终坚持“古文万无灭亡之理……”[26]。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权力关系和话语网络里面,在与西方殖民文化的碰撞、交锋、抗拒、控制、角力过程中,林纾坚定地捍卫古文地位,即便在晚年饱受批评乃至激烈的言辞攻击,也未有丝毫改变。林译作品及其书名不仅简约晓畅,寓意深厚含蓄,流露出一种古文所追求的简洁利落的清新之气,而且缩短了翻译文本与接受主体之间的距离,减少国人对外国小说的陌生感和对域外文化的异质感,因此,林译作品及其书名能够吸引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的眼球。下面以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的题名为例,来解析林译书名的古文体风采。TheMerchantofVenice(威尼斯商人)被意译为《肉券》,有助于读者从原有知识“凭肉券买肉或取肉”联想到“凭借款契约割借款人身上的肉”,书名映射戏剧故事的情节和内容,便于读者理解;RomeoandJuliet(罗密欧与朱丽叶)被改译为《铸情》,意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犹如铸铁般坚固;Hamlet(哈姆雷特)被创译为《鬼诏》,讲述王子哈姆雷特按照父王之鬼魂下的诏书为父报仇的故事[23]。
四、林译书名的社会意义
林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顺应,促成了林译话语的社会建构作用。林译书名虽与原著之书名相去甚远,但拉近了西洋文学与中国读者的距离,促进西方文化和先进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林纾通过翻译开启民智、警醒国人,激发国人奋发图强、维新救国的热情和反抗外来侵略的斗志。比如,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出版后,产生极大的反响,全国上下反帝国主义的决心和热情日益高涨,这种爱国热情甚至感染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另一方面,林纾小说借鉴西方小说的叙事手法和结构方式是对中国传统小说艺术的一种自觉变革,林译小说为中国文人学习外国文学打开了一扇窗口,对当时及“五四”新文学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甚至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走向,在近代文化建设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林译所传递的西方现代人文精神,成为孕育反叛封建传统的现代精神之温床,例如,林译言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不如归》等作品表现出现代爱情观念的觉醒,肯定了女性享有爱情和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突显小说的社会批判功能,这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妇女观”的挑战,为当时的女性启蒙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林纾和林译作品对近代社会和文化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林纾生逢时局大变动、中华民族屈辱的年代,在民族危亡之际,他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大无畏精神,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林纾以不谙西文的古文家身份跻身于翻译界,本着“有益于今日之社会”的翻译目的,摒弃“小说为小道”的思想,用古雅而又灵活的文言创造性地翻译外国小说,为国人打开了一扇“睁眼看世界”的窗口,将西方小说推上了中国新文学之师的位置,使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悄悄蜕去“鄙俗”的陈套,换上了“雅”的衣衫[27]。胡适曾对林纾翻译给予充分肯定:“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狄更斯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因小传》等书。”[28]使用译文读者喜闻乐见的、符合他们语言表达规范的言语形式和文言文体是林译小说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林纾在译介西洋小说的同时,介绍外国小说的文章技法,并以此作为对读者作文的指导,在林译小说的示范和影响之下,我国近代小说创作与翻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五、结论和启示
批评话语分析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技术因素和翻译意识形态(translational ideology)因素的双重制约[29]。林纾翻译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服务的,他的翻译行为也不例外地受到其所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著书名是林纾进行意识形态操控的重要方面,他对翻译原著的选择、书名翻译策略的应用以及书名文体的选用均受其翻译意识形态的制约。显然,归化翻译策略是林纾翻译实践的选择,他通过有目的地改译或创译书名,向读者再现和强化自己需要的声音,同时湮没那些“无关紧要”的声音。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让读者了解林纾意识形态对其翻译实践的显著影响,揭示林译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也提醒读者以批判的眼光诊断性地阅读林译小说,客观公正地评价林纾及林译作品。
林纾作为引介西学的先锋,主张开启民智、西学救国、变法维新,以译作辉煌于当时,推动我国20世纪初的小说界革命,对中国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样一位中国近代的社会文化先驱、启蒙文学和白话文运动的先导者,只因旗帜鲜明地反对废弃古文传统,被新文化阵营定为重点打击的“守旧派”,显然有失公允。日本著名的晚清小说研究者樽本照雄先生力图推翻近百年来学界对林纾的不公正评价,在他的《林纾冤案事件簿》一书中指出“林纾冤案”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文学革命派给林纾加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二是在翻译史中将林译小说视为价值不高的作品,其中重要的理由包括他将戏剧、诗歌译作小说,随意删减作品内容等。樽本不仅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林纾冤案”说,还全面呈现了该冤案的现象始末[30]。樽本的“林纾冤案说”还原了林纾作为晚清社会文化先驱者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