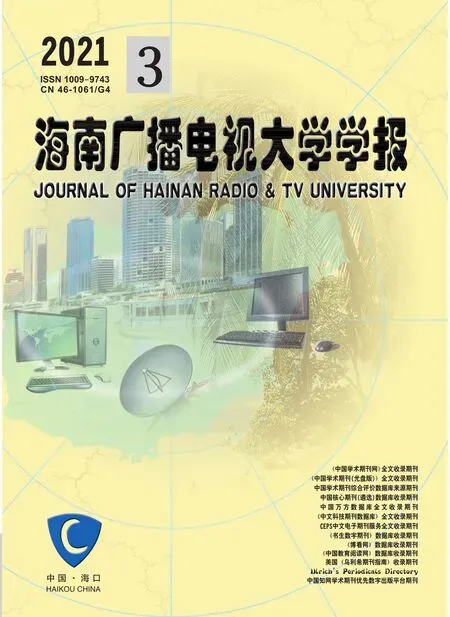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与戛纳电影节的关系
刘献弘,彭万荣
(武汉大学 艺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罗马尼亚电影对于大多数中国观众而言并不陌生。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译制片厂就陆续引进了一些罗马尼亚电影。比起《橡树,十万火急》这样的反法西斯战争片,拥有零星亲密片段的《多瑙河之波》显然更受观众欢迎。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的俗语:“朝鲜电影哭哭啼啼,印度电影唱唱跳跳,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罗马尼亚搂搂抱抱。”“搂搂抱抱”这个刻板标签,一直长存数年。罗马尼亚电影可以泾渭分明地划分为两个高峰和一个低谷时期。
第一个高峰期——20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初。一些名著改编电影和意识形态较重的电影获得国内外观众的青睐,频频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
低谷时期——20世纪最后三十年。1967年上台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以经济手段管理电影事业,导致电影活力不足。随着他的垮台与身亡,苏联解体带来的东欧剧变,以及外国电影的文化入侵,罗马尼亚电影一度陷入僵局,处于凝滞期。
第二个高峰期——21世纪初至今。罗马尼亚掀起新浪潮电影运动,以辨识度极高的作者风格再次立足于欧洲三大电影节。它们在威尼斯电影节收获较小,而政治性较强的柏林电影节、擅长挖掘新作者的戛纳电影节则更乐于伸出橄榄枝。柏林电影节我们权且不表,本文将重点研究戛纳电影节。
21世纪入围戛纳电影节的罗马尼亚电影不在少数,获奖作品集中于2004至2016年(具体可见下文表格)。克利斯提·普优、克里斯蒂安·蒙吉、柯内流·波蓝波宇等年轻导演带着他们青涩又生猛的作品闪亮登场,这场轰轰烈烈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运动也拉开了帷幕,从黑海边缘席卷到戛纳海岸。

表1 2004至2016年入围戛纳电影节的罗马尼亚电影
一、罗马尼亚新浪潮:民族电影与作者电影
罗马尼亚年轻导演们在国际影坛上的齐齐发力,被冠以“罗马尼亚新浪潮”的名号。和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新浪潮一样,年轻导演们力求摆脱以卢奇安·平蒂列为代表的上一代国宝级导演的影响,走出名著改编型优质电影的窠臼,扛着摄影机走上了破败喧闹的街头。在电影节的镁光灯下,他们被期许成为罗马尼亚的特吕弗、戈达尔与里维特。
对于“罗马尼亚新浪潮”的名号,不同导演持有不同的态度。克利斯提·普优在采访中直言不讳道:“根本就没有浪潮,甚至连这个概念也只是对新空泛主义的一种借用。” 克里斯蒂安·蒙吉也曾笑谈:“当有一位导演时,我们称有一位作者;有两位导演时,便算有了一种学派;有了三位导演时,我们说这是新浪潮。”(1)Pop D:Romanian New Wave Cinema.An Introduction, Mc Farland, 2014. P31.但不管他们赞许或反感,罗马尼亚新浪潮都立足于某种相近的电影语法、可套用的拍片公式。
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首先是民族电影的典型,这群年轻导演无疑是民族电影的扛旗手。将民族电影(National cinemas)一词拆开,便可得到“民族”与“电影”二个概念。何为民族(Nation)?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给出概念——“给某个仔细划定的地缘政治空间描绘为一个,具有共同身份、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想象的共同体”。(2)厉震林主编:《电影研究 性别、民族与文化探析 4》,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版,第14页。它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同根同源,还是文化层次的濡染继承。如此一来,便不难理解安德鲁·西格森给“民族电影”下的定义,他将其定格在“回家”与“出走”之间。换言之,民族电影具备内省性与外延性。它是植根于本土的民族遗产,反思在地历史与未来。同时,它立足于与其他民族的差异,在世界影坛上保持着独立地位。
戛纳电影节青睐的一定是可以反映罗马尼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民族电影。纵览2004—2016年间的获奖作品,不难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对前罗马尼亚社会的批判,齐奥塞斯库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人。最典型的作品就是让蒙吉声名大噪的《四月三周两天》,它反映了齐奥塞斯库时代违背人性的禁止堕胎法令,意外怀孕的女孩只好铤而走险,与黑市医生进行性交易以换取偷偷手术的机会。入围2009年戛纳电影节但爆冷失奖的《黄金时代的故事》,由六个短小荒诞的故事组成,折射了领导崇拜、阳奉阴违、物资匮乏等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问题。第二类作品聚焦于1989年的革命,以齐奥塞斯库的垮台为表现内容。波蓝波宇的《布加勒斯特东十二点八分》就是一部诘问历史之作。真人秀节目邀请了几位嘉宾共同探讨1989年12月22日那天,小城广场上到底有没有发生革命,这关乎市民们有没有在齐奥塞斯库登机逃离前抵达广场。结果自然是众说纷纭,真实历史藏在重重迷雾之中。卡塔林·米图雷斯库的《爱在世界崩塌时》以大胆笔触,虚构了一个小男孩密谋推翻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故事。他为了姐姐放弃偷渡出国,便想到暗杀领导人的计划。最后,在一番阴差阳错之下,齐奥塞斯库顺理成章地失去民心。第三类作品最为常见,揭露了当今罗马尼亚的社会问题。这些电影颇有贯通古今之味,毫不留情地批判了齐奥塞斯库时代的遗留问题以及日渐僵化的社会体制。普优的《无医可靠》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借独居老人之死切开了当代福利制度与医疗制度的漏洞。英年早逝的导演克里斯蒂安·内梅斯库留下伟大遗作《加州梦》,反应了罗马尼亚人民对美国士兵及文化的复杂态度。波蓝波宇的《警察,形容词》凸显了警察与长官的分歧,讽刺了人物沦为僵直体制化的工具。蒙吉先后拍摄了《山之外》与《毕业会考》两部杰作,前者折射了宗教与世俗的矛盾,亦不忘讽刺当代医疗制度的弊病;后者关注中产阶级的教育与移民问题,其言下之意是对如今罗马尼亚社会的极度不满,解决方法唯有下一代的逃离。
对于戛纳电影节上的新鲜面孔,笔者不可避免地想到一个关键词——电影作者。从“作者论”到“作者策略”,从“作者已死”到“作者依旧在野”,相关的电影论调一直在渊源绵长、此消彼长地发展着。倘若回到“作者”的起点来评判,那么这场黑海中掀起的浪潮有无数位电影作者在锐意掌舵。正因为由个体走向了集体,作者们表现出了相近的美学旨趣,才缔造了罗马尼亚新浪潮,而非意外掀起的小浪花。作者们的共通美学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现实主义和极简主义。
较之巴赞的现实主义、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罗马尼亚电影更贴近的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正如中国古人言:“国家不幸诗家幸”,意大利电影人在城市瓦砾和精神废墟中扛起摄影机,记录着战争时期的残酷与诗意。罗马尼亚电影人对现实主义的追求,来源于齐奥塞斯库时代的遗留伤痕。蒙吉、普优、波蓝波宇等作者们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恰好经历了集权统治下的个人崇拜、堕胎禁令、月经警察、打字机法案等创伤往事。当政治与生活变得不可分割时,便成为与影片主线水乳交融的存在。正如前文所提,罗马尼亚新浪潮作品都以现实主义见长,或是过去完成时的历史横截面,或是现在进行时的遗留性创伤。他们在电影中熟练使用长镜头,在连续的时空内表现连续的动作,以确保真实性。虽然他们不愿承认新浪潮运动,但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长镜头的偏爱。(3)Pop D: Romanian New Wave Cinema.An Introduction, Mc Farland, 2014.P41.明星并不是这些电影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事实上,年轻作者们更乐于寻找素人演员,他们无需扮演便已然是角色本身。
极简主义风格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术领域,从诞生之际就是繁冗华丽的表现主义的反义词。电影中的极简主义通常和导演的个人美学息息相关,如信奉“少即是多”的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罗马尼亚新浪潮中呈现明显的极简风格,则更多地来源于无心或无奈之举。年轻作者们资金匮乏、囊中羞涩,只好一切从简。为了和旧电影泾渭分明地划清界限,他们从一开始就拒绝了以塞尔玖·尼古拉耶斯库为代表的片厂大片。于是,我们看到电影的叙事基本局限于某段时间内,场景多半寒酸萧条、简单质朴,音乐与色彩也鲜有高调华丽。马里安·克里尚的短片《威震天》讲述了小男孩过生日的半天故事,镜头流转于家宅、田野、公路、公交等场所,一派粗犷天真的风味。波蓝波宇的电影大多拍摄于故乡瓦斯卢伊,尽可能地利用原生态环境与现有资源。普优擅长在封闭空间内讲故事,如咖啡厅、运货车、医院等场所。没有矫饰,没有美化,只有事物的原本模样。相比其他新浪潮导演,普优的电影台词偏多。但大量无意义的对话,更好地还原了毫无重点的庸常生活。
总的来说,罗马尼亚新浪潮搭上了戛纳电影节的顺风车,成功从本土走向了世界。虽然这场运动没有宣言、没有杂志、没有影评人,但年轻的作者们自发地组成了同一流派。集体记忆和文化烙印,让他们的民族影像存在某些共通之处。
二、戛纳电影节:虹吸效应与美学适应
戛纳电影节创办于1939年,因战争原因直到1946年才开始正式颁奖。设立初衷是为了抗衡威尼斯电影节,抗衡不仅体现在对优质电影的争取上,还体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两大政治阵营的博弈。彼时的威尼斯电影节借文化产物进一步巩固法西斯政权的意识形态。法、英、美三国联合起来,策划了戛纳电影节。主办人员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电影展,不仅仅是为了独裁者做宣传。”(4)Valck M de:Film Festivals. from European Geopolitics to Global Cinephilia.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7.P49.随着国际格局的转变,随着好莱坞霸权的确立,戛纳电影节慢慢绕开了美国,挑选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试图与好莱坞电影竞争。在电影节上放映电影,不仅不必依赖中间发行商,还构建了跨文化交流的良性国际环境。久而久之,戛纳电影节成为全球电影节争相模仿的范本。它是每年一度的行业聚会,把来自全世界的优秀电影人聚集一堂。从融资到制作再到发行的一条龙服务,形成虹吸效应,引来了 “第二世界国家”罗马尼亚的资金短缺的电影人。所谓“虹吸效应”,原是物理学名词,后引申为:某区吸走其他区域的资源,从而增强自身综合实力,削弱其他区域竞争力。在“走出去,引进来”的过程中,罗马尼亚本土电影业失去了优势。罗马尼亚电影频频参与戛纳电影节,是该国电影人主动融入欧洲、走向世界的文化心态的反映。
蒙吉、普优、波蓝波宇等电影作者的出现,也恰好印合了戛纳在全球范围培养嫡系导演的策略。戛纳的造星计划是循序渐进的:首先,挑中的导演们的新片项目会入选戛纳电影节的创投单元;接着,成片会入围戛纳的平行单元;后续作品会入围官方次级单元;待时机成熟,该导演的作品会入选关注度最高的主竞赛单元。近年来,戛纳成功培养的嫡系导演有:日本的河濑直美、加拿大的泽维尔·多兰、土耳其的努里·比格·锡兰、泰国的阿彼察邦等等。偶尔,嫡系导演也会发挥失常。但戛纳对他们低于水准的新片仍然持有包容态度,充分体现了一保到底的关照机制。
戛纳为何挑中蒙吉、普优、波蓝波宇,并将他们作为新的嫡系导演进行培养?其一是因为他们的影片质量过关,并引领了和而不同的新浪潮美学。影片质量固然重要,但电影人的国别、文化、身份属性也是重要考虑因素。1990年前后,东欧共产主义集团解体,从而激发了罗马尼亚电影的创作高峰,也为十年后在国际电影节上的厚积薄发打下坚实基础。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往事,成为年轻作者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宝库。如果把戛纳电影节比作一座博物馆,那么罗马尼亚电影是它们梦寐以求的,来自东欧的历史陈列品。戛纳电影节在千禧年以后对东欧的兴趣,正如其在20世纪50年代对日本、20世纪60年代对意大利的兴趣一样,是对新的地域版块与历史伤痕的收集。蒙吉凭借《四月三周两天》问鼎金棕榈后,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我在早些年拍摄同样的电影,获得金棕榈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现在,我利用了人们对罗马尼亚电影日益增长的兴趣。”(5)Wong CH-Y:Film Festivals: Culture, People, and Power on the Global Scree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1.P95.可以说,戛纳电影节更看重的是蒙吉等人背后的“罗马尼亚”名片。
戛纳电影节的品牌构建之下,有一套关于美学倾向的法则。在《东方学》中,萨义德认为,“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6)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页。如果把他陈述的范围从全球改为欧洲,那么东欧电影与西欧电影节之间存在着这种不平等关系。通过对东欧电影的凝视,西欧电影节确立了自身优越性,满足了对非西方文明的想象构建。
在戛纳亮相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从不吝啬对“西方”的理想化建构。对他们而言,本土是无疑的异托邦;西方是存疑的乌托邦。没有比《幸福在西方》和《加州梦》更为直白表达向往的电影标题:前者顺应罗马尼亚的移民热潮,在三段格式中尽显讽喻功底;后者以辩证的视角,探讨了美国梦的激情与幻灭。而在《无命钱》《威震天》《爱在世界崩塌时》这些电影中,不断出现西方元素:蜘蛛侠、麦当劳、宣传册等等。即便是在后新浪潮电影《毕业会考》中,导演也借助中产阶级医生之口,期盼更为年轻的下一代人能离开这个国家。“逃离”似乎成为了被乐于表现的母题之一。这些议题无一例外地落入“东方主义”的视角中,尤其符合西方观众及影评人的口味,后者会在观影中确立自身文化的优越性。
阿尔都塞把马克思主义下的国家理论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电影隶属于艺术,即是“文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为“阿尔都塞派”成员之一,特里·伊格尔顿借助审美学的桥梁,把“身体理论”和“意识形态”搭建在一起。质言之,意识形态以软性方式,控制了身体与个体。纵览戛纳电影节上展映的新浪潮电影,出现较多的电影辞格是“领导者”。
齐泽克认为,“领袖只能通过拜物教的代表而存在,也只能存身于拜物教的代表之中。”(7)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新浪潮电影中的领导者家国同构,在外是从不正面出场的齐奥塞斯库,在内是或永久缺席或关系欠佳的父亲们。领导人出现次数较多的新浪潮电影,当属《爱在世界崩塌时》。在电影开端处,两名高中生不慎打碎了齐奥塞斯库的雕像,从而接受了学校的规训与惩戒(被送到工读学校改造)。这一行为充满了预兆性,直白地暗示了片尾处齐奥塞斯库的倒台。电影中段,普通人装扮成齐奥塞斯库的模样,以小丑般的举止逗弄着两个孩子。电影尾声,齐奥塞斯库的形象终于出现在了电视直播里,被屏幕外无数双群众的眼睛凝望。这些见证者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凝视电视里领导人的样子,与我们凝视电影屏幕的样子如出一辙,由此构成了嵌套的观看行为。在《黄金时代的故事》中,齐奥塞斯库如同《蝴蝶梦》中的瑞贝卡,他从未出场却在暗处操纵着所有人。神秘的领导人是“基层视察的领导的领导”,是会晤照片里矮小的男人;是消灭文盲的指挥者;也是导致普通人吃不起猪肉/卖瓶子赚钱/偷公家鸡蛋的元凶。从短片《威震天》中,能一窥家庭中父亲的缺席。单亲家庭中成长的男孩迎来了自己的8岁生日。他的愿望看似是麦当劳套餐中的玩具,其实是期待与父亲团聚。从母亲冷漠的态度,我们可以推测男孩的父亲并未付到应尽的责任。影片结束时,男孩依旧等待着缺席的父亲,其难度不亚于“等待戈多”。
由于罗马尼亚导演们的个体倾向,使中性的电影辞格受其影响,成为建构意识形态的工具。这种创作倾向恰好适应了戛纳电影节的口味。
三、总结:合谋与共赢
戛纳电影节需要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因为它象征着电影节国际化、民族化策略的成功。这些新浪潮电影顺应”泛欧洲化“潮流,以独树一帜的民族电影,满足了电影节的后殖民主义口味,也征服了西欧艺术影片的主流观众。戛纳将蒙吉等人培养为嫡系导演,亦是一次稳赚不赔的买卖。以波蓝波宇为例,从《布加勒斯特东十二点八分》起,他就在影评人和影迷中逐渐形成认可度和知名度。《警察,形容词》则是巩固作者地位、走向国际市场的一步妙棋。2019年,他的新作《戈梅拉岛》虽口碑平平,但依然入围戛纳电影节,并在首映前吊足了观众的期待。自此,波蓝波宇的个人品牌已在戛纳电影节的帮助下得以建立,他也心照不宣地把新作投放给戛纳电影节,而非存在竞争关系的柏林或威尼斯电影节。他只是戛纳手握的热门作者导演中的一员,依靠培养导演的策略,戛纳不断加强着自身的精英氛围。
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也需要戛纳这一平台。无论是成本资金、国际声誉还是目标群体,都是本国难以给予他们的馈赠。罗马尼亚新浪潮的电影人早已顺应“泛欧洲化”的潮流,转变对国内外观众的期待倒置。蒙吉在拍摄《四月三周两天》后,跑遍了罗马尼亚的小镇,期待影院的上座率。时隔数年,他决定《山之外》不在罗马尼亚本土上映。和他做出相似选择的新浪潮导演有不少,他们逐渐认清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这些讲述罗马尼亚现实的电影,征服不了罗马尼亚观众。或许《每日新闻报》对蒙吉的采访,正好能概括他与同行们的心理根源:“我们想继续当作者,以及一个真正的欧洲人。”(8)Pop D: Romanian New Wave Cinema.An Introduction, Mc Farland, 2014.
与其说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是被戛纳电影节挑中的幸运儿,不如说它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双方存在着合谋与共赢的关系。2017年,蒙吉受邀担任第70届戛纳电影节短片和电影基石单元的评委。近年来,罗马尼亚电影已不再是戛纳电影节的宠儿。在西欧媒体看来,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在惊艳四座后,已逐渐恢复了平静。罗马尼亚电影是否还能再次在戛纳掀起巨浪,未来是否会有新鲜的罗马尼亚作者们涌现,一切只能交付给时间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