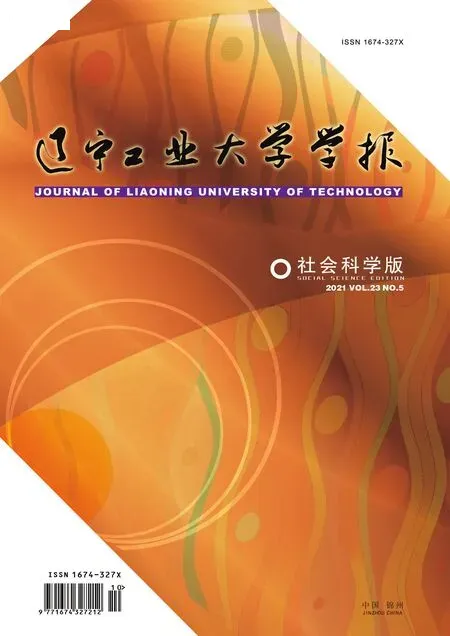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辽宁省红色文化资源英译研究
刘艳华,曹 静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阜新 123000)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众所周知,辽宁省丰富、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俯拾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将辽宁省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英译并适时“推出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生态翻译学中的三维转换理论,从“语言维度”“文化维度”“交际维度”对辽宁省几个典型红色文化资源地(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葫芦岛市塔山阻击战纪念馆、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等)的红色文化资源中的文字部分进行英译研究,以期进一步提高译文语言的准确性、规范性、可读性,从而助力红色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提升辽宁省红色文化的对外形象,弘扬红色文化,发扬红色文化精神,为辽宁老工业基地新一轮振兴作出贡献。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
胡庚申教授指出:“生态翻译学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抑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2]由此,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理论”,将翻译活动设定在生态学的背景之下对其进行解读。在翻译过程中,强调翻译的中心是译者,翻译的过程是适应和选择交替的过程。适应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的内在文化及其所属的社会环境的交替适应、对翻译过程中源语和目的语在其各自生态环境中的交替适应。胡教授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包括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源语自我认同的适应和目的语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在内的多个方面,以多维度转换方式阐释和探讨翻译现象。
为了使中国的红色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基于红色文化资源的特殊性,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中的“三维转换”翻译策略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英译,有利于红色历史文化和红色资源信息的对外传播,从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红色文化。
三、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辽宁红色文化资源英译策略
如果说将植物从一个环境移植到另一个新的环境并且使植物适应新的环境而存活下来才是成功的移植,那么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就是将语言从一个语境移植到另一个语境并且使其能够适应新的语境,这就是有效、成功的翻译,也就是译作生态适应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即“三维”[3]。
(一)语言维
语言维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语言表现的形式对目的语进行适应性转换。语言表达的习惯和表达规范因不同语系而不同,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将英汉两种属于不同语系的语言进行符合其各自表达习惯和表达规范的适应性转换,使源语和目的语能够更加适应新的翻译语境,从而达到有效传递原文信息的目的。
在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一个碑牌上有这样一段介绍,原文:“1932 年9 月16 日上午,日本抚顺守备队、宪兵队、警察署和炭矿防备队倾巢出动,将平顶山村二千七八百名手无寸铁的平民驱赶到村外平顶山下,进行了集体屠杀。”译文:“On the morning of September 16,1932,the Japan Fushun garrison,the police department and coal mine defensive teamed out in force.About 2 700 or 2 800 unarmed civilians were driven out of the village Pingdingshan and the Japanese committed a mass killing.”本句中存在的翻译问题是,译文中忽略了英汉两种语言中地点排序的不同规则:在汉语中,地点顺序往往依据“先大后小”的原则;而英文地点状语的排列语法规则是小地点名词在先,大地点名词在后。按照以上规则,“the village Pingdingshan”应该译为“the Pingdingshan village”;“日本抚顺守备队”应译为:“the Japan garrison in Fushun”更为适合。
因此,原文的翻译修改为“On the morning of September 16,1932,the Japan garrison in Fushun,the police department and coal mine defensive teamed out in force.About 2 700 or 2 800 unarmed civilians were driven out of the Pingdingshan village and the Japanese committed a mass killing.”更为恰当。
(二)文化维
源语和目的语的文化内涵在各自的性质和内容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于源语和目的语文化内涵的理解、阐述和翻译便产生了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文化维适应性选择重点强调源语与目的语在文化传递方面的转换,防止单纯从目的语文化视角考虑问题而造成原文理解偏差[4]。在辽宁省的许多红色旅游景区内,对景区的介绍常常蕴含大量的文化信息,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务必要从中西方语言文化思维的基础出发,时刻考虑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将原文中的文化内涵一一解读清楚,再进行翻译,以免引起目的语读者的困惑。
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中,有这样一段对辽沈战役发起的文字介绍,原文:“On September12,1948,the Northeast Field Army (organized in August 1948)began the Liaoxi-Shenyang Campaign by moving southward to the Beijing-Liaoning Railway.It captured Changli,Beidaihe,Suizhong,Xingcheng and Yixian in succession and isolated Jinzhou.”这个句子中的“发起战争”用了“begin the Campaign”。虽然在语义上不影响读者理解,但是begin 表示开始,一般性用语,强调时间的开始。众所周知,辽沈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其地位之重要、规模之浩大、战争之强度和战火之猛烈在这里用“begin”一词难以表现出来,不能体现源语所承载的文化概念,无法表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面对当时严峻形势时所表现出的英勇战斗精神。因而,此处的翻译只注重源语在译为目的语时的基本意思,忽略了其承载的文化内涵信息的传递。应该将其修改为“ launched a fierce campaign in Liaoxi-Shenyang by moving...”更恰当。红色文化文本蕴含许多历史重大事件、历史信息等内容,译者在翻译时应尽量保留源语中的文化内涵[5]。
在葫芦岛市塔山阻击战纪念馆里,有这样一段对塔山狙击战的介绍,原文“我参战部队以英勇无畏、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顽强固守、反复争夺,抗击了国民党陆、海、空军的猖狂进攻和轮番轰炸,歼敌9 000 余人。”原译文为:“Our partaking troops fought boldly and heroically and defended tenaciously though undergoing furious attacks and waves of bombing from Kuomintang’s naval,land and air forces,finally annihilating more than 9 000 enemy troops.”
在这一段简介中,提及了诸如“我参战部队、国民党”等几个具有丰富文化历史信息的词语。对于很多不是非常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外国友人来说,文化背景的缺失会严重影响读者在阅读信息时对译文的有效理解。塔山狙击战是辽沈战役中的关键战斗之一。辽沈战役参战部队有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这里的“我参战部队”指的是代表共产党军队的“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国民党则指的是参加此次战斗的国民党军队11 个师。因此,将译文修改为:“Our partaking troops (the Northeast Field Army-2nd Legion) fought boldly and heroically and defended tenaciously though undergoing furious attacks and waves of bombing from Kuomintang’s naval,land and air forces (11 divisions of the Kuomintang Army),finally annihilating more than 9 000 enemy troops.”更为恰当。
译者在翻译这段极富历史文化的简介中应适当增译相关历史文化信息,或者在后面标注其相关的文化历史背景,以实现译文提供有效文化信息的传播功能,这样会更有利于读者对景区展示内容承载的文化概念内涵的理解。
(三)交际维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实际上就是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除了文化维适应性选择所强调的源语与目的语在文化传递方面的转换,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还重点强调源语与目的语在交际层面的转换,在译文中能否体现源语中的交际意图就成为了关注重点[6]。翻译时,译者通过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将译文简化并删除对于读者来说意义不大的源语信息内容,使译文得以优化整合,从而更符合目的语的表达规范及语言习惯,进而在满足目的语读者阅读要求的同时,准确地传递源语的语言文化色彩,实现源语与目的语交际的目的,从而实现有效翻译的目的[7]。
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运动厅中有这样一则介绍,原文是“为对全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爱国教育,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以各种方式和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统筹组织,在全国人民中广泛深入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译文为:“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resisting U.S.aggression and aiding Korea,arouse their patriotic enthusiasm and support the Korean War in different ways,Chinese People’s Resist-America-Aid-Korea Federation organized vigorously the Resist-America-Aid-Korea Movement by making comprehensive arrangement among the people extensivel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这里的“为对全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爱国教育”这句话被翻译后容易产生歧义,“the Chinese people in resisting U.S.aggression”很容易让译文读者理解成为对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中国人民进行爱国教育,而事实上原文想表达的意思是“要基于抗美援朝战争的事实对广大中国人民进行爱国教育”。因此,这里改为“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among Chinese people through the movement to resist U.S.aggression and aid Korea”更为准确。另外,本句中的其他译文对于不是十分了解中国抗美援朝历史的译文读者来说,也容易产生理解上的偏差,因此本句整体修改为“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among Chinese people through the movement to resist U.S.aggression and aid Korea,the Resist-America-Aid-Korea Movement is organized vigorously by Chinese People’s Resist-America-Aid-Korea Federation among the people extensivel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o arouse their patriotic enthusiasm and support the Korean War in different ways.”更为合适。修改后的译文既体现了中国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又表明了基于抗美援朝战争对国人进行爱国教育的事实,从而再现了原文蕴含的中国红色文化资源内涵,使目的语读者对中国这段抗美援朝的历史有所了解,进而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增强其对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认知。
四、结语
对辽宁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实地调研、识别、整理和归纳,运用“三维转换”理论,对已有源语红色文化资源译文中存在的翻译问题进行深入剖析,采用灵活的翻译技巧和策略,提供更加规范、恰当、得体的参考性译文。一方面,可以丰富红色文化翻译研究内容,使之进一步走向深化和系统化,规范基于“生态翻译学”下的红色文化资源翻译的标准和原则、策略和方法,更有效地指导红色文化资源的翻译实践;另一方面,辽宁红色资源规范化英译研究,有利于提高红色文化资源翻译的质量,提升辽宁红色文化对外宣传形象,推动作为老工业基地的辽宁省的经济振兴,进一步展现其独特、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