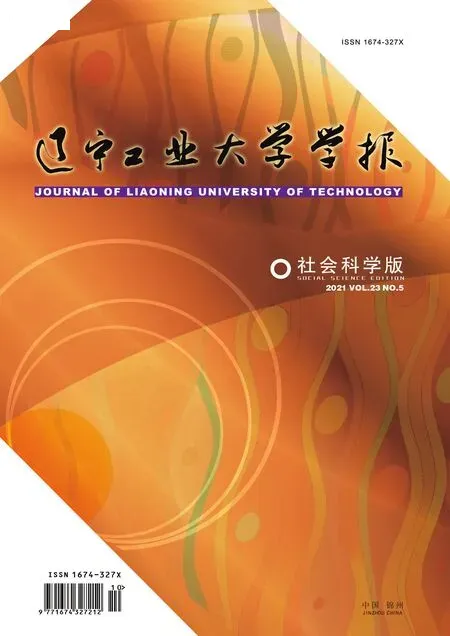马克思对资本逻辑逆生态性的批判及其价值
范 雪,刘建涛
(辽宁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1)
当今社会,资本已然把现代社会关系纳入自己的运行范围,它将无限增殖的发展原则投入到人与自然之间,对生态造成了伤害,具有难以克服的逆生态性。迄今为止,马克思对资本的这种逆生态性分析最为深刻。因而深入分析马克思对资本逆生态性的批判对于我们辩证审度资本,开创绿色发展道路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一、资本逻辑逆生态的表现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固有规律和必然发展趋势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在经济环节中得以体现,我们称这种规律和趋势为资本逻辑。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资本的本质性逻辑就是不断地扩大自身,增殖自己。但是资本的这种扩大与增殖是无限度无节制的,这就与有限的自然资源、环境处于不可调和的境地,一旦资本突破自然设定的界限,就必然会导致对自然的破坏,进而影响到人类的生产生活。资本逻辑对生态的破坏如下。
第一,自然资源枯竭。马克思指出,出于扩张的本性,资本自身的运动必然要冲破自然界为其设置的种种自然界限。因此,在资本逻辑视域下,作为资本范畴人格化的资本家或企业家贪婪地追求剩余价值的更多获取,他们将目光投向于任何可以获取利益的自然领域、社会领域,并将物质无限性的思维代入到自然界中,将自然界看作是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这种错误认识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实践中导致了“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1]。
第二,环境污染严重。资本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不断地把自然界货币化和商品化,而对资源利用之后所剩下的废渣、废水、废气等废料随意地排放到自然界中。这样一方面使得资本的环境成本社会化,另一方面也严重恶化了自然环境。马克思以伦敦不会处理450 万人的粪便而将粪便排入泰晤士河为例子,严厉地批判了因废物排泄导致环境污染的不良后果。此外,空气也和水一样遭到了污染。譬如在当时的英国,许多城市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
第三,自然生产力遭到破坏。以上两种现象导致的后果就是自然生产力遭到破坏,导致经济持续发展与循环发展的自然根基也被资本损害。以土地生产力为例来讲,譬如农业资本家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取尽可能多的产品,便在土地上使用了大量的农药化肥,过量的化学物质导致了土壤的生态结构失衡。因此,马克思认为,提高土壤肥力必然会阻碍土壤肥力的持久发展,这是同一个过程。并且这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难以克服的生产悖论。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因自然生产力遭到损害而受到阻碍,乃至陷入衰退,因为二者本来就是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二、马克思对资本逻辑逆生态性的批判
马克思从三个方面对资本所具有的逆生态性进行了深入批判,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逆生态性。资本家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目的是一致的,这就是不断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他们只专注于生产的商品及其量的扩展,只注重抽象的一般财富的积累,缺乏对自然的人性化利用。从而使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2]157,即劳动者的劳动产品、自然界与劳动者自身相对立。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方式发生了自我异化。我们知道,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需要通过劳动进行连接,当作为中介的劳动发生了异化,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就产生了裂缝或断裂,进而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异化,自然界退化为纯粹的有用性,成为资本自我增殖运动所使用的材料,沦为了被资本支配和改造的角色。人与自然的地位发生了颠倒,人被异化为绝对的主体,自然被异化为无生命的客体,二者相互否定,自然失去了自己的活力和持续发展的动力,人也无法发现自然界本质上是感性存在着的人,人因此失去了自己作为人的本质。从此,二者彼此产生了尖锐的对立,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局。马克思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异化劳动的作用下被深度异化,这种异化渗透在自然的各个领域,从而造成了土地肥力退化、森林减少、河流污染等。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逆生态的性质,随着异化程度的加深,生态失衡的现象便会层出不穷。
第二,资本主义制度的逆生态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出维护其运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资本主义制度保障资本运作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制度也由此具有了逆生态的性质,扩大了资本对自然破坏的广度和深度,使得资本增殖与生态破坏呈现正相关。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制度里忠诚地效力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最多的价值这件事情上,只注重眼下利润的获得。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不断扩大再生产,提高产业技术,以此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获取更多剩余价值。譬如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和科技开发与运用制度就是如此,通过市场经济制度把环境各要素纳入市场,并对其进行市场定价和交易,这样自然界就更加退化为有待技术处理的材料,自然环境就会更加恶化。马克思对这种情况给予深刻的批判,他指出:“一切生灵,水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植物,都成了财产;但是,生灵也应该获得自由。”[2]52而支配科学技术开发和实际应用的是资本逻辑而并非人们的美好愿望,若某项技术有利于环境而不利于资本,那么这项技术也是难以实行的。总之,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相互强化和共谋,二者携起手来展开对自然界的生态掠夺,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然界的双重不可持续性。
第三,资本主义消费的逆生态性。生产与消费是资本流通过程中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生产环节中产生的剩余价值最终要通过交换和消费环节才能得以实现。资本逻辑是生产劳动的内在驱动力,因而生产劳动追求资本无限增殖,这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绝对目的,由此必然导致消费的异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消费被纳入资本的运动之中,成为资本增殖的一个必要环节。资本家为满足自己的获利需求而制造出许多“虚假性需求”来诱惑民众进行奢侈消费和炫耀性消费,使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偏离正确的轨道。这种非理性的消费主义本质上是马克思批判的拜物教观念在消费领域的延续。但是,资本家为了资本的增殖,不断地通过各种形式向民众灌输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使他们在异化的消费中忘却精神的追求而认同资本运动的逻辑,将“我消费故我在”的消费理念作为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而那些从自然界中获取的生活和生产资料经过消费环节又部分地以垃圾和废弃物的形式排入自然界,至于这种垃圾和废弃物是否破坏环境,甚至超过环境的承载力和净化力则不在这种消费方式的考虑之内,它奉行的理念就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3]马克思对这种消费主义的观念给予了严厉批判,他指出:“工业的宦官迎合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2]224,以便从他的口袋诱骗货币这种“黄金鸟”。而在这种异化的消费方式中,自然界成为了不用偿付任何费用的“垃圾场”。当异化消费的程度足够深时,当排放的废弃物数量超过了生态的负荷能力时,生态危机就会随之而来。
三、马克思对资本逆生态性批判的价值
资本逻辑的场域不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在世界各个角落都不难发现资本逆生态的趋势。因此,我国需要充分理解马克思对资本逻辑逆生态及其成因的批判,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解决生态问题奠定制度前提。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利润至上的本质,它的逆生态性与自然发展的规律是相违背的。习近平深刻地指出,各种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深入反思”[4]10。我国生产目的与资本主义不同,在制度上具有解决各种环境问题的优势。资本主义将人与自然界作为材料纳入自身增殖的场域中,一心只为资本的增殖,走的是非理性的破坏式发展道路,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只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引入和利用资本便服从于这个目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人为本,为实现自然界的生态性、经济性、社会性的统一创造了根本的条件,它在根本上就是要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我国要构建的是把生产、生态、生活三者融合为一体的生态文明式发展道路,并大力推进环境制度和科技制度的生态化改革,改善环境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能与自动解决各种环境问题划等号,仍需要我们从观念、具体制度等各方面进行探索,以不断提高环境治理水平,促进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辩证审度资本,为资本的运行划定生态界限。若任资本在我国肆意发展而不加限制,那么资本的破坏性本性就会得到无度释放,从而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退化。因此,为了合理利用资本,我们必须谨慎地接受,而不是全盘地拒绝。从利用资本的角度讲,资本仍然是现代社会发展生产力的强劲动力,金融资本更是整个社会生产的神经系统,连接着生产和消费。因而我们必须要充分利用资本,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淘汰落后产能,健康发展金融资本对生产和产业的引导与支持作用。从限制资本任意扩张的角度讲,尽管资本逻辑有创造巨大生产力的文明作用,有利于市场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建立。但如果放任资本向社会的所有领域扩张,那么就会对社会、生态乃至整个国家与民族造成严重的危害,至少要限制资本向医疗、教育、生态领域过度扩张。资本如果在生态领域肆意横行,松懈对它的监管,那么生态环境必然会遭受重创。比如在2020 年,与敦煌阳关林场签订租地协议的飞天科技生态园不顾确保林地可持续发展的条例,为了发展公司的鱼类养殖产业,擅自将河流截道,导致河流下游的泉眼被风沙封堵,河道内堆积满泥沙,河道两旁植被由于缺水逐渐退化,河流周围动植物的生存环境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在2020 年12 月11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监管的重点。这就要求党和政府为资本的运行划定生态界限,制定生态制度,要求企业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使资本在合理的范围内运行。
第三,破除拜物消费观念,推动绿色价值观变革。拜物消费是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诱因之一,因而我国必须要破除这种异化的消费观念,倡导绿色、适度的消费理念。对此,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4]15。一方面,我们要冲出消费异化的围栏。在拜物思想的影响下,人们被“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所迷失,失去了自我判断,只看到商品所呈现出来的图像、符号等等,盲目地追求符号的意义而不关注自我的真实消费需求。消费者往往沉溺于异化消费的逻辑怪圈,意图通过获得消费商品的交换价值来填充精神的空虚。习近平对社会上的浪费和奢靡现象进行了严厉痛斥,强调务必狠刹社会浪费之风。同时,很多人将拥有金钱的多少作为标准来衡量自身幸福与否,更有人热衷于金融投机,利用虚拟资本赚取高额差价。这样的拜物现象不单单导致了人的物化,甚至由此还导致了生态的破坏。因此,习近平提倡人们回归最本质的消费理念,提升劳动的幸福感,走出消费异化的怪圈。另一方面,倡导绿色的消费价值观。我国从制度和政策方面对绿色的生产和消费进行了积极引导,并提出了对塑料污染等各种污染的治理措施,积极培育绿色消费的新模式,比如我国对一些塑料制品已经提出明确的禁限标准。同时,广泛培养公民绿色的消费价值观念,加强对公民的道德舆论引导,强调节俭、适度、绿色消费,避免消费异化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