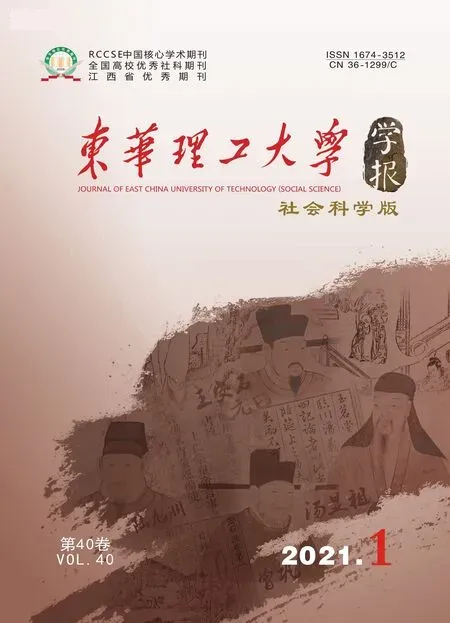共荣与互鉴:元代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文学特色
王 硕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元代文人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既要面对纷纭的世事,又要坚守文人的独立品格。蒙古铁骑南下,在带来灾难与战争的同时,也带来民族大融合。草原民族勇猛进取的文化因子,为中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在这种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元代文人感受着时代变迁,科举断行,入仕机会减少,文人更为注重自我的人生价值。大元王朝统一全国,混一四方,他们既学汉法理政,同时又最大限度地保护蒙古贵族利益。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为元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化环境,元代文人的创作也带有多民族融合的新特点。探究元代特殊的文化环境,有益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元代文人生活与文学的创作。
1 草原民族的文化习俗
元代是一个民族大融合、大聚居的时代,蒙古草原的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碰撞、冲击中互相渗透:一方面,农耕文化为蒙古人民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与中原传统文化的礼仪制度;另一方面,中原文化也受到草原文化的冲击,渗透着蒙古草原的习俗与文化品格。这种特殊的文化环境也影响到元代文人的生活,文人的内在心理也随之发生微妙变化,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带有新的草原风味。
草原民族的道德标准、思想观念与中原文化大不相同,很多传统习俗为蒙古人终身信奉,成为流淌在他们身体里的文化血液。草原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较为恶劣,这塑造了他们强健的体魄与坚强的品格,形成了勇武善战的民族性格。《出使蒙古记》中记载:“他们的小孩刚刚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骑马和驾驭马,并骑在马上飞跑,同时大人就把适合于他们身材的弓给他们,教他们射箭。他们是极为敏捷和勇猛的。”[1]他们风俗淳朴,诚实守信,即便无人监督,他们也会遵守各项制度,“其俗,淳而心专,故言语不差;其法,说谎者死,故莫敢诈伪”[2]6。这种规定似乎过于严厉,但却能体现蒙古人的信义与坚守。每次征战时,蒙古人对背信弃义之城都会痛下杀心,就与这种习俗有关。他们长年生活在草原,无边无际的野草不仅哺育着牛羊,也是他们辨认季节的一种指示,“其产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八月又枯,草之外咸无焉。”[2]2他们根据野草自然生长的规律来判断季节流变,这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可以弥补他们对某些地理知识的空缺,“其俗每以草青为一岁,人有问其岁,则曰几草矣。亦尝问彼月、日,笑而答曰:初不知之,亦不能记其春与秋也。每见月圆为一月,见草青迟迟,方知是年有闰月也”[3]2。这些习俗是早期游牧民族所特有的,影响到草原民族日后的生活与发展。
成吉思汗于1206年统一蒙古诸部,在斡难河源即皇帝位,建立大蒙古国。此后他一直坚持对外扩张,先后灭掉西夏、金与南宋,不到八十年就完成了全国统一,改变了世界历史格局。蒙古族热爱音乐和舞蹈,即便他们外出作战也带有歌舞团队,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忽必烈汗与乃颜对战,“乃颜及其众见之大惊,立即列阵备战,当两军列阵之时,种种乐器之声及歌声群起,缘鞑靼人作战以前,各人习为歌唱,弹两弦乐器,其声颇可悦耳。弹唱久之,迄于鸣鼓之时,两军战争乃起,盖不闻其主大鼓声不敢进战也”[4]188。《蒙鞑备录》中也有类似的叙写:“国王出师,亦以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弦等弹大官乐等,四拍手为节,甚低,其舞甚异。”[2]8作战前蒙古人竟以歌舞为始,这些景象与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奋力厮杀迥然不同。在每次战后必有封赏,“奖赏诸臣战功之事,其为百夫长有功者升千夫长,千夫长升万夫长,皆依其旧职及战功而行赏。此外赐以美丽银器及美丽甲胄,加给牌符,并赐金银、珍珠、宝石、马匹。赐与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盖将士为其主尽力,从未见有如是日之战者也”[4]196。游牧生活让他们尤为看重眼前的物质财富,喜欢以简单的方式获得物品,“他们保有财物,是绝不放松的,而以财物给人,则最为吝啬”[4]17。从元朝的理财政策可以看出他们注重经济财物,一些权相重臣皆有较强的理财能力。
蒙古人热爱饮酒,热情待客,他们在宴会中畅饮,极为欢快,很少被礼仪束缚。宴饮歌舞是蒙古族人的重要活动,“喝得酩酊大醉被他们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即使任何人由于喝酒太多而因此致病,这也不能阻止他以后再一次喝酒”[4]16。耶律楚材就曾劝止君主饮酒,“上素嗜酒,晚年尤甚,公数谏不听,乃持酒槽之金口曰:‘此铁为酒所蚀,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脏,有不损耶!’上悦,赐以金帛,仍敕左右日进酒三钟而止”[5]87。酒伤身体,人人皆知,但皇帝仍不能以此为戒。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即便身患重病也要出门狩猎,“辛丑春二月,上疾笃,脉绝,诸药不能疗。”等身体有所恢复,“冬十一月,上勿药已久,公以太一数推之不宜畋猎,奏之数回,左右皆曰:‘若不骑射,何以为乐!’猎五日而崩”[5]88。他们与中原文士不同,汉族人在闲暇时可以读书作文,而蒙古人重要的寻乐方式是饮酒、狩猎,生长在马背上,想要放弃这些生活方式实属不易。《蒙鞑备录》中的相关记载,对于蒙古族人的民族性格体现得更为明显:
鞑人之俗,主人执盘盏以劝客,客饮,若少留涓滴,则主人者更不接盏,见人饮尽,乃喜。如彼击鞠,止是二十来骑,不多用马者尔,恶其哄闹也。击罢,遣人来请我,使人至彼,乃曰:今日打球,如何不来?答曰:不闻钧旨相请,故不敢来。国王乃曰:你来我国中,便是一家人。凡有宴聚打球,或打围出猎,你便来同戏,如何?又要有人来请唤!因大笑而罚六杯,终日必大醉而罢。且每饮酒,其俗邻坐更相尝换,若以一手执杯,是令我尝一口,彼方敢饮;若以两手执杯,乃彼与我换杯,我当尽饮彼酒,却酌酒以酬之,以此易醉。凡见外客醉中喧哄失礼,或吐或卧,则大喜曰:客醉,则与我一心无异也。我使人相辞之日,国王戒伴使曰:凡我好城子多住几日,有好酒与吃,好茶饭与吃,好笛儿、鼓儿吹着打着[3]9。
蒙古人宴饮聚会,打球娱乐,即使没有受邀也可自来,这些让来自礼仪之邦的汉人难以理解。他们饮酒作乐尽兴而归,不重礼仪,无尊卑高下,这和汉族官员有目的性宴饮截然不同,终日以大醉为乐事体现出蒙古族豪放不羁、自由洒脱的性格。宋代以文治国,倡导文人注重享乐,如晏殊的“及时行乐”主题就有所反映[6],蒙古人的宴饮之乐也影响到元人的休闲生活。
2 汉法治国中的文化差异
蒙古人早期并无文字,以大汗的法令与习俗治理各部。他们的文字由佛教人士所创,“元起朔方,本有语无字。太祖以来,但借用畏吾字以通文檄。世祖始用西僧八思巴造蒙古字。然于汉文,则未习也”[7]460。“因金国叛亡降附之臣,无地容身,愿为彼用,始教之以文书,于金国往来,却用汉字”[3]2。在多次战争中,蒙古人大量掳掠工匠艺人,把他们带回蒙古草原,草原中有了汉族百姓生活,他们也带去了中原文化因子。蒙古人的礼仪简略,谈话直率,即便是对外来使者也毫无顾忌,“近使臣到彼国王处,凡相见礼文甚简,言辞甚直,且曰:你大宋好皇帝、好宰相。大抵其性淳朴,有太古风,可恨金虏叛亡之臣教之,今乃凿混沌、破彼天真,教以奸计,为可恶也”[3]8。在外交场合使用上述言语非常少见,这让当时的汉族使者感到不适。礼仪粗疏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其俗多不洗手,而拿攫鱼肉,手有脂腻,则拭于衣袍上。其衣至损不解浣濯,妇女往往以黄粉涂额,亦汉旧妆,传袭迄今不改也”[3]7。与辽、金相比他们保存了蒙古族文化自身的草原特色。可以说,在国家治理中他们是以蒙古草原文化为主,以汉族中原文化为辅,两种文化既相互冲击又相互融合,“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8]。多元的文化环境,为元代文人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儒家文化受到冲击,他们开始更加注重自我的生命意义。
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体现在大元王朝的治理政策上。面对广袤的中原土地,复杂的环境和人事,必须用汉人的治理方法才能使其长治久安。忽必烈早年对中原汉文化很感兴趣,金莲川幕府中聚集了大量儒家文士,如较为有名的姚枢、窦默、许衡等,这些汉族文人,为他夺取汗位,建立国朝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1260年,忽必烈在部分诸王的拥戴下,在开平即汗位,建元中统,并下诏称:“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群下。朝廷草创,未遑润色之文;政事变通,渐有纲维之目。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惟即位体元之始,必立经陈纪为先。故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仍以兴利除害之事、补偏救弊之方,随诏以颂。”[9]65忽必烈身边的汉族文人,经常为他讲解儒家文化与中原明君的治国之道,为元朝的汉化治理打下坚实的基础。“元太祖起龙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阳,平南宋,天下一统。取大《易》‘大哉乾元’之义,国号曰大元,取‘至哉坤元’之义,年号曰至元。设经陈纪,以垂后世。”[10]48从国号到年号,皆有儒家经典为依据,仿照中原王朝国体,改造旧制,成为新一代蒙汉两族共同的帝王。蒙元上承天命,下治四方,既有儒家文化的理论支持,又有蒙古族文化习俗的坚守。两种文化理念互相交融,成为元朝治理的重要文化导向。因此,元政府也遵循汉法,也曾注重书院的发展,如元代抚州书院就得到元政府积极地保护,其明显的特点是“官学化的进程明显加强”[11]。
蒙汉两种文化差异使政策的制定争论不休。游牧民族自身的文化习俗让蒙古人更为偏爱眼前的现实经济利益,难以像汉族人那样,有长久的经济打算。虽然他们学习汉法,但蒙汉之间始终存有一层隔膜,很多汉法规制都不能很好地实行。“大元受天命,肇造区夏,列圣相承,至于世皇至元初,尚未遑兴建宫阙。凡遇称贺,则臣庶皆集帐前,无有尊卑贵贱之辨。执法官厌其喧杂,挥杖击逐之,去而复来者数次。翰林承旨王文忠公磐时兼太常卿,虑将贻笑外国,奏请立朝仪。”[12]此时已经更改年号,但礼仪制度并未完全制定。这样的朝拜非常混乱,不成体制,汉族官员不能容忍这样的礼仪,就阻断喧杂,“请立朝仪”。甚至一些蒙古官员要把中原土地作为牧场放牧,这位官员知放牧可获利,却不知道中原农耕、商贸可获利更多。清人赵翼说:“元初起兵朔漠,专以畜牧为业,故诸将多掠人户为奴,课以游牧之事,其本俗然也。及取中原,亦以掠人为事,并有欲空中原之地以为牧场者。”[7]472赵翼所说之事,在《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中有详细记载:
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赀至巨万,而官无储偫。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9]3458
当耶律楚材拿出直接的金钱数字,太祖便让其试行。游牧民族以放牧为生活的重要来源,所以蒙古大臣别迭建议“空其人以为牧地”,但在中原生活许久的耶律楚材,深懂中原地产特点,并依汉族统治方式收取相应税额,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
大元王朝不断加强经济上的掠夺,这与他们的民族特性有关。他们敢直接向人讨要财物,汉族官员上奏但无法禁止这种行为。“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10]62早在元初,耶律楚材已认识到这些危害,上奏朝廷令行禁止,“贡献礼物,为害非轻,深宜禁断”。但所得结果是对于其他建议“帝悉从之,唯贡献一事不允,曰:‘彼自愿馈献者,宜听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于此。’帝曰:‘凡卿所奏,无不从者,卿不能从朕一事耶?’”[9]3457可见,与生俱来的文化习俗是很难改变的,元朝从治理初期就已经体现出治理中的缺陷。耶律楚材所虑不差,果真贪赃枉法之事横行,直到元末还有各种名目要钱,元朝国运之短也为必然。蒙思明先生指出:“元王朝将得到的主权力,惟用之于经济之榨取耳。”[13]明知过分敛财有伤国体,但还是不能下令制止,很重要的原因即出于草原民族一直以来对经济利益的强烈追求,游牧生活塑造的本性使然,处于统治阶层的蒙古贵族愿意利用权力快速敛财,保障他们奢侈生活的享乐需求。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元世祖混一天下,定官制,立纪纲,兼能听刘秉忠、姚枢、许衡等之言,留意治道,固属开国英主。然其嗜利黩武之心,则根于天性,终其身未尝稍变。”[7]458
3 疆域辽阔与两种文化的交流
蒙古习俗实行收继婚制,是为保存自家经济不被外人夺取。“以国俗父死则妻其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父母死无忧制”[9]4288,这与中原文化大相径庭,儒家注重三纲五常,父子君臣皆有严格等级,汉族王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元末至正十五年(1355),“大斡耳朵儒学教授郑咺建言:‘蒙古乃国家本族,宜教之以礼,而犹循本俗,不行三年之丧,又收继庶母、叔婶、兄嫂,恐贻笑后世,必宜改革,绳以礼法。’不报”[9]921,这一建议未能被采纳和施行,汉族官员没有实现改变蒙古婚俗的目的,整个元代草原民族依然坚持本族习俗,没有被完全汉化。但元代属于多族聚居的时代,没有禁止异族间通婚,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提升了自家文化修养,也利于他们科考成功。萧启庆先生提到:“蒙古、色目进士出身之家庭多与汉族家庭——尤其是士族——通婚。嫁入蒙古、色目之汉族妇女往往教导或鼓励子孙读书应举,有助于这些家庭在科举中之成功。此外,与其他蒙古、色目士人联姻亦有助于家庭科举传统之开始与延续。”[14]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民族间的通婚较为普遍,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融合。蒙古学习汉族儒家文化,汉族同样吸收蒙古文化习俗,多元的文化环境塑造出元代独特的文学风貌。
元朝疆域之广,超越历代。《元史·地理志》中载:“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9]1345疆土辽阔加之武力强胜,使元朝没有外患之忧,“横跨亚欧的版图以及驿站制度的完善,使一向不曾处在统一控制下的东西交通至元代畅通无阻:陆路北穿东欧、西贯伊朗,直接与大都相通,海道从波斯湾直抵泉州等港。”[15]水陆交通便利,万里亦如比邻,元代文人为之自豪。李穑在《益斋先生乱稿序》中提到:“元有天下,四海既一,三光五岳之气,浑沦磅礴,动荡发越,无中华边远之异。”[16]虞集在《崞山诗集序》中表述更为明确:
天运在国朝,元气磅礴于龙朔,人物有宏大雄浑之禀,万方莫及焉。是以武功经营,无敌于天下;简策所传,有不可胜赞者矣。世祖皇帝混一海宇,人文宣畅,延礼巨儒,进讲帷幄。宗亲大臣,多受经义,而经天纬地之文,勘定祸乱之武,于是兼举而大备焉[17]。
国土广阔,民族众多,文人感到盛世之下有“经天纬地之文”。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同民族共同铸造元代的文化精神,他们互相学习,不断改进各自的文化品位,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形态。
正如陈垣先生所说:“盖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18]中原文化深深吸引着少数民族,他们学习汉文,习用汉音。长久的中原生活提升了他们自身的文化素养,写诗作文可与汉族文人并肩。元人马祖常说:“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方偏之语,不相通晓,互相憎恶。惟中原汉音,四方可以通行,四方志人皆喜于习说。”[19]中原汉音成为蒙汉共同使用的交流语言,沟通便利,这使蒙古族人对汉族文化的学习更为深入,使自身的文化气质也发生变化。赵孟頫在《薛昂夫诗集序》中提到:“吾观昂夫之诗,信乎学问之可以变化气质也。昂夫西戎贵种,服旃裘,食湩酪,居逐水草,驰骋猎射,饱肉勇决,其风俗固然也。而昂夫乃事笔砚,读书属文,学为儒生。发而为诗、乐府,皆激越慷慨,流丽闲婉,或累世为儒者有所不及。斯亦奇矣!”[20]薛昂夫本为西域人,通过汉文化的熏染,成为一代名儒,甚至超过汉族文人,汉文化的影响可谓深远。如元人戴良所言,各少数民族皆受汉族文化影响,在《鹤年吟稿序》中提到“舍弓马而事诗书”的情形:
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而西北诸国,如克烈、乃蛮、也里克温、回回、西蕃、天竺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宠泽,与京国内臣无少异。积之日久,文轨日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至其以诗名世,则马公伯庸、萨公天锡……此三公者,皆居西北之远国,其去豳秦,盖不知其几千万里。而其为诗,乃有中国古作者之遗风,亦足以见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变,虽成周之盛莫及也[21]。
大量少数民族文人“以诗名世”却为少见,这与元朝地域之广与文化的交融分不开。草原民族在充分学习中原文化后,他们与中原文人一样乐于诗歌创作,以文会友,与汉族文人交往密切。
在蒙汉文化交融的大环境下,汉族人也学习草原文化,他们学习蒙古语言文字,这大大加强了民族间的沟通与交流。大元王朝拥有多元民族,在统治中坚持以蒙古文化为主导。大德元年(1297)有中书省奏文言:“如今蒙古文字学的宽广也,学的人每多是汉儿、回回、畏吾儿人有。”[22]可见,各族人学习蒙古文化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也引起了朝廷的关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有些士人喜爱蒙古文化,自愿主动学习相应的各种文化内容;另一方面,官方大力推广蒙古文化,换句话说朝廷给蒙古文化创造了适宜的政治环境。如果普通汉人学习这种文化,他们就会增加入仕机会,在官场上有一席之地。“人知国字之足以进身,而竞习之”[23]49,对于蒙古文化的学习一直延续至元末,顺帝至元中,曾有大臣廷议“禁汉人、南人勿学蒙古、畏吾儿字书,”结果是汉族官员许有壬“皆争止之”[9]4202,这说明中原地区对蒙古文化的学习现象一直存在,不同民族之间互相学习的现象也比较普遍。汉族官员在朝中也占有一定地位,成为元朝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元朝的一些特殊制度也有益于两种文化的融合。如元代“两都巡幸制”有利于汉族人深入了解草原文化,他们进入草原地区,能够亲眼看见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与民族风貌。对于汉族文人来说,这些新异的内容成为他们诗文描写的对象,也使他们逐渐接受不同的文化风格。元代文人撰写了大量诗文记述随行的感悟,也有对蒙古上都居住习俗的描写,如有特色的毡房与土屋引起诗人的关注,袁桷诗云:“毡房联涧曲,土屋覆山椒。”[24]252“土屋粘蜜房,文毡围锦窠。”[24]255草原的居住风俗与中原居民不同,他们住在毡房土屋中,具有鲜明的游牧特色,这些都体现出了两种文化的相互交融与渗透。
元代广阔的疆域与多元的民族文化为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大元王朝以强大的武力统一天下,打破了南北隔绝的分裂状态,各族士人不受疆域限制,自由地游览自然山川,这是前代难以实现的。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不断交融,越来越多的文人对这两种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学习并吸收各种文化的精髓,扬长避短,互助互进,不断地提升诗文创作的视野,提高自身的写作创新能力。这为元朝的文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启了元代文学绚丽多彩的新篇章。
4 元曲与诗歌创作中的民族特色
两种文化的交融为元代文学带来新的特色,元曲中文人用直白通俗的语言描写自己的内心情感。少数民族文人群体为元代文学注入新的血液。他们从小生长在草原,游牧生活养成勇武善战的性格,他们的诗歌创作体现出雄奇壮阔,豪放洒脱的特点。
草原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文化风俗,植根在少数民族文人的内心深处,从而使他们自然地生发出豪放超脱、劲健有力的诗风。畏兀儿人贯云石,自幼受儒家文化熏染,读书识礼,修武习文,初荫袭父位,出任两淮万户达鲁花赤,血气方刚,治军威严,后辞官让爵于弟,追求文人自适的生活。“年二十三,膂力绝人,善骑射,工马槊,尝使壮士驱三恶马疾驰,公持稍前立而逆之,马至,腾上,越而跨之,运矟风生,观者辟易。挽强射生,逐猛兽上下。”[25]少数民族文人的突出特点是神武勇猛,超越众人。这与文雅的汉族文人不同。再看他的诗歌《蒲剑》云:“三尺青青古太阿,舞风斫碎一川波。长桥有影蛟龙惧,流水无声日夜磨。两岸带烟生杀气,五更弹雨和渔歌。秋来只恐西风恶,销尽锋棱恨转多。”[26]这是贯云石有名的咏物诗,菖葡的叶子形似宝剑,故称为“蒲剑”。全诗描写了菖葡叶子由荣到枯的过程,寄托作者深切的人生感慨,体现出作者勇敢尚武的精神。贯云石出身于习武世家,他的这种性格亦与家传有关。邓文原在《翰林侍读学士贯公文集序》中提到:“示所著诗若文,予读之尽编,而知公之才气英迈,信如先生所言者,宜其词章驰骋上下,如天骥摆脱絷羁,一踔千里……公之先大父丞相长沙王,统师南伐,功在旂常,公袭其休泽,尝为万夫长,韬略固其素谙,词章变化,岂亦有得于此乎?”[27]从他的诗文可见,豪迈勇武已融入他的内心。他的诗歌创作是两种文化交融下的杰作,草原的空旷辽阔,中原的沃野千里,两种文化基因以自身的特色影响着文人。萨都剌也有类似的诗歌,他的《泊舟黄河口登岸试弓》云:“泊舟黄河口,登岸试长弓。控弦满明月,脱箭出秋风。旋拂衣上露,仰射天边鸿。词人多胆气,谁许万夫雄。”[28]文人英武豪迈的性格铸就挺拔劲健的诗风。少数民族文人的创作为儒雅的汉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草原文化融入元代文学,形成一种超越时代的强健有力的文学特色。
元曲具有鲜明的通俗化与口语化特点。草原民族粗疏简约的文化性格影响了元曲创作。多民族的交往互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文人的性格,元曲通俗直白的语言特点也与此相关。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提到:“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宋词既不可被弦管,南人亦遂尚此,上下风靡,浅俗可嗤。”[29]草原民族的勇猛刚毅,对中原文化是一种冲击与挑战,但同时也带来雄浑刚健的民族性格。元曲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艺术形式,它继承了唐诗、宋词中言志抒情的传统精神,也展现出草原文化带来的狂放爽朗、自由灵活的特性。如无名氏[正宫·塞鸿秋]《村夫饮》中所描写的饮酒场面,“宾也醉主也醉仆也醉,唱一会舞一会笑一会。管甚么三十岁五十岁八十岁,你也跪他也跪恁也跪。无甚繁弦急管催,吃到红轮日西坠。打的那盘也碎碟也碎碗也碎”[30]。文人在曲中体现的欢快自由、无拘无束是其他时代所没有的,他们完全无礼法束缚,无长幼尊卑之别,只有在饮酒中获得的快乐。这种场景与前文所写的蒙古族人“嗜酒”的特点有关,他们的饮酒之乐溢于言表。在元曲中还有很多这样的饮酒描写,语言生动活泼又不失文学雅趣,自然地流露文人情感,这符合元代文化交融的特色。
在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蒙古贵族为了维护统治,借鉴汉族文化来治理国家,建国体制和风俗文化都有所改变。元朝皇帝实际有两重身份,既是中原各族的共同君主,也是蒙古族大汗。无论谁做皇帝都必须经诸王开会进行推选,他们的身份才能得到合法确认。蒙元王朝最终的目的是维护蒙古贵族利益,所以对汉文化是有选择地接纳和吸收,“其基本原则,即既要适应中国固有的情况,又要符合元朝统治者的利益。如果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即使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他们也不感兴趣”[31]。因此,他们在学习汉文化时是有所保留的。元代施行“两都巡幸制”,这一政策利于蒙古文化的独立生存,使它没有完全被汉化。
居住在中原的少数民族深受汉文化熏陶,他们主动学习儒家文化,为元代文学增添草原民族特有的民族气息。同时,中原汉族人也主动学习蒙古文化,彼此通婚,诗文唱和,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各阶层间不断融汇,共同构筑元代共有的文化精神。正如查洪德先生所说:“在元代独特的文化精神下,作家们有着与中原传统文人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也获得了中国文人从来没有过的思想和创作自由以及观察认识问题的多元视角。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新面貌才得以展现。”[32]元代文人生活在特殊的文化环境中,他们吸收蒙古人热爱音乐、注重享乐的文化习俗,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追求一种新的适意的生活方式。
5 结语
元代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深深影响了元朝的治理与元代文学的创作。在这样特殊的时代,文人可以深入地接触草原文化,开始产生新的人生价值观念,他们更加尊重自我的生命价值,充分发挥文化上的优势,依托文学才艺传名后世。少数民族文人的数量开始增多,他们创作出带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他们久居中原,与汉文学家广泛地交流,吟诗唱和,游览四方,共同创造了元代独特的文学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