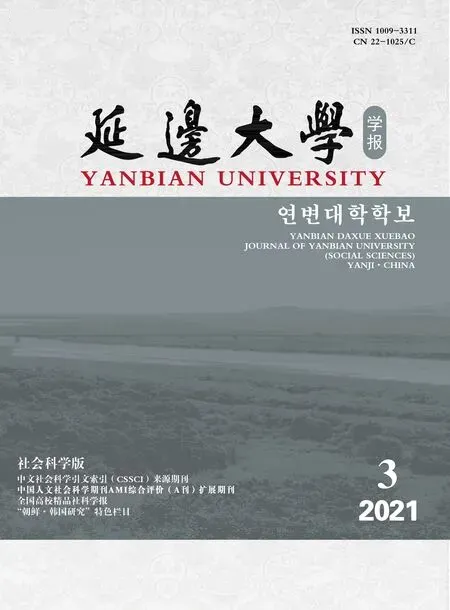父母以外的第三人享有探望未成年人权利之形塑
——以《民法典》第1086条为基准
吕春娟
2020年5月28日,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26条、第1058条规定了婚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共同行使亲权。父母离婚后,根据《民法典》第1084条之规定,亲权由单方行使。此外,根据《民法典》第27条规定,在特殊情形下,除亲权人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者兄、姐以及相关组织被指定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此时监护人的监护权一般与亲权内容并无二致。为了保障父母离婚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民法典》第1086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1)探望权,学界也称探视权、会面交往权。参见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849页。本文出于行文需要,探望权与会面交往权根据具体上下文替换使用。子女的权利,并规定只要父母行使该权利不损害未成年人的福祉,就不应被限制或被剥夺。伴随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核心家庭基本成为我国家庭的样态,年轻父母因为工作压力无暇照顾未成年子女,未成年人的(外)祖父母大多参与到照顾年幼的(外)孙子女的“事业”中,无论是一孩家庭还是二孩家庭,(外)祖父母在未成年(外)孙子女成长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的感情心力,祖孙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心理与感情联系。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迁使得离婚率逐年攀升,未成年人父母离婚不免会打破未成年人与(外)祖父母业已形成的亲密生活状态,继而(外)祖父母思念(外)孙子女,探望(外)孙子女遭到与未成年人直接生活的父或者母的拒绝,为此闹至法院,法院较多支持(外)祖父母的探望权。《民法典(草案)》中也曾规定了祖孙之间的隔代探望权。《民法典》颁行后在司法实践中不免会再现此类案件,尤其在二孩政策下父母离婚还会有兄弟姐妹之间的探望交流需求。因此,有必要尝试基于立法论与解释论,参照外国立法例,结合我国国情与司法判例,形塑父母以外的第三人与未成年人之间探望交流的权利。
一、父母以外的第三人享有探望未成年人权利之正当性
一直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当父母双方因为离婚都想成为亲权人而引发纷争时,法官一般多采用分离亲权和监护权的方式,指定与未成年人同居父母一方为亲权人,非同居父母一方为监护权人。与此同时,父母双方有轮流抚养,即共同抚养子女的意愿时,法官也会采用通过分离亲权和监护权的方式以达到共同亲权的目的。如上所述,核心家庭中(外)祖父母承担了养育(外)孙子女的重任,一旦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婚,之后随其父母任何一方生活时,其与(外)祖父母的亲密生活状态将被改变。所以,学理上,我国学者提出应该在符合未成年人利益原则上赋予(外)祖父母探望(外)孙子女的权利。(2)梁慧星:《中国民法典建议稿草案附理由:亲属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200页。立法上,2018年9月公布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中,赋予(外)祖父母享有探望(外)孙子女的权利,恰是基于伦理亲情,尊重客观事实而对民众需求的回应。立法机关在2020年5月28日《民法典》正式颁布时将这一规定取消,其中缘由,笔者揣测是交由法官自由裁量纷繁复杂之个案。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关系既是因血缘产生的自然法上之权利义务关系,也是我国《宪法》《民法典》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基本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伴随整个社会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关注度提升,父母离婚后一系列与未成年人利益相关的问题随之显现,诸如(外)祖父母对他们悉心照顾、疼爱有加的(外)孙子女因为其父母离婚使得祖孙之间的探望交流被阻隔,未成年人的兄弟姐妹因为父母离婚被迫分开,日常的亲情互动也被打破。(3)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的做法是将未成年人分别判由父母抚养。《民法典》之所以规定父母离婚后不与子女生活的一方享有探望权,主旨则是以此维系与未成年子女的亲情,避免未成年子女心灵受创,保障其身心健康成长,与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原则吻合。但是,与未成年人之亲情联系,并不止于父母,(外)祖父母或兄弟姐妹也有与未成年人亲情互动的需求。
笔者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以“隔代探望”为关键词搜索(外)祖父母探望(外)孙子女的纠纷,主要收集了2015-2019年之间极具代表性的9起隔代探望权纠纷判例,法院无一例外全部支持了(外)祖父母探望(外)孙子女的诉讼请求。(4)王某罗某等与李某探望权纠纷案(2018)川0182民初2780号;徐某李某与倪某探望权纠纷案(2015)锡民终字第01904号;胡某某与王某某探望权纠纷案(2015)克民初字第5135号;冯志男陈天安等与应甜甜探望权纠纷案(2019)赣0103民初1692号;杨某某胡某某与宋某某探望权纠纷案(2017)沪02民终1696号;孙某甲黄某某与孙某乙马某某探望权纠纷案(2015)甘民初字第7348号;丁某王某与白某探望权纠纷案(2016)渝0112民初5648号;董某某张某某与谭某乙探望权纠纷案(2018)渝0103民初11722号;王某罗某等与李某探望权纠纷案(2018)川0182民初2780号。足见法官并没有拘泥于法律规定,而是本着同理心正视案件事实,基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作出判决。早在我国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法发[1993]30号)第5条中就已有父母离婚让10周岁未成年人参与表达对自己以后生活安排的权利,此规定充分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参与权,该权利在后文中提及的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与《未成年保护法》中都有具体规则的体现。如果未成年人能表达其意思,也会向法官表示自己不愿与父母以外的第三人,即(外)祖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分离,然而如果父母行使亲权没有任何不当,仍应由其行使亲权。一旦父母离婚,亲权由一方单独行使,未必愿意对方的父母来探望未成年子女,与此同时,单独行使亲权的一方,因离婚或对方去世等因素,一般也会让未成年子女与对方亲属断绝往来,此处亲属大多是未成年人的(外)祖父母,与笔者检索到的判例完全一致。典型如在丁某王某与白某探望权纠纷案(2016)渝0112民初5648号一案中,未成年人丁某从出生至前往德国居住之前,一直随祖父母共同生活居住且由二原告抚养长达9年多,祖孙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感。未成年人丁某离开二原告前往德国后,也时常通过微信向祖父母表达回国探亲的希望。再如,杨某某胡某某与宋某某探望权纠纷案(2017)沪02民终1696号一案中,未成年人宋某某父母离婚后由其母亲行使亲权,后来母亲去世,亲权改由父亲行使,父亲阻止宋某某的外祖父母行使探望权,对宋某某而言,失去母爱的关切已经备受打击,对其外祖父母而言,成为失独老人后又不能顺利探望挚亲挚爱的外孙宋某某更是雪上加霜。上述两案法官确认(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的深厚感情事实,既是对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原则的司法践行,又充分考量了(外)祖父母感情之需求,从而支持了(外)祖父母请求探望(外)孙子女的权利。由此,单独行使亲权一方的行为未必就是最符合未成年人利益的,甚至可能还会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有滥用亲权之虞。法官在处理因父母离婚导致亲权归属问题时,也不会预料到直接行使亲权一方会拒绝他方父母与未成年人探望交流之情形,从而导致很多(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无法见面,使彼此的感情受到伤害,尤其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不可逆的负面影响。
二、父母以外第三人探望未成年人权利之法理简析
亲子关系立法理念经历了一个利益转变的过程。现代以来,亲子关系立法的理念从家族利益优先的“家本位亲子法”到父母利益优先的“亲本位亲子法”,再发展至子女利益优先的“子本位亲子法”,(5)陈明侠:《完善父母子女法律制度(纲要)》,《法商研究》1999年第4期,第24页。从国际公约之规定到国内基本法的规定凸显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逐渐成为各国亲子关系立法的核心。《儿童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9条第1款规定:缔约国应确保不违背儿童父母的意愿使儿童与父母分离,除非主管当局按照适用的法律和程序,经法院审查,判定这样的分离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而确有必要;第9条第3款规定:缔约国应尊重与父母一方或双方分离的儿童同父母经常保持个人关系及直接联系的权利,但违反儿童最大利益者除外。这是《公约》关于父母离异时对未成年人的利益安排,除了父母之外,其他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之人对未成年人的责任之规定体现在《公约》第5条规定:缔约国应尊重父母或于适用时尊重当时习俗认定的大家庭或社会成员、法定监护人或其他对儿童负有法律责任的人以下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符合儿童不同阶段接受能力的方式适当指导和指引儿童行使本公约所确认的权利。
未成年人生活在父母婚姻存续的家庭,其与第三人之探望交流实属容易之事,但父母离婚,则必然导致与父母一方生活的未成年人与第三人(尤其是对方父母)探望交流的困难,因此不免会涉及法官裁判时必须衡量的一个原则——儿童(6)《儿童权利公约》第1条:“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民法典》第17条:“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18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可知,儿童与未成年人含义等同。最大利益原则,该原则也是现代各国家事司法的基本原则。该原则来源于《公约》第18条规定: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首要责任。儿童的最大利益将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通常认为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雏形源自英国普通法,美国继受并进一步发展,《公约》最后将其定性为现今的国际性指导原则,现在很多国家将其作为法院处理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行使亲权案件的最高准则。基于遵循该原则,法院处理未成年人亲权问题时,摒弃父母权利本位思想,将“子女最佳利益”置于“父母权利”之上,使得对子女的亲权焦点问题从“谁有权行使亲权”转变成“由谁行使亲权对子女最为有利”,从而使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内化到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之中,以此确保儿童利益。(7)雷文玫:《以“子女最佳利益”之名:离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行使与负担之研究》,《台大法学论丛》1999年第3期,第33页。我国政府于1990年8月签署了该《公约》,并将儿童生存、保护、发展与参与的主要目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了儿童优先原则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且在目标的制定上明确了保障儿童利益最大化;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颁布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4)24号)第2条规定,处理监护侵害行为,应当遵循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充分考虑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人格尊严,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2020年10月17日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案第4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享有的各项权益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这是我国践行《公约》之规定的中国式表达。
对于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内涵,有学者根据德国立法的规定,将其界定为“未成年人的自我发展和独立人格之培养”。(8)王葆莳:《“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德国家庭法中的实现》,《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4期,第36页。子女的自我意愿和观念是其迈向完全独立之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所以,理性的教育不宜压制子女的自我主张,而应当对父母的权威加以一定的限制,令父母权威的实施方式和程度符合子女的年龄和发展状况,并与争议涉及的问题相适应。随着年轻人的成长,他们可以逐步承担完全责任,父母的引导作用就会相应缩减。(9)[德]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王葆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336-337页。
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不仅是立法的基本理念,而且是制度设计的核心。(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是除父母子女关系之外最亲的直系血亲,《民法典》第27条规定了(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在特定情形下的监护权,第1074条也规定了(外)祖父母在特定情形下抚养(外)孙子女之义务,第1128条也有(外)孙子女代位继承(外)祖父母财产的规定,这些权利义务的基础均在于(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之间的法定血亲关系,依据此血亲关系,(外)祖父母在特定条件下负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外)孙子女的义务,相应的(外)祖父母也应享有探望未成年(外)孙子女之权利,此权利源于《民法典》规定的亲属身份权。
三、父母以外第三人探望未成年人权利的域外立法经验
域外立法例上,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在法律上赋予父母以外第三人享有探望未成年人的权利。《德国民法典》第1685条第1款与第2款规定,除了父母之外,未成年人的祖父母与兄弟姐妹以及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并对未成年人承担了或承担过“事实上责任”的人均享有与未成年人会面交往的权利。(10)[德]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王葆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391页。这里“事实上责任”的人主要是指长期和未成年人在共同家庭中生活,从而形成事实上责任关系的人(社会家庭关系)。2004年之前的德国法律规定,只有配偶和子女在家庭中长期共同生活过的前配偶或生活伴侣、养父母才享有对未成年人的探望交往权。联邦宪法法院认为,该规定违反了《基本法》第6条第1款,因为其意味着,若未成年人的亲生父亲没有被确认为法律上的父亲,即使其和子女建立了事实上的联系,也不享有探望交往权,这显然不合理。法院认为在此情况下,应当用“社会家庭关系”这一概念来表示那些事实上已经为未成年人承担责任的人。因此,在2004年的改革法案中,立法者在上述判例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和情形,任何人只要通过长期的共同家庭生活与未成年人建立了社会家庭关系,即享有探望交往权。但在《德国民法典》第1685条中规定了未成年人自身没有独立的交往权。父母有权决定其子女和其他人的交往是否符合儿童最大利益,但父母的决定权受《德国民法典》第1626条“维持子女与之有联系的其他人的交往有益于子女发展的,该交往即属于子女的最大利益”的限制,继而第1685条第3款规定了倘若和其他人的交往符合儿童最大利益,但父母却阻止该交往,法院可以对父母采取干预措施。(11)王葆莳:《“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德国家庭法中的实现》,《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4期,第48-49页。显然,德国法凸显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之规范与追求。相较而言,瑞士法与法国法在立法规范上没有使用“儿童最大利益”之表达。《瑞士民法典》第274条规定: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前提下,父母以外的第三人,尤其未成年人的亲属,可以请求与未成年人会面交往。(12)《瑞士民法典》,殷生根、王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1页。此条表达是“有利于未成年人”,且所列亲属没有明确列举,但应该包括未成年人的(外)祖父母以及兄弟姐妹。《法国民法典》第371条第4款规定:除有重大理由之外,父母不得妨碍子女与其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关系。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家事法官裁定之(第1款)。家事法官于特殊情形之考量,得同意其他人的通信权或探视权,无论该人是否是亲属。(13)《法国民法典》,罗结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84页。由此可见,法国法中无“有利于未成年人利益”之规范,除了(外)祖父母,第三人范围更是突破了亲属的限制,只追求符合未成年人利益之原则。在英美法系中,美国法院对于父母离婚后未成年人亲权人的判决曾经有三种符合子女最佳利益推定的原则:“共同监护”(joint custody)、“心理上的父母”(psychological parent)、“主要照顾者”(primary caretaker)。(14)Cheryl Buehler and Jean M.Gerard,“Divorce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A Focus on Child Custody”,Family Relations,Vol.44,No.4(1995),pp.439-458.这三种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经过锤炼检验,“主要照顾者”作为最适合的原则被法官采用,其理由有:一是主要照顾者比较了解未成年人的需求;二是主要照顾者照顾未成年人,也证明其尽力保护、照顾未成年人的心意;三是主要照顾者通过长期照顾未成年人,与其建立起来的联系对于未成年人的成长非常重要。(15)Cheryl Buehler and Jean M.Gerard,“Divorce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A Focus on Child Custody”,Family Relations,Vol.44,No.4(1995),pp.439-458.我们根据主要照顾者与未成年人之间的生活现状与心理感情联系,可以推知曾经与未成年人感情联系紧密的(外)祖父母与未成年人在其父母离婚后保持会面交往可以充分保证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
四、父母以外第三人探望未成年人所涉之法益冲突与调和
通过上述域外立法以及判例原则可知,父母以外第三人享有探望未成年人之权利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我国的司法实践也充分体现出祖孙对此强烈的需求性。但第三人的探望不免与亲权人行使亲权以及宪法所保护的家庭完整性形成冲突。
(一)未成年人需求与亲权人或监护权人监护权之冲突调和
未成年人与父母以外第三人会面交往权之实现与亲权或监护权为主要冲突法益。假如会面交往漫无限制,可能形成(外)祖父母频繁探望,干扰未成年人与其亲权人的生活安宁,而且(外)祖父母过度介入亲权或者监护权之行使,也会使得父母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管教困难以及未成人面临多元管教之无所适从或从中钻空子,反而不利于教养未成年人。因此,对未成年人负担权利义务的父母一方或双方,或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权,均应予以尊重,否则对于未成年人之照管出现多方干涉,反而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利益。
(二)亲权人或监护权人之权利与宪法保障的家庭完整性之冲突调和
未成年人与父母以外第三人探望交流,其主要冲突法益即为亲权人或监护权人之权利与宪法保障的家庭完整性。20世纪,美国很多非核心家庭(单亲家庭)的非核心家庭成员帮父母一方照顾未成年人。因此,允许第三人与未成年人探望交流实属美国家庭变迁过程中的普遍性存在。(16)郭钦铭:《父母以外的第三人与未成年人的会面交往》,《现代身份法之基础理论——戴东雄教授七秩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49页。但不可避免的是,因为(外)祖父母的介入不免会有亲权与监护权人行使权利时受到不适当的干涉。美国加州1994年《家庭法》规定,如果父母不同意,即推定祖父母之探望不符合孙子女之最佳利益;明尼苏达州法律规定,只有在不影响父母亲权或亲子关系的情况下,才允许祖父母探望孙子女;内布拉斯加州法律规定,法院必须确认第三人探望不干涉亲子关系,法院才允许祖父母探望孙子女;犹他州1998年的法律亦是如此规定。(17)郭钦铭:《父母以外的第三人与未成年人的会面交往》,《现代身份法之基础理论——戴东雄教授七秩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51页。综合上述法律之规定,凸显美国《宪法》第14条正当法律程序在于保障父母决定如何照顾、具体行使亲权的方式。在我国,父母对未成年人的亲权行使受《宪法》保障,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受《民法典》第34条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11条保障。
综上,笔者认为,就具体个案而言,“未成年人之需求”与“亲权人或监护权人之权利和家庭完整性”二法益之强度可能差异很大,彼此间可能形成冲突状态,因此在个案操作上须小心谨慎,尤其父母基于人伦天性,所作所为应符合子女之最佳利益,倘若允许父母以外第三人享有探望未成年人之权利,不免会影响父母行使亲权。
关于未成年人的需求,个案差异也很大。例如,杨某某胡某某与宋某某探望权纠纷案(2017)沪02民终1696号一案中,宋某某随母生活,后来母亲去世,父亲行使亲权将其接回,致使其与外祖父母隔离,但该未成年人与父亲隔阂很大,不愿意与其共同生活,且思念外父祖母强烈,自然应该尊重其与外父祖母的探望交流权;又如,有一未成年人出生后由其亲姑姑照顾一年,后被父母接回,但姑姑思念侄子心切,前来探望,该未成年人却对姑姑毫无印象,并没有探望交流的需求。
就“亲权或监护权人的监护权和家庭完整性”而言,具体个案也不相同,有些家庭功能健全,不适宜外人打扰。相反,有些家庭功能不健全,甚至有疏于保护照顾未成年子女之情况,此时允许未成年人与第三人探望交流,不仅是对未成年人身心需求的满足,更是对未成年人的亲权人或监护权人的监督,以此可以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如果法律允许父母以外第三人享有探望未成年人之权利,对于主体、要件不适宜僵化规定,应交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以便维护未成年人之利益、亲权或监护权和家庭之完整性,由此《民法典》正式颁布时去掉(外)祖父母探望权之缘由便被显现出来。
五、父母以外第三人探望未成年人的主体范围与条件
如前所述,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在《公约》被予以明确,我国《民法典》与《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有中国式的意蕴表述,父母以外的第三人与未成年人探望交流,需要明确其主体范围与探望条件。
(一)父母以外第三人探望未成年人权利之主体范围
关于探望交流主体,《德国民法典》第1685条第1款与第2款例示概括规定为未成年人之兄弟姐妹、祖父母、前配偶之父或母、曾与未成年人长期共同生活者,以及其他曾长期照顾未成年人之第三人;《瑞士民法典》第274条第1款概括规定为父母以外第三人;《法国民法典》第371条第4款例示规定为(外)祖父母,后概括规定为父母以外第三人,均没有采取列举的方式(未经列举者则予以排除),生怕挂一漏万,皆因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与精神需求因个案不同而差异很大,交由法官适度裁量最为妥适。比如,保姆、寄养家庭的阿姨、未成年人的小玩伴等都是非亲属,但与未成年人感情深厚,如不准许其探望交流,则会伤害未成年人的感情。具体在我国的立法建构上,可以借鉴《瑞士民法典》之规定,概括为“父母以外的第三人”简单明了,具体个案由法官适度裁量,不失为一种妥当的选择。
(二)父母以外第三人探望未成年人的条件
首先,在何种条件下法院才允许父母以外的第三人探望未成年人,是否以亲权人或监护权人有不适格的情形(如疏于照顾保护未成年人或者对未成年人有家暴行为)为必要。笔者认为,即使在功能健全的家庭,未成年人也有与第三人会面交往的需求可能性,本着为未成年人利益着想的原则,应不以亲权人或监护权人有不当行为为必要,但如果亲权人或监护权人有不当行为之时,法院在允许第三人享有探望权之时,应注意不能造成不当干涉亲权或监护权之行使,探望交流的频率应降低。法律条文则最好为法院“酌定”之表述。
其次,法院允许第三人享有探望未成年人权利是否需要符合“未成年人最佳利益”,还是仅需“有利”即可。《德国民法典》第1685条规定要求符合“最大利益”;《瑞士民法典》则是规定“有利”即可;《法国民法典》第371-4条甚至没有“有利”之规定,完全交由法官个案裁量。
以“最大利益”之文义解释而言,实际上很难判断何为“最大利益”。同时,“最大利益”与“次大利益”之间仅有些微差距,这种差异不应成为未成年人与第三人探望交流愿望之障碍。因此,笔者认为,不应以“最大利益”为条件,而适宜以对未成年人有利即可。且法院在准许第三人享有探望未成年人之权利时,一般是对该未成年人有利,重点在于对该未成年人有利时,如何避免过于干涉亲权或监护权,亦即重点在于法益冲突之调和,而不在于是否需要明文规定“有利于未成年人”为要件。具体则如:在功能和家庭结构都完整的家庭中,为避免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应该承认未成年人与父母以外第三人交流的必要。常见如未成年人父母工作忙碌,家中有保姆照顾未成年人或者父母将其寄养,未成年人与保姆或寄养家庭的阿姨产生深厚的感情,后来因各种原因保姆辞去工作或父母将未成年人从寄养家庭接回,此时该未成年人家庭环境健全。但他思念保姆或者寄养家庭的阿姨,如果不让其探望交流,可能会影响其正当之精神需求,进而影响其健康成长。在功能有瑕疵的家庭中,第三人则扮演监督者的角色,其探望交流还可以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例如,杨某某胡某某与宋某某探望权纠纷案(2017)沪02民终1696号一案中,宋某某母亲病故,其与父亲一起生活,假如父亲酒后常会对宋某某实施家庭暴力,宋某某与外祖父母感情深厚,法官允许他们之间探望交流,既可以阻止该父对宋某某的家庭暴力行为,还可以依据《民法典》第36条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8条之规定,杨某某与胡某某有权向法院申请剥夺宋某某之父的亲权,由杨某某与胡某某担任宋某某的监护权人。至于第三人与未成年人探望交流之方式与时间,应该准用《民法典》第1086条规定父母与未成年人探望交流的方式与时间,以便适用于多样个案之需求。
六、结语
针对父母以外第三人享有探望未成年人的权利之形塑,基于个案差异的缘由,法院可以依请求或者依职权,于有利于未成年人时,与该未成年人有特殊情感关系之父母以外的第三人,酌定其与未成年人探望交流的时间和方式;但其探望交流不利于未成年子女时,法院依职权或者依请求予以变更。未成年人父母假如没有婚姻关系,或者未成年人由父母以外第三人监护的情形,也可以参照父母之间缔结合法婚姻关系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