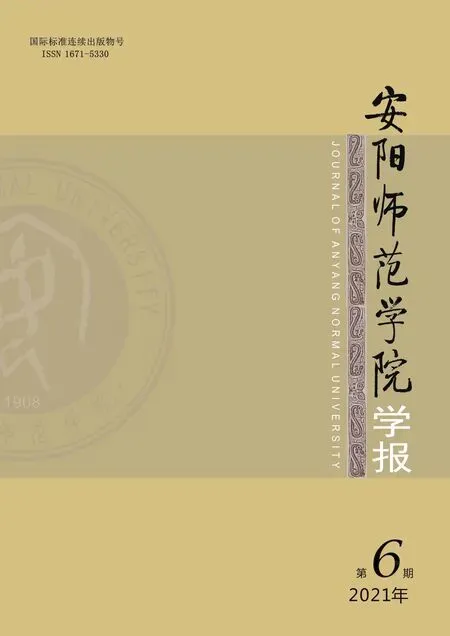姚舜牧《书经疑问》以经解《书》的特色与启示
于 周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姚舜牧,字虞佐,号承庵,浙江乌程(今浙江湖州)人。生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卒于天启七年(1627)。姚舜牧《书》学之作有《书经疑问》(或称《尚书疑问》《重订书经疑问》)传世,是书解《书》大体依宋儒之说,但并不盲从,对于朱子点定的经文予以认可,而且“可与天下共疑者,姑存之以问于有道”[1]。创作是书目的在于批判《书经大全》“固泥其辞而不通其解”的弊病[1],在诠释实践上以回归经文为主要解经原则,这使得他对《尚书》的解读颇有新义。其书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颇大,陈第《尚书疏衍》、陈泰交《尚书注考》等书均受到此书的影响,尤其在解经实践上继承姚氏以经证经、重经文、轻传注的理念。然而目前关于姚舜牧的研究较少,除韦祖辉有专文讨论《五经疑问》与《五经大全》关系[2],并藉此说明明代经学的退步情况外,涉及姚舜牧本人及其著作的相关内容仅仅在专经研究史中略有提及,另有少量针对其家训《药言》的研究,(1)郭长华:《初论〈药言〉的德教思想及其现实价值》,《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徐丰铭、董竞:《〈药言〉的伦理教化思想》,《文史博览》2006年第2期;付庆芬:《〈姚氏家训〉:吴兴姚氏的望族之道》,《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1期;王改花:《浅析姚舜牧〈药言〉家训中蕴含的伦理思想》,《经贸实践》2017年第13期。针对姚氏解《书》方法而研究者尚付阙如,今就其对以经解《书》的独特运用与贡献尝试论之,以求姚氏解《书》之精义。
一、以经解《书》的条例
(一)训解字词
姚舜牧在解《书》过程中经常关注到关乎经义的重点字词,常通过援引他经的方式,将字词置于相似语境中以明其义。如舜典言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姚注曰:
“慎徽”,“徽”字训“美”字,似未妥。《易》曰:“系用徽,寘于丛棘。”《说文》云:“绳三股曰徽,二股曰。”《中庸》云:“经纶天下之大经。”五典有亲义序别信之伦,其中又有许大条款节目在,故史臣酌用“徽”字以取经纶之意。随承说“五典克从”,见各从其类而不紊也,恐不宜作“美”字解。敢问高明。(《重订书经疑问》卷之一)
姚舜牧此处解“徽”字,意在驳斥蔡《传》“徽,美也”之训。首先直斥释“徽”为“美”未妥,进而引《易·坎》上六爻辞,意图在于举出同处经文中的“徽”字,再引《说文》以释义,明“徽”义本作三股之绳,与“美”毫不相干,因而节引《礼记·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句,进而提出应作经纶之义解,以为“徽”字在此即是强调五典各从其类,描述有条不紊的状态。案:通过核验原书,此处姚舜牧所引《说文》云云,实引自《经典释文》,此为《释文》所载刘表语。文章虽主要关注姚舜牧引经解《书》,然姚氏尝恃博而未复核所引书籍,此即是一明证。此处引《易》以提出二经所共存的单字,引《释文》以解《易》中字义,又引《礼记》以解《书》义,最后再次申述对蔡《传》解释的不满。
再如:《汤诰》:王归自克夏,至于亳,诞告万方。王曰:“嗟尔万方有众,明听予一人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姚注曰:
“衷”“性”“猷”三字无别。在天降曰“衷”,即《中庸》所谓“命”也,在民生曰“性”,即《中庸》所谓“道”也,“绥”“猷”即“修道”之谓。(《重订书经疑问》卷之四)
此处解“衷”“性”“猷”三字,姚舜牧以为三字一义,通过征引《礼记·中庸》的“命”“性”“修道”类比见义。此处为汤告诫天下诸侯治国之道,“衷”“性”“猷”三字不易解,遂举《中庸》这一更为常见的文献进行类比。《中庸》首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处以“衷”“性”“猷”与“命”“性”“道”相比,上天降下的是衷福,与民生相关的是天性,二者本质无别。《书》此句谓上天降下衷福给天下民众,应当顺从人的自然天性,能安定教导他们的就是君王,姚氏以此为《汤诰》一篇之纲领,有宋以来对于《中庸》之“性命”更是极为重视,以此二者相类比,即是借重理学的经典概念来诠释《书》之字义。
(二)考订名物
姚氏解《书》以求得圣贤之心为最终目的,因而在名物、制度等方面阐发不多,以最为众说纷纭的《禹贡》篇为例,姚氏曰:
此当递递看下,始得叙事之意。若逐句为解,则但泥字义,而神禹一段施功之次第不可识矣。(《重订书经疑问》卷之三)
但如遇宋儒解经至难合经义处,仍常援引他经以疏通经义,如《禹贡》:厥土青黎,厥田惟上下……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姚注曰:
孔氏曰:“璆,玉石也。”《尔雅》曰:“璆琳,玉也。”且下文自有磬,蔡氏以为玉磬,误矣。(《重订书经疑问》卷之三)
姚舜牧此处对于梁州所贡之“璆”进行讨论,首先引伪《孔传》,再引训诂专书《尔雅》,意在证明“璆”即为玉无疑,最后驳斥蔡沈以“玉磬”解“璆”,并说明经文中已明言有磬,此处不应复作磬解。姚氏此处先引伪《孔传》立异,又由于其重经文、轻传注的一贯思想,复引《尔雅》一经,目的在于以经明物,对于《书》中难解名物加以探求。《尔雅》作为经书中唯一的训诂专书,其在训解字词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姚氏即借经考名物、明经义。
再如:《费誓》:今惟淫舍牿牛马,杜乃擭,敜乃阱,无敢伤牿。牿之伤,汝则有常刑。姚注曰:
《易》“童牛之牿”,本义训施横木于牛角,以防止其触,似矣。然马则无角也,当是施牿于其足,以防走失耳。(《重订书经疑问》卷之十二)
姚舜牧此处对“牿”之形制进行研究,先节引《易·大畜》六四爻辞,此处“童牛之牿”意思甚明,即是束缚在小牛头上的木牿,《说文》引作“僮牛之告”,观此知“牿”为防止触人所做,《说文》等以为专为防牛,所以施横木于牛角,姚氏认为此种说法近乎其义,不通之处在于《书》中所说为“牛马”,马并无角,因而他在此处用郑玄的说法,以“牿”为“施梏于牛马之脚”,如此解释,则适用于牛马两种动物了。此处引《易》,在于领起对于具体事物的讨论,以对《大畜》中“童牛之牿”的讨论类比《书》中的“今惟淫舍牿牛马”,以此明义。
(三)补苴史事
由于《尚书》成书过程复杂,其所记载史事亦有互见于他经者,对于《书》中所记较为简略者,姚氏常援引他经以补充说明。如《尧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姚注曰:
凡人不幸处父子、兄弟之变,惟一孝可以感格。然要在此心之和平,此心稍有不和,亦勉为孝焉耳,如何可以感动得?若舜谓己职未尽,父母之不爱我也,我求尽己之事,略无一毫憾怨于其中。其所以“夔夔齐栗”者,皆自中心和平中发出来,斯谓“克谐以孝”耳,不谐如何能孝得?(《尚书疑问》卷之一)
姚舜牧此处解“克谐以孝”,先说唯有孝可以感格父子、兄弟之变,又说明此孝应发自和平之心,不可勉强为孝,若勉强便失去感格之用。论舜事谓舜检讨自身是否称职,未尝有抱怨之心,此处并非《书》所记载,其来源为《孟子·万章上》,据节引“祗载见瞽叟,夔夔齐栗”可知。《书》仅“克谐以孝”数语称舜之孝,此处通过引用他经,对内容进行补充,使得舜之孝行更为直观,谓舜侍奉瞽叟的谨慎畏惧即是源自和平之心。案:《孟子》称此句为“《书》曰”,一般认为此句来自逸《书》,姚氏此处虽未明言,然将此则材料放置于此处并加以使用,或可见其对于逸《书》的有意关注。
再如《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姚注曰:
……“惇信”二句所该甚广,时说但将出令贴明义,将官赏贴崇德报功,恐不尽。凡王者所以孚协内外,何者而非信?所以区画上下,何者而非义?《乐记》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何者而非崇德报功?……(《重订书经疑问》卷之七)
姚舜牧不满自蔡《传》以来对“惇信明义,崇德报功”的解释,他认为这二句含义深刻,不应该仅仅以发布命令来树立信义,尊有德者为官、奖赏有德者来进行解读。在姚氏看来,凡是《尚书》所记王者皆是大圣贤,一举一动无不合乎信义,不必刻意求得。在解读“崇德报功”上,他征引《礼记·乐记》中孔子对于武王伐商灭纣后情形的描述,以此来证明王者所作所为无不在于“崇德报功”。由于《武成》篇对于武王获胜后的情况并无详细记录,此处引述《礼记》之文对此处细节进行补充,无疑十分利于对《书》义的把握。此一段引文出现在《武成》篇中,不仅为姚氏所述观点服务,同样有补苴史事的作用。
(四)经义互通
姚舜牧解《书》重视阐发经义,在对于思想内涵进行阐发时,常常通过引用他经中相近的表述来深化与延伸经义,这种引用并不局限于史事的互证,更多的是思想层面的互通。如《尧典》,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僎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姚注曰:
驩兜是党恶的人,与放齐不同。然“共工方鸠僎功”亦是实事,小人欲自见于天下,何尝不竭力共职,微著其功?唯是言行相违,表里不一,实落任以大事,便必至于倾覆耳。《论语》所谓“佞人殆”是也,故尧黜之而不用。(《重订书经疑问》卷之一)
由于后文《舜典》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语,知驩兜与共工结党作恶,故向帝举荐,因而姚氏说驩兜不同于举荐朱的放齐,且根据“静言庸违,象恭滔天”二语说明小人的劣性,不可轻易任用,进而与《论语·卫灵公》中夫子向颜渊论及为邦时所提出的“郑声淫,佞人殆”相比,同为经邦治国之大道,尧不轻信驩兜语任用共工,正与夫子告诫警惕奸佞之臣的危险相合,二经相比,经义自见。
再如:《多方》: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姚注曰: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惟明此德以率其民耳。民有不率,不得不用罚焉,而又深致其慎,是则帝王之所谓“明德”也。“殄戮”“开释”,正是致慎处、正是用德处。(《重订书经疑问》卷之十)
此篇为告诫多方诸侯之作,此节则专就“明德慎罚”展开。姚舜牧先节引《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句,阐明天地德泽之宏大处正在化生万物,戕害生灵自然与之相悖。姚氏以为《书》经中所“明”之“德”就是此好生之德,因而认为即使民有不驯顺处,不得不惩罚他们,也应该慎之又慎,以明此德。无论“殄戮”“开释”,用心均在“明德慎罚”,因而所作无非致慎、用德。“大德曰生”与“明德慎罚”经义互通,正是由于天地之间以生德为大,在上者需要谨慎于刑事,一有疏漏即是大德昏蔽。
(五)文献互见
姚舜牧对于不同经书间的相近表述十分重视,尤其是记载相同史事或表述相近思想的文献材料,处理方法即是将他经材料引于经文之左。如《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姚注曰:
《乐记》云: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重订书经疑问》卷之七)
《武成》此段记载与《礼记·乐记》十分接近,所述事件高度一致,均在述说武王获胜后收敛武力,姚氏遂将《礼记》经文放置于此,提示读者二经记载之相近。
再如《武成》: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月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姚注曰:
祀庙所以告成功也。庶邦来受命者尚在,故各骏奔走,执豆笾以助祭焉。《记·大传》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正道此事。(《重订书经疑问》卷之七)
《武成》此段与《礼记·大传》记载接近,两书经文所记均与获胜后的祖庙之祭相关,语言虽有不同,所记实是一事,故将《礼记》经文放置于后以供比较。
(六)以经证经
《尚书》中所记多有不与后世普遍共识相近者,面对这样的问题,姚舜牧通过援引他经的方法为《尚书》提供佐证,疏通经义。如《洪范》: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姚注曰:
王者顺时以出治,何事于疑?然国家遇着大可疑的事,如武王牧野之师曰“朕梦协朕卜”,如盘庚之迁殷曰“卜稽其如台”,如周公之管洛曰“来视予卜休恒吉”,则卜以决疑,亦所不可少者。《易》曰:“以卜筮者尚其占。”又曰:“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非决疑其何以出治?(《重订书经疑问》卷之七)
九筹之稽疑为以卜筮决断疑问,姚氏释此节先提出问题:王者因时而治,为何还有疑问存在?长久以来认为《尚书》所云王者均为创至治之世的圣人,一举一动无一毫之瑕疵,由此推导下去,自然得出王者是不会存在疑惑的,而旧说认为《洪范》所录为箕子向武王所陈天道,因而此处产生了矛盾。姚舜牧对此做出的解释为国家如果遇到可疑的事,卜筮乃是不可或缺的判断手段,列举武王牧野誓师、盘庚东迁、周公营洛三例以证,这属于本经自证,而节引《易·系辞上》两句则属以他经为证。“以卜筮者尚其占”为《系辞》对《易》的赞扬,认为它可以用来指导卜问,并且使决疑的人崇尚占筮的原理,这显然是申说卜筮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不可将卜筮简单视作一种随机占问。“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一句则针对圣人无所疑惑而引,明说圣人也需要断疑,不过所断乃是天下之疑,关涉甚大,如不决疑则难以为治。此处以《易》证圣人亦有疑,亦需要卜筮决疑,巧妙化解经义上可能存在的冲突,使经义通达无碍。
再如《微子之命》下姚氏题解曰:
微子是本爵,武王虽封之于宋,篇名仍称“微子”者,原其罔为臣仆之心与箕子之心一也。使武庚不以叛诛,微子其肯出就封哉?武王封命之辞曰“崇德象贤,统承先王”,亦体微子存祀之心耳。《诗》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此作宾之一证也。噫,知微子作宾于宋,则箕子之朝鲜必其所自处,而非受封命矣。(《重订书经疑问》卷之八)
微子篇所记为成王分封微子建宋的命令,而由于微子、箕子、比干为孔子口中的“三仁”,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因此对这一篇名即提出:为何微子受封后仍沿袭旧称,而不代之以封宋爵名?这一问题所关甚大,涉及微子是否降周为臣而背叛殷商。姚氏以为微子与箕子一样,并无臣周之心。微子之所以会受封,是因为肩负存殷重任的武庚发动叛乱,武庚伏诛后微子不得已而接受分封以奉其先祀,因而从根源上看微子并非降周,是往周之宾,非降周为臣,故沿用殷商时本爵。《书》称为“微子”,正表示对他的尊敬。继而引《诗·有客》二句,以此作为微子宾于周之一证。《有客》一诗历来认为是微子朝周祖庙后,周王为其饯行之歌。“有客有客,亦白其马”中,“客”即指微子,所乘马为白马则由殷人尚白,以此示微子不忘故国之意。此二句诗所述正与姚氏欲说明的情况相吻合,因而以此来佐证《尚书》之篇目的命名十分合乎情理,达到了以经证经的效果。
二、引经的个性化表现
(一)引经范围较广,以《易》《诗》《礼记》为主
《书经疑问》全书征引经书范围较广,据笔者粗略统计,全书除《尚书》外共涉及《易》《诗》《礼记》《周礼》《论语》《孟子》《左传》《尔雅》等八部经书。其中引《易》89处、《诗》58处、《礼记》49处、《周礼》1处、《论语》8处、《孟子》9处、《左传》3处、《尔雅》1处。显而易见的是,姚氏引经侧重十分明显,《周礼》《论语》《孟子》《左传》《尔雅》五部经书征引数量仅占10%,而《易》一部就超过了四成。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全书引经以《易》《诗》《礼记》三种为最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必然与姚舜牧个人的受教育背景有关。姚舜牧自著文集《来恩堂草》书末有自著年谱《自叙历年》一篇,该年简谱以年为序,兹摘录数条:
十一二岁,始附学于毕、宋二家。冯贸泉先生命牧治《诗》。十三四岁,又苦无师承也。十五岁,附学杨家,改治《易》。……甲子,二十二岁。……改治《礼记》。乙丑,二十三岁。以治《礼记》徃汇沮潘家,师绍兴王三江先生。是秋,屠屏石宗师歳考,原以《易》试优等,遂卒治《易》[3]。
根据其自述,姚舜牧离开乡塾后首先治《诗》,经一二年而无师承,遂投师杨氏治《易》,用功数年,为举业而改治《礼记》,经一年有余又因在考场以《易》列优等,于是又重新投身《易》学。姚舜牧之所以辗转修习数部经书,根源在于当时的科举制度。明朝乡试会考察经义,第一场即是《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然而经义虽从《五经》出题,但并非每位考生都应试五部经书,而是选取一经来考。在这一政策下,士子读书的首要目的便不是求取真知,而是尽量降低难度,提升应举的概率。从姚舜牧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早年转益多师,旁求经义,也是由于从事举业的缘故。然而这一复杂的受教育经历在另一方面却也使得姚舜牧对于《易》《诗》《礼记》三经格外熟稔,这也是造成《书经疑问》引经出处极不均衡的重要原因。
(二)引经多凭记忆,不免舛误
姚舜牧为晚明著名学者,勤于学问,一生著述宏富,博涉四部,由于其博闻强记,引书难免依靠记忆而不进行核对。由于古人并无极强的引用意识,引书多为解义,因而在其《书经疑问》中有少量失误之处。如《益稷》: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姚注曰:
……此个“止”原无动静,若《易》所谓“时止而止,时行而行,动静不失其时”。……(《重订书经疑问》卷之二)
此处节引《易·艮》之《彖》以释“止”,原文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姚氏误两“则”字为“而”,足见其引书多凭记忆。未经详审。
再如:《咸有一德》: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姚注曰:
《记》曰:“祖有功,宗有德。”但说庙以崇德,所以要修德以居庙,不必说到祧不祧处。(《重订书经疑问》卷之五)
此则引文实不见于《礼记》,笔者目力所及最早出处为贾谊《新书》,此条更可见姚氏不核对原书之失。
(三)引书偏重经书,少见史籍
从数量来看,姚舜牧《书经疑问》全书引经书接近300处,足见其对经部文献的看重,然而对于历代解《尚书》均无法回避的《史记》《汉书》等重点史籍,全书仅引用《史记》2处、《汉书》2处,远远少于其对经书的利用率。从引用方式来看,姚氏没有对材料进行充分合理的使用,论述较为简单,如《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姚注曰:
按:《汉书·除肉刑诏》云:“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司马迁《报任安书》亦曰:“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重订书经疑问》卷之一)
此处为说明上古无肉刑,先节引《汉书·孝文本纪》,以汉帝诏书为证,后节引《汉书·司马迁传》,通过汉将魏其实例进行论证,以解“五刑有服”句,属于以史证经。
再如:《盘庚中》: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姚注曰:
……水曷称凶德?司马迁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水利民处颇多,然汛溢为害,则凶莫甚焉,故曰“凶德”。(《重订书经疑问》卷之五)
此处节引《史记·河渠书》,意在借重司马迁之言说明水之利害,进而解释何以称水为“凶德”,仅仅是随文而发,借司马迁之口述己之意而已。
事实上,《尚书》与《史记》《汉书》等史书关联度极高,其中有大量记述资料高度重合,史书中更是存在对《尚书》文字为数不少的摘引或全录,姚氏没有充分使用这一类型的材料,而仅仅将重心全部放在经书上,实为遗憾。
三、《书经疑问》以经解《书》的实质与启示
姚舜牧以经解《书》十分注重《书》的内容与所引经文的契合程度,既有在解释《尚书》文句后选择他经文句加以佐证,也有以文辞的相同或相近为条件进行的内容并列,而其引经诠释的核心在于对多种经典针对类似话题的有理融合。这种解喻结合的做法既没有放弃对经书字词的训释,又将关注重点放在了不同文献在义理层面的相似性上,因而十分注重不同经书间的关联性,从而达到融合的境界。这种引经解《书》做法的实质即在于根据义理上的关联将不同经书内容相互贯通,以期达到不同文献间的联动,力图用义理上的共性把握不同文本。这种诠释实践不同于仅引他经用作添饰或炫博的手段,而是提升文献间关联度的自觉的体现。这不同于简单的印证或总结,是一种以义理为核心的逻辑关联,从这一层面来看,姚舜牧的引经解《书》实践是相当成功的。当然,他过于依赖经书文献,而对史部文献少加关注的不足也是毋庸讳言的。
姚舜牧在书前的《自叙尚书疑问》中曾明言:
唯举业制科一遵传注,载在令甲,请诸士子无视余言耳。盖余疑、余问窃与世知问者共疑之,与世知疑者共问之,而必求其见终归无疑、无问,与天下万世共知、共由耳。然此可传之学究哉,藏之名山可也。(《重订书经疑问·自叙尚书疑问》)
在姚氏看来,自己的著作不是专为举业服务的,也因此告诫士子如欲应试无须看此书。他作《书经疑问》的目的在于发问,即使不能解疑,也可以留下有价值的问题供学者思考。此处可以看出姚舜牧有意将自己的著作与《五经大全》一系的举业书划清界限,从书中为数不少的与以《书集传》为代表的宋儒观点立异也可看出姚舜牧已经有了一定反叛宋学的倾向。事实上在姚氏所处时代,对以朱子为代表的宋学的质疑和对汉唐注疏再度重视的现象已经出现,但是在普通知识分子阶层中,宋学还未完全垮台,尤其在晚明政治逐渐凋敝的氛围中,对意识形态的稳定性需求很高,官方所认可的依然是三部《大全》,在这种条件下,姚氏敢于在书中发问,质疑《书传大全》中的不合理之处,无疑是极具意义的。
林庆彰曾将明清之际的部分经学研究成果视为一种“回归原典”运动,“在回归原典要求下的‘正经’工作,不但廓清了经书中的种种附会,也为各经典的时代定位”“有了这一阶段的工作,文字音义的研究才有可能顺利展开”[4]。他充分肯定明末清初的学者向经典进行回归的实践,并且给予高度评价。事实上在时代稍前的姚舜牧身上就可以看到他对回归经文的高度重视,该文所讨论的引经解《书》即是明证,他重经文、轻传注,尤其重视不同经书间的互证。在《书经疑问》全书中征引经书的数量超过援引宋元儒者经解的数量,且对于所引前说也多有驳斥,因此将姚舜牧视作导向“回归原典”运动的重要一环毫不为过。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清人对姚舜牧的评价不高,《四库总目》甚至将《书经疑问》定性为“穿凿杜撰”“游谈无根”之作[5],今人姚舜牧其人及著作的相关研究还远远不够,尚需对其经典诠释特点等方面做更多的专题性研究。